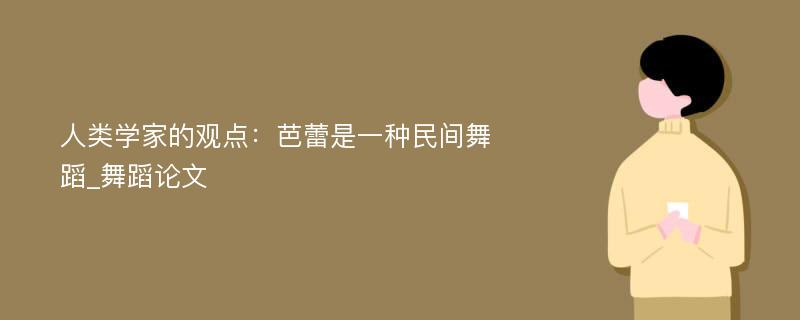
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芭蕾是民族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家论文,芭蕾论文,视角论文,民族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18(2016)03-0114-05 人类学家想通过民族舞蹈(Ethnic Dance)来传达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的舞蹈形式都反映了它们生长于斯的文化传统。从论文中可以看出,舞者和舞蹈学者通常用“民族舞蹈”和“民族学的”、“原始的”、“民间舞蹈”这些词来阐释问题,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非西方舞蹈的认识局限。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了大量学者的论文和新韦伯斯特世界词典。作为人类学者而不是舞者来这样密集地阅读,既受益也烦恼。没有证据、未经证实的推演比比皆是,模棱两可的事实,错透了的观点,普遍存在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最令人失望的是,即便是七十年后重版著作,这些作者瞧着合适也只是更换图片,而不是对正文有所修改,更甚,他们只更新欧美的舞蹈图片。 纵览这些文献,能看出一个惊人的观念分歧。我们会读到“舞蹈起源于演戏”,而它不是为着演戏,那是为着宗教的目的;“舞蹈是为了求爱”,但那不对;“舞蹈是交流的首要形式”,但还没成为“艺术”之前,它还没这功能;更有甚,“舞蹈是唯一团结部落的集体活动”,严格地说它是娱乐和自我表达;“动物比人更早有舞蹈”,但舞蹈是人类活动呀! 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家自认为对起源的问题一无所知,我也不会再弄个舞蹈起源的理论,因为我不认识那时的人。然而,我们的舞蹈作者却把考古发现和当代原始群体当作舞蹈起源的证据和范例。首先,必须得记住:人在画洞穴岩画和做雕塑之前很久,就已行走于这个星球了,所以考古学家的发现说明不了什么舞蹈起源的问题。第二,原始人的舞蹈,我们确实一无所知。而关于当代原始部落的舞蹈,我们知之甚多。在这里,我们要清楚,没有那么个东西叫“原始舞蹈”。原始人所跳的那些舞蹈种类繁多,不可能用任何一种类型来规约。 有个大错特错的认识就是:用一个名称统一称呼某个群体所跳的舞蹈。“非洲舞蹈”根本就不存在,而是Dahomean舞、Masai舞、Hausa舞。“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个虚构,用Iroquois、Kwakiutl、Hopis这些部族名来命名他们的舞蹈才准确。 虽然人类学家都给出了反证,西方舞蹈学者还是自恃权威于原始舞蹈的特点。瑟雷尔(Sorell)总结了所谓原始舞蹈特点的陈词滥调。他告诉我们说:原始舞者没有技巧,没有艺术性,但“他们是其身体永恒的主宰者”;原始舞蹈是混乱而迷狂的,但是他们能把情感转化成动作;原始舞蹈是自发的又是有目的的;既严肃,又善于交际;他们非常自由但男女不能同舞。最后又说男女在纵酒狂欢当中,又舞蹈在一起了;原始人不能区别具象与象征,他们可以在任何场合跳舞,围着卜签跺脚;舞蹈在原始社会是男子的特权,尤其是部落首领、萨满和巫师。柯尔斯坦(Kirstein)说,他们虽然全身投入,但动作的重点是下半身。他得出结论:原始舞蹈是重复、动作有限、无意识、迟缓内敛的,虽然是无意识的,舞蹈对部落是有用的,是植根于季节的。原始舞蹈是人类活动的早期表现,在哪儿都是一样模式的。但是他从没确切说过所谓的模式是什么,除了对方法论来说有丁点用。 特里(Terry)用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例子来描述原始舞蹈的功能。在他的《美国舞蹈》一书中,他同情地把印第安人写作“原始兄弟”。然而,他的家长作风和民族中心感还是让他保留了当代人认同的舞蹈特点,他最后说到“除了最远古时期之外,白人的舞蹈遗产与其是决然不同的。”[1]3-4,195-198特里历数了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国舞蹈的种种特点。但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国的人也许会非常厌恶被那些陈词滥调的术语来命名种族。这种以特点称谓的群体并不是普遍存在。 西方学者标示非西方舞蹈的另一个明显障碍在于,像瑟雷尔一样,赋予“民族的”(Ethnologic)”这个词以“种族之艺术表达”的意义,其“寓教于乐”是个双重迷思:舞蹈始于群体的自发行为,并且一旦形成就固定了[2]14。美国人类学家和许多民俗学者已经为这些流传甚广的误解弄得非常不堪。很显然,它满足了我们民族中心主义的需求,笃信自己舞蹈的独特性,也很轻易地相信原始舞蹈就是那么产生的,并且民族舞蹈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一部分。关于世界舞蹈的书和文章有四分之三的文字和图片在讲西方舞蹈。我们阐述我们的历史时期、皇家赞助人、舞蹈大师、编导和表演者。而世界的其他部分被历史地和同步地压缩在剩下的四分之一。美国黑人舞蹈只在后记中,我们对待西方舞蹈,尤其将芭蕾奉若神明。我们在图片的注释中可以看到,除非这个非西方演员获得成功,否则不会留下姓名。对于爪哇舞蹈的介绍就不见演员的名字,但玛莎·格莱姆一定是要标注的。有的学者只对自己的舞者有兴趣。而非西方舞蹈的就没有上述各方面因素了?显然不是。这使得舞者也对自己的舞蹈抱有偏见。但是,必须提醒我们自己:所有的舞蹈一定都是变化和发展的。 因为我们假定原始或民间群体缺乏创造者,那就来看看马丁怎么说这个问题:“在比我们的文化要简单一些的文化当中,艺术大众(A Mass of Art)确实被人们视为一个整体而实践着。”针对这个:什么是“艺术大众”,马丁从没明确定义过艺术,如果他把艺术定义为精致的审美表达,那这个审美表达又怎么能作为一个集体产物?他是说艺术自发地产生了?那他当真认为会存在没有艺术家的艺术?如果他相信确有艺术家,那他指出的“作为整体的人们”就是艺术家了吗?如果是这样,那群是艺术家的人们多么精彩呀,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无疑,马丁可能会说我已把他的表述搞得离题甚远,但我认为这种毫无思考的表述值得这么逼问一下。 确实是有些文化不像我们的文化,把创造者的名字看得那么重。这也是个传统问题。但我们不能被蒙蔽地相信:几百人在一起,群情一致地创造一个舞蹈传统,打开始就从未发生变化。 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印第安原住民霍皮(Hopi)人就没有给编导留名的习惯。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清楚知道在一个小群体里,做了什么创新,并且为什么做。为了说明这个,我在1965年到1968年间的冬天,观察了五个霍皮村落的“大豆舞”,这个重要的舞蹈每年二月举行。一旦熟悉了一个村落的风格,村落间的风格差异就显而易见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创造性和没必要预见的差异,发生在这一刻到下一刻的过程中。霍皮人非常清楚知道可预见的差异,他们也知道由谁在什么环境下引领阶段性的创新。他们不仅知道这些,他们对那些差异的优缺点的评价也是自由的,而且他们“自己”经常出现,得到更多审美上的满足。 在马丁(Martin)的《舞蹈概论》里,第一个图版有霍皮人卡其那神灵的两个绘图复制品。从图版的位置可以判断,这一定是马丁引用的唯一一例原始舞蹈。德米勒(DeMille)也用了霍皮人作为例子[3]33,35。让我们比较一下霍皮人舞蹈特点和被归纳的那些原始舞者属性。 霍皮人的舞蹈组织地无可挑剔,既没有迷狂(即便是在他们著名的蛇舞中),也没有把情感转化成动作的热望。认为霍皮人的舞蹈有“彻底的自由”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观念,因为舞蹈的形式和行为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当然从不会失之放荡,也不会等雨下了以后“蜷缩在地上滚泥巴”[3]33,35。 如果你说他们没法区别具象的和抽象的东西,那霍皮人肯定会反对。他们毕竟不是孩子。他们当然懂得自然因果。但通过定义,如果他们跳舞祈雨要玉米快长就是说明他们原始吗?大部分美洲和欧洲的农民不也是遇到同样的事去祈祷天主、耶稣的?霍皮人为祈祷而舞,而不是像我们参加宗教团契做一系列的起立双手合十的动作,难道就少些逻辑? 把霍皮人放在原始舞者各种假设的特点下反复评估,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出生、婚礼、葬礼的时候是不跳舞的,而我们却认为这三个重要时刻总是要跳舞的。 很显然,不能说他们在“每一个”场合都舞蹈。如果瑟雷尔(Sorell)期望霍皮人“让地球在脚下颤动”[2]15的话,霍皮人的跺地肯定要让他失望了。德米勒也会奇怪霍皮人的舞蹈并没有“兴奋的状态”或者“迷狂”[3]34,67。 有一点倒是真的,霍皮人的舞蹈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跳的,但女人也跳舞,是在特定环境中唯女性专有的仪式上跳舞。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女人都参与,如果有人(一定)认为她们不是作为舞者参与其中的,那是因为对霍皮人来说重要的是整个舞蹈“活动”而不是有节律的动作。 对霍皮人而言,说主要的舞者是祭师、巫师和萨满是没有意义的。传统上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政府”,每一个氏族都有其仪式和分住各村落的小社群。因此每个人都会一定程度地成为各种角色。没有萨满,当然也就不会是萨满舞蹈。就巫师而言,他们尽管是要完成他们在氏族里的职责,但并不跳舞。 我不知道“自然的、无忧无虑的社会”意味着什么,但无论是什么我肯定这种描述不适用于霍皮人。他们整个整体都不参与舞蹈动作,没有胯部的动作。舞蹈确实是重复的,但那与表演的戏剧影响毫不相干。在舞蹈文化的“限制”中,霍皮舞蹈仍然有大量的变化,因为舞蹈“活动”如此丰富。 为了避免有人说霍皮人是个例外,说也许他们不是真正“原始的”,那让我指出两点。第一,如果他们不是“原始的”,那他们就不适合分类到任何一种这篇文章里舞蹈学者们所讨论的舞蹈种类。他们的舞蹈既不是所描述的“民间舞蹈”,也不是“民族舞蹈”,或者“艺术舞蹈”,或者“剧场舞蹈”这些写作中经过深思熟虑的词儿。很清楚,在学者的笔下,他们是“原始的”、“民族的”群体在跳舞。第二,我知道没有什么群体能符合德米勒(DeMiller)、瑟雷尔(Sorell)、特里(Terry)、马丁(Martin)关于原始舞蹈的描述。当然我也知道没法判断哈斯克尔(Haskell)所说的“许多仍然存活的原始部落舞蹈据说是与鸟和猿的舞蹈是一致的。”[4]很遗憾,哈斯克尔没有资料引证,我们也不能循迹看看这个错误信息。 有必要硬性灌输一下这个观念:没有“原始舞蹈”这么个形式。那些教授“原始舞蹈”课程的人正在渗透一种危险的神话。推论可知,没有什么活着的原始部落会解释我们欧洲祖先的行为。每一个部落都有其特有的历史,并且会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的影响制约。实际上,当代原始人不是儿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按照进化的尺度行事。 我认为,造成对原始群体相关议题有如此多错谬和惊人曲解的原因,是对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和库尔特·萨克斯(Kurt Sachs)说辞的过度依赖,他们著作里的那些材料都过时三十多年了[5]①。 在跨文化意义上,舞蹈这个词从来没有一个可以穿越地域和历史的充分定义。 我曾经认为:“舞蹈是一种瞬间表达的模式,由空间里的人类身体活动在既定形式和风格中表演完成。舞蹈发生于有目地选择和控制律动,而认定这一现象为舞蹈则要具有表演者和观众群体。”[6] 对于舞蹈的定义,韦伯斯特世界词典在第二版和第三版有着明显的差别,原因不言而喻。第二版的舞蹈条目是西方舞蹈的编导多丽丝、韩芙丽(Doris Humphrey)写的,她就把舞蹈界定在表演者——编导的范畴内,而第三版的条目则是舞蹈人类学家格特鲁德·库拉斯(Gertrude Kurath)写的。 马丁(Martin)在描述舞蹈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没有普遍模式时,谈到舞蹈审美的相对性,还是有洞见的[7]12。他进而表示:“不可能说有什么舞蹈方式是唯一正确或错误的,这个比那个差或好……因而它们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都是在特定环境的产物。”[7]17 文化相对主义可以使我们看待问题不绝对。观察分析文化和人类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是有必要的,各种舞蹈文化的差异源自环境。但说什么“种族”、“种族记忆”、“天生的”、差异是“血液中流淌的”,这多少让人回到19世纪末的文化观念。由于基因决定的体质差异和后天文化模式的不同,舞蹈的风格和审美当然有跨文化的差异。 有两个词应该讨论一下:“原始舞蹈”和“民间舞蹈”。英美的民俗学家很关注对“民间”的定义,以便知道“民间舞蹈”是什么。而另一反面,这些学者又常常把“民间舞蹈”当作包罗万象的概念。我以下的讨论并非是为继续谈论萨克斯关于“民间”或“乡村”是“原始”和“文明”之间的进化阶段,我是想更多地从人类学的复杂差异来探讨问题,以反思我之前对于舞蹈的定义。人类学家拉德菲尔德(Redfield)曾在其书《乡民社会和文化》中讨论过[8]。简单地说,原始社会是一个有其风俗和制度的自治独立系统。它也许孤立,也许或多或少地与其他系统有联系。它经济上独立,人们一般都是不懂文字的(注意:不懂文字“Nonliterate”这个词是指这个群体从未有过自己发明的文字语言,它与文盲“Illiterate”这个词大相径庭,后者指有自己的书写系统,但人们未受教育所以不能读写)。相比之下,乡民或民间社会不是自治的,这样一个小社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与大社会共生的,并不断与之互动。一般来说,在乡民社会里多少会有些人是文盲。如果有人把“舞蹈”这个词加到如上所述的原始或民间(乡民),那可能会和所谓的“原始舞蹈”和“民间舞蹈”意思一致。 另一个麻烦的词就是“民族舞蹈”。从人类学一般可以接受的观点来看,民族是指一个群体拥有共同的基因、语言和文化上的关联,尤其强调其文化传统。因此,每一种舞蹈都是一种民族舞蹈形式。既不存在一种普遍的舞蹈形式,也没有什么世界样式的舞蹈,是否有这么种理论上存在的舞蹈都是值得怀疑的[1]187。 然而,芭蕾作为西方世界的产物,它是高加索人发展的舞蹈形式,这些人讲印欧语,拥有共同的欧洲传统。得承认,芭蕾是国际性的,同时芭蕾又属于欧洲国家和有着欧洲血统的美国,但当芭蕾出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时,就说它是借鉴的或外来的舞蹈形式。另外,芭蕾有一个复杂的对他文化的影响流传史,这就不能有效地说明它是民族舞蹈。 马丁就曾说过:“西方伟大的舞蹈形式当然是芭蕾,……恰当地说,芭蕾这个词是指剧场舞蹈的特有形式,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其一套传统、技术和审美基础。”[9]他可能没想到他的话会被拿来当论据。 芭蕾的民族性 我曾列过芭蕾主题和表演的诸多特点,这个清单反复证明了芭蕾具有“民族性”。极具西方式的传统,比如:前台装置、持续两个小时的三段式表演、明星制、幕布开阖之间的返场喝彩、芭蕾里的法文术语。看看那些约定俗成于舞台的格调,比如骑士年代、宫廷、婚礼、葬礼、洗礼、哀悼等等,都文化性地揭示了这一点。想想我们的世界观是如何被揭示的吧:一再上演不求回报的爱、巫术、以长久受难来自我牺牲、错乱的身份、对悲剧后果的误解。想想我们的宗教遗产是怎么展现的:华尔普吉斯之夜②,使用圣经主题,圣诞节这样的基督教节日,笃信死后的生活。我们的文化也体现在那些反复出现在芭蕾的角色:变成动物的人、仙女、巫婆、侏儒、邪灵、恶棍、黑衣淫女、恶毒的继父母、贵族和农民,尤其还有那些纯洁少女和她们的伴侣。 我们的舞蹈价值体现于身体托举与伸展中的长线条,完全展示女性的腿部、小脑袋、细足尖,两性的修长身躯,还有在托举女性时梦寐以求的轻灵如气的质感。这些都获得了审美上极大的愉悦感,但是在有些社会里观众却会惊骇于演出中男性触碰女性的大腿。因而差别就在于芭蕾的“看”,如果把它看成图式剪影大概永远不会有错。 同时,芭蕾的民族性还体现于对动植物有规律的表现。马和天鹅是受到推崇的动物,相比之下我们没有推崇猪、鲨鱼、鹰、水牛和鳄鱼的传统,即便这些动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舞蹈主题中是受到尊重的。在芭蕾中,谷物、玫瑰和郁金香是恰当的植物,但我们不会找到诸如芋头、山药、椰子、橡木或者南瓜花这类东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芭蕾是否反映了它自己的传统,而是为什么我们似乎相信芭蕾不那么具有风俗习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芭蕾叫民族舞呢? 答案是西方学者不能客观地看待“民族的”(Ethnic)这个概念,把它当作“野蛮人”、“异教徒”的委婉代名词,更有甚是“异国情调的”。当这个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广泛应用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提到所谓“高级”文化(如印度和日本)的舞蹈形式的时候,“民族学的”(Ethnologic)在一些舞蹈学者那里有了现在的意义。 民族舞蹈应该是指拥有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特定群体所跳的舞蹈。在集合和对比的方式中,这个术语才最为有效。 很显然,全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希腊人管“他们”叫“野蛮人”,罗马人称“他们”为“异教徒”,夏威夷人称“他们”为Kanaka'e,印第安原住民霍皮人称“他们”为Bahana③。所有的那些叫法都不仅仅是“外国的”,也是指粗俗的、无知的、少些人性的生物。人性的准绳是“我们”。“我们”总是好的、文明的、出众的。总之“我们”才是唯一衬得上人类的生物。这个现象说明每种语言的说话人所持的世界观,这个现象很有戏剧性。 我们害怕把芭蕾叫做“民族舞”,是因为“民族”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他者意味。当我们谈论民族舞蹈样式的时候应该提到芭蕾,不该觉得有嘲弄的意思,因为芭蕾反映了其发展土壤中的文化习俗。 原文参见KEALIINOHOMOKU.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Ballet as A Form of Ethnic Dance[J].Impulse,1969-1970:24-33。 ①作者写作时间是1970年,可见当时20世纪30、40年代的人类学观念仍然流行。而这种观念在当今中国舞蹈研究中则是潜在的、仍然没被反思的。——译者注。 ②Walpurgisnatcht,原文使用了德文,指4月30日之夜,民间传说这一天夜里女巫要在德国布罗肯山聚会,进行狂欢酒宴。——译者注。 ③夏威夷语Kanaka'e和霍皮语Bahana都未有对应的中文术语。——译者注。 ④此书英文版由郭明达翻译成中文,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出版,2015年再版。 ⑤此书1965年的版本由欧建平翻译成中文,名为《生命的律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2005年再版,更名为《舞蹈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