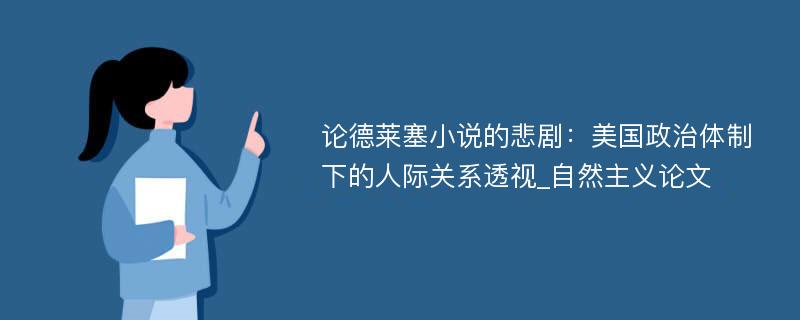
论德莱塞小说的悲剧性——透视美国政治制度下的人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塞论文,悲剧性论文,美国论文,人际关系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5-0079-08
文学评论界对德莱塞小说创作的曲折评论纷纷扬扬,说长道短,已近一个世纪。但最 终都得承认一个现实:作为小说家,德莱塞是开一代新风的伟大作家;其成功的秘诀在 于他善于在小说中创造出一幅幅悲剧画面,以其文学创作的悲剧美赢得了读者,为美国 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悲剧作为戏剧的一种形式,是将社会生活中的悲剧现象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观众 的面前,而德莱塞的小说创作,则是借鉴这种戏剧形式,把社会生活中的悲剧现象写进 书中,以悲剧的冲突来表现其小说主人公的苦难、死亡或衰落,以此表现出他对美国现 实社会的理想和美学评价。所以,德莱塞小说中的悲剧并非是狭义上的戏剧形式,而是 指现实社会中具有正素质的、肯定性的社会力量或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斗争 中的失败、毁灭和灭亡。需要指出的是,德莱塞在其作品中也同时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 作为悲剧主角,虽然这与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人物所下的定义相悖,但在服务于小说家的 社会理想和美学评价方面仍是相互融通的。正素质、肯定性的社会力量或人物方面的悲 剧,用我国文学家鲁迅的话来直述,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任生名 先生则以“人处于极限生存困境的张力”[1](P4)来阐释悲剧的新模式。这种张力是由 个体生命形式显现的人本体和危及人的生存和人本体意义上类的延续的种种因素这两极 所构成的。两极冲突构成的张力因素包括自然、社会、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宗教、 精神心理、人本体等诸方面。德莱塞小说创作中的悲剧张力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然或精神 心理等因素,而是侧重体现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其小说创作的悲剧氛围主要体现了美 国国内阶级矛盾、垄断与反垄断矛盾的激化使小说家对人们生存的社会及其前途的忧虑 和思索。德莱塞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2](P19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德莱塞的小说悲剧是一种社会悲剧。
德莱塞的小说创作生涯起始于本世纪初叶,时值美国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关 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内的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以托拉斯为主要垄断组织形式的少 数大资本家财团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命脉,由此而产生的是一小撮富翁的奢侈生活与广大 下层社会劳动大众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鲜明对照。与此同时,19世纪以来以尼采、达尔文 、斯宾塞、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各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学思潮也如洪水般涌入美国 这块文化阵地,使刚刚步入文坛的德莱塞一开始就冲破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束缚,以现实主义作家的面目出现,伴随着一定成分的自然主义色彩,以其自身经历、所见所闻 、社会调查的结果为基础,展示了世纪之交美国现实社会这个大舞台所上演的一幕幕人 间悲剧,揭示了人的本质、人在社会变革中位置的变更,记录了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和 下层社会平民的痛苦呻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博爱”、“平等”的真实 面目,使我们在痛苦之中享受到这位文学大师为我们所塑造的文学悲剧美。
20世纪初期,美国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为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歌功颂德的“糖浆小 说”,尽管美国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弊端已经出现,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在心理上仍对美 国的前景抱有美好的梦想,用华顿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天真的时代”。这个时期,小 说中的美国人永远是开朗、乐观的,并且充满了歌声和美德,其小说模式常以恶魔被除 以后所表现出欢天喜地的场面来结束。德莱塞则以流行文学反叛者的面目出现,以美国 梦的破灭为主题,在美国文学这块阵地上确立了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
泛性论是德莱塞小说悲剧氛围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这一点,应做辩证的分析。第一 ,应该承认,追求性的解放,实行男女平等,是对禁欲宗教思想的反叛,是人类文明发 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而有其进步的一面。从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禁 欲主义在早期被看成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到后来,人们发现,禁欲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人的一切本能包括性欲都是与人的理性统一着的,是‘合理’ 的人的需求,而西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与中国儒教的‘存天理,灭人欲’是非理性主义 的产物。‘天理’恰恰不是肯定人的正常欲求的‘人理’。当然,反之,仅仅‘人欲横 流’而抑制理性,那么这个‘欲’就很难言‘人’欲了。”[3](P59)马克思在《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 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 度上成了人的行为,……”[4](P119)第二,德莱塞小说中的不同人物在对待性欲的态 度及其表现行为上,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不同类 型的悲剧人物:有些人成了受害者,有些人成了害人者,有些人两者兼而有之。其前期 小说《嘉莉妹妹》的主人公嘉莉和《珍妮姑娘》中的珍妮就是这种悲剧人物中受害者的 典型人物形象。嘉莉向往大都市贵妇的生活方式而来到芝加哥,初次看到大都市的繁荣 和贵妇人的衣着打扮与生活方式,不禁感到相形见绌。在虚荣心和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下 ,她不得不先委身于推销员杜洛埃,而后又投入属于中产阶级地位的酒店经理赫斯渥的 怀抱。与传统悲剧的结局不同,嘉莉后来成为舞台明星,终于圆了她的发迹梦,但最终 她给读者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成功的”悲剧人物形象:她意识到,剧院老板之所以给她 那么多钱,因为她是老板的摇钱树;高级旅馆给她提供豪华的住房,因为她能为旅馆招 揽更多的顾客;新闻记者跟踪采访,无非是借用她的名义来猎奇,以此来扩大其报纸的 发行量;接踵而来的富商绅士,无非是都想占有她的肉体。应该承认,在欲望与理性的 关系上,嘉莉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主义“适者生存”这一特征。在《嘉 莉妹妹》一书中,德莱塞写道:“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在宇宙扫荡、摆布一切的势力之 下,只不过是风中的一棵弱草而已。我们的文明还处于一个中间阶段——我们既不是禽 兽,因为已经并不完全受本能的支配;也不是人,因为也并不完全受理性的支配。…… 人已变得相当聪明,不愿老是听从本能和欲念;可是他还太懦弱,不可能老是战胜它们 。作为野兽,生命力使他受到本能和欲念的支配;作为人,他还没有完全学会让自己去 适应生命力。”[5](P59)嘉莉从哥伦比亚城来到芝加哥,马上就被这个“大地方”的繁 华给吸引住了,也几乎就在同时,嘉莉注意到自己的穿着打扮与城里的阔太太相比而感 到“寒伧”和“缺乏风度”。妒火在她心中燃烧,她发誓要把使她生色的东西——财富 、时髦和安逸弄到手。在美国资本主义上升的这个阶段中,到处都充满着倾轧、欺骗和 陷阱,“公平竞争,只要经过个人奋斗,人人都可富起来”的美国梦只不过是一块掩人 耳目的遮羞布而已,嘉莉这棵“弱草”,在资本主义竞争的狂风中,漂浮不定,奋斗的 结果只能是做了欲念的俘虏,她的发迹也只能是透过微笑所展示的“成功者的失败”这 样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珍妮是继嘉莉之后更为成功的一个悲剧人物。如果说嘉莉身上在 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功利主义成分的话,那么珍妮则完全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在危难 时刻,议员白兰德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了珍妮一家,于是就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珍妮 面前,使珍妮失去了贞操并怀孕在身。这对珍妮来说,无疑是悲剧的开始。因为议员的 年龄与珍妮的父亲相仿,在他们之间是难以有什么爱情可言的。好在议员答应回华盛顿 处理完公事之后就准备同珍妮结婚。似乎这场悲剧有转为喜剧的趋势,但是,德莱塞善 于制造悲剧的冲突,他把议员安排为暴病而死,使这场悲剧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富商 之子雷斯脱最终承认了珍妮的现实,并同意她把女儿接到一起生活的时候,珍妮面前似 乎出现了第二个小阳春。德莱塞此时笔锋一转,在接受遗产和保住珍妮的两者选择面前 ,雷斯脱终于抛弃了珍妮,同富家女基拉特夫人结了婚,使珍妮的悲剧达到了第二个高 峰;珍妮被雷斯脱抛弃后,移居乡下,女儿味丝搭成为她惟一的精神寄托。屋漏偏遭连 阴雨:与她相依为命的味丝搭又染上了伤寒,年仅14岁就离开母亲而去。“珍妮那时仿 佛觉得大地已经沉落了。一切的维系都断了。她一生的无限黑暗里,什么地方都没有光 明了。”[6](P253)万念俱焚,天昏地暗,使珍妮的人生悲剧达到了顶峰。德莱塞在塑 造珍妮这个悲剧人物时,已有嘉莉这个悲剧人物为基础,以此为基础,突出反映了社会 制度与悲剧人物的关系,以高潮迭起的方式,加重了珍妮的悲剧氛围。“悲剧是社会生 活中悲剧现象的艺术反映。剧作家从悲剧冲突中表现主角的苦难或死亡,以显示作者的 社会理想和美学评价。”[7](P9)现实社会中,苦难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但这样的 现实不一定都能构成悲剧。德莱塞把珍妮这个人物主角放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大舞台上加 以考虑,突出体现了她出身于一个自由人的家庭,但由于社会原因所致,她没有选择的 自由,她追求幸福,但又无望,每当幸福即将来临之际,却又随风而去,接踵而来的是 新的、更加深重的苦难。几个高潮过后,悲剧人物留给欣赏者的是痛苦之中的怜悯和恐 惧感。在怜悯和同情珍妮这个悲剧人物的同时,读者不能不去思考这场悲剧产生的社会 和政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莱塞在其小说创作中已突破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 而坚持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揭露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制度给下层劳动人民所带 来的深重苦难。因此,无论哪一位读者,不管他怀有何种心态去欣赏这场悲剧,都不会 因为珍妮先后同两名中上层社会的男性同居而贬低她的品质和道德操行。
德莱塞在其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悲剧人物形象,除珍妮这类纯社会因素造成的阶级压 迫下的悲剧人物形象以外,还有三种受欲念驱使下导致人间悲剧的人物形象,即上面提 到的嘉莉这种在欲念和理性之间摇摆不定而最终成为“成功者”的悲剧人物、克莱德在 欲念支配和社会教唆下导致“美国的悲剧”这种“失败者”的悲剧人物以及渥斯沃这种 纯科学主义受欲念支配而导致自取灭亡的悲剧人物形象。但是,不论是像嘉莉和珍妮这 样的社会牺牲品、像克莱德这样的社会殉葬品,还是像赫斯渥和柯帕乌这样的中上层社 会人物的衰落者,既不论是被害者,还是害人者,都有一个共同点:社会要把他们碾碎 ,把人们所向往的美好前景化为虚无,使他们成为悲剧式的人物形象。
在这后三种悲剧人物中,如果说嘉莉是以成功者的悲剧来展现美国梦的幻灭的话,那 么克莱德则是以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失败者的悲剧来展现这一相同主题的。德莱塞在小 说中借用克莱德这个普通人的犯罪事例来揭示这个社会制度的罪恶。克莱德是一个向往 发财、出人头地,最终不仅未能圆了“美国梦”,反倒搭上了自己性命的一个悲剧人物 。克莱德的最大悲剧在于:社会的教唆使好人变成了坏人。更有甚者,是政治斗争,而 非他的蓄意谋杀,把他最终送上了断头台。也正是由于克莱德是个普通人,他上演了一 出普通人的悲剧,因而才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深刻意义。
在德莱塞的小说创作倾向上,评论界历来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在美国的文学 评论界中,有人狭隘地把自然主义等同于“悲观的决定论”,似乎自然主义和“悲观的 决定论”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术语。与之相关的,是德莱塞的成长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问题。在艾伦·摩尔斯看来,德莱塞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倾向 ,“在德莱塞的小说中,非人格的力量总是要吞噬欲望,也就不能成为克莱恩的虚无和 诺里斯那具有激情的自信。成败仅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而已,而他笔下的人物生活舒 适,甚至道德纯洁,却没有一个人物显示出一种去支撑持久自我的力量。由于大家都是 直接按照连续的冲动和诱惑的反应来行动的,因而谁也不能慎重考虑或进行一番选择。 环境不再控制欲望,而是尽力表现欲望,而最终仅能证实欲望本身永远也不能得到满足 。德莱塞把欲望与城市的环境等同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来予以描叙,使他成为美国 城市生活最伟大的忠实记录者。”[8](P542-543)在德莱塞小说创作的悲剧大氛围中, 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悲剧人物。不可否认,这些人物中,有的做了欲望的俘虏。但有一点 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从嘉莉到珍妮,最后到克莱德,这些悲剧人物的塑造 ,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个社会制度的罪恶现实,反映了在精神毒害和阶级压迫下各 种类型人物的最终悲惨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德莱塞很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人的 内心世界,反映出社会人美好与丑恶的两个方面。赫斯渥在德莱塞的全部小说中是具有 典型性的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中兽性的悲剧人物形象。赫斯渥在纯粹生物学生理欲望的 驱使下,使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幕自取灭亡的人间悲剧。生理本能(本能欲望或弗 氏理论中的力比多)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不论是人类自身的繁衍还是追求性生活的 美满,这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未考虑到人是社会群体中的 单一元素,仅从“力比多”的自我角度出发行事,就必然要受到社会道德的惩罚。赫斯 渥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德莱塞借助赫斯渥这个悲剧人物形象,重点表现了在 兽性的性欲方面所上演的一幕人间悲剧。在人性与兽性,也就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两者之 中,赫斯渥的内心世界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赫斯渥的 自杀是德莱塞用自然主义手法,直接表现了人在理想破灭后的失望甚至绝望情绪。作为 一名现实主义批判作家,德莱塞在赫斯渥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上采用一定程度的自然主 义手法,其用意有两点:其一,真实地揭露了人的心灵中所固有的丑恶的一面,以此来 教育人们要弃恶从善,要多一点责任,少一点私欲,光明磊落地做人,否则就是死路一 条;其二,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肮脏心灵,用赫斯渥之死鞭笞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行 径及其可耻的下场。
“欲望”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柯帕乌是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过程阶段企业界 斗争中受欲望支使,几起几落的悲剧人物。在德莱塞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幅资本 主义竞争中的残酷场面:这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也没有道德观念的上流社会,在这场竞 争中,最强大、最不择手段、最傲横肆虐的人才能取得胜利。柯帕乌正是在这场相互厮 杀、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投机钻营,买通政客,不择手段地跻身于上流社会。金钱上的 成功,使他在色欲场上得意忘形。成功之后,他的野心和胃口更大,似乎这个世界难 以填平他对金钱和性欲要求的沟壑,虽然他一次次地被对手击败,但在欲望的驱使下, 他又一次次地重新启动,但最终还是在这场冒险的角逐中被竞争的旋涡所吞噬掉。柯帕 乌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德莱塞除其意在表现美国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性以外,还在于 他要表现出无论什么样的强者,也难免失败的命运。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颓废、堕落 腐败的悲剧,是英雄悲剧负价值的体现。
悲剧是社会生活中悲剧现象的艺术反映,是作家从悲剧冲突中表现主人公的苦难或死 亡,以显示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评价。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意在揭露社会现实 ,展现下层社会平民的苦难和无助的境地,借以批判社会的不平等,暗示了作家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自然主义方面,德莱塞给读者展示了在欲望驱使下而失去道德观念的人 的天生“恶”的一面,写出了“人”的兽性一面,尽管自然主义强调不偏不倚、不加任 何评论地再现客观现象,但是,德莱塞在其自然主义悲剧结局的意义上却迈出了新的一 步:如果不加以节制,随心所欲,不论成功与否,其结局必然是可悲的。因而我们应该 弃恶扬善,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兽性,以此表达了作家对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
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受流行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潮流的影响, 在以小说创作的方式来表现、审视、评价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时,一开始就从本能和 观察出发,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美。“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和个人感情 ,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悲剧描绘的激情都是最基本的,可以毫无例外的感染一 切人;它所表现的情节一般都是可恐怖的,而人们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变得严肃而 深沉。他们或者对生与死、善与恶、人与命运等等问题作空前深邃的哲理的沉思,或者 在悲剧情节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有相似之处时,……便沉浸在自己的悲哀和痛苦之中 。”[9](P31)不论是在社会舞台上还是在戏剧舞台上,悲剧的这种审美价值及其审美者 的接受心理都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 难是两回事。只能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有些具有悲剧性,有些并不具有悲剧 性。用朱光潜先生悲剧“心理距离说”来解释这一现象,是因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悲 剧人物、情境和情节的不寻常性,艺术程式和技巧,强烈的抒情意味,超自然的气氛, 最后还有非现实而具暗示性的表现技巧,都使悲剧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悲剧 情节通过所有这些“距离化”因素之后,可以说被“过滤”了一遍,从而除去了原来的 粗糙与鄙陋。德莱塞的小说在将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向悲剧转化时,作家注意使两 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使读者在审视珍妮、嘉莉、赫斯渥、柯帕乌和克莱德这些不同 的悲剧人物时能够确实产生和保持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审美标准。珍妮、赫斯渥和克莱德 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但作家的用意却是相同的,即用处于悲剧氛围中的悲 剧人物来打动读者的情感。这三种悲剧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死和痛苦保持着一定的联 系,在他们的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悲剧氛围。然而悲剧的审美效果正是如此:悲剧表现的 场面越可怕,它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情感就会越强烈。其缘由就在于悲剧和可怕是联系在 一起的同一种东西。德莱塞在其小说中创造悲剧氛围时,致力于把这种可怕的场面变成 具有真正悲剧性的场面,使读者在欣赏其笔下的悲剧人物珍妮和克莱德时,绝不会产生 沮丧感,反倒会感到一种鼓舞和振奋。读者在假设自己会处于这种悲剧境地时所产生的 恐惧感使自己同悲剧人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读者痛恨社会的不公,害怕悲剧会落在主 人公的身上,实际上,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读者害怕的是这些悲剧会落在自己的头 上,由于“距离”的因素,读者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幸灾 乐祸的心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都会使读者产生变悲剧为喜剧的自然欲望。德莱塞 在其正面价值的悲剧人物面前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通往喜剧的障碍物,使悲剧氛围愈演愈 烈。读者所感受到的是痛苦中的快感,因为读者是在同情受苦的人。“悲剧鉴赏是一种 审美感情,因而悲剧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珍妮代表道德正面价值的悲剧人物, 能够产生悲剧的崇高,因为这类悲剧人物表现了对亲人的爱、儿女对父母的孝敬、母亲 对儿女的慈爱及责任等具体的、合理的人类感情的形式,因而这类悲剧人物就成为这类 伦理力量的化身。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德莱塞的社会现实批判小说才具有净化人们的心 灵、鼓舞人们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诸如赫斯渥和柯帕乌一类具有 道德负价值的人物由福转为祸,虽不可能达到崇高,但仍可以构成悲剧人物形象。美学 理论界曾有人认为“对于悲剧说来,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亚里士多德理想的 悲剧人物“在道德品质上正义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 于某种过失或弱点。”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难以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因为在阶级社 会中有阶级的对立,在伦理道德上有善恶之分,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看问题的立 场不同,因而对这类伦理道德负价值方面人物的悲剧也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以鲁 迅先生给悲剧所下的定义来分析德莱塞小说中的这些具有负价值的人物,我们仍可以把 他们看成是悲剧人物。因为不论是赫斯渥、柯帕乌,还是雷斯脱,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以 不同的手段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不同于具有道德正价值的悲剧人物 ,他们不是阶级压迫的牺牲品,而是中上层有闲阶级在优裕的物质享受中,在生物学性 欲和物欲达到无法战胜时而自我毁灭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类悲剧人物形象也可以使欣赏 者产生恐惧感,接受心理的“距离说”仍起作用。《嘉莉妹妹》中的赫斯渥,属于亚里 斯多德理想的悲剧人物,即“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并不 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从客观因素上看,赫斯渥的妻子在家庭生活 中表现为一个暴君的形象,使赫斯渥这个为其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赢得了一切的贡献者 则最终被异化为其妻的奴隶地位,他不敢在家庭中争得他本应得到的地位,此时,年轻 貌美的嘉莉又闯入他的生活中,加之酒店保险柜偏巧又未上锁,导致他铤而走险,在“ 犯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主观因素上看,赫斯渥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仅服 从于自然规律,忽视了人还有社会性这一重要方面,即他仅追求了人的本能欲望而忽视 了人的理性。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如本能欲望)两个方面同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 而理性是主导的方面,失去了理性,那么人就会成为纯动物性的人,而人的非理性因素 便会成为兽类的兽性。动物性即以本能或欲望来作为支配力量而没有理性,人类社会中 的人应该既有本能欲望又有理性。在动物性与人的理性之间存在着意志、情感、心态等 过渡地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赫斯渥“所犯的错误”正是没有 处理好理性与非理性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于在家庭中受到妻子的肆虐和儿女的 慢待,在外面又遇到了嘉莉所产生的强烈情感冲击,他在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的过渡地带 中变得意志薄弱,失去了“天真”那一面而完全导致“野兽”那一面,终于使他在走向 死亡之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德莱塞虽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对赫斯渥的悲剧加以评 论,但在由于欲望占支配地位,从而导致了人生悲剧的事实面前,有谁还会不清楚应如 何摆正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呢?文学评论界有人把赫斯渥的悲剧看做是德莱塞用以说明 外界力量是主宰一切的典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持有这种观点,就等于承认人的 非理性一面占统治地位,决定了人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实质上,这种观点是为这那些 本该免入歧途而又步入歧途的人开脱他们所犯“错误”的责任。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在 贬低德莱塞小说创作的进步意义。在“欲望”三部曲中,德莱塞在悲剧人物的塑造上来 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美国资本主义上升和垄断阶段为背景,突出表现了柯帕乌 这样一个在“靠吃别人为生”的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恶战中坚持优胜劣败和适者生存的资 产者的形象,实质上,柯帕乌就是德莱塞笔下典型的负价值的悲剧人物形象。这个悲剧 人物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中的残酷性,表现出德莱塞一贯坚持的“生活是一 出悲剧”的观点。
德莱塞小说中的悲剧氛围既不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翻版 。况且,自然主义并非等同于“悲观的决定论”。如果说德莱塞的某些小说含有自然主 义创作倾向的话,那么也应该把其划归为抵制“个人自由选择”的自然主义作家,因为 其小说中的悲剧主角(除柯帕乌一类具有负价值的悲剧主角外)多数是美国社会的下层人 物,他们出身低微,也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或是受欲望和社会舆论的支使和教 唆,或是迫不得已,随风而去,最终被这个社会打得粉碎。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莱塞的 小说创作倾向应该划归现实主义。其悲剧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的社会悲剧。小说同 戏剧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要折射出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和伦理道 德等诸方面的现实。但是,德莱塞的小说并非是对这些现实的机械描述,而是作家本人 对其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展示。德莱塞是 一位极其负责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符合“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创 作原则,其小说中各种类型的悲剧主角都有其人物原型。德莱塞曾到监狱实地考察,在 此基础上写出的《美国的悲剧》,清楚地表现出美国社会制度、环境、时代对其悲剧人 物走向灭亡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从事记者生涯时,德莱塞就致力于搜集有关工业、金 融巨头的资料,研究他们的发家史,为其日后完成“欲望三部曲”打下了基础。
德莱塞通过其悲剧小说的创作,展示了美国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其悲剧氛围服务 于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方式突破以往美国文学的“高雅传统”、“糖 浆小说”,也摆脱了旧现实主义致力于描写“微笑的美国”俗套,开辟了美国现实主义 文学中社会悲剧的题材领域,强化了其文学创作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奠定了德莱塞的文 学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收稿日期:2003-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