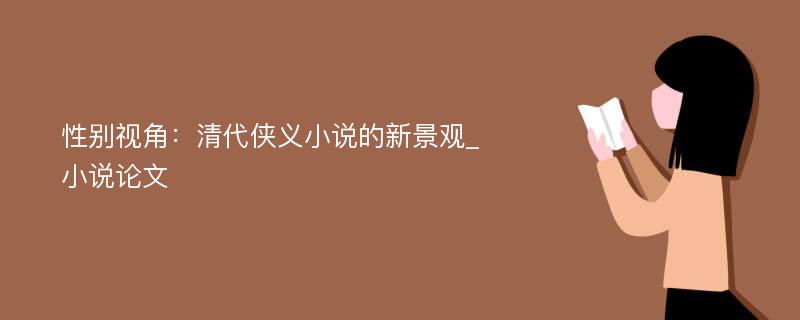
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侠义论文,清代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新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119-06
清代处于古代与近代的过渡与交汇的时代,各类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都带有一些融合乃至集大成的色彩,但具体到某一类题材或人物的源流考辨和具体的研究,则有相当多的空间有待深入。如侠义题材自古有之,在清代小说即特别突出。不但白话小说出现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风靡一时的名作,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是绳绳不绝,在王士祯、蒲松龄以及晚清的王韬等人笔下,都产生过有影响力的侠义形象。本文拟从性别视角、道德观念的演化以及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定性等方面,审视清代小说侠女叙事的演化过程,描述这类文学形象在清代的转向及其原因。
从性别视角检视侠文学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以往的文学景观。侠从秦汉社会的历史存在,到成为一类文学的主题和形象,其内涵和趣味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以小说中的行侠手段而论,有剑侠、武侠、义侠之分,人物身份从神仙、异人到有血性的凡人。男性侠客能随着时代的演进、小说题材主题的变化,而呈露新身份和精神内质,如从唐代的豪侠到白话小说里凭朴刀杆棒抱打不平的英雄、活动在市井中的侠盗,再到为清官奔走的侠客,他们的形象和故事紧随着社会审美而变化,呈现出延展与可塑的弹性。与此相反,侠义小说的中的女性则缺少变化。清代以前,白话小说很少有侠义的女性人物①。飞剑的聂隐娘成为文言小说侠女的标本,飞剑、法术符咒和世外栖托的想象,代替血淋淋的搏杀成为侠女的标志。这类淡化了暴力色彩的侠女以“理性的‘智’与超理性的术”[1],受到士大夫的偏爱,成为文人寄托理想的话语模式。直到清末,一些文人如王韬等还热衷于写那些鼻中吹剑的侠女。文言小说简略、不事描摹的叙事方式强化了这些特点,使侠女形象的意义和影响仅限于同类题材和人物的零星复制和重复。
在文言剑侠小说系列中,以明人所辑《剑侠传》和清末的《续剑侠传》为例,从唐到清的二十余篇侠女故事,除《扶余国主》是写红拂慧眼识人的胆识,其他主人公基本都是怀有异术、身为仙道的剑侠人物。不但历史上“以武犯禁”的游侠和汉代豪侠之中绝无女性身影,小说中那些体魄强健、舍生取义的武侠也很少由女性充当。原因是侠女既已属神仙超人,就没有了牺牲的可能和必要。这些以术称侠的人物,没有涉及精神人格和道德情怀,诚如李贽所言,应该算是英雄中的展品:“夫侠之有术,亦非真英雄者之所愿也。”[2](P194)这些人物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题材范围内,不需“依赖于现实生活的刺激”,仅靠“人物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3](P7)产生。这类寄托着文人理想的符号化人物,在文言小说中相沿不绝,“几乎没有一代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4](P333)。
在文学源属上,文言和白话小说各奉正脉。章回小说的侠女有雅化和俗化两种分向,但她们都接续了宋元白话小说的精神传统,以相对现实的态度涉及了女性性别生存的世相。樊梨花、十三妹一流人物的“人间化”气息来自宋元话本世界。宋元说书人用保守的性别意识、喜剧化的贬抑态度评价剑侠女性。《平妖传》中的胡永儿可视为传递话本精神的一个中间人物。她的基因决定了清代侠女身上的很多共性。这类女性以法术武功做嫁资,以遭受折辱的求婚经历换取主流社会的接纳。“英雄儿女类”小说的侠女融合了下层女性与理想佳人的特点,将人物塑造成治家贤妇。通过婚姻的形式,这些侠女们得以重返家庭伦常的社会秩序之中。
一、性别视角中的侠义人物
清代侠义小说在创作持续时间和数量上都超出了唐宋元明各朝,并在清初和清末形成了两个创作兴盛期,与其时的社会世风发生着互动。统观前后期的小说,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清代文言和白话小说都出现过较有影响的侠义小说。以三部选择标准不同的文言小说侠义小说集为例,可以见出创作的繁荣。清末郑官应编辑的《续剑侠传》收录有清代侠义小说39篇,包括王士禛、蒲松龄、朱翊清、吴陈琬、乐钧、长白浩歌子等写的侠女故事10篇。《续剑侠传》在叙事风格上延续了《剑侠传》所收小说的剑侠神秘模式,人物以神仙化的剑侠为主。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义侠类》收清代侠义故事420篇之多,大多抄录历史人物轶事和闾巷传说而成,写名士和普通人的侠义举动和道德情怀,较少涉及神怪或武力,其中女性的故事寥寥可数。以上三种选本体现了几种不同的“侠”观念,即剑侠、武侠和义侠。女性在其中所占比例,随着虚构性的降低而依次递减,分别为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直到披卷难觅。
另有1909至1911年间成书的《香艳丛书》,收录侠女故事数篇,如《女盗侠传》、《女侠翠云娘传》、《女侠荆儿记》等,其中人物似受《儿女英雄传》影响,都是武功尚未超出常情的普通女性。
总体上说,清人文言小说固守着唐代剑侠女性的叙事模式,主题和人物多囿于剑侠的传统写法,很少涉及人物境遇、情感等具有现实性的内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着剑侠模式民间化的创作倾向。他将民间的子嗣、财富、性道德等问题写进了侠女世界,拓展了女性行侠的主题,如“不爱其躯”的报恩故事(《侠女》)、以色行侠的女子(《霍女》),还有报答知己的女性(《乔女》)等。
晚清侠义小说多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是在叙事风格上,《聊斋志异》式的传奇笔法广受欢迎。在程麟、王韬等人笔下,侠女形象变得脂粉化,小说情节每近于中篇,以缠绵细腻之笔敷演男女之情。“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年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十三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5](P174)这些小说包括《淞隐漫录》中的《女侠》、《姚云纤》、《徐笠云》、《剑仙聂碧云》,宣鼎《夜雨秋灯录》中的《郁线云》、《谷慧儿》,程麟《此中人语》里的《广寒宫扫花女》等。尤可注意者乃小说情节的烦琐曲折,人物的情感生活丰富了故事的主题和层次,突破了剑侠故事短小简略、手法单一的模式。在王韬小说中,仙侠和十里洋场里的风尘女子神态相通,言与粉黛合流者,正于此等处露出端倪。从王韬小说可见,侠女除补偿人生缺憾、寄托出世理想之外,又渐渐回到红颜知己的老路。此亦为侠女回归生理性别与社会角色的一种。
白话小说中称为“侠女”的人物甚多,而内涵却较庞杂,行侠手段包括了剑术、武功到女性的才干等各方面。计其大端约有三类:一是带有民间色彩的妖术化侠女。这些人物可能来自宋元话本把“西山聂隐娘”等剑侠女子归为“妖术类”②的影响。《征西说唐三传》中的樊梨花、《第一侠义奇女传》(又名《宋太祖三下南唐》)中的刘金锭,都可归入这类人物。这些具有仙道背景的女性也还是具七情六欲的凡人之身。樊梨花和刘金锭都是从世外仙人那里学成移山倒海、撒豆成兵的仙术。她们奉师命下山为朝廷效力,并成就个人姻缘。这些人物身上尚带有早期话本里民间小女子那些乖张的举止或令常人嫌憎恐惧的妖异色彩。二是佳人化的女性,多出于文人创作,较为出色者如元翠绡、十三妹等。《续侠义传》是《三侠五义》的续书之一,在众多男侠之外,出现了聂隐娘弟子元翠绡。这位剑侠女性扮演着拯救侠客的角色,虽性格飘然不群,但她和白展堂的情爱纠葛成了贯串小说的线索,最终“奇男侠女奉旨完婚”。文康《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是个有着家传武功的凡人,在众人帮助下嫁夫生子、安身立命。三是世情小说中的侠义女性,如“三言”中的“侠妓”、慧眼识人的女子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侠女。这些女性以其对性别角色的出色担当而被称为侠义,因在清代小说中成就并不突出,故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白话小说中的侠女,有着具体的出身和处境,也有着生存发展的个人欲求,因而被赋予更多的女性气质和具体的身份特征。她们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和顺服程度,要高于文言小说中的剑侠。
总体上看,侠女形象在白话和文言小说中有一种共同的演化趋势,即性别内涵的丰富和女性性别角色的回归。这种演变和小说中男性侠客竞相向统治者俯首称臣的趋势相为表里。
二、文言小说与女性的性别回归
文言小说中侠女性别意识的回归,指向的是女性的生理性别。清代文言小说对虚构剑侠女性的偏爱,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唯故事主旨由崇侠而趋于尚情,对侠女的态度渐近于狎昵。其原因在于叙事风格的改变。《聊斋志异》之后的侠女小说,由简短的笔记志怪趋于婉转铺衍的传奇,侠女的剑术、柔情和身体构成了新的性别文本。在《耳食录》、《萤窗异草》和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受《聊斋志异》风格影响的篇目中,其演进之迹最为清晰。
清初侠女小说沿袭唐宋剑侠模式,用旁观者的限制视角,片段化叙事时间等手法保持人物的神秘性。小说往往篇幅短小简略,尚带有轶事小说或志怪小说的余韵,同“叙述宛转,文辞华艳”[5](P51)的传奇体迥然有别。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多径直取材于前人旧篇,缺乏新鲜元素的引进。如曾衍东《小豆棚》中的《齐无咎》写齐无咎见一美妇求为妻而不允,求为妾乃可,后侠女报仇毕,杀子径去。这个情节显然来自《原化记》中的《崔慎思》,而侠女买驴磨面治生养家的情节又迻自洪迈的《侠妇人》。金捧阊的《女侠传》写一女子头上簪子化为飞剑斩杀逆子,“腰间取青囊覆人头,头化为水”,行止类似聂隐娘。朱翊清《空空儿》中侠女将失物放到高塔上的情节,与《剧谈录》中三鬟女子若飞鸟般登上慈恩寺塔取下宝珠如出一辙。其他尚有管世灏《影谈》里的《绳技侠女》、汤用中《翼駉稗编》的《隐娘尚在》多篇,人物行迹俱不能出唐人小说藩篱。
清人在人物叙事手法上也非全无创新。王士禛的《剑侠传》用两个人物的旁观视角,倒叙讲述两个时段的侠女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小说讲康熙二十七年有人目睹一高髻妇人,腰剑骑黑马驰于章丘道上。另一叙述者莱阳生言顺治初年,此女子身为尼姑,曾为人手刃强盗追回财物事。时隔四十年,这位侠女尚如“三十余岁”,同一人否?是耶?非耶?两个叙述者的安排本身就增加了悬念。小说到结尾处依然保持着侠女身份的神秘:“人不知何许人”。
从性别视角看,文人笔记对剑侠女性持续的创作兴趣,出自文人自卑心理与优越感交集的微妙心态。从社会身份上讲,每个人面对社会固然都渺小无力,而女子受到的性别规训和生理局限远大于男性。当文人们向壁虚构,在想象中“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时,由自由的仙侠与性别等级中的弱者结合而成的侠女,使创作者“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较幸运的人们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6](P12-13)的心理,更易得到满足。从唐代到清末,社会的性别规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审美习惯促成了文人笔下如出一辙的侠女模式。宗教的世外空间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女性提供了归宿和庇护;道教的符咒、法术、法物、道法想象弥补了女性体魄的柔弱。神仙化的身份设定摒除了女性生理、心理乃至社会性别的特征,其实质是对女性意志和体魄的怀疑:“以女子柔弱之质,而能持刃以决凶人之首,非以有神术所资,恶能是哉!”[7](P2617)最早的剑侠人物就是随女性的出现而出现的。东汉末年的《吴越春秋》,写了一位剑术出神入化的越女,这是对侠女武艺虚幻化叙事的开始,而其时对男性侠者的描写,如《燕丹子》中的荆轲,则是以侠义的精神气魄而非剑术著名。无形灭影、怪诞奇诡的剑术配合着神秘化的叙事方式,成为凝固的文学符号,限制了侠女故事在题材等级上的发展。
《聊斋志异》的问世打破了剑侠人物萎弱僵化的发展趋势。蒲松龄对侠女形象的贡献主要在主题和叙事手法上。他第一次把“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坐实到了侠女的生理性别上,女性身体、才干乃至性魅力都成为行侠的手段,从而把新气息带进了这类枯淡的形象类型中。《霍女》写了一位放浪挥霍、专以姿色魅惑男子的出奔女子,她用美色让不义男子败家散财,而对穷书生黄某却能躬操家苦,亲爱甚笃,并为之娶妻延嗣。小说对霍女行止及其家人的描写,隐隐揭示了她亦仙亦侠的身份,“异史氏”认为霍女:“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女非无心者也。”[8](P1097)这位女性惩恶扬善用的是色相而非剑术。
《侠女》故事的基本元素,同唐人小说的《崔慎思》、《贾人妻》看似别无二致,其内涵却殊异其趣。唐人故事的重点在报仇,结婚产子是侠女为托身立足而寻找的掩护,为了断绝情念,她们还亲手杀死了婴儿。《聊斋志异》故事的关键却是侠女以性行侠,用身体报恩,体现的是民间社会重子嗣的性道德观。由此,在传统的题材和人物中融入了民间生活的新鲜和亲切感。
清代文言小说里“摹仿赞颂”《聊斋志异》者,如乐钧《耳食录》、曾衍东《小豆棚》、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宣鼎《夜雨秋灯录》、邹韬《浇愁集》以及王韬《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所写侠女篇目大多叙事婉转,善于刻画情态,人物在剑术、神秘性等符号之外,渐渐焕发女性气韵。乐钧《耳食录》的《何生》写“雄服游戏人间”的侠女为何生杀掉仇人并赠飞剑。故事的主旨是何生与两剑仙的奇遇。冷然无情的侠女“不图为君缠绵至此”,自甘投进情网。曾衍东《小豆棚》略晚于《耳食录》,集中两篇侠义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浣衣妇》写贪渎的抚军欲加害总藩,总藩家中的洗衣妇愿为主释厄,往见抚军。“抚见之心荡,妇承以目,抚乐甚,留不返”,抚军私会浣衣妇时,女乃以剑术惩治之。与红线故事不同的是,曾衍东笔下侠女的厨艺和美色也成为行侠的辅助手段。再如《萤窗异草》的《姜千里》,这篇模仿《婴宁》的小说,蕴涵了一重新鲜的主题,即处于伦常秩序之外的侠女,通过婚姻回到了父子伦常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了她在性别秩序中的位置。
清末随尚侠之风又兴起了一股侠义小说热。出现了邹韬《侠女登仙》、程麟《广寒宫扫花女》和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中的一批篇目。以王韬的侠女小说影响较大。王韬本人多狎妓冶游之作,笔下侠女也浸染了若干风致。侠女的性别特质受到关注,小说用缠绵笔意,描摹侠女的容貌、仪态乃至内心情感。细腻婉曲的情节和内心观照使人物冷峻的面貌变得柔和温婉,乃至侠女形象渐趋于烟粉化。篇幅曼长、摹画绮丽,虽名为剑侠实同于书生艳遇。所谓“侠之所在,即情之所钟也”(《广寒宫扫花女》)。因男女之情的泛滥,剑侠女性所处的世外空间也带上了狭邪小说的色彩。
三、回归家庭角色的女性
白话小说中的侠女故事以回归家庭为人生价值的旨归。对雅俗两类侠女而言,接受家庭角色或许有着不同的意味,而无论是作为物质的保障还是个人道德的完善,婚姻都是她们回归正统社会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唯一途径。
(一)带有妖异色彩的下层侠女
从源属上讲,“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女性更接近宋人话本的人物精神。如鲁迅所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年而再兴者也。”[5](P229)目前所见的宋元话本侠义人物,可分为两类:一为宋四公、赵正(《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尹宗(《山亭儿》)等市井人物;一为归入“妖术类”的唐代剑侠,如聂隐娘、红线等。以性别而论,接“侠义”之正脉者应是《平妖传》中的胡永儿一流人物③。盖因与胡永儿相关的《平妖传》中人物,如王则、圣姑姑(或即“千圣姑”)都和“西山聂隐娘”、“红线盗印”一同出现在“妖术类”的话本中;同时,胡永儿身世又和聂隐娘颇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由老妇人传授法术,又都是冒犯家长的女孩儿。胡永儿对下层化侠女的影响有两方面。
首先是妖寒的出身为“英雄传奇类”小说的女性所继承,身份又决定了她们攀附正统的婚姻追求。胡永儿一家穷处在不厮求院,得圣姑姑授“九天玄女法”,才家致小康。她的父亲对其妖法极度恐惧厌恶,想杀掉女儿不成,就把她嫁给了痴傻丈夫。清代小说中的樊梨花、刘金锭都是圣母仙姑传授法术,都有撒豆成兵、攻城斗阵的本领。同胡永儿一样,她们也不见容于家中父兄,樊梨花更弑父杀兄。从出身上讲,樊梨花是西番哈迷国的女子,刘金锭是北汉官员的女儿,相对煌煌天朝的世家勋贵之子,她们自然是邪门歪道、受人歧视的妖女。这些泼悍难驯的女性散发着草莽气息,可视为剑侠女性的下层化。以性别视角看,这些侠女具有双重的化外身份:低贱的出身和妖异的色彩,既是主流社会的异端又游离于性别规范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女性求偶的挫折经历,就是她们回归主流社会和传统性别角色过程的隐喻。她们对天朝勋贵之子有着热切的攀附欲望。樊梨花和刘金锭都是不避羞辱,主动向朝廷勋贵子弟求婚,被拒绝后又利用仙法幻术几次逼婚,遭到男方的无情刁难和嫌憎。这样的女性并非个别,而是形成了一种人物类型,如《说唐后传》、《罗通扫北》中爱上罗通的屠炉公主,《五虎平南后传》中擒狄龙的段红玉,《说唐三传》中的窦仙童,都是带有妖寒色彩和类似经历的女性。在这些类型化的人物和俚俗荒唐的情节背后,似乎另有性别政治的隐衷。
其次,《平妖传》对胡永儿法术的工具性定位,在“英雄传奇类”小说中发展出侠女助夫的主题。这一主题固然是对女性才能的限定和轻视,但侠女也因此而具有了被正统社会接纳的可能。清代侠女们的因人成事,正是社会性别制度的现实写照。女性要在公共空间中发挥影响,只能以男性为媒介,她需以某姓之女、某人之妻的身份获得社会接纳。侠女助夫主题,一方面消弭了妖术女性的异端性;另一方面,法术武功也成为女性改变命运的工具。当番邦异国的女性钦羡天朝将领,志愿辅佐丈夫报效朝廷时,让人畏惧的法术、令人嫌弃的妖女,就有了正面的价值。刘金锭的父亲劝她“趁今太祖受困之时,往彼效力,立下功劳,可化仇为好,完此姻盟”[9](P626)。《说唐三传》里,薛仁贵和程咬金之所以逼迫薛丁山与樊梨花和好,是因樊梨花的武艺和法术能助唐军取胜。靠着挟仙术而斗妖魔的才术,女性从妖寒的出身,进入到梦寐以求的上层社会,获得显赫地位:“身入王家显贵,真乃福禄齐眉。”
(二)佳人式侠女
这类人物多出下层文士之手④,虽未属意于诗文酬唱,但亦以写情为线索,终于婚姻的美满。谭正璧先生以“才子必兼文武之才,或佳人亦娴武艺,如《好逑传》”[10](P177)为标准,列出“英雄儿女类”小说。概括来说,这类佳人式的侠女多出身清贵,受过良好的教育,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和男女大防的性别规范已是深植于性情之中。她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不是积极进取,而是羞涩避让、反复推拒。在她们看来,行侠仗义与结为婚姻之间,存在着公义与私利的矛盾,接受婚姻的安排会破坏侠的道德。小说的主题则在宣扬侠义与儒教伦常观念的统一,女性只有承担世俗的伦常义务,担当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才能获得道德完善和人生的圆满。
佳人式侠女可以视为“中国男人如何通过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先将女性理想化,又将其驯化、压抑的极佳例证”[11](P177)。能仁寺里勇杀恶僧,有着超人体魄的十三妹,立志要将英雄侠义的手段用在安家:“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妇,要不给公婆节省几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怎报得这天恩,副得这人望?”接受婚姻生活和家庭角色的侠女,就意味着对儒家道德训条的彻悟与皈依。和所有礼教中人一样,侠女应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获得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在这类侠女身上,“侠”的异端性和违反性别规范的本质已经尽数洗去,完全转化为可接受的、有利伦常秩序的力量。
要之,白话小说以女性追求婚姻、回归家庭为经线,叙述她们的侠义故事,通过人物的身体和角色的限定性来展示女性的人生世相,因而具有一定的表现深度和隐喻性。这些番邦女子或名门之后,通过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或得到了进入正统社会和世族门第的入场券,凤冠霞帔,得偿所愿;或在婚姻中寻找到了人生意义和精神的归属。她们的法术武功和个人才干之所以为正统社会所青睐,正是明清社会妇德观念转化的结果。
四、侠义人物与小说中的妇德观念
明清社会经济和道德风俗的变化是侠女叙事演化的内在原因。小说用不断更新的女性形象,建构和表达着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其要点有三:
一是对女性经济才能的要求。女工本是四德之一,而在明清人口繁密,经济生活普遍贫困化的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才能受到格外的推重。现实的家庭经济中,女性的重要性超过了男子。“女性角色几乎填补了所有男性角色没有覆盖的领域。”[12](P279)女性不得不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夫难养妇力自任,生涯十指凭一针。”[13](P715)文康所在的旗下,多是妇女操持家务、支撑门户。女子以精明能干,泼辣厉害为“好样的”[14]。传统的闺训已经过时,有御穷安家的才智才算有妇德。冯梦龙声言“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15](P1511)没落的安家,非何玉凤这样具有出众才能的女性不能拯救。
二是对治家才干的期许。女性佐夫成名、治家御下的故事是世情小说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三言”常将“有智妇人,胜如男子”作为主题,揄扬女性的治家才干,临事机谋;李渔劝导贫士之妻就该受些辛苦,替男子挣家业做人家[16](P426)。蒲松龄所写的佳人,在才貌要求之外,还需具有持家的本领,如黄英、细侯等。对陈云栖那样的传统佳人则颇有微问。陈云栖虽有旷世无俦的美貌,且为人孝谨、善琴棋,但作者却不免略寄褒贬:“画中人不能作家,亦复何为?”
三是表现女性的社会性才能,如临事机谋、破阵立功,等等。才子佳人小说的主旨多“显扬女子,颂其异能”[5](P153),在颂扬佳人“以冰雪为肌肤,以诗词为心”[17](P63)的才情美貌的同时,女子之才往往超出了闺中静女文翰辞华的界线。佳人的胆识、智慧在满足个人婚姻欲求的挣扎中被激发出来。《好逑传》中的水冰心的机智干练、泼辣有识,“既美且才,美而义侠”;《玉娇梨》中白红玉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才干。这些都被佳人型的侠女如元翠绡、十三妹所继承。在英雄传奇小说中,女将助夫破阵立功成为流行的模式。如《说唐三传》中的薛丁山所娶的三位妻子,都是阵前逼婚,倒戈助夫的。这些情节的一再重演,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性别期待。男性占据了成功的机会和公共的空间,但也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和失败的焦虑,对女性的依附角色也暗生嫉妒:“闺中人身不到场屋,便以功名富贵似汝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于顶,恐亦犹人耳!”[8](P767)这是失意书生对妻子抱怨的回敬。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书生们期望得到外力的帮助,在创作中会“杜撰出一些代表‘外力’的佳人”[18](P139)满足攀附的欲望。如讥诮丈夫的颜氏,改易男装,外出应考,中举为官达十年之久,后让丈夫“承其衔”,自己“仍闭门雌伏”。
这些理想女性的光环背后是男性过奢的要求和矛盾的心态。现实中的女性卑服于性别规范之中时日已久,平庸柔脆。“有才有德有智有貌,样样都可胜过须眉”的女子,只能从幻想的侠义女性中去寻找了。
综上所论,在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中,清代侠女形象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都终于自甘雌伏,回归到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之中。这些侠女的意义就在于用人物对性别角色的追求与回归,重申了性别规范的价值和意义。女性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设定,进入父子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收稿日期:2009-08-16
注释:
①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系从嘉靖间人胡汝嘉的文言小说《韦十一娘传》改编。
②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举宋代话本“妖术之事端”,有《西山聂隐娘》、《红线盗印》和《贝州王则》等,将唐代侠女和千圣姑、胡永儿一并视为妖人异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韩南在《〈平妖传〉著作问题之研究》中提出《平妖传》的胡永儿可能受《聂隐娘》的影响,两人都由老乞妇传授法术,又同为冒犯家长的女儿。(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俊《清代小说史》所列八种清代英雄儿女小说,除不知名者外,其余五种都是文人创作。(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侠女论文; 平妖传论文; 性别角色论文; 淞隐漫录论文; 耳食录论文; 萤窗异草论文; 淞滨琐话论文; 小豆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