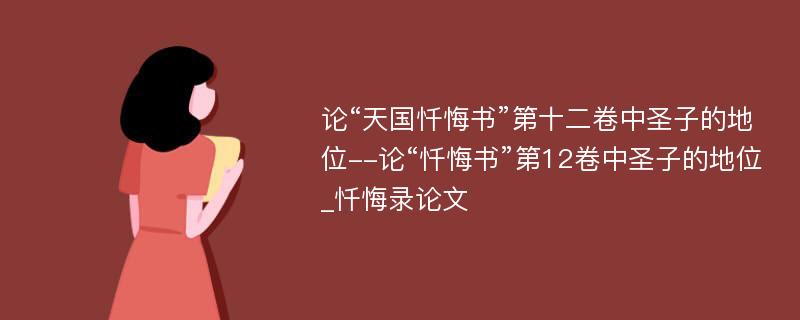
“天外之天”①——续论《忏悔录》第十二卷的圣子位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忏悔录论文,天外论文,圣子论文,第十二卷论文,续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救赎既然是记忆的降临,记忆既然已经在圣子道成肉身的历史中化身为时间的“现在”,那么什么是基督徒面向上帝的作为记忆的居所?记忆的主题一以贯之于《忏悔录》的后四卷,诚如“失忆”的主题贯穿于《忏悔录》的前八卷。既然前八卷的“失忆”使奥古斯丁流离失所于大地之上,那么后四卷的“记忆”的主题则引奥古斯丁回归于天国的居所。前八卷的“大地”与后四卷的“天国”形成对比,也造成转换,这就有了第十二卷的“天外之天”和“混沌之地”的比照。或许有学者会认为摩尼教的影子在这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显现,只不过摩尼教把这上升为第一原理,然而奥古斯丁把它下降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事件。然而无论如何,奥古斯丁是从记忆神学的角度继续探究上帝内在于人的方式,从记忆作为居所的角度显示圣子作为“为我”的位格特性。《忏悔录》第十二卷不是旨在探究圣子位格呈现为何,而是旨在诠释相信圣子已经降临的人们会生活在何处,进而呈现那些相信圣子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人们的居所为何,这是奥古斯丁所谓的“天外之天”。“天外之天”既非上帝居住的永恒之所,也非上帝创造在时间之中的伊甸园,“天外之天”在永恒与时间之间,如时间那样拥有开端,然而又享有永恒的福祉却没有时间的流变和沉沦。“天外之天”是人恢复了对上帝的记忆之后人的安居之所,是“天使的时间”。凡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当已在这流离失所的世界看到自己在“天外之天”得到的安居。第十二卷赞美的正是这圣子作为“居所”的记忆。
一、“天外之天”与作为居所的记忆
《忏悔录》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卷都诠释《创世记》第一章。第十一卷讨论《创世记》第一章第1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引出圣子与时间的关系;第十二卷讨论《创世记》第一章第2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十三卷讨论《创世记》第一章第3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对圣灵的赞美。第十一卷的前半部分(第1节至第13节)讨论圣父,第十一卷的后半部分(第14节至第31节)则讨论圣子。第十二卷顺着第十一卷的后半部分继续讨论圣子,表明圣子位格之于奥古斯丁神学的重要性。《忏悔录》后四卷(第10—13卷)的精彩之处,在于其以三位一体神学为叙事的文本基础,并以《创世记》作为三一结构的《圣经》依据。奥古斯丁以《创世记》第一章的释经开展出三位一体神学的进路,以赞美和忏悔作为对上帝已临的活动的面向,用福音的救赎诠释创造论,阐释三位一体上帝与人类救赎的历史关系,其叙事艺术可谓炉火纯青。
《忏悔录》的独特之秘还在于它对《创世记》的独特的理解视角。《创世记》是记录上帝创造诸天和世界的经文,记载上帝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格共同参与世界创造的行动,奥古斯丁的释经却匪夷所思,把《创世记》的释经指向上帝的救赎活动。更匪夷所思的是,创造活动作为上帝的经世活动原以圣父位格为中心,圣父是《创世记》第一章所记叙的上帝的经世的聚焦,与此相关的则是圣子和圣灵在参与创造过程中所显示的上帝的内在关系,即创造作为上帝自我启示的经世,并密切关系到上帝行动的其他方面,这也正是基督教的希腊传统例如巴西尔等人的阐释,然而奥古斯丁却把以圣父位格为主旨的创造活动转换成一种救赎活动,即把“创造”理解为“重新创造”,把创造中上帝与第一亚当的关系转换为上帝与第二亚当(耶稣基督)的关系,由此转换成第二亚当对第一亚当及其后裔的救赎关系。这种诠释方式只能说匪夷所思,令人叹为观止。
《忏悔录》从第十一卷到第十三卷都在讨论“重新创造”,也就是由“创造”的主题呈现“救赎”的道路,是向着上帝在人类历史中将临的图景启示救赎的含义。这种救赎的含义固然以“创造”之“好”显示为上帝创造活动的历史特性,重新定义“好”(神意)与人类秩序所根源的神圣之爱的关系,引出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相互交织的论题,由此指向救赎的关系,即人的重新创造,“创造”的“好”即上帝的秩序如何被理解为“重新创造”的好,创造的秩序与救赎的秩序之间形成面向上帝之城的朝圣之旅。由此《忏悔录》第十二卷以一种非常哲学化的方式诠释了整部人类历史向着圣子这个位格显示出来的所有方面的关联,并在基督论上面最终所获得的居所(终末论关联)。也可以说,《忏悔录》的第十二卷内含了某种色彩的终末论,然而不是以末日审判的方式呈现的终末论。
《创世记》第一章1-3节的经文起初于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et nimirum haec terra erat invisibilis et incomposita,tenebrae errantsuper abyssum);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文字,②是《忏悔录》第十一卷至第十三卷的《圣经》依据。《忏悔录》第十卷是总论性的,从记忆讨论圣父的位格,追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遗忘天父以致堕入罪中的路径。遗忘是通往罪的道路,《圣经》的教导在于唤回人们对圣父的记忆。对圣父的记忆要追溯至时间的尽头,超出记忆的时间限制,因为圣父是在永恒之中透过圣子进行创造,所有用内含时间的事件所塑形的圣父形象都背离了圣父作为记忆之根源的非时间性。由于人常以时间中的自我的有限经验记忆圣父,意味着人们单凭对事物的记忆不能够恢复记忆的本源,必须要有在时间中超越时间的记忆然后才能够跨越时间的河流,这在时间中的非时间经验及其探究指向就是纯粹非时间性的永恒。《忏悔录》第十一卷把永恒引入时间的主题,正呼应于第十卷把时间引入永恒。第十一卷把永恒引入时间在于呈现人们的记忆所指向的对象总与对天父的遗忘相关,即永恒的天父形象被偶像化为具体的物欲冲动例如对天体星辰和金钱权力等的崇拜。第十一卷则把在时间中并因时间而迷失的人类重新引向天父,显明时间之中的盼望,或者时间本身所深藏的盼望。第十一卷把天父上帝在太初(元始)中的创造行为之太初(元始)训诂为“圣子”,是奥古斯丁释《创世记》的关键内容,因为时间在这里获得与创造之初的永恒重新联结的可能,也只有从创造的联结中才能够显示救赎的安排。创造暗示了上帝救赎的经世,只有那万物借以受造的太初并在这对太初的依赖里面才会唤起堕落之人对罪的忏悔,只有他能把人从时间的沉沦中,从没有片刻停留的时间(用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的话说,这样的时间就是“人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引回以永恒为形象的时间。正是圣子使没有任何片断的时间得以重续长度,使懊悔成为救赎之路对天父上帝记忆的长度,因为正是永恒才使时间具有长度,是太初使得时间重新成为连续,使记忆的碎片得以存在的朝圣。
第十二卷紧接着第十一卷诠释《创世记》的经文,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奥古斯丁的释经同样出人意料,他运用寓意解经演绎出这节经文的丰富内涵,揭开了人在圣子里面所恢复的记忆的长度(延续性)的特质,将此理解为人从罪中治疗所寄居的家园,是重新与圣子联结的太初,是“天外之天”作为救赎论的国度观念。由此,第十一卷在圣子里面对天父的记忆成为第十二卷的复和的居所,对上帝创造活动的赞美被阐释为上帝的行动安居于人类历史中的经验,而赞美竟然是一种居所!正是出于第十二卷对圣子位格的进一步接纳,方有《忏悔录》第十三卷对圣灵的咏叹,那是在居所里面的人已蒙救赎的人的圣洁。
第十卷和第十一卷有关天父的记忆以及在圣子中降临的时间的永恒(现在向度)在第十二卷有了落实:救赎的历史透过天外之天的诠释被表达为作为居所的记忆。第十卷讨论对天父的记忆,论说记忆天父是救赎的降临,因为只有面向天父而记忆,才有可能恢复人的儿子身份。记忆与身份相关,没有对天父的记忆,就必失去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身份正是上帝在人身上的神圣形象。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与儿子的身份始终并且最终相关。一个叛离父亲之爱冒犯父亲甚至要杀死父亲的儿子,他肯定已经不可能是“人”,因为他既然甚至要“杀死”他最“好”的伙伴,那么“好”就不可能作为他的形象呈现。第十一卷则探究恢复天父的记忆所要经过的道路(中保),要恢复记忆的长度(可操持性),形成记忆的意识长度,使记忆重获位格的形式,不然倏忽即逝的印象只是“影子”而已,不可能构成自我的定向。而记忆的长度不可能依凭于上帝之外的存在物,只能够透过上帝自身,因为唯有非时间性的存在才使时间存在,所谓使时间存在就是使时间显示为“现在”。圣子,这个上帝的位格正是恢复记忆长度的动力,因为上帝作为儿子的身份降临,是要把记忆中已经失去的儿子身份重新赋予人的记忆,这是人之重新面向“好”的不可或缺的开端,人必须要重新成为儿子,才可能重新“成人”。这就是说,只有当圣子居住于人身上而人重新意识到他作为儿子的身份时,人才被上帝所居住,人也才居住在上帝之中。第十二卷继续以此诠释《创世记》,是对记忆作为居所的训诂,也是对上帝之城的展示。③第十二卷用《创世记》第一章第2节诠释天父的记忆以及记忆的“已临”(时间性)的落实,讨论圣子“已临”在时间之外的含义,从时间推进到时间之外,从记忆的已临的时间性推进到记忆的居所(空间性)。已经有了现在的长度并向着已临的现在停留的存在性时间被呈现为居所,④如同第十一卷从“永恒”开始咏叹,第十二卷则以对“永恒”的赞美结束。
《忏悔录》第十三卷将继续第十二卷的作为居所的记忆主题。第十三卷讨论《创世记》第一章第3节至第一章的第31节的经文。奥古斯丁用“水”/“大海”、“黑暗”/“光”的对比,探讨圣灵像“水”洗和“光”照,引人脱离“大海”的苦涩和“黑暗”的笼罩,显示永恒的安居之所将承受圣灵的光照,而不是生活在天体的光照之下。那“安居之所”那“天外之天”以圣子为记忆智慧的太初,指向作为智慧本身的圣父,然而人不是自有且自然地在这种开端之中,也不是自然自有地承受智慧,人是因着圣灵的运行才唤起人愿意居住在永恒中的意愿。人不能够按着创造者的意愿生活在创造的“好”之中,然而人获救后将生活在永恒之中,此时的人从意愿里面接受圣灵的光照,圣灵自身的永恒成为人意愿的清洁者,从而接受圣子的向着人呼喊而在人意愿中重新成为儿子的渴望,这才真正并永远地恢复出面向天父的记忆,你的德能渗透到我心坎深处,我在信仰之中感到喜悦,歌颂你的圣名。⑤虽然这居所不是上帝自有的永恒,却得以分享永恒的福祉;⑥这样的居所、这以记忆为安居之处虽然是得蒙救赎之人的居所,却也是上帝的居所,因为圣灵显出了居所里面圣子的荣耀圣父的恩宠。这居所甚至超出了上帝透过创造显示出来的美好,因为这是上帝本身在人的意愿中为洁净的居所做的预备。
二、“天外之天”的位格特性与救赎的形象
奥古斯丁以“天外之天”为上帝的第一次创造,以第一次创造的“天外之天”为得救之人的上帝形象,得以把第十一卷有关时间记忆的讨论转化为第十二卷有关居所的讨论。古典基督教思想家使用二次创造论解释《创世记》不在少数。这可能与他们普遍使用寓意解经法有关,还可能因为他们普遍有柏拉图哲学的背景,虽然对于后者之于教父们尤其是奥古斯丁的影响要审慎地分辨。基督教的希腊传统从犹太哲学家斐洛、殉道者查士丁、伊利奈乌、奥利金、阿波里拿留到尼撒的格列高利,都认为《创世记》讲的是二次创造,不过他们所释的是《创世记》第一章第26节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们注意到七十士译本用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表达“形象”(eikona)和“样式”(homoiosin)。他们认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先是创造普遍形式的人(人的理念),然后才创造个体的人。所有个体具有一般的人的形式,后者在时间之先受造,有开端但没有终结,是所有个体的人受造的原型。这个一般的人不会为时间败坏。古典希腊基督教思想家虽然认为这个内含了一般的人的个体就其作为个体而言被罪所败坏,然而其内在之人依然渴求善,这是人犯罪后继续追求善好的原因。⑦奥古斯丁的二次创造论没有以《创世记》第一章第26节为文本,他所释的经文是《创世记》第一章第2节,其神学指向也非人的受造,而是人得救后的居所。奥古斯丁同意古典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对第一次创造的受造物的存在状态的描述,也认为第一次创造的受造物虽不能和天主同属永恒,但它在天上具有另一种永恒,在它身上你们找不到时间的变化。⑧然而《忏悔录》第十二卷要诠释的第一次创造的对象却是《创世记》经文的“天”和“地”。“天外之天”乃是居所,就如在“天外之天”没有时间的特性,“天外之天”也没有空间的形式。居所不是空间,因为居所乃是一种形象,是人身上再也不能够与对上帝的记忆分离的形象。
奥古斯丁注意到《创世记》第一章第1节记载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第2节则提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天”无有论说,⑨人居住之所包括我们所见的苍天和大地,统名为“地”。这是《创世记》一章1节的“天”,是太初所造的“天”。⑩“太初”所造的“天”不是在时间中所造的天,此时时间尚未被造,然而已经有“天”被造。它在时间之先被造,它就仿佛永恒,(11)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是另外一种“永恒”。这样的“天”在苍天之外,又被称为“天外之天”。
“天外之天”没有日子,没有时间,没有开端。“地上之天”与“天外之天”相比,不过下土而已。“天外之天”没有“质料”,永远与质料分离。质料只呈现在时间中,在时间之先的质料却并不呈现,虽然质料(地)在时间之先已经受造。“天外之天”有开端却没有时间,时间是物质受造物的属性,不是天外之天和“地”的属性。这是《创世记》第一章第一句讲创造却不提“日子”的原因,时间出现在第3—5节上帝创造了昼夜之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12)《创世记》对时间的谈论则始自第5节,然而有关日子(时间)的谈论既无关乎受造的单纯形式,也无关乎受造的单纯质料。在头一日之前,质料已经受造,但也没有时间。上帝单单创造时间,而不是所创造的物体的运动表示时间,虽然《创世记》只用“头一日”而没有特别指出时间的“受造”。这“头一日”的提法意味深长,它表示从那一天开始日子(时间)的存在。日子的存在显然与具体事物有关,或者说日子(时间)是具体事物的载体,因为“头一日”或者说“日子”出现在具体事物的形成之中,与光和暗相关,与轮替相关。然而光和暗是时间的实体记号,却不是实体本身,因为《创世记》在光体之前说光已经存在,这意味着时间并不是光体的运动,而是在光体之前存在。因此,在“天外之天”与“物质之天”之间还隔着时间的创造。(13)“天外之天”是你“在元始创造了天地”的天,意味着“天外之外”是在基督里面,是基督的形象,是上帝的居所,是纯粹的形式。“天外之天”没有时间的箭头,物质之天有星象运动为其记号,人类之天则有历史活动为其形式,“天外之天”超越了时间的变动,完全仰望于“你”而绝不堕落。(14)天外之天只在元始之中就如它在元始中被创造并只仰望天主,“天外之天”只依附于天主。人蒙救赎之后进入的不再是伊甸园的物质之天,也不是以创造之初的伊甸园为最后的天堂,因为天堂是在时间之先被造的“天外之天”,是只对天主上帝的仰望,是在以基督为源头的“天外之天”里面仰望天父上帝,是永恒而不再堕落的超越时间的形式。
“天外之天”虽然是受造物却不具有时间的属性,充其量它只是具有开端而已,开端并不意味着时间。其他的受造物例如天体、人物和万物则不仅有开端而且以时间为开端,奥古斯丁对《创世记》第3—5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的释经蕴意特别,《创世记》第一章的其他经文(第6—31节)发生于时间创造之后,其他受造物虽然也是天父透过圣子并运用先行已经被造的质料而造,然而它们既是在时间中被造就以时间为开端。“天外之天”却不是在时间中被造,它是单单在元始中受造。“天外之天”虽然是受造物,然而由于单单在元始中受造只以元始为开端,而创造者天主和元始者基督都是无始也无终的永恒,那受造的“天外之天”就只以无始无终的永恒为开端,以耶稣基督为开端,永远披戴耶稣基督的形象,而不离开耶稣基督如同其他受造的万物那样动变不止。天外之天虽有“开端”,然而“开端”却是元始;世界万物有开端,开端则是时间。天外之天既是以元始为开端、以圣子为存在的位格,那它就是一种受造的智慧,保持着自我的永恒一致性。(15)奥古斯丁点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人当以这受造的智慧为自我知识的榜样,当以其智慧的本性为其知识之源,因为真正的智慧只仰望上帝的光明,那将得救者的智慧所看见的比受造之初看见的智慧更具智慧的本性,因为以后的智慧将只在圣子中以仰望天父为依归,将以圣子为开端。(16)受造的万物虽然是在伊甸园中,然而他们是在伊甸园的时间之中,而不是如“天外之天”在以永恒为开端的持续存在之中。伊甸园的万物需要透过持续聆听上帝的话语为存在之源,就连时间也要聆听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维持它所本的永恒形象。
奥古斯丁既赞美天主所创造的天外之天,也指出天外之天所享的永恒与天主所是的永恒的区分,指出圣子作为智慧的永恒与天外之天作为智慧的区分。(17)天主和圣子是自有的永恒,天外之天则以圣子为开端属于披戴的永恒,两者的永恒不能混淆,同时还要区分天外之天的永恒与具体的受造物的时间。在永恒和时间之间存在一个居所,虽然也有开端却始终持存,它的永恒不是如受造物的时间开始于独立的实体,而是来自于它以天父为仰望的对象。而在仰望之中,天父之为记忆之源绵绵不绝降临而成为居所。天外之天的永恒并不是时间观念,也非长度问题,它显示的是荣耀,因为圣子以其为居所,并且圣子把这样的居所赐给以其为源头的人们。
“天外之天”正是作为居所的记忆,而永恒是居所的本体。不能把永恒视为一种类似于时间的绵延,不要把永恒视为一种类似线段的长度,长度只存在于时间之中,由长度表现出来的数量也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因此有关记忆的居所领会,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诚然,人在回转的过程中需要经过时间的长度(现在性)这个环节,然而人的救赎并不是停留在这作为长度的时间之中,这个停留的长度只是暂时的居所,在现世经验的上帝之城仍然与世俗之城混淆,而这两者必须要完全分开。人在进入时间的长度或者恢复时间的长度时,是透过圣子的“已临”在世俗历史得到疗伤,是领会到人性本可以如圣子所取的肉身和人性那样洁净没有罪性,然而救赎不止于此也不限于此,还在于透过这“已临的”(现在/人性)披戴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耶稣基督的人性已经与罪性完全分离,已经与第一亚当的以时间为开端的人性完全分离,从而与世俗的世界完全分离。人在进入“已临”之后,恢复的不仅是受造之初的人性,而且是如天外之天以永恒为其开端的人性。已临的圣子透过时间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真实也是不止于无罪的人性,而在于得到恢复后再也不犯罪的意愿,把人保守在再也不会犯罪的意愿之中,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意愿为意愿,而这不是仅仅透过或者仅仅满足于把救赎看成一种疗伤能够达成的,它意味着要透过时间而降临的永恒,即不只是进入圣子借时间降临的现在,还要进入圣子借时间已临的永恒,圣子本身所安居的是永恒,时间已被安居于其中。人们要进入的不只是圣子所安居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已经为圣子开展出记忆的长度,而且要进入时间所已经的安居之所,而时间只能够安居于永恒之中。这就足以显明第12节接着第11节由时间的现在性进入时间的居所即永恒,这两卷这两个主题的延展和交织如交响乐般轻柔且雄浑。这是圣子位格的双重性所奏出的歌呀,也是由圣子位格的双重性所咏出的诗:时间作为圣子居住的历史长度以数量给出救赎在人心灵中的停留,这种停留导向绵延而为空间的记忆;永恒是作为记忆的这种居所之名,一种非数量的原理,一种单纯的在,一种荣耀,一种新的身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外之天”表达了圣子位格在得蒙救赎的人身上的整全,它是心灵渴慕的目的,它不再受激情的支
配,如秋日的阳光在歌者身上无边无际地漫过的福祉,是令所有的苦难和一切苦难的形式(例如焦虑)为之停步的辉煌。(18)这样的居所将不会有再次的堕落发生,甚至与在时间中创造的伊甸园都会显示深刻的差别,那苦痛的灵魂、那为尘世之影所拘束的灵魂将汲汲于永恒,将不再有离开圣父的远游,那回归的浪子以享受与圣父的同在为福祉,以享受同在为其自身之在,以享受为其自身的日子。
脱离了世俗之旅的灵魂向天外之天飞升,救赎之谓得救不只是脱离了罪,更是指获得了永恒的安居。他们所得的安居之所不是圣三位一体自有的永恒,而是以圣子为其仰望的受造的智慧。圣子以之为居所的是得救的人也以为的居所,是再也不会颠沛流离的家园。而在世俗之旅中,人居无定所,而且没有居所。人不断地寻救居所却不见安居,失去居所、居无定所是世俗之城的象征。“天外之天”则是得救之人将要前往的上帝之城,是从未离开上帝远游的居所,是再也不会为罪荒芜的存在的家园。(19)天外之天以圣子耶稣基督为披戴,受造的智慧以永恒的智慧为智慧之源,是要在圣子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就是天都,它是直涌到永生的智慧,是披戴上耶稣基督的天国之旅者。
三、“天外之天”:复原在人身上的“圣子”形象
《创世记》第一章第1节的经文还记载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地”的形态描述似乎较“天”清晰。虽然第十二卷有关“地”的具体阐释没有“天外之天”的篇幅多,却构成第十三卷的思想脉络之一。奥古斯丁认为“地”与“天外之天”都在太初之中受造,“地”也具有“天外之天”的特性。“天外之天”不是时间之中的受造物,以圣子为开端,是时间之外的存在;“地”也如此,也不是在时间之中的受造物,就“地”的混沌空虚的性质而言,也永远在时间之外,然而“地”不以圣子为开端。(20)渊面黑暗的“地”固然如“天外之天”那样不会有变化,在时间之外,然而它不会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天外之天”虽然也有可变性,却因着仰止天父而不变。混沌无形的“地”则不会从一种形相向另一种形相变化,没有可变性。
“天外之天”和混沌无形的“地”都无形相,但两种无形相截然不同。“天外之天”的无形相是因为谛视天主而享受天主本有的欢愉幸福,并借着圣子以为源头的永恒压制了天外之天作为受造物本身的可变性,(21)它的无形相是圣子的无形相,是圣子形象的显示。天外之天不以其自身受造的特性显示它自身,它以受造之身显示永生之神显示太初受生育的圣子,这是它的无形相。天外之天的无形相不着于物的变化的形相,是联系于爱的无形相,因为爱本不变,无形相的东西也不变化。天外之天的无形相是相对于一切以“质料(原始的“地”)”说的,是说它不具有任何的质料要素,而不是相对于眼不能见的形状说的,不是相对于例如眼不能见的“混沌空虚”这样的属性说的。天外之天始终享受着的无形相是圣父透过圣子造它时的爱。爱本无形相也不着形相,所谓爱没有形相,是说爱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天外之天”承载的不仅是始终如一的爱而且它始终如一地爱创造者,这样的爱合乎爱本体的自有,是常在的本体,天外之天本身虽然不是本体,但是因着它也始终如一地爱天主它的上帝,把它自身关联为向着上帝的停留,这样的爱不因变化而是此或彼,而是因着它始终是“是”而没有穷尽,因为它不是要用变化用各种爱的花样表达爱的本身,爱就其是无形体的来说它不借助于任何形体而表达,表达爱并且维持在爱之中的最好办法就是只是始终如一地以爱为其生活。(22)奥古斯丁用“中午的光明和热力”中的“中午”这个最能表达阳光最鼎盛消除了所有的阴暗维持着同一性的最高状态的比喻说明爱的无形体性,上帝的经世之爱即是如此,天外之天拥抱并且完全地敞开它的所有视野接受并环绕这种爱的经世,天外之天根源于这常在的本体而在时间之外,停止自己变化的欲求,因为变化本身是为了寻求好,然而天外之天却深悉真正的好全然的好已经降临,既然如此就不需要再去向着变化寻求好,那种好肯定是不一致的肯定最终是要离弃好的好。不变化和无形体性虽然不是天外之天的本身欲求,虽然它自身仍然具有可变性,仍然有趋于成为形相的欲求,却因着这样的接纳而消除了这种欲求。这是何等的盼望!有形相的人在时间中漫游,而失去边际的人岂不也是以其可变性在大地之上游荡?可变性岂不正是其所谓好的根源?人岂不是经常以其所谓的可变性为生活的时间框架?然而天外之天给出的盼望是何等的伟大,那受造而具有可变性的存在却可以因着那对于圣子的爱的活动的全然接受,成为它活动的内容,因为它在这样的活动中就已经满足了所有的好。或许奥古斯丁这里使用的释经运用了柏拉图的哲学,然而他在主要的观念上离开了柏拉图,奥古斯丁对于无形相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柏拉图,虽然他也使用了柏拉图的无形相的哲学术语。无形相不等同于纯粹形式,天外之天不是纯粹的形式,无形相是上帝爱的本体,只有以上帝之无形相为其“形相”时,人才可能无形相。
混沌无形的“地”的无形相却非如此。无形相的“地”是一种物质。这物质却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是一个描述其不可名状的概念,指它不具有目睹和可以捉摸的条件,不能够用感觉分辨,(23)因为凡可以看见和分辨的都有形相。说这棵树不是那棵树,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棵树的形相与那棵树的形相的分别,例如这棵树更高大、结的果子更多等等,无形相之物不能以诸如此类的感觉和感知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不具备可感知的条件,也没有任何形成感知的条件。而人没有办法想像无形相的空虚混沌,因为凡人所想像的必已经按照某种形状模拟,当想像用某种形状模拟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使用某种形状,已经具有了形相。通常所谓的无形相其实是极端丑陋极端恶的东西,然而丑陋和恶仍然都具有形相。(24)既然物质的无形相不是指各种丑恶可怖的形相,那也就是说“恶”不是来自与原初混沌的“地”的关系,后者则是柏拉图的理解:原初混沌的“地”是恶的根源。奥古斯丁说,无形相的物质(质料)无从模拟,不存在无法模拟的恶,恶都是模拟出来的结果,正如好一样,它也是仿效。恶既然是模拟的结果,那么恶就是一种形相并且只能够来自形相,是形相之间的变化。我们无法想像无形相的事物,我们只能够想像种种形相。我们无法想像的无形相的东西,即在时间之外虽然不像天外之天具有可变性,而它自身是一种在时间之外因着无法获得形相而无形相的,就不是恶。即使《创世记》第一章第2节说上帝创造了空虚混沌的“地”,这“地”也不是恶的。
《忏悔录》第十二卷为何给出对混沌无序的“地”这样的主题的讨论。正如对“天外之天”的讨论不是创造论而是救赎论的释义,是对于“好”之“成为好”的阐释(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好的,那被创造为好的则要保持为好,而不是希腊哲学所谓的成为好),同样,对混沌无序的“地”的阐释也包含着救赎论的神学指向。奥古斯丁否定混沌无序的“地”是“恶”的根源,否定恶存在于创造之初,而强调恶是形相之间的模拟,都是在回应《忏悔录》第七卷有关恶的讨论,批驳摩尼教对恶的解释。“我探求恶(malum)的来源时,我探求的方式不好,我在探求中就没有看出恶(malum)……恶原来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怎样钻进来的?……是否创造时,用了坏的质料,给予定型组织时,还遗留着不可能转化为善的部分?”(25)这种对恶的本体存在的寻求,引导奥古斯丁对所存在恶神的理解,是他身陷摩尼教的原因。(26)在皈依之前,他才解决了这个令他栖惶不安的问题。(27)《忏悔录》第六、第七卷的忏悔表明奥古斯丁曾持柏拉图和摩尼教的看法,即物质(质料)和恶密切相关,这是第十二卷质料论(“地”)的背景。第十二卷阐释说,恶并非来自质料,质料在时间之外不具形相。它自身无法进入受造的人之中,它本身无法成为人作为受造者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不可能如摩尼教所谓的不存在成为人的主导者的本体性质料,质料不可能自动地是恶的根源。由此而论,恶也绝不来自天主,即使那天外之天和地都在时间之先被造,“地”本身没有所谓的恶,也就不会因着透过圣子而成为恶,圣子也不是恶的传递者。奥古斯丁透过对质料的讨论以及第十二卷第16节之后他为自己所作的艰难辩护,是要与一切形式的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彻底分割,也与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的救赎论彻底分割。
虽然这“地”混沌无形,不能从一个形相变化到另一种或动或静的形相,(28)就是说,这“地”本身没有动和静的变化属性,变化意味着已经有时间作为条件,虽然这“地”不具备时间限制的条件,然而它也不会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29)这后半句话的论述相当惊人,它意味着这“地”不会驻留为非时间,然而显然它又不是时间。它不会驻留于非时间之中(天外之天不驻留在非时间之中),因为它只能够呈现在时间之中(而天外之天则可以呈现于非时间之中),因为它在非时间之中虽然混沌无形也不能够呈现,因为只有进入时间才能够呈现,然而它又不是作为本身而是透过“形相”呈现,它虽然呈现出来却依然不能看见。这“地”本身(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不具有可变性,它只能够透过时间中要呈现出来的形相变化显示出它参与其中,这也与“天外之天”形成比照,因为“天外之天”具有可变性。“地”本身不具有可变性,形相则呈现出可变性,一切能变化的事物,所以能接受各种形相,因而能形成各种事物,是由于它们的可变性。(30)奥古斯丁说他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这种可变性,然而可以肯定“地”是不透过虚空也不透过物质,这也是论证“物质”的非恶,然而物质是诸形相变化的中间环节,我注视物体本身,并深一层探究物体的可变性,由于这可变性,物体从过去的那样,成为现在这样;我猜测到物体从这一种形相进入另一种形相的过程不是通过绝对的空虚,而是透过某一种未具形相的原质。(31)可变性存在于物体之中,却不能够说可变性是精神抑或物质,只能够说在物体里面总存在变化的指向,“地”不能够停留在非时间状态正是受了物体的可变性的推动。当物体处在变动中时,或者说由于物体总是处在变动中,其原材料就要不断变动补充处于被运用的过程。作为“地”的原质只是被运用的,它不是自身的运用者也不能够运用有形相者。正如给出“天外之天”是要给出永恒的“安居”,给出天上之旅的本质即安居,奥古斯丁给出“地”也是要给出创造之初上帝给予人的“安居”,在创造之初上帝曾把人安居在大地之上,时间也曾是人安居的度量,那时候万物有序,人的生存美好幸福,形相的迁转可度量却不局促奔忙,在那个透过空虚之地形成形相迁转的世界之中天父曾经为变化不定且不真实存在的万物提供存在的根基,使万物的可变性蕴含时间的秩序,人和万物变迁却不流离。虽然“地”空虚混沌,然而上帝创造之初的肇成品类却依然有受造的智慧在于其间,显示太初智慧的形象。
注释:
①J.O'Donnell认为第十二卷透过趋近圣言可以逐渐地把圣言的统一性和清晰性从话语的多元性和含混性中表达出来。这种关注点也以别的方式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中保留下来:这种对《创世记》的实质性释经关注的是《创世记》的经文,即创造系列中物类的出现或者空缺。这卷书开始于直接的经文释经,而后转向释经过程本身,透过释经整个反思得到扩展和丰富。在释经过程中,奥古斯丁借重的是话语(verbum)的意义明确性(univocality),即在话语背后的意义,这种透过教会事工而进行的caritas的力量保证了他的选择;奥古斯丁会宣称他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又宣称没有更好的做法。(James J.O'Donnell,Augustine Confessions,Vol.Ⅲ,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0-301)第十二卷的结构可以描述如下:
12.1.1 导论
12.2.2-13.16 《创世记》1∶1—实质性释经
12.2.2-8.8 天外之天和空虚混沌
12.9.9-11.14 时间之先的创造
12.12.1513.16 小结
12.14.17-29.30 《创世记》1∶1-方法论的考虑
12.15.19-22 对立的看法
12.16.23-26.36 如何处理对立的看法,例子
12.20.29-22.31 《创世记》一章的五种观点:评价
12.23.32-26.36 如何评价作者的观点
12.27.37-29.40 《创世记》1∶1-重新考虑
12.30.41-32.43 结论:多种意图,多种阅读,一位圣灵
②文句中的拉丁文出自奥古斯丁。见于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括号中的数字为拉丁文本《忏悔录》的卷和节。
③《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5节,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20).
④《忏悔录》第十二卷第9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9).
⑤《忏悔录》第九卷第4节。
⑥《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5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9).
⑦相关阐释可参看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1511—1538页。
⑧《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5节。
⑨《忏悔录》第十二卷第2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2).J.O'Donnell认为本节是以《诗篇》第113篇第23节释《创世记》第一章第1节,而《圣经》经文内的互释具有特殊的权威。此外,斐洛和奥古斯丁有类似的思想,奥古斯丁可能并不直接地受了他们的影响,其价值在于可能主要地看见《圣经》与柏拉图化的观念之间的趋近。Caelum-caeli是一个令人烦恼的主题,但是奥古斯丁也很清楚地划出了“天外之天”表述的界限,它是被赋予理智的创造的一部分(12.9.9,“creatura aliqua intellectualis”,12.11.12,mentem puram),就如domusdei和圣言(但不与圣言同一,而是作为第一个受造物)。在每个地方,天外之天都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者,但不是必然受限制于时间也不是与上帝同为永恒。(James J.O'Donnell,Augustine Confessions,Vol.III,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p.302).
⑩《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3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6).
(11)《忏悔录》第十二卷第28节,这个“在……先”是逻辑在先。
(12)《创世记》第一章第5节。
(13)《忏悔录》第十二卷第8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8).J.O'Donnell认为第8节的引人入胜是用诗体去思考上帝。上帝总是从无中创造,而无是最低限度的某种事物(de quo paene nihil),并透过for ma(形式)加于其上而提升它。这是非普罗提诺的语言:就普罗提诺而论,降临是第一原理的生成;而就奥古斯丁而言,降临是有条件的,是由于受造物错误的选择,违背了上帝普遍的意愿,所有人都必须要透过中保得拯救。创造的历史就是上升的历史。在注释tempora时,J.O'Donnell指出奥古斯丁思想的一个习惯是探索一个主题(例如第十一卷,时间),然后移向另外的主题(例如第十二卷,从无中创造),然后再回到他后半的主题,重新思考这个主题以探讨他第一次所讨论过的内容,以把两个部分整合成一个整体。(但是第十二卷接下来的论述从第一卷的结论略为后退一些,第十一卷的结论是时间作为意识的延伸:这可以被读解成前面的观点:时间是变化的。)在注释vertuntur species时,J.O'Donnell评论说,可变性是无形式的质料的特性(12.6.6),但是运动和美都来自于无形式质料的提升,即透过被赋予神圣的形象,也就是在世上的圣言的各种工作。(James J.O'Donnell,Augustine Confessions,Vol.III,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pp.310-311)
(14)《忏悔录》第十二卷第9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9).
(15)《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5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20)。J.O'Donnell认为到这节为止一直在讨论永恒的主题,接下来开始阐释时间(James J.O'Donnell,Augustine Confessions,Vol.III,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p.318)。
(16)《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3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6)。
(17)《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1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2)。
(18)《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1节。
(19)《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1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2)。
(20)《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2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15)。
(21)《忏悔录》第十二卷第9节。
(22)《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5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21)。
(23)《忏悔录》第十二卷第5节。
(24)《忏悔录》第十二卷第6节,Augustine,Confessions,Vol.I introduction and text by James J.O'Donnell,(12.6)。
(25)《忏悔录》第七卷第5节,Ibid,(7.7)。
(26)《忏悔录》第七卷第7节。
(27)同上。
(28)《忏悔录》第十二卷第12节。
(29)同上。
(30)《忏悔录》第十二卷第6节。
(31)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