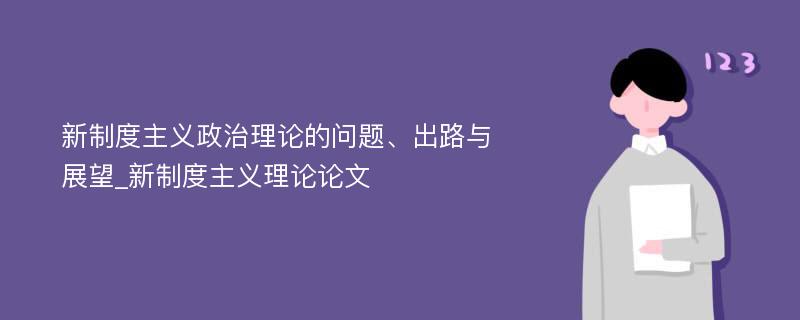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的问题、出路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路与论文,前景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8)05-0041-11
引言
新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热情,以至于有学者惊呼“我们已经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但同时也受到批评。① 有些批评认为新制度主义“存在理论与概念上的混乱,缺乏解释力,并没有给政治学科带来新东西”。[1](P1-36) 面对众多质疑,新制度主义者试图反思自己的理论观点,或通过修正已有观点和视角,或通过引入新的概念或分析路径,回应这些批评。
一、制度的概念及其拓展
新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是制度形塑行为,但由于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在理论基点、分析路径与重点等诸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它们对制度、制度化等基本概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基本概念差异的存在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不仅造成了制度等概念的模糊性,而且影响了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统一性和理论解释力。琼·布隆德尔(Jean Blondel)指出,“政治学中很少有人考虑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制度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把社会学和经济对制度的现有解释引入政治学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同时,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概念也存在许多问题。”[2]
为了解决制度模糊性问题,学者们一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制度。如约翰·R·瑟尔(John R.Searle)认为制度是任何被集体接受的规则(程序、实践)体系。[3](P1-22)
阿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演化制度主义等理论的制度概念的基本内容、优长和不足之后,指出为了推动制度分析,需要能够结合不同制度分析路径,容纳各种因素、力量,吸引二选一式的制度分析路径所勾画的分析框架和见解的长处,建立一个综合性制度概念。还需要在相互作用个体的层次上研究制度,同时把与行为规则相伴生的动机当作构成分析的必要部分,从而为研究这种制度的持续性、内生的制度变迁、过去制度对它们后续发展的影响,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性和分析性框架。[4]
基于这一认识,阿纳·格雷夫提出了一种大大拓展了的制度概念。他认为,制度是由那些结合起来产生行为规律性的社会因素的体系。(“体制”一词突出一项制度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但一项制度不一定具有所有体系性因素,如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这个体系的每一部分是社会的非物质性因素,并内在于每个受其影响的个体。这些因素一起激发、引导个体,使之遵守社会中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行为中的一种。通常把这些影响行为的社会因素称为制度因素。本书中的制度因素主要是规则、信念和规范及其表现形式组织。制度是由那些联合起来产生社会行为规律性的规则、信念、规范与组织组成的体系。每一种因素都满足上述条件。[5]
很明显,阿纳·格雷夫把制度概念扩展到正式结构之外,“也许能在制度路径(在传统的物质主义意义上讲的)与强调规范、价值观、文化和观念路径之间存在的鸿沟上架起桥梁”。[6](P7-8) 但作为以制度为中心分析概念的新制度主义,如果赋予制度某些区别于其他概念范畴的基本特征,制度主义就很难称之为制度主义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奥韦·佩德森(Ove K.Pedersen)就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新制度主义都需要“考虑如何能把制度从价值观中、把价值观从规范中、把规范从规则中、把规则从程序中、把程序从角色中分辨出来。简言之,弄清制度何时成为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如价值观、规范、规则或角色等。”[7](P125-148) 但把制度概念扩展到正式结构之外不但没有解决旧问题,反而带来了新问题,对制度基本含义的拓展并没有解决新制度主义内部对制度的争论与不同界定,反而增加了制度的模糊性,使之难与其它概念区分开来。
二、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与内部整合问题
实际上,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分别处于不同的知识传统中:即传统的历史的政治科学、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学。而与这三种知识传统大体对应的方法论则是社会结构、个体主义和文化路径。历史制度主义坚持从宏观社会结构出发,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想把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模式化。
方法论上的不同引起了新制度主义内部的争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提出结构研究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太过于依重经验的(历史的)细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受到批判,批判者认为它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牺牲了细微差,建立起来的理论也过于抽象。”[8](P15-16) 从新制度主义内部不同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差别来看,“制度代表的是这些传统演进的一个交汇点,并不是三种传统的全部汇聚。从广义角度讲,考虑到加强三种知识传统的各种因素,对统一的研究路径来说,制度代表的共同基础过于狭窄”。[9](P18) 正是因为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由不同的学科、研究传统滋养起来的,把各自的制度分析放到不同的路径中,对学者们来说,通常很难充分地理解二者之间已经形成的富有成效的相互学习的大量共同基础”。[10](P4) 方法论差异引起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流派能否融合,以增强新制度主义的整体说服力与解释力。
为了避免方法论方面的差异带来的限制,新制度主义者正在努力在这些方法论与认识论两极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有的学者指出新制度主义各分支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重要,各分支之间可以展开对话,甚至是综合。最近有学者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的相互批评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要做的是寻求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整合点,考察它们是如何相互学习的,这种相互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想借此证明二者对制度的关注是如何成为会聚点的,这种会聚点已经为二者的合作与整合提供了富有成效的依据。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偏好与制度两个概念上,因为它们处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明显的重大区别的核心,二者在这两方面正在形成共同之处。就偏好方面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转向制度分析,从而促进了对偏好的研究与理解,丰富了对偏好是如何被纳入它们知识范围的理解。……由于对制度的重视,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都把更多的注意力随环境而定地转向了偏好。② 就制度方面而言,由于二者都通过建立规则、符号、规范和激励,集中关注大规模的通常又是长期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模式的形成过程,两个流派的学者都逐渐形成了共识,即制度能解决人类协调和合作这一关键问题,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还可以确定并建立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已经分别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方向向制度靠拢。对二者来说权力和问题的解决在制度安排中相遇了。它们都重视特殊性,都相信情势的独特性,它们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这些情势的规则。”[11](P16) 总之,理性选择传统已经开始更系统地注意历史的制度过程,以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的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制度是如何导致偏见和其他曲解产生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已经开始研究偏好是如何在实践中被展开和重塑的。尽管二者的研究各有其特点,但都已经把制度和偏好放在新的路径方法的前沿和中心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制度主义内部(主要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差异更有利于增加它们在各自的研究议题和议程中的解释力。正如安德烈·勒库尔斯(Andre Lecours)指出的那样,“新制度主义的多样性给新制度主义巨大空间与能力,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不同的政治过程。而且,新制度主义的复数性、同株异蕊性、不可化约的差异性等,并没有妨碍它传递大量理论信息,也没有妨碍它在政治科学中产生重大影响。”[12](P19) 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治现象至少都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的多种因素,更确切地说,都是由分属于两个层面的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构成或影响着具体的政治现象。因此,只从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宏观结构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偏爱的微观个体来分析政治现象,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也正是由于方法论认识论上的差异,使不同制度主义分支之间面临理论上通约的困难。20多年前著名制度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就指出,“‘制度与行为之间的核心问题远没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结构与集体行动、微观个人行动之间存在巨大裂痕,没有联接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机制还没有弄清,没有给出更合理、更完整的解释。”[13](P684-688) 时至今日,新制度主义的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追其根主要在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困境没有根本得到缓解。质而言之,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是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如何协调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益处与不足是社会科学难以根本解决的问题。而处理这些概念问题与方法论问题的最现实可行的方式,就是“透过多元方法的研究来寻求其汇合之处,不是以某种理论存在的缺点为由而将之弃之不用”,[14](P83) 同时,又不宜完全消除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差异,如此看来,最有前景的方法可能是容纳宏观与微观,并且揭示二者之间联系的研究途径。
三、新制度主义的论域与适应范围问题
很明显,新制度主义的研究从一开始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案例的研究。无论这些解释如何适用于西方成熟政治制度的变迁,它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限制了用它研究这种背景之外的制度变迁时的适用性。正如历史制度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在人类行为还受不同时空的制度作用的条件下,政治科学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对政治知识的有限概括”。[15](P124) 库尔特·韦兰(Kurt Weyland)以拉美政治研究为例,指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超越其所处时空背景后表现出明显不足。他认为“很难把拉美地区复杂的政治利益塞进非常简约的理性选择分析模式。过分强调选举竞争、立法操控和一般政治输入,过多强调正式制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些不足也影响到了它对美国政治的解释效果,不过,这种影响对拉美更为严重。当把源自美国的见解运用非常不同的背景中去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上述不足就更明显了。这种张力不仅来自方法程序和基本理论原则,而且——多或少地是有意识的——来自建立普适模式的野心,其实这一雄心早已隐藏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中了。尽管在原则上,理性选择的发展能在不危及其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克服这些弱点,但代价可能是它更具理论复杂性和实质的特殊性,最终的结果也许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而只能根据具体背景而进行剪裁。”[16](P57-85)
这样看来,最大限度地把握政治生活的现实是建立和完善政治制度变迁理论的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国内政治学者林尚立指出:“在政治社会学看来,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17] 当然,最可行的办法是在研究过程中努力促使政治现实与制度变迁理论良性相动,用对鲜活政治现实的把握去丰富制度理论,同时用制度理论深化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个案研究结论与一般理论化模式之间的区别。库尔特·韦兰指出,“政治科学能否建立能普遍运用的一般性理论洞识?是否存在一种理论,能够让学者理解并解释具有广泛背景的政治呢?过于复杂的因果因素、背景依赖性和相互作用是否使可以普遍运用的理论洞识在分析对象方面受到限制?还有,有效的分析是不是要求要进入特定的背景,注意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呢?把寻找普遍性理论的雄心暂时放在一边,只寻找一种中观的一般化理论,来分析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现象,是不是更现实些呢?”[18](P57-85)
个案经验研究与普适性制度变迁理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从根本上说,社会科学研究中,个案分析得出的规律与普适性结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的。③ 但新近致力于拓展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新制度主义学者,非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试图发现一个普适性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④ 不管试图建立普适框架的研究者是把其研究范围限定在民主国家中,还是从社会政治经济与组织因素的角色及其影响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提出构建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变迁框架的研究野心都显得过于宏大。总之,任何经验性个案研究也不可能穷尽现实多样性与无限性,从而建立一种适用于宏观与微观制度变迁的普适性理论,或是致力于联结宏观与微观层面制度变迁的中观理论,或是在建构宏观理论时说明其所适用的时空条件也许是最优的选择。
四、制度变迁:内生还是外生?
在新制度主义论点中,招致批评最多的一个缺陷就是它不能有效地解释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共同内核或中心论点是把政治制度看作一个独立变量,认为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从而拥有较高的稳定性、自主性,能够自我实施甚至是自我强化,因此,“政治制度安排典型特征是难以变迁”。[19](P475-499)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它更适合于解释制度稳定而不是制度变迁。同样的原因使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变迁只是对重大危机或关节点作出的反映。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所指出的,“变迁是困难的,制度变迁是一时的、急剧的,而不是持续的和渐进的,危机具有核心的重要性”。[20](P223-244)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认为,“制度结构一旦建立起来,很难变迁,即使潜在的社会力量不断发展,结果是,变迁可能是一时的,只能在战争或萧条等危机时产生,只有当存在制度断裂或受到质疑,或者在基本的博弈规则产生分歧斗争时,才能产生。[21](P219-243) 这样制度变迁的过程就呈现出一种均衡——被打破新制度出现——新均衡重建——再被打破……这样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
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解释的质疑和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1.对路径依赖理论的批评。路径依赖本来是新制度主义用来解释制度稳定的一个关键概念。路径依赖所依靠的基本概念是“报酬递增”或说是“正向反馈”。[22](P251-267) 不过,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历时性意味着把制度有效性从背景的发展分离出来,这与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一致。如施瓦茨(Schwartz)指出的那样,政治科学中的许多理论与证据证明制度一般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不是路径依赖所强调的报酬递增,锁在外面(lock- Out)也许比锁入(lock- in)更常见。[23] 这一批评对新制度主义来说是致命的。2.对“不断被打断的均衡”模式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不能完全解释制度变迁,原因有三:(1)它把外部冲击看成是打断先前制度模式,导致制度创新的力量,但我们从经验上发现并非如此,至少并不总是如此。反过来,经常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长时间持续的制度安排中不断进行的但通常是微妙的变化所产生的积累式影响。[24](P8) 尽管有的学者从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假定渐进适应只会使存在的制度“僵化”,或只是提及这一点,并没有给出解释。渐进性变迁也能摧毁或改变制度结构。而且,和瞬时性制度变迁一样,对渐进性变迁也必需给出解释,因为它对政策形成、联盟的建立过程,进而对政策选择有重大影响。(2)由于它注重危机带来的剧烈变迁时期,而忽视了个体对影响民主制度结构变迁上的作用。而凯瑟琳·西伦指出,“集团和个人并不只是政治力量的平衡中随着条件变化而接受赞扬或处罚的看客,更是策略行动者,他们有能力按转变的背景条件所提供的机会采取行动,以维护或提高自己的地位。”[25](P369-404) 也就是说,国家官员决定什么时候、怎样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寻求变迁。(3)制度持续与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但“不断被打断的均衡”模式认为在下一个关键节点到来之前,制度被当作是稳定的,正如西伦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模式倾向于在制度创制时期与制度稳定时期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把制度的起源、维系、变迁分开来分析,把它们看成是不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这样就很难发现制度持续中的变迁因素和制度变迁中的传承因素,这也没有抓住制度历时性变迁的重要方式。
为回应这种批评或说是反思,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很有必要考虑建立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新近致力于内生制度变迁研究的学者是由阿纳·格雷夫和大卫·莱廷(David D.Laitin)等。他们提出并试图解决自我强化均衡的博弈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不能回答的三个问题:一是制度为什么变迁,如何变迁;二是在变迁的环境中,制度是如何持续的;三是制度开启的过程是如何导致制度自身终结的。为回答这三个问题,他们把博弈论及其历史制度主义所重视的历时过程结合起来,引入准参量(quasi- parameters)和自我强化(self reinforcement)两个概念,在重复博弈理论基础上,提供了一种能够描述制度内生变迁的动态方法。其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观念是作为博弈理论均衡的制度,并不排除制度变迁是由制度内在特征引起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制度所必需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自我强化行为的破坏。因此,制度也可能会自我削弱,制度所必须的行为也能培养制度终结的种子。然而,只有当自我削弱过程达到一种关键层次,以致行为方式不再能够自我实施时,制度变迁才会内在地产生。内生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是制度的隐含意义持续地削弱相应的行为。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制度盛行的必要条件是相应行为自我实施的条件范围不会随着时间而缩小:制度的行为意义必须强化制度,至少在最弱意义上是如此。因此,除非制度是(较弱地)自我强化,它最终会达到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与制度相应的行为不再能自我实施。外生制度变迁就会接着发生。总起来说,制度的自我强化强调另一种间接方式的重要性,即当制度影响外部冲击的量级与性质时,并且这些外部冲击将必定会引起与制度相关的信念与行为变化,制度能内在地影响制度变迁。当制度自我强化时,与制度相应的行为并不会变迁。但被强化的制度会因此比原来的制度更有活力。即使在与原来不同的条件下,与制度相应的行为也能自我实施。与此相反的是制度自我削弱的情况。通过强化或削弱自己,通过决定参量的外部变化(这些参量则是使与制度相应的行为停止自我实施所需要的),制度间接地影响变迁的速率。制度能够变迁是由于内生过程、外部冲击或二者结合起来。[26](P633-652)
阿纳·格雷夫在其新著《制度与现代经济学之路:中世纪贸易的教训》中提出一些长期困扰着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制度分析的问题,包括“制度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得以持续?外部变化与制度开放过程如何导致制度毁灭?也许不再能有效影响行为的原来的制度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为什么社会沿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演化?为什么改变制度动力使以产生更好结果很困难?”[27]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能容纳稳定与变迁的框架,这一框架一方面能解释变化环境中制度的持续与稳定,另一方面能解释内生制度变迁与制度持续受到的限制,同时它还必须有助于研究过去的制度为什么、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续制度。阿纳·格雷夫认为通过深究制度、制度因素和相关行为之间的内部相互关系,能扩充原来关于制度自我实施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使之能涵盖源于内生或外生原因而产生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案例,也可以使我们能考察制度影响变迁速度的内生制度变迁。简言之,制度、制度因素与行为之间的区分能扩充上述研究制度稳定、惯性和内生变迁的框架。制度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是自我实施的(self- enforcing),但如果它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是(至少是)能自我强化的(self- reinforcing),而正是在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中,制度通过使准参量在更大或更小环境范围内运行的方式,使之发生内生变迁,这种积累的变迁最终意味着制度元素与相关行为间的不一致,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将会从内部发生。就制度如何影响变迁速度来说,一项制度能够以两种但不是相互排斥的方式影响其变迁速度:即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当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导致新行为或制度因素出现(它们的出现并不取决于外部的和环境的变迁)时,制度会直接影响其变迁速度。当制度对外生的和环境的变化变得或多或少地敏感时,就是说当它影响到那些会引导其变迁的重大外部冲击的性质和数量时,制度会间接地影响其变迁速度。⑤
格雷夫和莱廷的内生变迁理论存在一些具体问题:(1)他们所提及的准参量只能通过经验分析来辨认,使他们的理论模式失去了预测行为的能力,放弃了博弈理论研究的演绎方法。(2)研究者如何知道为博弈的每个阶段所选择的时间段(timeframe)是足够长的,能对参量与准参量做出区分。如果研究者运用的是不正确的时间段,那么这种方法就不能从参量中区分出准参量,就可能受到和常规博弈理论一样的批判。(3)研究必须把制度划分为自我实施的制度和自我毁灭的制度,而内生变迁只发生在后者中,因此在制度失败之前做出区分是困难的。奥赖恩·刘易斯(Orion Lewis)等人认为,通过更多地运用归纳法和更明确地把焦点集中在变迁过程上,演化框架能避免上述不足。而演化框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制度的起源、稳定维持和剧烈变动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演化过程。
凯瑟琳·西伦认为“不时被打断的均衡”模式明显划分制度创立和稳定时期对研究制度发展没有多大用处,清楚地区分历史中的稳定时期与不稳定时期也是不明智的。相反,“更现实更精炼地分析来说,理解制度如何演进也许更富有成效,这些分析旨在寻求区分出特定制度构造的哪些方面是可重新修改的,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重新修改”。[28](P233) 因此,她对制度产生研究的特征是强调激烈的权力的分配性竞争,即政治联盟与政治冲突,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制度出现、存续、演化的政治过程。她讨论的案例证明,稳定与变迁的因素实际上常常是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的。这也是她主要用制度演化⑥ (Institutions Evolve而不是Institutions Change)来指称或研究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她指出制度是在一种由多重的,同时也是实用的和政治的需要所构造的背景中建立起来的。结果,为了服务于某一特定利益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常常成为其它利益的承载者。从建立有目的性结果的制度意义上来说,制度建立者通常不只做一件事。这有助于我们解释制度的权力分配方面的起源与发展。制度也远不是自动再生的,在一些案例中,适应部分社会行动者原来的制度创新的潮流,在强化现存制度的同时,很可能促进对制度的进一步修改。……换言之,在关键节点上,旧制度不一定被废除和被取代,而经常部分地或整体地被重新校准,或者是进行功能改宗。[29](P33) 制度一旦形成的确会对置身于制度中的行动者的策略与计算及其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然而,正如权力分配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是正在进行的政治竞争的目标,制度所依赖的政治联盟中发生的变化会驱动另一种变化,即制度在政治社会中起作用时所采取的形式的变化。她的研究展示出与路径依赖明显不同的另一视角,即强调制度发展的竞争性质,这样可以揭示驱动制度产生、再生与变迁的政治动力。总之,西伦的研究展示出了一种通过正在进行的政治谈判而产生的制度变迁的模式。制度持续与变迁的因素非但不能被分开成一种交替的次序,在这种次序中或持续或变迁(更不用说是行为与结构了)占主导地位,而是从经验上来说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面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转换,制度的存续常常涉及作为特定制度安排基础的联盟的重新谈判,即使这些重新谈判会驱动这些制度的形式和制度在政治与市场中的功能发生变迁。[30](P34-35)
与凯瑟琳·西伦的分析不同,奥赖恩·刘易斯等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分析了理性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存在的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它们对制度变迁解释的缺陷。他们借鉴从演化生物学关于生物演化的基本观念,建立解释偏好起源和制度变迁演化的框架。他认为演化框架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个体、制度和环境经常以一种复杂的适应性演化方式相互作用。换言之,渐进变迁而非均衡是制度的典型方式。“相互依赖和独立”变量实际上是人为做出的区分。演化方式的类型既能解释制度发展,也能解释制度变迁过程。如果我们从长时间段来观察事件,那么个体与其环境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我们的环境是经常变化着的,我们也经常改变我们的环境。演化框架能让我们理解内生变迁和外生变迁的源泉,也能让我们理解这些变迁源泉是如何在一个增量过程中相互影响的。[31] 在演化框架看来,内生制度变迁的源泉来自复制和选择过程(replic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es)。首先,制度的不完整复制产生的结果是历时性渐进。正式制度规则像基因一样,并不能完全决定制度如何被复制,这就像某人的父母的基因构成并不能完全决定其孩子的特征一样。新的个体们在某个制度中拥有正式位置,规则会约束他们,但他们也会与其前任采取不同的行为。因此个体转向是制度不能被完整复制的一种方式,会引起制度的增量性变迁。在适应性系统中,内生制度变迁的另一种源泉是发生在制度与环境两个层面上的选择(selection)。如相关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变迁的可能源于法律规章的环境以及它们给予某些组织优于其他组织的特权。这些层面上的选择和不完整复制之间的摩擦是内生制度变迁的主要机制。把复杂的制度变迁归结为上述摩擦似乎过于简单,不过这种研究路径更接近于制度变迁的现实,就此而言,它是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总体来说,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正在超越原来的“不时被打断的均衡”模式与路径依赖理论,它将着眼点放在制度演化的时空过程上,强调各种相关内生和外生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使与原来强调一种或几种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方法区分开来。然而,这些努力也可能因引入过多其他因素而使其对制度变迁论证失去“制度主义的特征”,从而使其对制度变迁的论证成为一个“拼凑物”,甚至是走进“死胡同”。[32](P137-145) 不应否认的是,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目前还处于开拓阶段,要使这些理论努力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大量的后续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将是不可或缺的。
五、从权力角度解释制度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对以政治制度研究为中心对象的新制度主义来说,权力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论题了。研究政治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制度看作是自愿合作以解决集体行动和共同利益问题的一种结构,但实际上,在政治市场中的制度往往与经济市场中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是政治市场基于非对称性的、受时空局限的权力关系,而经济市场主要基于相对对称的、平等的、可自由出入的权利关系。⑦ 政治过程常常产生的制度对某些人来说是好的,而对其他人来说是坏的,这取决于谁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制度之上。这样看来,政治制度“也许是合作的结构,但也可能是权力的结构”。[33](P213-253) 因此,正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en)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理解权力的逻辑,目前自愿交换理论并不能解决这类问题。
新制度主义学者曾对权力与制度的关系作了若干分析。如North已经指出过,如果统治者能够选择“正确”的制度,如果他们能够保护产权,那么经济会增长,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受益。然而,统治者通常并不选择这种使多方受益的路径,部分原因是它可能威胁到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他们常常建立那些掠夺性的,对社会来说是无效的制度。Robert Bates在研究肯尼亚统治者与产权制度形成时,发现政治权力能够产生使社会多方受益的制度(如产权制度)与结果,但即使如此,他的主要议题仍是权力与合作是密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的,如果制度不被承认,那么就不能被理解。玛格丽特·列维以新制度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政治制度是由权力不对称形塑的,它们所保护与促进的那么有权势者的利益。[34](P402-418) 罗伯特·贝特斯(Robert Bates)和玛格丽特·列维把权力带入研究的中心,推进了理性选择理论,但并没有担负起挑战理性选择分析的更基本的任务。纳特(Knight)是向理性选择分析发起挑战的第一人。他从个人选择与策略互动为起点,认为对制度的最好解释,不是把它解释为是为了解决集体目标或利益的一种帕累托最优,而是为利益分配而进行冲突的副产品。[35] 他的目的是表明制度理论是如何源于讨价还价关系与权力的不对称,而权力的不对称形塑了制度结果。他的分析是为了把权力结合进经济理论基础,并没有具体涉及政治制度。纳特的分析成功地唤起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基础的注意。但是他的分析并没有对理论变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原因之一是他只关注非正式社会制度,而对构成国家的正式政治制度关注不够。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讨价还价的分析,几乎是对个人如何争夺利益分配的分析,而不是对使一部分人获益,而其他人受损的再分配(或强制与暴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后一原因,他的分析发生了什么变化仍不清楚,Knight其实是有意忽视了这一点。理性选择用来分析自愿进行利益分配的讨价还价的框架,并不能把损失强加给非自愿的牺牲者,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体看来,当政治学者把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纳入对制度的分析时,很自然地想到了权力的角色,但对权力的关注还是不够的。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特里·M·莫(Terry M.Moe)进一步分析了权力与制度的关系。他认为在特定政治空间与时间内,赢者通吃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使社会福利长期无效的政策、制度也会存在。因为政治权力运作的逻辑与经济权力不同。能产生有效政策或防止无效政策的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只有在交易成本非常小或不重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但按新经济学的解释,交易成本是非常大,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是它分析制度的基础。如果政治中的交易成本很大,很重要,许多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可能并不得以维持,补偿可能根本得不到支付,政治结果可能是无效的,对胜负双方都可能如此。更糟糕的是,平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受损者的情况也可能变得更差,因为对方掌握着公共权力。
现代政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空间的博弈场所,这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制度会强制所有公民(主动的或被动的)参与政治博弈,自然而然地把博弈结果强加于所有利益相关的公民。因此,即使在成熟民主制度下,上述情况也经常发生,甚至支配着政治制度的运行,决定着制度的价值指向。⑧ 特里·M·莫指出民主制度的共通之处,通常并不是使受其影响的多数人民合作或共同获益。民主制度涉及权力的运行。主要的原因是,建立和设计受雇的公共权威机构,可能被在立法机构(通常是多数派)获得支持的派别控制。不管谁赢得了以所有人的名义进行决策的权力,不管谁是失败者都必须接受获胜者的决策,这是由以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法律所要求的。这意味着任何靠正式规则获胜的集团,都可以合法地运用公共权力迫使官僚制度从结构上为自己所控制,这种官僚机构也许会使失败者每况愈下,甚至是损失惨重。这样看来,官僚机构是由获胜者强加于失败者的制度。但对同意建立官僚机构的人来说,它们也是合作性的,是互利的。实际上,每种属性都是基于另一种。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合作,通过合作,获胜者能够利用公共权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成员。正是对掌握权力的期望,激励获胜者进行合作。因此,制度理论需要认识到权力不仅在内部人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其他人的努力中,而且在他们内部努力达成契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36](P215-233) 那么如何使权力对理性选择来说更重要呢?并没有给出具体而完整的解决办法,只是指出了需要对权力做出基本的界定,需要说明权力关系。不过在特里·M·莫的讨论中,把与权力和制度相关的行动者分成制度的受益者和受损者,这对解释制度的自主性、效用及其价值指向问题提供了某些启示。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是重要的,决定着行动者的选择范围、行为偏好及其序列、行动能力。但制度并不会自动产生效用,它的效用表面上看起来不仅取决于内部特征,也取决于行动者运用制度的方式,还取决于外部因素,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对制度采取什么样方式予以回应。如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强度(the strength of institutions),部分地与支持相关,而支持主要是指向那些可以博得社会欢心的制度。[37](P717)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制度重要、对谁重要、对不同的行动者哪些制度更重要、制度的重要与否由什么来决定等具体问题,否则“制度重要”就是空壳,不能说明制度的实质性问题。同理,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具有自主性观点,我们也必须进一步讨论制度自主性的来源、不同制度的自主性有什么不同、制度的自主性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等问题。特里·M·莫的研究提示我们,对于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同一制度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同样,制度的自主性也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来自能从其中获得利益的行动者的支持。⑨
上述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学者们考虑,需要系统研究”, “当我们描述外部支持者(external constituency)在某一组织生活中起部分作用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们会遵守规则,制度化将会因此‘自主地’、‘在短时间内形成’。实际上,制度化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这解释了制度化为什么是政治科学家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尽管如此,制度化概念并没有受到令人满意的系统研究,这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事。”[38](P717;725)
六、新制度主义的整体拓展
除了上述对新制度主义原有某些概念与观点提出批判和发展外,近来学者们还提出了不少更新颖的制度主义模式,主要有过建构制度主义、网格制度主义和实践制度主义。
(一)建构制度主义(Const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科林·海(Colin Hay)认为,现有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并没有摆脱理性选择的理论范式,而理性选择固有的还没有完全克服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对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研究的完整性与完善性。[39](P221-256) 因此,他试图解决制度化完成后制度变革(post- formative institutional change),特别是与非均衡动力相关的制度变迁问题。实际上,建构制度主义相当地强调社会制度的潜在无能与低效特征,强调制度主题与政治斗争的焦点,强调这些斗争的随机性,斗争结果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是源自其现存的制度背景。从这种建构制度主义角度看,制度变迁存在于行动者及其所在背景关系之中,存在于制度“建筑师”、制度化主题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之中。更具体地说,是从策略行动与构想行动的策略背景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的,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变迁结果都是在策略背景展现出来的。与正统新制度主义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建构制度主义不仅强调制度的路径依赖,而且强调观念的路径依赖。换言之,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观念,正是观念是制度的基础,为制度设计与发展提供信息,对政治自主权施以约束。制度是建立在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对制度的后续发展起着一种独立的路径依赖作用。建构制度主义还试图确定、详细弄清和探询,通过规范化和制度的嵌入(institutional embedding)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已经确立的观念被法典化,并起着认识过滤器的作用,而行动者正是通过这一过滤器来解释环境信息的。但关键是,建构制度主义也与环境有关,在这种环境下已建立的认识过滤器与范式是相互竞争、质疑与代替的。而且,建构制度主义还把范式转换看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变迁。[40](P57-65)
(二)网络制度主义(Network Institutionalism)。网络制度主义的假设:第一,从关系的角度(relational perspective)研究社会政治与经济等行为。与从个人、群体或组织态度的品性角度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不同,网络制度主义者强调关系(relationships)是基本的解释单元,而且这种关系是不能化约为个体品性的。第二,关于复杂性的假设。连结个人、群体与组织的关系被认为是复杂的。群体与组织间的界线并不清晰,也不一定整齐划一,而常常是相互渗透的。第三,网络既是行动的资源,也约束着行动。作为资源,网络是动员信息与援助,以追求特定目标的渠道;作为约束,网络是限制行动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控制的结构。第四,网络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信息、社会影响、资源与社会资本进行动员。网络路径之所以适合用来研究政治科学在于:(1)政治科学家很早以前就对权力与影响通过个人关系渠道起作用的方法感兴趣了。(2)政治科学中的许多问题都关系到利益集团、公共机构和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关系和平等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同盟”、“派系”、“联盟”等,但网络制度主义认为简明的联结方式对解释政治结果是重要的。(3)网络制度主义反对任何把个体主义与群体解释方法简单分裂开来的做法。它坚持认为必须从背景来理解个体行为,但反对有机群体的假设,因为这种假设是以一种静态视角。[41](P75-76) 网络制度主义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可能更适用于诸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的政治。比原来把制度定义为观念、规范、组织等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当然,网络制度主义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网络的界定不清楚,网络更适合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而不是解释。
(三)实践制度主义(Practical Institutonalism)。我们之所以去理解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是因为有许多实践方面的原因。关于传统的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这些问题,已经有大量的认识。但制度能做的,远非仅仅是人们协调其活动,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制度还能有助于建立和转换目标本身,此外,还有助于转换行动者(agents)的认同与对自己的认识。对新霍布斯主义者来说,还有可能存在使集体行动的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的麻烦事。如果不能确定行动者所渴求的目标,那么就很难理解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得到根本的解决。但观察的角度越宽,制度越可能提供能认识和解决新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有吸引力的前景。实践制度主义认为知识对政治导向的变迁具有杠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代价的。代价从经验相似性来命名的,或说关于制度结构与人类动机以及二者关系的假定是不准确的。
对于设计制度问题,实践制度主义认为制度通常不是被设计的,而是按因果或其它程序发展或演化的。一般认为英国宪法或罗马共和国宪法是演化而来的,被认为是来自社会规则与阶级的斗争的演替。而实践角度对制度采取我称之为的“设计视角”(design stance)。它也许可以与由英国或与罗马的例子而约简出来的因果视角(causal stance),以及解释视角(interpretive stance)区分开来。如果我们试图解释美国宪法的创制,那么自然地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设计观”。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美国宪法的最初创制解释为只是设计的结果,而没有其他背景或因果因素起作用。解释性视角把制度变迁看作是受规范(norms)或价值观的控制的,这些规范与价值观是在制度的一般机能中产生或演化的。实际上,解释视角也是设计视角,不过它主要是关于自然产生的或主观目标,而不是本来先于制度设计的目标。[42](P72-77) 总体来看,实践制度主义远没有形成一种具有独立特色的理论,其论点与立论过程都比较模糊。
七、评价性结语
上述新制度主义的拓展大大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及其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不过,新制度主义这些理论努力并没有解决制度变迁研究所需要解释的全部的旧问题,甚至某些新的解释还带来了更棘手的问题。
第一,新制度主义的关于制度及制度变迁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通过把观念、权力、环境纳入对制度的分析,增加制度主义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力,但同时这些概念并不是制度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其它任何理论都可以运用的,因此用这些概念来清晰地解释制度变迁等问题面临不少困难。正如阿尼尔·海勒(Anil Hira)和罗恩·海勒(Ron Hira)几年前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一个由诸如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构成拼凑物,被用来以不明晰的方式解释变迁。实际上,应该直接而不是通过制度代理研究这些用来解释变迁的因素”。[43] 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这些任何理论都能运用的概念纳入对制度变迁等问题的解释,可能意味着“放弃它们在解释政治现象时所强调的制度首要性”,[44](P137-145) 即可能损害制度主义本身的“制度”特征,我们不禁要问,新制度主义还是以制度为中心变量的研究方法吗?
第二,个案经验研究与普适性制度变迁理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也没有完整的解释。著名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列维在2006年美国政治学学会年会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缺少一种动态理论,即一种把转型机制内生化的动态理论”。[45] 在笔者看来,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还是行动者的利益。尽管行动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从长时间段来说,行动者大体还是能够辨清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从与制度相关的行动者的利益应该是研究制度变迁最佳切入点。当然,这还需要与制度、环境、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结合起来。
另外,就新制度主义内部而言,不同分支之间的融合面临着方法论上的障碍。就新制度主义外部而言,对制度主义的整体性拓展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要使这些理论努力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大量的后续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将是不可或缺的。在开拓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变量与参量时,对自己的论域及其适用范围作出界定是必要的,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引入过多变量可能会导致新制度主义失去自身的“制度”特征的问题。
文校编辑:康宁
收稿日期:2008-07-20
注释:
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Ove K.Pedersen就比较全面地指出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存在的九大问题。参见Ove K.Pedersen,Nine Questions to A Neo-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Vol.14.No.2,1991.P.125-148.
② 但需要补充的是,这并没有代替它们先前的重点,即分别强调偏好是宏观历史结构的结果,偏好是被输入特定行动者的。
③ 在Mark Irving Lichhach,Alan S.Zuckerman等学者提出,在比较政治中,关于方法论的议题亦有持续不断的辩论。当比较研究者提出了涵盖若干案例,以因果叙述为基础的解释时,他们必须处理与理论建构、概念形成,以及案例选取等相关的问题。例如,一个概念如何能够普通地适用于不同案例?将概念视为可以用各种指标测量的变项时,其价值为何?当我们将特定的案例的资讯运用于涵盖许多案例的理念时,该如何适当地使用这些特定案例的资讯?是否有任何要件与判准存在,使我们得以此要件与判准来界定需要被含于分析中的案例数?单一案例研究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为何?单一案例研究如何才能够被用来指涉普遍性的静现象?是否有可能(或是否可以期待)将所有相关的例子皆涵盖于分析中?是否有可能想出一种适当的方法,使我们以少数案例的观察为基础就能推展出强而有力的通则?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有关外在效度的问题。所谓外在效度指的是从观察的个案进一步通则化的能力。Mark Irving Lichhach,Alan S.Zuckerman,《比较政治:理性、文化与结构》,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页。注释2。
④ 例如安德鲁·科特尔(Andrew P.Cortell)、苏珊·彼特森(Susan Peterson)、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阿纳·格雷夫等人在其新近的研究中,或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框架,来研究制度的起源、持续、内生变迁与过去制度对后来制度的影响,或试图为理解民主国家中的制度结构变迁(不管是一时的还是渐进的)提供一种对普适性框架。参见Andrew P.Cortell,Susan Peterson,Altered States:Explaining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9,No.1 ,(Jan.1999),pp177-203;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Introduc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in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edited by Wolfgang Streeek and Kathleen Thelen.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Masahiko Aoki,Endogenizi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es (2007) ,3 :p.1-31 ; Avner Grel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⑤ Avner 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ter7.Avner Greif 指出,尽管制度可以自我实施,但通过这一过程制度破坏它们自己的自我实施似乎是有具体例证。更具体地说,因为几乎没有相关分析专注于从上述角度研究这种过程,迄今还没有人概括这一过程。本书的第七章对这一过程的初步的尝试性概括。
⑥ 政治科学的分支领域经常运用“演化”一词,不过政治科学家几乎没有阐明它的准确意义。它常被用来指称渐进变迁概念,其主要特征长期细微增量变迁的渐进积累性。Orion Lewis,Sven Steinmo,Jessica C.Teets,Evolutionary Theory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Politics,http://www.itsmyev.eom/cv/Teets-Jessica/research,htm.
⑦ 关于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差异是一个更复杂问题,关于它的讨论可参见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un 2000,Vol.94,No.2,p.251-267 ;Terry M.Moe,Power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No.2 (June,2005),p.215-233.
⑧ 基于社会契约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循环多数、甚至是循环少数的问题,及由此带来的那些使社会福利长期无效的情况,是民主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没有(也许根本不可能)得到理论清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关注制度正义性或说制度价值偏向的政治理论或分析框架,都不能绕过这一问题。
⑨ 当然,对利益的界定与认知会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细致分析的问题了。
标签: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前景理论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