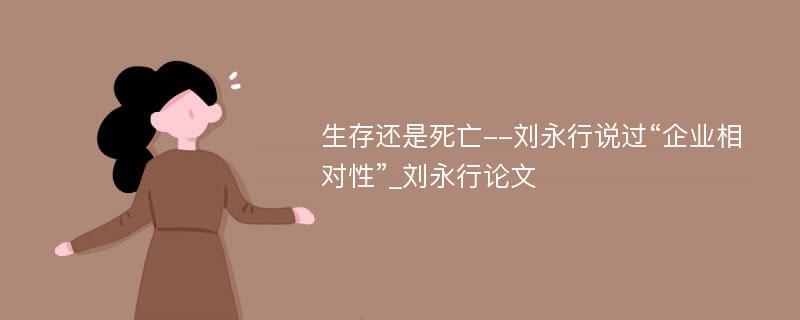
生存还是死亡——刘永行话说“企业相对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话论文,相对论论文,刘永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正遭受着严峻的市场考验,外有跨国公司的虎视,内有国企复活,而旷日持久的市场萧条更使诸多企业如临深渊。企业界有识之士提醒,真正残酷的市场竞争不过刚刚开始。
如何在最困难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生存下去?这个问题让每个企业家都头疼不已,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归纳他与国外财团多年交手的体验和中国企业起落成败。提出用“企业相对优势论”的思想抗御市场风险,保持企业持久的活力。日前,刘永行在成都向记者全面介绍了他的这一新理论。
“企业相对论”无时不在
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不是资金、技术,更不是规模
记者:最近你经常谈论企业的相对优势,有相对优势便有相对劣势,我们姑且称之为“企业相对论”,你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怎样升华出来的?
刘永行:我去年才考虑到企业的相对优势问题,发现这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许多企业失败并非是资金不行,也不是技术落后,更不是规模不够,而是企业没有相对优势,也就是说企业没有把生产、经营、销售体系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我国投资的大化肥厂,每个厂生产能力50吨,投资32亿元。认真算一算就会明白,32亿元每年折旧费为3.2亿元,还款利息每年3.2亿元,两项加起来共有6.4亿元。仅此两项费用每吨化肥需摊成本1280元,当时工厂投资时每吨化肥市场价为1800元,而投产后跌到1200元,因此企业不用说盈利,正常折旧、还款都不可能。我们不能把企业亏损原因仅仅归咎于市场疲软,因为在同样环境下,德州市一个年产18万吨化肥的乡镇企业,年创利润几千万元。因此说那些国家的大化肥厂投资时仅仅考虑到技术的先进性、投资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就是没有考虑企业相对优势,没有考虑市场变化。
记者:我理解所谓“企业相对论”是指企业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之路,那就要在相对的环境下考虑问题,比如说市场疲软是绝对的,但增加市场份额却是相对的,说到底就是企业在任何条件都应有所作为。
刘永行:应该说,在经济工作中处处会遇到相对的问题、相对的优势、相对的竞争,经济“相处论”的精髓是说要把企业建立在市场经济、竞争经济基础之上。企业能否生存下去,它不是政府、银行、领导决定的,甚至不是企业董事会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的用户决定的,而是看企业能否相对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价值与价格之比的产品。
记者:你所说的价值与价格之比是什么涵义?
刘永行:这个概念有点像性能价格比,我们衡量产品好坏,要看它给消费者、用户带来什么好处,对消费资料来说是指使用的方便程度,对生产资料来讲是指综合效益。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下,建立在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基础上,因此产品的价值要同价格相比。
景气与萧条时的“企业相对论”
反道而行与正道而行
记者:时下,商品跌价与商场倒闭势不可挡,大部分生产企业对市场萧条叫苦不迭,各行业普遍生产能力过剩,“买方市场”与“微利时代”成了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企业生存应该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刘永行:市场疲软绝对是坏事,但坏事也会转成好事,企业也能在不利的大背景下确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市场疲软搞得大家都唉声叹气,但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考虑能否在绝对数字下降时扩大相对的市场份额。下大力气研究市场、开发市场,等市场恢复后,市场就是你的,而不是人家的。市场疲软实际上正是企业大练内功的绝好时机,因为这时候,人员和时间都相对富裕,市场景气时根本没时间、没精力做的工作现在终于有机会做了,可以抓职工培训、机器检修、合理化建议、降低成本和深层次开发市场等诸多问题。
记者:对企业而言,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但市场疲软确是检验企业生存能力的试金石,此时可以检验出企业是否具有相对优势,是否有长远打算?
刘永行:市场疲软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哀叹的,因为你日子难过,你的竞争对手也是如此。去年一季度,饲料市场非常好,我们比去年同期销售增长60%,我告诫职工:“不要高兴太早,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如此。”
5-6月份市场进入低谷,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的相对优势才会凸现,可一进入7月份,市场又恢复了,我意识到我们淘汰对手的机会过去了,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活过来了。
记者:市场疲软实际上是考验企业能否输得起,传言不久前你在南方发表讲话,称“希望”准备了20亿元迎接3年的亏损。
刘永行:作为低利润的饲料行业,外资企业非常强大,他们考虑不是眼前的赢利,而是3-5年后的市场份额,国内也有近万家饲料企业。我希望市场疲软能持续2-3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只是增长慢一点,而与此同时,大批没有长期打算的企业纷纷倒闭,诸多外资企业巨额亏损,我们迎接3年市场疲软至少要有20亿人民币的资金规模,否则到了2010年,外资企业吃透了中国国情,渡过了难关,资金实力和商誉均成上升趋势,我们与之对抗要多付出几倍的代价。
“企业相对论”是知彼之长克己之短
竞争是要自己比别人好而不是希望别人死
记者: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涌入中国对国内企业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很多企业惊呼“狼来了”,“与狼共舞”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无法逃避的现实。
刘永行:这些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个个都是来者不善,志在必得,他们几乎都是战略性投资,开始以抢战市场份额为主,准备几年后赚钱,这无形中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不要为其财大气粗所迷惑,初期竞争时我们占有相对优势,因为他们即使巨额亏损也占领不了市场,而我们相对成本低可以打开市场。很多国外企业规模大,但运转不灵,销售盈利率和利润率都很低。外资企业投资饲料行业动辄1-2亿元,资金成本过高,这恰恰是他们的劣势。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要按中国的模式运行,他们那一套不行,可以说在学我们的坏处。我们要实施同外资企业和跨国企业完全相反的谋略,我们的企业初期要有适当利润,通过三五年积累后把企业规模做大,等外资企业和跨国企业要利润时,我们开始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抢市场。我们并不追求规模越大越好,只是追求适度规模,在强大的跨国集团面前找出生存之路。
记者:如何同国外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对此你有丰富的经验,因为希望饲料一直是同外资企业面对面交火中成长起来的。
刘永行:1988年我们涉足猪饲料市场,当时正大几乎成为神话,国内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猪饲料只有国外企业才能做。但我们始终认为猪饲料并不神秘,自己用土设备生产出来后,一算成本有很强的竞争力,当时市场呼唤价格低一点的国产饲料,这给了我们机会。我们用几个月时间便同成都正大打了个平手,正大开始对付我们,连续两次每吨降低20元,我们跟着降价,等到第三次再降价时,我们一下子降了140元,正大不敢再降,这就等于退出了四川省的饲料市场。1990年3月底,我们月产饲料4500吨,一下子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饲料厂。从1990年到1995年初,我们的饲料厂门口前一直排长队,我们没有仓库,所有原料都是别人送来,一直到1992年,我们没有采购员,只有一个原料部负责人打电话联系,没有管理人员,没有推销员,没有会计,没有出纳,没有流动资金,周边地区的每个粮食部门都成了我们的仓库,都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
记者:你去国外考察同行企业,能否谈谈国内企业同国外企业差距何在?
刘永行:1992年我去美国一家饲料企业访问,这家企业每天生产饲料160吨,只用7个人,这个印象深得不得了。我们“希望”当时日产饲料300吨,用了100多人。当时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但直到1997年才琢磨出来。我们同美国相比,不是差在资金、技术和设备,而是差在国民素质上。因为这家企业根本没有验货员和化验员,他们凭的是契约关系,厂里也没围墙,厂长集守门人、保安、收货人、出纳、会计于一身,还负责微机操作和贴标签。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过商品社会的契约经济和合同信用,我们对人不信任,因此要有庞大的审计、出纳、会计等制约和监督体系,这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些,每个员工的工资肯定要翻番。
记者:在同国外企业竞争中,你的“企业相对论”追求什么样结果?
刘永行:优秀企业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是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好,而不是希望别人不好。我们与跨国集团的竞争是为了确立我们民族饲料工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他们好的地方我们要认真虚心地学习。世界上最大的饲料生产国应该是中国,世界上最大的饲料生产商也应该出现在中国。拿到这个第一的是谁?有可能是希望集团,也有可能是跨国集团,如果我们在竞争中被挤垮,那是我们的耻辱。
“企业相对论”如何化解风险
企业经营与经营企业的商誉与效益
记者:从1992年开始,希望集团开始在全国购并企业,进行低成本扩张,你提出了变企业经营为经营企业的概念。
刘永行:我们一直想把“希望”做成名牌,并提出了“让农民富裕,让市民满意,让政府放心”的口号。从1991年开始,全国相继有上千封来信要求我们去当地投资,这同我们渴望快速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安徽等10多个省市兴办了40多家合资合作企业,个个成功,家家盈利,一至两年均收回全部投资。
记者:从近两年许多企业的失败可以看出,失败的原因不是产品不行,而是分裂式扩张后,管理和干部跟不上,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应该说风险很大。
刘永行:“希望”1995年在全国发展了10多个合资合作企业,1996、1997年又是高速度发展,这样做的确冒了很大风险,但不这样做就占领不了制高点。我当时非常清楚毛病在哪,不是资金问题,资金不够可以贷款,而是管理不到位,派不出合格的高素质干部,但我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
1995年我们在河北省办了一个工厂,当地一路绿灯提供优惠条件,但企业1-5月连续亏损,我当时非常清楚毛病出在哪里,就是没有合格的干部,这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认为“希望”不过如此,甚至怀疑“希望”是不是来骗钱的,政府领导是不是受贿。后来我派了一个跟随我多年、年仅16岁的工人任总经理,同时在社会上招聘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副总经理,他们把“希望”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带了过去,很快便扭亏为盈,成为了当地的典型。
记者:有些民营企业在实施低成本扩张时,除了权衡市场因素外,都热衷于同当地政府拉关系,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永行: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着眼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所以说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
记者:希望集团的扩张实质上是品牌的延伸,但如果哪个企业搞砸了,麻烦也就来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永行:商誉是个巨大的无形资产,不能卖钱,更不能透支。1996年由于市场疲软,上海“希望”屈从了一些经销商的要求,降低了价格,同时也降低了质量。1996年底销售额明显下降,1997年初丢掉了2/3市场,经销商有奶便是娘,可客户骂我们。后来下大力气扭转局面,到1997年年底才有1000万元盈利,其中400万元是对企业挖潜找出的。
“相对论”与“绝对论”
中国企业要“简单”还是要“复杂”
记者:希望集团在经营理念、用人之道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成就了集团的相对优势。
刘永行:不随大流是我们的一贯做法。比如说大家都在抱怨市场不规范,其实市场不规范就是商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讲商誉,而我们大讲特讲,我们便鹤立鸡群,便确立了我们的相对优势。反过来,如果大家都守契约,便显不出我们。实际上我们做的不过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别人便对你另眼相看,对你百分之百的相信,把你看成神似的,商誉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很多企业抱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念头,进入了多元化经营,希望集团何以对此无动于衷?
刘永行:中国的企业成功在于“简单”,失败在于“复杂”。“简单”在于资源集中,主业突出;“复杂”在于投资分散,主业不突出。多元化经营既有诱人的前景,又可能是一个大陷阱,搞不好就会栽进去。我们的投资都要做最坏的分析,要考虑一旦失败了,自己能否承担起这个责任,会不会损失我们的商誉,累及我们的根基。
记者:“希望”专用外行,不用内行,用意何在?
刘永行:我们有个原则,不去同行挖人。我们之所以不用内行,因为如果到跨国企业去挖人,待遇很高,既然你能用高工资挖走,别人将来也会用更高工资将其挖走。而且这样的人进入“希望”,整合起来也困难,他会自视高人一筹,难以执行“希望”的管理、纪律和规范。许多国营饲料行业的厂长、经理前来应聘,我们从来不用,用他们什么?管理方法肯定不行,假使他们优秀,早把企业搞好了。我们从非饲料行业招聘企业的厂长、经理、车间主任,我们用人一般“跳槽”三次以上的不予考虑。
记者:外行真能管内行吗?
刘永行:外行不懂技术,我们可以给他配备生产部、销售部、技术部人员,我们看重是他的廉洁奉公和努力学习。外行通过努力学习可以转变成内行,而一旦成为内行,他便成了希望人。我们的干部都很年轻,许多人30多岁便当上总经理。
记者:如何看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刘永行:不光做企业,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风险,不对企业承担风险的人就不成其为企业家。企业家同资本家、企业管理者是有区别的,有些创业者不一定是企业家,他只不过抓住了一个暴富的机会,并不能把企业做下去。企业家说到底是个辛勤的劳动者,是以企业为生命的人。
标签:刘永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