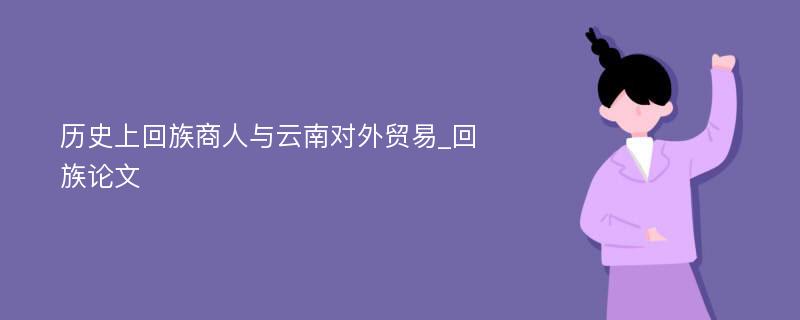
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云南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云南回族商帮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云南回族商人与缅甸等国的贸易始于元代,之后不断发展,至清代中期以后达到高潮,出现了一批回族商帮、商行和商号。回族商帮的足迹遍及我国西南地区,以及邻近的东南亚、南亚等国,为发展云南的对外贸易做出了贡献。
云南的对外贸易主要为回族的西南支即大理及其周围地区的回族所从事。云南回族商帮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在我国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及缅甸、越南、老挝、泰国、印度、尼泊尔等国都留下了足迹,并有部分回族定居在云南邻近国家。回族商帮的对外贸易活动,不但促进了历史上云南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拓展与繁荣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
云南的回族商帮形成于近代。在此之前,回族对外贸易的货物是靠马帮运输。马帮商队的头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马锅头(马帮的首领),又是行商,依靠长途贩运作为赚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因此,回族商帮的兴起与繁荣,与马帮运输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一些回族商帮就是靠马帮长途贩运发展起来的。
云南的回族马帮,主要是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开展与我国四川、西藏地区,及缅甸、泰国、老挝、印度等国的贸易。作为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份,云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其他地区与南亚及东南亚各国或小邦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地。通往境外的商道起自昆明(云南府)、大理、腾越(今云南腾冲)以及南部的思茅等地,向西和向南蜿蜒伸展,穿过崇山峻岭,向西由西藏地区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国,向南则抵达缅甸、泰国的富庶平原,直到其最南端的一些港口城市。在云南人看来,贸易先是趋向于南方的,而由于云南回族逐渐在这一长途马帮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他们的聚居点及清真寺在许多云南的城镇里也是趋于向南郊发展。到18世纪末叶,云南穆斯林商人马帮的足迹已遍及印度阿萨姆、缅甸、泰国和老挝,以及中国四川、贵州、广西等省的广阔地区。虽然有许多汉族及山区各少数民族参与了这种贸易,但有资料表明,这种长途马帮贸易最初是回族穆斯林的特有行业。这些商道在沟通云南与邻近东南亚诸国联系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回族定居在缅甸、泰国及老挝山区。[①a]
可以看出,回族马帮商队贸易的重点首先是南方,由此沟通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国的贸易。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回族商人也注意到了另一条贸易通道,即由云南、四川经西藏到达印度的“茶马古道”,并拓展了与印度阿萨姆等地的商业交往。“茶马古道”是历史上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起自云南的普洱等地,南北穿过整个云南,又经四川、西藏,最后到达印度、尼泊尔等国。[②a]
云南回族商人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北部之间的陆路贸易始于元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回族在此时期进入云南,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元代云南及其通向邻近国家站赤(驿站)的设立。[③a]在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回族商人逐渐定居在当地,但他们大多仍继续从事长途马帮贸易。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失败以后,又有相当数量的云南回族商人迁居泰国、缅甸等国,推动了长途马帮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回族商队在邻近东南亚国家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广泛,并通过两条主要商路开展对外贸易。一条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经缅甸景栋进入现今泰国境内的清莱府,向西可达夜赛;另一条从思茅进入老挝的丰沙里省,先向南穿过琅勃拉邦省,然后向西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清迈地区。
云南马帮商队出境贸易通常是在旱季,即每年的11月至翌年4月,以方便途中行走。前往泰国清迈,他们带去的货物有胡桃、栗子、丝绒、布料和黄铜器皿;前往缅甸掸邦的景栋和八莫,他们带去的货物有毛织品、精美的棉布、地毯、毛皮和食盐。[④a]在同一季节,马帮商队向北返回,所携带的商货有原棉、宝石等,有时还有粮食。在货物运输途中,马帮商队要依赖那些商队必经之地的控制者,利用他们对道路的所有权,更重要的是要寻求他们的保卫和庇护。虽然商队常常是全副武装,但仍无法抵御沿途土匪和对其抱有敌意的地方土著的袭击。云南马帮商队的长期存在并通行于各条商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向控制商道的各种势力缴纳通行费。克钦山是征收这种通行费的最典型的例子。在克钦山地区的昔马、赛董和新仑等地,有许多用栅栏防卫的村寨座落在云南西部和缅甸胡康之间的山区,克钦贵族控制着这些村寨,通过对途经的商队收取通行费获得财富和实力。有时这种通行费是以食物缴纳,比如缴纳为短途商运而准备的盐和大米。[⑤a]另外,云南商人还不得不在其货物运进云南时缴纳国内税。这种税称为厘金,在商队进入云南边境城镇时征收。在每一个县地都设有关卡,根据商队运输货物的多少而确定厘金的数额。被山民或地方头人征收的过路费,通常是一些个人和团帮的收入来源。但是,过路费不能征收得太多,否则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就无利可图,任何商队也不愿意被沿途靠此为生的人对其进行劫掠。如果过路费太高,或者如果商队遭到抢劫,原来的道路就会逐渐被其他路线所代替。
马帮长途贸易需要掌握地理和低地中国人社会范围以外民族方面的知识,云南商人的生存和发财就是依靠这种知识。他们定居在云南的邻近国家,与当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因此,19世纪后期云南回族起义失败后,这些中国穆斯林并非作为陌生人进入东南亚,而是继续作为山区贸易者和中间商。[①b]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叶,云南穆斯林聚居区的中心已在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方建立起来,例如泰国清迈和缅甸佤邦的班弄。[②b]定居在城镇里的云南人主要是穆斯林,他们仍基本上保持着与马帮贸易的联系,而且还渗透到其他贸易领域。事实上,最早定居在清迈的云南穆斯林,可以被看作是当地的代理商;或者是以滇缅为基地的华人穆斯林贸易帮会的商务代表;或者是为了满足上述那些人以及来这里的云南回族马帮商队的需要而经营一些小客栈或清真餐馆的华人穆斯林小业主;或者在稍晚些时候作为社区的宗教领袖。根据S·松吞帕萨克的研究,最早定居在清迈咏芬区的云南回族移民,就是以一位名叫“崇·林”的回族人为首:“崇·林早年曾通过掸邦的景栋往返于云南府(今昆明)与夜赛、南邦、达府、南奔和清迈,从事马帮贸易。在迁居清迈之前,他与妻子从事清迈府西北的夜占与缅甸之间的贩运买卖。1915年,他迁到清迈城,并在暹罗国王通过清迈亲王赐给他的一块封地上定居下来。”S·松吞帕萨克认为,崇·林就是定居在清迈咏芬区的回族商人首领,并进一步说明:“他最初建造房屋的地址便是云南商贾装卸货物、落脚休息及喂养牲口的地方。”[③b]
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社区繁荣起来,并日趋扩大。除了继续参与长途马帮贸易以外,这些回族商人以中心城市特别是清迈、清莱和南奔等为基地,还渗透到各个零售行业,如出售水果、蔬菜、布匹及副食,经营餐馆和茶叶店等等,并开始经营玉器。由于他们的这些服务业,清迈以及泰国北部其他主要都市的云南回族,成为那些往返的马帮商队与平坝泰人之间成功的“中间人”,其中有些变得极为富有。例如回族商人崇·林,除了自己的贸易业务以外,他还与泰国地方政府签订过一项合同,通过他的驮队向清迈府一些边远地区分送牛奶。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得到了供应修建南邦——清迈铁路所需建筑材料的专卖权。后来,当铁路修建到清迈时,他还捐出大约100莱土地(1莱=2.4亩)用于修建铁路。鉴于他长期为政府服务以及他对公益事业的贡献,泰国王授予他“坤”的爵位封号,并赐给他一个泰姓:翁略加。坤崇·林·翁略加(此后他便以此名而广为人知)一直是清迈的一位富商和头面人物,直到1964年他93岁高龄时死于去麦加朝圣途中。[④b]
除了在诸如清迈、清莱、南奔这类大城市与大集镇建立了“城镇云南人”的社区以外,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小镇及村子里也有许多“乡下云南人”在那里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寨中只有一、二户云南人居民,他们在那里最初是作为小店铺掌柜或货郎来满足当地泰人或山地民族的生活所需。至迟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人店铺掌柜和商贩们便在泰国北部乡下活跃起来,他们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作为回族长途马帮贸易的后继者,他们仍从事着相同的行业,只是贩运的路程已大大缩短。在马帮商队继续穿过泰缅边界,将玉石、宝石、茶叶等运往泰国,并将日用品和药品等运到缅甸的同时,泰国北部的这些回族商人大部分还充当着泰北各山地民族与清迈这类平坝商业中心之间贸易的“中间人”角色。他们最初活跃在沿缅甸与老挝边境的山寨里,特别是在清迈、清莱、难府及夜丰颂等府,他们同样也活跃在并不直接与缅甸或老挝接壤的一些山区,如清迈府北部的帕劳,偶尔甚至向南到达达府,并有人在那里定居。
19世纪末叶以后,定居在泰国清迈的云南穆斯林人数日趋增多。有些是从云南携家眷同来,有些人则在同非穆斯林华人或北部泰人女子结婚后,按照回族的习俗,其子女成为穆斯林。另外,云南穆斯林男子与南亚穆斯林(主要是孟加拉人)女子之间的通婚也是很普遍的。随着清迈的云南穆斯林社区的扩大,在当地也建立了一座主要为云南籍穆斯林所使用的清真寺,并于1917年9月9日正式开放。[①c]
二
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回族大多居住在城镇、坝区等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这就为他们进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而与境外的长途马帮商队贸易,又为回族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回族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云南逐渐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商帮、商行和商号,他们不仅从事对外商业贸易活动,而且拥有马帮作为进出口货物的主要运输工具,这也是云南回族商帮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清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代,云南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回族商帮、商行和商号。如在滇西方面,腾冲的“三盛”商号久负盛名。“三盛”系明清宠、马如灏、朱大椿合股创办,专营花纱、布匹和玉石生意,在昆明、下关、保山,及四川、广东等地都设有分号,生意十分红火。1840—1850年,明清宠3人首倡捐修潞江惠仁铁索桥,花费了数十万两银子,历时10年才完工。明清宠当时富甲一方,被称为“明百万”。[②c]
楚雄的回族擅长做黄金、布匹等生意。如马超群,在昆明、上海、南京、天津、香港,及泰国和缅甸等地都开有商号,资金数百万元。钱万一、马鸿义、马伯亮三兄弟等也都在泰国开设有商号。[③c]
下关回民马名魁曾在当地开有“福春”、“裕顺”、“泰来”3个商号,后又在四川宜宾、云南昆明及缅甸的仰光、曼德勒等地开了13个商号,还拥有一个100多匹骡马的马帮,往来于云南和缅甸之间进行贸易。此外,他还从事缫丝、印染等手工业及开采石黄等,产品直接销往国外。马名魁曾是当时滇西较有影响的对外贸易和工商大户之一。
在保山县,马润五曾开有“永丰祥”商号,有资本三、五万银洋,从事外汇和进出口贸易。自己备有汽车,雇佣工人,进口货物以棉花为主。
腾冲观音塘明绍林创办的“鉴记”商号主要经营进口棉花、洋纱等,在保山、下关、昆明、重庆和境外缅甸曼德勒等地开设有分号。
腾冲朱静亭在缅甸密支那勐拱设有玉石加工厂,并在中国的下关、保山、腾冲、长沙、上海、香港及缅甸设有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沙甸白亮诚在当地开辟了数千亩的农场,把内地的木棉、甘蔗、蔬菜引进到当地种植,运往个旧销售。另外,他还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成立了制茶厂,种茶树数万株,年产红、绿茶2万余斤,制成茶叶销往境内外。并在靠近边境的勐海县成立了纺织厂,自产自销,出售布匹。1938年,云南思普企业局成立,白亮诚出任经理。[①d]
在滇中、滇南方面,原信昌、兴顺和是两家较大的商帮。原信昌商号原是通海大回村马同惠、马同柱、马子厚、马泽如等人开设和经营的,地点初设在昆明,先经营长途马帮生意,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的商业往来相当频繁。1910年,为了发展思茅等地的生意,在墨江开设杂货店,沿用源馨斋牌号,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及泰国、缅甸的商品到墨江销售。并在墨江收购紫胶、獭猫皮、牛羊皮运销昆明。后来,原信昌商号又经营茶叶出口业务,“先到江城买茶,驮入老挝销售,并由老挝交木船运往越南销售;为了发展业务,又在思茅成立了原信昌杂货店,不久交给二仔马子明负责经营,他才前进到泰国去,并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地设立了几个货运点。此后原信昌即以墨江、思茅为主要基地扩大贸易经营,在思茅销售的货物,由昆明运到墨江后,从墨江按照需要拨到思茅来,进泰、缅的货物再从思茅拨出去。至于泰、缅、老驮来的货,能在思茅、墨江销售的则酌量留下一些,多数货由思茅、墨江转运昆明。老挝方面,由于大仔马子厚曾去江城买茶运销老挝并经老挝运销越南,得知许多石屏人在江城附近的易武揉制饼茶,经老挝、越南外销香港创出了牌子,很得利,于是由四弟到江城成立了茶厂,牌名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驮入老挝转运越南、香港销售。并在江城开一个百货店,销售的货物从墨江拨过来,于是江城也就成为原信昌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这里距离老挝较近,出入也很方便,饼茶驮入老挝后,即可交船转运越南、香港。”[②d]经过数年的发展,原信昌商号的业务基地,从昆明、元江、墨江、磨黑、思茅、江城以至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地连成一线,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业务也不断扩大。抗日战争胜利时,原信昌财产的总值达二万两黄金,其中60%为在国内外的流动资金和货物,40%为田地、房屋等不动产。
兴顺和原名“兴泰和”,1846年由玉溪大营回民马佑龄创办。因见玉溪农村妇女的土布生意有发展前途,马佑龄便由昆明购纱运往玉溪,在当地以纱换布后又运至昆明销售。进而将白布用土靛染成青布、蓝布出售,销路更好,不仅在昆明卖,还运往四川、贵州销售,均受顾客欢迎,生意日益兴隆。1855年,马佑龄前往麦加朝圣,取道缅甸、泰国等国学习和考察商务,后得知泰国清迈有洋靛,染布效果好,便组成马帮,到清迈采购,运到昆明销售,遂开始经营对外贸易。[③d]光绪(1875—1908)后期,马佑龄将商号交给儿子马启祥经营,商号更名“兴顺和”。除经营布匹、草帽、洋靛等外,还经营川盐,资金增至20多万银元,对内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先后在昭通、东川、曲靖、蒙自、个旧、文山、下关、保山、玉溪、墨江、元江、思茅、汉口、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号。在经营国内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兴顺和还与人合股兴办个旧锡务公司,开采、冶炼大锡,运销香港。马启祥被推选任公司总经理,他聘请了德国专家到个旧锡矿,改进了掘矿、吊车、运送、冶炼等设备及技术,不但增加了锡的产量,而且也提高了锡的质量,大锡也成为后来云南出口贸易中的大宗货物。[④d]由于成功的经营国内商业、进出口贸易及产销一体化,兴顺和商号发展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云南最大的三个商号之一,在当时云南的工商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以上回族商帮和商号,大多拥有自己的马帮,以方便从事对外贸易业务。另外,还有一些回族商人没有成立商号或商行,一直是利用专业性马帮开展长途对外贸易。如保山的马应才、闪春福、李行兰等马帮,每个马帮至少拥有100匹骡马,多时可达300匹,经营昌宁、镇康、耿马和缅甸之间的贸易。丘北县赛宝章家马帮,有200多匹骡马,从丘北经广西到越南进行长途贸易,带去的货物多为云南的中药材,返回时主要驮运食盐、百货在滇南销售。沙甸的马帮,最多时达到3000多匹驮马。巍山、通海、寻甸、玉溪、永平、洱源、砚山、德钦的回族,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马帮长途对外贸易。
三
虽然回族在元代才大批进入云南定居,但由于他们擅长于商业活动,所以很快在沿西南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中占居了一定的地位。马维良指出:“进入傣、藏、白、彝族地区的回族人通过马帮商业贸易在三条线路与邻国贸易,与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密切关系。第一条是通过大理、保山、腾冲到缅甸,再通过缅甸仰光出海朝觐、贸易。如白族地区土庞村回族,至今还有二十家归侨,三家在缅华侨。第二条是藏区回族人,从德钦县出发到西印度,或从德钦到拉萨、尼泊尔进入印度。至今在德钦升平镇回族坟地里还埋有二百年前进入我国的印度穆斯林老巴巴的坟。现在住在德钦县回族的老年、中年人中许多人去过印度。第三条是从内地经过思茅、普洱入西双版纳勐海,进入缅甸景栋、仰光出海到印度、阿拉伯国家。‘帕西傣’寨就是必经之地,他们开有马店,方便过往行商和内地回族到缅贸易。”[①e]
元朝在中国西南地区及邻近东南亚地区设置了驿站,到了明代,商道和驿站更加普遍和完善。以回族为主的各族马帮主要沿以下路线开展贸易活动:自昆明通往贵州的普安州驿路及威宁州驿路;自昆明东南到广西再到越南的田州驿路;自昆明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驿路,多贩茶、盐于藏区而换回藏区土货;自昆明北到四川的宁远府路;自昆明东南出师宗至广西的南宁府路;自昆明经大理至缅甸等地的驿路。在上述各条路线中,尤以滇西回族马帮自大理到缅甸一路最为主要。当时,有许多云南人迫于生计到缅甸开采玉石和宝石,回族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之一就是盛产于滇西边外的玉石和宝石,故有人称其为“回回石”,可见回族马帮在当时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除了到越南和缅甸的驿路以外,明代云南回族马帮的贸易范围基本上是在现今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各省区之间,而到了清代,尤其是各回族商帮逐渐形成以后,云南回族的商业活动变成以对外贸易为主。这一时期,云南回族商帮对外贸易的路线已达十余条:(1)由通海经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至打洛,过江后分为二路:一路直达缅甸景栋,一路经大猛龙到泰国北部的夜赛。(2)由开远经砚山、丘北、广西百色到越南。(3)由峨山经坡脚、杨武、青龙、元江、墨江、通关到泰国、缅甸。(4)从景东经景谷、普洱、思茅到泰国。(5)从楚雄经大理、保山、腾冲到缅甸。(6)由昌宁经顺宁、镇康、耿马至缅甸的麻栗坝。(7)由大理经保山、腾冲、瑞丽、耿马至缅甸。(8)由施甸经昌宁、顺宁、云县、耿马至缅甸。(9)由永宁经丽江、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10)由德钦至印度。[②e](11)由思茅、景洪、猛腊至老挝。在上面的对外交往通道中,有几条就是由回族马帮开辟的。商道大多位于高山密林之中,行走非常艰难,气候炎热,瘟疫流行,人畜极易染病。比如从思茅向南走,多为深山密林地区,必须有一部分赶马人走到牲口队伍前面,用大刀砍掉草木,遇到泥塘牲口不能行走时,还要割草铺垫。有的地方还会遇到老虎和大象出来伤人,要随时荷枪实弹加以提防。有些地段只有回族马帮行走,其他马帮都不敢尝试。[①f]
回族马帮运到缅甸、老挝、越南、印度等国的货物,同到泰国一样,大部分是云南或西南地区出产的物品,换回的也多为当地的土特产品。如到老挝,运进去的货物有土布、黄蜡、蚕丝、铜器、铁锅、缎子、毡子、鞋子和故衣(清朝末年用绸缎做的衫子马褂,当地少数民族用来装老),收买的货物有鹿茸、象牙、山货等。
由于商业税收和经济利益的存在,中国封建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对云南与境外的贸易往来都比较关注,这种收益甚至是某些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例如,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族反清起义军,在19世纪中期曾建立大理政权,为了发展回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特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1)从轻征收商业税。各地商帮运输丝绸、药材和日用品等,每驮仅征一次税,数额为七两银子,便可通行各地,不再抽税。(2)切实保护外地商人利益。如果货物在其统辖地区遭受损失,负责赔偿。杜文秀还派军队在重要关口守护,保证贸易往来畅通无阻。(3)四川和缅甸是大理政权贸易活动的两个主要方向,因而杜文秀派人整修北到四川、西到缅甸的通道,以促进滇西回族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4)在大理城南门外、永昌(保山)、腾冲等地设立旅店和货栈,给予商人生活和经商之便。[②f]在上述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滇西回族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理至缅甸的传统贸易商道,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仍然畅通无阻。
另外,“大理产石黄甚多,俱销缅甸。下关商工,多营此业,输出则为石黄,输入则为缅棉。每驮石黄可换一驮棉花,而一驮石黄之值极贱,文秀乃收归国营。土人采石黄一驮,给工银一两,运往缅甸,换得一驮棉花,即可值银六、七十两,约有五十倍以上的利益,为军需国用所从出焉。”[③f]据生于大理的回族老人姚翠莲回忆,当时一个成人一天能纺织一件用缅甸进口棉花纺成纱的廿八方土布。每件土布市价五百文,棉花每斤(廿四两)一百五十文,除成本以外,织一件土布可收入三百文左右。六、七岁的小孩一天能纺纱线二两,可得钱十文;妇女一个通宵能缝120顶小帽衬里,两顶一文,可收入六十文。[④f]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大理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连杜文秀本人在保山、腾冲及缅甸曼德勒等地都开设有“福春恒”、“元兴”、“元发”等商号,专营缅甸棉花生意。这些活动既提供了大理政权的财政来源,又促进了滇西地区回族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注释:
①a A·D·W·福布斯著,关学君、郭庆译:《泰国北部的“钦浩”(云南籍华人)穆斯林》,《民族译丛》1988年第4期。
②a 申旭:《茶马古道与滇川藏印贸易》,《东南亚》1994年第3期。
③a 方铁:《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思想战线》1987年第3期。
④a L·迈尔尼:《掸人的故乡》,伦敦1910年英文版,第137页。
⑤a E·R·李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伦敦1964年英文版,第28页。
①b A·M·希尔:《泰国北部的中国云南人》,《泰国的高地人》,中津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125—127页。
②b A·D·W·福布斯著:《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云南伊斯兰文化论文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211页。
③b S·松吞帕萨克:《清迈城伊斯兰教的特征:两个社区历史和结构的比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7年。
④b S·松吞帕萨克:《清迈城伊斯兰教的特征:两个社区历史和结构的比较》。
①c A·D·W·福布斯:《泰国北部的“钦浩”(云南籍华人)穆斯林》。
②c 张竹邦:《滇缅交通与腾冲商业》,《云南文史资料选缉》第2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c 宋恩常:《楚雄、丽江、峨山等地回族情况访问杂记》,《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d 《玉溪地区回族社会经济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d 马泽如口述、杨润苍整理:《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d 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④d 马伯良:《云南回族商业巨擘兴顺和号》,《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e 马维良:《云南傣族、藏族、白族和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回族》,《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②e 杨兆钧:《云南回族史》,第204页。
①f 马祯祥:《泰缅经商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f 杨兆钧:《云南回族史》,第130—131页。
③f 何慧青:《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逸经》第16期,第29页。
④f 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与现状》(中),《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年第2期。 WW李大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