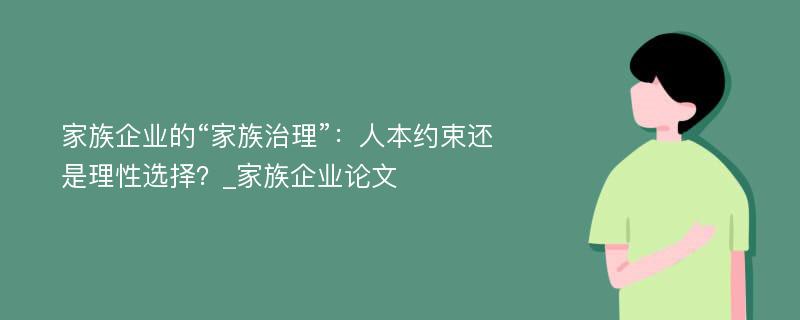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理性论文,人文论文,家族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现在有不少学者把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概括为“家族式治理”,并进而认为这种治理特点主要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是“人文制约”之结果。”[1] 应该说,这些学者们意识到了文化的惯性和组织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但是把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这种“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点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影响之结果却失之偏颇;实际上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影响之结果,而是出于家族企业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权威的“理性选择”。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一、不同的场域及其逻辑:从亲缘共同体到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从亲缘共同体衍生而来,这样一开始家族企业组织必须借助亲缘共同体中的一些规则来营建组织;在经济学意义上说,这种天然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节约了一定的交易费用;而在社会学意义上,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共同体不仅积聚了营建企业组织所需要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也提供企业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家族企业系统是由家庭、家族等亲缘共同体演变而来,就进一步断定家族企业系统中所出现的和亲缘共同体中相类似的一些特质就是传统文化影响之结果。而从现实中看来,虽然国内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采取家族治理的形式;从表面上看,这种治理形式和传统家族的治理形式颇为相似,但实际上两者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相似,其实质却颇为不同。
我们知道,企业系统和家庭、家族等亲缘共同体系统属于不同的系统,两个系统的价值目标、动力机制、生命周期、人事关系都迥然不同,而当家族企业从亲缘共同体中生成之后,在最初的阶段可能要藉助于亲缘共同体的各种资本和组织规则,但是随着企业系统的发展,企业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企业系统自身就有一个不断“脱嵌”的要求。钱德勒在他那本著名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就是对美国家族企业如何“脱嵌”转变为现代工商企业进行了翔实而严谨的分析;而很多学者往往只强调家族企业这个组织对于亲缘共同体的“路径依赖性”,而没有意识到家族企业在生成之后,必须要受到来自企业组织理性以及市场的经济理性的制约。
布迪厄的场域论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布迪厄在他建构的场域理论中提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2](p134) “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由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2](p145) 按照布迪厄场域论的解释,家庭、家族亲缘体系统和家族企业共同体系统分属于不同的场域,而两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要求,对于亲缘共同体而言,它主要遵循的是一种利他主义和情感理性;而对家族企业而言,自它生成之后,作为一个企业, 它必须服从企业场域的逻辑,更要服从市场的逻辑。
即便是家族企业,它也必须面临着投放资本的价值增值问题;当然亲缘共同体也涉及到经济生产问题,但是两者的性质不同,亲缘共同体的经济收益目标只是出于一种“生存理性”或者“满意理性”,其目标主要是满足亲缘共同体成员的生存和消费问题,但是家族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则必须服从“经济理性”和“发展理性”,这样,追求利润动机必然会成为企业行动的重要目标,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目标,不把经济理性作为贯穿企业行动的各个环节中,那么在市场的竞争中必然会被淘汰出局;而企业的治理和企业的绩效有着内在的关联,企业经济绩效也要求家族企业的治理必须遵循企业场域规则。
如家庭、家族中的权威并不一定就能成为家族企业中的权威。由于家族企业场域和家族场域的区隔性,亲缘共同体中的权威和家族企业中的权威生成方式颇为不同,尽管两者有时候会出现重叠现象,其原因在于两个场域对于权威的要求不同。在亲缘共同体中,权威主要取决于一种“合法性”身份。中国的家长制权威是和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分不开的。在小农经济中,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这时候情感和理性能相和谐,原因在于小农经济和简单的手工业分工简单,技术含金量低,通常并且没有来自外来的挑战;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他们是祖先所遗留的智慧与经验的库藏,因此权威常在老人手中,在农耕社会中,这也不会导致非议,因为农耕社会是依靠经验,家是以血缘为基地的身份取向的团体;[3] 而企业则基本是面对市场竞争的一个系统,必须具有组织理性,也必须是一个契约取向的团体,企业这种不同的理性显然需要的是一个“法理型权威”,即有能力治理企业、提高企业绩效的权威;尽管家族企业是从家脱离出来的,也会把一定的伦理关系带到企业中去;但是我在调查家族企业中发现家族企业中的权威尽管大都也是“自己人”,这并不等同于家庭中的家长或者家族中的“传统型权威”,而是出现了权威的“再生产”。①
家族企业的组织目标有时和家庭、家族的目标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企业利益目标也不一定符合家族成员的利益诉求;按照组织社会学的观点,企业组织目标和企业中的个人(包括家族成员)并不会完全吻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十分微弱。[4] 即便如此,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结构要素,家族企业组织在形成之后必然会型塑企业中的成员包括家族成员,使得他们的行为更加理性化,也治理模式上也会更加理性化。
二、非契约关系的“契约化”:“自家人”关系的理性化
很多学者在缺乏经验调查的基础上都轻易断言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和亲缘共同体中的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一样,是一种非契约性关系,即认为只要是“自家人”,就能相互信任,情感上相互依恋;也认为和外人相比,家族企业中的权力配置、资源配置也更倾向于“自家人”;“自家人”之间可以不需要理性的契约。例如李晓兵、李东两位先生在文中指出:家族成员在企业内,彼此也没有契约的约束。……反正都是自家人,何必一本正经的签署那些麻烦的契约,反倒显得对自己人不信任。并且认为家族企业中的“自家人”这种轻契约性特点和家族中“自家人”轻契约性一样,都是根源于家族主义文化。[1]
实际上述两学者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假定自家人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家人一样,同样缺乏契约的意识。实际上,这既经不起理论逻辑的推敲,也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正如上文指出,家族企业场域和日常生活中的亲缘共同体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在家族企业场与中,“自家人”这种情感性关系实际上也在不断“契约化”。尽管相对于“他者”,在权力分配和资源分配、用人制度方面会出现“偏私化”,即偏向“自家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家族企业中“自家人”关系内部,就会发现在权力和用人制度等方面,并不是完全按照先赋性的身份关系来进行权益分配;这意味着,并不是谁和家族企业主持人的关系最近密,谁就会被安排到最重要的岗位,家族企业中的“自家人”的关系相处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家人”关系的相处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家族家庭中的“关系”在介入到家族企业后被改塑和再生产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企业的场域规则要求自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理性化、契约化。
日常生活中的自家人之间强调的是先赋性的身份和相互依恋的情感以及信任和忠诚,但是在家族企业组织中,对于企业成员的人力资本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由于制度信任的缺乏,家族企业的私密和重要岗位都是由家族成员担当,但是并不是每个家族成员都具备相匹配的能力,这样,不可能完全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去安排“自家人”的权力、岗位;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必须“契约化”:例如利用正式制度来规制“自家人”的非契约倾向,甚至还有一些家族企业主极力避免“自家人”介入到企业中,对于企业中的“自家人”也“约法三章”,强调“自家人”进入企业之后,也和其他员工一样,并没有任何的特殊照顾。其主要原因是顾虑自家人之间的非契约化例如人情、关系、面子等会影响到企业正式制度的运作,同时关系的“契约化”还能避免“自家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权力争斗,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耗”现象。
“自家人”的关系的契约化不仅仅是对“自家人”之间非制度化倾向的矫正,同时也是对“自家人”中的机会主义的一种规避。在企业初建期间,由于企业的规模小,家族成员参与的人数少,家族的集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理性的萌发;即使“自家人”的个别成员想搭便车,实施机会主义,但由于自家人相互盯梢,这种机会主义也很难得逞。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家族成员的增多,利益格局的变化,“自家人”中也会有机会主义的发生。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如果由于某个个人活动改观整个集团状况,即使其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团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但如果付出成本的个人只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而集团中的其他每个人不论他们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都能共同且均等分享它,这样机会主义就会发生;[5](p4) 奥尔森接着推论,小集团能够做到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可能仅仅是因为集体物品对个体成员产生了吸引,但是就大集团而言,个体的投入尽管有所回报,但因为其他人的分享,所以投入和回报并不等值,因而也会失去动力。对此,奥尔森断言:集团越大,(个体)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5](p30) 按照奥尔森的解释,家庭小作坊属于小集团,机会主义很少发生,但随其规模的不断扩展,机会主义产生的概率就会增加。
既然“自家人”中也存在着机会主义,那么如何抑制“自家人”的机会主义?显然只能实行理性的契约,只有关系“契约化”,“自家人”对于未来才有确定的预期,这种关系的理性化不仅能和企业的正式制度良性互动,增进企业的绩效,而且能使“自家人”在情感和利益方面能得到一种均衡关系;“亲兄弟,明算账”可能会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理性、和谐,而“不算帐”的非理性行为倒更有可能恶化双方的关系。从现实看来,很多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付诸实践。
三、从“他者”到“自者”:理性关系建构的另一种路径
随着家族企业的扩展,家族中的人力储备将无法满足企业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这时候,家族企业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以家族为主,限制外人的介入,控制企业的发展规模;要么以企业为主,扩展企业的规模,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必须引进外来精英。而从现实看来,大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家族企业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因为固步自封的小企业更容易被市场淘汰。那么对于进入到家族企业的外来精英们,家族企业成员包括企业权威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不是就像雷丁所说的是一种“防御”和“不信任”?
雷丁在用同心圆模型来描述华人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时,认为“防御性、家长制和人情至上”是华人社会共有的文化遗产,而在回答“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在企业内要重用亲戚或者搞裙带关系”时就干脆地指出:因为不相信外人。[6](p146) 实际上,雷丁的观点和马克斯·韦伯、福山的观点相似,都认为中国是一种低信任度文化,即排斥外人,不相信外人,秉承了一种特殊主义的文化传统。
但是中国人真的对外人极度不信任吗?彭泗情博士认为其实对“外人不信任”实际上有两种情形。其一是起点上的不信任,由于信息不充分,对外人缺乏了解,不能确定其可信程度,所以不敢盲目地给予信任。其二是永远的不信任,即人际信任完全局限于自家人的小圈子之内,对外人一直有一种排斥感,在了解了外人之后,不管外人人品多么好、能力多么强,都会因为他的这种“他者”的身份而不予信任。所以彭认为,只有第二种不信任才会导致低信任度社会的产生。而第一种“不信任”是可以改变的,即当了解了对方的人品、能力等因素后,确认了其可信度之后就会信任他。因此,彭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人的“对外人不信任”仅仅是起点上的不信任,是可以在交往过程中改变的,这种不信任并不必然导致一个“低信任度社会”。[7] 雷丁和福山等人并没有区分“对外人不信任”的两种不同情况,只是静态地来分析中国人的信任观。而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中,“外人”在假以时日之后也是能够获取信任的。
而在家族企业场域中,由于制度信任的缺失,家族企业通常在经理人市场中根本搜索不到值得信任的经理人,因为在不规范的经理人市场中,那些经理人往往会提供虚假信息,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使得家族企业无法辨别真伪,但是为了解决企业的人才匮乏问题,家族企业除了提高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以外,还是需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引进“外人”,尤其是一些稀缺的经理人;但是这种引进的方式和西方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钱德勒对于美国的家族企业的演变史研究表明:当家族无法控制企业的发展规模时,家族企业成员和经理人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即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甚至控制权让渡给经理阶层。[8](p9) 但是这种经营管理权的顺利让渡是和美国规范的经理人市场分不开的,实际上规范的经理人市场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信任,它既从经理人市场中剔除了那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经理人,也获取了家族企业成员的信任。
而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既然制度不能提供一定的可信承诺,家族企业成员(尤其是主持人)通常仍然会借助人际关系建构的方式来获取值得信任的经理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家族企业中的经理人都不是从经理人市场引介的,而通常都是双方在经过一定的交往后,经理人才往往在获得了家族企业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的信任后才被委以重职的。可以说,对经理人的能力信任可以通过业绩测试出来,但对于经理人的人品信任则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互动中慢慢确立一种信任关系。杨宜音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日常生活中外人是如何变成自己人的过程,认为中国人是能够将外人包容进自家人这个伦理实体,可以内外相互转化,内外交换的结果使得现实中的中国人的信任逻辑不完全是按照身份群体来确定,而是按照一种心理认同来确定。[9]
实际上,家族企业中也有内外相互转换这种现象,但是这种转换机制可能和日常生活的内外转换有所不同,尽管家族企业也是在制度信任缺乏的前提下通过人际关系的建构,把“外人”转换为“自己人”,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关系的建构比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建构更加“理性化”,会受到家族企业系统隐性的制约,因为“关系”的建立不是基于“关系”本身去建构的,关系的建构最终是指向企业的。陈介玄、高承恕对研究台湾家族企业中时发现,家族企业中的员工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人际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既有传统的“人情”的感性特质,又有立基于后天成就上的理性计算。也就是说,这种信任是人情付出与理性算计的结合。[10] 事实上,我们还会发现为数不少的华人家族企业中,家族企业的主持人会采取“拟血缘化”的手段,例如将能干的下属入赘为女婿或认为干儿子来加强关系纽带,从形式上看这种“拟血缘化”方式仍然藉助于传统,但是与传统不同的是,其中的理性成分显然大大增强了。
四、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限度
不可否认,文化基因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组织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儒家伦理而言,它作为一种知识、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不仅能影响并型塑人们的日常行为,同样儒家伦理的某些层面也能成为企业治理的某些规则;儒家伦理甚至也能通过影响到家族企业的主持人进而影响到企业的“风格”,这种韦伯式的“文化—经济”理路应该说对我们认识家族企业的治理有很大的启发;② 也能让洞察到“家族式管理”的一些特质是如何从“儒家伦理”中演变而来,以及家族企业和家庭、家族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但是文化论者的理论逻辑中没有意识到儒家伦理只是一种精神或观念的存在,它并不就是人们行为本身,“文化外化为种种社会制序,但文化本身并不就构成种种制序;文化虽然通过制度以及个体行为能进而影响到经济秩序,但文化本身并不包含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11](p15) swidler更是说“文化的本来意义不是决定行动的目的,而是提供了文化的组分去构建行动的策略”。[12]
不少学者都过度阐释了传统文化对于现实中的家族企业现象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随着场域的置换,家族企业成员会在企业的经营实践变为富于反思、并善于理性选择的一个群体;这样,日常家庭、家族以及日常领域中的一些文化规则例如人情、面子、关系等,到了企业领域,并不一定会延续;它们在受到企业这个变量的介入而发生改变;正如上文指出的,对于企业来说,一旦生成之后,它有自己的场域规则,不仅有一定的“组织理性”,同时还会受到“市场理性”的约束,企业会受制于“结构路径”,这样原本在日常领域存在的一些文化规则在企业领域很可能会被“拒斥”,因为理性的家族成员尤其是主持人会反思到“人情困境”对于企业运行的负功能,并进而主动规避这种“人情困境”,甚至借助一种正式制度来抑制这种人情现象的滋生。
我们在访谈中得知:杭州的金义集团是个有名的家族企业,但是作为这个家族企业的“业主”的陈金义(当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却于1998年演绎出一场“大义灭亲”的革命。“革命”之前,企业里有陈金义的30多个直系亲属,这些人半数以上担任了包括副总裁在内的中层以上领导职务。多年的实践使陈金义感到家族化管理弊端太多,1998年底,他决心向家族制开刀:他的亲属或辞退、或退休、或离职学习,其中,大哥退职,二哥退休,三哥连降三级,妻子退居二线,把不具备领导管理能力的亲属全部撤换下来,尤为彻底的是,他自己也辞去总经理之职,只任董事长,而聘请一位年轻的外人来担任总经理。此举被业内誉为家族企业中的“大义灭亲”。在浙江的家族企业中此类举动并不在少数,尤其是做到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主持人对此往往更有深切的认识和更果断的行动。
即使在家族企业的治理中我们会发现类似于传统文化的某些规则,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用文化的视角去解释,这些规则很可能是家族企业理性选择之结果。金耀基通过对香港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香港的家族企业主对亲属的雇佣多半是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并不是完全受儒家家族文化影响之结果,对亲属的雇佣并不只是出于“偏私化”或者人情、面子,而主要是企业主为了经济目的对于“文化资源”的一种运用,企业主只是觉得亲属比其他人更加值得信任。金称之为实用主义支配下的“智性选择”,是一种“理性传统主义”。[13](p162—163)
理性选择视角强调的是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但它既不是假设个体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并不没有忽视外在规范对个体的制约,但理性选择视角并不是视这些外在规范下的个体是被动的,而是认为个体是能动的、善于反思的,并且,个体所采取的理性行动也会不断改塑着外在规范。而文化的视角则从往往从规范着手,强调的是规范对于个体的强制性,而往往忽视了个体的实践性和反思性,更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文化资源的藉用和再塑。过度强调儒家文化对于家族企业的人文制约,正是一种文化的解释,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解释的限度。实际上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管理层面上的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注释:
① 这里的“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一对概念。韦伯在他的社会行动类型的基础上划分出三种关于权威的理想类型:即传统型(习俗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以及法理型权威。参韦伯:韦伯作品集:支配社会学[M].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韦伯的逻辑是:没有企业家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级;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宪章。雷丁在推断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基本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推演的。参S.B.雷丁.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