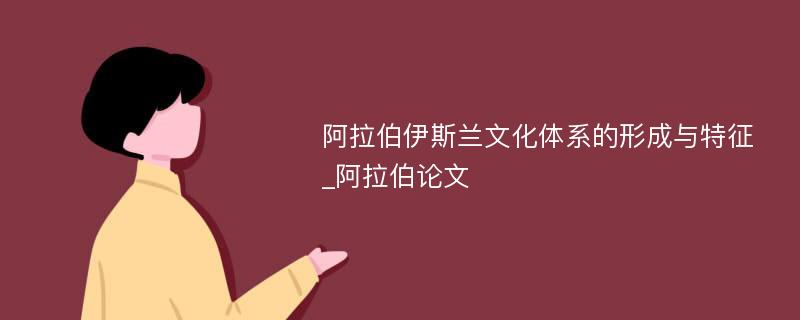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和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阿拉伯论文,特性论文,体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112 B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113(2000)03-0005-(05)
文化体系一般是指由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系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其他文化系统有所区别。据季羡林先生的意见,整个世界可分为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是以阿拉伯为基地,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这个文化体系在东方地区广泛传播,对这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酝酿最终形成的,并且有自己鲜明的特性。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是与伊斯兰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密不可分的。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这个半岛正处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半岛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和社会,多氏族部落各据一方,彼此经常发生仇杀、劫掠和战争,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危机四伏。与此同时,外族势力的侵入,更进一步加深了当地的危机。在宗教方面,人们信仰的是原始宗教,每个氏族部落都崇拜自己的神灵和偶像。可是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们对于这种原始宗教的信仰逐渐发生动摇。这时虽有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半岛流传,但这些外来宗教似乎也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种新的宗教,以便统一人们的信仰,消除氏族部落的隔阂,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和社会,就是大势所趋了。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创造人穆罕默德(570~632)应运而生。他自612年起,向麦加居民公开传教。后来由于遭到麦加一部分人的反对,于622年率大批信徒——穆斯林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并打破穆斯林的氏族部落界限,提出“穆斯林都是兄弟”的原则,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穆斯林公社。这个公社是兼有宗教和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团体,而穆罕默德则兼有宗教和政治、经济、军事领袖的资格。其后,穆罕默德将麦加定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中心,而把麦地那作为政治中心。伊斯兰教至此初步形成。
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在中古时代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伍麦耶王朝时期(661~750)、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和奥斯曼帝国时期(13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这四个时期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
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在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的率领下,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迅速向外扩张。随着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伊斯兰教开始了第一次大传播,为伊斯兰教由民族性宗教变为世界性宗教打下了基础。
在伍麦耶王朝时期,哈里发向西、向北、向东三个方向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其势力范围从西亚扩展到了北非、西南欧、中亚和南亚。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广泛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开始形成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时阿拉伯的学术研究工作,如宗教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学、星相学、哲学、化学等的研究工作业已普遍展开。例如:宗教学包括《古兰经》的诵读学、注释学、圣训学、教义学等;历史学主要研究氏族部落的历史和先知的生平活动;语言学主要研究如何大量吸收外来语,使之阿拉伯化,并改革阿拉伯语,使之容易为外族人所接受等。
阿巴斯王朝任用波斯人为首相,确立了以首相为中心的波斯式官僚体制。这标志着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封建制度进入了成熟时期。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因而这时的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则成为三个文化中心。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百年翻译运动”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促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得以最终形成,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展这个运动,既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和传播宗教的需要。阿巴斯王朝的几任哈里发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予以大力支持。如曼苏尔是翻译工作的首倡者,他命人将有关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的波斯文、梵文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哈伦·拉施德也对翻译工作加以扶持,在他的宽容政策的鼓励下,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他们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的范围,着手翻译哲学、逻辑学等理论性书籍和各种自然科学书籍;而麦蒙则将翻译运动推上鼎盛阶段,他派人四处云游学习,搜集各种典籍,并不惜巨资修建有名的“智慧宫”,集中大批典籍资料和学者、翻译家、编辑人员、抄写人员,专门从事整理、翻译、编辑、注释和校对工作。在“百年翻译运动”的推动下,阿拉伯人以及当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境内的各族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欧洲文化界尚处在摸索和彷徨的阶段,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却大放光彩。
但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尽管他们还在不断扩展领土,并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欧、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可是在文化上却没有取得特别引人注目的成绩,未能恢复阿巴斯王朝时期的盛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特性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二是以伊斯兰教为主导。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果说中国文化体系和印度文化体系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创造的,甚至是以一个民族为主创造的,那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则是若干国家和若干民族的共同创造,是若干国家和若干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阿拉伯则是中古时期新兴的国家,不具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但地理位置和种族关系却为它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条件。从地理位置来说,阿拉伯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处,位于世界最古老的两大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之间,北方与另一个文明发源地——希伯来接壤,东方和南方则通过海路与另两个文明发源地——印度和波斯联系起来。自古以来,这个半岛就处在东西方交往的要道上,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从种族关系来说,阿拉伯半岛是远古闪人(闪米特人)部落的故乡,闪人则是巴比伦人、亚述人、阿拉米人、迦南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而另一支闪人又移居埃及,与当地原有居民混合,创造了古埃及文化。由此可见,阿拉伯人与周围这些民族都有亲缘关系,阿拉伯文化与古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有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便很容易使阿拉伯文化成为当时业已中断或转移的古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继承者。
阿拉伯人是善于学习的。伊斯兰教的经典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为求学是穆斯林的天命,甚至认为求学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等于殉教。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上升时期,有些上层统治者和领导者也有远大的眼光,积极引导阿拉伯人向外国人学习,向外族人学习。正是在这种精神推动下,才展开了大规模的“百年翻译运动”,广泛地吸收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文化。
他们首先翻译的是波斯的典籍,吸收的是波斯的文化。这是因为在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人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首相和大臣几乎都是波斯人担任;而且在巴格达,波斯文化本来就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曾经长期统治巴格达)。在语言方面,阿拉伯人由游牧生活转入文明生活后,发现自己原有的词汇远远不够使用,于是一面扩大阿拉伯语词汇的意义,一面吸收外来词汇,而波斯语词汇则成了一个重要来源,诸如生活设施、化妆用品、食品、服装、办公用具、政治制度等的词汇(如水壶、盘子、绸缎、珊瑚、糖果、糕点、蔷薇、水仙、外衣、裤子、宰相、机关等)大部分来源于波斯语。在文学方面,不少波斯籍学者致力于将波斯文学作品以及译自梵文的印度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个故事》,前者对阿拉伯文学以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者则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还有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的人,在阅读波斯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思想得到充实,智慧得到启发,用阿拉伯文写出了新的文学作品,提高了阿拉伯文学的水平。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长达八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一书中写道:“在阿巴斯时代,这些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及接受了波斯文化的阿拉伯人,让整个世界充满了学术、格言、诗歌和散文,他们的作品中的波斯成分是很明显的。幸好当时阿拉伯语压倒了波斯语,以波斯思想为主产生的文学成果是用阿拉伯文,而不是波斯文写的。”[1](P167~168)在历史学方面,《波斯列王记》、《波斯诸王史》、《马兹达克》和《琐罗亚斯德教士》等许多传记著作由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这些译著不仅丰富了阿拉伯人的历史知识,而且为阿拉伯人写同类著作提供了借鉴。以上所述仅仅属于举例性质,事实上波斯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在政治上,阿拉伯人仿效波斯人的统治方式,学习波斯萨珊王朝的官僚体制,设立首相和大臣等;在宗教上,波斯人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原来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仍然在心底长期存在,并且通过种种途径使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染上了波斯民族色彩;在学术上,由于波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波斯学者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当他们掌握了阿拉伯语之后,便很快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就,成为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在介绍和翻译波斯文化的学者中,伊本·穆格法是最出色的。他原籍波斯,本来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才改信伊斯兰教。他
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几乎把波斯文最重要的典籍都译成了阿拉伯文。有人在评论他时说道:在非阿拉伯人中,再没有比伊本·穆格法更聪明、更博学的了。他的主要译著和论著有《小文学》、《大文学》、《近臣书》和《卡里来和笛木乃》等。
其次是翻译印度的典籍,吸收印度的文化。阿拉伯人早就知道印度,早就与印度人有商业贸易往来。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攻占了印度的西北部地区,印度各种文化也就随之传入阿拉伯。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可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政治统治、军事战争、商业往来、杂居通婚所造成的影响;后者是指经过波斯人的中介,印度各种典籍被译成了阿拉伯文,阿拉伯人接受了印度的多种文化成果。例如:在宗教学领域,由于婆罗门教和佛教典籍的关系,轮回解脱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对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数学领域,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零的符号和十进位法,然后加以改进,又传到了西方。据说印度用(·)作为零的符号,阿拉伯人也用圆点作为零的符号,传到西方后才改用圆圈(0)作为零的符号。在天文学领域,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法扎里根据印度学者于公元628年写成的一部理论著作,制定了著名的《天文历表》,根据这部历表制定的历法,在阿拉伯使用了很长时间。在文学领域,不少印度语言的词汇融入阿拉伯语中,有些修辞学的理论是印度人教给阿拉伯人的,最初产生于印度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个故事》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受到阿拉伯人的热烈欢迎,并对阿拉伯的寓言故事和散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印度短小精悍的格言也深为阿拉伯人所喜爱。
第三是翻译希腊的典籍,吸收希腊的文化。阿拉伯人之所以对希腊典籍和希腊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不仅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与希腊隔海相望,而且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境内的许多地方(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等地)都曾被古代希腊马其顿帝国占领过,受到过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到阿巴斯王朝时期,又有众多学者专门从事希腊典籍的翻译和校勘工作,几乎将古代希腊的全部重要典籍都译成了阿拉伯文(有的是从波斯文转译的,有的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在哲学方面,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含《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主要论述一般理论问题,《工具论》(含《范畴》、《论辩》、《解释》、《前分析》、《后分析》、《智者的驳辩》),主要论述逻辑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论述自然哲学问题;柏拉图的早期作品《申辩篇》、《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中期作品《斐多篇》、《费德罗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晚期作品《费雷波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法篇》等;玻非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导论》等。在数学方面,如阿波罗尼罗斯的《圆锥曲线》、《比例截割》、《有限极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数据》,阿基米德的《论球和圆柱》、《圆的测定》等。在医学方面,如格林的《解剖学》、《小技》,获奥斯科里的《药物学》,获奥科里迪斯的《医典》等。在天文学方面,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在地理学方面,如托勒密的《地理学》等。在物理学方面,如托勒密的《光学》,欧几里得的《光学》等。在文学方面,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众多翻译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侯奈因·本·易司哈格(809~877)。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和著述工作,有时给译著作解释,有时对译著进行改写。他翻译最多的是医学著作,特别是格林的著作。据说他将格林的75部著作译成了古叙利亚文,又将其中的39部译成了阿拉伯文,此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校对工作。通过易司哈格等人的手,阿拉伯人广泛地吸收了希腊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并以此为借鉴进行创新,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和新发明;但相比之下,阿拉伯人却很少吸收希腊人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这可能是因为哲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更多的世界性,而文学则具有更多的民族性,阿拉伯人能够接受希腊人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却不大欣赏希腊人的文学,在文学领域,阿拉伯人似乎更
欣赏波斯和印度的作品。
第四是犹太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境内,有大量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杂居在一起,彼此交往,互相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犹太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些宗教学家,将犹太教文化融入到伊斯兰教文化里。伊斯兰教接受犹太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在伊斯兰教《古兰经》里,有许多与犹太教《圣经》(即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内容相似的部分,特别是有关先知的故事;但二者讲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圣经》讲述的比较具体,而《古兰经》却只是点到而已,一般不叙述细节,不叙述经过。犹太人将上帝形象化,甚至相信人死后还可以复活,这些观点为伊斯兰教的某些教派所接受。有的伊斯兰教学者认为,在教义学中存在的许多分歧,其根源就在犹太人身上。除了犹太教以外,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基督教文化主要体现在《新约》以及有关《新约》的注释书籍和故事传说里。这些东西一是通过阿拉伯人中的基督教徒传入穆斯林世界的,二是通过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传入穆斯林世界的。我们不难看出,《古兰经》有些章节容纳了《新约》的内容。不过,《古兰经》的写法较为简明概括;于是有些注释者便依据《新约》进行详细解释。另外,还有些人把《新约》中的一些故事和思想,说成是穆罕默德的圣训;甚至把《新约》中的一些违背伊斯兰教精神的观念,也说成是伊斯兰教的观念。因之,在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中,都能看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子。据《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作者研究,基督教的许多观点已经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学之中。其一是有些阿拉伯诗人原来是基督教徒,他们创作的作品自然会有基督教的蛛丝马迹。如伍麦耶王朝时期的诗人艾赫泰勒(640~710)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既信奉伊斯兰教,又不免残存着基督教的影子,他在诗里既颂扬真主安拉,又经常出现“穆萨(摩西)”、“十字架”之类的形象,其二是围绕基督教修道院所创作的诗歌。按理来说,修道院应当是远离尘世、虔诚修养的场所,但实际上,许多修道院却成为文人骚客调情取乐、醉生梦死的地方。有些修道院周围开设了很多酒店,还定期举行节日集会。
正是由于百年翻译运动,正是由于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东方和西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这一点如今已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家和文学史家的共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作者认为:
在阿巴斯王朝初期,上述各种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以及犹太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都汇集到了伊拉克。但是,每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韵味,最初它们都在各自的小溪中流淌,没有多久,这些小溪就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1](P348)
黎巴嫩著名文学史家汉纳·法胡里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具体的剖析,他指出:
不同的外来文化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传播,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希腊智慧偏重哲理分析,偏重精神多于物质,偏重精神和科学性,这是使阿拉伯人撰书立说和献身科学的巨大推动因素。印度智慧偏重思考,印度思想中诗情的成分多于科学性,富于想象和表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情。印度人的苦行和清修倾向很强烈,并对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对阿拉伯人的睿智、苦行和故事艺术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素。波斯智慧几乎是一个包含所有古代文化的容器,它由波斯、希腊、印度诸成分构成。印度文化对波斯文化的影响大于希腊,但波斯文化中物质的成分占上风,它对语言和创作中的浮靡艳丽,夸张铺陈,以及对音乐领域和各类乐器的扩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素。波斯人对阿巴斯文化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人,这种文化上的超越不过是政治上超越的结果。[2](P246~247)
也正是由于百年翻译运动,由于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才很快得到了充实,得到了丰富,迅速地提高了自身的水准,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达到了繁荣和昌盛的阶段,甚至足以与其他三个历史悠久得多的文化体系并驾齐驱。这一点如今也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是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从上层统治者和领导者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属于这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文化都应当是以伊斯兰教的思想为指导的,至少是不能违背伊斯兰教的思想的;属于这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文化都应当是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至少是不能违背伊斯兰教的教义的;属于这个文化体系的所文化都应当是为宣传伊斯兰教服务的,至少是不能反宣传的;属于这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文化都应当是为强化国家政权服务的。因此,宗教学被置于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受到格外重视;语言学者要为研究《古兰经》以及一系列宗教典籍服务;历史学是从为先知和圣人立传起步的;文学创作要为宗教唱赞歌等。当然,在事实上,上层统治者和领导者的这种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完全左右各种文化的发展的,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常常走向它的对立面,就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往往不受它的限制。然而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毕竟是不可忽视的。
伊斯兰教在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民族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人——上层社会的人——认为只有念诵和研究《古兰经》才能加深其信仰,完成其宗教。为此,必须学习阿拉伯语,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教育。这样,他们就掌握了两种文化:本民族的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必然会把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将两种思维方式聚集在一起。很多波斯人阿拉伯化了,很多罗马人和印度人阿拉伯化了,很多奈伯特人也阿拉伯化了。阿拉伯化的含义就是为接受阿拉伯文化敞开了思想和语言的大门,使阿拉伯文化与他们从小就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结合成一体。阿拉伯化还意味着为使伊斯兰教代替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敞开大门。思想、语言和宗教的融合是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一个原因。[1](P360)
[收稿日期]2000-05-16
标签:阿拉伯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波斯论文; 犹太教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