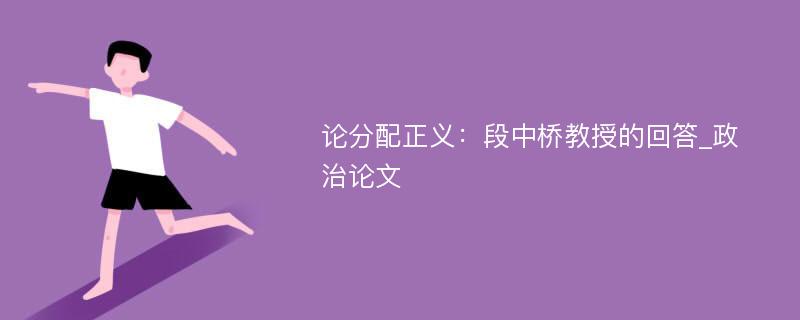
再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分配论文,教授论文,段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发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文(下引仅注页码),表达了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原则。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如下:首先,一种分配只有得到弱势群体的同意,它才能是正义的;其次,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最后,虽然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有利于弱势群体,但是也能够得到其他群体的同意。段忠桥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三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下引仅注页码),就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一些与我不同的观点,并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我非常感谢和赞赏段忠桥教授的批评,因为这样的学术批评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分配正义问题。段忠桥教授与我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观念上面,即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
一、我们为什么需要分配正义?
关于分配正义,段忠桥教授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其文章第一节的标题之中:“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第17页)这句话既是对我的观点的一种批评,也是对他的观点的一种表达。在段忠桥教授看来,“分配正义的目的指的是它所要达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什么则是由分配正义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而“分配正义的性质是由平等主义所规定的,因而分配正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平等主义的分配”。(第23页)这些话语表明:如果我们持有某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那么这种分配正义的观念就决定了分配正义的性质;至于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与分配正义无关。
这种观点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因为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具有客观的权威,所以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而无需考虑其结果如何。就西方政治哲学而言,这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或者来自于上帝的神法,或者基于形而上学的自然法。然而我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存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以致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分配正义观念,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我也不认为分配正义观念需要建立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权威上面,无论它是神法还是自然法。
按照我的理解,分配正义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提出这种政治哲学的问题源于现实的困境。例如,我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源于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分配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我的分配正义观念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思考目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正义问题(比如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然后我们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并提炼出相应的正义观念。政治哲学是实践取向的。我们遇到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然后思考如何解决它们,提出解决的方法。例如:洛克提出“人民主权论”,是因为在他的时代“王权”一统天下;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因为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是因为无产阶级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而受到了剥削;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是因为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加以解决的分配正义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需要一种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分配正义原则,需要一种与这种正义观念和正义原则相对应的制度设计,以便能够最好地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分配正义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中提出了这样的分配正义的原则:“社会安排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第112页)
因为正义涉及制度设计,所以在面对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问题时,不同的人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制度,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可以基于不同的正义观。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侵犯自由是最大的不正义,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确保自由优先性的制度。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贫富两极分化是不正义的,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达到最大程度的平等的制度。功利主义者认为幸福最大化是一种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幸福最小化是最大的不正义,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确保幸福最大化的制度。至善主义者认为使人的潜能(或某些特性)得到发展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阻碍人的发展是不正义的,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能够使人的潜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制度。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正义观,不同的正义观导致不同的制度设计,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
在阐明我所主张的分配正义观念之后,现在我可以为自己辩护了。
我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个是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第107页)对此段忠桥教授评论说:“在他看来,分配正义问题不仅涉及人们在分配上得到平等对待,而且还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进而言之,只有既使人们在分配上得到平等对待,又使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的分配,才是他认为的正义的分配。这样说来,姚大志教授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实际上持有这样一种见解: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是与人们在分配上得到平等对待同等重要的决定一种分配是否正义的一个因素。”(第17-18页)而且,段忠桥教授认为,这里的福利改善“包含所有人的福利都将得到提高的意思”(第19页)。这里段忠桥教授有两个明显的误解。首先,我说“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中之一是希望自己的福利得到不断改善,这是指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的国家。但是显然,制度设计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没有必要考虑所有人要求改善福利的愿望,正如我在提出分配正义的原则时只考虑了弱势群体的愿望,而没有考虑富裕群体的愿望。其次,我主张分配正义应该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处境,但这里并没有“包含所有人的福利都将得到提高的意思”。因为我提出的分配正义原则是“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按照这个原则行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对于那些百万富翁们的福利,即使不会降低,但也不会提高。
段忠桥教授也引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相关论述,来论证分配正义只涉及社会或国家如何在人们中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的不断改善,并以此说明我的见解“难以成立”(第18页)。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论述不是证伪了我的观点,而是证明了我的观点: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是为了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德沃金提出“资源平等”,是为了改善由客观因素导致的不利者的处境;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平等”,是为了改善“残疾者”(the disable)的处境;戴维·米勒和约翰·罗默提出的平等观念,是为了改善底层群体的处境。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上述西方政治哲学家,提出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处境,乃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处境实际上是分配正义所要达到的目的。
简言之,我们之所以需要分配正义,是因为当前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分配的不正义;而这种不正义集中体现在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从而需要改善他们的福利处境。
二、平等意味着什么?
关于平等,段忠桥教授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第二节的标题之中:“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第19页)他引用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来证明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关于正义的分配为什么应该是平等主义的,段忠桥教授给出了两个理由:“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应把人当做平等者来对待;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第21页)
对于上述观点,我赞同其前半部分,但不同意其后半部分,即“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做是正义的”和“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我将以提出并回答下面三个问题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首先,平等主义意味着什么;其次,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如何能够成为正义的;最后,一种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
1.平等主义意味着什么?有两种基本的平等观念,一种是“结果的平等”,一种是“机会的平等”。“结果的平等”不考虑人们之间的所有差别,无论人们做什么,它都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分配。“机会的平等”主张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但是它接受结果的不平等,并且承认这种结果的不平等是正义的。那么,我们应该接受哪种平等观念?
平等主义正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加以矫正。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应该加以矫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问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政治哲学家们通常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有四种,即社会环境、自然天赋、运气和责任。其中社会环境、自然天赋和运气是客观的,是行为者无力改变的,而责任则属于主观的因素,与行为者的选择和抱负密切相关。这样的推理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不平等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环境、自然天赋和运气方面的差别,从而他们对此是没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应该加以矫正;如果不平等产生于人们的选择和抱负方面的差别,从而他们对此是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不平等就不应该加以矫正。
承认责任在分配正义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拒绝“结果的平等”。如果我们承认责任的观念而拒绝“结果的平等”,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机会的平等”。事实上,当代绝大多数的平等理论都主张“机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的机会平等”,另一类是“实质的机会平等”。下面依次讨论它们。
在罗尔斯之前,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就是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观。这种机会平等观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地位,将人看做完全自由的个体。这种自由个体作为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从事竞争,并获取回报。就此而言,这种机会平等完全是形式的: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进入各种有利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形式的机会平等”中,由于社会没有作出努力来提供平等的条件,所以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和运气的好坏,等等。这些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因素往往造成人们在机会、收入和财富方面的极大不平等。简言之,“形式的机会平等”通常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
因此,对于很多平等主义者来说,这种“形式的机会平等”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更希望达到“实质的机会平等”。“实质的机会平等”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福利平等”,当代功利主义是其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当代功利主义在两种意义上是平等主义的:首先,功利主义平等地看待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福利比其他人更为重要;其次,考虑到功利最大化之要求和资源的边际功利递减之事实,最好的功利主义分配在原则上是平等主义的。对于功利主义,所谓福利是指偏好的满足。“福利平等”观要求资源的分配能够使每个人的偏好都得到平等的满足。
第二种“实质的机会平等”是“资源平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三种重要的资源平等观念,它们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的资源平等是广义的,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是狭义的。对于罗尔斯,如果人们所得到的基本善是平等的,那么资源平等就达到了。对于阿玛蒂亚·森,如果人们所发挥的功能是平等的,那么资源平等就达到了。对于德沃金,如果在起点以某种方式使人们获得了平等的资源,那么资源平等就达到了。
第三种“实质的机会平等”是“优势平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其代表。在柯亨和罗默看来,“福利”的平等是一种结果的平等,它忽视了责任问题;“资源”的平等是一种物的平等而不是人的平等,因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资源。基于这种考虑,他们把自己主张的机会平等称为“优势平等”。“优势平等”理论主张社会资源应该这样来分配:当人们面对相同环境的时候,所分配的社会资源使他们能够获得平等的优势;当他们的行为是由自由选择所决定的时候,则允许他们获得不平等的优势。
我自己的观点是:在两种基本的平等观念中,我赞同“机会的平等”,不赞成“结果的平等”;在“机会的平等”中,我赞同“实质的机会平等”,不赞成“形式的机会平等”;在“实质的机会平等”中,我赞同“资源平等”,不赞成“福利平等”和“优势平等”。
2.“结果的平等”意味着平等的分配,“机会的平等”意味着不平等的分配。如果我们接受“机会的平等”,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可以是正义的。问题在于: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如何能够成为正义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要是城镇)实行的是大体上的平等分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不平等分配。这种由平等的分配变为不平等的分配有其必要性。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收入是平等的,但是都非常低,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贫困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尽管增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两种分配方案供我们选择:一种是现有的平等分配方案,每一个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另外一种是不平等的分配方案,但是出于某种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会大大增加总体收入,从而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即使对于收入最少者也是如此。为简便起见,我们把所有相关者分为两个群体,即“收入更多的群体”和“收入更少的群体”。“收入更多的群体”显然会赞成不平等的方案,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他们得到了新增收益中的大部分。问题在于,“收入更少的群体”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这些收入更少者是理性的,而且不平等不是非常严重,那么他们也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即使另外一个群体的人会比他们的收入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如果“收入更少的群体”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就是正义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上帝授权的分配正义,也不相信有天赋的分配正义,那么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分配正义的观念,即一种分配方案被所有相关者都接受了,这种分配就是正义的。把上面的假设转换为现实,“收入更少的群体”就是弱势群体。因此,如果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得到了所有相关者的同意,特别是得到了弱势群体的同意,那么它就是正义的。同时我应该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也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分配正义原则行事,那么这种分配或许是目前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大程度的平等。
3.现在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段忠桥教授认为,“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与其相反的观点应该是“平等的分配是公正的”,而这个观点也应该是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我则持有相反的观点。由于我更愿意使用“公平”(fair)而非“公正”一词,所以我将这种相反的观点表述为:“平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仅仅表明观点是不够的,现在我还需要证明: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
平等的分配意味着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什么东西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我认为主要有三种东西,即机会、资源和收入。首先,机会不能平等地分配,因为它们是有限的。所谓机会,主要是指上大学、就业和升职的机会。由于上大学和升职等需要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即使机会可以平等地分配,这种平等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其次,资源也不能平等地分配,因为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各种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医疗资源。我们知道,医疗资源只应该分配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病人),而那些健康者则没有这种需要。因此,如果我们平等地分配医疗资源,这对于病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最后,收入似乎是最适合平等分配的东西,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勤奋,劳动时间更长或者更累,创造的价值更多,从而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有些职业(如医生和飞行员)需要很多的知识和复杂的技能,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长期的培训,为此所消耗的费用应该在其收入中得到补偿。有些职业(如常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和测量工作者)是令人不快的、艰苦的或者危险的,也需要给予额外的补偿。因此,如果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收入,这是不公平的。
说“平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理由是它抹煞了个人的责任,切断了个人行为与其收入之间的关联。我曾说过,分配正义的根本目的是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加以矫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分配正义理论应该区分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从而对不同的不平等采取不同的态度。一些不平等产生于环境(家庭、天赋和运气),而人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在道德上是任意的,他们对此没有责任,因此这种不平等应该得到矫正。另外一些不平等产生于偏好和抱负,而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偏好和抱负在道德上则不是任意的,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应该得到矫正。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某些人更有抱负或者更为勤奋,从而拥有更多的收入,那么那些收入更少者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抱怨。
三、什么是“应得”?
对于政治哲学来说,分配正义问题的核心是原则。如前所述,我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中提出了一个原则:“社会安排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段忠桥教授在批评我的分配正义观念时,引用了柯亨、戴维·米勒和麦金泰尔的观点,以说明分配正义意味着“应得”(第18-19页),并且在文章的第三节也批评了我的“应得”观念(第21-22页)。因为麦金泰尔等人确实把“应得”当做分配正义的原则,而段忠桥教授是以肯定的方式来引用他们的观点的,所以我有理由推断,他也把“应得”当做分配正义的原则。
但是我认为,“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而且,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平等主义是冲突的。因此,我在下面将首先讨论我所理解的“应得”观念,然后说明“应得”为什么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
所谓“应得”(desert),就是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自古希腊以来,“应得”在分配正义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古希腊,“应得”有两种特别的含义,一是意味着“道德的应得”,一是与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相关。由于“应得”具有这种道德的含义,而且这种道德“应得”是前制度的,所以很多当代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主张“应得”与分配正义无关。即使我们承认可以把“应得”排除于分配正义,但是“应得”一直在分配正义中占据的位置也需要有某种东西来充填。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方一些主流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和诺齐克)主张,这种取代“应得”的东西是“资格”(entitlement)。
按照这些政治哲学家的理解,“资格”与“应得”的关键区别在于制度:“资格”是基于现行社会制度和规则而获得的,而“应得”独立于制度和规则,它在本性上是前制度的。我们现在关心的东西是“应得”而非“资格”,这样就需要澄清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应得”与制度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应得”与“资格”的关系。
“应得”与制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我认为“应得”以一定的制度为前提。在许多场合,没有相关的制度,我们很难说谁对什么东西是“应得”的。“应得”是一种道德评价。我们作出道德评价的时候,总是以相关的制度或者规则为背景条件。例如,一名高中生以全省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我们说这是“应得”的。除了赞扬这名学生成绩优异之外,这种道德评价是以中国的高考制度为前提的,其中包括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按省招生制度、评卷制度和录取制度,等等。
另一方面,“应得”又是前制度的。“应得”作为一种道德评价,不仅包含肯定的评价,也包含否定的评价。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应得”,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或规则的批评。例如,假设一个人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说这个人对于院士的头衔是不“应得”的。这种道德评价除了对该人的学术水平表示怀疑之外,还对目前的院士评审制度提出了批评。这种对现行制度的批评是独立于现存制度的。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应得”有独立于制度的一面,也有依赖于制度的一面。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应得”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用法,“应得”的前制度性质主要表现于否定的用法之中。我们说,A得到了G,这是其“应得”的。这是“应得”的肯定用法。否定的用法有两种形式:A得到了G,这是其不“应得”的;A没有得到G,这是其“应得”的。只有在否定的用法中,“应得”的前制度性质才凸显出来,并且发挥了批评的功能。而在肯定的用法中,“应得”与制度是一致的,其前制度性质和批评功能并不显现。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区分“应得”与“资格”的关键并不在于制度。假设一个大学的哲学系有10名教授,而系主任应该由其中一名教授担任。现在有两种方法来决定由谁做系主任。一种方法是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次序由这10名教授轮流担任,另一种方法是由全体教师按学术成就和工作经历选出一名教授担任系主任。按照前一种方法,系主任现在应该由“常教授”来担任,因为他依照姓名的汉语拼音次序排在头一位;按照后一种方法,基于其学术成就和工作经历,大多数教师会选择“张教授”担任系主任。如果按照前一种方法由“常教授”担任系主任,我们会说,他是有资格的,但他不是“应得”的。按照规则,“常教授”有资格做系主任;但他在姓名的汉语拼音次序中排在第一位则是偶然的,排在第一位不是他“应得”的——人们也可以按照姓名的汉字笔画来排序,或者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这样第一位就可能是其他的教授了。如果按照后一种方法由“张教授”做系主任,我们会说,“张教授”不仅是有资格的,而且也是“应得”的。
在后者的场合,“资格”与“应得”是重合的。在前者的场合,“资格”并不等同于“应得”。如果一个人A对某种利益G是有“资格”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是“应得”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应得”的呢?
我们可以说,通过全体教授的选举,“张教授”对于系主任不仅是有“资格”的,而且是“应得”的。但是,“投票选举”这种民主程序能够使他具有担任系主任的“资格”,而不能赋予他以“应得”。决定他是否“应得”的不是投票本身,而是投票选他的理由。如果人们投票选他是出于对原有规则的不满,从而按照姓名汉语拼音的倒数次序(“张教授”是倒数第一位)来进行选择,那么他就不是“应得”的。前面说过,人们是基于学术成就和工作经历的理由而选择“张教授”的,业绩是其“应得”的基础。
现在“应得”与“资格”的关系变得清晰了。使一个人对什么东西具有“资格”的是规则,这可以简单表述为:A(某个人)基于R(规则)对于G(利益)是有“资格”的。使一个人对某种东西具有“应得”的是业绩,这可以简单表述为:A(某个人)基于P(业绩)对于G(利益)是“应得”的。也就是说,“资格”的重心是规则,“应得”的重心是业绩。“应得”以一个人过去所做的事情为基础,而“资格”不必如此。
那么“应得”能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我认为不能。“应得”最多只能当作“初次分配”的原则,而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主要是“再分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制度中,“应得”是一种确定工资的原则。在竞争性市场的条件下,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从需求方(公司)来看,一个公司对员工的需求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也就是由每一劳动单位的贡献之净价值决定的,而这种贡献的净价值则按照它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价格来衡量。这样,公司愿意按照贡献来分配,付给那些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员工以更高的报酬,因为他们作出了更大的实际贡献。从供应方(劳动者)来看,那些需要特殊训练而才能胜任的工作,那些特别危险或者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付给更高的报酬,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做。按照实际贡献或者特殊才能给予报酬,就是“应得”。
当代西方的主流正义理论(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反对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例如,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中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从而得到了更高的报酬,通常是由于这个人拥有更好的自然天赋或者出身于更好的家庭,而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自然天赋和家庭出身则是偶然的,从道德上看不是“应得”的。因此,“应得”不能成为分配正义的原则。但是,除了自然天赋和家庭出身以外,一个人还可以通过抱负和努力来获得成功。如果一个人通过更远大的抱负和更勤奋的努力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收入,那么我们会说这个人是“应得”的。分配正义把“应得”包括在内的主要障碍是如何确定“应得”,而如何在“应得”中区分自然天赋和家庭出身与努力和抱负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认为,在理想的市场环境中,“应得”是由市场来评价的。一个人通过勤奋工作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市场会给予公平的回报。从另一方面说,市场也只能以“应得”为评价的尺度来回报每个人的社会贡献。当然,这里所说的市场必须是理想的。因此,如果背景经济制度是市场,那么“应得”必然是一种初次分配的原则。
然而,“应得”作为一种初次分配的原则,存在着缺点。按照“应得”的原则进行分配,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是不同的,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如果这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非常严重,而且它们产生于自然天赋特别是家庭出身,那么这种不平等就是不正义的,从而需要分配正义来加以矫正。正是在这里,平等的观念显现出了在分配正义中的重大意义。也正是在这里,段忠桥教授的观点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他的观点是平等主义的,主张“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另一方面,他又赞同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把“应得”看做分配正义的原则。问题在于,平等与“应得”是冲突的,按照“应得”的原则行事必然导致不平等。
以上既是我对分配正义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也是对一些主要批评的回答,以就教于段忠桥教授和其他学界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