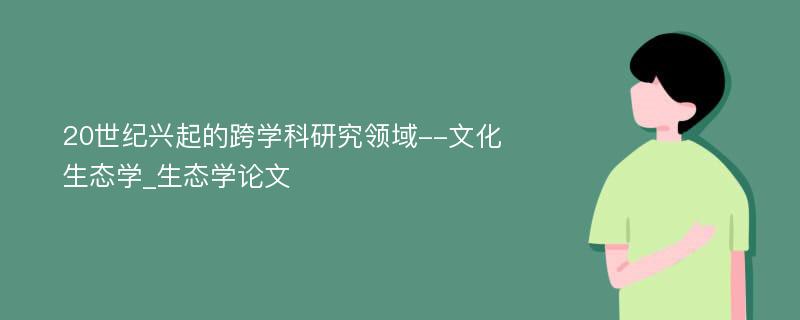
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研究领域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一个发展与破坏、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纪。在即将过去的世纪内,人类的许多追求和预言已成为现实。它既目睹了人类登月梦想的实现,也目睹了广岛、长崎于一瞬间化为灰烬。科技进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带来的后果使人类日益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和在改造外界环境方面所蕴涵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同时,又使人类逐渐认识到自身脆弱的一面和与外界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一、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
文化生态学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中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文化;或者说,人类文化如何在其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而人类的谋生方法又在如何影响着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注: Bates, Daniel G .,1998 , Human Adaptive Strategies:Ecology,Culture,and Politics,l/e,http://www.abacon.com/books/ab-0205269982.htm)
1.斯图尔德和早期的文化生态学
最初的文化生态学是作为美国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美国许多早期重要的人类学家都致力于研究北美的土著民族,他们通过认真思考文化与环境的联系,即所谓的“文化区”,为文化生态学开辟了道路。例如,一批精通欧美哲学传统的人类学家曾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人类学家深受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有关“超有机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播等多种思潮的影响。其中论证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并对后来的几代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如F.博厄斯和A.克罗伯,都采取了一种环境可能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或可供选择的机会,由本身的历史和特殊习俗决定的文化可以从中作出选择。这种文化-环境关系的“可能主义”的观点有时被认为是文化决定论(即只有文化决定文化)与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决定文化)之间的一种妥协。环境可能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重大改变,即在认识文化及其所处的环境时,转向一种互动和辩证的观点,而不是决定论的观点。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中叶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J.斯图尔德(1902~1972)发表了他的《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Change),试图证明不同文化发展的规律并概括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混合文化的类型。它的发表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作为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曾研究美国西南部土著人群体,并提出应集中研究“文化内核”,即文化中与自然界关系最直接的部分——生存或生产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内核(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形成。按照这一“文化内核”的思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形成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有着互动作用。这一想法被普遍视为最早为文化生态学奠定了明确的基础。斯图尔德的兴趣并不在于为文化生态学下一个定义,而在于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他从一种“可能主义”的观点出发,试图解释面对历史和环境提供的选择机会,文化如何作出选择。他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生态因素尽管不是唯一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他认为文化生态学就是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特殊类型的生态决定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特征 。 (注:Matquette,Catherine,Cultural Ecology,http: //www. indiana.edu/wanthro/eco.htm)
斯图尔德采用的研究方法是:(1 )用文献记录人类利用环境——即谋生——的技术和方法;(2 )观察与利用环境有关的人类行为方式和文化;(3 )提出这些行为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他指出,在旱区,人们对于降雨形式的极大关注意味着这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并导致形成一种极度突出降雨和水的宗教信仰体系,而这样的信仰体系在一个风调雨顺或实行灌溉的社会中却不大可能出现。(注:Bates,Daniel G.,Human Adaptive Strategies:Ecology,Culture,and Politics,l/e,http://www.abacon.com/books/ab-0205269982.htm)
文化生态学在形成时并没有一套正式的原理、理论或方法论。在整个50年代,它不断对以往的文化变迁理论表现出不满,认为这些理论或因其含糊不清而无从验证,或因其过于刻板而无法说明变异。文化生态学提倡的是采用一种生态学的观点来观察人类文化,主张更深入地思考自然环境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而反对当时盛行的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到了60年代末,第一代受斯图尔德影响的人类学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The Hill Farmers of Nigeria)(1968)、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Pigs for the Ancestors)(1968)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Northern Plainsmen)(1969)。由于此时的文化生态学已日臻成熟,这些著作一般都界定了文化生态学的范围,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这部著作被视为文化生态学分析的典范。拉帕波特认为,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以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来使社会正常运转:每隔几年,马林人就要举行一次仪式,把在此之前大约7年间养肥了的猪屠宰,把猪肉分给部落的每一个成员。拉帕波特说, 如果观察一下能源在马林人中间的流动,就会发现这种古怪的仪式其实寓意深刻。这种仪式是在负责养猪的妇女无法饲养那么多猪的情况下举行的。宰猪不仅为部落全体成员提供了他们所缺少的蛋白质,还减少了与临近部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为男人在打仗前要吃腌猪肉,这会使他们渴得无法长期作战)。不过,拉帕波特并没有详细介绍马林人对此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的“适应战略”。
斯图尔德对于早期文化生态学的影响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特点之一是强调过程。于是, 一些来自进化生物学的用语(如“适应”)就经常被文化生态学家们引用,来描述文化与其环境之间的联系。“适应”的概念反过来又促使对其他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如“生态龛”);(2)在概念和方法论方面, 文化生态学一直努力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通过保留文化—环境链的选择性的思想,斯图尔德还将R.默顿的中程研究和中程理论引进文化生态学;(3)文化生态学往往集中研究具体的文化, 而且经常集中研究某一具体环境中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如生产制度)。在过去几十年内,文化生态学曾注重研究所谓“自动平衡”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或多或少是平衡的),不过,近来也已开始更多地注意那些造成环境恶化和负面的环境后果的群落和背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4)文化生态学研究往往集中于农村环境, 城市环境还有待于得到文化生态学家们更多的注意。
2.对于早期文化生态学的批评
正如学术界内常见的情况一样,对于文化生态学研究也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人们对早期文化生态学的批评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早期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应被视为一个真正相互依存的自然—人类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适应环境,但并非环境的奴隶。其实,适应是指为了生存和更加繁荣而对变化作出反应。这一术语可以指由于对食物的更大需求而发展更好的技术,或随着气候和土壤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耕作方式。文化生态学应深入研究人种科学知识。一些文化生态学家(如P.理查兹和R.内廷)感到,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通常都积累了有关本地植物、动物和其他资源的丰富知识,正是这些知识使人们可以很好地适应并生活在可能非常边远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对其当地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动,是研究这些小型社会系统的重要方面。于是“生态系”研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们表明了在特定社会中这些相互关系的形式。例如,当对某一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应该将耕作对土壤质量、植物生长、水资源、病虫害的影响纳入考察范围。把“生态系”作为研究的依据常常是很有帮助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土壤侵蚀和其他环境问题(有些是由于贫困和开发不当造成的)就可以得到解释。
第二种批评是针对文化生态学研究的规模。文化生态学研究通常都是在“小型地区”进行的,因此所取得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的地区。不过,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也有其优势,即通过对不同耕作制度的比较,把像人口密度这样的因素与耕作方式、生产强度(为生产食物投入的人力和土地)和为支持这些耕作制度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联系起来了。由于文化生态学相信人类的适应能力,它已经向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和第三世界生活质量的想法提出了挑战。
第三种批评是文化生态学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长期以来,文化生态学在利用史学的研究成果(如文献、考古学著作或简单的口述历史等资源)来说明过去的状况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如对史前的灌溉系统、非洲农村生活在若干个世纪内的变化等。但同样重要的是解释耕作系统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了解地区和社会的“生态变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后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以数字化为前锋的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则使得技术与媒体的古老联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主任M.德尔图佐斯所说,信息技术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并将向人类提出严峻的挑战:穷人将变得更加贫病交加;罪犯、保险公司和雇主们则将侵犯我们的银行账户、 医疗档案和人际交往。 (注:The Cultural EcologyResearch Committee,1999,Impact of the Bit Bang & CulturalEcology,p.3.)由技术的巨大变迁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已经日益引起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关注。
在信息革命浪潮的巨大冲击下,近年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和方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环境”的概念在文化生态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文化生态学对环境的理解主要指自然环境。而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对于“媒体环境”的研究。
20世纪后期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将全部信息储存在小小的计算机芯片上的问题,带来了被称作数字革命的爆炸性的技术进步。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便捷,并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引向信息文明。文化生态学家们认为,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裨益的同时,也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污染、温室效应、能源枯竭、臭氧层空洞等。而信息文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则将更加深刻,并同样向人类提出了挑战:人们必须学习计算机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方式;还面临着认同危机和现实的丧失。它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冲突、群落的瓦解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些又将对社会的统一产生深刻影响。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下,一些文化生态学家提出:“如今能源和信息已成为我们可以交换的主要自然资源。它们是正在形成的新经济结构的价值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注:Information Revolutions—— A
Call
to
Arts, http: //infozone. telluride. co.us/radlab/InfoRevs.html)
信息文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主要在于随着以信息通信(媒体)为前锋的数字革命的深入,人类社会的传播日益借助于新的媒体,其中包括个人计算机、因特网和移动通信,从而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媒体环境”,并不断增加了媒体环境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是,如何调节人类社会(群落)使之适应飞速变化的新媒体环境,或者说,新媒体环境或新出现的信息通信系统如何影响人类文化就成为当代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鉴于媒体环境很容易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一些文化生态学家认为,可运用生态学分析技术,把文化生态学定义为对媒体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分析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考察信息流动的量变和质变,研究信息技术在某一符号环境中的影响。此类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们运用了生态学的概念,如“链”(对应于“食物链”的“信息链”)、“演替”、“顶级群落”和“共存”等。文化生态学家们认为,在即将步入新的文明的时候,人类需要明智地利用信息革命,特别是爆炸性的新媒体环境,并创造一种与文明的新发展相适应、可被称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这种崭新的信息文明应是一种持久的文明,应有助于保护和保持一种健康的全球环境,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它还应是一种鼓励社会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文明,以一种放眼全球的新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
1994年,在芬兰坦佩雷召开的国际传播研究会年会上,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他认为,新的信息社会是否能促进其成员之间的更大平等,或者,是否会加深那些有时被称作“上等”或“下等”公民的人们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教育为例,如果所有的学校——不管是城市的、郊区的、还是乡村的——都可以利用数据库、多媒体百科全书并与最优秀的教师进行网上讨论,这当然会大大促进平等。但是,只要这些条件只能被一小部分贵族学校享有,它们与其他学校之间的鸿沟就只会扩大。至于新技术在国际上是否将被主要用于扩展国际信息流动的“单行线”,或者是否有可能改善这种状况,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引用P.肯尼迪在《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的观点,认为现在与200年前的欧洲不同, 人口的力量与技术的力量不那么容易彼此抵销,因为如今的人口爆炸是在一定地区内出现的,而今天技术的飞速发展可能对生活在贫困的南方的人们不会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他担心,正在到来的电信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激化数十亿“信息无产者”对“信息有产者”的不满。他说:“政治家们现在呼吁全球关注可被称作‘文化生态’的问题。我们共有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还取决于文化和信息环境”。“对于传播问题采用一种生态学的观点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看问题时超越狭隘的国家或特殊利益的观点”。(注:Ahtisaari,Martti,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of Finland,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th]Annual Conference of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in Tampere,onSeptember 6,1994,http://www.tpk.fi/puheet-1994/p9404-IIE.html)
2.文化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在技术上的突破将根本改变现有的技术体系,带来一种可引向更美好生活的新文明。新文明将传达一种可有效利用它所产生的资源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它还会通过引进技术、制度、思想倾向和行动模式来尽量减少新文明的消极影响。围绕着媒体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当代文化生态学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承认媒体环境是一个人为的环境
媒体环境是一个人为的环境,只有通过人类社会发展和运用媒体技术才能形成。媒体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控制。国家、地区和群落可按其需要以不同方式和手段对新媒体环境进行控制。
(2)承认人类社会的灵活性
人类社会可以多种灵活的行动模式来适应环境。适应模式通常因社会群落(如地区、国家等)而异,而新媒体的扩散过程也随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电缆电视在美国十分流行并得到普遍接受,而在日本,BS卫星电视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电缆电视。在电信领域,因特网在美国十分普遍,而在日本,移动电话比因特网更为普及。
(3)承认文化的多样性
每一群落都有其自己独立的和与其他群落不相容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件好事。不过,为使多种文化社会共存,在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些最起码的共同的价值观。这是有可能做到的。此外,也可以利用这一新的媒体环境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4)应调整文化生态学的方向
文化生态学应认真研究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环境危机,探索一种可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的文化。因此,文化生态学应研究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和今后将要发生的事,而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要研究如何面对新的信息通信革命。
基于上述前提,90年代以来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主要有:
(1)数字革命和媒体环境的变化
文化生态学集中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是因特网、数字广播和移动电信,探讨这些新媒体正在如何发展以及它们对旧媒体(广播、电信和印刷媒体)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题目有:因特网、数字广播和移动电信在个人、群体、组织和群落之间散播的过程;它们对旧媒体的影响(主要指新旧媒体之间的功能替代、补充和合作关系;旧媒体是否有可能继续发展以及发展的条件);新媒体环境中,由于普及因特网、数字广播和移动电信而造成的它在“生态顶级”阶段存在的问题的特点;在全球、国家、地区以及组织、家庭和个人等不同层次上研究电视节目和电影内容的变化(包括电视节目质量的变化、互动节目的增加、内容的多样化、数字化节目的增加等)。
(2)数字革命和媒体使用的变化 公司和个人在使用因特网、 数字广播和移动电信方面的变化是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之一。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实际使用上述新媒体;调查用户的特点及其使用新媒体的动机、时间、地点、目的和方式;这些是否会影响对旧媒体的使用;哪些因素影响着对新媒体的使用;调查由于因特网、数字广播和移动电信的普及而带来的通信方面的新发明;由于新型的通信使得互动的、多媒体的、超级链接和虚拟现实成为可能,研究新的媒体使用机制、电子出版、电子商务和由于使用数字媒体而形成的虚拟社会;在个人、家庭、组织、学校和社区等不同层次上对媒体使用进行生态研究,即媒体使用中的功能替代、补充和协作关系,如何因不同目的而使用不同媒体并确保它们的共存,以及使用旧媒体的方式的变化。
(3)数字革命和媒体伦理学的变化
这是当代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之一。“媒体伦理学”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如何消除由于数字革命造成的社会问题;数字革命时代的媒体伦理学和法律;在数字时代,为使人们了解媒体知识应提供什么教育。具体的研究题目主要有:关于数字时代的媒体伦理学的常规研究和理论研究;数字媒体用户的风格;由数字革命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如在信息有产者和信息无产者之间日益加大的信息差距;信息的操纵、数字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及其防范措施等);有害信息(如暴力和淫秽内容)的传播;数字时代的隐私保护;个人信息的传播及其滥用;数字时代的媒体知识教育;数字革命的社会含义和数字媒体如何影响通信能力。
(4)数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
数字革命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研究题目有:文化同一性的变化,包括媒体的全球化是否会促进文化的同质化或多样化?数字革命对国家、民族和地区同一性的影响,由数字革命和虚拟现实引起的同一性丧失、新同一性的形成和同一性解体,虚拟社区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社区的关系等;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数字革命造成的生活方式(如衣、食、住、消费、娱乐和工作)的变化,如时尚的变化、购物方式的变化、交往方式的变化、时间利用的变化、工作方式的变化、消遣或闲暇的变化等;价值观和规范的变化,包括价值体系的变化、规范意识的变化、人的需求和兴趣的变化等;符号环境(即语言、艺术、宗教和构成现实的基本要素)的变化,包括语言的变化(如英语作为因特网上的标准语言的传播、本土语言的变化、通过使用因特网促进语言的多样性、新语言的创造和普及、口语的变化)、对虚拟现实的研究(如现实的剥夺、现实的两极分化、虚拟现实如何削弱了人的感觉、虚拟环境作用的增加及其对人们价值体系的影响等);艺术、思想和宗教的变化,包括虚拟艺术和宗教的增多、后现代思想的新发展等。
3.研究方法的调整
文化生态学研究所依据的前提是对新媒体环境的适应过程很可能因社会群落而异,因此,应将研究集中于不同社会群落适应新媒体环境的过程的异同,对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或地区的适应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新媒体有可能使边缘文化消亡,应研究新媒体环境对于曾被认为是边缘地区或边缘群落的影响。儿童——即极易受到新媒体影响的脆弱的社会群体,以及那些过分适应新媒体的人群——即媒体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4.文化生态学家构成状况的变化
从文化生态学家的学科背景来看,由于早期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人类学内部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那时的文化生态学家也大多有着文化人类学家的学术背景,另外也有一些人文地理学家参与此类研究。时至今日,在美国一些大学内,文化生态学教学也仍然主要在人类学系或地理学系作为应用人类学或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进行,其讲授的内容仍以斯图尔德的学说以及人类文化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主,这可以说是文化生态学在美国发展的主流。然而,在对于新媒体环境的研究中,为了从多角度来分析新媒体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学提倡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开展合作研究。目前,除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外,一些来自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文化生态学研究者的行列,呈现出一派多学科合作的景像。
此外,当前文化生态学家的分布改变了多年来以美国学者为核心的状况,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仅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加入了研究者的队伍,而且其他地区的学者也积极参与或开展了有关新媒体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例如,1995年,在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的资助下,国际传播研究会举办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此后,在它的每届年会上都要讨论这一问题,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变化中的传播》一书。又如,在日本,在四家与媒体和传播有关的基金会(国际通信基金、电气通信普及财团、多媒体振兴中心和放送文化基金)的支持下,日本学者发起了题为“传播新技术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究,并已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本国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情况出发,探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斯图尔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应用、媒体伦理学、文化资本的思想、城市信息环境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儿童成长与媒体生态、媒体的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传播革命的基本性质、传播革命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尤其是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新媒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多媒体与社会改造、后现代思想与新媒体的关系等。1999年9 月在吉隆坡召开的“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上,就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分别就其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交流。
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人类即将迈进信息社会的关键时刻,正确全面地认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媒体环境将给人类社会文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培养和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社会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结合时代的需求,及时了解国外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现状和趋势,开展和加强中国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不仅很有意义,而且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