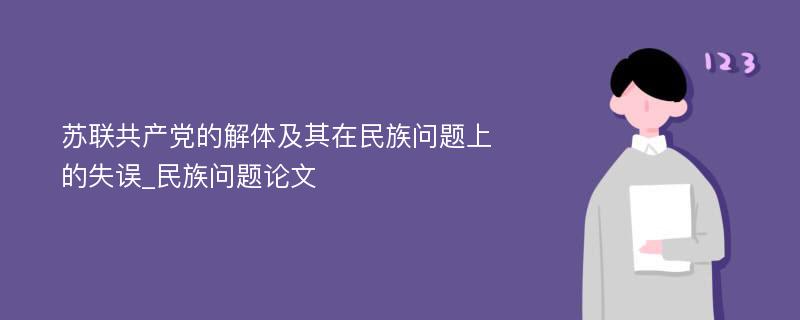
苏共自行解散与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始终极为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各民族的自主发展同社会和谐与国家进步看作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在评述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时说: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碍了它的对外政策;“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马克思尤其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民族团结。1870年7月,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盛赞:“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因为每个民族都将有一个共同统治者——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处理党内民族矛盾的,是苏联共产党。苏共在处理党内民族矛盾中所留下的,是太多的思考。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革命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被全世界共产党人作为建设的楷模。1952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的面,傲然地称苏共为“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突击队’”(注:《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2页。)1986年,它拥有1950万党员;1986年“27大”之后,每年平均约60万人入党。1991年,由苏共执政的苏联发生剧变,庞大的苏联顷刻从历史上消失,社会主义化为乌有,这支“突击队”也无声无息地自行解散。苏共的解散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苏共党内民族矛盾的翻滚和激化,是苏共自行解散的重要原因。把苏共党内的民族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大俄罗斯主义”是很片面的。应当说,苏共在民族问题上,从理论认识、方针政策,到实践举措,始终是它存在的90年历史上难解的一个死结;解不开这个死结,是苏共自行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苏共是个多民族的党。(注:80年代初,在苏共1800多万党员中,各加盟共和国党员约640万,占三分之一以上,还不包括各自治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州的党员数。党员最多的是乌克兰共产党,达280万;最少的是土库曼共产党,约4万。党员数超过50万的还有哈萨克共产党(70万)、白俄罗斯共产党(60万)、乌兹别克共产党(60万)——作者)作为多民族的共产党,尤其是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以后,如何对待和处理党内的民族矛盾,理应是苏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苏共在其存在的90多年中,长期没有正确妥善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和党内的民族矛盾,简单地以行政暴力镇压“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际上各民族(包括俄罗斯)都心存不满,各怀异志;稍有表示,即遭镇压。
在苏共作为执政党之后的74年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说,影响最深刻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在处置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的影响表现得尤其明显。
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在正确地认识到“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的同时,却在总体上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工人运动中的“瘟疫”,是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运动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0页。)斯大林不正确的思想,在苏共早年的历史上没有被其他领导人所认识,因而不仅没有澄清和纠正,反而被作为正确的思想确认下来,斯大林也被苏共认为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专家”。十月革命后,当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组成时,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职,就成了非斯大林莫属!这样,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错误思想就愈加发展起来,并成为苏共和苏联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付诸实践。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就是根据这样的错误思想制定政策,并具体执行的。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5月作出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要求原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俄联邦)结成军事联盟。(注:十月革命后,俄联邦接受和承认前沙皇俄国境内的各民族有权成立独立国家。但是,得到俄联邦承认的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都隶属于俄共(布)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俄联邦也正是通过共产党的系统,协调和指挥各苏维埃共和国。因此,十月革命后,前沙皇俄国境内的各苏维埃共和国,从法律上说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仍受俄联邦统一领导,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国际关系”——作者。)到1920年,俄联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布哈拉、花拉子模、远东共和国等国,以签订双边条约约的形式,结成军事同盟。1921年11月,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通过决议,要求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这一决定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抵制。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书记奥尔忠尼启则对此十分恼怒,宣称:要用烙铁烙平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俄共(布)中央的压力下,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屈服。1922年3月,格鲁吉亚等国成立了外高加索联邦。
1922年8月11日,俄共(布)中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草拟《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作为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苏联)的法律文本。决议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联邦。按照这个方案,俄联邦将作为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和管辖其他共和国。该决议草案提交讨论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明确反对;白俄罗斯党中央婉转地不赞成;乌克兰党中央因内部有分歧,暂不表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党中央表示赞成。
斯大林已经看到,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关键在于格鲁吉亚党中央的态度。1922年9月15日,斯大林指派奥尔忠尼启则出席格鲁吉亚党中央会议,讨论决议草案。尽管有奥尔忠尼启则亲临镇慑,但讨论的结果,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仍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斯大林的方案。但是,专门委员会无视各国党的强烈意见,于9月下旬强制通过了斯大林的决议草案。此事在俄共(布)中央引起轩然大波。
在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养病的列宁,终于出面干预此事。列宁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建议将方案的第一条:“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还批评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操之过急”。
斯大林并未接受列宁的正确意见。9月22日,斯大林复信列宁:“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真正的独立,……要么是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地联合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并将俄罗斯联邦的人民委员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正式扩展到各独立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也就是说,用语言、文化、司法、内务、农业以及其他这种含义上的真正的共和国内部自治取代虚假的独立。”(注:《斯大林就民族自治化问题致列宁信》(1922年9月22日),见苏联解密档案,载《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9月号。)斯大林尤其不能容忍在共产党内出现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情绪。他警告说:“在共产党中培养出了一些真正的、彻底的社会独立党人,他们要求在一切方面实现真正的独立,把俄共中央的干预看作是来自莫斯科的欺骗和虚构。”写到这里,斯大林觉得意犹未尽,再进一步说: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边疆年轻一代共产党人拒绝把独立游戏理解为游戏。他们对谈论独立的言辞执着地信以为真,而且执着地要求我们把独立共和国宪法逐字逐句地付诸实施。”(注:《斯大林就民族自治化问题致列宁信》(1922年9月22日)。)
看了斯大林的信,已被医生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的列宁震惊了。他不顾医生的禁令,于9月27日约见斯大林,批评了斯大林。列宁仍不放心。27日,列宁致信加米涅夫转全体政治局委员,要求重视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2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对斯大林说:“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斯大林听后,很不以为然,回答说:“我以为,反对伊里奇需要坚定性。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影响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而后者影响伊里奇,试问,这就是其中的‘独立性’吗?”(注:苏联解密档案:1922年9月28日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言外之意,似乎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意见,是孟什维克的观点;斯大林的意见,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意见”。不过,出于种种考虑,斯大林还是表示愿意按列宁的意见,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改。由于没有从理论认识上分清正确与错误,虽然对成立联盟国家的方案作了修改,但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11月,由于格鲁吉亚党中央对成立怎样的联盟国家仍有不同意见,奥尔忠尼启则竟然动手打人。斯大林则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抗议俄共(布)中央的粗暴压制,要求集体辞职之机,更换了格鲁吉亚党的领导。列宁虽然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斯大林,并且要求严肃处理此一连串事件,怎奈一则是自己重病缠身,已力不从心;二则斯大林已经坐大,并且有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等的支持,列宁想依靠加米涅夫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问题的分歧和争论以后就不了了之。
事实证明,由于没有从思想认识上加以澄清,为以后的民族政策的错误埋下祸根,贻害无穷。
在斯大林的观念里,民族是属于阶级的范畴;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也要缩小和消灭民族差别。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因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反对一切奴役而忠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因为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8-89页。)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的历届领导人基本上顺着这一理论往前走,并根据这一观念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事务。赫鲁晓夫提出了“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口号;勃列日涅夫又对“新的历史共同体”作了具体的发挥。
一、勃列日涅夫认为,由于“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在我国诞生”,所以“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就超越了民族感情”。1971年5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维埃格鲁吉亚成立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说:“没有一个人不曾体验过对于祖先的土地,对于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的语言、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习惯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和眷恋的感情。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感情——爱国主义感情——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充实了新的内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勃列日涅夫完全以虚无主义态度,否认了民族感情的存在。
二、否认民族文化的存在,认为苏联已经形成没有民族界限的“共产主义新文化”。1972年12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文化就其内容、就其发展的主要方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就其民族形式来说是多样化的,就其精神和性质来说是国际主义的。”(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4页。)勃列日涅夫称苏联的文化为“共产主义新文化”,它有着“共同的国际主义特征”,“多种多样的民族形式”,“这种文化没有民族界限,一视同仁地为所有的劳动人民服务。”(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8-89页。)对于苏共中央所宣扬的“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其他民族都嗤之以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屑地评论“苏联人民”说:“关于苏联领土上形成了所谓‘苏联人民’的神话,仅仅是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理论家们玩弄的神话。”(注: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民族是在血缘和种族等因素的基础上,由地域、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联系而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差别;但是,民族差别是否也会消失,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从现实来看,民族将是长期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多民族的长期存在,是个不争的现实。因此,正确妥善地处理民族问题,应当是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的新课题,更需要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总结,这也是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不仅会使矛盾郁积得更深;而且,即使是善意的主观愿望,也办不成好事,反而会多方面、多层次地伤害民族感情,导致民心丧失,党心涣散。苏共领导在苏联存在的74年里,应当说为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做过很多好事;苏联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历史时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有的民族甚至从中世纪状态跃进到现代文明社会。苏共中央历来也都注意吸收相应比例的非俄罗斯成员,进入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1981年3月,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后选出的22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有8名非俄罗斯人,占1/3以上。各民族共和国的部委、州、区,乃至乡镇、集体农庄等的主要领导人,差不多都由当地的本民族干部担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大俄罗斯主义”来评价苏共的民族政策。可是,尽管苏共为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培养民族人才做过诸多好事,却没有得到各族出自内心的好评,得到的是更多的怨恨。苏共在对各少数民族的工作中,之所以不能“种瓜得瓜”,主要原因是苏共中央历来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民族矛盾,刺伤了各民族的心灵。
苏联全国有150多个大小民族,仅俄联邦境内就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自治州、10个民族区,生活着100多个不同民族。各民族在宗教信仰、经济和文化水平、生活习俗、语言、心理素养等各方面,差异很大。斯大林当政年代,在大清洗中,各民族的党、政、军领导人,曾遭到大量的杀戮。斯大林推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对各民族居民的生活来说是一场灾难,曾遭到各民族激烈的反抗,但都被武力镇压。在这同时,斯大林又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将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波兰人、德意志人,统统迁往远东地区;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统统迁往哈萨克斯坦。卫国战争前夕,又以苏联国防安全为由,公然吞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强占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地区。卫国战争期间,高加索地区的少数民族,确有某些人对入侵的法西斯德国心存幻想。发生这样的事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也和苏共中央历来的民族政策有关。可是,卫国战争后期,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在这过程中,车臣人有3078人被处死,3745人被逮捕。(注:苏联解密档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治安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3年2月13日)。)集体放逐也是以军事命令的形式,按解押罪犯的方式进行的,冻饿而死、就地掩埋者,难以统计。新居住区实际上是准集中营。如此处置,从心灵深处伤害了民族感情,制造了民族仇恨。
斯大林死后,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纠正强迁少数民族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确想通过纠正过去在处置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缓解民族矛盾。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的决议。1957年2月21日,俄联邦部长会议也通过《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帮助的办法》的决议,规定在1957年内,应将17000个车臣—印古什家庭迁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苏共中央希望通过这些努力,缓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矛盾。
但是,由于苏共中央仍然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简单化、命令式地进行这一工作,不仅没有实现民族团结,反而成为对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又一次伤害。
1943年春,随着车臣—印古什等自治共和国的被撤销,车臣人、印古什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被集体放逐,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苏联政府就有计划地把大批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迁入。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后,这里也是集体安置复员军人的主要地区之一。新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以及各种企业,兴建起来。到1957年,这片土地上的新主人,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动,已使这里旧貌换新颜了;新主人也已在这里扎下根了。
苏共中央和俄联邦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帮助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家园的决议,没有在相关的苏共州委中进行研究和作出安排,甚至也没有在相关的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具体安排。象车臣—印古什原州委班子及第一书记雅可夫列夫,对即将返回的大批人的居住、工作安排,以及其他紧迫的安顿问题,毫无计划和安排。恢复后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所辖14个区的区委书记,对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也一无所知,袖手旁观。(注:苏联解密档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
1957年初,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早已闻风而动。他们自发地变卖家什,甚至不顾铁路部门的规章,强行拦车、扒车,潮水般地涌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使沿途交通秩序和社会生活,一片混乱。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大多拒绝接受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的新居住区,坚持回到原来被强迫迁出的旧住所。像沙利区,按俄联邦政府的安排,1957年应迁入1100户车臣人,但是到5月间,已有1700户车臣人涌入。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有的以暴力把新主人赶出去;有的强占学校的校舍,使学生无法上学;有的强占为少先队夏令营准备的房子;还有29户车臣人集体占据了格罗兹尼正在修理的化学建筑公司的集体宿舍。
此外,当地的区委,甚至州委领导,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更拒绝接受或安排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1957年1月14日,舒拉加特区列宁集体农庄召开庄员大会,州委书记马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也出席大会。965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成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和车臣人共同生活、工作。”(注:苏联解密档案:《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15日)。)苏共舒拉加特区区委第一书记阿布杜拉耶夫明确表示:无法为迁回的车臣人安排工作。类似的事情在安达拉尔区、里特良布区、维杰诺区,以及其他区,都不断发生。苏共中央只是简单地给予阿布杜拉耶夫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草草了事。
不少地区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返回之前就开始流传:“我们无法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共同生活”;“强盗来到共和国”;“不能把他们放进来,要么我们离开”。(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15日)。)于是,人心惶惶,大批俄罗斯人、达尔金人、阿瓦尔人和奥塞梯人,纷纷逃离。斯大林集体农庄出逃的庄员有100多户。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几天之内就拆毁住房和农庄建筑物,然后出逃。到1957年5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已1298户庄员出逃,其中971户是俄罗斯人。(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4日)。)自1957年春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被强迫迁徙的人返回家园开始,群殴、集体械斗、集体逃离等事件,层出不穷。直至70年代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塔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不同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3年1月,格罗兹尼发生大规模车臣人聚众游行示威,演成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此上报苏共中央,请求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增派特种警察部队,重新部署苏联军队,加强暴力措施。197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以及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增强国家安全机构,加强现有技术装备,以确保社会治安。
苏共中央有关民族问题的决策和处置,首先,当然是理论认识和政策制定问题。但是,除了认识和政策问题之外,如何具体实施,也是个重要问题。像苏共中央一贯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置民族问题,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不能收到良好的结果。
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民族回归家园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迫迁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别地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三
苏共中央没有根据执政的多民族党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的民族问题,结果使党的干部对如何处置民族矛盾失去了方向,各民族早已离心离德;当苏共中央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后,过去的暗箱操作都被公开曝光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急剧发展,导致党的权力中枢转移,一旦有变,瞬即自行瓦解。
苏联以民族的名称,冠名各共和国(包括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但是又不允许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表现自己的民族特点,不顾客观现实,强行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取代民族精神。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撰写《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乌克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55年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因为书中也为乌克兰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而自豪,因此被勃列日涅夫斥为“宣扬民族主义”,遭撤职的惩处,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1974年12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以下简称纳—卡州)州委书记阿鲁文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而遭批判、撤职,多名州委领导同时遭殃。
苏联的民族积怨极深,只不过一直被苏共中央以强力压制住,没有爆发出来。当苏共中央的改革遭遇挫折,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过去暗箱操作、严密封锁的情况被公之于众,引起各民族的不满。1988年3月2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由于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以来,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有248人制作和散发鼓吹民族分离、成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匿名材料。(注:苏联解密档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8年3月21日)。)一旦当苏共中央中枢权力转移,立即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1987年底开始,持续一年多的纳—卡州事件,预示着苏共中央的权威殒落。
纳—卡州位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交界处,全自治州18万人(80年代),80%是亚美尼亚人、18%是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争夺对该地的统辖权,在沙皇俄国时期就屡屡发生大规模武装争斗。1921年春,阿塞拜疆曾表示放弃对纳—卡州的统辖权。7月4日,俄共(布)高加索局通过了把该州划归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但是,斯大林得知后,立即反对,理由是:“不利于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和平。”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只得重新宣布,把纳—卡州划归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对俄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个人意见,出尔反尔改变已通过的决议的作法,十分不满。以后,一有合适时机,就要求苏共中央“纠正错误”。因此,这里的任何火星,都可能引发两国的领土之争。1987年10月,阿塞拜疆政府决定将纳—卡州恰尔达赫卢乡的亚美尼亚人国营农场的部分土地,划归邻近的阿塞拜疆人的国营农场。亚美尼亚人国营农场场长因反对这一决定而被撤职。该农场的亚美尼亚人群起反对,被阿塞拜疆政府以武力压服。消息传到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立即有市民集会游行,声援恰尔达赫卢乡的亚美尼亚同胞。1988年2月11日,埃里温街头遍布要求将纳—卡州划归亚美尼亚的传单,事态扩大。20日,纳—卡州的党州委卷入,该州的苏维埃代表集会,要求将该州划归亚美尼亚。
1988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出面,否定了亚美尼亚的要求。苏共中央在给亚美尼亚的公开信中说:目前改变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将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此决定,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和纳—卡州的亚美尼亚人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罢工、罢课。24日,纳—卡州的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28日,阿塞拜疆所属的苏姆盖特发生了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大规模暴力群斗,32人死亡(其中26人是亚美尼亚人)、197人受伤。两国互相驱赶不同民族的居民,社会秩序大乱。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党、政领导,早就卷入争斗了。实际上,早在20年代,两族之间民间争斗的背后,都站着各自的党政要人。从纳—卡州划归阿塞拜疆后,阿塞拜疆党和政府就废弃了从纳—卡州通往亚美尼亚的主要公路,70年没修过一回。到80年代,该州可以收看土耳其的电视台节目,却不能收看亚美尼亚的电视台节目。两国党、政领导人,从不相互来往;干部之间也不来往。纳—卡州的州委书记从1973年任职以来,从未去过亚美尼亚。就在苏共宣扬“新的人的历史共同体已经形成”的时期,民族对立情绪在加深,纳—卡州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1988年5月21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被撤职。10天以后,纳—卡州州委第一书记、苏姆盖特市委第一书记均被开除出党;埃里温市委书记被撤职。这一切都已于事无补了。7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重申,纳—卡州归阿塞拜疆是不可改变的,导致纳—卡州更大的混乱,在冲突中14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很多汽车被焚毁。1989年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在该州实施特殊管理形式,组成特别管理委员会,直属苏联最高苏维埃权力机关。这样,纳—卡州事件才渐趋平息。
纳—卡州事件刚趋平静,挑战苏共中央权威的第比利斯事件又爆发了。事件的起因是格鲁吉亚属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于1989年3月要求脱离格鲁吉亚;该自治共和国内的格鲁吉亚人立即集会,反对脱离格鲁吉亚。于是,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出现了对峙和互斗。从4月6日开始,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出现了严重的局势。20几万格鲁吉亚人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共产主义制度”、“打倒俄国帝国主义”、“苏联——民族监狱”、“取消阿布哈兹自治”等口号。4月7日晚,格鲁吉亚党中央向苏共中央请求支援。当天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利加乔夫的主持下举行会议,研究格鲁吉亚局势。会议同意格鲁吉亚党中央的请求,指示苏联国防部和苏联内务部向格鲁吉亚增派武装部队。4月8日,从国外访问归来的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4月7日晚政治局会议的处置意见。4月8日,三个军事直升飞机航空大队,低空在第比利斯盘旋,以示威慑。这些行动,更加激怒了群众,秩序更加难以控制。4月9日凌晨4时,2550人的苏联武装部队,使用新式战斗技术装备、毒气弹、军用小铁铲,驱赶集会群众,当场打死16人(其中13名为年轻妇女)、3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去;3000人受伤,其中183人当时就住院治疗。这一惨案招致全苏抗议,以致苏共中央组成专门调查组前去调查,惩办“肇事军事指挥官”,以平民愤。
至此,苏共中央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已无威信可言;苏共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党,已丧失了各联盟党之间的联结的纽带。1988年8月17日,苏共中央公布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提出:必须改革联邦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全联盟的权利之间建立最佳关系。但是纲领认为:联邦制的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原则上是不能采纳的。那就是说:作为联盟党,苏共中央对如何联结也茫然失措。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共产党的脱离苏共;大批党员退党,特别是一大批有影响的高层领导人退党,终使苏共这个庞然大物冰消。
1989年8月23日,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经过周密准备,于这一天举行200万人的跨国大游行。游行的人,手拉着手,组成的人链足足有600公里长,高喊:“打倒苏共”、“脱离苏联”,以此来表达对“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的抗议,显示争独立的决心。这样的游行示威,在世界游行史上也是空前的。11月2日,立陶宛共青团宣布和苏联列宁共青团脱离关系。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独立决议,宣布脱离苏共。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可夫列夫、梅德维捷夫赶紧去做工作,但不能动摇立陶宛共产党坚持独立的立场。
1991年7月3日,俄罗斯电视台向全苏报道:苏联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已正式通知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退出苏共。谢瓦尔德纳泽的退党,是和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一样,投向苏共的又一枚炸弹。7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总统令,禁止各政党在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活动。接着俄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辞职。叶利钦则进一步宣布:武装部队里的苏共基层组织为非法;封闭苏共中央总部机关;中止俄共的一切活动;禁止俄罗斯境内的武装部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党组织的一切活动。
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是“光杆司令”了。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签署法令,禁止共产党在武装部队、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警察部队及国家机关内活动。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外交部也都决定,解散机关内的党组织。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时停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活动。于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等几个最大的国家共产党,或宣布停止活动;或宣布脱离苏共,改称社会党。阿塞拜疆共产党则决定自动解散。11月6日,在十月革命74周年的前夕,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的一切活动;没收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财产。列宁创建的、在20世纪叱咤风云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结束了。
苏共的自行解散,从党内的民族关系来说,是令人扼腕的。
沙皇俄国是个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最终建立起来的周边殖民大帝国。作为周边殖民帝国,它和世界上其他老牌殖民帝国不同,即:“宗主国不仅没有靠殖民地富起来,而且自己还拿出不少东西去帮助殖民地发展。”(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语,见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这种特殊的俄罗斯式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结构关系,被苏共历史地延续下来了,还被苏共中央用“新的历史共同体”等理论包装起来。当然,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体制上的个人专制,使苏共在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科学、军事等事业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聚集在各共和国党内的民族精英,出现各共和国的个人专制独立王国。他们对苏共中央表面上是服从的;但在各自的共和国内部却是不受约束的。苏共中央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共同体”的神话,使苏共中央自愿充当各民族共和国精英集团的政治风险保障;各地方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顺理成章地推给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关于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指导、政策实践、实际情况基本上分两个阶段:50年代以前的民族精英是受难者;50年代以后的民族精英是受惠者。年轻的党内民族精英们,在改革进到“民主化、公开性”阶段,立即以先辈们的受难纪录为炮弹,万炮齐鸣,轰向苏共中央权力中枢。从民族关系方面说,苏共的悲剧几乎难以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