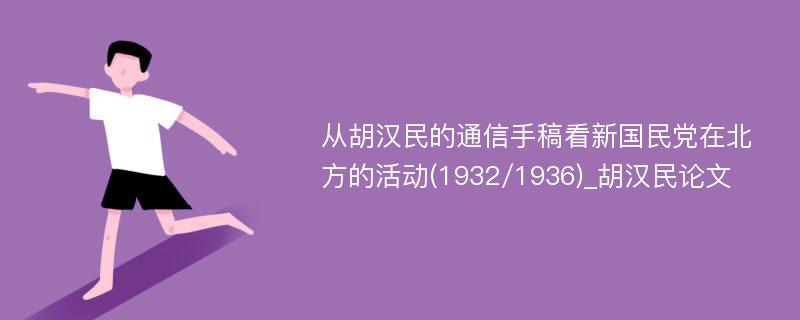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电论文,国民党论文,胡汉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6-0034-07
胡汉民等人在1930年代是否组建过“新国民党”,曾是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新国民党”的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所存留资料极其有限,一些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否认与该组织的关系(注:如1976年傅启学回忆称,“从来没有组党的提议,甚至没有组党暗示。……仅是一个谣言”。见“有关展堂先生的两件事与一个谜”(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蒋永敬教授受其误导,在研究中称,胡汉民“组党之事,……据以后证实,并无其事。”见《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4页。)。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中,有大量资料涉及“新国民党”,不仅确凿地证明“新国民党”确曾存在,且使对“新国民党”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注:关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基本情况,详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笔者依据“往来函电稿”,结合相关资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系列研究(注:参见拙作:《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载《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载《史学的传承》,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本文着重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一、以天津为中心的“新国民党”北方党务
“新国民党”建立后,胡汉民、邹鲁等人十分重视地方党务的拓展与基层组织的建设。“新国民党”地方组织重点在上海和天津,在两地设办事机构——“干部”或“交通处”,上海兼管长江流域各省的党务,天津则兼管北方各省党务。在工作重点上,上海主要是联络各路反蒋人士,从事对外宣传,天津则主要是争取北方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天津是北方大港,经济重镇,邻近北平,因而成为“新国民党”在北方的重要据点。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邹鲁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重要成员,在北方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北方“新国民党”的工作由邹鲁直接负责,“成绩(比上海)要大一点”(注:《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49页。)。因此,“往来函电稿”中涉及北方党务的,多是胡汉民、邹鲁间讨论人事与经费等重要问题,党务活动的细节并不多。然而,从中仍能看出北方“新国民党”党务的端倪。
在天津主持北方的“新国民党”党务,是曹任远(字四勿)等人。曹任远系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谢与邹鲁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曾参加北平扩大会议,对蒋介石不满,因病较少公开活动,曹任远充当了他与外界联系的代表。曹写于1986年的回忆中称:“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谢持——引者)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北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注: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著者谢幼田系谢持嫡孙。)
天津“新国民党”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永定里(今岳阳道55号),系1931年夏天用广州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子,房主人刘承烈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与西南联络的电台设在该处。由于表面上是住宅,加上一些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天津“新国民党”兼管北方各省的党务,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北平、天津、青岛在内的七省三市党务统归其负责,包括分发经费,发展新成员,传达西南方面的指令等。此外,对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也做了不少工作。
天津“新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张岱岑、裴鸣宇、蒋景瑞、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其中曹任远为总负责、张岱岑负责政治工作、裴鸣宇负责宣传工作、蒋景瑞负责民运工作,但他们“很少开会,很难开全体会,东一个西一个,很难凑到一起,有事时几个人碰碰头。”(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宣布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确定其成员的分工与经费:“天津干部鉴:顷党务改组案决定:一、上海、天津两干部、西北执行部一律取消,由主席指定一二人暂任交通之责任,经费另定;二、各省分部及各小组一律取消,至取消后应办何种实施工作,及经费若干,具拟意见及办法报告主席核定举办之;三、津宣传机关每月经费民风日报一千六百元,两通讯社共四百元,新路、民风、理论三旬刊合并为新路旬刊,以便充实内容,月费三百元;四、主席指定曹四勿同志任交通,张岱岑同志任政治问题,裴鸣宇同志任民风日报。请分别查照办理。邹鲁。马。”(注:邹鲁致天津干部电,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2件。“往来函电稿”原件均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
根据“新国民党”主席胡汉民的指定,曹任远、张岱岑两人每月津贴500元,裴鸣宇每月津贴200元(注:邹鲁致天津交通处电(10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0件。)。从上海“新国民党”的帐目看,每月500元是“新国民党”对地方干部的最高补贴。
天津“新国民党”开展了一些活动,但也有不少弊端。有人向胡汉民报告,经济方面“每月经费之浮报当在二千余元之多”;党务方面“各地党务除接洽领薪外,直无工作可言”。如“东三省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一人,山西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二人,仍月支四百元且未实际到该地办事”;宣传方面所资助之报纸为“淫词浪语之平市小公报”,等等。写信人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党务倘不加整理,则纠纷事小,其萎靡不振精神涣散则影响颇大也。”(注:述贤致胡汉民(6月16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41件。)
胡汉民对北方党务也不满意,数度与邹鲁讨论革除弊端,振兴党务的办法,他曾给邹鲁一长函,痛陈过去弊端,提出改进意见。此信不仅有助于了解“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也可窥出胡改革“新国民党”的基本思想,全文如下:
海兄大鉴:昨函言北方党务事,计已达览,顷奉手示所列七端备悉。殿英(孙殿英——引者)处款月底可汇出,请即转告相如,并略言因金融风潮,不能不稍迟之故。此外各点条答如下:
(一)华北军事政治目前无大希望,关于北方工作,弟以为有彻底更张之必要,今津部中人互相攻讦,即采取会议制,其工作成绩最多亦惟与过去等耳(即改组等于不改组),党之方针计划固未能藉以推行也。弟意津部实不需如许人,能将四勿、景瑞、岱岑调回(景瑞、岱岑等曾中央仅给予名,不予工作),只留鸣宇继续办理一部分宣传工作,另易与各方情感融洽之人(对四勿不满者不仅为津部中人,四勿自有长处,今或用非所长也)主持电台及其他应接事务,庶工作可符实际,经费方面亦可节减甚多;
(二)鸣宇等所拟宣传预算为三千五百元,属于民兴报者为二千元。弟近阅民兴等报,似无甚精彩,且此时公开办报在津沪一带色彩不能鲜明,否则必遭禁忌,不准发行,即能发行,亦无从与各大报争衡,而态度和平又失我拨款办报之本旨,故弟以为在津宣传工作应注重发行秘密刊物,定期固好,不定期尤好,式样务取于玲珑,言论务求犀利,则收效必大;
(三)新路、民风两旬刊内容粗疏浅陋,每转载报章文字以塞篇幅,装订亦极简劣,此种刊物实无从在智识界中发生力量,亟应从严整顿,大加改革。弟意应将两刊物合并为一,延能文同志主持其事,务使材料充实,并将原有新路旬刊经费裁节,如如(疑为“此”字之误——引者)办理,关于宣传方面月可节省经费二千元,而宣传之功效必能较大于前;
(四)政治活动委员会,弟以为无成立必要,岱岑延揽在华北有资望之同志,恐岱岑资望亦嫌不够,真有资望者亦未必肯来。而此项委员会之工作内容亦极难规定,至谓凡所延揽之人各人月送二百元等方法,尤非我人所宜引用也。故关于北方党务望能如第一项所言办理,以贯彻弟前拟之改革党务办法;
(五)军事特驻员固可裁撤,即军事委员会亦不必组织。锦帆(熊克武——引者)或可嘱其南回,如仍愿在津,亦可任之而月予以若干生活费。以后关于军事之工作,集中全权于中央,有所接洽则迳向中央商承,毋庸在津再组织,如此则可免组织中人之自生纠纷。而各方之军事秘密亦可保守,中央亦可观察北方各部队之需要,随时派遣人员接洽联络。个别运用较之组一委员会,罗致各方人员于一处而事不能举者为佳,且来函中所列诸人,其中数名亦断非月送贰百元即可使其来归,真为我党效力也;
(六)接济叔平(方振武——引者)事即如来拟,函协之设法可就省与商。
以上数端,请兄察之,并斟酌实行为幸。顺颂党祺
(自签)二十三、一、十四(注:胡汉民致邹鲁函(1934年1月14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21件。)
信中显示,天津“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包括在北方发展政治势力;联络北方部队,策动军事行动;办《民兴报》及《新路》、《民风》旬刊进行宣传;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从事联络。然而,其内部成员不和,矛盾重重,胡汉民对各项工作均不满意,要求缩小组织规模,调整人事,减少经费,合并报刊,暂停其对各省党务的指导功能等。邹鲁后复函胡汉民,提出如人员调整幅度过大,“似反不妙,即其对各方亦恐减少信用”。结果,只将曹任远调到广州了事(注:邹鲁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32件。)。
二、“新国民党”与地方实力派:以冯玉祥、方振武为例
吸收各地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参加,是“新国民党”拓展地方党务的重要手段。“新国民党”吸纳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收“反蒋最坚决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与蒋介石矛盾最大的人。而受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也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与经济后援。互相的需要,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天津的“新国民党”组织在功能上与上海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策动与联络北方军人的任务。因云集北方的军人多非蒋介石嫡系,是西南联合反蒋的重要争取对象。西南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部、孙殿英部的援助,均是通过天津“新国民党”完成的。曹任远回忆:“我们几个华北党部负责人除了搞党员登记,就是做军政联络工作,泰山、张家口、阎锡山那里、宋哲元那里、孙殿英那里……到处跑。”(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上海的“新国民党”成员熊克武、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等也曾为争取实力派人物而数次到达平津地区。有资料记载:“刘人瑞等人相继在华北四省、东三省和山东、河南及平津两特别市建立了国民党部。通过在老党员中重新履行登记手续,和新党员的发展,推动新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到察哈尔抗战前后,已拥有党员一千多人,其中主要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邓熙哲、熊观民、方振武、孙殿英、刘汝明、孙丹林等。”(注:江之洲、刘绍韬:《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1987年)。)
据曹任远回忆,几乎所有原西北军的将领均加入了“新国民党”,包括鹿钟麟、宋哲元、韩复榘、佟麟阁、孙良诚、秦德纯、高树勋等人,“宋哲元二十九军系统的副军长、师长、旅长都参加了新组织。”(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有胡汉民托人“送宋哲元母礼三十七元”的记载。见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卷号:173-1-171-1。)晋系阎锡山也参加了,“而且他下面的几个参议和一些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新组织,但人数远不如冯玉祥的人参加的多。”此外,傅作义系统、孙殿英系统及东北军中均有人加入“新国民党”(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张学良也是胡汉民等人争取的对象,双方一度关系密切。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注:胡汉民批注,“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2件。关于胡汉民等争取张学良的具体经过,见拙作:《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由于冯玉祥坚定的抗日立场及历史上与蒋介石较深的矛盾,争取他加入似乎是“新国民党”建立之初就有的计划。邹鲁在1932年4月让熊观民赴港面见胡汉民,请示北方党务计划。邹告诉胡,“观民兄已入党”,“冯(玉祥——引者)处各事托观民兄进行,请示以机宜”(注:邹鲁致胡汉民函(1932年4月29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8件。)。冯玉祥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五时,裴先生来见:一、带来海滨(邹鲁——引者)、佛成(萧佛成——引者)二先生之信。二、谈党务成立之条例;三、有四人在天津办党务,裴先生在内。”(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从中可以看出,裴鸣宇是从广东北返的,已将“新国民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冯,包括入党的条件(条例)及天津办党务的秘密等。两天后,冯又记道:“熊观民先生从广东来,谈各方面情形甚详,又带到陈、胡、邹、萧各一信。”(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底,熊克武与陈嘉祐再到泰山,争取冯玉祥。他们转达了胡汉民关于党务的三个条件:“第一,党的工作必须秘密。第二,党费不能用公款。第三,制度的总是须有一定的决定。”(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6日熊克武等离开时,冯似乎已下定了决心。他写道,熊等来访,“是救国抗日的一件极重大的事情”(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此时,曹任远也加入了“新国民党”,领受胡汉民等指令后返回华北,途经泰山时介绍冯玉祥加入了“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在泰山见冯玉祥,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说‘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他宣誓,我是监察人。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1933年春夏,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注: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第373页。曹任远的回忆写于1986年,其中有关“新国民党”的部分有相当参考价值。江之洲、刘绍韬著:《刘人瑞事略》(未刊稿,1987年9月)也证实曹任远为冯玉祥“办理了包括宣誓等重新登记手续”,及转交西南巨额援助款项,助其组织旧部抗日等事。见第21-22页。)冯玉祥在8月7日的日记中有与曹任远见面的记载(注:冯记道,“见裴鸣宇、曹四勿两先生,谈大局情形及锄奸团事甚详。”[《冯玉祥日记》(3),第677页。]冯日记中关于他与各方联系的记载多闪烁其辞,此处“锄奸团”似是指“新国民党”。)。
冯玉祥对“新国民党”在北方的发展也曾提出过建议,“力主北方非有干部组织不可,盖机会一至,变化立生,必有完备组织,始可与言改造全国,大局遂亦随之转移,所谓凡事豫则立也。”(注:孙丹林致胡汉民函(1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7册,第29件。)1933年下半年“新国民党”整顿党务时,胡汉民曾专门致信冯玉祥,讲述整顿的内容与目的:“党务方面,最近微有改革,一切机关式组织概行废弃,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经费之分配随之,冀矫空疏无当之弊,为实事求是之谋,想为左右所同意。”(注:胡汉民致冯玉样函(1933年11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31件。)胡汉民与冯玉祥的联络,一直保持到1936年胡汉民逝世前(注:1936年1月11日,胡汉民致书冯玉祥,提及冯派熊观民等到广州与其相见事。5月,胡过世后,冯有唁电、悼诗与挽联。见《冯在南京第一年》(冯氏丛书Ⅺ),三户社1937年5月印行。)。然而,若干年后,冯却试图否认参加过“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道,1936年“我在南京看见冯玉祥,他只点了一下头,假装不认得。下来才解释‘泰山之事不要提了’。”(注: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第373页。)冯的态度在曾参加过“新国民党”的人士中非常典型,“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这也是“新国民党”逐渐在历史记忆中消失的重要原因。
在北方实力派人物中,方振武(字叔平)与“新国民党”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率其所部3万人集体加入“新国民党”,更是一个特殊的事例(注:受西南之命在北方运动军队的汤位东,也曾向胡汉民报告某团长官拟率部集体加入“新国民党”的情况:“现驻察省赤城沽源一带之察省张北警备队骑兵第一团,原为吉省抗日部队,其团长柳树堂,连长张洪升、严起云、左行恕、崔鸿志、高振声、傅鸣九等已由柳裕民同志介绍,加入本党,其排长、班长后均可加入,全团官兵一千七百余人,诚恳的愿为本党革命基础武力,且请求西南给以相当名义,可否,请示复。”见汤位东致胡汉民电(1934年4月2日),“往来函电稿”,第14册,第17件。)。
方振武与西南建立联系较晚。1932年5月,方振武的代表孟芸生携方之亲笔信到港见胡汉民。方振武与胡原先关系实属一般,但方在信中抨击南京政府“迄今非但无抗战之决心,亦且无国防之准备”,同时表现了比一般军人对胡汉民更坦诚而恭敬的态度,表示“无论为公为私,为党为国,惟我公之命是遵。”(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2年5月9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30件。)胡汉民托人对方振武当面嘉许,并赠送照片(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1月20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29件。)。双方关系热络起来。
1933年初,冯玉祥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西南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方振武率部从华北赴察省参加同盟军。行进途中,方振武派其弟方芷南等人南下求援。方在给胡汉民的信中报告其坚定的抗日信念,提出部队行进给养异常艰难,要求西南“设法接济,速利戎机,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此外还特别提及其部队“经长时间之训练,普通均认识主义”,他“拟再涮新整理,一律加入新党之组织,以阐吾党之精义。”(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4月7日),“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46件。)由此信的内容看,方已加入了“新国民党”,且有意使其部下全部加入。这似乎是从当年冯玉祥“五原誓师”,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得到的启示。方的部队完全由他个人控制,一般军官及士兵惟命是从,没有选择政治信仰的权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加入“新国民党”与其说是政治信仰,不如说是执行命令。然而,一支部队集体加入的消息,在心理上与宣传上还是有相当的作用,或许这是胡汉民等人对方振武特别重视的因素之一。
方振武到察哈尔后,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参与收复失地工作。6月,方再派姚觉五等人南下,向胡汉民“面陈一切”,并“代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兑现其诺言。方振武还提到党与军队结合的重要性:“北方党的基础与军力之建筑不容再为忽视。否则,不但背道而驰,且将陷党国于不利。”(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6月21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33件。)
南京方面压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使其处境艰难。8月,冯玉祥被迫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事业。方振武与胡汉民等的联系更近了一层,他于8月底给胡汉民的电报如下:“展公钧鉴:仁密。前承中央电示,任武为中央干部委员兼张家口执行部委员。理合立即就职,因军事倥偬,锦帆(熊克武——引者)病津未到,兹术即克日宣誓就职,实行组织本中央党员入党条例办理,党务、军事同时并进。现已就代总司令职,统率各军亲到沽源多伦一带布防,梗午与日伪军索景星、李守信等部激战抗争,战线仍固。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如何,乞覆。职方振武叩。敬。”(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4件。)电报显示,方振武是在冯玉祥去职,抗日同盟军瓦解后才接受“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就任职务的。“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一句,表达了对胡汉民的忠诚。9月初,方振武又向西南报告党务方面的重要进展:“中央党部钧鉴:敬电谅达在案,属部已于有日正式组织成立,除熊委员(熊克武——引者)因病留津,冯委员(冯玉样——引者)去鲁休养外,武已负常委兼组织部责任,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惟经费无着,进行维艰。恳请从速确定属部每月经费五千元,以利工作,俾资活动。再,属部现称‘独石口张家口执行部’,名称似难固定,可否改称‘西北执行部’?统希电示指遵。张家口执行部常务委员方振武叩。世。”(注:方振武致中央党部电,“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4件。)可见“新国民党”在西北的组织已具备雏形: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有名称,委员间有分工,开始登记党员,要求经费。胡汉民在收到方振武的电报后,立即复电:“密。津部转方叔平同志鉴:密。世电悉,执行部得同志独力撑持,至为佩慰。名目照改为‘西北执行部’,经费已嘱按月照拨。中央。汉民。庚。”(注:胡汉民电津部转方振武电(1933年9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3件。)在“新国民党”的机构中,原无“执行部”一词,“西北执行部”更易使人联想到与之性质并不相同的“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无暇细考辨,完全照准,显露出他拓展西北党务的急切心情。萧佛成提出,对方振武的支持不能仅限于钱款,“方处党事亦不可不顾及”,他向胡汉民推荐派法国留学生、在北方从事党务的张岱岑去方部负责(注:陈融致胡汉民函(11日),“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31件。)。然而,当月方振武就因军事行动失败而流亡香港,“新国民党”的“西北执行部”随之流产。
方振武抵港后,继续保持着对“新国民党”的热诚及对胡汉民的忠诚恭敬,胡也曾多次帮助方振武(注:王养冲教授回忆:“方振武在举国不抵抗的时候,能孤军抗敌,胡先生很赞赏,特别重视这支抗日力量,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方对胡先生也很尊重。方振武军事失败后,到了香港,住在跑马地,我还受胡先生命去看过他,他也来拜访过胡先生。后来方出国,胡先生又尽其可能对随方来港的部下进行了安排。记得有人送到了广西,有人去了《三民主义月刊》编辑部。”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他对方振武褒奖有嘉:“方叔平数来弟处,渠甚振奋,晨夕读书,且分遣其旧部,到处为党务军事之工作,政会通过月给千元之费,乞按月照送之。”(注:胡汉民致陈融函(6月4日),“往来函电稿”,第18册,第17件。)胡汉民1934年6月仍将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委托给方振武负责。
总体上看,胡汉民等人拓展地方党务与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基本目标是组织反蒋统一阵线,不问其他,故许多人并未参与“新国民党”的活动,甚至对其活动知之不详。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一条线,“新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活动是另一条线。实际运用中,两条线分开,不能集中使用本已有限的资源,自然效率不彰。虽然阎锡山、韩复榘等许多原西北军、晋绥系的将领加入了“新国民党”,但“往来函电稿”证明,确实与“新国民党”有明确组织关系的,仅冯玉祥、方振武与孙殿英,其他人则相当暧昧。实力派人物加入“新国民党”,多是出于一时利益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受党的约束,谈不上对“新国民党”理念的认同与组织忠诚。
胡汉民多次提出,西南与北方实力派合作,共同实行抗日反蒋最为理想。他在致韩复榘的信中称,“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苟不能矫正此弊,则狡黠者乘之,必且正气销沉,共即沦亡。”(注:胡汉民致韩复榘函(1933年4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2件。)但南北实力派各有打算,仍是互相观望,胡汉民希望的局面始终未出现。因此,他联络北方实力派的目的基本上未达到(注:关于西南与北方实力派的联合问题,“往来函电稿”有大量资料,笔者将另立专题研究。)。
1935年下半年,胡汉民等与南京进入新一轮的接触,不久又出国养病,对“新国民党”投入的热情与时间明显减少。王养冲教授回忆,胡汉民病逝后,“新国民党”重心顿失,化于无形(注: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胡汉民死于1936年5月12日。)。曹任远的回忆是,1936年4月末,他带着新的电台密码从上海北返,准备迎接胡汉民等赋予的新使命,“不料未半月,而胡先生逝世,至此倒蒋团体失其重心。”(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胡汉民逝世后,天津“新国民党”还承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命,为胡汉民举办大规模的治丧活动,陈中孚、曹任远、任援道等人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重要职务(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此后,其成员也就各奔东西了。
“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中,除策动支持冯玉祥、方振武等进行察哈尔抗战(这也不是公开以“新国民党”名义进行的)稍有影响外,其余的联络、宣传与民运等均乏善可陈。胡汉民等多次进行调整与整顿,效果也不明显。究其原因,固然与在天津主持北方党务人员的能力、品德与失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党,“新国民党”有着许多致命的缺陷,如它的名称与政治理论含糊,只有宣传而无行动,领导机关官僚化,社会基础薄弱,内部矛盾重重,各级干部为权位、经费支配而勾心斗角,经费匮乏等等。对此,笔者拟另撰文全面探讨。
附注: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上宣读。刘绍韬先生对本文初稿提供了若干意见,谨此致谢。
杨天石研究员的《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两篇短文涉及到“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分别是:《冯玉祥与胡汉民》、《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北方“新国民党”成员刘人瑞的后人刘绍韬等撰有;《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及《“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