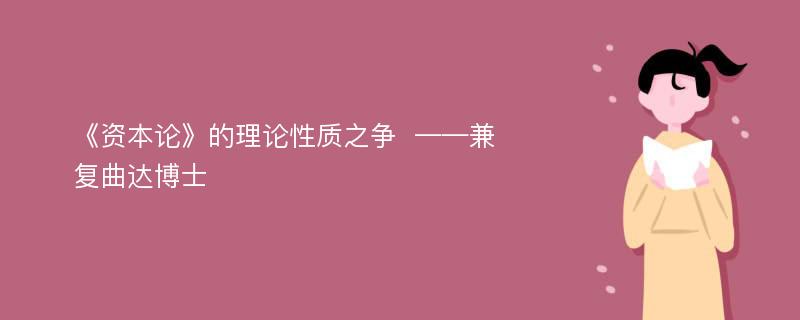
摘要:《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既非从来就有,也非没有意义。这一争论是在对《资本论》的攻击和捍卫中产生的,它不只是如何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术问题,更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事业的道路问题。《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就研究对象而言,一种学说对另一种学说的超越是以二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为前提的,如果《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那就谈不上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就研究方式而言,科学进步的历史就是其研究方式从思辨向科学发展的过程,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哲学思辨优于科学研究。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主张《资本论》是在哲学领域进行哲学思辨的成果,这种阐释不仅违背事实和逻辑,而且佐证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资本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捍卫《资本论》的科学价值提供科学哲学式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资本论》;理论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的《2017年终特刊:争鸣·哲学》将“《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评为“2017年哲学争论热点”。该刊指出:“近年来,哲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哲学著作。”而拙文《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则“对当前《资本论》泛哲学化阐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资本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一部典型的科学作品,我们要在合理的界限内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1]。曲达博士撰写《试论〈资本论〉的哲学性——兼与高超博士商榷》一文对拙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尽管拙文已经比较充分地指出了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所面对的理论困难,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里还是有必要就以下几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为什么进行《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以及这一争论涉及哪些方面?第二,什么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它为什么是经济学的而非哲学的?第三,什么是《资本论》的研究方式?它为什么是科学的而非思辨的?第四,我们应该如何捍卫和发展《资本论》?
政策二:4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意见提出,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厨亮灶。公开的重点内容包括厨房环境卫生、冷食类食品加工制作、生食类食品加工制作、烹饪和餐饮具清洗消毒(使用洗碗机进行清洗消毒以及提供一次性和集中清洗消毒的餐饮具除外)等。
一、《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的起源和内容
在对拙文的具体观点和论证提出批评之前,曲达博士首先否定了这一争论的意义。他认为,“《资本论》到底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个问题其实早已成了一盘冷饭”;“争论《资本论》所属的学科性质原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2](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白刚教授认为“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关于其理论性质的争论,就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114),石佳副教授也认为“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关于《资本论》的一个首要争论,就是《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之所以说它是首要的,是源于这一争论本身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时间之长。对马克思而言,《资本论》是作为‘哲学’著作,还是作为‘经济学’著作?这个问题……引起众多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争论”[4](1)。
在回应曲达博士的批评之前需要指出的是,白刚教授和石佳副教授的说法也是可疑的。《资本论》问世之后,杜林、洛贝尔图斯等人对其展开了攻击。杜林反对《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洛贝尔图斯自称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污蔑马克思是“剽窃者”,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捏造引文,洛里亚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庞巴维克则试图用“时间偏好理论”取代剩余价值理论。而在马克思逝世之际,世界上很多组织和个人都对他发表了评价,但无论褒贬,人们几乎都将其视为经济学家,将《资本论》视为经济学著作[5]。可见,从《资本论》出版到马克思逝世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特别关注《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至极少有人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或《资本论》理论性质问题的是柯尔施和卢卡奇;阿尔都塞也曾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波普尔、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则否认马克思主义或《资本论》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认为它只是哲学思辨的产物。然而,无论是柯尔施、卢卡奇、阿尔都塞,还是波普尔、拉卡托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关注都发生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后。《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绝不是《资本论》问世以来的“首要争论”,其影响的时间和范围也比较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确实愈发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如何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术问题,更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事业的道路问题。比如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797-798)如果我们赞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这种表述,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找到了“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非哲学著作。再如,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经济理论的批评,有学者认为他们没有读懂《资本论》——《资本论》是哲学著作,因而经济学家的批评是无效的;面对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资本论》科学资格的否定,有学者认为他们既不懂《资本论》也不理解科学,因为科学不应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资本论》恰恰是超越自然科学的“新科学”。但这些批评大多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这样的“独断”是难以驳倒论敌的。
单就“批判”而言,日心说对地心说、氧化说对燃素说、进化论对神创论都是批判的关系,但新学说并不因此就不再是天文学、化学、生物学而成为哲学了。当然,孙正聿教授所说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科学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批判。这些新学说所批判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此它们仍是科学,但《资本论》所批判的也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也必须承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像哥白尼批判托勒密那样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学说,而不关心以往哲学家们关注的那些问题。某一门学科中各种学说的更替并不会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马克思学说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也就足以成为断定《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决定性依据。
“理论性质”这一概念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主要在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82),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但阿尔都塞却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一些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也主张《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并非属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属于哲学的。第二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论》是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的成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固然认为《资本论》错了或过时了,但也不否认它是严肃的科学作品。而波普尔、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则认为《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哲学思辨的产物。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否认《资本论》是以数量化和实证化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同样认为它是哲学思辨的产物。有趣的是,资产阶级科学哲学家认为,说《资本论》不是科学或是伪科学,是对《资本论》最严厉的批评,因为这意味着《资本论》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则认为,哲学思辨是超越科学的研究方式。
“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词都具有双重含义,所以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也涉及两个方面。“哲学”“科学”可以指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的集合,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通常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集合,心理学、经济学有时也被算入其中;“哲学”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学科集合的名称。但我们也都承认,今天所说的科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比如运用数学模型和实验仪器进行物理学研究不过是16世纪之后才有的事情,但研究物理现象的专门学科在古希腊就已存在了。可见,物理学并非从来就是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以思辨的方式研究物理学,后人通常将这种研究方式所得的结果视为哲学学说。而牛顿以数学方式研究物理学所得的成果,则塑造了现代人心目中的“科学”形象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将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区别开来的唯一要素。如果我们要捍卫《资本论》,那么就必须捍卫其“硬核”——剩余价值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亲人、战友、学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做的斗争。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应该做什么呢?王南湜教授《回归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一文的标题就指出了一条道路,具体而言,“那就是正视马克思所全力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现实历史中的遭遇,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24](6)。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与主张《资本论》是哲学思辨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都认为《资本论》拒绝或无需科学检验,但前者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彻底否定,后者却认为正是这一特征,使《资本论》超越了经济学甚至超越了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全部科学。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理论困难。
高校和社会合作方的合作往往比较随意,由于合作方领导层人员的变动等原因,有可能导致合作项目流失、搁浅,甚至被取消。合作机制往往停留在口头协议、框架协议上,很难进入合同协议、制度协议等层面,有可能导致合作时有时无、前途不定。
二、如何判断《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围绕《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展开的争论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否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等于断定《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通过与经济学的关系来判断《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可以避免对经济学以及哲学本身的探讨,而只需要进行逻辑上的分析。
以自然科学为例,在哥白尼革命、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等科学革命中,新学说都对旧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有一种东西是未曾改变的,那就是这些学说的研究对象。日心说与地心说都以日地关系为对象,氧化说与燃素说都以燃烧现象为对象,进化论与神创论都以物种起源问题为对象。但显然,进化论不可能推翻燃素说,氧化说也不可能推翻地心说。因为无论一种学说是批判了、推翻了还是修正了、发展了另一种学说,它们都必须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否则新旧学说的竞争就无从谈起。这不是一个经验事实,而是一个逻辑事实。
马克思自己就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做出过明确的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82-83)在向库格曼介绍《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情况的信中马克思写道:“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10](170)而在给克林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更是直接使用了“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10](189)这样的表述。尽管马克思曾做出过如此明确的论断,但仍有学者抓住《资本论》的副标题,强调古典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而《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许是因为孙正聿教授提出“哲学是思想的前提批判”,一些学者就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提批判”,从而将《资本论》视为哲学。
正是出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分析和澄清《资本论》的理论性质才变得首要。因此,说《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早已成了一盘冷饭”还为时尚早。
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固然有一定的文本支撑和理论依据,固然也是为了捍卫和发展《资本论》,但这种阐释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徒劳的。就研究对象而言,一种学说对另一种学说的批判与超越,都是以二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对同样的理论难题为前提的,如果《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就是无稽之谈。就研究方式而言,自然研究诸学科的历史就是其研究方式从思辨向科学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已广泛出现在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诸学科中了,认为哲学思辨优于科学研究的观念得不到任何历史证据的支持。说《资本论》不是科学的而是思辨的,这不是对《资本论》的辩护,反倒是为资产阶级哲学家作证。
(2)中量营养元素CaO、MgO,主要与Corg、Na2O、Cd、Hg、B、Cu、Mn、N、Ni、P、Pb、Zn、pH呈正相关。其中,CaO与Na2O、SiO2、N、P、Zn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正相关,与Al2O3、TFe2O3、Ge呈显著反相关;MgO与Cu、F、Ni、Zn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正相关。
阿尔都塞认为,作为经济学家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是不同的。确切无疑的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所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但这与《资本论》本身的研究对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当然会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读出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科学家来说是科学著作,而对哲学家来说是哲学著作。否则对于哲学家来说,学科之间的区分就毫无意义了——事实上,确有一些学者主张对《资本论》进行所谓“超学科阐释”。
最小邻近距离法是对研究对象到达最邻近目的地的最小距离进行定量测度,从而实现可达性评价[30].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不需要设置繁琐的参数,求解过程简单,用其计算结果来分析可达性水平的高低,只是数据的定量反映,很难直观地描述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的合理性.
不仅《资本论》没有探讨以往的哲学问题,而且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还明确区分了社会变革中两个不同方面的变革,其一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其二是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认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7](3)。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得更为明确:“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797-798)⑦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说法是诚实的,那么马克思怎么会耗费其“一生的黄金时代”[10](137)以及之后更多时间去研究哲学呢?
《资本论》所要批判的学说都是经济学学说,这已经足以证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经济学是一致的。如果说《资本论》研究的是物与物关系背后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只是研究“物”的吗?如果它们只是研究“物”而不能触及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又何必将它们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呢?又何必去批判它们呢?显然,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的不是对象,而是结论,不是一方研究“物”、一方研究“人”,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斯密和李嘉图都为既有的范畴所束缚,拉瓦锡和马克思则分别实现了各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革命”,但正如拉瓦锡并未因此“超越化学”而进入哲学思考,马克思也与斯密、李嘉图一样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领域中。如果《资本论》是哲学著作,那么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应是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来源、真善美的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③。至于有学者以《资本论》关注“人的存在”为依据证明其是哲学著作的做法,拙文《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已经做出了确切的批 评[11]。
当一名哲学家认为全部经济学家都没有读懂《资本论》,甚至马克思自己说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也不可信,而只有他洞见了《资本论》真实的研究对象时,那么他的阐释就越过了合理的界限。
三、如何判断《资本论》的研究方式?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哲学本身就是物理学,不过是理性物理学”,“精确地说来,把自然哲学同物理学区别开的东西,是两者各自运用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物理学的普遍东西是抽象的”,“不向特殊性过渡”,“特定的内容就是在这种普遍的东西之外,从而分得支离破碎,各各孤立”[12](15)。可见,黑格尔认为自然哲学与物理学(即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区别在于研究这些对象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⑤。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标题就已经清楚表明,他要以数学的方式研究自然。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牛顿的研究方式称为“科学”,而黑格尔的思辨的研究方式则继承了“哲学”的古老名称。需要注意的是,物理学并非从来就是科学的,作为学科的哲学也不必然是思辨的。赖欣巴哈就认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13](3)。
六是要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重点,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采取综合措施,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政策和市场环境,逐步建立起节能和能效、洁净煤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及森林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前文已经表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本不该有争议,甚至不必考虑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只需看到绝大多数人都不怀疑《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竞争关系,就足以在原则上证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经济学是一致的。如果一定要说《资本论》是哲学著作,那就等于说经济学是哲学,进而就没有什么不是哲学了。但《资本论》的研究方式却是可以争论的。一方面,《资本论》写作的宏观背景是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并深入到一切领域的时代,马克思也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4](191)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说过他的“实际方法”就是“辩证方法”[7](93)。
但是,运用辩证法并不等于就是哲学著作。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6](902,892)。科学家也要以辩证的方式思考,因而辩证法绝不能与哲学思维方式画等号。与之类似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抽象力”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是否运用“抽象力”构成了《资本论》与其他科学研究的区别。他们认为其他科学研究都只是观察和归纳,《资本论》运用“抽象力”则超越了经验水平的研究。然而,科学家当然也要运用“抽象力”。马克思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研究是十分艰难的,不像自然科学还有实验工具可用。但是,经济学研究绝非只依赖“抽象力”,它同样需要经验材料,马克思就多次指出他的学说是实证科学⑦。可见,对辩证法和“抽象力”的运用都不能说明《资本论》是哲学思辨的结果。
资产阶级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对《资本论》的科学资格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批评是多余的,因为《资本论》根本就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波普尔就批评过《资本论》的不可证伪性,说它“永远不必担心未来经验的反驳”[15](475)。虽然拉卡托斯反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但他同样批评马克思主义“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纲领,而且总的来讲是毫无价值的”[16](122)。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谈“马克思思想的实质”时说,马克思“从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的汇合中得出一种批判性的观点”,“他对资本主义的大灾难和世界通过革命得到拯救的预言性幻想表面上植根于严格的科学”,“然而,它包含了许多拒绝科学检验的因素,并且使他的观点有了一种可做各种不同解释的特征,被解释为某种戏剧性的观点,某种充满魔鬼和英雄的神话或者某种特殊的现世宗教”[17](394)。
作为不同学科或学科集合的哲学与科学是分工且合作的关系,物理学或许能够为伦理学奠定基础,但它并不能取代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存在所谓的“科学把哲学驱逐出其世袭领地”[8]的说法。而作为不同研究方式的哲学与科学则是竞争关系,它们面对同样的对象,无论它们得出不同的结论,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得出相同的结论,都意味着两种研究方式之间存在优劣之分。文德尔班在批评谢林的自然哲学时说:“如哲学得到的是与科学相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无用,如哲学还希图提供与科学不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危险了。”[9](12)之所以要将这双重含义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关于《资本论》是科学还是哲学的争论,有些是围绕其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有些则是针对其研究方式而进行的,不能一概而论。那么,《资本论》究竟是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它到底是科学的还是思辨的?②
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相信,哲学是超越科学的,科学只是对事实的描述,哲学却是理想性的、批判性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一些学者表面上承认《资本论》是科学的,但却要求重新理解科学,认为仅仅描述事实的自然科学是不能真正代表科学的。实际上,他们就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资本论》来塑造科学的形象。因此,如果以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典范,那么这些学者也就不承认《资本论》是科学了。黑格尔是认为哲学高于自然科学之观点的典型代表。与康德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牛顿力学的推崇相反,黑格尔对自然科学持批评意见,并对牛顿抱有成见,他认为现有的自然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有学者就主张德文“科学”(Wissenschaft)所指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高于”英文“科学”(science)的所指,认为《资本论》是前者,因而超越了作为后者的古典经济学⑧。但包括康德对“科学革命”的论述在内的大量证据表明,这两个词并没有先天的区别[18](145-15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者们已经明确表明他们反对思辨而主张实证科学,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更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19](233)。且不说思辨方式是否真如一些分析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所言是无意义的、落后的,就说这些学者为了证明《资本论》是哲学思辨而非科学研究的结果,不仅要反对科学哲学已取得的基本共识,还要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相关表述,实在是得不偿失。
至于波普尔等哲学家,实际上他们批评的不只是《资本论》,同时也批评了与《资本论》进行理论斗争的经济学家,批评他们没有看到《资本论》根本就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本来无需严肃对待。然而要想驳倒《资本论》,就必须在科学上对它严肃对待,因为《资本论》的理论是可以验证的。作为《资本论》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就是可证伪的——皮凯蒂宣称通过大数据计算证明了“长期以来资本纯收益率事实上的稳定性”[20](210),这在经济学上对《资本论》是一个挑战,但在科学哲学上却恰恰证明了《资本论》并非哲学思辨的产物,它是可以验证的。
科学哲学家们往往片面夸大科学某个方面的特征。事实上,实证性、可证伪性、拥有研究纲领、拥有范式、数学化等特征共同构成了科学与其他意识活动的区别。就这些特征而言,《资本论》的研究方式既属于经济学范式,也属于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科学的范式。比如见田石介就认为,《资本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很久以前的数学、自然科学就开始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被看做是科学的唯一方法”[21](5)。王南湜教授也认为,《资本论》“在本质上与作为科学之典范的自然科学著作并无实质上的不同”[22](5)。
干预前两组生命体征循环指标相近,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命体征循环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2.
但科学学说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主张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的学者很可能就是为了使《资本论》免受经验的检验而将其阐释为哲学。他们甚至主张,《资本论》以哲学的方式超越了以科学方式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然而,科学研究方式固然还未完全取代思辨的方式,但思辨的方式取代科学研究方式的情况则从未出现过。因此,说《资本论》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哲学思辨的结果,一方面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则可能不仅达不到为《资本论》当代价值辩护的目的,反而为控诉《资本论》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证词。
四、结论:应该如何捍卫和发展《资本论》
对于《资本论》与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关系,恩格斯的一系列表述提供了确切的说明。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恩格斯提出,“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7](6-8)。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但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无法解决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要求利润之间的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7](70-71)。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用化学史上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与前人的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但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7](302-303),马克思是剩余价值真正的发现者。这正如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最早析出了氧气,但人们却将拉瓦锡视为氧气的真正发现者一样。
实话实说,本期针锋相对是我们结论下得最晚的一次。当你越是了解两台机器的特性,就越难分辨孰好孰坏。对于拍摄体育或者野生动物这类“硬核”需求,尼康D500的优势明显。尽管两者纸面数据非常接近,但在极限条件下,D500的光学取景器具备先天优势,表现超强的对焦系统保证了更高的拍摄成功率,再加上超大的缓存容量以及更快速的存储介质支持,D500在这一领域上优势明显。
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它徒劳无功。这些学者不是一般性地研究《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他们的研究是为捍卫和发展《资本论》而服务的,是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做辩护的。辩护是针对控诉而做出的,没有控诉的地方,辩护就没有意义。一些学者用大量笔墨阐发《资本论》对人的存在的剖析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试图以此来证明《资本论》的意义和价值。但对于《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道义力量,就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严厉的批评者们也是抱有敬意的。资产阶级学者宾克莱对马克思的评价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23](106)。我们能否严肃对待并驳倒宾克莱?还是嘲笑他根本不懂马克思?
2.2.3 插秧深度的调整。根据农艺生产要求,机插秧深度应达到“不漂不倒,越浅越好”。早稻的插秧深度一般为10 mm,插秧深度调节是通过插秧深度调节手柄来调整,共有4个档位,往上为浅,往下为深。还可通过换装浮板支架上6个插孔来调节插深。
温度计不能直接接触试管瓶底,更不能待燃烧完全后再测水温,用橡胶塞打孔后将温度计固定在水层中部,同时试管瓶口部加橡胶塞也可以减少热量散失。
面对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规律的批评,王南湜教授分析了这一规律尚未得到证实的原因,即这一规律必须在单一市场中才是有效的,而当前现实世界市场并非如此。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正在展现出走向世界单一市场的趋势”,“如果全球化发展的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最为重要的规律就有机会获得经验证实,从而也就能够直接展现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现实力量”[24](6)。这是一项典型的科学哲学工作。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在科学接管了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之后,哲学的对象就只能是科学了。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这种看法,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科,《资本论》理论性质问题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对象。
关于自媒体舆论监督权对审判权规约作用介入的时间选择,现阶段的制度规范对此则疏于规定。鉴于自媒体舆论监督与传统新闻采访报道在价值取向、规律特点以及传播内容等层面的显著共性,现阶段用以规范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报道的制度规章,无疑为自媒体舆论监督限度的厘定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示范。
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存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争论——包括《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就不会停止,但在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内部,则应尽可能地达成共识。维特根斯坦将《逻辑哲学论》比作“梯子”——“登上高处之后,要把梯子丢掉”,同样,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也不应该持久地存在下去。这一争论最终将成为一盘“冷饭”,而那时我们也已真正理解了《资本论》的性质和意义。
注释:
①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标题最恰当地说明了,科学就是以数学的方式去研究在传统上属于哲学的问题的活动及其成果,因此,自然科学也就是数学化的自然哲学。
② 当我们讨论研究对象时,更适合说具体学科而非“科学”;而当我们讨论研究方式时,更适合说“思辨”而非“哲学”。物理学并不从来就是科学的,它也曾是思辨的;哲学不必然是思辨的,它也可能成为科学的。
③ 关于《资本论》与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研究对象的一致性问题,参见拙文《〈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第255页。
运用丰富多样的交流互动形式来开展各类活动,并逐步形成一定的模块和一套完善的系统,使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框架体系至关重要,也是打造一项品牌活动的关键。世界文明之旅文化季活动的视觉影像、珍本图书、专题讲座、学术研讨、电影展映、文化体验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不同类型活动的开展,对于激发读者参与图书馆活动的积极性、吸引读者更多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④ 有学者或许会指出,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哲学特指“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这样的哲学。但是,一方面,恩格斯从未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这样的表述(参见拙文《〈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一词是否适合称谓马克思的理论》,《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22-28页);另一方面,如果“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是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经济学和经济史又该研究什么呢?
⑤ 曲达博士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划分,至少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传承体系中,是糅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是科学,因为哲学是把真理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哲学是高于一般的具体科学的。”其错误在于:(1)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明确区分了哲学与科学;(2)既然“哲学是高于一般的具体科学的”,那么它们就不是“糅合在一起的”;(3)“哲学高于具体科学”的观念早已被学界主流抛弃,遗憾的是,主张《资本论》是哲学著作的学者通常都是通过“哲学高于科学”和“《资本论》是哲学著作”来证明“《资本论》高于经济学著作”的。
⑥ 曲达博士反对将“数学化”视为科学的本质特征的看法。这一看法不是拙文的突发奇想,而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不仅柯瓦雷、克莱因、卡尔纳普等一大批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主张这一观点,就连对科学持审慎态度的胡塞尔、阿尔都塞,甚至主张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的学者们也都认同这一观点。曲达博士试图以《物种起源》和斯宾诺莎《伦理学》为例分别证明“数学化”对于科学来说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但《物种起源》的科学性在于其能够得到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进化论至今仍是一个假说,现代生物学建立的标志则是数学化的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伦理学》试图模仿《几何原本》,但“几何化”不等于“数学化”,何况《伦理学》跟“几何化”也没有任何关系,它试图实现的是“公理化”且最终失败。曲达博士显然混淆了“正确性”与“科学性”、“数学化”与“公理化”。
⑦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与通常意义上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实证科学不是一回事。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
⑧ 参见庄忠正:《〈资本论〉的“科学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3日第3版。关于“Wissenschaft”在范围上宽于、在层次上高于“science”的论述,参见邓晓芒:《作为“大科学”的人文科学——一种“正位论”的思考》,《哲学分析》2016年第2期,第111-119页。
参考文献:
[1] 周丹.2017年终特刊:争鸣·哲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1-09(06).
[2] 曲达.试论《资本论》的哲学性——兼与高超博士商榷[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14.
[3] 白刚.《资本论》:“科学”还是“哲学”?[J].社会科学,2019(2):114-120.
[4] 石佳.《资本论》的术语革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5] 丰纳.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孙正聿.论哲学的表征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7(3):246-252.
[9]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1] 高超.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J].哲学研究,2017(8):11-17.
[12] 黑格尔.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 拉法格.忆马克思[C]//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5]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6]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7]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8] 高超.“科学”意谓一种标准——与邓晓芒教授商榷[J].哲学分析,2017(3):145-151.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1] 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22] 王南湜.《资本论》的辩证法:历史化的先验逻辑[J].社会科学辑刊,2016(1):5-17.
[23]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4] 王南湜.回归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3):1-6.
The debate over the theoretical nature of Das Kapital: Also in response to Dr.Qu Da
GAO C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debate over the theoretical nature of Das Kapital was born in the attack and defense of the book.It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problem about how to read Marxist classics,but also a path problem about how to develop Marxist career.The debate is mainly related to two aspects.As fa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s concerned,the transcendence of one doctrine over the others is premi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two have a common research object.If the object of Das K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lassical economics,then there is no transcend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cs.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progress is the process of its research from specul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There is no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is superior to scientific research.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in the final analysis advocates that Das Kapital is the result of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This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violates facts and logic,but even corroborates the bourgeois philosophers' criticism of Das Kapital.Marxist philosophy should provide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fending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Das Kapital.
Key Words:Das Kapital;theoretical nature;research object;research method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5-0016-07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5.003
收稿日期:2019-01-01;
修回日期:2019-04-03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科学性问题研究”(19YJC720010)
作者简介:高超(1988—),男,辽宁本溪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联系邮箱:gaochao@jlu.edu.cn
[编辑:胡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