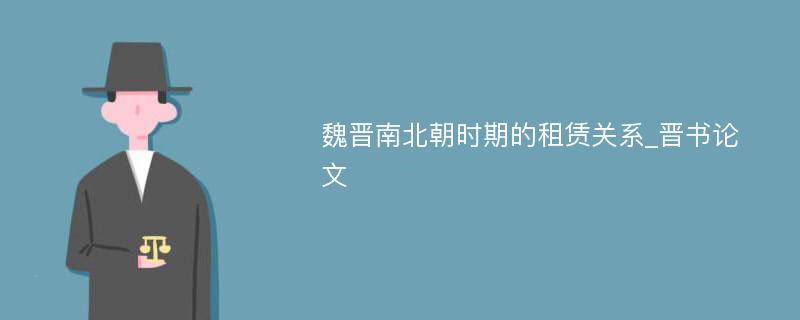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时期,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的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分田劫假”和“与田户中分”之类的租佃关系。隋唐时期,无论在公私土地上,租佃关系均有所发展。介于两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怎样,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呢,还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呢?长期以来,庄园经济论较为盛行,其后则有田墅经济论和田庄经济论。三者之间虽然有些区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集中经营是本时期地主阶级处置其土地的主要方式。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本时期地主经营其土地的方式,既有集中经营的庄园或田庄,也有租佃方式,但无论在地主土地上,还是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均占主导地位。本时期的租佃关系确实有其特征,租佃者的身份地位普遍低落,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继秦汉封建法令中的良奴之分,此时出现了良贱奴三者之分。其中的贱,就是地主的依附民和官府的依附民。受此影响,贫困农民或逃避赋役的农民以投充的形式成为租佃农民后,身份地位急剧低落,我们称之为非法依附民。他们是租佃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里先讨论地主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当另文撰述。有关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论者甚多,本文只是约略涉及,不再展开,以便集中在租佃关系上进行讨论。
一
在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中,有两桩“借”田事件颇堪注意。一桩出现在汉末魏初,一桩出现在北朝后期。跨越三个多世纪,包罗了魏晋南北朝的一首一尾。今先抄录再作分析。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说:“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
《周书·寇儁传》说:“永安初,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下,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儁曰:‘史底穷民,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知之,嘉儁守正不挠……其附椿者,咸谴责焉。”长史以下所以皆言椿直,关键是杨椿坚持这块田地是“借”的。不过,《魏书·杨播传》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借”田的不是杨椿,而是其兄杨播:“授安西将军、华州刺史,至州借民田,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 披诉积年”。既然说杨侃“等”“披诉积年”,必有杨椿参加。因为这一家是以“不异居、异财”,“昆季相事,有如父子”闻名于世的。所以实际上是杨椿以司徒之尊代其兄杨播打官司,最终杨椿败诉,说杨椿“直”的官吏都遭到了谴责。
任嘏没有向邻居收租,杨家也决不可能向穷民史底缴租,表面上这两件事看不出什么租佃关系。但任嘏说邻居没有“擅耕”,是他“借”给的,抱不平者就此无话可说。杨椿坚持其兄是“借”田,只要成立,便可为其兄翻案昭雪;阿谀奉承的官吏也就认为“直”在杨椿一边。他们目的不同,用意有异,为人开脱或为己辩解都牢牢扣住了一个“借”字,岂非说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民间还是官府,都认为“借田”是合理合法,天公地道的吗?而这正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租佃关系盛行的一种反映。因为租佃关系的产生,恰恰是从借种他人田地开始的。借种田地,向田主纳租,这就是租佃关系。它确立于秦汉,到此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实经济生活中又普遍地、大量地存在,才会在民间和官府形成合理合法的观念。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租佃关系更多地以投充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借田毕竟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投充只是其变相而已。
如果说上述借田只是租佃关系的推论,那么下述史料是确实可以看到租佃关系的。
《晋书·李特载记》载,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朝廷及地方官吏勒令他们限期返回故乡,“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华阳国志·大同志》有关李特起事的经过,与《晋书》大体相同,有关“佣力”却略有小异:“随谷佣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有的同志诠释“随谷佣赁”为“哪里有粮食吃就到哪里当雇工”(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31页。)。 唐长孺先生据“求至秋收”认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农而是当佃农”(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8页。)。 我们认为既有雇农,也有佃农,而且是以佃农为主。就文义而言,“佣力”讲的是雇农和雇工,“佣赁”则既有雇农、雇工,也有佃农,这里应以佃农为主。因为大凡佣作,大都是按日计酬,随即领取的。如三国时的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日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注:《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管宁传》注引《高士传》。)扈累“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注:《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管宁传》注引《魏氏春秋》。)。又如刘宋时的郭原平,“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炊”(注:《宋书》卷九一《孝义·郭世道附子原平传》。)。正史中是这样,杂史中也是这样。如《高僧传·亡身》记载,释昙称在彭城“佣赁获直,悉为二老福用”。可见这是当时通行的惯例。只有佃种土地,才须“秋收”“冬熟”方有收获,所以唐先生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何况这支流民队伍有“数万家”“十余万口”(注:《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之多,他们进入梁益二州后,分布在梓橦、广汉、蜀郡和犍为四郡,以成都平原居多。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全盛时,这四郡合计不到9万户,约58 万左右人口(注: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平均每户6.4—6.6人。)。流民即便以10万计,也已为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上下了。在成都平原,比例将会进一步增高。若非租佃关系,是极难容纳的。因为租佃制下,佃种土地的多寡,具有相当大的弹性。退一步讲,即便他们大都是雇农或雇工,也必须以这里租佃关系盛行为前提。如果是集中经营,想在短期内就容纳这么多雇佣劳动力,也是决无可能的。
若是梁益二州因“佣力”“佣赁”诠释的不同有所歧义的话,汉中地区就明朗得多了。《晋书·张光传》记载,张光发兵讨伐杨武和李运等统领的流民的借口是:“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佃农”,大概应以“佃租土地从事农耕”这样的诠释较为合适了吧。这支流民群有“三千余家”。《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全盛时汉中有“户一万五千”,流民相当于当地居民的20%左右,他们流入后,官府要求他们立刻“佃农”,否则便是罪不可绾,必须讨伐,岂非说明这里盛行着租佃的关系。
此外,在吐鲁番文书中,有编号为66TAM62:6/1和66TAM62:6/4两张文书,记载了翟强和一位叫绩(责)的人因共治六亩葡萄而打官司的事。这是两张残缺文书,但文书中“要”字甚多,且有“绩蒲陶六亩与共分治”,“蒲陶三分枯花”,“强家理贫穷”,“绩辞索诉”,“要从大例”等语。胡如雷先生《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注:载《文物》1978年第6期。)一文, 参照同时的其它文书,对此进行了考索论证,指出:1.时间为十六国后期。2.“要”字的含义是契约。3.所谓“共治”是翟强佃种绩的葡萄园。4.因葡萄枯花减产,双方在分配上发生争执而打官司。最终断言这是“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这两件文书是打官司的申状,并非契约原件,因此是否契约尚可讨论。但上述考索及指出翟强和绩之间是租佃关系,我们是同意的。值得一提的是“要从大例”这四个字。所谓“大例”,应是指当地的惯例,如租佃纳租和减产减租之类。只有吐鲁番地区盛行租佃关系,才会出现这种习惯法,否则不会用“大例”二字概括租佃纳租及减产减租之类的内容。
一般而言,吐鲁番地区租佃关系的发生和发展,要比凉州和中原稍许迟后一点,或者说受凉州或中原的影响。凉州地主是否用租佃方式来经营其土地,此处暂时存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曹魏统治时期,凉州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相当发达。《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他出刺凉州后,“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我们知道,曹魏民屯是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地方官吏无权处置民屯。同书《仓慈传》注引《魏略》说,京兆太守颜斐和长安典农是“各得其分”,正说明曹魏民屯官吏和地方官吏各司其责,严格区分,互不干涉。所以这里的“募贫民佃之”,不是募贫民屯田,而是募贫民佃种国有土地。即便是民屯,那也是租佃关系(详见另文)。
二
持庄园经济和田庄经济论的学者往往视东晋南朝为其典型阶段,以谢灵运和孔灵符等为主要例证,特别是谢灵运的始宁山墅。再说一次,我们无意否认此时有集中经营的庄园或田庄的存在,鉴于地主合法占有依附民后,具有世代奴役的权力,如果其地产集中,是有利于他们采用庄园或田庄之类经营方式的。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固然有地产集中或相对集中的大地主,也不乏地产分散的大地主,甚至后者要多于前者。如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注:《晋书》卷三三《王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注:《晋书》卷三三《石苞附子崇传》。石崇的金谷园十分著名。据其《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三),这个园也不过是“金田十顷”,显然不是其全部地产,否则不可能说“称是”。其他地产应是分散各处的。);魏咸阳王元禧“田业盐铁,偏于远近”(注:《魏书》卷二一《咸阳王禧传》。);谢弘微经营的田产,至少分布二十余个地方(注:《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王羲之和谢安借游山海之名,“行田,视地利”(注:《晋书》卷八○《王羲之传》。),估计其地产也不可能集中。史称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注:《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注:《宋书》卷五四《孔季恭附子灵符传》。)。他们并非只有一个始宁山墅或永兴墅,还有不少地产是分散的。很难说他们在分散的地产上建立起一个个庄园或田庄。对于分散的地产,似乎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比较合宜。《陈书·周迪传》说,他“外诱逋亡,招集不逞”,“害及四民”,在临川侵占了大量土地以后,其役属者“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然后“征敛毕至”。“民下肆业”表明其田产是分散的,其奴属杂在农民中进行生产,有“征敛”负担,显然该是租佃的方式。即便集中的地产,有时也往往采用租佃方式。如王导在大爱敬寺侧有田80顷,传了好几代,直到梁朝时才被梁武帝强买了去,送给大爱敬寺。据《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齐书》,这80顷地一直是和“故旧共佃之”(注:查《南齐书》、《梁书》及《南史》,《王骞传》中均无是语,《太平御览》所引必有所据,此处不予考证。)的。也就是说从东晋到梁,这片地产采用的是租佃方式。又如晋安帝王皇后在琅邪临沂和湖熟交界处有40顷脂泽田,也是很集中的大地产,是“悉以借食(贫)民”的,直到她死后,才“以赐贫人”(注:《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晋要事》,《晋书》卷一○《安帝纪》。)。既然说“借”,肯定要收租,否则脂泽从何而来。前述梁州、益州、汉中、河北等地租佃制盛行,同样是包含大地产和相对集中的大地产在内的。
众所周知,自东汉中后期起,地主、特别是士族和地方豪强,就已拥有大量的依附民,被称为客、僮客、奴客、僮仆、田客、附从、部曲和佃客之类。适应这一趋势,封建政府被迫承认其合法性。合法依附民的出现,是从东吴的复客赐客制、曹魏的给客制和蜀汉的配客制(注:有关蜀汉配客制,参见拙文《由户口变动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主经济》,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开始的。西晋的荫亲属和荫客制及东晋的给客制使士族及官吏普遍享有了这个特权。在《晋书·食货志》中,凡属合法依附民,被统称为“佃客”,即便依附民中地位稍高,以人计数的典计等,《隋书·食货志》也不忘特意说明:“皆通在佃客数中。”《晋书》和《隋书》都是唐代官修史籍,《五代史志》更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和通人撰写,隋及唐初公私土地上的租佃关系比两汉发达,他们应该清楚。他们用“佃客”来统称合法依附民,而且两史的《食货志》都一样,就不能以文人撰文或随意书写这类情况来解释了。一句话,封建史学家在这里使用“佃客”二字统称合法依附民,是与地主经营其土地的方式,特别是合法依附民实际的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在奴役和剥削其依附民时,更为普遍和通常的行为,是采用租佃方式。中原如此,江南如此,置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凉州也应如此,所以才对吐鲁番有深远的影响。有关于此,刘宋初年尚书省就符伍制度召开的一次八座会议,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佐证。这场争论是由同伍犯罪,士族应否连坐引起的。与议者大都不同意连坐,理由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庶缅绝,不相参知”。有人主张士族虽不连坐,其“奴客”却应代替主人顶罪,理由是“奴客与符伍交接”。尚书王淮之反对最烈,他承认“奴客与邻伍相关”的现实,但却不是主人的邻伍,而是与主人毫无关系的邻伍,要他们与主人的邻伍连坐,于理不合。即奴客是杂居在其他邻伍之中的。进而指出:“有奴客者,类多役使,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注:《宋书》卷四二《王弘传》。)有关奴客应否连坐,这里无需讨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类多役使,东西分散,住家者少”。王淮之并没有完全否认奴客“住家”,即与主人共居的现象,但很少,且从事家内劳动,“出门甚寡”,即不从事生产。更多的、大量的被“役使”,即从事生产的奴客是“东西分散”的,就是典计在家者也是“十无其一”。对此,与议者均无异议,岂非说明“东西分散”,实质也就是分散经营是地主役使其依附民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吗。既然如此,租佃方式无疑是较为适宜的。这就无怪乎颜延之在其《庭诰》中阐述他“役徒属而擅丰丽”的要诀时说,听其“自理于民,自事其生,则督妻、子而趋耕织”(注:《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了。在颜延之看来,被他役使的“徒属”们的生老病死与他无关,若让他们“自事其生”,他们必然会全家努力从事耕织的,他只要坐享其成便可以“擅丰丽”了。
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方式盛行,才会在国有土地上出现二地主的现象。所谓国有土地上的二地主,指的是豪家富室借取公田之后,转租给贫困农民,收取高额地租。《梁书·武帝纪》所载大同七年(公元514年)的诏令堪称典型:“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 贵价蹴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贵价蹴税”,指的就是借取公田后以高昂的地租转租给贫民。这相当普遍,否则不会反映到诏令里来。“伤时害政,为蠹已甚”,看来是为时已久。“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显然是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并承认这个现状。“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其实,相当数量靠租佃为生的贫民,基本上不具备“种粮”或其它生产手段。这个诏令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允许“贵价蹴税”继续下去。豪家富室借取公田后采用租佃方式来经营,实质上是将他们经营自己土地的方式使用到借来的国有土地上而已。
寺院地主出现于东晋,形成于南北朝,同样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民。北方叫僧祇户、佛图户或寺户;南方叫白徒养女或寺观户。寺院地主是怎样经营其土地和役使其依附民的呢?《魏书·释老志》说:“(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民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里,对僧祇户采用的是定额租剥削方式;佛图户除了服劳役外,还得“营田输粟”,可能是定额租,也可能是分成租。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其原先的身份地位不同。僧祇户是平齐民及诸民转化来的,原先身份地位和编户齐民差不多;佛图户是囚徒和官奴转化来的,原先身份地位很低。僧祇户属僧曹,佛图户属寺院,合称寺户。平齐民及诸民是有土地的,“有能”二字表明,他们带有投充的性质。既然如此,分散各地是必然现象,“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既然如此,只有租佃模式更有利于僧曹对其控制和管理。佛图户是“请”来的,是封建政府的抑配,不见得有土地,他们应在寺院附近或周围,耕种寺院土地,兼服劳役,缴的也是实物租,多少则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僧曹或寺院的租佃农民。
南方寺院的状况不如北方清晰,但其劳动力的来源几乎和北方相同,有赏赐的,也有投充的。《金石萃编·宗圣观纪》载,早在西晋元康年间重修宗圣观时,“给户三百供洒扫”。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 年)建选齐隆寺时,“敕蠲百户用充资给”(注:《佛祖统纪》卷三六。)。梁武帝强买王骞在大爱敬寺侧80顷地赐给大爱敬寺,想来也会有劳动力的赏赐的。《南史·循吏·郭祖琛传》说寺院“资产丰沃,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则既有赏赐、施舍,也有投充,而且应以投充为主(原因见下文),否则不可能达到“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地步。这些劳动力同样是“供洒扫”和“资给”的,估计南方寺院的经营方式和北方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三
必须强调,寺院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及其依附民大多来自投充,完全是从世俗地主那里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投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法依附民的主要来源。所以如此,原因基本上是二条:首先,长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乱使自耕农难以为生,被迫以极高昂的代价投奔大族或坞堡主的门下,求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其次,也是最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及士族合法占有依附民后,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从复客赐客制和给客制的实施就开始了。所谓“复”,《汉书·高祖纪》载颜师古的诠释说:“除其赋役也。”“赐”与“给”的含义与此相同。《晋书·外戚·王恂传》说:“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前文的“客户”和后文的“田客”显然是同义词,“小人惮役”表明,投充贵势门下为田客,就可以免除赋役。西晋的荫亲属和荫客的规定,将这一特权普遍化。《魏书·食货志》说:“荫附者皆无官役”,《隋书·食货志》说被荫者“皆无课役”,表明无论南北,都继承了这个制度。寺院地主也享有这一特权:“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注:《广弘明集》卷二四《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两汉田租是三十税一,表面看来似乎很轻,加上口赋、算赋、徭役和兵役,就非常重。早在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们就指出,当时赋役的总量为“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注:《盐铁论》卷三《未通》。);王莽在推行王田令时也说“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即赋役额相当于农户全年收入的一半。仅法定额的征收,农民的负担已如此沉重,而封建政府完全按照法定额征收的时间往往是少而又少。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按照法定额征收固然有,更多更大量的是超额征收,临时性的摊派和征发则无穷无尽,赋役的总量已远非“中分其功”或“实什税五”可以概括。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尚且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豕之食,时逢乱世,这也难以维持了。对比之下,成为租佃农民,“见税什五”,还可以维持其奴隶般的生存条件,这便是“多乐为之”奥秘的所在。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投充士族、达官贵人或寺院地主门下,是个体农民逃避赋役,求取奴隶般生存条件的主要途径之一。众所周知,除复客赐客数额甚巨外(注:东吴享有复客赐客特权的人数有限,故可达二三百甚至更多。若官吏们都享有此特权,就不可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封建政府必须控制编户齐民,确保取赋役收入。),给客和荫客都是有限额的,这极难满足地主们的贪欲,他们总是力求扩大其土地占有及奴役对象,两者结合,势必使投充的形式成为其依附民的主要来源。“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表明,投充者的数量已为合法依附民的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此类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未见减少,而是愈演愈烈。在北方,“或千丁共籍,或百室合户”(注:《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注:《通典》卷三《食货·乡党》。);或者像《通典·食货典·丁中》所言“多依豪室”;少的也是“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注:《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在南方,“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注:《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百姓不能堪命……或依附于大姓”(注:《梁书》卷三八《贺琛传》。);“多依人士为附隶”(注:《南史》卷五《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注:《陈书》卷五《宣帝纪》。)等等。“依”、“庇”、“附”、“依附”这类词汇,岂非是投充的最好说明,乃至“全丁大户,类多隐没”(注:《陈书》卷三四《文学·褚玠传》。)。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他们属于非法依附民,封建政府经常通过整顿户籍、土断、括户、大索貌阅或输籍法之类措施,企图将他们全数清查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那么地主是如何处置这些非法依附民的呢?《通典·食货典·丁中》的记述相当具体:“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坠繁,奸伪尤兹。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对此,杜佑特意加了一个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难看出,在杜佑心目中,“浮客”、“流冗”和“佃家”与汉代租佃农民并无什么区别。杜佑是中唐人,娴熟历史,尤谙典章制度,十分注意社会经济问题,故把《食货典》列为其名著《通典》之首。唐代公廨田、职田和官田大都“借民佃植”(注:《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或“抑配百姓租佃”(注:《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因此,他对“佃家”这个名称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使用也是确切的。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初推行大索貌阅后,“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举并没有将隐匿人户和浮客全部清查出来,只是在推行输籍法后,才达到了“奸无所容”的目的。所以杜佑说:“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注:《通典》卷七《食货·丁中》。)汪篯先生统计,隋统一全国后,实际人户应为六百万左右,其中脱漏户籍者为二百万左右,是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清查出来的(注: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隋代户数的增长》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中大多数是“浮客”,那么在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户是租佃农民。“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似乎是指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时的情况,其实均田制实施前及北魏后期远比此时严重。魏孝庄帝时,宋世良充任河北括户大使,“大获浮惰”。孝庄帝嘉勉说:“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注:《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宋世良传》。)此处的“浮惰”,显然与《通典》中所说的“浮客”和“流冗”是同一含义。按孝庄帝的口吻,北中国租佃农民在全部人户中,竟占二分之一上下了。
《通典》有关浮客的叙述,主要源自《隋书·食货志》。像北方那样的浮客,南方也有,只是名称不同,称作“浮浪人”。他们自东晋起就存在,“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封建政府之允许其合法存在,与北来流民大量拥入,侨州郡的设置,及无遑也无力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有关。他们在法律上还是良民,还有课输义务,但比一般编户齐民轻得多。他们可能是没有户籍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更多的应是“庇大姓以为客”者,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大都与“庇大姓以为客”者一样,是租佃农民。加上前文所讲的投充者,那么在南方,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不会比北方少多少。
在投充者中,有无地少地的农民,“全丁大户”肯定是有土地的。无地农民投充后,佃种地主土地自不待言,有土地者投充后,其土地怎么办?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除了将自己劳动所得无偿地奉献给地主外,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土地,才能获取地主的庇荫。其二,只要年年奉献劳动所得,便得获取庇荫。如果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作为提供庇荫的条件,农民不见得那么“多乐为之”。因为在封建时代,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无需多言,更何况地主所提供的庇荫也是不稳定的。史籍所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步骘和卫旌避乱江东,种瓜为生,他们生息之地恰值焦征羌的势力范围。为求取焦征羌的庇护,自认身份地位低于焦征羌,无偿地奉献了他们所种之瓜,并没有涉及到他们的瓜地。《梁书·良吏·沈瑀传》说:余姚“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这里的互相庇荫,显然是指规免赋役,不存在土地的转让。《通典》所言在封建政府减轻赋役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也应以保有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为前提。如若他们已丧失了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不可能“悉自归于编户”的。也就是说,有地的农民投充后,较大的可能是保有其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四
租佃农民所受的剥削,诸史记载大同小异。《魏书·食货志》说“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通典》说“被强家收大半之赋”,“浮客输大半之赋”。这些说法都是与其身份地位相联系的。就此,《隋书·食货志》的归纳最为完整,共有“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和“客皆注家籍”三条,其中,“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最重要。“佃谷”是指佃种土地后的收获,它表明租佃农民缴纳的是实物租,或者以实物租为主。“量分”即指剥削量,也指剥削方式。就剥削量而言,应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也就是中分和大半之赋之间;不大可能低于二分之一,这是秦汉以来比较通行的剥削量,否则地主冒触犯刑律的风险去隐匿非法依附民就将无利可图;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临界点。因为超过了,农民无以为生,对地主也毫无好处。农民无以为生就不可能自愿投充,地主也无从剥削。何况要维持对租佃农民的剥削,总得以保障租佃农民奴隶般的生存条件为前提。就剥削方式而言,既可以是定额租,也可能是分成制,两者没有截然的区别,视时地而异,或者因地主的愿望而异,哪种方式对他更有利,他便会采取哪种方式。就皆无课役和佃谷与大家量分来说,合法依附民和非法依附民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地主不能提供庇荫,非法依附民还要缴纳封建政府的赋役的话,他们也决不愿去投充。他们的区别只是在“皆注家籍”上。合法依附民之“皆注家籍”是指他们身份地位远低于主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世世代代处在贱民的地位上。只有通过放免等一系列手续后,才能取得编户齐民的地位。非法依附民无需注家籍,他们名义上还是编户齐民,是封建政府清查的对象,但一旦被“庇”、被“荫”,其身份地位也就被深深地打上合法依附民的烙印。也就是说,在其主人面前,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合法依附民是一样的,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集中经营的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与分散经营的租佃关系并不互相排斥,也决不可能非此即彼。他们可以互相共存,哪种形式对地主阶级有利,或者说地主愿意采用哪种形式,便可采用哪种形式。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在于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占主导地位,还是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从三国到隋统一,从梁州、益州和汉中到吐鲁番,从中原到大江南北,租佃关系都大量地普遍存在,中小地主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其土地,大地主也往往采用租佃方式,正是士族和官僚贵族大都采用租佃方式,封建政府才会用“佃客”来统称其合法依附民。在这种经营方式的制约和影响下,租佃农民的数量有时竟将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数量如此庞大,难道不说明租佃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经营其土地的主要方式吗?其所以如此,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有关,更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地主阶级所追求的只是“役徒属而擅丰丽”。就此而言,租佃方式是简捷而又方便的途径。
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制约和影响着日后形成的寺院地主。寺院地主对其土地的经营,基本上是从世俗地主那里移植过来的。
魏晋南北朝租佃关系下的“大半之赋”与“量分”,和两汉以来的“见税什五”、“与田户中分”及“分田劫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时期,实物地租是最常见、最大量的,但也不绝对排斥偶或出现的劳役地租的特殊现象,与主人共居的奴客所提供的就可能是劳役地租。还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兼而有之,而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的现象,如佛图户和供寺院洒扫的寺观户等。后两种地租形态并不是主要的,所占的比例估计相当少。
就实物地租而言,本时期既有定额租,也有分成租。在这里,定额租或分成租都无关紧要,租佃制可以是定额租,也可以是分成租,他们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可以互相转化,无非是哪一种对地主阶级有利,地主阶级便采用哪一种。所谓“大半之赋”和“量分”本身就相当含混,既不排斥定额租,又不排斥分成租。
就剥削量而言,基本上维持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间。这类差异由租佃农民是否有生产资料所决定的。有,剥削量可能轻一点;没有,需地主提供耕牛、工具甚至种粮,剥削量肯定会加大。后者的专有名叫“共营作”或“共治”。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北朝僧祇户每年纳60斛便属此类现象,结果是产子不养,弃婴停炊或自断肢体,被视作伤天害理,最终会被历史淘汰。
在分成租下,减产减租不在话下。在定额租下,减产也得减租。吐鲁番地区因葡萄枯花减产而在分配上有所争议,正反映了这一点。看来减产减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关系上通行的惯例。
上述一切对隋唐时期的租佃关系是有所影响的。至于吐鲁番出现的文书,则表明租佃契约正在孕育,开隋唐租佃关系先河。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有其时代的特征。其一,租佃农民的身份地位普遍低落。地主役使的租佃农民有合法依附民和非法依附民,合法依附民的身份地位自不待言,受其影响和制约,非法依附民与他们并无多大差别,至少在其主人面前是如此。其二,投充是当时租佃农民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数量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合法依附民。只有合法依附民的租佃关系是稳定的,投充而形成的租佃关系是不稳定的,很可能投充者不但保有对原先土地的使用权,甚至还有所有权,只是为求取庇护而年年向地主奉纳地租而已。如果不是这样,封建政府难以将他们搜刮出来,即便搜刮出来,也将形成更复杂、更尖锐的社会问题,带来无穷的祸患。这里要说的是,无论稳定与不稳定,都无碍于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
标签:晋书论文; 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汉朝论文; 宋朝论文; 通典论文; 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