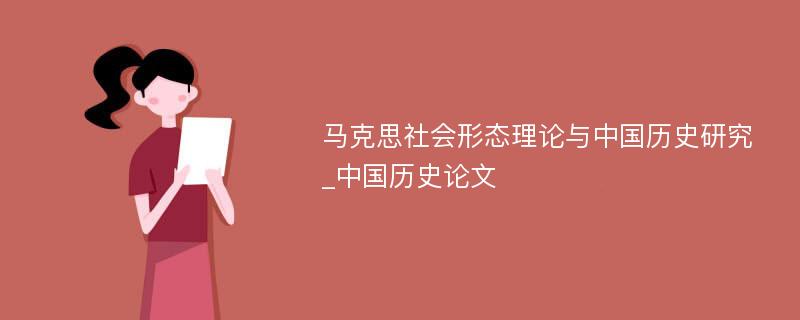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形态学论文,中国历史论文,说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坚持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历史就是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就是坚持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而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严格地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这一学说,唯物史观才成为被人类社会历史所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任何离开马克思这一学说的言行都意味着对唯物史观的背离,更遑论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了。马克思这一学说之所以用“社会形态”命名,是因为它始终坚持用社会形态学说研究历史,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做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的变迁使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呈现出阶段性来。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必经的五个发展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显然,不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无法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更谈不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走向了。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作出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① 在这里,恩格斯把研究社会形态同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联系起来,因为这关系到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重温恩格斯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历史一直是广大历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之所以重提这个早已成为共识的话题,是因为出现了与上述共识相背离的情况,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
二、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及其主要表现
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是指把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不再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一种史学思潮。不管主张这种非社会形态化的人主观愿望如何,作为一种史学思潮,其实质是挑战唯物史观,对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值得指出的是,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由来已久。在国外,早在20世纪前半叶,盛行于西方史坛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就是其典型代表。为了证实这一理论,理论的鼓倡者硬是将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前的中国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只有“乡村社会”和“城镇社会”的地区划分,而不存在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这样,他们就用“传统社会”这个极其宽泛的概念把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给“泛化”掉了。实际上,这是用“传统社会”来取代对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研究,因而社会形态自然不再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既然在西方侵华前中国历史始终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那么,他们所鼓倡的“中国历史停滞论”也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20世纪后半叶继起的“中国历史循环论”,则是以中国封建王朝的轮流交替或秦朝以后国家的治乱交替为立论的依据。实际上,这是一种用封建政权的更迭或国家的统一与分裂这种政治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排斥对于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政治史观。它与“中国历史停滞论”一样,同属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20世纪80-9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史学,以“历史是反理论的”为由激烈地反对将历史理论化或模式化。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只不过是由“稍纵即逝”、不具确定性和关联性的历史事件拼结而成的,其间既无共性,更无规律可言,有的只是一堆历史的“碎片”。后现代史学的“历史碎片论”,实际上是用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孤立研究来取代对历史的整体研究。90年代以来,西方史坛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愈演愈烈。与全球化浪潮相呼应的全球经济史观,以公开挑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姿态出现。它借口“转换”研究视角,用所谓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来取代对于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研究,反对用生产方式研究社会历史,攻击“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是毫无意义的闲扯,指责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阶段划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科学根据。而这些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指控,又都是在“转换”研究视角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就更具欺骗性和蛊惑性。
在国内,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之西方兴起的这股思潮,显然要晚出得多。其理论形态或表现形式也与西方不同,它是以证伪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证伪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行切割,试图证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按照自己的观点套改马克思思想的产物;二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与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切割,试图证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根据经验历史所做的归纳,而是马克思根据逻辑必然性所做的演绎,因此是一种缺乏历史实证的“理论假说”;三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与中国历史进行切割,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同中国历史进行切割,否定中国历史与上述社会形态的联系,试图以此证明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超越”社会形态问题而另辟蹊径,走非社会形态化的道路。开始于80年代后期中国史坛的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90年代以来,其势头有增无减。它突出表现为,由原来侧重于理论观点的证伪转向历史体系的重构。从近年来已经出版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来看,这个非社会形态化的中国历史体系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再用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例如,不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国家的状况;或者只讲生产力水平,不讲生产关系状况;只讲具体经济制度,不讲所有制形式的属性;只讲社会阶层划分,不讲社会阶级结构分析:只讲政权形式的特点,不讲国家形态的阶级实质;等等。这样,就否定了生产方式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是,不再把生产方式的变革看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内在根源,而把“人类的相互作用”(指民族的迁徙、外部的征服)的“互动论”看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样,就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外因论取代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因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因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就不再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三是,不再把社会形态的变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或根据,而代之以朝代的更迭、国家形态的演变、文化形态的转型等政治标准或文化标准。这样,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就不再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而是政治、文化演变的过程。
四是,在研究方法上,重个案、轻整体,重微观、轻宏观,重狭义的社会史研究、轻广义的社会史研究,激烈地反对宏大的叙事方法,片面地强调细化的研究方法。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历史不能给人提供关于历史的整体认识,更谈不上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至多只能给人提供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知识。这不是另辟蹊径走历史研究的新路,而是重蹈旧辙走传统史学或实证史学的老路。按照非社会形态化的路子走下去,历史研究的前景令人堪忧!
三、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
西方史坛的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无论是“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循环论”,还是后现代史观的“历史碎片论”、全球经济史观的反生产方式理论,它们本来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物史观的,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反对把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这是它们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国内史坛的非社会形态化,就其证伪五种社会形态的论据和重构中国历史体系的特点来看,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历史认识和理论认识问题。例如,上述证伪中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和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对经验历史的理论总结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假设”等说法,就属于这类性质的问题。其实,只要熟悉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读一读马克思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此相关的论著,上述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众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开始从事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相关论著,主要有:《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等。50年代是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开始关注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历史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与恩格斯关于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历史问题的通信(185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前半部分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半部分的《序言》(1859年)等。60年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撰著《资本论》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和总结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和第三卷《论地租》等篇章。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重点研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探索历史“超越性”问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历史学笔记》(1878-1881年)和关于俄国问题的通信(1877-1881年)等。
从上述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中我们应该得到哪些基本认识呢?
第一,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日起,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就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首次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二是对“未来共产主义”进行展望;三是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② 从他们所论述的所有制内涵来看,这是三种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所有制,三者之间有着承续演进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怎样决定着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实际上,这已经涉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问题——生产方式理论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着后来称之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最初表述;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它的提出是与唯物史观的发现同步的,是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从发现唯物史观至逝世前夕,马克思从未中断过对五种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重点有所不同而已。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研究五种社会形态的重点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诸社会形态,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以前三种所有制的论述、《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③ 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与恩格斯通信中关于印度村社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制度问题的论述,等等。6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他精辟地论述了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资本形成的过程、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运行及其规律和特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终将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70年代至80年代初,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研究了有关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历史,如毛勒的《日耳曼公社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等。这些研究不但没有推翻马克思此前所做的关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形态的结论,反而用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无比正确。二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④ 而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政治形式”⑤,“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他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程度,首次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指出这两个阶段实行不同的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高级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将随之消失,劳动由“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将得到“全面发展”⑦,等等。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
第三,生产方式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础,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来,并以历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更替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而作为生产方式的基本构成——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在区分社会形态的性质中又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⑧。必须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借以进行生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也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性质。正因为所有制在生产方式中具有更为根本的性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作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⑨,更把“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的特征”,甚至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⑨ 由此可见,所有制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反观近年来国内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无视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回避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研究的情况,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显然有着启示的意义。
第四,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所做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并非马克思的纯属主观的“理论假设”。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五种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便爆发了社会革命。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可见,我们只能“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1) 会形态变迁的原因,如实地把社会形态的变迁看做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是马克思对于五种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的伟大贡献。正如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的研究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五种社会形态,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及其终将被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研究历史的“超越性”就是为了证明:不管历史如何“超越”,它终将走向共产主义。例如,马克思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农奴制国家,由于长期保留着村社制度,因此,如果它继续发挥这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历史的“超越”,径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2)。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超越性”仍然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前提和归宿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五种社会形态问题时,一定要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因为这是马克思研究五种社会形态的最终目的所在。如果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谈论唯物史观、谈论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却闭口不谈社会形态问题,特别是不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那么,这无异于将唯物史观空洞化,将历史的必然性虚泛化,其结果势必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岂有他哉!
由上述的基本认识,我们的结论也就十分清楚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是构成马克思全部思想学说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由于它是一种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因此是一种科学理论,而非主观的“理论假设”。
四、国内史坛的非社会形态化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实
国内史坛的非社会形态化是当前中国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最大现实。
如上所述,国内史坛的非社会形态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其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非社会形态化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主张,而且更是一种学术实践,即用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重构中国历史体系。从前面我们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这种按非社会形态化要求而重构的中国历史体系的主要特点,其要害有两个:一是否定生产方式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否定社会形态分期法在划分历史阶段中的方法论意义。而这两者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试想,如果否定了这两者,那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还剩下什么?岂不名存实亡了吗?可见,在非社会形态化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现实是多么严峻,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国历史研究向何处去?
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特别是作为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分期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简要地说,这是由上述两者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
生产方式理论所以对社会认识史,因而也对社会历史研究极具重要性,是因为它是构成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正是由于有了生产方式理论才使唯物史观从根本上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对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生产方式”概念的由来。“生产方式”概念最早见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就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13) 马克思把这种“方式”归结为“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4)
由此可见,“生产方式”概念是为了阐发人类社会历史的首要前提即“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而提出来的,它深刻地揭示了“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基础性的本质特征,因而就从根本上戳穿了千百年来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的存在问题上所编造的“上帝创世说”、“长官意志说”、“思想产物说”等种种谎言,纠正了18世纪以来启蒙学者在社会本质问题上所宣扬的“社会契约论”的曲解,克服了主观社会学家在同样问题上所散布的“社会正义论”的奢谈,从而恢复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惟其如此,对于生产方式理论究竟持何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研究究竟坚持什么历史观的方向问题,而这正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当前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对此,我们只有面对,不能回避,更不能文过饰非、“粉饰太平”。
历史研究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理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也是方法的根据,方法则是理论的具体贯彻和应用,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为用。中国历史研究也不例外。非社会形态化论者既然反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运用生产方式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否定生产方式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那么,它势必也要反对用社会形态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否定社会形态分期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因为这两者有着内在逻辑关系。
如上所说,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的变迁使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呈现出阶段性来。这应该成为历史分期的根本依据。而促使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所引起的变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迁—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形态分期法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根据依据、以社会形态变迁为根据标志、充分反映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上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分期法。
对于这样的历史分期法,非社会形态化论者自然持否定态度。他们有种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且又似是而非的说法莫过于“西方说”,即认为这一历史分期法源自马克思对于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因此,它只适用于西方历史,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既不存在过奴隶社会,也不存在过封建社会,更谈不上有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此说法看似有理,是因为这一说法道出了部分实情,如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历史阶段的历史分期法确是来自马克思对于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但由此断言:这一分期法只适用于西方历史而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问题不在于这一历史分期法来自何方,而在于这一历史分期法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即历史的本质;只要是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即历史的本质,它就不应受到地域的限制而具有普适性的品格和属性,因为历史的本质所反映的是历史的共性。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迄今为止,只有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法才能够如此关注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够如此深刻地揭示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而这是科学的历史分期法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这一历史分期法才具有普适性的品格和属性。
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进行专题研讨。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有关此问题研究的现状谈点意向性的看法。
众所周知,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争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当时所说的“社会史”是指社会形态的历史。因此,那场争论始终是在“社会形态”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心怀不满的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使用“社会形态”的话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大讨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这种“结合”难免有“粗糙”、“生硬”之处。然而,通过那次大讨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因而表现出日益“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新趋向。这是3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走势。
第二次大讨论的显著特点是: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情况。一方面,这次讨论是在反思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得失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下展开的,这无疑是必要的,应予肯定:另一方面,这次讨论又同时存在着借“反思”之名行非社会形态化之实,因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的错误倾向,这是毋庸讳言的,应予否定。这种错误倾向表现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是:主张标准“中性化”、方法“多样化”和理论“多元化”,而唯独不主张社会形态分期法、不运用生产方式理论。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历史分期“意识形态化”、避免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不必要的“争论”。难道采用朝代分期法、年代分期法或别的什么分期法以及生产方式理论以外的别的什么“理论”,就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了吗?难道“争论”只要“避免”就会自行消失、不复存在了吗?可见,行非社会形态化之实的结果势必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如果说,第一次大讨论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走势是“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那么,第二次大讨论以来所出现的非社会形态化却使中国历史研究面临着“远离”马克思,“告别”马克思的严峻局面。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当今的处境,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总而言之,综观最近20年来国内史坛的非社会形态化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正如上面所说,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用什么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方向问题。事情很清楚:按非社会形态化的路子走下去不仅整个中国历史必须重新改写,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起来的中国历史体系也必须推倒重建。从近年出版的某些关于中国历史著作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非社会形态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风起于青萍之末”。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任其坐大,而应该不平则鸣,以正视听。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7-43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7页注①。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