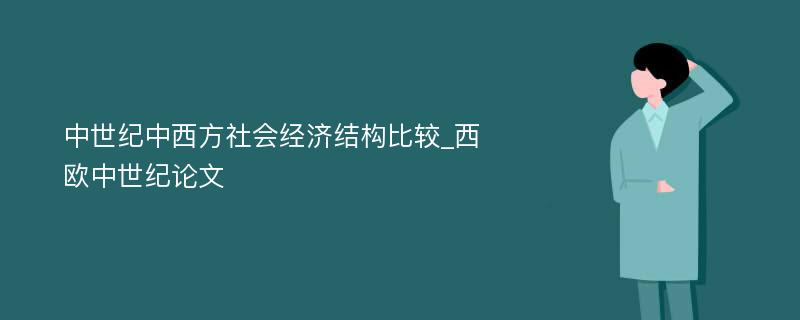
中世纪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中世纪论文,社会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欧中世纪初期,随着日耳曼铁骑蚕食西欧,其亲兵分封制的滥觞,至8世纪法兰克王国全面的采邑改革,封臣制大大地兴盛起来。因为日耳曼人的文化落后,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只有依靠封臣制来加强中央的权力,于是国王的封臣不断增加。许多大封建主也同时大量进行封臣,而这些封臣,如有一定实力的话,也在吸收更低一级的封臣。其中,不仅官职采邑化,甚至许多教会职务也采邑化,如主教、修道院长之类。土地在层层分封中,基本被不同等级的封建主全部刮分完毕。原来马尔克公社的自由农民,也因逃避战乱而依附于各级封建主,大多沦为农奴,部分成为自由的佃农。“一般来说,拥有自己私有土地的自由农民较少,在大陆上还零星散布着一些,英国则几乎全部消失。大部分西欧的自由农民仍是封建主的佃农。”(注:马克思:<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158页。)
所以,当时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单位是拥有一定数量奴隶、农奴和佃农的领主经济,它时常以庄园或类似的村庄形式,出现在西欧的大地上。领主庄园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体,庄园的耕地一般分为三部分:领主自营地、自由领有地和农奴份地,各部分土地错综相间,很少连成一片。庄园中一般还有公共牧场、草地、果园、菜圃、池塘、森林及教堂、磨坊、仓库等设施,当然各地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庄园大都采用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即领主自营地由农奴服无偿的劳役进行耕种,实际上也还是要交纳自己份地上的一些产品;而自由领有地则由佃农耕种而交纳一定的实物地租,所受剥削的程度要比农奴轻一些。科斯敏斯基曾统计了英国中部地区十三世纪时领主庄园的情况,得出的一般比例是:领主自营地32%,农奴份地40%,自由领有地28%。他还将有耕地1000英亩以上土地者定为大庄园,500-1000英亩者为中等庄园,500英亩以下者为小庄园,而庄园越大,农奴份地比例也越高。(注:马克思:<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158页。)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领主庄园不仅是一块经济多样性的地产,而且还是一个基层政权单位,它是当时统治权和土地权合一的地方区划,设有庄园法庭诸机构。当时大规模的庄园毕竟是少数,也存在许多非庄园化的地区,如数个村庄联结为一个领主封地,也可以是一个村庄为数个领主所分割,但总是一种领主经济体系。总之,当时社会经济动作的基本单位是领主庄园,而自由的自耕农民极少。
而中国古代则呈现的是一幅与此不同的图景。在经过了春秋、战国一系列集权专制变法的社会型之后,国家的行政与经济管理系统已相当完备。在战国、秦代的授田制下,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几乎大都为五口百亩的国家自耕农,军功官僚所得的赏田、赐田、实为赏赐该地农户之租税。西汉初期也同样,大臣晁错所说的,当时农夫普遍为百亩五口之家的情形无须赘引。<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载:“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最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史记·货殖列传>谓:“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所谓“岁率户二百”,乃是对每一农户年应交租税折合成现钱的约数,从中可见当时国家自耕农的普遍。
西汉时期地主阶级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浪潮出现,农民土地被兼并而僚地主势力不断发展,同时政府对豪强、商贾地主势力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的,采用了没收逾制田宅、强迫徙居实陵、财产算缗告缗等手段,尤其是“代表汉政权的‘酷吏’对战国以来旧势力的地主豪强的攻击,差不多贯穿着西汉一代。”(注: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6页。)它不但以打击强宗大族来巩固中央集权,而且也要不断维持自耕农的经济格局来保护国家的财政运作。
至西汉末年,朝政腐败而官僚地主势力膨胀,尽管制定了限田令,然而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注:<汉书·王嘉传>。)随着王莽王田制的失败,刘秀度田令的不了了之,东汉政权与豪强地主势力妥协,用刘秀的话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虽然政府也时春分田与贫民之举,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但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放任政策,加上朝政的日益腐败,土地财富大量集中于贵戚豪门和宦官集团的手中,自耕农经济遭受很大打击。
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常借血缘关系为号召,聚结起数百上千家的宗族亲属,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其中包括大批徒附、佃客、部曲和奴隶,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地方势力。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至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许多营堑、堡垒、坞壁之类地方豪强的军事实体与地主庄园,内部有田园、陂池、山林、牧场及小作坊等,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主庄园,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身,只是前者的主人并非封君人封臣,且带有一定的血缘家族纽带。
这是士族豪强地主经济利用朝廷政治腐败、战乱时起的机遇,摧垮国家自耕农经济的一次异化过程。期间,统治者依旧在采取一些办法,竭力扭转国家自耕农经济的劣势,如两汉至曹魏、东吴诸政权采取的屯田制度,西晋颁布的占田令等。到北魏开始实行全面的均田制,它又重新构筑起国家自耕农格局的经济基础。此后,北齐河清三年(564年)、隋开皇十二年(592年)、隋大业五年(609年)、唐武德七年(624年)、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朝廷都有均田领颁布,唐代国家财政的徂庸调制便完全建立在均田的基础之上。这一段三、四百年的时间,经济主体又回到国家自耕农普遍的格局,而使地主制经济退居次要地位。
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渐遭破坏。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的废除,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的结束。宋代政府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宽松经济政策,使工商业商品经济也渐显繁荣,在此基础之上,地主制经济不断扩展。有所谓:“今郡县之间,官户民田居其半。”(注: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1。)总之,晚唐、两宋时期出现的地主经济第二次膨胀,又使国家自耕农经济稍据劣势,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颇有关系。
金、元少数民族政权,用征服战争掠得大量土地作为官田,对地主经济有所遏制。明、清初期,也是靠农民起义与征服战争对土地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如明朝初年,在长期战乱后荒地很多,政府采取鼓励农民垦荒政策,垦出的土地“许为永业”,并规定不许豪强兼并的政策;同时,许多农民佃种的官田,“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已业,实与民田无异。”(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4,引<明上元县志>。)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家贵族、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更是疯狂,许多自耕农丧失土地而转化为佃农,生活状况更为恶化。明末,顾炎武说过:“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地主制经济与自耕农经济犬牙交错,此起彼伏。
不过,从一些实地调查中分析,明、清时期许多地方还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体。有人具体统计了明代万历及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所留至今的鱼鳞册和编审册中关于徽州休宁县的土地占有状况,其中70%以上耕地在占地30亩以下的农户手中,而占地30 上者一般不超过耕地总量的10%。(注: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4页。)而据康熙初年江苏长州县部分鱼鳞册,其中占地在100亩以上的地主,拥有土地的总数占总耕地面积的19.6%。(注: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江三角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再看北方,康熙后期河北获鹿县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0%,就是说农民占有70%的耕地。(注:史志宏:<从获鹿县审册看清代前期的土地集中和摊丁入地改革>,<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1期。)有关例子不少,总之,大地主不多,而自耕农较为普遍。
我们看到,西方中世纪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是一种贵族经济,它是与西欧封建制度完全匹配的经济基础。而中国古代从两汉至明、清,社会经济结构则是国家自耕农与地主佃农二种体系并存的局面。应该说,国家自耕农体系是中央集权专制其财政动作所主要藉靠的经济基础,是主体结构;而作为贵族经济的地主佃农体系实为应官僚政治制度的要求而在经济领域内的一种补充。尽管两者一直在发生激烈的交锋,甚至会出现地主制经济占上风的局面,但这毕竟是一种异化现象,国家在动作中会出现各种方式加以调整。
二
在工商业经济结构方面,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9世纪法兰克王室庄园中的情况。据当时颁布的<庄园敕令>,庄园中各色工匠有:铁匠、金银匠、木工、纺织、皮鞋匠、刀剑匠、旋工,及制肥皂、酒、醋、蜜、油脂、干酷、面包、面粉、屠宰、捕鱼等行业。敕令第30条规定,庄园中的产品分二类,一类供国王及其家族的日常需要,一类供应战争等的开支。(注:参阅马克:<西欧封建形态研究>,第160-163页。)实际上,法兰克王国的主要开支便出自王室庄园,当然其庄园规模是相当大的,且分成好些庄园分别管理,有的占有数千英亩的土地,有的稍小一些,都配备有各级管理人员,估计一个庄园总共有几百人。庄园中生产活动主要为农活,并从其产品主要为满足封建主消费所需来看,其中手工业生产的总规模不会很大。
在领主庄园,也包含有所需要的一些手工业和食品加工作坊,如磨坊、酒坊、面包房、砖窑等,而基本自给自足。如阿眠修道院的一个庄园,占地约2500公顷,居住着约500人,包括自营地47份,农奴之类份地84份,放牧400头牛的牧场1处,放牧2000头猪的森林1处,另有2个磨坊、3个啤酒坊和石灰窑1座。(注:参阅马克:<西欧封建形态研究>,第160-163页。)可见,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庄园,其中工商业的成分是很有限的,只为自身的消费而已。其实,领主庄园的经济性质不属国家官府,所以前不与中国古代官府工商业的概念对应。
而中国古代官府工商业的规模就极为可观了。秦代的情况,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经济>一文已有详述。(注:参见<史学月刊>1995年4期。)西汉自武帝时管榷盐、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地方上设的盐官,分布于26个郡(国),共32处,包括沿海地区和西南、西北之产池盐、井盐之地。铁官分布于40个郡(国),共45处,几遍布当时全国的铁矿产地。其生产、运输、销售,官府全部垄断经营,而主要采用徭役或刑徒进行劳作。从以后铁官徒不堪压迫,一地就有数百人造反起义的事迹记载来看,这些官府作坊的规模不小。<汉书·贡禹传>言:“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南织室亦然。”西汉官府工商业已有如此规模,也是对秦的继承与发展。
接下来让我们对与西欧中世纪中期社会同时的宋代官府工商业作一下简略的扫描:<宋会要辑稿>方域3、职官16诸处有载:北宋京城的军工南北作坊共有兵校与工匠约八千人,弓弩院有工匠千余人,加上地方军工作院的人数,北宋初年的官府军工业规模就相当可观,同时禁止民间的武器生产。铸钱业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官府垄断的手工业。其铜钱监和铁钱监共达数十处,“北宋熙丰年间铸钱的最高额达六百多万贯,因而铸钱的工匠至少要有七千五百人,高可达一万五千人,取其中数,约一万一千人上下。这大概是宋代铸钱业全盛时期拥有的全部工匠和役卒。”(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页。)
官府造船业也有相当规模,由造船务负责,在水路交通便利的各地,都置有造船埸,朝廷时下达造船定额。<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载:“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其主要为漕运船,而朝廷对战船的需求量也相当大。<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3载:“庆历二年二月诏,京东西濒河诸州造战船五百只赴河北。”
宋代官府纺织服饰业的情况,据<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7-8载,京城开封的绫锦院“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内侍三人领兵匠千三十四人。”染院“领匠六百十三人”,裁造院“领匠二百六十七人”,加上文绣院绣工三百人和尚衣库、后苑造作所的有关作作坊及其工匠,便是京城官府纺织服饰业的大致规模,其可达数千之众。地方官府纺织业以成都锦院为最,约有数百工匠。其他大城市规模略小,具体数字已不得而知。
官府的造纸、印刷业规模也十分可观。宋代官府印书,朝廷有国子监、崇文院、国史院、秘书监诸机构外,地方更有安抚使司、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公使库、郡斋、郡庠、县斋、州学、府学、军学、县学、书院等机构,其中以郡斋、州军学所刻为多,官府印书繁盛。<咸淳临安志>卷九载,当时临安(杭州)的造纸局就有工匠一千二百余人。
北宋京城的官府建筑业,由三司修造案或将作监总领,下属官司还相当庞杂,有修内司、东西八作司、竹木务、事材埸、麦埸、窑务、丹粉所、作坊物料库、退材埸、帘箔埸等。其中事材场“领匠一千六百五十三人,杂役三百四人。”“京东西窑务,掌陶土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领匠千二百人。”窑务千余人,岁产一千多万件砖瓦,人均万件,数量可观。其他官司规模也应在千人上下。另外,“提举修内司领雄武兵士千人,供皇城内宫省坦宇缮修之事。”(注:<宋会要辑稿>食货 54之15,食货55之20,职官30之1。)可见京都官府建筑业规模就有一、二万之众,分工也极细密。
宋代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就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宁官窑。官府的矿冶业,主要为冶铁、铜、金、银、铅、锡、水银等,约各有数十场,总计数百处,产量也很可观。漆侠先生估算:“从当时的生产技术以及个体生产能力估计,从采掘矿石到冶炼加工成各种产品,宋神宗熙丰期间的产量没有二十四五万冶户(或者说没有二十四五万个劳动者)是完不成的。”(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二编,第588页。)另外,京城还有制酒、油、醋、乳制品和粮食加工等官府手工业,各有数十或数百人的规模。
再看一下官营商业。太府寺所隶此类官司有:都提举市易司,掌贸易货物,其下属官司市易上界,掌乘时贸易;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杂买务,掌宫禁、官府所需和市百物;杂卖埸,掌宫禁、官府多余之物以待出售;及各州市易务。还有榷货务,掌折博金帛、禁榷之事物。交引库,掌给印交引钱钞。抵当所,即官府当铺。和剂局、惠民局,掌出卖良药。店宅务,掌管出租、修造官屋之事,单京城赁屋就达万余间。石炭埸,掌受纳出卖石炭。其中尤以市易司的官商机构规模为最。市易司是王安石变法时推行市易法时特设的官商机构。先在京城设立市易务,以后逐渐向全国各地普遍推开,不但路、州,一些地方甚至县、镇、寨都设置。并且几乎什么买卖都做,包括长途贩易、抵当赊请、贷米收息、一些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等,单开封市易司的资本就达一千五百余万贯。“熙丰年间,开封都市易司最兴盛时期的规模:MWF赊卖系统、抵当系统、贩易系统、征税系统、催索系统、簿籍系统的各级官员、各类办事公吏及本务行人、牙人等等,决不会下于数千人。就人数而言,已令人讶异不浅。”(注:拙作:<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此外,各级官府的“回易”,即赢利性经营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沿边地方官府和军队回易之记载更是大量的。汪圣铎指出:“宋代回易特点,首先表现在回易本钱上……数额之大,动辄万、十万、百万。其次,宋代回易特点表现在经营方式上,是以商业为主兼营别样,见于记载的有运贩绢帛、粮食、盐酒以至文具、饮食品、洒扫之具等,开柴埸、立解库、置塌房,倒卖钞引,出贷收息等。……最后,宋代回易特点表现在经营规模的大和波及面的广上。”(注:汪圣铎:<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
宋代官府酒务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南宋临安府官营酒成库为规模较大的酒业造、卖统一体。户部赡军酒库所,作为统一管理户部酒库之机构,首先有自己的曲院、钱库及各方面官员和办事人员。每一个酒库又都几乎包括三部分:清界库、煮界库和酒楼。其官营酒楼,不但数量多,而且“每库设有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注:<武林旧事>卷6。)其豪华、奢侈之埸面,完全可与私营酒楼匹敌。其次,南宋一些小城镇的官酒坊规模都相当可观,各地官营酒楼林立,如平江府有清风楼、黄鹤楼、花月楼、丽景楼等;丹徒县城有八角楼、清和楼等。总之,官营酒业不但数量多,县经营也很有特色,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官府除直接经营建安茶苑、解州盐池之外,还设立了榷货务诸机构,实行榷茶、榷盐、榷酒、榷酒、榷香、榷矾制度,从政府控制专卖的政策中获取大利。宋代由此禁榷专卖制度所获得的收益已开始超过土地上的赋税,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官府在将其自身变为一个最大的商人的同时,又把数量众多的普通商贾变为供其驱使的零售商或小伙计。”(注:汪圣铎:<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当时的私营工商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其身份地位低下,受到官府贵族的种种掠夺,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它们扮演的不是主角,而常常都是国家官府的配角,受到种种的束缚,无法开拓出自主发展的局面。(注:参阅拙作:<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西欧中世纪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官营工商业,其私营工商业又基本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了有自治权的城市独立实体,走着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三
西欧中世纪在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逐步解体的基础上,进入了以领主采邑为单位的封建等级社会。在这种制度之下。“从法律原则上来说,西欧封建封土有似一种职田,它之所以由封君赐给封臣,是为了保证封臣能按时应召服军役。封土既是由君赐给臣,当然所有权在封君那里,封臣只有用益权。”然而“封君对土地的权利因封臣的权利而受到限制,而封臣的权利相应又受到封君的限制。他们之中谁也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而同时,“土地大部分属封建主所有,农奴和许多依附农民都没有土地所有权。”(马克yáo@①<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146、118、243页。)由于土地占有权、所有权的互相牵制、地产运动相对来说很是缓慢,比如世俗贵族一般要经几代析产,其地产才逐渐分散;还有就是分封、捐赠,或者因背叛而没收。
就是封土已变成世袭领地,封臣有自由处分的要求,比如进行土地交易,也得采取重新分赐封土的形式进行。129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时通过的<买地法>,虽规定封臣可以自由转移其封土之一部或全部,但也须采取代替的方式,即原封臣退出而由新受地者与封君直接发生关系,相应封建义务一仍其旧,亦即成为新的封臣。其在向自由的土地财产方面跨出了一步,土地变相买卖的情况似有所增加,但对旧制度冲击不会很大。同时,就是上述形式发生的地产运动,也大多是在封建主之间进行,而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内涵。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其经济结构和等级格局都比较稳定,或者可以说有些僵化。
14、15世纪,是西欧社会激烈变运时期,由于灾荒引起的农业危机及战争、黑死病等各种原因,引起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秩序混乱,使领主庄园经济逐步解体,许多农奴取得自由文书而得到解放,贵族或富绅开始将土地划成小块而出租,于是农民大多数成为佃农或半佃农,并且自由的自耕农经济也开始不断壮大。“领主-农奴关系慢慢让位于地主一占用者(即地主-承租人)和工资所得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大量残存的习惯权利被吸收合并,不成文法同样审慎地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让位于将个人权利和财产作了明确规定的成文法。特别在要素市场上,条件得到了改善。劳动现在通常可以自由地寻找其最优报偿,并保留其大部分所得,而土地已开始被看作是可以转移的财产。”(注: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37页。)如1086年,王田占了英格兰耕地的1/7到1/5,180个大封建主占有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而到了1436年,王田只占全国耕地的5%,51个大贵族加上183个骑士的地产只占20%。15至16世纪的英国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注:格拉伊:<1436年英格兰的土地收入>,<英国历史评论>1934年第2期。转引自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认为近代初期(指16世纪前后)的法国是一个大地产的国家是一种误解。相反它倒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的国家。”(注: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37页。)
这时,西欧与中国中世纪大部分农村的状况已相当接近。而一旦领主制经济瓦解,自耕农经济脱颖而出,其封建制度便也已走到了尽头,开始逐步解体。尤其是自治城市中资产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触角开始深入农村,自耕农的自由发展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和出现,西欧农村经济的转折于此开始,整个西欧社会迈向了资本主义。
中世纪的中国,土地买卖现象相当普遍。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势头已相当迅猛,东汉、魏晋时期主要为豪门士族地主。而到宋代,庶族地主也加入竞争行列,土地的买卖转移更是极其频繁。宋代词人辛弃疾有过这样的诗句:“千年田换八百主。”(注:<稼轩词>卷4<最高楼>。)社会上产生了“十年财东轮流做”的观念,而没有西欧中世纪地产、等级格局那种僵化的感觉。
然而中国古代地产运动的活跃,并非是其经济制度深入私有化的反映,它实际上是以权力的天平为准衡的。东流、魏晋时期的选官规则是九品中正制,土地自然归依于豪门士族;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为平民百姓也打开了通向“权力”之门,庶族地主登上历史舞台,至宋代形成了气候,而地产运动依然在官本位的基点周围,前所谓:“今郡县之间,官户民田居其半。”正如刘泽华等所指出的:“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与政权的频繁更迭和权力在个人手中的频繁转移相对应,封建地主个人地权的归属总是大集大散,处在经常的流动之中。有权则多地,权亡则地亡,地权流动的基本趋向是视权力为归依的。”(注: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它既是官僚权力结构整合机制的一种特殊需要,也受到国家最高权力的无形控制。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控制结构即国家经济统治体系的强化,它对土地的分配运作,存在一种极不规范但又确实存在的强制性调整机制:或以强权、诏令为归依;或以没收、掠夺为手段,或以均平、等级为政策。再如南宋末年的回买公田,官府可对富民田产进行肆意掠夺;满清统治者的圈地方式;或朝廷动辄可将某官员的田产尽数“没入官府”,有关事例不胜枚举。然而由于缺乏控制操作的规范性,加上政权日益腐败,不能有效遏制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趋势,国家只得将负担加重转嫁到自己直接控制的自耕农头上,此饮鸩止渴之举,必将引发农民的反抗斗争,最后也只得以起义、战争为代价,进行手术性的大调整。
我们看到,中世纪中西方社会农村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要点在:自耕农经济对于两者社会制度的意义几乎截然相反,自耕农的发展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的序幕,而它却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基石。原因何在呢?从中国古代自耕农的沉重负担,及其私有权的不完整诸方面看,可称为国家直接控制下之佃农,(注:参阅王家范:<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国有”性质辩证>,<华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详尽论证了“自耕农为国家佃农”等问题。)所以一般将中国古代自耕农看作“小私有”者经济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其本质上实为国家经济的基础部分。而西欧中世纪后期的自耕农,由于其法律传统的缘故,有其实在的土地私有权内涵,是货真价实的“小私有”者经济,决非国家佃农。
当然,中世纪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关键性差异,还在两者城市才工商业经济成份的截然不同。西欧的封建割据局面造成的统治松弛的状冲锋 领主庄园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就是说基本不存在一个相当强化的中世纪国家控制管理体系,从而对一般民众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引导出一条康庄大道:集聚于交通繁华之地,建立有自治权的工商城市。通过城市市民数百年的艰苦奋斗,资本主义经济的幼苗就在这里萌发,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就在这里诞生。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向农村的渗透中,借助的是自耕农的私有环境。
而中历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体制长期的严厉统治,城市决不是私营工商业自由活动的天地,加上存在如此庞大规模的官府工商业,再如到明代初年,单其官府手工业所征用的工匠和民夫,就达180万人之巨,(注: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这些都对民营工商业的发极为不利。在这个制度之中,民营工商业享受到无情的压抑和摧残,往往只能在官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城市也始终是“封建”统治的坚固堡垒。
最后需要进一步指出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农业经济结构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它既要维护和保持国家自耕农经济的主体地位,又不得不默认地主制经济的必要参与性,要求将其经济模式束缚在一个以国家经济为主导,私有经济为补充的鸟笼中,但始终找不到维持两者和平共处的一个“度”,从而陷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中:自耕农与地主都是专制集权统治国家所藉靠的两种力量,其经济基础需要的是自耕农,其政治统治又要倚靠官僚地主。当朝政腐败,地主制经济不断吞噬自耕农经济,而终将旧政权的经济基础破坏而导致败亡,在靠战争等手段重新建立新政权并重建国家自耕农经济主体的同时,也是地主制经济悴然衰败之时。由于没有出现新的经济成份,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只有如此无休止地循环着。
标签:西欧中世纪论文; 经济论文; 庄园经济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中世纪论文; 历史论文; 权力论文; 宋朝论文; 领主论文; 神圣罗马帝国论文; 大航海时代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明史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