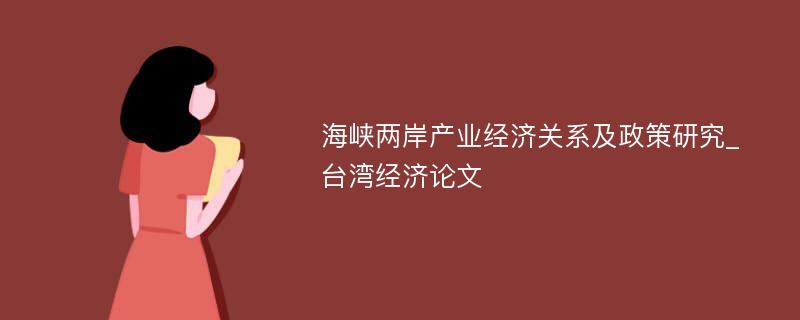
对两岸工业经济关系及政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两岸论文,关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台湾财团法人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丁守中先生的邀请,我于今年7月26日赴台湾作为期20天的学术访问和交流。在交流中,两岸工业经济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是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一、两岸工业经济之比较
从工业经济规模来看,大陆已进入世界几强行列,若干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煤、水泥、棉布、电视机等已居世界第一;钢、原油、发电量、硫酸、化肥、化纤等也列世界前几位。与此相比,台湾的经济规模要小得多,其中,棉布、洗衣机、自行车、发电量、钢、水泥、硫酸的产量分别仅为大陆的4.3%、3.5%、27.8%、13.2%、4.3%、7.7%和7.1%。但是,从以人均产量衡量的工业发展水平来看,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陆远落后于台湾。其中,大陆的棉布、洗衣机、自行车、发电量、钢、水泥、硫酸、乙烯的人均产量分别仅为台湾的40%、50%、6%、13%、40%、23%、25%和4%。
再看两岸的产业结构。1991年,大陆一、二、三次产业构成为26.6%、46.1%和27.2%;而台湾一、二、三次产业构成为3.98%、43.35%和52.67%。而且,在三次产业中,大陆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1991年,一、二、三次产业的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人民币1516.40元、7335.87元和4906.85元,三者之比为1:4.8:3.2。而台湾则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一、二、三次产业分别为新台币151804元、533196元和553901元,三者之比为1:3.5:3.6。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态势表现为:在三次产业中,大陆第二产业不仅比重最高而且增长最快;而台湾则第三产业比重最高增长最快。据预测,到2000年,大陆三次产业构成将为18.2%、52.0%和29.8%;台湾则为3%、40%和57%。这表明,大陆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而台湾已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按一般规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500美元左右为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标志。目前,大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0美元,而台湾已达10000多美元的水平(1993年为10566美元)。
由此可见,大陆与台湾间的经济差别是很明显的:大陆经济规模巨大,综合实力较强,但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却较低;相比较而言,台湾经济规模较小,综合实力不很强,但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却已相当高。
二、互补结构及合作亲和力
按照比较利益原理,一定的经济差距和结构差异是不同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前提。当然,在地区间存在经济差距和结构差异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区域分布以及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实际状况可能很不相同。因为,区际经济交流过程中会有各种力量发生作用,区际经济关系能否趋于良性循环状态,除了取决于经济互补性之外,还取决于是否具有交流合作的亲和力。
大陆正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储蓄率已相当高,国家公布的积累率近年来一直高达34~35%,但由于大陆的工业化本身就有需要大量投入资金的特点,特别是目前不仅需要向资金系统较高的交通运输、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倾斜,而且,90年代以来,工业发展正从消费需求拉动为主向投资需求拉动为主转变,这意味着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加上90年代劳动人口的增长处于高峰时期,更增加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所以,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储蓄缺口很大,资金的短缺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台湾多年来经济持续高储蓄、高增长,资金充裕,而且,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到90年代,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之一。1993年末,仅中央银行的外汇存底就达850亿美元。但近年来,岛内投资环境日趋恶化,积累的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从80年代上半叶起,台湾外流资金主要投向美国和东南亚各国,而从1987年起,随着台湾当局对向大陆投资的解冻,大量资金开始转向大陆。
从劳动力供求看,大陆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尤其是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仍占近60%(1991年为59.8%)。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向二、三产业。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水平也较低。而在台湾,劳动力价格高攀,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成为降低其产业国际竞争力、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因此,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出去,大陆自然成为企业界看好的发展空间。
再看土地资源。大陆的地产业是个正待开发的市场,土地利用程度不高,地价较低。而台湾土地面积本来就小,人口密度为大陆的4.75倍(1991年,大陆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20.75人,台湾则高达574.15人)。若以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大陆的10倍计算,台湾土地的经济承载强度(即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大陆的50多倍。因此,地价高涨,使许多工业企业难以承受。同时,对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和投入越来越高,这些都已构成对台湾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而隔海相望的大陆则正是一块开发中的“工业乐园”。
再看技术资源。台湾历来融于世界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多年拼搏,使它的一般科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程度较高,不少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占有相当份额的国际市场。但是,高新技术、尖端科学的实力却显得不足,成为台湾产业升级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大陆则一方面由于多年搞了封闭的计划经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水平低,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科技积累,加上大国效应,在高新技术和尖端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已具有相当的实力,只是由于体制上的缺陷使之与工业经济相互脱节而尚未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大陆与台湾之间在资源方面的互补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两岸间的交流与合作将会产生互利互惠、相辅相成的良好结果。
在存在经济互补性的条件下,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实际成果还要取决于两岸间的亲和力,即两岸经济相互沟通、衔接、渗透、融会的可能性和趋向性。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文化传统上看,大陆台湾同文同种,有深厚的血缘、地缘、亲缘、情缘关系。这方面的亲和力是十分强烈的。台湾学者曾对向大陆投资的台湾制鞋业企业的投资动机作过一个问卷调查。在所列举的促使其投资大陆的11种因素中,“相同的文化和语言”是第二位的动因(样本企业认同率为82.3%),仅次于居第一位因素“低工资劳动力”(样本企业认同率为95.8%)。(Lee-in Chen Chiu & Chin Chung,1993)尤其是大陆的广东、福建两省与台湾更具有传统的人文亲和力。
第二,从经济体制上看。70年代末以前,大陆实行计划经济,台湾实行市场经济,两者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在那时,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封锁敌对,也很难想象两岸间的工业经济能正常交流与合作。70年代末以来,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使两岸经济在体制上的差距大为缩小,资源配置机制相互衔接,交流与合作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第三,从法制条件看。两岸虽有差别,但是,就规范经济行为和协调两岸经济交往而言,两岸的法规并无不可相容之处。台湾和大陆都在从人治传统中挣脱出来,逐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在这方面,台湾具有先行之利,但大陆近十年来急起直追,法制条件日趋完善。
第四,从政治上看。自从70年代末以来,两岸的敌对状态结束,但对立状态依然存在。过去,政治以至军事上的敌对状态完全抵消和损毁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亲和力,使两岸经济毫无往来;现在,政治对立状态仍对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亲和力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两岸间至今尚未实现直接“三通”。为此,双方的企业和生意人不知损失了多少资金、时间、精力和机会。当然,这方面的情况也在逐步改善,但其改善的进展是远远不如人意的。
总之,两岸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实现互补的亲和力总体来看也是良好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政治上的对立以及改善这种对立状态的进展过于缓慢。
三、两岸政策取向之差异
对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大陆和台湾所实行的处理两岸经济关系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方面,大陆与台湾的政策取向表现出一定的差别。过去,我们总是从政治需要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来说明造成两岸政策取向差别的原因。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原因是存在的。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尤其是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意愿的维护越来越让位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因此,在分析两岸间政策取向的差异时,应特别注意其背后的客观处境和实际经济利益的差异。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两岸工业经济之差异性,以及双方在互补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陆和台湾对于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不同政策取向。
第一,在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总体政策上,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台湾方面迫于寻求生存空间的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受客观经济要求所驱使,显得缺乏主动性。台湾工商业界面对国际竞争,面对台湾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导致一些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充满对海岛型经济空间狭小的危机感,希望当局更开明地对待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台湾当局则顾虑较多,步履蹒跚。往往是民间“越轨行为”四起,既成事实已不可否认,然后,当局才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而大陆方面则由于巨大的经济规模,政策回旋余地较大,因而主动性也较强。
第二,在具体的项目决策上,台湾方面往往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大陆方面则往往处于被动。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市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谁能把握市场,谁就拥有主动权。而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台湾方面更多地拥有资金和国际市场营销经验,而且,大陆经济规模巨大,空间范围也广,各地区之间往往还有竞争,所以,台商可以有更大的加旋余地进行更为主动的选择。大陆往往得以政策调整来避免这种不利,但常常已是事后作为了。
第三,由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两岸差距很大,大陆居于优势,所以,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时,台湾方面更为谨慎,更多地考虑对台湾整体经济以及安全的影响。而大陆方面则更为大胆豁达,不必因顾忌两岸经济交流的负面影响而谨小慎微。因而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的政策安排上,大陆方面以种种优惠相吸引,台商不仅享有一般外资企业可以享有的待遇,而且还享有“同等优先”(即在品种、质量、价格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从台湾进口或对台湾出口)优待以及《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所赋予的各种特殊优待。同时,大陆各地区还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台商,并积极推动大陆企业发展与台商的交流与合作。而台湾方面则以“间接”和“不对等”为基本的政策安排原则,力图控制两岸经济交流推进的节奏。例如,至今为止还坚持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都必须经过“第三地”;允许台商赴大陆投资却不允许大陆企业去台湾投资。这常常被批评者斥为“有失大度”。
第四,对于赴大陆投资,台湾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进取心比大中型企业更强,台湾当局对大中型企业投资大陆又存有更多的疑虑。所以,与一般的国际(区际)贸易和国际(区际)投资通常由大型企业开路的情况很不相同,两岸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台商投资大陆,跨海经营,中小企业居领先地位。大陆方面从吸引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能力方面考虑,当然更欢迎技术水平较高的大中型台商企业的合作,但这类政策至今难以得到台湾方面的积极配合。相反,台湾当局囿于海岛型经济的条件和对所谓“产业空洞化”的担心,常常为“根留台湾”还是“根移大陆”的问题所困扰,主观上希望与大陆间形成一种“垂直分工”状态。这种政策意向当然很难得到大陆方面的认同。
以上分析表明,两岸间政策取向的差异往往与各自所处的客观地位以及面临的实际条件有关,但是这些并不构成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只要坚持互利,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就会良性发展,互利性越强,交流与合作就越是不可阻挡。而真正的困难是来自两岸间的政治对立。因此,在现阶段,发展两岸经济交流需要最大限度地实行政治与经济分开。当然,政经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策上尽可能分别对待和处理政经问题,则是当今世界解决分歧和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能否做到政经分开,是现代成熟和理智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只要实行政经分开的原则,经济关系发展了,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广泛,终将为消除政治对立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