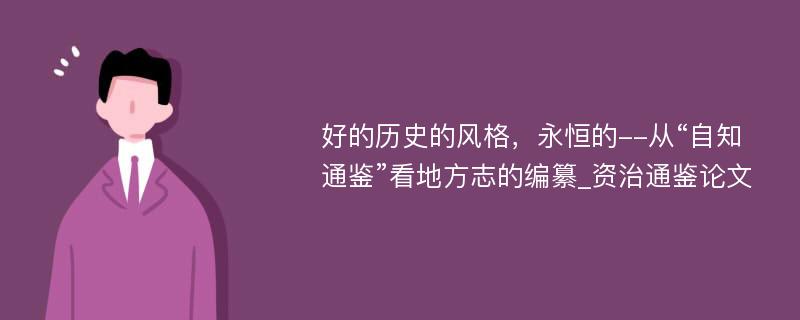
良史风范,千古永存——从《资治通鉴》看地方志的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资治通鉴论文,风范论文,千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 (2000)01—0028—05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编年史钜制,自问世以来,即为历代学人所称誉,对宋代以后包括方志在内的史部典籍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史家治史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
既得益於集体修书之力,又收个人裁断考索之功,这是《通鉴》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清代潘耒论修史之要说:“搜访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遂初堂文集·修明史议》);可以说《通鉴》都做到了。《通鉴》虽编成于过去,其意义却指向将来,一如任何文本在与当前的关联中,都可以产生新的诠释学意义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集体编书成功的典型范例,它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为当代方志的修纂提供了有益的诠释学启示。
一、妙选人才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
地方志多数是众手修成,故如何挑选人才,乃是质量保证的关键。唐代史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史通·核才》)。清代史家章学诚亦认为“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而历代史馆修史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引进者多非其才,以致恩倖贵臣,凡庸贱品,终日饱食安步,毫无作为。《通鉴》的修撰成功,首先是妙得人才的结果,总结其经验,对新修志书当是有益的。
司马光先后荐召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协修,他们是否都为当时天下之选呢?
先看刘恕,时人称他“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氏曾撰《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北魏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又撰《通鉴外记》,以记周威烈王以前事,多《史记》、《左传》所不载者。如此难得人才,故凡遇纷错难治之史事,司马光都慎重委之于他,甚至谦谓自己担任主编,实际只是蒙成而已。
次说刘攽,亦邃於史学,博记能文章,曾著书百卷,其中《东汉刊误》,尤为人称颂。王安石从不轻易赞扬人,却有诗赠他:“刘郎高论坐嘘枯,幕府调腼用绪余,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且复弦歌穷塞上,只应非晚召相知。”(《王荆公诗集·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倾挹如此,可见其才高当时。
再论范祖禹,在司马光的编书集体中,他年纪最轻,即知识明敏,好学能文,著作有《唐鉴》十二卷、《帝说》八卷、《二皇政典》六卷。而《唐鉴》专详李唐一朝,深明三百年治乱,学者极为尊崇,以致称他为“唐鉴公”。
司马光慧眼识人,朝廷馆阁之士一个不取,却精选天下人才而得此三人。他的这个编书集体,年龄参差,老少结合,他们道相合而情相笃,各具学术专长,都是当时第一流学者,难怪晁说之称:“《通鉴》之为书,有贤杰辅相相攻坚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嵩山文集》卷十八)而刘恕等三人之遇司马光,司马光之遇英宗、神宗,亦可谓时也。顾炎武认为修志必其人有学识,且要有逢时之机缘(《亭林文集·营平二州史事序》);章学诚亦主张应立志科以广搜资料,“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文史通义·方志略例一》);瞿宣颖更慨叹:“不得真史家,则无宁但保存史料”(《志例丛话·通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七十馀种名志,无一不是名儒精心结撰或参与商榷的结果。他们或“手定议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或既物色得人,则隆以礼貌,专其委任,拱手有成,不予牵掣”;都可见无论良史或佳志的修撰,必以先得人才为前提,揆之今古及未来,绳以志乘及他书,当无一有例外,所谓事在人为也。反之,历代府州县志,凡“浅俗不典,迂谬可怪,油俚不根,猥劣可憎者”(《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一般都是因为操觚者不学无术,肆意漫笔。著述无主,必然猥滥,所以顾千里批评说:“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具文,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縻餐钱,虚陪礼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谈。”(《广陵通典》序)
二、明确分工才能发挥专长
集体修志,个人专长固然重要,如何相互配合,尽展其能,亦值得重视。刘知几指出:“设官分职,伫勣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史通·辨职》)章学诚亦云:“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章氏遗书》卷十五《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都强调明确分工,各有专职的重要。而司马光的具体做法,也颇值得志家借鉴。
《通鉴》分工进行编修,是根据各人的专长。刘恕“于魏晋以后事尤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委而取决焉”(《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攽是汉史专家,则负责汉纪部分,范祖禹稔熟唐事,故分职唐史,以后又兼及五代。最后成书,则“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鉴问疑》)。
助修诸人,分工明确,各尽所长,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范祖禹入志局较晚,司马光曾告诉他:“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让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祜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答范梦得》)可见各有专门,担负责任,又互为录致,铨配合理,增上之缘,彼此补益。而刘恕因风挛早卒,五代部分初稿未成,最后也是由范祖禹继续补完的。
除助修诸人互相配合默契外,主修司马光也主动与助手讨论义例方法。特别是刘恕,素为司马光服膺,商榷尤频。《通鉴问疑》集二人往复相难之语,涉及书法、正统等体例及有关史实问题,发明深广,启发宏富,以致刘恕之子羲仲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通鉴问疑》)
刘知几曾激烈批评史馆科条不立,铨配无人的弊病,认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丧失史家职守,“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史通·忤时》)。历代修志,职守不专,相互推诿,彼此牵制,坐啸无事,累年难就的情况也很多。《通鉴》的成功,说明能否研讨互助,激发灵思,配合有效,富于创意,即既重视激励切合每一个体的个人学术专长,又注意发挥集多数人为整体的结构性优势,也是关系到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问题。
三、众手修书必须统一方法
众手修书,明确程序,规定步骤,统一方法,最为重要。否则人多庸杂,如散钱无串,例既不精,稿何能善?又“譬为巨室,千门万户,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史通·忤时篇》有云:“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可在?”痛哉刘氏斯言,可永为鉴戒矣。
司马光统一撰史方法,首先明确三个步骤。一是作丛目,即按年月采摭异闻,排比史料,标出事目,注明篇第,尽量详备。二是作长编,即就丛目铨选修辑,锤练组织,凡有去取,须加考订,小字附注,宁矢于繁,不失于略,无以考者,必两存亡。以上两个步骤,明确规定助手负责,书吏抄录。三是定稿,由司马光一手裁定,删其繁冗,整齐杂越,考订异同,修改润色,如出一炉。
除在具体步骤上有统一安排外,《通鉴》更强调发凡起例的一贯功夫。如纪年以后来者为定,借年纪事,授受相承,不别正闰,无所抑扬;叙事先提其纲,后原其详,首详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及之;载人不为宋讳改书,人之初见者冠其邑里,国名人名相同者增文示别。宋乾道年间,司马光曾孙仍掇取家藏遗稿,辑为《通鉴释例》一书,推论当时凡例有用天子例、书列国例、书帝未即位及受禅例、书称号例、书官名例、书事同日例、书获斩例、书复姓例、书字例、书反乱例(《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鉴》条),从中不难窥见,早在著书之始,对全书义例方法,已逐条明确规定。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批评他“俱未曾附注,如何遽作长编”。可知其要求是何等严格。
史志专书方法的重要,直接关系到历史本体的再现。章学诚认为“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不仅应有前后一贯的方法,甚至“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氏遗书》卷十四,《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因为“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行远”(《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特别是集体修志,最忌条理混乱,杂沓重出,详略失体,文词浮泛,如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所说:“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衷,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矣。”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有光绪《顺天府志》,秉笔者既多博学通人,方法又极为严格缜密,洵夫有典有法,艺林称颂。负面教训历代屡见,以致章学诚讥贬下焉者为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上焉者亦不过文人游戏,小说短书,清言丛谈。一言以蔽之,方法不好或不明确不统一,绝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志书。
四、集体修志应做到日程宽与紧的合理统一
司马光主修《通鉴》,一方面由于神宗的眷顾优隆,使他有潜心治学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如潘耒所说,假以悠闲宽松之岁月,历十九年而磨成一书;一方面又有鉴于史馆徒延岁月而无所事事的前辙,明确限定每卷完成期限,从而最终保证了这部浩繁巨著的按期毕役。朱子说撰述乃生命之大业,应“宽着时限,紧着功夫”,“宽”“紧”二者统一,正是立言不朽的经验之谈,也是《通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做到后一方面的课以日程呢?司马光在《与宋次道书》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年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比,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纬略》“《通鉴》”条)。
可见他是以三日完成一卷的速度进行工作的。尽管北宋政府对他“量加常俸,不责课程”,然而司马光督课依然甚勤,而于己尤严。特别是中间遭到小人浮言中伤,诬告书久不成后,他更“严课程,省人事”(《司马温公年谱》卷七),促修益急,计日起功,且不惮烦费,细大不苟,自谓“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助手如刘恕,虽得风挛,右手足废,仍不罢修书,病亟乃止,辛苦之状,课程之严,实不难想见。如此则避免了终年卒岁,毫无刊述的史馆陋习。
人之生命有限,日力自当爱惜,何况著述大事,岂敢虚掷光阴,徒延岁月?清钱泰吉撰《海昌修志开馆条约》,列举四条撰作原则,其中一条即日力宜爱惜,颇值得今人反复玩味,不妨节录此:“欲成佳著,固难刻期,……若草率从事,有愧于心,然不惜分阴,淹滞岁月,则继晷无资,汗青何日?……资脯无多,冷斋共事,所望在馆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诸。各镇采访诸君子,不惮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各列姓氏,共疑则辱,共信则荣。泰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拟立日课簿,与诸君子共考焉。”(《甘泉乡人稿》卷十七)司马光实践在先,钱泰吉警言在后,今日睹其行而听其言,愿与各地修志者共勉!
五、广泛取材方能避免疏误
编纂志书,必取材多方,踏勘调查,证之文献,辅以见闻,联贯比勘,对照稽核,方能不疏不误,传信天下后世。《通鉴》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亦足资修志者借镜。
《通鉴》征引之书达三百余种,其中径自采用而未注书名的尚不在此数。不仅广泛利用了龙图、天章、三馆、秘阁等丰富的国家图书资料,而且还多方搜求或借本誉写散在民间闾巷的私家载籍。如宋敏求家富藏书,多至三万卷,而且都校过三、五遍,人皆以为精密。刘恕亲自绕道亳州借阅,敏求每日具办佳馔为主人礼,刘恕婉谢不受,独自闭门,“昼夜口读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宋史·刘恕传》)。司马光在洛阳时,读书堂聚书达万余卷,晨夕取阅,虽累数年,仍新若未触手。《通鉴》编成后,书稿在洛阳放满两屋,举凡《崇文总目》史部所录,几乎无不搜采,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纬略》卷十二),可谓博征详考,左右逢源,原原本本,取用不竭。司马光亦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扶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章太炎更盛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功力之深也。”(《史学略说》)《通鉴》记事确凿,无一不有根据,极少疏略或违谬,无疑是与既征引广泛,又辞约事丰分不开的。
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指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稿,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官,以凭详慎诠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章氏遗书》卷十五)这是将史料的范围尽量扩大,以求搜访时真正做到巨细毕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仅没有遗阙疏讹之虞,而且能进一步博观约取或详慎诠次,编出纲纪天人,究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志。刘知几曾批评史馆修史,视听不周,搜访不博;钱大昕认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可谓负面教训之总结。正面经验是鲁一同撰《邳州志》,凡“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鉴》、《通考》、山经、地志、官书、吏牍、世家谱牒、金石文字之类,反复研索,证之以旧志、府志、淮安旧志七八家,参以己意,断为一书。其自有明以前,宗诸正史,大都正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后,史所不详,则以志证志,兼考官牍,旁采舆论,增损匪多,而劬苦倍至”(咸丰《邳州志》后序)。征引既如此广泛,取舍又如此精严,洵其与《通鉴》一样,都是史海志林中成功的范型。
六、贯串折衷要靠主修裁断
主修裁断去取,最重要的是个人心识,必须烛然察照,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智慧卓绝,才能运斤施雕,权衡予夺,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刘知几说:“直若南史,才如司马,精勤不懈若杨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载言记事,藉为楷模,搦管操觚,归其准的。”(《史通·辩职》)司马光主修《通鉴》恰恰具备了这些品格,不仅发挥了集体编书的优势,而且表现出一家独断之史识,史学史常将地与史迁并列,称前后两司马,的确并非虚誉。
司马光少好史学,自幼至老,精勤不懈,苏轼称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司马温公行状》)。欧阳修虽与旧派政见不合,也说他“德性谆正,学术通明”(《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八)。而他自谓“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表现在学术上,即十分踏实认真,周慎细致,又眼光犀利,游刃有余,是才、学、识兼擅的大家。章学诚曾把三位助手的长编说成是比类(记注),司马光最后定稿方为著述(撰作),比类方以智,而著述圆以周,即可看出主修裁断的重要。
与一般史官主修虚衔领修,多趋兢无学之士不同,司马光学术深醇,识学严谨,既善于领导,使协修诸人有相济之美,又亲自动手,躬劳其役,抓义例,定书法,明步骤,草提纲。最后又狮子搏兔用全力,反复增删笔削,陶铸炉锤,断以心裁,一出己手,使历十九年而集众修成,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大书,风格统一,脉络井然,体例严谨,文学醇美。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神识哀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这部学术史上不朽名著的成功,正是司马光毕生心血贯注的结果。
主修裁断对方志编修的重要,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因为“苟非折衷以归于一,无以传后而信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瞿宣颖在《志例丛话·方法》中曾举过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不嫌冗长录之:“分修之人虽极一时之选,而无负责者为之主裁,则仍于无绩。嘉庆《宁国府志》未尝不分聘贤硕,如疆域舆地属之洪亮吉,沿革表属之凌廷堪,食货志、武备志属之震泽举人沈沾霖,选举表、营建志属之芜湖举人葛蓥,然观其沿革疆域为表冠于卷端,而舆地志于星野之后继以风俗,遂于郡土之广轮,乡社之区域,无一语及之,此宁非众手修书,无以主裁之过耶?”更严重的是光绪《云南通志》,不仅分纂多“风尘俗吏”,兔园学究,袜线猥材”,甚至“总理(无总纂)不任笔削,拥虚名以束下,分纂各持意见为选述,无所禀承折衷,总理既于分纂之优劣勤惰不甚别白,分纂则益轻总理,于是志在薪水,相率故怠,缓延数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纳贿,行恩报怨”(赵藩《续云南备征志》序),秽我志坛,岂能容忍!如此则何有良构佳志,遑论什么信今传后?这是与《通鉴》编修形成强烈对照的负面教训,颇值得今人反省沉思。
七、结语
《通鉴》作为中国古代集体编书的优秀范型,为今天史志工作者留下的启示,当然远不止上述六个方面。
清代章学诚曾提出“志属信史”的理论主张,此即显示志家一样担负着传承历史文化的天职。因此,今天参加修志实践的志家学者,在从事撰述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力量的较量,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写出有份量有质量的志稿,而且更要在志稿完成的过程中,创造真正属己的人格精神。伟大的人格是与伟大的作品相联系的,这是司马光人品与作品统一昭示的真理。反之,粗制滥造、庸鄙浅俗的作品,只能导致自我人格的否定或丧失,是生命精神及意志力量的失败。所以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即是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而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亦必须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撰之古今中外,大凡其人其书,或褒或贬,皆各有定位,原因即在于此。
志书无论今古,多数为集体修纂,因此每一个参与者,都应主动承担自己分工的部分,如同二刘一范那样,相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认真写出有学术水平的初稿,同时注意相互间的灵思引发,心智激荡,在配合默契因而具有创造性生机的境域中,把理想与价值落实在具有人间温情的合作事业上。科学史的经验表明,群体性的具有相同研究范型的人才,总是成批涌现在开放、挑激、引发、鼓励、竞争的机制环境中。每次阅读历代史志之书,最感慨那些无名氏的奉献,他们尽管默默无闻,各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多数遭受着时代的不公平,然而集少数为多数,对志乘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忽视。他们实际已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具有深长意义的志乘事业。
时代需要重新历史性地领会自身民族的精神世界,新时代的志乘事业,更需要司马光式的总纂人物。瞿宣颖特别强调一切学问,以贯串为难,史书无贯串之功,即等同堆积一大堆无用的史料,只有经过主修分擘综辑,才可能有活泼详尽之史志。设想如果仅有二刘一范而没有司马光,如何能有《资治通鉴》这样的不朽名著?正是由于司马光践履了自己的史家职责,认真进行分擘综辑的贯串工作,才使《通鉴》避免了百纳被的弊病,成为一气贯通的结构性完整著作。司马光峻立崖岸,总揽纲要,风声所树,人人知为圭臬。他作为主编留给我们的诠释学提示,就是时刻不忘志家之神圣位置,以主动自觉的精神传导全局,形成新的群体修志的规范,使集体协作如出一人之手,再创领袖时代的名志,不断开拓新的局面。
收稿日期:1999—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