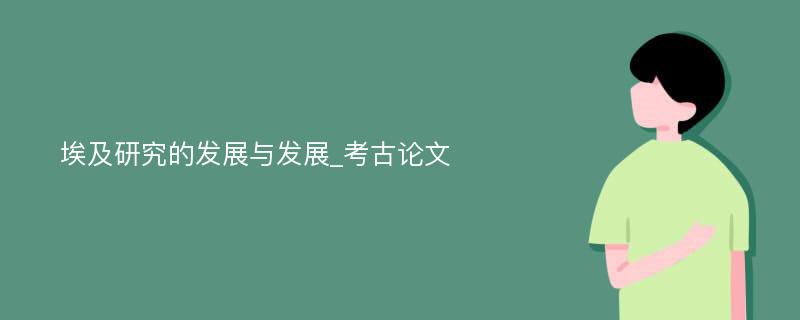
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2-0080-05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国家之一,其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 000年代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结束了埃及历史上近3 000年的所谓“ 法老时代”。由于希腊文化的渗入,有关古代埃及的知识逐渐湮灭。只是在19世纪20年 代埃及学诞生之后,古代埃及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才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埃及 学开创初期的情况如何?埃及学是怎样成长与发展起来的?这些问题是埃及学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为了加强我国埃及学的建设和发展,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 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 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 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 ,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 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 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 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 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 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 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 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 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 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 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 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 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 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 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 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 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 ,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 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 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 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 》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 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 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 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 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 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 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 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 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 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 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 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 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 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 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 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 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 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 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 。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 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 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 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 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 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 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 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 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 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 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 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 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 ,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 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 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 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 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 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 《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 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 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 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 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 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 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 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 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 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 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 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 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 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 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 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 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 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 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 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 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 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 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 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 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 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 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 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 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 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 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 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 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 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 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 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 ”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 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 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 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 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 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 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 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 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 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 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 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 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 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 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 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 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 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 。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 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 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 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 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 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 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 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 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 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 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 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 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 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 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 。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 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 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 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 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 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 。[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 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 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 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 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 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 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 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收稿日期:2002-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