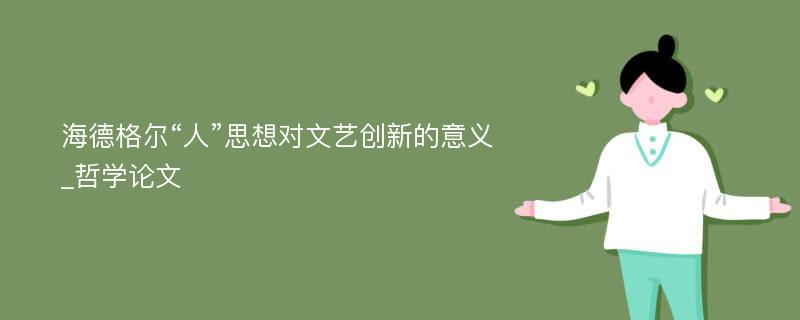
海德格尔“人”之“思”对文艺学创新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文艺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人类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人”的问题凸显。面对困境,“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浮出水面。“人是谁”这个问题要求的不是一个知识学上的答案,而是对人之生存状况的正视,是从本根上对人之为人的追问,它针对的是人类具体的生存困境,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它是一道古老而又常新的难题,它无关乎我们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深奥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恰在知识的无能处,这个问题才以本真的形态现身,它是在人的实践着的行动中被迫反省自身时进入人的意识中,“人是谁”与“做人”相关联,“做人不只是与头脑中的概念有关的一个术语,而是人这一特殊存在方式的一种处境,一系列条件,感觉能力或必要前提。”[1](p3)它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是求知的欲望和好奇,而是人之生存活动中的难题。疑难起源于处境,现代人的疏忽正在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存的艰难处境,忘记了自己是谁。因此,“当代很多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远远离开了那导致哲学得以产生的处境,以致他们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系。归根到底,哲学是为人创造出来的,而人却不是为哲学创造出来的。”[1](p2)问题的症结点是我们对人的思考必须回到人,回到具体生存活动中的人。
一、海德格尔“人”之“思”内涵阐释
海德格尔以其现象学视野的深刻洞察力,把人置于科学甚至哲学(形而上学(注:此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梳理委弃的所谓“柏拉图主义”。通过对哲学源头的追溯海德格尔终结了实体形而上学,但他在致“思”于“无之情形时”,仍有一种非认知的形而上学的建构意味。笔者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肯认,并把这种努力视为对价值形而上学的一种祈向。价值形而上学解构的是实体形而上学,建构的是一种以人生态度或人生意义指点为宗趣的虚灵的真实。参见黄克剑先生的《价值形而上学引论》等著述。))都无能为力的始源处,将人植入贫困状态来思人之人性。为此必须把自己从对“思”的技术阐释中解放出来,这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思”本身被视为一种τεχυη[技艺],就是一种为行为和制作服务的思考方法。于此,“思”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把思想称为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行为,这都已经是在对思想的‘技术性’解释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了。”[2](p368)结果作为“思”之要素的存在即作为本有的道说(Sage)的存在,在对“思”的技术性解释中被牺牲掉了,即此“思”放弃了本有的道说。始自智者派的“逻辑学”强化着这种解释的认可,人们按照一种与“思”不相干的尺度来评判“思”,当“思”偏离其本真性时,“思”便完结了,变成一种根据最高原因来进行说明的技术,人们不再运思而去从事哲学,哲学下坠为知识,甚至沦落到在诸科学面前辩护的窘境。因为存在被遗忘,人沦落于无家可归状态,现代人所经验的危险已昭然若揭。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由存在之天命而来,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掩盖起来。在临近的危险面前,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不能思“存在的荒芜”,只好在主体性的高扬中,如履薄冰自鸣得意地陶醉于理性编制的花环,为自己是“理性的动物”而欢呼,为掩饰悲哀和不幸,至多在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形而上学之规定中作些修补。无论笛卡尔的理智实体,富兰克林的制造工具的动物,还是尼采的权利意志,弗洛伊德的心理能量,都没有触及到人之为人的本性,反而凸显了人之无家可归状态。人因无法归属于存在而仅能在表象中审视存在,存在成为存在者的“最普遍的”,因而涵括一切的东西,或者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一种创造,或有限主体的制作物。鉴于人之根本性的无家可归状态,就要恢复“思”之力量,“思”之运思完成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思”作为存在之“思”有双重内涵,首先“思”归属于存在;其次“思”在归属之际倾听着存在之调音,作为倾听着归属于存在的“思”,就是按其本质渊源而存在。以此来思“人是理性的动物”及其修补论,就可洞悉其是以那种对存在之真理不加追问的存在者解释为前提,人与存在本质的关联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被遮蔽了。只有“无之追问即‘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被思时,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才能得到揭示,则人之人性才有了谈论的前提。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海德格尔把此之在带到了存在之本有和存在者与存在区别面前,体悟道人之本质就基于他的绽出之生存。“绽出之生存只能就人之本质来道说,也即只能就人的存在方式来道说,因为就我们所经验到的情况来看,惟有人才进入绽出之生存的天命中。”[2](p380)绽出之生存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既非某个对象性的东西,亦非某个人格性的东西。只有从“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生存论分析”之领域内才能得到思考。人是生存在世界中与物、与人烦忙着打交道的存在者,只有在“世界”的建构中,人才体验着他的本质,并体验着绽出之生存(Ek-sistenz)的绽出(Ek-)。人归属于在且以其本己的方式向着存在而在场的方式就是绽出地内立于存在之真理(无蔽的敞开)中。反观将人性视为理性(包括精神、人格、灵魂等)的规定则尚未经验到人的本真尊严,只涉及到人的机能,而无关乎人的生存处境。“只要人是绽出地生存者,人就存在并且就是人”。[2](p412)与其说我们离动物很近,不如说我们更不远于“神圣者”,当我们居于存在之敞开域的澄明中为“神圣者”之光亮所指引时,我们才能本真绽出地生存,才能思存在之真理,才能比形而上学所问更为原初。“恰恰是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恰恰是神权,限制并阻遏了王权;恰恰是神道,推进了人道精神的宏布;恰恰是神本,提高了人的地位。”[3]问人是谁,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人,这是一个含有应当的价值的问题,这个价值并不是人之属性也非人之高贵的表征。“人之本质的高贵并不在于:人是存在者的实体而成为存在者的‘主体’,以便作为存在的统治者让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消融在那种被过于聒噪地赞扬了的‘客体性’中,倒不如说,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们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2](p388)因此说到底,当把人之人性规定为绽出之生存时,强调的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人,而是存在,即作为绽出之生存的绽出状态之维度的存在。当存在之澄明自行发生时,存在才能转让给人,人亦须从绽出之生存出发来思存在之真理。此之在(Da-sein)因存在本身的天命而被发送到存在的切近处,此"Da"才会明起来,才能思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才有可能克服存在之被遗弃状态。只有在绽出地生存着的被抛中,人才比理性的动物更源始些更本质些,也比那个从主体性来理解自身的人更少些,人才进入存在之真理中,才会获得看护者的根本赤贫,而将自身召唤到对存在之真理的保藏中,而居于存在之切近处。“人也决不首先只是主体,这个主体诚然始终同时也与客体相联系,以至于他的本质就处于主体——客体关系之中。毋宁说,人倒是首先在其本质中绽出地生存到存在之敞开状态中,而这个敞开域才照明了那个‘之间’,在此‘之间’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才有可能‘存在’。[2](p412)这就要借助“思”之强力的指引,把人指引到他的历史性逗留的源始维度中去,并深思存在的本质,“当思想回降到最切近者之切近处时,思想才克服了形而上学。尤其是当人已经在攀登时误入主体性中时,这种下降就比那种上升更为困难更加危险。这下降引入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绽出之生存的赤贫中。在绽出之生存中,人就离开了形而上学的homo animalis[动物的人]的区域。”[2](p415)应强调的是把人之本质规定为绽出的生存,这种“思”是一种行为,但它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它发生在这种区分之前,这种思想之为“思”在于它对存在的思念。此“思”参与存在的建构,并把人之本质嵌入存在之真理的栖居中,这种栖居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本质。作为绽出之生存,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处于当下鲜活体验着的境域中,人时刻都要面临抉择,没有哪一次选择是一劳永逸的。人生来就被抛于困境,时时面临生存的难题,这难题表现在人的苦恼、困惑和精神痛苦中,其解决不在于拥有多少知识(理性),而在于这种知识中涵淹着的智慧,更在于这种智慧融贯于人的生命践履中。因此做人就是行走在路上,风雨飘摇,有期待,有鼓励,甚至一路歌着唱着。
二、对海德格尔“人”之思的挑战
海德格尔的“思”远远地偏离了西方哲学的思想,以致于连胡塞尔都感受到了一种危机。胡塞尔在晚年提出“生活的世界”,大声疾呼建立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塞尔的“生活的世界”因其“理智直观”的直接性,而把“生活的世界”理解为“现时的世界”即当下向我现身的世界。这是一个“理念的世界”,他以“理想性”来保证其实在性、现存性,以此回应海德格尔的“此之在”。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知识论转变成现象学的存在论。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通过对“为什么世界是有而不是无?”的追问,反思形而上学以之为“有”进行研究但却在研究“无”,可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在内,都不能以“无”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哲学(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对于这种“哲学”的危机,胡塞尔力图以科学的严格性来保证哲学的可能,使其研究不沦于“无”。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不能通达“无”,且拒斥或根本不愿知道“无”,但又须求助于“无”以便道出其本质。因此传统的科学(哲学)便提不出“无是什么?”,如同“存在”问题一样,这是被遮蔽的问题。而海德格尔问“无之情形如何?”,只有基于“无”,此之在(Da-sein)被带到并洞悉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面前,且深入到存在者那里,因把自身嵌入到“无”中,此之在已经超出存在者整体之外而存在了,即处于“超越”状态,以此他才能与存在者也与自身发生关系。“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4](p133)“无”乃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根据,它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因在“无”的问题中发生着一种超越,故“无”的问题就表明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4](p137)如果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是“形而上学”涵盖一切的问题,则“无”之问题就涵括贯穿着“形而上学”的整体。“唯当科学的此在并不抛弃无时,科学的此在才能在其存在中理解自身。”[4](p140)因为“无”的敞开,科学才能把存在者视为研究对象,因从“形而上学”处获得根据才能有所作为。人因把自身嵌入无中,此之在才能对存在者有所作为,才能有所超越,这种超越就是“形而上学”本身,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属于人之人性,只要我们生存着,我们就已是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只要人绽出地生存就会以某种方式运思,哲学就会赢得自身。通过对“无”形而上的追问,海德格尔从本根上否认了一切所谓的哲学(包括“人道主义”、“人性论”等)的本源性,从根本上否认了对于生活的世界可以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的可能性,终结了哲学的虚妄性,从现象学走向了本源性、历史性、存在性的“思”。
回应于胡塞尔的疾呼,以雅斯贝斯、萨特为代表的实存主义,力图在新的形式下保持、恢复和发扬西方哲学的内在精神和传统。雅斯贝斯把海德格尔的Da-sein降为经验的现实的人的存在,认为“实存”(Existenz)是对Da-sein的超越,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他始终为“现时”,因而是独一无二的自由的“创始者”。他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它不仅是一个现存的生命,在其发展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5](p209)同海德格尔一样,他也反对把人作为对象来研究,对象化了的人是被贬抑的人,不再有自由,而只是被束缚被规定的东西。人的本质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理性概念无法把握的绝对个体的可能性,是无法规定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实存”。“现时”的人具有不可重复性,这决定了每个人既有至上性又有不可否认的局限性,故人须超越内在存在,在理性王国中达到相互交流、相互理解。雅斯贝斯对“现时”的强调,恢复了西方哲学传统的“自由”观念,“现时”超越“过去”和“未来”的当下正是“自由”的体现。“实存”内含着一种包容和超越,是人在本己自由真切的人生体悟中返求诸己的本源性,由此觉识到自己的“实存”,并在自律中祈向“超越个人内在存在”。这样,雅斯贝斯就以“实存”为立足点接续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因“现时”永远是当下的,所以人时刻都能感受到这种“自由”。那末为哲学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而战。
萨特以《存在与虚无》为书名旨在批评海德格尔学说中缺乏“意识”的维度,“意识是这样一种存在,只要这种存在暗指着一个异于其自身的存在,他在它的存在中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存在。”[6](p715)建基于“实存”观念基础上的“无”是人之“意识”的灵机所在,他对“意识”维度的凸显意在表明,因“无”而使人自己成为自己,人因其能“无”而有自由选择。“实存”作为萨特思想的核心其涵义就是“现时”,就是自由,任何自在之物都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但作为另一个自由的他人却能限制规定我的自由。在这里“实存”是指一种自由生存的现实性,它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绽出之生存。“从绽出方面看,绽出之生存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同于实存。在内容上,绽出之生存意味着站出来进入存在之真理中。而实存即现实性,乃是区别于作为理念的单纯可能性。绽出之生存所命名的,是对人在真理之天命中所是的东西的规定。而实存始终是表示某个在其理念中显现而存在的东西的实现的名称。”[2](p383)形而上学自柏拉图始就说"essentia"[本质]先于"existentia"[实存]。萨特将之颠倒仍为形而上学。
列维纳斯在海德格尔"Sein"的基础上,吸收了马丁·布伯的你-我理论,以弥补“共在”状态中,为海德格尔所忽略的“他者”的维度。“他者”不是日、月、山、川而首先是“他人”,“他人”与“我”是对立的,“他”不能消融于“我”之中。“他”对“我”有一种不可回归性,不可把“他”归结为“我”的知识的对象,“他”对“我”永远有着神秘性。据此他批评海德格尔把“他”亦当作“我”,使“他”与“我”处于同一层次,这意味着化“他”为“我”进而取消了“他”。并进一步指出他仍没有摆脱希腊人“求同求全”的思想传统,依然要求从存在入手探寻存在的意义,可是面对“无限”这一“彻底的外在性”,包括西方文化的任何文化都是有限的,都不过是“无限”的一种见证罢了。因此他呼吁一切为“他者”的责任,呼吁创建为“他者”的哲学。
雅斯贝斯的“自由”,萨特的“意识”,列维纳斯的“他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切入海德格尔“人”之“思”的弱处。虽然在本根上对海德格尔没有形成威胁,且受其启发和影响,但他们以其视野指出了此在的“贫乏”,且又接续了西方文化内在的传统。可以看作是对海德格尔人之思内涵的补充和丰富,因而有可取之处,但要警惕把人再次沦落于形而上学的窠臼。
真正对海德格尔“人”之思进行挑战的是德里达,他以“延异”(différance)来解构海德格尔的“区分”(difference),"différance"严格来讲不能作为概念来把握,否则会把中心和在场等涵义重新纳入“延异”中。作为一个策略性名称,其涵义为(1)差异(to differ),即包含着在场与非在场之间的非同一性;(2)延异(to defer)即从“过去”向“未来”的过渡,在场既与非在场相异又延搁到非在场,同时非在场又延滞了在场。他以"différance"作为“活的现时”的对立物,意在表明“现时”不是自明的和显现的,以此向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切哲学挑战。德里达认为一切显现的学说,都只抓住“现时”的独立性以使意义显现出来,而人是其明证。德里达不承认有一个本源性的“思”,不承认超越性意义的“显现”,“延异”既非“有”又非“无”而是“变”,不断留下又涂抹“痕迹”,这如同“游戏”,“游戏”既非在场又非不在场,游戏者因游戏而在,但这种在不是“显”而是“隐”。故此游戏是形而上学和存在论所不能及的,所以说对“意义”、“真理”的追求是西方人包括海德格尔也在所难免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顽症,故德里达把海德格尔视为欧洲思想史上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德里达解构了“人”,就形而上意义而言,他比海德格尔更为彻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人的历史性存在,并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存在,而始终不放弃一种“解放的承诺”,提出建构一种新“人文学”的可能。
其实真正能和海德格尔的“人”之思对话的还是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在二者的互动中,以马克思的“劳动”观弥补海德格尔的空灵,使其人生落于当下现实生活的真实处。同时又以海德格尔的绽出生成性防止人的僵化,还其人的鲜活的本真形态,二者的相互契合进而融合可能会结出人学的丰硕成果。就历史的深度而言,海德格尔对马克思评价极高,认为是萨特等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就人的生存来说,对象化活动是人不可扬弃的最为基本的实践方式,它并不必然导向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关键是要把人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人作为自由自觉有反省能力的人,应注重人生内外两个向度的和谐统一。这在海德格尔,就是人的绽出地生存应以不破坏世界的统一性为底线,即不破坏天、地、神、人四环一体的世界建构。在此四环共舞中,人获得了神圣性的尺度,并进而将之收摄到人之人性中,这种对神性的呼唤意味着人内心信仰的复活。在当下体验的人生境遇中与自然、他者处于一种互蕴互含的共在中,但并非东方天人合一式物我双忘平面的静止的世界。天、地、神、人因源初的统一性而统归为一,在互蕴互含中相互限制相互规定又各自独立,不即不离合一又不相同而相互吞没。当说到其中之一时,也就伴思着其它三者。因而绽出地生存的人一同带出的还有其它三者的在场,因此人之筹划的行为就通过拯救大地,悦纳苍穹,期待神明与引导众生而达至栖居,这种人性的栖居就是守护性的和平的揭蔽。于此人是存在的牧者更是自己的主人,但不是世界的霸主亦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
三、对文艺学创新的启示
经过海德格尔追问、悬置、梳理的“人”,就从形而上学的理性枷锁中回复到人之始源性的生命践履中,人才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处境。严格地讲,在海德格尔那里并没有“人学”思想,有的只是“人”之“思”。在后期思想中更是将天、地、神、人的互动融合,作为对存在的本真的“思”,以“思”之强力带领我们在语言中穿行,去“思”始终被遮蔽的存在,但存在并不是思想的产品,恰相反“本质的思乃是存在的一个居有事件。”[4](p359)绽出之生存的人因对存在的本真的“思”,而使人在与存在的关联中承担其对存在守护的责任,进而在生存中建构一个世界,让存在者的存在进入澄明状态。在存在之家中,人作为守护者而居于存在之旁,在世界世界化的过程中,人只是天、地、神、人共舞之圆环中的一环,因人之人性被放于适当的位置,就不会形成主体性的膨胀和各种僭越。人因对神圣性的信仰而拓展了内在心灵深层的维度,因此人在建构的世界中关乎的不再是一己的悲欢,世界成为共在的众生欢歌泣语的舞台。大地就是这舞台的基础,是这舞台得以展开的时间性境遇,更是守护这敞开的归隐。故而人成了大地上、苍天下充满神性信仰的自品自足自乐的歌者舞者。据此,海德格尔眼中的古希腊神殿才可能是,生与死、福与祸、胜利与屈辱、持久与衰竭的汇聚,而成为这个历史民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建构中,人对大地并非毁灭性的使用、掠夺性的开发,而是使大地成为大地,岩石开始负载和安居,金属开始闪光,颜料开始光彩夺目,音调成为歌唱…乍看,大地似乎是作品的质料,是天然的存在。其实不然,在大地之为大地的过程中,是人以守护性的和平方式与大地共在。大地不离又不止于土地,它浸润了人之人生的欢乐与悲凄乃至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恰是在四环一体的运思中,我们进入了生之澄明的境界,存在之天命(是一种关乎人之本真性生存的动势的本真时间性境遇,有专文阐释)有可能亲临我们的此在。按存在的天命,作为绽出地生存着的人必须守护存在的真理,即守护存在之光。存在之光就从世界与大地相互冲突的张力中投射出来,是日常状态的突然中断,于是进入作品就进入了和凡俗沉沦迥然相异的世界。但中断只是瞬时,因而敞开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事件,真理的本质被“无”所派生的否定性所支配,才使瞬时过后又落入日常意识的沉沦状态又被这种否定性所打破。即而作品处于永不止息的张力的互动,就不会僵化成现成性而指向一种超越与多种可能的生成性。存在之光是真理的闪现亦是美之光,美是对真理的揭蔽而显现的一种方式,是艺术光源之所在。在此海德格尔“把艺术提升到哲学(美学)本体——人性本体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人进入生存之境的表达方式。从而唤醒了遗忘久远的艺术的生成性即是攸关人生的一个创造性本源。他赋予了艺术以最积极真诚的意义。艺术、真理、美奇妙同一(同一非相同非合并)了。”[7]因此人对存在的守护就是一种光明朗照的活,亦是人自足怡然诗意绽出地生存在大地上。同时人因在实践的缘构境遇中,基于现实的单面性和不完善性,而具有了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
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的人,回到人当下生存体验的境遇,直接遭遇着现实生活中的烦心与烦神。因有真理之光的引导,人在世界中与众生共在于无蔽的敞开之境,亦即人从遗忘存在的沉沦状态中绽出地生存,受存在之言的召唤人倾听并应答“道言”,人就可秉气勇毅的来做诗和运思。人因洞悉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和“居有之事件”,就突破了逻辑之网和概念的僵壳,就会在当下的体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进而才会展开人生的筹划和建构,以求获得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人生。语言是存在之家,源初的语言就是诗,因而诗就是人之生存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对存在的守护就是对家园的守护,就是对诗的一种吁求,就是对人心皆有诗这一维度的呵护和提撕。人们可以做诗和读诗,甚至纯粹的散文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有“诗意的”,宛若诗一样,和诗一样珍贵。因而对人之心灵中“诗”这一维度的守护,就是对审美这一超功利的价值向度的首肯,它对于绽出地生存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如远方的地平线,召唤着我们前倾,使我们仰望着。人是充满信仰的行走在途中的永远的未完成者,其间充满了诸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因此就不能用任何现成性的模式来套用人,也不能抽离人的某一特性而使人僵硬化。回复到人的真实境遇中,在敞开的“几微空隙”中天、地、神、人居焉,进入各自的本体,物成为物,人成为人。并在互动中处于人与人、人与物互为好意的揭蔽中,此时的人就会获得一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就不会高奏主体性的凯歌。以这样的人之人性契入文学活动中,则文学就会获得一种新气象,文艺学研究就会获得一个新的平台,就会拓展研究视野,打破狭隘的学科分界,拓宽研究领域,但不是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是承认学科分化意义基础上的融合。即以文学的审美的视角关注诸多人的生存境遇的问题,并把问题一同带入人的生成中,在共同游戏规则下言说历史性人之绽出活动,因此,人基于现实的生存发展问题就成为文艺学关注的焦点,人因绽出的生存的观念的生成,而把文艺学置于健康合理的生态环境。文艺学不再是党同伐异的棍子和依附创作的附庸,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同化边缘文化话语的工具,也不会僵化成现成性格局,而是形成一种多元共生、多方对话的互为主体的敞开域。在此平台上就激活了文艺学的活力,在人之人性与文学性相契合中既把人生纳入审美中,又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维护了文学的自主性,审美的价值向度也在其应有的层面凸显出来,这在当下精神家园丰富的贫困状态下,尤有其现实意义,把美从萎缩中拯救出来,作为人生一个独立的价值向度存驻于心中;因美的掣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的人,就不会沉溺于感官欲求而难以自拔,也不会因自身的理性而僭越天、地、神的领域,不会以其技术的所向披靡而使自然彻底“祛魅化”,而是以柔性(人性)的技术使人与自然共在中处于和谐的状态,自然环境生态化就成为可能,自然就会再度成为人类的“家园”。这犹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揭蔽的,正是艺术而非其它使艺术家之为艺术家,使艺术品之为艺术品。但在艺术的生成中,人是大有作为的,在植入真理之光的天、地、神、人共舞中是有着人这一维度的,去掉有用性而孑然独立,同时又是人参与创造的器具不就是艺术吗?可见艺术作为一种揭蔽方式是对真理(存在意义)的守护,其中人之绽出作为重要维度参与了真理的在场,是人之作为使存在从暗夜中明亮起来。因此,作为人之绽出地生存的筹划活动之一的文学,就不能堕落为语言的游戏和闲谈,它是人感天动物的当下生命体验的形式,是沟通天、地、神、人之内在心灵的方式之一,是对神圣性的一种价值祈向。与海德格尔人之有为相反,老子强调“为道日损”,“道之为道”贵在“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知其白,守其黑”,自然而然,才会“见素抱朴”,是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在此人只有无所执著,有所觉悟“为无为”,“道之动”才会返归为“朴”,“朴”散则为“器”,可见“朴”、“道”、“器”相通相化,这就打破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现成性格局。庄子以遮诠的方式描述了得“道”之人的逍遥游境界,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展示的是高超的技艺,成就的却是“道”,但在它的描述中却使我们感受到“道”之导引和“技”之驱动,这里纪录的虽是寓言,在场的仅是技艺,但却以得“道”的境界为旨归。在此境界以技进“道”,可谓“道”技相通,亦可谓“道”“器”相通,呈现的是一种化感通变的灵活。在文学建构世界的活动中,不仅在审美意味中对人有着现实的关怀,更有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道通天地有形外”的终极关怀。在此人不是征服者,也不是丧失人之本根的臣服者,而是处于绽出地自然而然的状态,人只有活在鲜活真实的生命状态中,面临真实的不完满、片面性的生存处境,才能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觉识到人应审美地生存和人生的审美化这一价值向度。有此内省的觉悟,文学作为人体道这一式的内涵就会获得提升,文学是人参与四环世界建构的方式之一,纪录的是天、地、神、人交汇的神圣文字。
海德格尔“人”之“思”对文艺学的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注入多少新知识,而在于他以“思”之强力矫正了我们当下“人”的虚妄性,以“思”之本源性来思人之人性,使我们正视了生存境遇中的“人”,唯此“人”才是我们文艺学的研究者、反思者、关注者。因此“人”之作为,我们的文艺学才有所创新,唯此“人文学”视野,文艺学才会获得新的生长点,文艺学学科建设才会有一个新的平台。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艺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哲学家论文; 人性论文; 科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