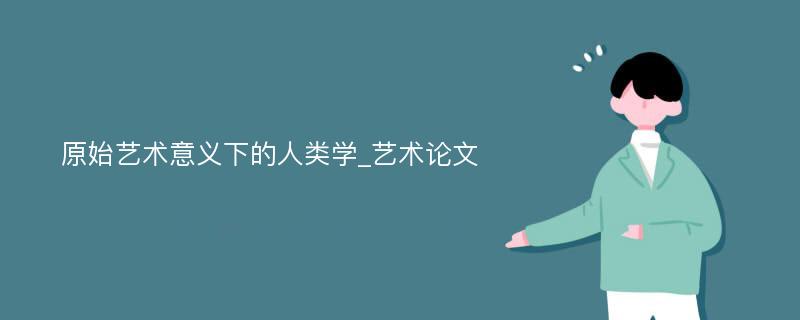
艺术之原初意义上的人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艺术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文的“艺”字,古来有“种植”、“才能”、“准则”、“区分”等意义;“艺”与“术”合称,泛指各种技术和技能。中国古代教育以“六艺”为主,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至于人们今天把“艺术”理解为音乐、舞蹈、美术,甚或文学,那是中西交流的结果。英文art或指“美术”,或指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等在内的“艺术”,或指人文科学,或指方法和本领,或指与自然相对的人工;另有“奸计”、“学问”等含义。从总体上看,汉文和英文有关所指在总体上是相通的。
如果,我们仅从汉文“艺”字的原初意义考虑,即仅考虑其“种植”、“才能”、“准则”、“区分”等意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竟然是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种植”与英文的culture(文化)的本义相通,显然是对自然的加工,是人工。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仅要适应自然,还要改造自然,并且在适应和改造中,赋予自然以美。在他们那里实用与审美合而为一。人类是符号动物,他们在加工自然的同时,也加工意义,为加工对象施加种种社会意义。野生的动物和植物固然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食物和能量,但是,如果要能够生存的更稳定、更安全、更惬意,那就要种植;人口的增加,动物的饲养,社会的分工,都和种植密切相关。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学问,这是共识。人类学家至今在研究着人类对于自然的“种植”,对于符号的“种植”,对于意义的“种植”和对于情感的“种植”。
人在自然与社会的生存斗争中,培养起了各种才能,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是其中的几种。艺术人类学注重研究人类平面的立体的造型艺术,文化人类学注重研究他们的舞蹈艺术(仪式)。但是,他们自己也很难找到这些艺术的界限何在。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中,有着求雨的龙舞,有着遍布南北的狮舞,有荷花舞、芦笙舞、安代舞、孔雀舞、十二相舞等等。人们常把舞蹈说成是“表达人类心灵的动态语言”。不过,从起源上说,舞蹈并不比语言晚,甚至还要早。中国古代的各种岩画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等视觉艺术,为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佐证,使我们后人在观赏他们的作品之余,也为他们的才能所折服。相传伏羲造“琴”和“瑟”,“女娲作笙簧”。汉魏之际的散乐,又称“百戏”,包括音乐、舞蹈、杂技、幻术、角抵杂戏等内容。但是,人类学家更关心这一类才能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关心这些才能的培养过程、运用过程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上结构意义。这就要求他们深入田野,参与观察,同时也注意文献记载。田野调查意味着现时,而不是历史;但现时在每一刻都在成为历史。
中国古代儒家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关系:语言有圣俗之别,举止有尊卑之分,一切显得自然有序。这种不平等或者横向差别在农业社会等造成了阶级差别,而在工业社会这种差别则构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界线。就如同英国人类学家格尔纳所说,识字和阅读能力制造了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之间的大分裂:权力和文化(认知)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他们与广大的农业生产者,也就是农民,分离开来。在统治阶级中,军事、行政神职人员形成不同的阶层,他们强调阶层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认同。在横向分层的少数人之下,有侧向分隔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小社群。在农业社会文化和权力还不能整合。强调阶级差别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社会稳定。所谓“准则”意味着边界。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边界,功能是相对流动的边界。以什么为标准以及如何贯彻这些标准,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就拿姓名制度作例子。居住在中国西南的独龙族,过去存在氏族和家族组织,婚姻实行称为“伯惹”的对偶婚制,即:在固定的婚姻集团中,甲氏族一群兄弟与乙氏族一群姐妹,可以同时或者先后结成配偶关系。其突出特点是,甲氏族每一个成年男子可以娶乙氏族每一个女子,但是乙氏族成年男子不能娶甲氏族成年女子,而必须娶丙氏族成年女子,以防止“血倒流”,这就形成了单向环状联系婚。独龙语把两个通婚集团的男子称为“楞拉”(意为“丈夫”、“男子”),女子均称为“濮玛”(意为“妻子”、“女人”)。至于哪些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则取决于家族名或者姓。因此,根据族名形成若干个婚姻集团。据《论语》载,姬姓的鲁国国君鲁昭公,从同为姬姓的吴国娶妻,为了不触犯周朝礼法,避免非议,这位按理应称为吴姬的吴国女子,改称吴孟子。由于鲁昭公与吴孟子系同姓婚娶,故吴孟子死后,《春秋》并不记载她的姓;不发讣告,不称夫人,安葬后免去到祖庙哭号的礼规,吊唁时孔子脱丧服下拜。在这些例子中,姓氏是规定婚姻边界的一个标志。
其实,无论任何准则,都要建立在区分之上,而区分又与整合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就以上面提到的姓名制度为例,任何民族的姓名,不论其特点如何,都具有对内整合和对外区分的功能。姓名的整合与区分功能既涉及社会分类、民间知识、行为规则、交际、信息传递等应用方面,也涉及想象、创造和记忆等心理活动及其表达。在姓名表达的整合与区分心态的最底层,潜伏着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具有稳定生物性基础的本能。但是,姓名所反映的这种人类整合与区分的生物本能,已经演化成为社会和文化的衍生物,已经不能和最初引发它的原始冲动强为比拟;政治、经济、审美和情感的维度,已经为它造就了限制性的网络和框架。无论是姓还是名,其首要功能是区分个体或者集团;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和交际需求的不同,姓名的区分对象和区分层次也会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姓名不分,区分的对象主要是群体;在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姓名区分个体的比重增加。从总体上观察,姓名的区分层次可以分为三种:个体区分、身份区分、血缘区分,在现代化社会,个体区分是最基本的。身份区分包括族属、阶级、财产、信仰、态度等方面。血缘区分涉及父子、母子、父母双亲、婚姻、血族等等社会认知因素。姓名区分身份和血缘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特征:它们在传统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比较重要,而在现代化社会中却并非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非现代化社会,姓名身份区分功能和血缘区分功能之间的关系,也有历史变化。在前阶级时代,个人的族属和血统观念是没有差别的,个人利益与血缘关系紧密关联,姓名区分身份和血缘的功能并未分化;在阶级时代,血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动摇甚至取代,姓名区分身份和血缘的功能则已分离出来。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一般把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职业称为“位置”(seat,place,berth)。在巴厘人的思想和活动中,“位置”分成家户的(domestic)和公民的(civic)等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在每一个层次,从村社到王宫,公共事物与私事、家事决不混淆,因为在巴厘人眼中,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有它自己的利益和宗旨。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把公共领域看成是密封的整体,而是由一些互相分离、有时互相竞争的自立组织构成:村社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地方寺庙是一个宗教联合体;灌溉社团是一个农业联合体;以贵族和高级僧侣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和祭祀结构。公名可以和排行名、地位称号连用,以区别个体。公名资格与地位称号制和种姓制密切相关,受到有关道行资格教义(the doctrineof spiritual eligibility)的制约。根据这个教义,超地方的政治和宗教“位置”只能由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占居;首陀罗只能占居地方“位置”。虽然荣誉地位在总体上与公职有联系,从而在公众眼中,政治秩序与超自然秩序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个人身份并不取决于年龄、性别、才华、脾性或者成就之类的世俗因素,而是取决于个人在整个精神等级的位置。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文化类别集(a set of cultural categories)中的归属。即便是神也只有通名Dewa(Dewi)或者用于高层的Betara(Betari)。公名制的核心是宇宙结构,而非政治、经济或者利益层面;那些有公名的公共事物管理者(stewards)是一些没有世俗特征的、只作为结构成分的个人。与此同时,那些几乎没有面孔、千古不变、只以公名行世的神,在巴厘岛上千百个庙会上,表达了巴厘人有关个人身份的真正观念。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区分的目的在于控制。国家掌握了大量有关分类、知识和控制的权力、机构、设施和手段,并把它们用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创造。在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文化的生产中,划定边界,即对全球流通进行“分割”,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之一。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涉及文件、档案、登记、证明的综合工程;民族国家既是想象物,也是出自“存货清单”(inventory)的产物。个人要效忠自己的国家、国土、人民、合法的统治制度、国家象征等等;同时,他们在性别、种族、族群、年龄、籍贯、职业、宗教信仰、语言等等方面,被划入不同的类别。民族国家的隶属(国籍:nationality)与个体身份特征(individual identities),是通过分类和分界来实现的。
在现代社会,艺术主要用来表达情感,主要表现的是直觉。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们争论美术和社会科学之间是否存在同一规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经验与直觉等等哲学问题,已经争论了上千年,恐怕以后还要争论下去。信息时代是概念爆炸的时代,也是概念危机的时代。知识的增加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从前那些习以为常的概念都在受到质疑: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艺术?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不可避免,撇开通则、我行我素的做法也在继续。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美术的主流是直觉和感受,而社会科学的主流是理性和推论。当然,这只是现代的一种惯例,其中又有不少例外。情感与理性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对立,恐怕这是一个事实。西方文化容易把非西方文化看作是情感的,而把自己看作是理性的;男人把女人看作是情感的,而把自己看作是理性的;多数民族容易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情感的,而把自己看作是理性的。而实际上,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每一位个人,都有着情感与理性的两个方面,只是此时此刻的选择与彼时彼刻的选择,有所不同而已。
在艺术之原初意义上,人类学与它多方面的相通之处。从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都在证明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艺术与人类学的相通之处被掩盖起来,被理性与情感的对立隔离开来。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不能轻易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原初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