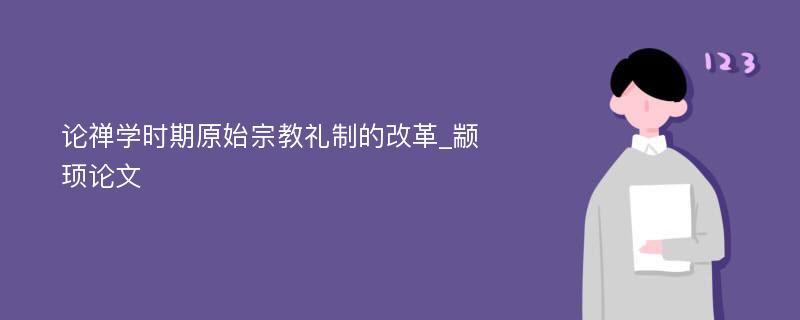
浅论颛顼时代的原始宗教礼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制论文,原始论文,宗教论文,颛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7)03-0024-03
古史中所说的五帝,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而比较认可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喾、尧、舜,其中颛顼是五帝中成就比较杰出的一位。《史记·五帝本纪》云:“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1] 这说明颛顼是位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他能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聚集财物,又以观天象,按日月运行而定四时,改革原始宗教礼仪,教化人民,促进生产发展。颛顼是“五帝时代承上启下的重要代表人物”[2]。原始宗教礼制改革,就是颛顼对中华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一、颛顼时代前的原始宗教状况
王国维云:“巫之兴,在少皋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3]。在原始社会,自然环境恶劣,原始人类生存条件差。人们常常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试图利用虚构的“超自然力量”来实施某种法术。其表现为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对自然、图腾、祖先的崇拜。正如龚自珍所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4] 这就是原始宗教最初的表现形式,即所谓的巫术时代。古文献中有少量原始宗教的记载:山被视为神之居所,可以“通天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天山”上“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高山”成为“群巫所从上下”之天梯,巫师柏高能登肇山至于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或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5]。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巫术宗教已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赤铁矿粉,应是原始巫术宗教活动的遗物。早期的巫术“民神不杂、民神异业”,宗教活动是以“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方式进行,即以家庭个人的方式进行;而到仰韶文化晚期发展到由氏族长来执行,但宗教活动尚与一般社会活动混在一起,还没有专门搞宗教活动的巫师出现[6]。
原始社会中晚期,当炎黄部落在中原地区兴起的时候,海岱地区的东夷部落也强大起来,并对炎黄部落形成威胁。其中,九黎部落对炎黄部落的冲击最大。虽然黄帝在涿鹿之战中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但九黎部落西进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楚国大夫观射父在《国语·楚语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所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齸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7] 46观射父将“民神杂糅”、祭祀混乱的局面归罪于“少昊之衰”及“九黎乱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即将解体,私有成分已经产生,部落联盟形成,各大氏族集团、部落首领争夺天下,兼并战争不断,社会急剧变化,导致了社会巫风弥漫,人人祭神祀鬼,且祭祀名目繁多而无度。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民神不分,人人可装神弄鬼,玩弄巫术,使得巫教秩序混乱。二是人人祭祀无分别,家家自称为巫史,结果是“无所要质”。何谓质?《逸周书·尝麦》说:“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8] 77可知当时的宗教祭祀权相对较为分散,严重缺乏司管祭祀及巫史的职官。三是由于多祭淫祀,导致物质匮乏,人们生存受到威胁,故“不知其福”。四是蒸享严重缺乏社会法度约束,对神灵亦缺乏必要的虔诚与崇拜,反而出现“民神同位”的反常现象。五是黎民非郑重发盟,轻慢盟誓,无有诚信,亦不畏惧神灵的惩处。六是神灵习惯黎民百姓如此状况,不求祭祀洁净,亦可谓“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9] 35。七是黎民浸淫巫风,疏于耕种,谷物不受神灵降福,最终导致无物可用于享祭。八是祸乱灾害频仍降临,万物疡夭而不能尽其生气,万事懈怠而不能尽其善。这种轻慢之巫风浸淫社会的各个角落,结果是世事空疏,殃及社会。导致人言与神旨混杂,势必会干预部落联盟的政要大事;舞神弄鬼,势必会亵渎联盟之威严;物资匮乏,势必会动摇政治联盟的基础;如此民神“杂糅”与“同位”的状况又势必会影响到部落联盟的政治变革,乃至阻滞国家形成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颛顼承担起这一原始宗教变革的历史使命。
二、颛顼推行的原始宗教变革
颛顼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宗教的初步发展期,人们的宗教意识相当混乱,而此时的社会组织通过兼并与战争已出现更大范围的部落联合体。然而,疆域的统一并没有消弭各部族间相互交恶的矛盾。在此情况下,一场顺应社会发展及文明进步的原始宗教变革运动就在所难免。颛顼进行的宗教礼制改革,目的就是以宗教意识为手段,使原始礼制规范化,在管理社会、规范人们言行中发挥它的权威作用,此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颛顼进行原始宗教礼制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如下措施:
1.原始宗教特权化。颛顼所处的时代,由于九黎的扰乱,巫教秩序混乱。人人祭祀无分别,人言与神旨混杂,亵渎了神的权威。颛顼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使社会重认可与神沟通是少数人的特权。《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较详细地叙述了颛顼进行的宗教变革:“古者民神不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昊之衰也……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7] 58颛顼依靠南正重和火正黎的帮助,使地民与天神断绝沟通,只有颛顼和重、黎可以与天神沟通。随时传达天神的旨意,来规范万民的言行。颛顼成了天神的代言人,即是高度集权的宗教主。这样颛顼传达天神的意旨就有了权威性。颛顼为了发挥宗教的威力,建立了宗教中心[10]。《庄子》云“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就是宗教中心。
2.原始宗教礼制化。九黎作乱,社会失去了以原始宗教为基础的礼制法规。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其结果是原始社会逐渐礼制化,如男尊女卑地位的形成。《淮南子》中载“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忂”,意思说在路上,女人碰上男人如果不让路,就会被流放。又颛顼时代的宗教改革,将乐应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礼乐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帝位。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凤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11] 这说明颛顼时代有了定型的音乐,创造的《承云》主要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反映此时的乐已经纳入礼制的轨道。礼制的确立和乐的形成与发展,为殷商礼乐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宗教神权同一化。颛顼时代既是一个英雄神话时代,还是一个图腾崇拜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部落联盟时期的著名首领都是与巫师形象分不开。例如,《韩非子·十过》云:“昔者黄帝会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蚩尤居前,风师边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蟒伏地,凤凰复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12] 颛顼当然也是大巫师,颛顼除人格外还有神格。《国语·周语下》云:“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13] 颛顼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原始宗教领袖,倘若欲施行原始宗教变革,统一各部落之神权,看来并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尚书·吕刑》记载,当时三苗复九黎之凶德,正处于“民神杂糅”的状态,以至社会秩序混乱,“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9] 31。颛顼若治理三苗之神权,定会招惹三苗的不满与怨恨,亦会受到阻抗。但颛顼仍旧“遏绝苗民”,己平教权,“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淮南子·天文训》还记载共工与颛顼争帝,实亦为争夺宗教领导权,从而导致大的战争。“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4] 这里记述的既是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又是一场巫术之间的较量。山为天柱,这正是巫师借助于通天地之工具,“天柱折,地维绝”,可以想象当时战争伴随巫术施法相攻之激烈,最终以颛顼部落胜利而告终。这些都为颛顼领导宗教变革扫清道路,亦为宗教变革成功提供了保障。颛顼破除一切阻力,发动原始宗教变革,治理原始宗教的混乱局面,于是“绝地天通”,结束人神不分的历史。颛顼统一了宗教信仰,统一了原始宗教活动,整顿了人神社会秩序,达到了政教权力的高度集中,强化了颛顼的地位,增强了部落之间联盟的凝聚力,有利于推进国家形成的大业。
三、颛顼进行原始宗教礼制变革的社会意义
原始信仰是原始社会人类共有的世界观,与神灵交往是每个人向往并皆可参与的事情。人事与神事不分,整个社会在神权上是相等的,而且是自由而无序的。巫教在上古社会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但自颛顼施行“绝地天通”变革之后,历史上的巫教便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的巫师阶层。在“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时期,社会上不可能存在专门从事原始宗教事业的巫师阶层,但并不代表没有原始宗教活动,氏族长可以执行各种巫术活动。自从“绝地天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天人分离”,巫师成为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重新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执掌巫教之权的专职巫师,神权被巫师阶层所垄断。鲁迅说:“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15] 巫师开始成为神明之象征。《国语·楚语下》云:“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女曰巫。”[7] 71从此,神权受部落首领及其助手巫师的支配,整个部落联盟处于一种正常稳定之状态。正如徐旭生言:“把宗教的事业变成了少数人的事业,这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16] 34
2.神权成为特权,且垄断于统治者少数人之手。这些少数人,通过对宗教活动的垄断,树立了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权。这从仰韶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墓中,墓主对礼乐器的垄断中可以看见。宗教权力的集中也会带来财富的集中,宗教权力的大小决定其占有财富的多少。张光直说:“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师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17] 这种财富集中的结果,就会造就一些所谓文明成就,并且推进文明的进程。巫教权力的垄断开始率先在社会中产生了等级观念,带来了社会分层,促进了国家诞生的步伐,因为“首领是通过宗教和超自然手段去更实际有效地‘诱取赞同’。在酋长制中进行思想操纵是获取百姓顺从的主要手段”,“所有早期史前政府的神权政治的发展方向都是统治阶级通过运用宗教的外表,以维持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特权并合法地使用强制性制裁手段”[18] 36。在神权至上的社会,谁握有神权,谁就统治着社会。于是,巫师的“法器”,就演化成象征统治权的礼器[16] 49。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能够统治人类社会的就是巫师阶层。“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人种学上已知的酋长社会和等级社会,首领总是宗教系统的核心人物,掌握着某种形式的宗教的或超自然的象征物。事实上,由于这些首领说成是神的直系后裔,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本身就是神的象征”[18] 53。
3.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开始分离,社会意识构成发生了变化。颛顼罢黜百家,使重、黎二氏司天司地,使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员成为劳心者,从事社会精神生产。颛顼“统一了巫教政令历法,宗伏羲,建寅,颁颛顼历”[19]。专职巫师的出现,亦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为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奠定了基础,使人们在精神世界划分出等级。巫师可以上天通神或请神下地,成为精神世界的领袖,统治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最初一批的精神领袖——巫师。从此,社会宗教意识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宗教意识受到约束与控制,不再能自由地传达神灵之旨意;群体的宗教意识已经形成,成为群体宗教活动的产物,并对群体的宗教生活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黎民百姓仍旧表现出低层次的宗教情感、祭祀风俗和自发的信仰倾向,却是一种不系统、不完整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社会宗教心理,而整个社会却呈现出一种系统化、抽象化的、具有相对稳定形式的、自觉的社会宗教意识,并对普遍的社会宗教心理起着控制和影响作用。氏族社会之末期,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工,以及社会意识构成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氏族社会解体的进程。
4.巫教管理开始呈现秩序化与规范化。颛顼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他所代表的阶段应当是阶级社会开始萌芽的仰韶文化晚期。在“绝地天通”之后,巫教人员已形成自己特有的组织体系,各巫分司其职,不得混乱,一直延续至帝尧时代。《尚书·尧典》记述了各巫职责情况:“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分命羲仲、羲叔、和叔负责各方天时。“原始的全民性的宗教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20] 宗教管理的秩序化与规范化能够与联盟政治得到很好的结合。这种统治方式,不但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青睐,而且一直沿用到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国家。夏朝是一个“巫政合一的时代”,“有夏服天命”[9] 59,“夏道遵命事鬼敬神”[21],从此巫教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每当后世之宗教出现无序化的时候,人们就会追忆起颛顼时代,并产生“颛顼死而复苏”之神话[8] 47。
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变革与部落的利益是相关联的。原始宗教变革帮助了以颛顼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反过来,政治力量亦促使了原始宗教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为即将到来的阶级社会的神权政治做了铺垫。因此,颛顼领导的这次原始宗教变革的作用和意义,决非仅局限于原始宗教本身,而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