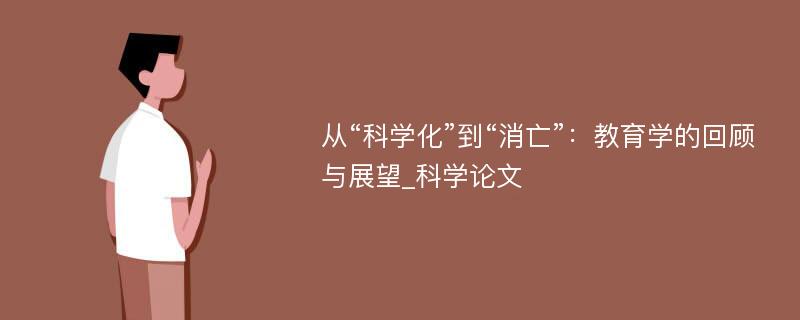
从“科学化”到“消亡”——对教育学的回顾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04)05-0009-04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从其产生到现在,如果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1632)算起,已有近370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学科演变过程,一直到现在的分化和整合,经历了一系列的质疑和彷徨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的教育学正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很多人都在质疑教育学的发展,教育学的未来充满了困惑,教育学受到很多人的猜疑。教育学有沦落为一门次等学科的危险,人们都在追问一个相同的问题,教育学到底怎么了?很多人用困惑、迷茫、失落、尴尬等一系列的字眼来描述当前的教育学,面对着这些问题,教育学又该作何解?
由于教育学的发展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其产生说起。
一、历史中的教育学(教育学向科学靠近)
从词源上看,教育学(pedag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pedagogue,意为教仆即照顾孩子的奴隶。单纯从词源上看,教育学作为一个名词在其产生之初就未被人们所关注,教育学在其出现时就先天不足,且带有极度的局限性。再从教育学这一理论的产生来看,夸美纽斯虽然完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1]但是严格来讲,夸美纽斯只是从经验出发,未将教育学放在大的基点上来考虑,而且当时大家的一致看法就是教育不过是一门职业训练的方法,夸美纽斯就直接说到他写作《大教学论》意在“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人的全部艺术”[2]。从一开始,教育学就仅被认为是一门艺术。
在此后的150年间,历史和教育学开了个玩笑,这门学科中间出现了相对的“真空时代”,教育学处于默默无闻的发展中,教育学在迷茫中找不到出路。“教育(学)是一门艺术”作为一种预设和先验理论固定在了人们的思维和历史的镜框中。从经验而来出于实际需要的教育学首先在理论上就面临着一大难题:如何发展,怎样发展?
1774年,德国柯尼斯堡大学率先开设了“教育学讲座”,由哲学教授轮流主讲,此后康德和赫尔巴特相继在此讲授“教育学”,教育学能在大学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极富历史意义的事,很多人都把这作为教育学开始学科化进程的标志。此时,人们受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教育问题变得关注和敏感起来,很多学者特别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这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已不仅仅满足于停留在夸美纽斯的阶段,仅仅将教育学看作是一门艺术,而试图尝试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化和向科学化方向靠拢,构建“科学的教育学”,试图由此指明教育学的发展方向,近代教育学面临着其诞生后的一次重大挑战。
为了解决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赫尔巴特这位公认的“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竭力主张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致力于教育学的科学化,来证明教育学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在赫尔巴特前的教育学充其量只能是哲学形态的教育学,它只是一种教育哲学,哲学在教育领域的分支。赫尔巴特试图让教育学成为有其自身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的学科,在他的一系列著作《普通教育学》(1806)、《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1831)、《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中,赫尔巴特以不同于夸美纽斯的方式来看待教育学,他试图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从伦理学出发构建一套自认为是科学的教育学体系。虽然赫尔巴特的尝试不是很成功(注:赫尔巴特试图建立一门有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独立的教育学,但他思想的步伐始终为哲学和心理学所带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独立的科学教育学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形态,教育学必须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因而哲学和心理学大厦的震荡会引起教育学的眩晕。吴钢:《教育学的终结》,载《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但是,不可否认赫尔巴特的尝试为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片生机。
教育学一方面向科学靠近,一方面这期间还有另一种相对的意见,即使是康德也认为教育学是一种艺术。新人文主义教育家沃尔夫也认为教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而只能是一门艺术。黑格尔也明确指出“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3],到福禄倍尔更是把教育研究分为“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理论”三个方面,试图回避这个问题。
19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和孔德实证主义的传播,人们更加相信能将教育学置于科学中,以科学化作为教育学的目标,用科学来阐述教育,寻找教育学存在的科学依据或者说教育学是科学的依据。斯宾塞开其先河,到孔佩雷、狄尔泰和拉伊,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加以提倡和论述,并试图寻得教育科学的独立性。虽然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等人表示出不同意见,认为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艺术,教育学只能依赖于科学,但是他们的观点被淹没在这种趋势下。此后,教育学主要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单轨而行,带上了浓重的科学色彩,教育学面临着其如何科学化的挑战,实验教育学和教育研究科学化思潮发展迅速。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敲醒了警钟,到了战后,科学的权威被打破,人们对机械的工具理性和冰冷的科学产生了疑虑:科学能解决一切吗?反映到教育上,60年代以来复兴的人文主义对教育学产生了大冲击,教育学是重归人文还是选择科学,亦或兼而有之?
二、批判视野下的教育学(目前的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20世纪中期开始,教育学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学科分化和综合化交叉整合时期,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相继诞生,到60、70年代,产生了复数的教育学(sciences of education)和单数的教育学(science of education)两大概念。到现在,教育学的分化整合仍在继续,教育学在经历了其产生、停滞、学科独立性、学科的性质及理论基础的长时争论后,形成了学科群,到了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伴随着元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反思文化的勃兴,人们带着对教育学的理性批判,从教育学的种种反思入手,站在元教育学的高度对教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现在的问题焦点是:教育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此时,人们对教育学的批判越来越突出。
“教育学过去是一门艺术——教学艺术,而现在却成为了一门科学。”[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里对教育学有这样的论述,也由于此,很多人也把它作为反驳一些人对教育学目前地位和性质的质疑的一个论据。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狭义上的“科学”单指自然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教育学算是其中的哪一类呢?而且人们对“科学”的涵义有不同的看法,一段哲学史,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就多种多样,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像历史主义者库恩(T.Kuhn)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费依阿本德(P.Feyerabend)的多元方法论、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K.Popper)对科学划界判据的分析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对“科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依据”就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可是目前却很少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注:我国,由于一开始就把科学的概念问题作为不证自明的问题,大家对科学的看法有着普遍的倾向,就认为是自然科学,能被经验所证明的。而在西方,却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即便如巴伯(Bernard Barber)、萨顿(George Sarton)等科学史的专家,也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说,连科学是什么还没搞清楚,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有什么意义?退一步来看,教育学自身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单从教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以下几点阻碍着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从历史上看,教育学的各种概念、命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致造成目前教育学的各个概念、命题模糊不清(注:德国著名的分析教育哲学家布列芩卡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桂生教授也在其所著的《“教育学视界”辨析》一书中,对教育学的概念的泛化和命题的模糊进行了一一分析。)。人们对目前教育学的一个认识就是教育学缺乏一整套概念、范畴、专门术语,教育学的命题也缺乏逻辑性。单就“教育学”这个概念来看,西方各国除了前苏联和德国外早已用education代替pedagogue,而且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名词即educology(意为教理学),类似的这些概念没有统一的规范,以至不同的学者对“教育学”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同样的在教育学的各个概念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再说教育学的命题形式,命题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要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有统一稳定而又可以转换的命题形式,而在现在的教育学中,运用的是规范性的命题,但是仅仅有规范性的命题是不够的,还需要转换成可操作性的命题来指导实践,许多学者由此对教育学提出一系列质疑:教育学的许多概念、命题有时只是对哲学的移植罢了,没有规范的教育学概念和命题体系,教育学谈何科学。
其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教育学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对象,而且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教育问题,因此要使教育学有科学的特征,教育学应采用的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模式,然而目前的教育学普遍采用的却是“提出理论,适应理论”的方法和模式,更多的情况是教育家们把自己的或者实证的或者思辨的道路上得出的理论不加应用就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付诸实施,一些理论没有经过检验就自称能对教育学的一切负责。同时,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学理论中对自身研究对象的划分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它迫切需要打破教育学自身的学科边界,重构教育学科体系。而且在各个子学科内部,还有个如何看待教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教育学还有一段的路要走,“学科边界日益森严,既造成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离,也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分离”。[5]
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学一直不能为自己正名,从一开始,教育学自身就潜伏了一个最大的危机,教育学不能完全割断自身和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教育学也不可能割断多少年以来留下的哲学思辨的烙印。这就使得教育学要想成为科学并以独立的形态出现,只能靠别的学科的发展来给予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养分。即使教育学努力做了一些尝试,可是不是被认为是方法上不科学,就是理论上受打击。教育学的解释域被人为地限制了,它只能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解释域留下的一点点范围内艰难地生存。它解释的是教育问题,然而它只能在其他学科的基础上解释教育问题,这时我们就会有疑问了,如果教育学的解释域已经被其他的学科所包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被分割了吗?这种教育学解释域消失的现象,连同上述的以及更多的教育学自身的种种问题,让教育学始终徘徊在科学的大门外,也由于教育学一直没被科学所接受,虽然我们自认为有教育科学、科学的教育学、教育学科学化等多个不同的说法和解释,仍然改变不了教育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次等学科的一个可怜的局面,对此,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曾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也鉴于此,一批人认为教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就有学者对教育学给予了相当悲观的批评和悲观的反思,认为教育学已经没有其存在的价值了。他们认为,当前许多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蚕食了原来大一统的教育学而变成了其他学科的亚类了。而有的人则认为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打算对教育学的科学与否进行讨论。面对这种种的问题和质疑,现在的教育学研究者在追求教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时候总是被如何为教育学找到被社会承认的方法而困扰。
简言之,目前的教育学问题涉及的是教育的事实判断和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教育的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问题。如果是科学,就只能涉及到事实判断和实然判断,如果不是,就可以涉及到价值判断和应然判断。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布列钦卡把教育学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实践教育学三个方面,在这一点上,她很聪明地把教育学的单一问题转化为教育学的多元化问题,把教育学的一个事实换作多个事实来讨论。这可能就是将来教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三、未来视野下的教育学(变革中的发展和重构)
正是由于目前教育学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教育学未来的发展显得格外的重要。从长远的眼光看,教育学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关于教育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只能由教育学来完成而不是心理学或者是其他学科,如哲学和社会学来完成。尽管教育学仍未完善仍有不足之处,但是不可否认教育学在教育领域是有自身独特的发言权的,虽然很多教育学子学科衍生成为其他学科的亚类,但是实际上教育学分化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统一的基础,也就是所有分化出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聚焦于教育问题的,而这与物理学与化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等等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以后自身依然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教育学还有很大的前途。
目前教育学遭受的质疑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教育学的完善和发展,但是它必须勇于接受挑战和批判,而且对这些挑战和批判其实也是它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支持。波普尔在论述科学理论时提出了“试错法”,即大胆猜想,严格反驳,他认为科学理论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其可证伪性,只有使科学理论面临最剧烈的生存竞争,这样才能选择那个最适应的科学理论。这个观点对教育学也同样适用,因为只有经得起批判和挑战的教育学才是我们需要的教育学。
展望未来,教育学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点:
首先,教育学应该向科学的方向前进,但是这种科学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自然科学。从目前对科学划分的争论和对科学的解释来看,由于科学的解释和划分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有的教育学理论的述茫。美国的文化学家怀特就认为人们对科学的本质是存在着混乱的,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各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的混乱。怀特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用以解释实在的方式,同时也指出了人们对科学的错误认识和一些学科是不是科学的狭隘判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更明确地指出了科学的动态涵义:“科学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6]而教育学就是要成为这样的科学,我们最终所要的是一种基于科学的动态意义上的,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量化的“中立”的、“客观”的教育学。就像布列钦卡分析的那样,教育学包括了教育的自然科学一面,但是教育的自然科学一面不等于教育学,教育学还包括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学,进一步说,其实就其本质来说,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但是它也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特征成分,它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涵。教育学的真就是教育学的科学价值的一面,它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教育学的善就是教育的哲学价值的一面,它也可以说是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价值介入,实证的、实验的方法所带来的教育学只是教育学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部。
其次,教育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学科基础,不应仅仅局限于心理学或其他的现在正被用于教育学的学科,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实验教育学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一个不能不断创新和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学科犹如一滩死水,是没有发展前途可言的。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脑科学、心理科学等的进一步发展,教育学可以加以更好地借用,就如同当初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现在新三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被引入到教育学一样,教育学可以也应该借用更多更好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己。
最后,教育学必须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包括自身的概念、命题、结构及其自身的学科体系。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方法论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争议的焦点是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自然科学中常见的“科学范式”。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缺乏“范式”是社会科学相对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社会科学本身就不存在类似自然科学的“范式”。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所谓“社会的科学”的硬科学,也不可能出现“牛顿”。但是这场争论的导火者科恩站在了少数人这边,他认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共同信念和公认的范例使科学共同体在采纳一般性假设时能达成某种默契,从而引导科学家取得成就。科恩的观点虽然受到了一些质疑,却很能发人深思,反思现在的教育学,如果还是用现有的模糊不清的那些概念和理论,那么它只会越来越乱。同时,目前教育学学术语言的混乱带来教育学理论的含糊不清,关于这一点,语言哲学家们就提出过发人深醒的观点:只有把语言区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两个方面,建立一套合适的学科语言体系,才能在根本上消除理论上的歧义和不确定性。现有的教育学在学术语言上借用了哲学和其他的日常语言,只会导致自身的混乱,它不能在方法上用自然科学实证的方式描述事实,却在描述上用哲学的经验的方式描述价值,两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学的发展。
总之,教育学的未来肯定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就是教育学只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希望台湾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世纪新梦》中所说的“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7]会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