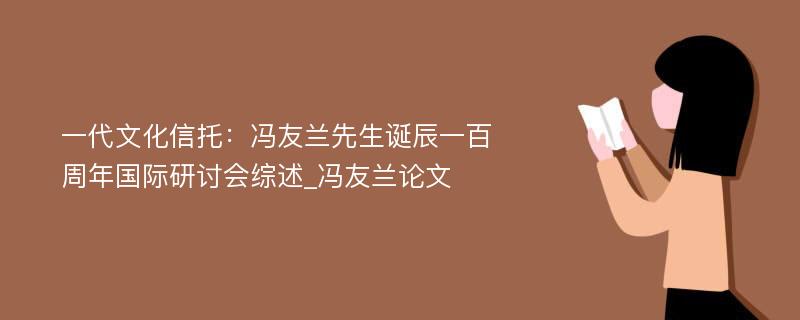
一代文化托命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命人论文,周年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筹委会联合发起,于1995年12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冯友兰学术研究会”,设立了“冯友兰学术基金”。约15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 会议高度评价了冯友兰在当代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造诣和地位,特别是对他在19世纪以来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所作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现将会议研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摘要纪述如下。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在大会发言时,任继愈、张岱年、张岂之等先生高度评介了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巨大贡献,认为他融合中西思想而创立的思想体系是重要的文化精神财富。
陈鹏通过对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思考及其在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的控讨,揭示了冯友兰关于哲学、哲学的发展、中西哲学、民族哲学、未来世界哲学的整体架构。并在此着重阐述了冯友兰的思想在该方面普遍的方法意义。(1)方法意识和方法建立。 这种方法体现在哲学探讨中,就是对哲学的对象、方法、内容、结论、目的等的自觉和反省。新理学是自觉彰现理性精神的。(2)哲学的理论意识或“学”的自觉。新理学始终以为哲学是一种“学”,是“思议”和“言说”的系统。这是我们言说哲学和发展哲学的首要前提。(3)哲学、 理性和理的“本体意识”即“自身意识”。新理学是从客观的“理”本身(认知对象)、完全的“理性”本身(认知方法与过程)、完全的“哲学”本身(认知结果)出发来思考哲学问题的。(4)世界哲学意识。 即新理学的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化。
范鹏认为,冯友兰哲学的构成有机地融铸了道家、儒家、佛学、西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现代哲学的一种形态。范认为这种哲学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在可信与可爱之间周旋,使其成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中介;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游泳,使其成为纯哲学意义上复古与西化的中介;在思古与忧今之间穿梭,使其成为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中介;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求生存,使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在旧邦与新命的天平上权衡损益,使其成为今天与明天的中介。
胡军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是“接著”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著”宋明哲学讲的。《新理学》中的形上学系统与宋明理学有着思想渊源的关系,又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它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而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传统;差异于“宋明道学,没有直接受过名家的洗礼,所以他们所讲底,不免著于形象”。因此《新理学》的哲学性质在于冯友兰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重新建立形上学。胡又认为,由于建构的方法和起点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哲学传统,所以《新理学》中的人生境界说也不同于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说了。
刘仲林认为,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接著讲”是采用了“正的方法”即形式逻辑分析方法,和“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刘认为正、负两种方法在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地位轻重和出现先后十分微妙。刘说,“正的方法”是构成新理学体系的基础,是主导方法,深得冯友兰的偏爱,始于构想之初,贯穿贞元六书;“负的方法”是补充性方法,是为提高新理学“极高明”程度而引入的,在《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冯友兰才认识到此方法的重要性,直到最后一部书《新知言》时冯才予以正式讨论。
田文军认为,冯友兰与梁漱溟一类人物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生命的理解不同,而导致他们文化意识的差异。田认为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冯友兰与梁漱溟一类人物理解考察的文化范围不同。冯友兰是从广义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化问题的,梁漱溟一类人物则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精神生命的安顿,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上来考察中国文化的。田又说,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致使冯友兰与梁漱溟一类人物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状况的认识也不相同。另外,田还认为,冯友兰所说的“正的方法”是西方的逻辑方法,“负的方法”则主要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方法。
二、对冯友兰及其治学精神的评价
任继愈先生认为,冯友兰学术活动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是怀着屈辱走进的20世纪。冯友兰的哲学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它是一部学术著作,却又不是纯学术的著作。冯友兰从事哲学研究,不论治哲学史还是从事哲学理论构建,都与祖国的文化建设、民族振兴相联系,他不是寻章摘句地论述前代思想,而在于为民族、国家建立新文化准备条件。任先生主张,冯友兰的学术观点,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见仁见智,不必强求共同的认识,但是冯先生的爱国主义是明白清楚的,是值得钦重的。
张岱年先生认为,冯友兰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他是跟着时代走,但不是跟着潮流走的。二是他始终努力追求真理,不怕别人的诋毁。
朱伯崑认为,冯友兰作为一代大师,开创了以近代治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方向,并且将中国哲学传播到西方,对20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冯友兰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五年了,他为我们留下五百余万言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任剑海认为,冯友兰后半生的种种失误,与他的理论建构及其蕴含的人生自我期许有密切关联。任以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建构有相当明显的虚悬性,这内在地决定了他在人生境遇顺或不顺的情形下,无法从自己的学说中寻求可靠的精神支持和合理的行为指南。任还认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建构有强烈的社会应急性。尽管他的人生言说非常抽象化体系化,似远离现实社会人生实践;但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希图借天地境界的言说鼓舞中国人士气,以改变政治颓局的学术期求。从而导致他以社会政治需要调整自己的人生哲学理论与人生策略的危险。
台湾学者朱高正认为,冯友兰是杰出的哲学史家,又是具有洞察力、客观评价力、综合判断力的哲学家。朱提倡,我们自己的好的东西要多多发扬光大,只有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到认识它、反省它、批判它、超越它、创新它,才有重建文化的主体意识,才有现代化。
三、关于“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冯友兰现象问题
蔡仲德认为,冯友兰一生有三个时期,即从本世纪20年代至48年为冯友兰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想影响的时期;从49年至76年为全面否定自己以前思想并同时为自己辩护的时期;从77年至90年为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己思想作重新反思的时期。这三个时期也叫“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时期。蔡将冯友兰一生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历程叫“冯友兰现象”。
方克立认为,我们要用历史进步的眼光去看待复杂的冯友兰现象。他认为可以把冯友兰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里再分两个小阶段。方还认为,冯友兰晚年的回归只是部分的回归,而不是全面回归《新理学》和儒学。
牟钟鉴认为,“冯友兰现象”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就其普遍性而言,它可以与“金岳霖现象”、“贺麟现象”、“汤用彤现象”等联系起来考察,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其特殊性而言,只是冯先生一个人独有的现象,很难找到类同者。牟认为,“冯友兰现象”的独特性有五点:(1)冯先生在国共两党决战而胜负尚不分明的关头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从此不再离开。(2)从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前, 冯先生长期遭受海外和大陆两个方面同时的批判和攻击,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相当可观。(3)在文革时期一度丧失自我后, 冯先生带着病弱高龄的身体,能够及时爬起来,向世人作出诚挚的自我反省,使自己的思想跃入一个新的境界。(4)老当益壮,在八十岁以后, 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写作高峰,新的思路逐渐清晰,创作的个性逐渐增强,于是在理论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一个光彩的“冯友兰晚年”,弥补了他后半生的许多遗憾和缺陷。(5)冯学正在成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 受到普遍关注。
在对冯友兰思想变化与发展问题上,与会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台湾学者唐亦男认为,冯友兰指出客观的辩证法有两个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讲,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冯友兰引用了张载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认为这四句中的前三句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该怎样说呢?冯先生说他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然他的推测,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因为“仇必和而解”是讲和谐的,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唐肯定冯友兰以上的见解,认为这是冯先生的超越所在,从而也完成了他的辩证发展阶段。
方克立认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对立统一,看成是“仇必仇到底”、只讲斗争不讲同一,把“仇必和而解”看成是客观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将来,这种看法错误的。方对冯友兰在晚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感到十分的遗憾。
钱逊认为,冯友兰肯定了“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和”是宇宙发展的正常状态;对于“同归于尽”,打破原有的统一体,只说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当然要主张”这样做,没有从客观辩证的角度给以明确的评价。如果我们承认“裂而解”,同归于尽的情形在客观辩证法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认识“裂而解”与“和而解”的关系及它们的条件性,这才是有待于我们接着讲下去的问题。
还有的学者认为,冯友兰“贞元六书”的开头是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新编”的尾语仍旧是这四句话,这是冯先生的不变;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个过程,而冯先生的思想随之变化而变化,这是冯先生的变。
与会的学者们还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关于冯友兰哲学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关于以理性主义的态度作为研究冯友兰思想的新起点问题;关于在冯友兰现象中应该怎样吸取文化方面和哲学方面的教训问题;关于境界和存在、天和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关于文化交流、转型和回归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研究。
(《哲学动态》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