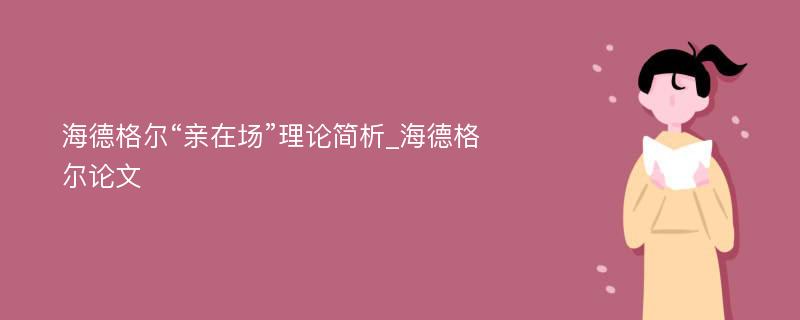
浅释海德格尔关于“亲在”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理论论文,浅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0)01-0073-05
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曾说过这样的话:“凡是真正的哲学家,一生所讨论的,只是一件事。”(注:柏格森:《心力》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页。 )德国存主义者海德格尔一生所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就是:存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引导海德格尔走向这条道路却是一件很偶然的事。1907年,18岁的中学生海德格尔从当地牧师格吕伯那里借到一本哲学著作,题目为《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重含义》,这是19世纪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坦诺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探讨的存在问题一下子吸引住了海德格尔,从此,海德格尔终其毕生精力寻求存在的意义,开始了他近70年的哲学生涯。
存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早在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就提出了关于存在和非存在的学说,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存在的多重含义,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逻辑学就是从“存在论”开始的,恩格斯也把整个西方哲学史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都在谈论存在,但他们所谓的存在只不过是“存在物”或“存在者”,都是浮在事物的表面上,而没有看到存在的真正本性,没有追问存在的意义。所以,他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是“无根”的哲学。只有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里,追问存在意义的问题才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发展。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和“存在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两个概念。所谓“存在者”,指已经以某种状态显现出自身的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物”。所谓“存在”,中文有时译为“是”、“有”,指优先于存在者并且决定存在者的某种更根本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既不是指构成某一具体存在者的全部外在属性的总和,也不是指这一存在者的某种抽象本质,而是指使一切存在者得以可能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是指某一存在者之所以成为此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而且他强调,这种存在方式不是指某种现实的存在方式,而是指某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存在就是指存在者的可能的、动态的活动方式,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存在起来”这个事实,哲学就是要去研究“比现实性更高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的存在“先于”存在者的意义所在。当然,海德格尔也意识到,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中,存在往往是以某种存在者的面目出现的,离开了具体的存在者,所谓的存在就是不可捉摸的,询问存在的意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追寻存在的意义又必须以存在者作为起点。
“我们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呢?我们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出发点是随意的吗?”(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才是破解存在的意义的出发点。因为一般的存在者对其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并没有什么关注和察觉,它们仅仅是“存在着”,不会追问存在的意义。只有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才能成为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提出者和揭示者。用海德格尔喜欢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就是:“人是谁?人是必须为其所是提供见证者。”就是说人必须为自己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作出解释。海德格尔称人这种独特的存在者为“亲在”(Dasein),即“亲临存在”的意思,又译作“此在”、“纯在”。
海德格尔认为,亲在的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就是日常所见的在世界中同各式各样的存在者打交道,他把亲在的这种状态称为“在—世界—之中”,这是他自己生造出来的一个德语复合词。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的“客观自然界”,而是指亲在生活在其中、不断与之打交道的开放的“原始世界”。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之中”,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空间意义上的“在之内”,像水在杯子里、衣服在衣柜里那样,而是指亲在和他的“世界”处于一种浑然天成、融为一体的情形。那么,亲在“在世界之中”(简称“在世”)的情形究竟如何呢?
一、亲在在世的整体结构——操持、操劳、操心
1.操持
亲在的存在方式就是在世界之中,但它最经常的表现方式不是那种静观、沉思认识,而是操持,亲在忙忙碌碌地、不断地同周围世界里的“物”打交道,海德格尔给这种“物”起了个专有名称——“器具”,例如书写用具、缝纫用具、交通用具等等,他把亲在同“器具”得以照面、打交道的方式称为“操持”。
器具的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的使用上手性。例如,一把锤子之所以成为锤子,不是因为我们把它摆在那里加以静观,并作出“理论分析”的结果,恰恰是因为我们用它来“锤击”。锤击揭示了锤子的上手状态,同时也就揭示了锤子的存在。我们使用器具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对它的性能和用途有了一定的了解,即有着对器具特性的“知”,并且还以恰当的方式“占有”着这一器具,在器具使用过程中的“知”和“占有”就清楚表明,操持不同于那种对某物的静观认识。
此外,器具还有“适用性”和“承用性”这两种属性。所谓器具的适用性,就是指器具总是用来做什么的,有其“何所用”。例如,锤子是用来锤击东西的,制作的鞋是用来穿的,装配着的钟表是用来指认时间的,等等,所以,海德格尔说,器具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所谓承用性,是指在对器具的操持使用过程中,这一器具为谁所承用、所制造,也就是说,“他人随同在工作中适用的器具一道‘共同照面’了,……例如,我们‘在外面’沿着走的这块地显现为属于某某人的,这本读着的书是在某某人那里买来的,是由某某人赠送的,靠岸停泊的小船在它的自在中就指向一个已知的用它来代步的人。”(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8页。)
2.操劳
从器具的承用性可以看出,亲在不仅要同形形色色的存在物打交道,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人打交道。亲在既不是在世界之外的单纯主体,也不是同他人无关的绝缘之我。亲在操持使用着器具的同时就指向了他人,同他人发生着关联,每一个亲在本身相对于他人来说又都是他人,所以,亲在在世是和他人共同在世、共同存在。海德格尔把亲在同他人的这种联系称为“共在”,意为“共同在世”,把亲在同他人照面、打交道的方式称为“操劳”。像互相关心、互相反对、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等等,都是操劳的可能方式。
3.操心
海德格尔认为,器具的使用上手性、适用性和承用性一起,构成了器具存在的整体性,而器具的整体化过程最终又归结到“何所用”即器具的意义的问题上。器具的“何所用”即意义是由亲在在其展开、活动过程中揭示出来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亲在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人交往、关联。正是在对器具“赋予意义”的过程中,亲在对自己的生存在世有所领会。总之,亲在在世,既要操持着与器具打交道,又要操劳着与他人打交道,无论是操持,还是操劳,都是操心。操心展示着亲在现实存在的全部本质,正是在这种操心过程中,亲在才得以展开自己本身。(注:参见《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二、亲在在世的生存过程——处身、领会、沉沦
1.处身
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可以不问亲在从何而来,也不管他往何处去,但只要亲在存在着,他就总是“已经在……”,即总是已经处身于世,在世界之中,而且“不得不存在”。我们猛地发现自己就在这里,没有人请我们来,也没有人“准”我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海德格尔又把亲在的这种处身状态称为“被抛状态”。美国存在主义代表巴雷特曾经解释说:“我们没有挑选过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注:(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3页。)
2.领会
海德格尔指出,亲在的这种被抛的“实际状态”,不同于某个既成事实的“事实状态”,不是一种完成了的、封闭着的状态,而是一个向外开放和超越的可能性状态。这种开放和超越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情绪状态,是在情绪中的处身于世,所以,只有情绪才能把亲在作为整体加以展开,才能洞悉亲在的庐山真面目。把握情绪的方法就是“领会”。海德格尔认为,领会不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概念,抽象的理性和一般的、静止的概念是无法把握情绪的。领会就是展开的意思,就是指亲在去行动本身。亲在对自身的真正领会,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现有的存在,不断筹划未来,向着种种可能性去发展,“超越性”是亲在之为亲在的本性,只有这样,亲在才能不断更新自己、丰富自己,“获得自己本身”,才能够对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6页。)海德格尔指出, 亲在的“行动”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存在者的“反应”,就在于其中包含着对存在自身的领会。
3.沉沦
海德格尔指出,尽管亲在的本性就是不断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情形却是,亲在往往既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种“被抛”的处身于世的状态,也不能领会自身、筹划未来。亲在或者沉溺于操持所及的器具即周围世界,或者仅仅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来筹划、领会自身,亲在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取决于“他人”的喜怒哀乐,这时亲在已经变成“众人”(das Man,又译为“世人”、“常人”)。亲在淹没在众人之中, 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人的个性丧失了,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处于“平均状态”之中。“众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众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判断;竟至众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就是这个众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平均状态是众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6页。 )这个众人还“独裁”地从每一个亲在那里拿去了责任,因为,这个众人不需要为自己担保和负责,所以也就很容易地为亲在负起一切责任。这样,当亲在变成众人时,就丧失了责任感,也摒弃了超越性,不再作任何选择和行动,也就更无所谓自由。在海德格尔看来,亲在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就是“失去自己本身”,沦入“非本真状态”,就是亲在的“沉沦”。从上述可知,海德格尔的“众人”就是克尔凯戈尔所极力贬低的“公众”。
海德格尔还把亲在的生存和时间性联系起来。时间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代表作起名为《存在与时间》就表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亲在的根本结构和性质只有在时间性中才能得到解释和澄明,他本人力图通过时间来揭示亲在的超越性。在他看来,说亲在在世界之中,也就是在时间中。将在、现在、曾在,这一时间性的整体和亲在在世的过程相对应。领会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将在”,处身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曾在”,沉沦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现在”。传统的做法以“现在”作为全部时间观念的核心,在这种非本真的时间中,亲在不具有“前行”的性质,这种现成化的“现在”就是亲在向着操持所及的器具、操劳所及的他人沉沦的原因。海德格尔则以“将在”作为全部时间观念的核心。在这种本真的时间中,亲在具有“前行”的性质,这种“将在”一方面构成了亲在不断展开自身、筹划未来的基础,即构成了亲在不断超越自身的根据;另一方面又为亲在在“被抛”情形下不断领会自身提供了可能性和广阔的背景,从前行的“将在”出发,才能把亲在从沉沦中拉回,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正像巴雷特所说的:“在海德格尔的笔下,未来是压倒一切的时态,因为他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可塑的并在不断运动的动物。”(注:(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4页。)
三、亲在在世的本真情态——烦、畏、死
海德格尔认为,研究存在,就是要“显现”人的情态,而人的最“本真的情态”,最能反映人的自我意识的情感,就是烦、畏、死。
1.烦
亦译为“担忧”,其基本含义是担心、焦虑的意思,也含有“渴望”的意思。烦有两种,一是“烦心”,指人和物打交道时的情感,例如,人为衣食而烦心。二是麻烦,指人和他人打交道时的情感。海德格尔的“烦”实际上就是“操心”的同义词。在他看来,在世界之中使烦忙成为可能,烦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状态。
2.畏
海德格尔认为,当亲在沉沦于众人,误把众人本身当作自己,自以为过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时,畏突然扑面而来,畏和惧不同。惧所惧怕的东西总是一个在世界之内的,从一定的境界来的。也就是说,惧是惧怕具体的人和物。而畏没有明确的对象,畏不知其所畏者为何,它是对整个世界的畏惧,是对存在自身的畏惧。畏这种根本的情绪体验,能使人真正领会亲在的“被抛”状态,这种被抛状态就意味着亲在将被嵌入“无”的境界,因为,所谓亲在的超越性,不过是从“有”向“无”的超越,一切都将归隐到虚无之中,包括生命的得而复失。总之,畏启示着“无”。有人可能自慰说,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宇宙毕竟还存在着,但虚无和不存在所说的,不是物质的消失,对亲在来说,恰恰是不再有一颗心灵感受着存在。面对这种虚无,亲在感到惶惶然失其所在,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不在家状态”。面对虚无,懦弱的人胆怯而逃避,但不是像“惧怕”那样,逃离开具体的人和物,而恰恰是躲避到我们熟悉的、在操持中的存在物中,逃避到“众人”或“常人”中去,浑浑噩噩,从而获得他的“家”。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任凭亲在如何逃避,只要他还在世,就总要面对虚无,惶惶然失其所在的无名恐惧感将永远追随着他,并始终咄咄逼人。(注:参见《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3.死
海德格尔认为,畏到头来实际上是畏死,亲在无论如何逃避,他上天入地,但终归逃不脱人生之大限——死。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可能性。死不是一种现存的、放在那里的事实,死亡是即将来临又尚未来临,是亲在生存的一种可能性本身,并且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其特殊之处就在于,死作为去世,是亲在在世生存的不可能之可能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方面,亲在在世生存,就表明死还没有实际发生,另一方面,亲在随时都有不存在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以取消亲在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死(去世)作为可能性,不给亲在任何可以‘实现的东西’”(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死是最极端的可能性。 二是唯一性。死总是自己的死,谁也不能代替谁,“‘死’要求亲在作为个别的存在”,“死亡是最本己的、无关联性的可能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4页。)。 三是既确知又不确知。这种性质告诉我们:“死随时随刻都是可能的,何时死的不确定性与死的确定可知是同行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58页。)也就是说,亲在确知自己要死的, 死是亲在不可超越的,死随时都可能来临,但何时来临呢?不得而知。
在海德格尔那里,烦、畏、死虽然是三位一体的,但最根本的就是死。人们一方面处处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方面又时时领会自身的即将趋于无,这种强烈对比使人震惊,而震惊之情是哲学的开端。巴雷特指出:“海德格尔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却似乎在暗示:哲学或许无非就是对死亡问题作出的回应。”(注:(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5页。)死是亲在最本真的情绪体验,死时方知万事空,方知人生在世,一无所有。死就像晨钟暮鼓,能把消溶在众人中、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的亲在从这种“异化”状态中唤醒。人最大的畏就是畏死,只有强者、大智大勇者才能正视死亡,果断地承担起到死中去的可能性,才能在嵌入“无”的境界的瞬间,一睹存在之真容,洞明在世之真谛。向死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畏转而成为大无畏,这是人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关于亲在的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了宿命论。尽管人无法改变被抛在世界之中不得不和物、人打交道的事实,人也不可能逃避从有趋于无的命运,但人生活在各种可能性中,生活在时间的“将在”本性中,所以人的在世生存不是命定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筹划、超越的一生。这和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是一致的。
2.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异化。海德格尔的操持、沉沦、操劳等概念,抨击了人们生活在“物欲”的世界中,人们拼命地把手伸向天空,一味地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使人与自然的原初同一被彻底破坏了。面对虚无和死亡,人则表现出懦弱胆怯,沉溺于众人中,为他人所左右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责任。这和尼采对“末人”的批判,对超人独特个性的推崇,以及克尔凯戈尔贬低公众,强调“孤独个体”,其实质是一样的。
3.透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的情绪,在政治上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海德格尔对烦、畏、死的解释,从理论上讲,是对克尔凯戈尔的“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的进一步发挥;从政治上讲,是为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服务的,鼓吹人要为希特勒政权卖命。正因为如此,希特勒执政期间,他禁止士兵读其他著作,却允许读海德格尔的东西,从许多阵亡的德国士兵身上,常常可以找到海德格尔的头像和著作。
收稿日期:1999—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