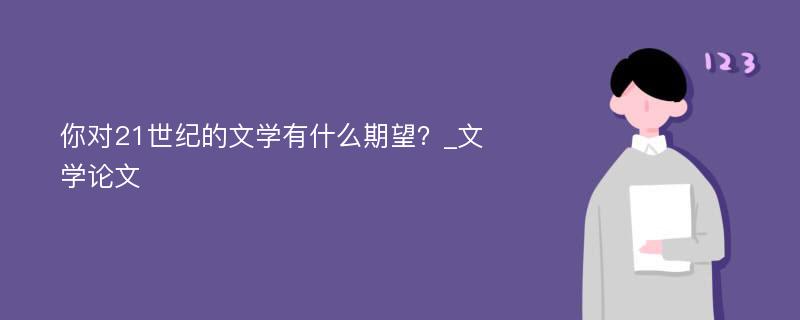
向二十一世纪文学期望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论文,世纪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铁舞:最近重读你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的《潜流与漩涡》一书,觉得你的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很有现实性,但这个问题被很多人漠视,甚至有人不敢提这个问题,觉得提了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便干脆把这个问题置之一边,使得带着障碍进行创作成为一种习惯。诚如你说的:“以遮掩的方式曲曲折折地抒发真情,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特性。”现在想来,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不满足(不仅仅是小说,也包括诗歌和评论),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我们期待的大作家没有出现。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前面就是二十一世纪。我想,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假如有大作家出现,那么出现大作家的条件首先就是作家能破除创作上的心理障碍。
王晓明:我讲的心理障碍,从那本书里讲,有许多类型,但相当一部分有共通性:作家感觉到心中有某一种冲动,甚至很强烈,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反而将它抑制或者减弱,甚至干脆把它推到内心深处,我想你主要指这一点吧。如果出不了文学大家,从作家个人一面看,这大概确是主要原因。我始终有这样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不比其它国家差,而且所遭遇的外部生活的刺激也非常强烈,甚至比其它地方更强烈一些,但就是由于这种自我压抑,作家没能够彻底放开来想,放开来写,所以始终出不了大作品。问题是,为什么作家要压制自己的内心冲动?一个原因自然是处境太严酷,鲁迅在二十年代说过一句话: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从更内在的方面讲,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作家好像是缺少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这个“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世俗处境,他对自己的处境看得太重,太看重社会对他的评价,包括太看重作品的出版,希望自己现在就得到某种承认。社会的承认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价值,比这更重要的关怀。前一阶段我们讨论人文精神,也就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普通人也好,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活在世界上,应该是能感觉到,有比实际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问题值得他关心的,这也就是你说的灵魂问题。其实伟大的艺术都是对灵魂的关注,是对这种关注所激发的激情的体会,如果一个作家对这些东西有强烈的感受,能陷进去,不顾一切地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如果不写出来,他的灵魂不得安宁),那就好了,我想,睥睨一切的气势和境界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不能选择时代,这是由我们出生的时间、地点决定的;而我们比较有能力做的事,就是培养一种承担这个时代的重负的能力,然后在这个承担的前提下努力做一个可以称做人的人,对作家来说,就是做一个可以称做作家的作家,在原苏联,会出现帕斯特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作家。帕斯特尔纳克也有他的现实处境要关心,他是否考虑到社会的挤压呢?也考虑,政府说:你如果去领诺贝尔奖金,就不要回来了。他就拒绝领奖。但在写作时,他却不考虑这一切,他不会把自己内心真切感受到的许多的东西删除掉,他一定要完整地写出他的灵魂。比较起来,许多中国作家就是缺少这个东西——一种不写出来就感到不安,一旦写起来忘乎一切的激情。我把这种激情的缺乏归之于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缺乏,而不仅仅是缺乏勇气,更不仅仅是缺乏才能。
铁舞:你在《潜流和漩涡》中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文学应该是超功利的精神天国,因此,你不时地表露出对自己未能潜心于艺术分析,不由自主地要跨进心理和思想研究的领地,即使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也还是常常要东张西望的遗憾。我相信这不是谦词。你做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拯救一种被遮蔽了的文学精神。我所说的文学精神是文学自身的东西,一种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光芒。中国是体现“功用诗学”的古国,所以我对你批评知识分子一开口就是“人生”、“现实”和“意识形态”,感到很理解。古老的“功用诗学”对纯粹诗学的精神阻碍性,从《诗经》就开始了。这种“功用诗学”在现在的文坛上依然如火如炽,表现得非常强烈具体,而且戴着种种标签,也许我们无法阻止这种现象,但问题是,要产生大作家,就必须超越“功用诗学”,走进精神的光芒里去。文学发展至今,对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作家都提出了对生存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任何功用都不能和它相比的,我认为,惟有这种关怀才是至高无上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不能阻挡许许多多功用性文学的存在,但我们更应该呼唤肩负终极关怀使命的大作家出现,那是真正的文学,世界意义的文学?
王晓明:最近,我和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交换过一个感想,我对他们说:我们是文学专业的师生,可是我们上课讨论的内容大部分却是在文学之外的,是应该在历史系、哲学系里讨论的内容,例如思想史啊,文化史啊,而文学专业应该讲的东西反而很少,这不大对头。再想到我自己,以我个人的性情来讲,最愿意写的,写得也可能最顺手的,其实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性、分析性的文章,可实际上呢,我写下来的大多数文字都还是属于思想史的研究,是对知识分子、作家精神状态的分析,从这一个意义上讲,我活得很被动。现实生活的刺激,那样有力地转移我们的兴趣,逼着我们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去做我们其实并不非常适应却又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不能自主,一个人的生活的被动性,没有比这更深刻的了。推而广之,你所说的“功用诗学”在中国那样源远流长,一直到二十世纪,文人一开口还是人生呀,现实呀,意识形态呀,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被动性在更大范围上的表现。这就使问题复杂了:一方面,作家介入社会现实,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责任感,是可以理解的事,尤其在特定的时刻,这种姿态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有很难得的道义感;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大范围来讲,文学还应该表现出它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的那些价值。照我的理解,至少在现代社会,文学艺术已经成为人保持自己的精神丰富性,甚至发展这种丰富性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也好,道德也好,更不要说实际的物质经济生活,都在使人平面化,甚至那些以逻辑方式展开的学术活动,也会加剧这种把人挤压成单向度的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的趋势。个人在这种巨大的挤压面前,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都是被动的,而只有艺术创造和艺术体会能另外给我们开辟一个世界,给我们网开一面,我理解你说的,唯有这种使命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功用不能跟它相比。所谓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里,也就是力图保持人的存在的丰富可能性,而文学的精神深度,也就表现在这个上面了,包括你说的世界意义的文学,“世界”这两个字就体现在这上面。一个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生存的主动性,能不能不受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状况的限制,比较自由地扩展自己的精神领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所谓大作家,就是指能够保持这种精神主动性,不被特定的现实完全压扁。说到终极关怀,每一个人都会向自己提供某种对生命意义的解释,譬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人,以为人的价值就是过一个富日子。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可、接受这个解释,根据它去决定自己该怎么做。但我们讲的终极关怀,就是不甘心这样,不满足这样,要在根据物质利益作出的种种选择之外,追求对生命意义的更有深度、更内在、更为根本的答案。这种答案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因此,这种关怀,经常体现为迷惘、焦灼的痛苦,但也往往以此体现了人的精神主动性——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源泉。
铁舞:你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第一个谈到的是鲁迅,你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恐怕鲁迅是第一个敏感到障碍又不能冲破障碍的人。你对鲁迅两种创作动机的尖锐对立的分析是非常精辟的,过去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分析过。你对鲁迅以自己的灵魂作原型的创作评价很高,把《孤独者》看作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甚至觉得它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要比《阿Q正传》更为重大。我的理解是,《阿Q正传》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热点,而从《孤独者》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社会热点,而是一个真实的灵魂,——这比《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泛指”更深地切入了人的生存境遇。自然,今天我们对鲁迅并不满足。鲁迅这位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人,偏偏停止了小说创作,中国新文学的唯一一条有可能通向世界文学高峰的道路,也因此而中断了——你的这一判断令人警惊。我们对鲁迅都崇拜惯了,经你一提,我们对过去习惯的那个“鲁迅”发生了怀疑,从而也更接近真实的鲁迅了。我想起有人曾呼唤今天的鲁迅,那多半是呼唤鲁迅的社会批判光芒,而不是伟大小说家的鲁迅——但即使这样,鲁迅之后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为什么再找不到第二个鲁迅呢?在小说里见不到灵魂已成为普遍现象,我们期望于二十一世纪文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王晓明:你说小说里见不到灵魂,这话说得真精彩。我对当代中国小说的最大不满,也就是看不到灵魂,看不到灵魂的痛苦。在今天的生活中,我想稍微敏感一点的人,稍微愿意想一想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出了问题,我们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和身上沾着很多泥水,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意,诸如此类的怀疑和痛苦非常实在地摆在我们面前。作家是比一般人更为敏感的人,悟性更高,对这方面的体验也应该是更深切的,可奇怪的是,在今天的大多数小说当中,我们就看不到上述这一切,这的确是使人大惑不解的事情。鲁迅有一句话,叫做直面人生,可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真正直面人生、直面自己的心灵,竟是那样困难。我最近给鲁迅写一本传,题目就叫“无法直面人生”,对人生的难以直面,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够自弃,要去尽可能培养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精神。你问我,对二十一世纪文学的期望应该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说: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小说里面能够看见灵魂,能够读到灵魂的颤动。当前中国文学界有一批很聪明的人,看透了这个时代,也很敏感,知道自己的灵魂出了问题,但他们认为一切都不可改变了,所以干脆把自己的灵魂团起来塞在一个再也不会去翻的角落里,然后他们说一些很聪明的似是而非的话,用一些表演性的,也确实能够吸引人的言行来掩饰自己的世故和功利心,这样一些人的热热闹闹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化界最令人心冷的现象,它清楚地表明,生活已经把人的热情和精神追求窒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过,希望能从以后的小说中看到灵魂,在这方面我倒不完全是悲观的。一个社会有没有好的文学状况,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一批好作家,甚至也不要很多,有几个真正好的作家,就可以撑起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厦了。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我觉得能够在自己笔下绘出灵魂的作家已经是有了一些的,比如说,史铁生、张炜、李锐,还有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从他们的作品中是能看到灵魂的一角的。当然,就灵魂呈现的深度来讲,这些作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似乎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就是能专注于自己的灵魂,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为外界的喧嚣所影响,在精神上比较成熟。这也许就是我敢于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要求灵魂的一个原因吧。
铁舞:既然说到破除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我觉得评论的心理障碍也还应该打破。最近我在看英国的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编的《现代主义》一书,想到我们中国当今文坛上也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地时髦着。在我看来,现代主义这只猫的爪子刚刚伸进中国,屁股还没坐下来,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观照中国的所谓“现代主义”,那都是时髦,我说的时髦是指这些东西不是从根部产生的,而只是枝上的装饰,并没有那种可以划出一个“现代主义”的时代的份量。我们可以借鉴别人,向各种源泉借鉴,但无法借鉴促使我们借鉴的历史和想象力,问题的关键是否也在这里呢?
王晓明:你所说的,是评论界和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的现实是很奇特的,一方面,中国正在被卷入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的过程,因为这一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对我们发生非常直接的影响,产生你所说的催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呢?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庞然大物,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它沿着自身历史的惯性轨道运动的力量也非常大,以至今天的中国作家在精神上仍然深深陷在自己历史和想象力的传统中。怎样来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和状况,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难题。我的想法是,正因为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影响,这种合力的结果,就使中国既不可能维持以前那种样子,也不可能变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化,认为中国会变得像西方那样,是一种幻觉。如果说中国也会进入现代化,那一定是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各种现代化都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再用现代化这样的词来描述它。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文化状况很可能会非常特别,和现代西方完全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会遭遇什么样的历史和想象力资源,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事情。在各种社会人物中,作家是受历史和想象力影响最大的人,因为他对灵魂的自我的追问,首先是在汉语的层面上展开的。用你的话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土壤,扎下什么样的根,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枝叶来,从借鉴的效果看,外来文化的催化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倘把外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根,我相信绝不会长出粗壮的枝叶的。马尔克斯尽可以用欧洲语言写作,尽可以接受欧洲文化的熏陶,但他能写出世界一流的小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拉丁美洲本土文化对他深层精神的影响。
从这个方面讲,80年代中国的文化寻根小说,虽然有种种问题,但从长远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它们毕竟提醒作家意识到了文化和文学之根的问题。相对于外来的思潮影响,中国文学的生命力毕竟更多是来自于自己文化的根。当然,如何理解中国的本土文化,讲起来很复杂,这里就不说了。但我十分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可以借鉴别人,向各种源泉借鉴,但无法借鉴促使我们借鉴的历史和想象力。
铁舞:在进行世纪回眸时,知识分子的整体价值问题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宿命般的联系,常常引人痛心疾首。我想这一个问题,在下一个世纪依然会碰到。现在的作家容易惧怕政治,其表现之一是希图通过与政治结盟,来避免被伤害,其二是不敢超越,采取回避的态度。应该声明,文学不是政治,政治不应干预文学,这都是对的。但我想提出来引大家注意的问题是:文学就其自身来说应该超越所有,政治是否也在超越范围?我想政治也应有诗意的和非诗意的区别,一个大作家应该具有诗意政治的理想,我想应该把这一点与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肯定联系起来。文学对当下被形而下充斥的生存面貌的描绘,也许能够以出示一种精神地狱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只是潜在的诗意政治现象作肯定的另一种方式。也许诗意政治在现实生活里永远是不存在的,但不能因为它在现实中不存在,就否认我们认定它的必要性,它存在于我们的心里。二十一世纪,我们期望着怎样的精神高度?
王晓明: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可以进一步澄清我们前面的讨论,当我们谈到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应该走出“功用诗学”时,并不是说作家和文学应该背对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你说文学应该超越所有,我觉得超越是有另一层含义的,就是在超越过程中同时包含了所有,这中间也包括道德,包括政治,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同时都包含深刻的道德性和政治性,包括对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美的憧憬,自然也就包含了对现实生活的强有力的批判,但是这种包含和前面所讲的“功用诗学”的最大区别,就是把这一切都融化在诗的状态里,是把这一切都凝聚成为对更好、更有价值的人性存在的一种追求,它容纳了这一切,而绝不是臣属于这一切,你所说的精神高度,是否就是指这一点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讲清,就是如何理解政治这个词。当我们说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奴婢的时候,这里的政治其实是指特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是指一套特定的政治观念,但是政治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指社会生活中具有政治性的一面,以及这样一个侧面对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广义的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一直影响到我们对存在意义的最深层次的思考,并且也是构成这种思考的一个重要依据。对这后一种更为宽泛的政治,文学其实是无法回避,也决不应该回避的。文学应该直面这种政治,只不过我们反复强调的是,这种直面和承担应该始终以文学的态度和方式去展开,而不是以披着文学外衣的政治方式去展开,如果是照后一种方式去展开,那文学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品格和精神的高度。我不大同意诗意政治的提法,你想说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一种能培养和促进理想的人性的社会形式。诗意是非政治的东西,是不可操作的,而政治是可操作的。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二十一世纪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王晓明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