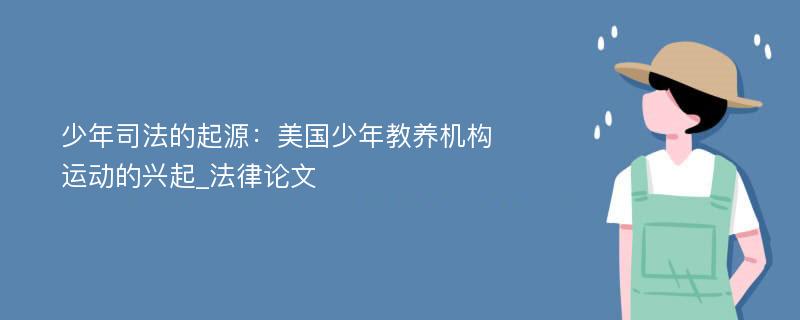
少年司法的起源:美国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年论文,美国论文,起源论文,司法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传统刑事司法变革之前的18世纪是一个特殊时期,它既是“惩罚犯人最野蛮的一个时期”,同时又被称为“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在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历史上最杰出的哲学家们认识到了人类的基本尊严的重要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性。”〔1〕 启蒙主义思想家针对封建刑事司法的种种弊端,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刑法与宗教分离、罪刑法定、客观主义、罪刑相称、目的刑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主张。尽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但是他们都反对苛酷的刑罚,反对肉刑、拷问和株连,强调用刑应当慎重宽和,即都主张“刑罚内容的人道化和宽大化”。〔2〕 在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古典犯罪学派高举理性的大旗,主张自由意志论、刑罚宽和,反对死刑和酷刑,对欧洲及北美的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通过肉刑和死刑来体现报应主义思想的刑事司法日益与尊重人类基本尊严的刑事司法新思潮相冲突,传统刑事司法面临着控制手段合理化的挑战。在启蒙思想家和古典犯罪学派的推动下,欧洲和北美各国兴起对刑事司法进行的改革,开始从野蛮向文明转变。“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到1830-1840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惩罚的对象发生了变化。”〔3〕
社会转型进程中所凸显的犯罪与少年罪错现象,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安全,而原有的以肉刑和死刑为最终控制手段的刑事司法机制瓦解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惩罚来约束邪恶者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运用劝善的戒律使其顿悟”,〔4〕 矫正比单纯地惩罚犯罪更为明智,通过监禁控制犯罪人的危险性,并在此过程中实施矫正,既是人道的,又是安全而且明智的。于是,肉刑、死刑逐渐被监禁刑所取代,矫正制度由此逐步诞生。大约在1750年到1820年间,欧美国家刑罚的风格逐步发生了变化:刑罚的客体从人的躯体转向人的灵魂或精神,刑罚的目的从对犯罪行为的报复转向了对罪犯的改造,刑罚技术从绞刑架转向了监狱。〔5〕
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和美国的监狱起源于教会对异教徒的控制。创建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宗教法庭,始设用以关押犯人的与世隔绝的监狱,并逐渐将长期监禁作为处罚手段代替死刑的刑罚来使用。〔6〕 监狱的另一个重要的渊源是16世纪欧洲一些国家所设立的矫正院。这些矫正院是用以关押有劳动能力但却好吃懒做的人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使他们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地生活。乞丐、流浪者、妓女、罪犯及恣意妄为的青少年都被送到这些机构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是1595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矫正院,这个矫正院以教育收容者成为社会上勤劳和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为目的。阿姆斯特丹矫正院名声很大,为各国所效仿,因此也被视为现代矫正制度的滥觞。〔7〕 早期的矫正机构接收的人员十分广泛,包括贫穷、体弱、生活无着和严重犯罪的人。其中有的年轻人是被父母送进去的,他们认为通过送进专门机构可以让孩子学会顺从。但是,年轻人是否从这类机构中受益存在着争论,不过无可争议的是,这些矫正机构的创立者希望这些孩子可以成为为地方产业服务的廉价劳动力。〔8〕 随着肉刑的逐渐废除,自由刑日益兴盛起来,到19世纪时它已经演变成为对犯罪者的主要控制方式。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传统刑事司法基本上是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刑事司法的承续。曾经“风靡各个殖民地的野蛮的惩罚手段,都来源于16、17世纪欧洲惩罚罪犯的方法”。〔9〕 在独立战争后革故鼎新的社会背景下,以及启蒙思想家和古典犯罪学派刑罚宽和思想的影响下,18世纪末期的美国也开始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努力用自由刑取代肉刑,并贯彻矫正主义思想,建立了监狱矫正制度。1790年,在教友派信徒(Quaker)的推动下,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矫正机构——胡桃木街监狱在费城建立,〔10〕 随后其他一些监狱也相继建立。监狱的创建者们认为,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是犯罪的渊源,要解决犯罪问题必须重建正常的家庭结构,因此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建立家庭式的监狱,让那些生活在监狱里的人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但遗憾的是,“犯人数量的剧增以及由此造成的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很快就使这些监狱变成了人间地狱,疾病、脏乱、寄生虫和邪恶成了监狱生活的家常便饭”。〔11〕
一 少年矫正机构〔12〕 的建立与发展
自由刑和矫正制度的出现,逐步替代了野蛮的以肉刑和死刑为最终控制手段的刑事司法,但是在自由刑和矫正制度兴起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令早期社会改良者强烈不满和反对的方面,少年犯与成人罪犯混押混管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现象很早就受到社会改良者的强烈反对,但在19世纪初期少年犯与成年犯混押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例如从1816年1月1日到1817年1月1日,伦敦的新兴门监狱就有20周岁以下的女孩85名、男孩429名与成年罪犯混押在这所充斥着邪恶的监狱之中,类似混押的情况也存在于美国的监狱之中。〔13〕 随着少年罪错的严重化,越来越多的孩子受到刑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投入监狱。不仅仅是犯重罪的少年会被投入监狱,那些犯有轻罪的少年也会被关进充斥着邪恶的监狱,他们大部分是因为无家可归不得不“自谋生路”导致触犯法律。被投入监狱的少年境遇悲惨,往往从成年罪犯那里学到了更多的犯罪技能而不是获得矫治。有的陪审团看到这种现象,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通过裁决无效的方式,以避免将少年送入监狱或者处死。由于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放纵了少年罪错而可能导致这些少年更加为所欲为,因而备受非议。
上述现象引起了纽约防止贫困协会的注意。这个协会所做的一项著名调查发现,在1822年间违警罪法庭所审理的人数共450人,年龄全部在25岁以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这些孩子仅仅是由于没有家而被迫“自谋生路”,流浪街头而受到控告。〔14〕 防止贫困协会认为,为了挽救这些孩子,必须将他们与堕落的监狱、不合适的家庭和其他不健康的环境隔离开来,将他们安置在更加人道和健康的环境中。1823年,该协会提出了模仿监狱建立一个专门的少年庇护所的建议。这些教友派的信徒们的建议既是出于保护少年的考虑,但显然也是出于试图在陪审团行使否弃权和将少年送入成人监狱或者处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考虑。〔15〕
防止贫困协会主要由富商和专业人士组成,他们的游说和鼓动活动十分有效,州议会很快同意在1824年为少年建立一个专门的庇护所。1825年1月1日,纽约庇护所正式开始运作。在此后的35年间,纽约宣判有罪的孩子都被送入庇护所关押。〔16〕 需要注意的是,庇护所是由防止贫困协会管理和负责矫正罪错少年,议会仅作为协会的辅助者。直到1829年,政府才开始资助这个私人慈善组织。
为少年建立专门庇护所的做法很快传播到美国东部其他一些人口较多的城市,例如波士顿和费城分别于1826年和1828年设置于庇护所。在南方,新奥尔良于1847年,巴尔的摩于1849年,辛辛那提于1850年,匹兹堡和圣路易斯于1854年,也先后设置了庇护所。到1860年,全美国已经设置了60个类似的庇护所。〔17〕
这一时期,对少年庇护所收容的对象——罪错少年的界定很宽泛,有时候还是模糊的。例如,纽约防止贫困协会对少年庇护所的收容范围是这样界定的:“在一定年龄下的少年,如果引起了我们警察的注意,不管是流浪、无家可归,还是被指控犯有轻微犯罪,都可以被收容。”〔18〕 再来看实际收容的情况。纽约庇护所运作的第一年,即1825年,共收容了73名少年。其中只有一名犯了较重的罪(重盗窃罪),9名犯了轻盗窃罪,其他63人犯的都是诸如小偷小摸、流浪、逃离济贫院等轻微违法行为。〔19〕 这些孩子绝大部分都具有父母属于贫穷的劳动阶层的背景,有很大比重的孩子因为父亲被迫远离家庭谋生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大部分属于移民子女,特别是爱尔兰移民的子女。据统计,从1825到1855年间,在被关押在庇护所的少年中,仅爱尔兰移民就占63%。〔20〕
从庇护所收容对象来看,这些被收容的少年基本上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其最为明显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贫困”。庇护所之所以将贫困作为罪错少年的本质特征,大体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当时的美国人信奉这样一种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他或她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贫穷被看作是懒惰、愚笨或者是恶有恶报的结果。”〔21〕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美国人观念中,穷困本身就是一种“恶”;其次,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贫困是少年不良行为和犯罪的根源,贫困者是潜在的罪犯,他们容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最终开始犯罪生涯成为罪犯,而尽早对他们进行干预可以防止他们堕落;第三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瓦解,这些贫困阶层的少年首先游离于社会控制机制之外并构成了对现行秩序的威胁。因此,由纽约防止贫困协会首先倡导建立的庇护所自然将来自贫困阶层的少年作为了他们“保护”的对象,试图通过将这些所谓潜在的罪犯带离街头及将他们安置在机构内予以矫正以达到“保护”少年的目的。
庇护所的倡导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是仿照公立学校而不是家庭来设计庇护所的。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勤奋工作、规训,而不是通过父母般的爱和照顾来拯救孩子。〔22〕 不过,从庇护所的运作来看,它更像是在仿效成人监狱的模式。庇护所的管理十分严格甚至是严酷,手铐、脚链、鞭打等用以管教成年罪犯的手段,在庇护所也被广泛地使用。庇护所在某些方面又像是早期的济贫院。由于当时人们认为,“游手好闲是邪恶的工厂”,因此被收容的少年经常被送去给农场主或其他人做学徒,作为回报,庇护所也因此获得不少好处。据统计,每年大约90%从庇护所释放的孩子都被送去做学徒。〔23〕 这实际上和早期济贫院的做法一样,后者在17世纪就开始采用了将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的做法。庇护所收容的大部分是贫困少年,加上类似于济贫院的运作方式,因此有的学者又认为庇护所实际上是一个少年济贫院,而不是教养院。〔24〕 和对早期济贫院所批评的现象类似,将少年送去做学徒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使庇护所异化为一种经济实体,被收容的少年则异化成了为庇护所挣钱的合法童工。
19世纪中期,庇护所被一些人狂热地宣布为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有些庇护所经营者甚至在青少年杂志上做起了广告,他们为自己成功地将完全不称职的年轻人改造成了有劳动能力而又勤劳的人而大感自豪。据说,还有的被转化好的孩子写信给庇护所,提供庇护所成功的证言。〔25〕 这种所谓的成功,显然被夸大了。庇护所把大量的少年变得在行为和思想方面都像个机器人,或者比以前犯罪更加严重的人,而不是将他们塑造成了理想的孩子。〔26〕 无论是庇护所内部的人员还是外部的人员,都对庇护所在管理、惩罚方式等方面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此外,由于需要收容的人太多,庇护所很快不堪重负,面临着收容能力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日益严重化的少年罪错现象事实面前,庇护所大获成功的谎言不攻自破。
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市政府和州政府开始对建立和管理少年矫正机构感兴趣,由他们设置的少年矫正机构称为少年教养学校,也有的称为工业习艺学校、训练学校等。这些新的少年矫正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均由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和负责管理。尽管在名称上不同,但这些少年矫正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家庭式少年教养所,另一类是机构式教养所。它们通常都设置在农村,目的是为了免受城市不良环境的影响。家庭式少年教养所一般收容20到40个少年,他们由“家庭父母”负责监督、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式教养所一般都很大,并且经常过度收容。〔27〕 少年教养学校的广泛建立,促使少年庇护所体系开始向少年教养学校体系转变。少年教养学校与少年庇护所的区别除了体现在资金来源方面由政府提供资金和管理以及由私人慈善团体提供资金和管理外,还体现在少年教养学校更为强调正式教育等方面。致力于推动建立教养学校的改革者们认为,庇护所诸多弊端的存在不在于庇护所的目标,而在于它们的方法。〔28〕 因此,教养学校在很多方面实际上仍继承了庇护所的做法,例如都将少年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弥补矫正机构经费不足的资源、都采用鞭打等肉体惩罚方式进行管教等。少年教养学校的出现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少年矫正机构体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庇护所还要糟糕。尽管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少年罪错现象的严重化,仍促进了少年矫正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各样的少年矫正机构都建立了起来以应对问题少年。例如,专为少女设置的矫正机构和专为黑人少年设置的矫正机构即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
19世纪中后期针对少年矫正体系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所谓机构外安置运动。由于很多救助儿童团体的慈善家看到少年矫正机构并没有阻止少年罪错现象的蔓延,因此对类似庇护所之类少年矫正机构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他们从“家庭是最好的教养学校而不是矫正机构”等传统观念中获得了灵感。这些慈善家们认为农业劳动是解决少年罪错现象的万能药,〔29〕 如果社会将流浪少年和贫民窟的少年集中起来安置到正在扩张和发展中的西部边境地区的农家,那么少年罪错现象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他们试图将大街上和贫民区的孩子全部安置到农户家里去。机构外安置运动构成了19世纪美国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纽约儿童救助协会(Children' s Aid Society)〔30〕 的创始人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领导的。许多救助儿童社团将一群群的罪错少年送给通往西部的沿途村镇的农户。据统计,在25年间,布雷斯和他的儿童救助协会使5万多个孩子离开了纽约,其中大多数是不超过14岁的孩子。〔31〕 尽管布雷斯等慈善家们极力为机构外安置行动辩护,但仍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很多人批评这种在东部有足够工厂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到遥远的西部是无知的做法。尽管布雷斯也认为家庭生活对孩子的重要,但却撇开了家庭的自然血缘成分——孩子的亲生父母。他的计划也显得很随意,很少花时间去调查寄养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从未再得到那些被安置的孩子们的消息。〔32〕 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被安置的孩子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有的甚至在接收他们的农户家中受到了虐待,很多孩子选择了逃回城市。1868年出版的不朽文学名著《流浪儿迪克》就记叙了这样一个逃回城市的孩子——约翰尼。恐惧、孤独是约翰尼对机构外安置行动的感受,最后他在某个早上三点钟起床,采用徒步和藏在一辆马车车顶的方式行程1000多英里逃回了纽约。〔33〕
主要由慈善家们推动的少年矫正机构运动是否真的像他们所宣称或者期待的那样起到了为少年谋福利的实际作用,是值得深思的。正如布雷斯所创始的纽约儿童救助协会所宣称的那样:“本协会就是为了解决纽约不断增长的儿童犯罪率与贫穷问题。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城市’。”〔34〕 可以肯定的是,当对少年的传统控制机制瓦解或者不足以实现对少年控制的时候,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的兴起的确具有弥补这种不足和加强对少年控制的作用,这种改革也为更加完善的少年控制专门机制——少年司法的形成做了重要的铺垫和准备。
二 关于少年矫正机构收容权的法律争议
19世纪美国少年矫正机构的收容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由于认为少年矫正机构收容罪错少年是出于少年最大利益原则的福利取向,而不是为了处罚他们,因此无论是前期的庇护所还是后期的少年教养学校,均没有像对待成年罪犯那样给予他们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少年并不享有成年刑事犯罪人那样的宪法权利。被强行收容的少年不需要经过任何正当法律程序,也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援助。这些少年矫正机构可以不定期地收容少年,或者收容到他们年满18周岁或21周岁为止,而且这种收容不需要经过法院听审程序,治安官、少年的父母或者市参议员均可以将少年送入矫正机构;其次,少年矫正机构的收容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仅那些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少年可以被收容,即便是那些没有任何触法行为的少年,只要被认为有收容必要也可以予以收容;第三个特点是这种收容权高于父母的监护权,少年矫正机构不需要经过孩子父母的同意即可以对那些被认为需要保护的罪错少年予以强制收容。
这样一种宽泛和几乎不受控制的收容权与刑事司法体系中监狱的收押权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合法性等问题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议也体现在一系列判例当中,这些判例为少年法院的诞生奠定了司法基础,对美国少年司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839年的克劳斯案(Ex parte Crouse)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尽管克劳斯(Mary Ann Crouse)没有犯任何犯罪,但这名少女在母亲的控诉下,被费城庇护所收容。庇护所收容克劳斯的理由是考虑到母亲无法管教这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同时也“考虑到这个孩子的心理和将来福利的明显需要”。〔35〕 克劳斯的父亲对这一起收容事件提出了质疑,要求费城庇护所释放他的女儿。律师认为,在没有经过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将克劳斯予以监禁收容是违宪的。官司一直打到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1839年1月5日,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宣布支持庇护所的收容权,驳回了克劳斯父亲的请求。法院在裁决中宣称:
庇护所不是监狱,而是教养学校,惩罚不是最终的……这个慈善团体通过训练其收容人员达致勤奋,将道德和信仰的原则注入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总之,是通过使他们脱离不当联系的腐化影响来达到矫正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生身父母无力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或不配这样做时,难道就不能为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或社区的普通监护人所代替吗?……这个未成年人已经从必须结束的确定堕落的过程中救了回来,不仅监禁她是合法的,再把她放回去也是非常残忍的行为。〔36〕
我们可以将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裁决的主要理由概括为四点:首先,法院认为克劳斯没有受到处罚,而是受到了帮助;其次,法院关注的是开办庇护所者的好心,而并不是被收容的少年是否真的在庇护所受到了帮助;第三,法院认为庇护所“帮助”克劳斯是合法的,因为政府居于国家监护人的地位;最后,由于法院认为克劳斯不是被惩罚,因此她不需要任何正式刑事审判被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37〕
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关于克劳斯案裁决陈述的理由对于美国少年司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案件第一次正式引用国家亲权哲学为少年司法的宽泛性干预权进行合法性辩护;肯定了少年矫正机构对仅仅被认为是“不可救药”而没有构成任何犯罪行为少年的收容权;克劳斯也是第一个生身父母还健在,而由政府行使国家亲权的正式案件。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的裁决明确了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的地位——即便是在生身父母中还有一人认为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子女的情况下。
在1869年的罗斯诉庇护所案(Roth v.House of Refuge)中,克劳斯案所确立的原则得到了肯定和发展。这一年,一个名叫马丁·罗斯(Martin Roth)的绅士向马里兰州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因为他12岁的儿子弗兰克·罗斯(Frank Roth)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巴尔的摩庇护所收容,这名父亲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有能力照顾其儿子。在上诉状中,这名父亲请求颁发人身保护令,将他的孩子送交法院处理并从非法监禁中释放出来。〔38〕 在经过围绕某些程序问题和人身保护令的漫长讨论后,阿尔维(Alvey)法官同样援引了国家亲权哲学并做出了非常简洁的结论,驳回了马丁·劳斯的请求。在裁决中,阿尔维宣称:
……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即便没有详尽陈述我们做出结论的理由,我们仍明确地认为,授予庇护所管理人员的权力……绝不和州宪法冲突……〔39〕
罗斯诉庇护所案再一次确认了国家亲权高于生身父母亲权的地位——即便是在生身父母具有良好的道德和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同时,再次明确肯定了少年矫正机构宽泛而无须正当法律程序限制的收容权并不和宪法冲突。
同样是在1869年,俄亥俄州高级法院也受理了一起有关少年矫正机构收容争议的案件。14岁的普雷斯科特(Benjamin Prescott)因为纵火而被认为是邪恶、无可救药的,应交给庇护所或者俄亥俄州教养农场收容。郡法院指令教养农场收容普雷斯科特直到成年,或者在矫正好后再依法于适当的时候释放。普雷斯科特的律师在上诉中认为,他的未成年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在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和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被剥夺了。怀特(White)法官在裁决中承认普雷斯科特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但同时指出,俄亥俄州的法律已经授予教养院委员会这种拘押权。〔40〕 至于辩护律师指出的普雷斯科特未经过陪审团审判问题,怀特法官采用了和克劳斯案裁决类似的理由,认定“这个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拘押……不是设计成对犯罪的惩罚,而是为了安置这类未成年人……他们被拘押的机构是学校而不是监狱……”〔41〕
与其他早期案件最大的不同是,普雷斯科特确实犯了罪,而且这一罪行足以将他关进州监狱。但是,俄亥俄州高级法院仍然认定庇护所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收容是合法的,由此实际上确立了国家亲权可以代替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42〕 普雷斯科特诉俄亥俄州(Prescott v.State)案所确立的国家亲权可以超越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影响深远,这一原则后来也演变成美国福利型少年司法模式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之一。
另一个曾经被忽视、但却颇值一提的重要案例是1870年的丹尼尔·奥康尼案(O' Conell v.Turner)。芝加哥教养学校同样收容了一个没有犯罪、只是有成为叫花子危险的男孩丹尼尔·奥康尼(Daniel O' Connell)。这一做法遭到孩子的父亲迈克尔·奥康尼(Michael O' Connell)的反对,他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面对与克劳斯案类似的案件,1870年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做出了与克劳斯案完全相反的裁决,命令释放丹尼尔·奥康尼。桑顿(Thornton)法官在裁决中尖锐地指出:
这个男孩被剥夺了父亲的照顾,被剥夺了家庭的影响;没有行动自由;被不确定期限地拘押;打上了像罪犯一样的标志;被要求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奴隶。〔43〕
桑顿法官裁决的理由几乎正好与克劳斯案的裁决理由相反:首先,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认定丹尼尔·奥康尼被送到教养学校不是被帮助,而是被惩罚;其次,在裁决书中,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描述了芝加哥教养学校严酷的实际情况,并且认为父母照顾会对丹尼尔·奥康尼产生好的家庭影响;再次,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否定了国家亲权原则是处理少年罪错案件的基础;最后,由于揭露了教养学校的真实情况,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自然地认为剥夺人身自由需要正式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44〕
颇为值得推敲的是,长期以来,丹尼尔·奥康尼案很少被法院或者政策制定者认为具有任何先例的价值,甚至在当时还被有的人认为是古怪的判决。〔45〕 例如,同样是伊利诺伊州高级法院,却在1882年的费里尔案(In re Ferrier)中又肯定了州工业习艺学校对无人抚养少年的收容权,并且仍然认定:工业习艺学校是学校而不是监狱,可以照顾那些得不到适当照顾的孩子,“我们不认为这是坐牢”。〔46〕 不过谁也没有预见到,80余年后的高尔特案(In re Gault)几乎重演了丹尼尔·奥康尼案,并且“幸运”地对美国少年司法的走势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三 结语
19世纪是美国少年司法发展史上的起源期,尽管少年法院尚未出现,但这种正式的少年控制专门机制已经萌生。一元化刑事司法体系开始出现裂缝,少年矫正体系率先从刑事司法体系中初步独立了出来,并形成了与刑事司法完全不同的少年司法规则。不管其实际效果和动机如何,少年矫正运动的确为美国少年法院的诞生和少年司法从刑事司法中分离出来做了必要的准备。我们可以将19世纪的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称为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首次分野。
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首次分野的鲜明特色是举着少年福利的旗号,试图改革一元化刑事司法的弊端,为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并矫正其罪错行为。但显然,在这一善心支配下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完善了对少年,特别是对下层贫困、移民和闲散少年(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父母)的社会控制机能。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一段深刻的话:“在此重演的情况是,保护儿童的呼吁被当作一项强有力的手段,用来动员群众的支持。对于那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人来说,成人的政治策略通常是借着童年的名义来实行的。”〔47〕 被丹尼尔·奥康尼一案所揭露出来、但是又很快被忘却的少年矫正机构的善心与事实之间的落差,似乎再一次印证了分野的实际结果主要是少年控制机制得到了完善,而主要不是少年从这一改革中受益。这也为美国少年司法的流变埋下了伏笔——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它才集中暴露出来。
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首次分野的另一个特色表现为国家亲权与生身父母亲权的博弈。在前少年司法时代,家庭而不是刑事司法居于对少年及其罪错行为控制机制的中心地位,父母的亲权高于国家亲权或者至少是受到国家亲权尊重的。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样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逐步瓦解,家庭在都市生活的条件下“已失去了纪律上的有效性”,〔48〕 父母无法再担负控制少年及其罪错行为的功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并不难以想见,这场博弈的结局将会如何。经过克劳斯案等案件,国家亲权成功地凌驾于父母亲权之上,并成为了少年司法弹性而宽泛干预权的合法化基础。这样一种转变,显然具有完善少年罪错控制机制(也是少年控制机制)不足的色彩。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在少年福利的名义下完成的。
学界基本公认美国是少年司法的起源地,并以1899年7月1日伊利诺伊州通过《少年法院法》,同时在库克郡设置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作为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标志。自20世纪以来,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对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前期的少年法院运动并不仅仅是少年法院在美国各州的推广,同时也是少年法院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制度化的少年司法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庞德曾经将少年司法制度称为“英国大宪章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49〕 而诸多的学者大都将少年司法制度的兴起看作司法制度和儿童福利保护进步的结果,甚至将少年司法制度提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和“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50〕 的高度。当前,我国正在抓紧推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少年司法制度的儿童保护价值受到了高度的推崇。譬如,有许多学者和儿童保护活动家多方呼吁要建立和健全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的司法保护,这样的观点和呼吁对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不无裨益。然而,本文通过探究美国少年司法起源时期少年矫正机构运动兴起的历史发现:少年司法制度起源的真正动力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儿童的福利,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保护儿童的福利,而是适应社会转型完善社会控制机制的需要,特别是针对底层青少年(同时也包括其家长)社会控制机制的需要;儿童福利是建构少年司法的旗帜,但少年司法在实现儿童福利保护的效果上是有限的,也是容易与制度号召者的初衷相悖的。但愿这样的发现,能够对于促进我国当前理性地开展少年司法制度建设、防止少年司法制度的异化,有所裨益。
注释:
〔1〕[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12页。
〔2〕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页。
〔4〕1703年,克莱门特十一世在罗马建立的圣米歇尔教养院大门上所铭刻的词句。引自[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5〕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其对法学的贡献”,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6〕[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6-12页。
〔7〕[德]京特·凯泽:《欧·美·日本监狱制度比较》,刘瑞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8〕Preston Elrod and R.Scott Ryder,Juvenile Justice:A social,Historical,and Legal Perspective,Asper Publishers,1999,pp.87-88.
〔9〕[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0〕Clifford E.Simonsen and Marshall S.Gordon Ⅲ,Juvenile Justice in America,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2,p.20.
〔11〕[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12〕少年矫正机构包括19世纪前期的少年庇护所以及19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少年教养学校、训练学校等,本文统称少年矫正机构。
〔13〕Clifford E.Simonsen and Marshall S.Gordon Ⅲ,Juvenile Justice in America,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2,p.12.
〔14〕Clifford E.Simonsen and Marshall S.Gordon Ⅲ,Juvenile Justice in America,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2,p.21.
〔15〕Robert E.Shepherd," The Juvenile Court at 100 Years:A Look Back" ,Juvenile Justice,Vol.Ⅵ,Number 2,December 1999,p14.
〔16〕History of Juvenile Detention,http://www.ci.nyc.ny.us/html/djj/html/facts.html(访问日期:2005年8月2日)。
〔17〕John C.Watkins,The Juvenile Justice Century:A Sociolegal Commentary on American Juvenile Courts,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98,p.5.
〔18〕Grace Abbott,The Child and the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348.
〔19〕Grace Abbott,The Child and the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362.
〔20〕Robert S.Pickett,House of Refugee:Origins of Juvenile Reform in New York State 1815-1857,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9,p.6.
〔21〕[美]查尔斯·H.扎斯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孙唐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2〕LaMar T.Empey,Mark C.Stafford and Carter H.Hay,American Delinquency:Its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4th ed.,The Dorsey Press,1999,p.40.
〔23〕Clifford E.Simonsen and Marshall S.Gordon Ⅲ,Juvenile Justice in America,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2,p.23.
〔24〕Thomas J.Bernard,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65.
〔25〕Thomas J.Bernard,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3.
〔26〕David J.Rothman,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Little Brown,1971,pp.258-260.
〔27〕Preston Elrod and R.Scott Ryder,Juvenile Justice:A Social,Historical,and Legal Perspective,Asper Publishers,1999,pp.100-101.
〔28〕LaMar T.Empey,Mark C.Stafford and Carter H.Hay,American Delinquency:Its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4th ed.,The Dorsey Press,1999,p.41.
〔29〕Clifford E.Simonsen and Marshall S.Gordon Ⅲ,Juvenile Justice in America,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2,p.24.
〔30〕该协会于1853年建立。
〔31〕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32〕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33〕[美]哈罗修·阿尔吉:《流浪儿迪克》,冯杨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6页。
〔34〕Walter I.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4th ed.,The Free Press,1989,p.111.转引自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35〕Ex parte Crouse,4 Whart.Pa.9( 1839) .
〔36〕Ex parte Crouse,4 Whart.Pa.11( 1839) .
〔37〕Thomas J.Bernard,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68-70.
〔38〕Roth v.House of Refugee,31 Md.329( 1869) .
〔39〕Roth v.House of Refugee,31 Md.334( 1869) .
〔40〕Prescott v.State,19 Ohio St.185-187( 1869) .
〔41〕Prescott v.State,19 Ohio St.187( 1869) .
〔42〕John C.Watkins,The Juvenile Justice Century:A Sociolegal Commentary on American Juvenile Courts,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98,pp.20-21.
〔43〕People ex rel.O' Conell v.Turner,55 Ill.287( 1870) .
〔44〕Thomas J.Bernard,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70-71.
〔45〕Thomas J.Bernard,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5.
〔46〕In re Ferrier,103 Ill.371( 1882) .
〔47〕[美]David Buckingham:《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下长大的孩童》,杨雅婷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48〕[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49〕[日]团藤重光、森田宗一:《新版少年法》(第二版),第2页,转引自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制度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50〕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页。
标签:法律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收容教养论文; 正当程序论文; 收容教育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克劳斯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