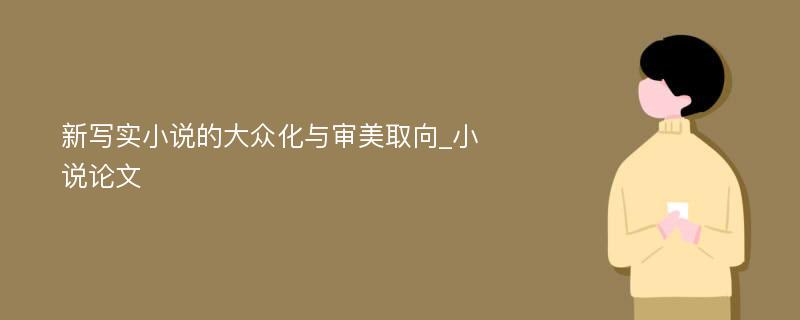
通俗化与新写实小说审美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通俗论文,化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写实小说创作不尚晦涩,不慕浮华,克服文学对生活的生硬剪裁和形而上玄思,而推崇朴实,追求深邃,注重强调生存状态的逼真还原,并力求将深刻的内容赋予在一种能为大众读者普遍接受的形式之中。这种艺术追求,使新写实小说“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呈现出一种浓重的“通俗化”美学色彩。一般而言,“通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出于两个方面:其一,作品所展示的是芸芸众生琐细而本真的凡俗生活,这自然使读者感到熟悉而亲切。其二,作家使用俗化语言进行平面叙述,这又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读者在阅读接受上的种种障碍。关于此,“新写实”的代表作家刘震云曾深有体会而又令人信服地谈到,“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二层含义,一是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作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什么价值。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1〕这无疑就是对小说“通俗化”方法及其意义的相当精到的理论阐发,是颇具启发性的。当然,这里所谓的“通俗”不能与“通俗文学”等量齐观,而仅指在纯文学意义上,新写实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而己。
如果从理论涵盖的特定角度观照新写实小说的“通俗化”艺术特征,我们就会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审美简化”的创作态势。所谓“审美简化”,简言之,就是指作家在择取生活反映生活的具体创作过程中,一般不重“形而上”地对生活进行抽象、精微的刻意加工,杜绝使用诸如隐喻、象征、怪诞、夸张等艺术形式,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之类的作品那样证明抽象的形而上的关系、道理和本质;也不象传统现实主义那样热衷于强化矛盾冲突,设置悬念制造气氛,使情节大起大落扣人心弦;更不象古典浪漫主义那样进行浓墨重彩、繁缛绮艳的渲染铺张。而是着力于“形而下”地做具体、普泛的状态绘制,擅长以平静、淡泊、庸常的话语方式构置具体琐碎的写实画面,以展示内蕴丰富驳杂的凡俗生活。这种艺术追求,必然使新写实小说从里到外都浸透着一种沉重的自然、本色、朴实、粗砺的美学蕴味,从而产生一种平实、通俗的审美效应。以下拟从“俗化语言”、“流水结构”、“平面叙述”三个方面论述“形而下”艺术形式的具体特征。
1.俗化语言。
新写实小说的语言操作追求生活化和日常化,与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雅化语言”相对,它属于十足的“俗化语言”。传统小说对客观现实生活的描绘是经过创作主体颇为严格的选择和精心过滤的,其语言也是经过净化和规范的,而且时有作者主观情绪的强烈介入。而新写实小说则注重口语化、俚俗化,强调客观性。它要求语言尽可能地涵盖现实,小说中的生活样相与原态生活一样,由于不事精心雕琢而显得浑朴自然生动真切,由此达到逼真酷似的审美效果。如果说先锋新潮小说的话语方式侧重对应于人的思维和情感,那么新写实小说的话语方法则主要对应人的具体行为过程。仅以《艳歌》中的一段对话为例:
下次见面时,沐岚问迟钦亭,为什么那天在她家不肯开口。迟钦亭赌气说:“在你那样的家里面,我怎么敢开口。”沐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我们家怎么了?”迟钦亭赌气不说,沐岚又问了一遍,说:“我爸我妈怎么了,难道对你不好,得罪你啦,看你生气的样子。你说,难道谁对你不好了?”迟钦亭恶狠狠地说:“好,好得不得了!”沐岚拿他没办法,只好说:“想不到你这个人也会这么不讲理,你喜欢生气,那活该。”迟钦亭憋了一会,头昂起来说:“别以为我配不上你,你想不做我老婆也不行。别说你是什么厅长的女儿,就是省长、国家主席的千金,我照样要娶,你去跟他们说好了。”
这可算是非常典型的俗化语言了,我们发现语言与行为的对应已达到了非常细密的程度。表面看上去,这种话语方式似乎显得很啰嗦,给人以拖沓之感。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种强化效果,即对真实感和事件过程的强化,使艺术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另外,这种话语方式最直接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是对最一般的阅读接受的一种尊重,而“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如果读者拒绝阅读,那就意味着一部作品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彻底实现,甚至意味着作品的自行毁灭。要让一部作品完全实现其艺术审美价值,首要的前提是必须赋予一种读者能够接受和愿意接受的叙述方式,尤其是同时代的大众读者所能普遍接受和愿意接受的叙述方式。先锋新潮小说就由于丧失了起码的艺术传达功能而终于使读者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最终走向自己的穷途未路。新写实小说也正是由于使用了平实通俗的话语方式,才受到来自阅读接受方面的广泛关注,这其实都是一种必然、一种宿命。
2.流水结构。
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结构模式。而新写实小说则有意淡化这种旧法结构模式。突出的特点是,它一般不特别注重以因果链来串连事件,而多以单一的时间顺序作较为随意的自注延续。作品中的诸多事件之间一般没有突出而显在的必然关联,不互为因果,也不刻意设置悬念相互照应,姑且称之为“流水结构”。如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池莉的中篇力作《烦恼人生》,作品主要状写青年工人印家厚从凌晨四点孩子摔下床到当夜十二点上床就寝这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过程,按时间顺序展开上班、下班、工作、家务等一系列琐碎而又极其平常的人生内容,并通过大量心理活动的穿插,坦露印家厚这一天的所有感觉、生存中的苦辣酸甜、失落与希望、烦恼与企盼,仅此而己。小说完整统一的情节最终并没有构成一个动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故事,却给人以自然而随意、庸常而亲切的感受。用流水笔法摹写原色生活样相,使小说显得象生活本身一样零乱而无序,偶然性迭出,生活与艺术简直达到某种程度的同形同构,使读者感受到了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常而凡俗的生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可触可摸的现实感、逼真感,因而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家虚构的文本世界之中,并感到意蕴深厚、滋味无穷。这种创作倾向在新写实小说创作中绝不是个别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都是在摆脱了刻意编制故事情节的纠缠后,获得了再现客观生活的巨大真实感。由于不再为某种片面的主题表现之需要而去过分地虚构生活、杜撰情节,而是用“流水结构”对应自然生活流程,这样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就更趋全面复杂而本真,审美意蕴自然也就更为丰厚,从而必然引发读者较强的阅读效应。
3.平面叙述。
新写实小说采用一种平面叙述的视角,从而确立了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新型关系。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总是喜欢充当读者的老师,常以一种高踞的姿态面对读者。中国以美刺教化为己任的大师们自不待说,即使重视客观再现的西方现实主义巨匠也不例外。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就说:“一个作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应该持有固定的见解,他应该把自己看作人类的导师。”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中国当代的“两结合”小说大都是表面上来源于生活而实际上脱离生活,都是些教育式“传声筒”式的作品,因而读者难以在同一层面上把作品中描写的生活同自己的实际生活相类比,作品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与读者拉开了一段距离。而新写实小说则由于作家采用“平面叙述”的视角,改“俯视”为“平视”,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作家由读者的老师变为同学、朋友。作家也并不打算硬灌输给读者什么,作家充其量也只能是生活的代言人,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他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与读者是平等的关系。如此,读者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作品的再创造,在主动的阅读接受过程中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探索和思考,而不再满足于消极被动地听候作家的指点和说教。池莉曾说:“我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而要让读者接受他的劝告,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2〕而接近的方式之一,就是采用平面叙述建构文本, 让读者主动参与作品的再创造。强调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是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的基本精神,也是时下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
凡俗是人的品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一面,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最深之审美地层。记得李贽在《明灯道古录》中就曾指出:“尧舜与涂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所谓高贵的圣人与卑贱的俗子在精神品格和生命欲求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一朴素真理。显然,任何人都不能免俗,或者说,从人的最自然最本能的生存境况来看,任何人都程度不同地是个凡夫俗子。每个人都少不了七情六欲,每日都少不了吃喝拉撒睡,都要经历人生的生老病死,艰难而又心怀某种希望地生活着。虽然纷纭繁复、粗糙芜杂的世俗生活并没有人们设想的虚拟的那般富有诗情画意,但却饱含着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等人生最基本最充实的内容。新写实作家将审美的聚光点投注在这些平常凡俗的社会生活之上,用自己的全部审美触须拥抱这些日常生活琐事,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纯真质朴如出水芙蓉般的自然美。读者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故事里窥见到自己的身影,听见别人讲出了隐藏在自己心底的生活进程中的诸般甘苦,自然就会带着异常亲切的心情去品味作品。由此看来,新写实小说之能赢得大众读者的认同和青睐,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情理之中势所必然的事情。
事实上,贴近现实生活,真诚直面人生,并追求一种较为平实的通俗的审美效应,是8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创作的共同价值取向,而非新写实小说独有的追求。可以说,自从前些年的报告文学热、纪实文学热、通俗文学热盛行以来,这种重平实的通俗的创作趋势和审美意向就一直居高不下,且具有压倒的优势。一个时期以来,除新写实小说创作而外,在诗歌界出现了具有轰动效应的“汪国真现象”;在散文界,紧衔“曹明华现象”余热,纪实散文正方兴未艾;在影视界,则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秋菊打官司》、《北京人在纽约》等等的又一次引起轰动;在音乐界通俗歌曲和流行音乐更是进入千家万户,对所谓“严肃音乐”造成了全面而强烈的冲击……这一切都在说明,在改革开放求实务实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伴随着生活内容的丰富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不断更新,广大艺术消费者的审美意向和审美需求也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不再钟情那些疏离生活艰涩冗长而又故做姿态的东西,转而青睐于平实的通俗的审美创造物。读者的这种接受心态必然要影响到作家的艺术创作,新写实小说就是在这种双向选择中应运而生的。新写实小说潜在地表达了一种社会意识和时代情绪,又以其通俗的艺术魅力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大众读者的接受心态和审美期待。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种审美取向是对艺术大众化的一种张扬和实践,更是一种探索和开拓。因此我们预言,这种艺术精神必定是长盛不衰的。
注释:
〔1〕《新写实体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3。
〔2〕《新写写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