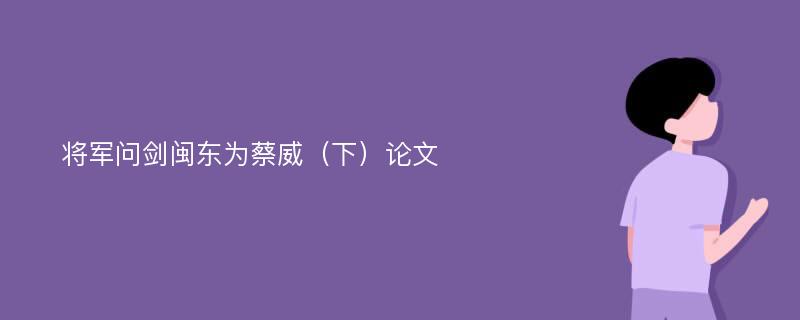
将军问剑闽东为蔡威(下)
邱文生
特别工作小组的查证
南国早春,花团锦簇,生机盎然。
1984年2月12日,由中顾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带领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联络员小组抵达福州,下榻在福州西湖宾馆。
为了保证混凝土柱与箱形钢柱斜率的一致性,模板斜率采用同一平面控制网,进行测量控制,利用投影法控制柱模的斜率,在楼面柱模定位放线中,弹出倾斜后柱模顶端及中部每个边在楼面上的投影线。柱模就位时,用线锤分别测出柱顶及中部的投影是否与投影线一致,这样一根柱通过三点(柱顶,柱中,柱根)控制其斜率。每次柱位放线后,用线锤测出每两层柱模投影线的差值。通过外控的方法检查每次放线的准确性,如实测值大于±2 mm,则必须重新放线。
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对宋侃夫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这位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的老同志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中央派他来福建指导整党工作,项南感到由衷的高兴。
同项南一起来看望的还有福建省政协主席伍洪祥,人们都尊称他“伍老”。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第一次见面,宋侃夫便道出自己的一桩心愿:“中央本来安排我去上海,我跟中央请求来福建,是想借此机会办一桩‘私事’。”
阿里的每句话都仿佛带着针,总能让阿东的心觉得被刺。母亲已经去世多日,阿里却浑然不觉。他见不到母亲,但他脑子里却没有她不在世的概念。他既然如此弱智,又怎么会把母亲记得如此牢固?阿东有些弄不明白。晚餐阿东真的给阿里做了粉蒸肉,阿里快乐地吃着。阿东怀有心思,吃饭时一直在想,这事应该怎么解决呢?要不要把录音机收起来?
“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办的,你就交办,我们尽力而为。”项南说。
“是这样,你们福建有个红军烈士,名叫‘蔡威’,是福宁府人。当年他跟我们一起受上海党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苏区,是我们党培养的早期无线电通信专业人才,对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牺牲在长征路上,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我们几个老战友都想寻找到他的亲属,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但还不能确定,必须做进一步调查。这件‘私事’,得请你们帮忙办。”
“哎呀,这哪是‘私事’?分明是一件大公事哦!”一说到革命先烈,伍洪祥就动感情了,“我们福建红军、游击队战士在长征中牺牲了一批,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一批,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也牺牲了一批……初步查明全省烈士有50000多人,还有不少同志失踪了,无法查清。这两年,我们都在查访,革命胜利这么多年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些英勇牺牲的先烈!”
“伍老兼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主任。”项南说,“这件事就请福建省委党史部门的同志协助查一查。”
“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一定想办法查清。”伍洪祥向宋侃夫表了态,并很快把这项任务落实下来,交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和原“福宁府”所在地——宁德地委党史办开展调查。
亲身经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伍洪祥,自然把访查烈士家乡和烈士亲属的下落看作神圣而紧迫的工作。
伍洪祥十分清楚:与英雄辈出的闽西一样,在血与火的岁月里,闽东同样是英勇不屈、红旗不倒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自1934年成立之日起,坚持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红军主力长征后,闽东红军在闽浙两省20个县的广大区域开展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就在蔡威烈士牺牲前后,闽东红军还经历了名闻遐迩的官岭、坂头、百丈岩和亲母岭战斗。特别是“百丈岩九壮士”的事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120名红军战士被3个连的国民党军包围,支队长阮吴润率20名红军战士奉命掩护撤退,血战到最后的9名勇士毅然登上陡峭的百丈岩,向国民党军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砸烂枪支,纵身跳崖,全部壮烈牺牲。
福建的整党工作全面铺开了。宋侃夫忙着开会、听汇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指导整党工作,稍有闲暇,便惦念、询问寻查蔡威祖籍地和后代工作的进展情况。
做好购置程序的严格控制,针对耗资巨大的机械设备需要建立专门的审批制度对其进行控制。以保证机械在运转过程中产生故障时能够及时和生产商协商解决。此外,还要将日常检修工作和维护工作放在工作的首位,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建立计算机检测机制,对机械设备进行实时监控,保证机械设备的运转正常。
当时,宁德地委党史办根据省委的要求已经介入了此项工作,但除了福鼎“张白弟”这条线索外,并无其他进展。
时间过去几个月了,“张白弟”就是蔡威吗?这个问题还一直悬着。
在北京的几位老将军得到宋侃夫的情况通报,感到很焦急,因为宋侃夫在福建帮助整党时间只有一年,他们生怕错过这一难得的寻找机会。这时,马文波、陈福初两位老将军提议“双管齐下”:以总参谋部某部的名义,让福州军区也介入调查,把情况搞清楚,该确认的确认,该否定的否定。
于是,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成立了。
南国8月,烈日如火。特别工作小组刘友燧(宋侃夫的老秘书)、黄仕珍(福州军区某部参谋)和杨的莺(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干部)从福州驱车8个多小时奔赴福鼎。他们不想惊扰福鼎县委,当晚只与庄友柱交换了意见,决定第二天就出发去管阳、白琳、点头3个乡开展调查。
特别工作小组的行动似乎有点儿神秘,因为寻找蔡威烈士亲属的事在闽东北这个小县城已经传扬开了,他们想尽量避免意外的干扰,让调查工作进行得更顺利些。
然而,这一次查访,让庄友柱感到意外!
在管阳,特别工作小组召集张氏家族部分老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词:“张绍榘是1906年出生的。”
庄友柱询问张芝玉、张时康两位老人:“上一次调查,你们都说‘白弟’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大约六十六、七岁,这次却说是1906年出生的,相差10年。为什么前后两次说法不一?”
两位老人支支吾吾说:“记不清楚了。”
看来,受访者受到了干扰。老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张白弟”如果被确认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一名英烈,这不啻是张氏家族的无上荣光啊!
座谈会后,特别工作小组又到管阳西山里——张家所在的村子,访问了一位名叫“杨月英”的张家媳妇。杨月英回忆说:“我8岁来到张家,给白弟近房侄儿当童养媳。第二天,就是我来到张家的第二天,白弟父亲过世了。办丧事时,我还看到张绍周和张白弟两兄弟。”杨月英的记忆很清晰,说的话很坦诚。据推算,杨月英8岁那一年,应是1932年。
得知张绍榘的姐姐张瑶英家住点头乡,特别工作小组又立即赶往点头。
张瑶英已经过世了,只有她的女儿方素琴在家。她显然并不知道来访者的身份和动机,便把自己知道的事如实说出来:“我外祖父共有5个孩子。大舅张绍周,二舅张绍华,下来是我妈,再下来就是三舅张白弟……我8岁时看到过张白弟舅舅。那时,我们家住在福鼎城关。有一次,他来我家,坐在桌边念英语。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方素琴时年58岁,按年龄推算,那次见到张白弟应是1934年。而张白弟那时正在读中学。
关于张白弟的年龄,管阳张氏家族座谈会上的“众口一词”与杨月英、方素琴二人的回忆显然是矛盾的。
当晚,特别工作小组回到福鼎县招待所,讨论分析调查的结果。
学过法律、有过律师查证工作经验的庄友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张绍榘的年龄尚不能肯定,理由有三:一是在座谈会上,张芝玉、张时康为什么推翻原证词?讲不出理由,只说‘记不清楚’。二是根据杨月英、方素琴两人的年龄推算,她们亲眼看见张绍榘的时间是1932年和1934年,这时,张绍榘还在中学念书,推算他的年龄也才十七八岁。三是据张绍榘的二哥张绍华讲,他今年虚龄79岁,出生在1906年农历五月初十,张绍榘怎么可能与二哥同一年出生呢?”
与此同时,宁德县也展开了调查。
福鼎的查访无果,怎么办?宋老的心情焦急啊!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于是,3天以后,庄友柱和他的另一位同事去了温州。
温州一中的校史馆资料非常齐全。庄友柱查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一本《同学录》,在“高中一年级学生名单”中,记载着“张绍榘·福建福鼎(籍贯)”字样。
这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证明张绍榘确实在温州一中(即原来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过书。
庄友柱又到该校教导处,请求提供张绍榘的学籍卡片。
式(7)为t阶段船舶贝内任意列的积载强度必须得到保障的约束,其中,STi为船舶贝第i列最大允许的积载强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籍卡片终于找到了,上写:“张绍榘,男,19岁,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入校,家住福建省福鼎管阳西山里。”卡片背后记着张绍榘1935年度、1936年度及1937年度上、下学期的学业成绩。卡片上还贴有一张张绍榘半身免冠照片,上面注明:“张绍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毕业”。
据此,庄友柱确认:张绍榘出生于1916年,19岁(即1935年)入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后改名“温州一中”),1938年在该校高中部毕业。这与《张氏宗谱》的记载及杨月英、方素琴的回忆相符。
张绍榘1938年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高中部毕业时,蔡威已牺牲两年了。由此可见,这个张白弟绝对不是蔡威!
于是,庄友柱写成了《关于张绍榘是否就是蔡威烈士的问题调查始末》,呈送宋侃夫、徐深吉、马文波等有关老同志及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张白弟”这条线索的调查就此结束了。
从收回的有效问卷中,我们针对数据进行统计和整理。数据显示,这次参加问卷调查的计算机类、电气类等理工科学生约占98%,而文史类大学生参加比例仅占2%左右。而对于其他问题,我们从答案中提取了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总结。
庄友柱的分析有根有据,福州军区黄参谋表示同意。
在宁德城关——蕉城,蔡氏家族远近闻名。这个家族中,有没有叫“蔡威”的这么一个人呢?似乎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叫“蔡景芳”、学名“蔡泽鏛”的青年人,50多年前在上海失踪了,其三代嫡亲几十年苦苦追寻,至今杳无音讯。
宋侃夫家的来客
调查“张白弟”的线索终止之后,在京的几位老将军、老部长思念蔡威之情不但没有冷淡,反而与日俱增。
大约过了半年,一天,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来到北京西城区一个大院门口按响了门铃。门卫打开小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你找谁?”
“我是福建来的,找宋侃夫爷爷!”年轻人说的是福建普通话。
门卫与宋侃夫通报后,便打开大门,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幢二层小楼,说:“喏,宋老就住在那幢楼。”
年轻人按门卫指的方向慢慢走向小楼。他毕竟是生长在小县城的一个青年,来到北京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大”——大城市、大街道、大宅院、大首长……现在要求见的这位宋爷爷也是个大人物,见了面,将会怎样呢?
1.2.1 一般情况及饮酒情况的调查 调查员首先调查患者一般情况,包括:出生日期、职业、吸烟史、饮酒史,主要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病、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通过访谈的方式调查每位入组对象的饮酒情况,包括每日饮酒量、每月饮酒量、累计饮酒量、饮酒年限、饮酒的种类,并用专门设计的调查表记录下来。凡饮酒每月≥l两白酒计为饮酒者(纯乙醇量320 g,l两=50 ml)[4]。酒精量(g/d)=日饮酒量(ml)×酒精含量×洒精密度(g/ml),大量饮酒:纯乙醇量>100 g/d,中量饮酒:纯乙醇量50~100 g/ d,少量饮酒:纯乙醇量<50 g/ d。
小楼的门开了,迎接他的是宋侃夫的家人。
走上二楼,他看见一位老人端坐在桌子后面,神色有点儿冷峻。
“宋爷爷好!”年轻人自报家门,“我叫蔡述波,是从福建省宁德县来的。”他递过一张中共宁德县委党史办出具的介绍信。
宋侃夫点点头,示意年轻人坐下。
“是的,从福州坐火车来的。”
“蔡威是你的什么人?”老人问。
“是我的爷爷!”蔡述波的回答很肯定,“我带来了爷爷的一张照片。”
宋侃夫接过照片,端详着,凝视着,思考着,过了许久,才摘下老花镜,几乎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蔡述波,又是许久没有说话。
这一刻,蔡述波感觉时间很长很长,好像长达几十年!
“你是坐火车来的?”
年轻人又递上一叠带来的材料。宋侃夫戴上一副宽边老花眼镜,慢慢地翻看材料。
新环境下,图书馆做为社会信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图书馆成为很多创新和创业团队的主要场所,尤其是一些馆舍比较充裕的图书馆为部分科研团队提供研修间、专题咨询、科技查新、定题服务等服务方式,其中产生的文档和电子文档是社会的宝贵资源,同时图书馆业务流程的计算机化也产生大量的电子文档,这部分文档对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图书馆电子文档的开发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来北京住哪儿?”
图5给出了传感信号探测端探测到的信号功率和拉曼泵浦激光器的泵浦功率之间的关系。随着拉曼放大器泵浦功率增加,剩余泵浦功率增加,剩余泵浦功率同时又用做掺铒光纤激光器的泵浦源。当此功率值超过谐振腔内损耗阈值的时候,就有信号激发出来。激射信号的功率随着泵浦功率的增加而增加。
2010年4月5日,中国陕西黄陵县举办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万多名华夏儿女参加了祭奠。客居他乡的华人华侨结伴回归故里,寻根祭祖,拉近了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地山水、文化的距离,通过亲缘与地缘连带的亲缘关系认同、祖籍地认同、方言认同,或者说是宗教信仰认同、生活习俗认同,达成了文化价值的认同,从中获得“我们”这种归属感。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润萍说:“认祖归宗、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化评论家智效民认为,各类寻根祭祖活动的举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海内外华人、华裔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住在大姑婆家。我大姑婆就是我爷爷的大姐,她还健在。”蔡述波回答。
过了一会儿,宋侃夫说:“你先回大姑婆家等几天,把住址留下,有事再通知你。”
全体成员在圈会上对血液透析患者内瘘穿刺点渗血的原因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从护理人员操作技术水平,患者自身血管条件以及操作流程等方面出发,讨论制订与主题相关的工作流程图,通过流程图充分了解穿刺操作情况,导致渗血原因。
蔡述波写下大姑婆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便告辞了。
走出大院,蔡述波的心情并不感到轻松。第一次见到祖父的老战友宋侃夫,他很紧张,也很拘谨。宋爷爷不多问话,神态上还有些疑虑,是不是不相信我?是不是怀疑我假冒蔡威的小孙子上门诓骗他老人家?……回到大姑婆家,他有点儿坐卧不安。
等待是很折磨人的,但等待中隐藏着美好的希望。
酒店前场功能区包括各类餐厅和会议区等区域,大开间区域通常采用集中送风空调系统,而小开间、包间和会议室等小空间通常采用风机盘管。
庄友柱提议:“张绍榘在温州一中读过书,老同志回忆他在上海读过大学。我们工作小组可分成两路,一路去上海调查,我去温州一中调查。”
大姑婆对蔡述波说:“不必急,是真的假不了。”
她找出一张蔡述波父亲蔡作祥的照片,说:“这是你爸爸的照片。你爷爷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蔡述波拿过照片一看,是他父亲于“文化大革命”前拍的一张免冠照片,年龄大约30岁左右。
位于繁华帝都CBD的阳光印网创立于2011年,是印刷业典型的“互联网+”概念网络平台。走进阳光印网,不同的会议室用客户的名字命名,体现其服务意识。更引人注目的是,会议室的展架上摆满了阳光印网的产品,有我们所熟悉的天猫物流纸箱,各种精美的印刷图册、礼品,还有阳光印网自行设计制作的服饰等,种类繁多,设计考究,制作精良。
(1)风荷载值:在计算搁板或刚架和支撑构件时,当高度范围较大时,可将其分为多个区段,高度范围约为5m,并使用相应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计算风荷载。如果风荷载值范围太大,则风压高度变化系数也将偏向大值,这可能导致大的风荷载。
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天,宋侃夫的司机找上门来,告诉蔡述波:“明天上午,宋老在家等你。”
第二天上午9点,蔡述波再次走进宋侃夫家。
“下一次,你把这张照片带去,让宋爷爷他们看看。”大姑婆嘱咐。
这一天,宋老的家里多了3位老首长——王子纲、马文波、胡正先。蔡述波一进门,3位老首长就不住地盯着他看,上上下下打量着,却都不出声,那目光既谨慎,又热切。
在四双如电目光的审视下,蔡述波显得手足无措。他不敢问3位老首长的姓名和职务,只感觉他们一定是祖父的老战友。
蔡述波从随身包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了过去,说:“这是我父亲的照片。我大姑婆说,这张照片很像我的祖父。”
照片在几位老首长的手上传看,突然,4位老首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像!非常像!”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蔡述波看到,4位老首长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
于是,问话开始了:“你家在什么地方?”
“福建宁德县。”蔡述波回答。
“福宁府在什么地方?”
“福宁府?”蔡述波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知道。”
宋侃夫拿出一封信,问:“你哥哥是叫蔡述道吧?”
“是的,是叫蔡述道。”
宋侃夫接着说:“你哥哥刚刚来信,说他作了调查,现在的闽东地区就是过去的福宁府,宁德县隶属于福宁府。”
王子纲接过蔡述道的来信看了一下,说:“不错,是福宁府,不是福鼎县,这就对上了!”
马文波问:“你祖上有谁在外地做过大官吗?”
蔡述波想了想,回答说:“有,听说我的舅公林振翰在宁波当过盐官。”
“还有谁在四川当过官?”
“在四川当官?”蔡述波眨巴着眼睛,“没听说,好像没有。”
马文波进一步追问:“祖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宝贵东西?”
蔡述波想了很久,回答说:“除了房屋,其他的没听说。”
“你家是否有一把祖传宝剑?”马文波单刀直入地问。
“祖传宝剑?”蔡述波思考了一阵,还是回答“没听说”。
尽管4位老首长从年轻人送来的材料中已经得悉他的爷爷就是蔡威,心中有了九分的把握,但由于发生过险些把福鼎的张白弟误认为蔡威的事,因此不得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4位老人没有立即表态,没有立即确认,但从他们亲切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蔡述波的关切和信任,而且他们脸上都洋溢着找到蔡威烈士后代的那种情不自禁的欣喜。
马文波将军确信:蔡威生前对他说过家里藏有石达开佩剑,那肯定是存在的,蔡述波不知其详情有可原,他年龄还小嘛。蔡家的老人肯定知道这件事,只要做进一步调查,石达开佩剑之谜一定可以解开。
当即,4位老人做出决定:由马文波代表他们专程去福建,再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这一天,蔡述波走出宋侃夫的家,心情显然轻松了许多。他仰望蓝天,似乎感到祖父的在天之灵在护佑着他。
蔡述波离开北京时,宋侃夫请他带一封信给福建省委党史办的杨的莺:
杨的莺同志并转省委党史办:
关于蔡威烈士的生前情况,最近有新变化。蔡的长孙蔡述道前不久给我来过信,最近其弟又来京。昨天,我们邀请了王子纲、马文波、胡正先等同志一起座谈,证实蔡述道及其弟所谈情况和我们记忆的情况大致相同,这就可以肯定蔡述道及其弟蔡述波确系蔡威烈士的后裔。至于以前我们找到的张绍榘,可以否定。还有个别情况需要进一步查实。5月份拟由马文波同志来福建,届时,我们再写信带来给你们。现在蔡威烈士的孙子蔡述波同志回闽,介绍他来和你们见见面,谈谈情况。至于今后如何处理,待马文波同志来闽调查核实后,将由×××出面,和地方有关部门联系解决。
此信阅后,请转地区党史办。并请将此情况转知黄仕珍同志。
你如来京,请来我家做客。
致敬礼!
宋侃夫
1985.3.25
蔡述波一回福州,就把此信交与杨的莺。
杨的莺一口气看完信,高兴地对蔡述波说:“有希望啦!有希望啦!”她认为没有必要对蔡述波再保密了,就将信复印了一份,让他转交宁德地委党史办副主任黄垂超。
蔡述波回到宁德,听说黄垂超生病住院了,就直奔宁德地区医院,一踏进病房,就喜孜孜地说:“黄主任,有希望了!”
黄垂超是个细心人,听完蔡述波上京情况的讲述,又认真看了宋侃夫的信,对蔡述波交代说:“马文波将军5月份会到福建来进一步调查核实。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你祖父的有关资料和物证都做充分准备,配合组织上搞好调查。”
蔡述波也到宁德县委党史办汇报赴京拜访宋老的情况,他们一致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全力配合,做好准备,迎接马文波将军的到来!”
追踪石达开佩剑
马文波将军南下福建之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早在5年之前,马文波将军特地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清史》仔细阅读。他想,蔡威祖上如果有人在四川当过大官,那么,蔡家先人就可能在《清史》上留下蛛丝马迹。
一有空闲,他就研读《清史》,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的章节。
研读中,他终于发现:蔡氏家族在福建的最早落脚地是泉州。
这一发现,使他感到蔡威踪迹的存在。他不顾身患高血压和冠心病,毅然决定赴福建泉州调查。正当准备启程时,医生来干预了:“不宜远行!”夫人金瑞英也劝阻:“听大夫的话,等病情稍好了再去吧!”
这一等,两年过去了,直到1985年春,健康状况略微稳定,他带着老战友的重托,决定南下福建。
这一年6月,宁德蕉城悄悄传开一条小道消息:北京一位将军要来调查蔡家的事,蔡家又要出贵人啦!
小道消息得到了证实,来的正是马文波将军。
马文波将军中等身材,国字脸,戴一副淡青色墨镜,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虽已75岁,但依然英姿勃勃,沉稳而潇洒。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兼任外交部副部长,常随周恩来总理接待外宾,协助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他的记忆力惊人,那么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那么多中国外交领事馆海外驻地、那么多中国外交官的名字,都烙在他的脑子里,他随口都能准确说出来。
要寻人,先寻剑。马文波将军抵达宁德,安顿甫定,就提出“先与蔡作柯老人见面”。
蔡作柯已经80多岁了,是蔡氏家族收藏石达开佩剑唯一健在的见证人。此前,宁德县委党史办青年干部陈国秋做过相关调查,并事先向马文波将军做了汇报。
第二天上午,蔡作柯老人在宁德县文化馆陈馆长陪同下,来到马文波将军下榻的宁德军分区招待所。稍事寒暄之后,老将军开门见山地向蔡作柯老人提出:“谈谈那把石达开佩剑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把宝剑有3尺多长,在剑柄的前面刻有‘青钢宝剑’4个字,剑身上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的确是件珍品。”蔡作柯老人平静地介绍说,“它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随身佩剑,后来成了我们蔡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我听蔡家的长辈说,每有祭祀活动,常拿出来舞弄它,日久天长,竟把剑柄上原来的漆带给磨破了。有一次,因为听说真宝剑削铁如泥,他们就找来一把砍柴刀,刀锋朝上放在条凳上,举起青钢宝剑,猛力朝砍柴刀砍去。结果,砍柴刀断了,而那把宝剑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把剑还在吗?”将军问。
“交上去了。”蔡作柯回答,“1956年,我们这里征集历史文物时,我亲手交上去的。”
“交到哪里了?”马文波将军追问。
“听说是中国历史博物馆。”
老将军停了一下,说:“来福建之前,我们已经查过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未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
原来此前,马文波将军曾叫丁德润大校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近代史组询问,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近代史组的同志提醒了一句:“请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查一查,如果确实上交了,说不定会收藏在那里。”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保存在太平天国京城南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马文波将军说:“那就请南京军区的同志帮助查一查吧。”
当天,电话通向南京,说明原委,请求协助。南京军区的同志热情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下午,回话说:“我们到太平天国馆查过了。馆方说,这里不仅没有收藏,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世上还留有一把石达开佩剑。”
……
“肯定是交上去了。”蔡作柯的语气也很肯定。
“有谁可以证明呢?”
“我们县文化馆的第一任老馆长可以作证。”
此时,坐在旁边的宁德县文化馆年轻的陈馆长插话了:“我没有见到过这把剑,但听老馆长讲过,是他经手送到当时的福安专署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宁德县属福安专区管辖。老馆长现在泉州,他可以证明。”
“石达开兵败川西,他的佩剑为什么会到你们闽东的蔡家来呢?”
马文波将军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关键所在。
“是这样的,”蔡作柯回忆说,“我祖父的祖父,也就是我们的高祖叫蔡步钟,在清朝的时候曾任四川雅州知府,官署就在今天的雅安。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正是雅州知府的辖区。石达开兵败被俘时,恰在蔡步钟任内,于是石达开的这把佩剑也就到了我高祖的手里。后来,我高祖被封为湖南按察使,有一年回乡养病,就把剑带回了宁德。这把剑乃是稀世珍品,他留下给长子长孙作为传家宝。我是蔡步钟的长门嫡孙,这把剑也就自然传到我的手里。”
这时,陈馆长对蔡作柯说:“方才你说石达开是‘兵败被俘’,恐怕错了,他是‘自投清军’,是降清。”
陈馆长也查阅了一些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就有记载:石达开“至大渡河,为川军唐友耕所败。至老鸦漩,势穷乞降,送成都斩之”。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印的《辞海》中也记载:石达开于“1863年在四川紫打地(今安顺场)失败,6月自投清军被杀”。
“不!石达开不是乞降,而是兵败被俘。”蔡作柯老人说话的语气很坚定,“我们家不仅保存了一把石达开的‘青钢宝剑’,还保存了一本石达开的‘口供’。这本‘口供’我看过多遍,那上面写得很清楚,是兵败被俘,而不是投降。”
“这本‘口供’现在哪里?”与马文波将军一起来的丁德润大校感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急忙插问了一句。
蔡作柯老人不无遗憾地说:“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口供’放在家里,后来找不到了。”
诚然,“投降”和“被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评说历史人物千秋功过的重要依据,也是与石达开荣辱攸关的大节。如果这份“口供”确如蔡作柯所言,那么翼王石达开的这段历史就应该重写,我们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位被“天王”洪秀全封为“五千岁”的“翼王”,应该重新做出历史评价。
虽然这份石达开的“口供”不是马文波将军要寻找的,但它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石达开佩剑保存在蔡家的真实性。这是马文波将军一行原先完全没有料到的。
马文波将军的调查仍在继续。在宁德三天,他又邀请蔡家几位年长的人来座谈,还找来当年与蔡威同在上海求学的女画家潘玉珂回忆与蔡威的交往……
三天查访,让马文波将军确信:宁德——曾经的福宁府,就是蔡威的故乡!
马文波将军提出,要去蔡威的故居看一看。
第三天晚饭后,蔡述波、黄垂超、陈国秋3人陪同马文波将军走进了蔡氏家庙隔壁的蔡威故居。
这座坐落在蕉城前林路文昌巷的深宅大院是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建的,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6扇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纵向多进,四周砌有高大的防火墙,其外观规模宏大,十分气派,具有浓郁的闽东地方特色。
蔡威就是在这座宅院里出生和长大的。
这时,蔡氏家庙连同蔡威故居被一个单位占用,居住着几户人家。
薄暮时分,灯光昏暗。马文波将军走到蔡威童年住过的房间,停住了脚步。
老将军沉默着,慢慢地抬起头,从上到下仔细观看,一句话不说,也不问。
他默默地巡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似乎在跟他逝去的老战友对话,悄悄地诉说着什么……
离开前,将军留下一句话:“地方政府要好好保护啊!”
因为将军的这一句话,于是,几经曲折,便有了今天的“蔡威事迹展陈馆”。
将军问剑,并不到此为止。返回福州后,马文波将军立即派他的两位助手前往福建省博物馆,寻查青钢宝剑的下落。
几天后,在福建省博物馆历史部藏品卡上,查到了这样一份记载:
项别:铁器
定名:(清)青钢宝剑
数量:一把
质地:铁
尺寸:(公分)长81.7,腰宽3.2,把长21
完残程度:铁锈、把纱带脱损
来源:福安专署文化科搜交
入馆日期:1957年12月
后来发现,福建省博物馆的这件藏品,有剑没有鞘。为什么呢?据说,日军侵犯闽东时,一个日军大佐不知从何处打听到蔡家藏有这样一件稀世珍宝——石达开佩剑,便上门搜查。蔡家人怎么也不肯交出这件传家之宝,谎说“剑已丢了”,只交出剑鞘搪塞了事。
日军投降后,时任宁德县承审员的胡尔瑛(福州人)登门观摩了这把幸存的青钢宝剑,偶发感慨,写下一首“七律”,题为《观石翼王剑口占》。诗曰:
慷慨河山百战中,燮门一溃负初衷。
十年如见横腰壮,三尺犹留杀血红。
成败事还归气数,摩挲我自拜英雄。
而今胡虏猖狂日,匣底伤心莫效忠。
诗末还有一注释:“邑人蔡步钟任四川雅州知府,与总兵唐友耕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乃得其佩剑。”
这是蔡氏家族曾拥有石达开佩剑的又一明证。
至此,蔡威生前在金川河边对马文波说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
马文波将军追寻石达开佩剑,不仅解开了1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谜团,更重要的是,一位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一个隐名了50年的密电破译奇才,一名被誉为“红军活菩萨”的功勋卓著的无线电侦察战士、闽东人民的好儿子蔡威的身世之谜,被发现、被揭密、被确认!
责任编辑 /陈 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