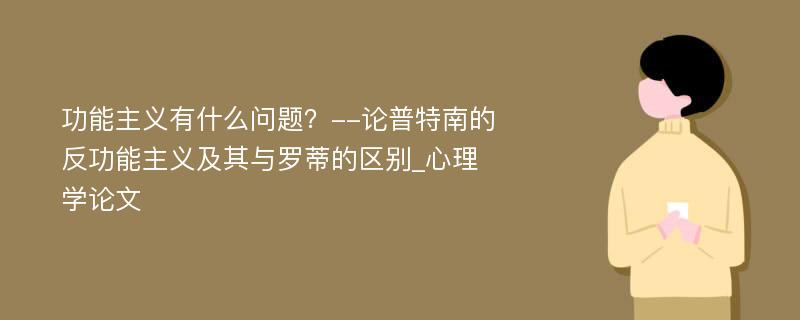
功能主义错在哪里——论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及其与罗蒂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功能论文,分歧论文,错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3-0057-07
普特南曾以创立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学说而闻名遐迩。他首次提出:人的意识活动可以还原为大脑的功能状态,而大脑的功能状态可以和计算机的功能状态相类比。功能主义的诞生,对“同一论”和“行为主义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并很快在当代心灵哲学的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在1985年前后,普特南出人意料地对自己的功能主义反戈一击①,提出了反功能主义的主张。这一转变是他后期整个哲学立场转变的重要一环。本文旨在阐释普特南这一转变的学理根据,并对罗蒂的相关立场提出质疑。
一、拒绝还原论
按照还原论的基本主张,高一级的学科可以还原为低一级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的话题可以还原为生物学、化学的话题等。毫无疑问,和斯马特等人的“同一论”相比,功能主义的还原论色彩大大减弱了。然而,它并没有真正摆脱还原论的基本思路,因为尽管功能主义反对将认知心理学还原为大脑的物理化学构成要素,但它坚持可以用这些构成要素所形成的功能状态来解释人的认知心理活动,这就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还原论。普特南对功能主义的否定,是从论证还原论何以不能成立入手的。②
普特南首先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混淆“推导”(deduce)和“解释”(explain)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从逻辑的角度说,一个系统的特性可以从它的基本粒子系统的描述中推导出来,但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它可以从那个描述中得到解释。”③如果要实现高级系统向低级系统的还原,则不仅要从低级系统中推导出高级系统,同时还要能解释它,而这一点,恰恰是低级系统难以做到的。
为说明这一点,普特南举了一个例子。设想有两个宏观物体,一个是一块木板,它上面有两个孔,分别是边宽一英寸的方形孔和直径一英寸的圆形孔;另一个是方形木钉,它的切面边宽小于一英寸。结果,木钉通过了方形孔而不能通过圆形孔。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可能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方式是,那木钉是坚固的,而那木板也是坚固的,木钉只能通过比自己大的孔而不能通过小的孔。在这种解释方式中,木板和木钉的微观结构是不相干的:不论那微观结构是什么,只要它和木钉、木板的坚固性不矛盾即可。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把木板、木钉看作一堆牛顿式的基本粒子,设想木板是“一堆粒子B”,木钉是“一堆粒子A”,再将圆形孔描述为“区域1”,将方形孔描述为“区域2”,然后经过难以想象的复杂计算,有可能证明“一堆A”将通过“区域2”而不通过“区域1”。这是一种还原论式的证明,但我们所需要的是这种证明吗?
普特南指出,解释必须是对有关事物的相关特点的揭示,而不是用一大堆不相干的信息将这些特点埋没。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第一种解释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一堆A”通过“区域2”而不能通过“区域1”,而第二种解释只是从基本粒子的位置、速度及其吸引、排斥等推导出作为背景的事实(何以会坚固,何以会是方的或圆的等)。然而,再由此出发对木钉通过方形孔而不是圆形孔进行证明,这种证明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解释。
为什么不能把第二种证明也看作是一种解释呢?普特南的理由大概是这么两点:第一,从逻辑的角度说,推导和解释是不能等同的。假定:我从G和I中推导出事实F,这里的G是真正的解释,而I是不相干的东西。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说“G和I解释了F”,而只能说“G解释了F”。现在假设,我们把G和I作一种逻辑的转换,产生出在数学上与G和I等值的陈述H,从实际角度说,G不可能由H中分离出来;这样,不论按照怎样的理性标准,H都不是对F的解释,但F都可以由H推导出来。在普特南看来,由基本粒子的种种性质来描述木钉和木板就类似于陈述H。在这种描述中,相关的信息,如木板和木钉的坚固性、木钉和木板孔的相对大小,都以一种无价值的方式被埋没在了不相干的信息中。第二,“解释是不能传递的”④。木板和木钉的微观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木板和木钉是坚固的,而坚固性又构成了关于木钉通过这个孔而不通过那个孔这一事实的解释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能推出结论,认为微观结构本身即基本粒子的位置、速度等解释了上述事实。在我们已经知道木钉、木板是坚固的背景下,木板孔的大小才是木钉能否通过这些孔的解释,而不是木钉和木板为什么是坚固的。“木板和木钉由按某种方式排列的原子所构成,这一点本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木钉通过这个孔而不是那个孔,即便它解释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反过来又解释了上述事实。”⑤解释是相关于背景的,在一种背景下是解释,但在另一种背景下它就不能再被当作解释而接受。⑥普特南指出:
解释的解释(可以说是解释的“前辈”),通常包含了第一种信息,它与我们想要解释的东西并不相干,另外,它如果也在某种情况下包含了相关的信息,那也是以一种或许不可能认出的方式包含了这些信息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种解释的前辈通常不是解释的理由。⑦
由此而导致的结论便是:“某些系统可以具有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与它们的微观结构大半不相干。”⑧普特南的观点是清楚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只要那木板是坚固的,只要那方形孔和圆形孔的大小是确定的,那么,木钉通过方形孔的现象就得到了解释。至于到底是构成榆木的基本粒子还是杉木的基本粒子在决定那木板的坚固性,则是个不相干的问题。
高一级学科对低一级学科具有一种自治,低一级学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高一级学科来说是不相干的,只有某些少数内容是相关的;是否相关不是由低一级学科决定,而是由高一级学科说了算。还原论者没有看到高一级学科的这种自治性,没有看到不止一种高一级的特性可以从低一级的性质中推导出来。
在一般地反驳了还原论的主张之后,我们来看看普特南的这一反驳在心理学领域或心灵哲学中,可能会导致怎样的结论。心理学问题能不能用生理学、生物学等法则来解决?甚至能不能最终用计算机功能组织来解决?普特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求先对“心理学”的意义给予澄清。既然认识要通过大脑来进行,当然可以从大脑功能组织的研究中来解释某些心理现象,比如像“痛”这样的心理现象便和生物学的研究密切相关。然而,更大量的心理学内容,也就是哲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所谈论的内容,如攻击性心理现象、智力、性倾向等心理学内容,却更多地或主要地和社会信念以及这种信念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相关。和心灵哲学处于同一层次的心理学是不能被还原为生物学、生理学等低级学科的。只要我们领会了普特南前面的论证,这里的观点当不难理解。生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当然也可以研究这类心理现象,一些哲学家也提倡并坚持认为可以把这类心理现象的研究还原为生物学、生理学的研究。但就像研究物理微观结构不能解释木钉何以能通过这个木板孔而不能通过那个木板孔一样,生理学、生物学的研究并不能解释这些心理现象,解释它们的是社会、文化。“主张独立于文化的固定的情感、态度等观点,很容易就能看出是令人怀疑的。”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傲慢”的心理,比如“优越”的心理,再比如上面提到的“性向”、“智慧”等心理,都和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普特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心理学之不能由生物学所充分证明,就如同它不能由基本粒子物理学所充分证明一样。人的心理部分地反映了深深确立的社会信念。这种主张的一个好处是;它使人们可以否定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有一种固定的人类本性,同时又不否定人类在生物学的层面是一个自然的种类。⑩
这样,普特南既保留了人类心理的自然基础,同时又否定了人类心理可以还原为这种自然基础,而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人类的心理现象。普特南最早提出这一思路是在1973年(11),这和他同时期在语义学上否定语词的意义可以通过讨论人的大脑得到解释,而倾向于从社会共同体、外在的环境中寻找答案的思路,是大体一致的。
二、否定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的种类形形色色,但基本主张大致相同,这就是普特南所说的:
心理状态(“相信P”,“期望P”,“考虑是否P”)也就是大脑的“演算状态”。思考大脑的恰当方式是把它当作一台数字式的计算机。我们的心理被描述为这台计算机的软件,即它的“功能组织”。(12)
按照这一思路,硬件的问题即大脑或计算机的构成质料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的质料可以有共同的“功能组织”。这就像计算机和人脑的构成质料虽不同,但却可以将人脑的认知心理活动还原为计算机的演算状态一样。于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质料比功能更重要,“什么”(what)比“如何”(how)更重要的主张便被动摇瓦解了。这一观点,即便在放弃功能主义立场之后,普特南仍然认为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用功能取代质料,而在于要更进一步,在心灵哲学领域里否定一切还原主义。不仅不能将认知心理状态还原到质料上,而且也不能将其还原为功能组织。“心灵不可能被‘自然化’。”(13)
功能主义的前提是,“信念”、“意义”是确定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可以和变化中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分割开来的东西,这样才能设想可以把它们还原为大脑的功能状态或软件状态。这一思路的错误早在普特南的《意义的意义》一文中便已被揭露。对此,普特南自己曾说道:“我的功能主义观点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它们和我自己在意义的‘意义’中所提出的关于意义的说明是不相容的。”(14)根据普特南在该文中所提出的论证,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其内容并不由个体说话者的内在性质所决定,而是取决于说话者所属的社会共同体以及这个社会共同体所处的物理环境。如果普特南的这一语义学理论成立,那么功能主义的做法便是行不通的。对此,普特南指出:
像哲学家们所说的“命题态度”,也就是如相信雪是白的,确切地感到猫在席上等这类事,并不是孤立于社会和非人类环境的人类大脑或神经系统的“状态”。而且,它们也不是“功能状态”——也就是说,不是可根据构成有机体的软件描述的参数加以定义的状态。被理解为主张命题态度只是大脑演算状态的功能主义不可能是正确的。(15)
按照功能主义的思路,两个认知主体可以被看作两个计算机模型。普特南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社会、文化和实践因素的加入,两个计算机模型本身不能说明同义关系,比如,这个模型说“官僚”,那个模型也说“官僚”,但两者的意义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意义的不同只能以社会实践环境来加以解释。
能不能采取一种类似卡尔纳普的做法,在一个形式化的语言中,通过定义的方式将一些句子规定为分析的,如“官僚就是政府机构中的官员”?普特南认为,这也行不通。因为除非已经有了一个同义性的标准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说的“官员”和你说的“官员”是同样的含义,什么时候我说的“机构”和你说的“机构”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否则,我们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所说的“官僚”是一码事情。卡尔纳普的方式会导致语义学上的无穷倒退。
能不能采用另一种思路来避免这种语义倒退?如果假定存在着一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是先天固定的并且是普遍的语词,如一些基本的观察语词,然后所有的语词都可以根据这些基本的观察语词加以定义,那么,分析的定义加上这些普遍的词义固定的基本概念,是否有可能解决说话者之间的意义沟通问题,还原是否就有可能实现?普特南指出,这样也不行,奎因已经使这一幻想破灭了:“奎因精心构造的‘gavagai’例子表明了同义性的麻烦甚至在观察语词的层面上也可能产生。”(16)面对同一环境,接受同样的刺激,并不能保证所用的语词具有同样的意义,原因在于,意义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划分世界的方式。
既然意义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说同样的话未必具有同样的意义,而同样的意义又不一定要同样的大脑功能作为基础,那么,放弃功能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反驳福德尔
在普特南转变立场之后,福德尔(J.Fodor)成了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此,普特南对于福德尔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对“普特南(我以前的自我之一)的反驳”(17)。
福德尔为躲避普特南“意义整体论”学说对功能主义的攻击,作出了一种新颖的回应。他把语言的意义或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个体化的成分”或“狭义的内容”,另一部分是所谓“外在的成分”或“指称”。福德尔认为,就语言的个体化成分而言,它的意义和某些知觉定型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计算机的语言(心灵语言“mentalese”)对它进行描述,这个知觉定型是超文化、超地域的;由于狭义内容可以用计算机语言(心灵语言)描述,因而是可以还原为大脑的演算状态的。但光是狭义内容还不足以决定语词的意义,因为由于语境的缘故,同一狭义内容可以和不同的指称(外在的成分、广义的内容)相联结,而只有在狭义内容和广义内容统一之后,语词的意义才得以被完整地把握。例如,我们可以说“榆树”、“山毛榉”,它们和某种落叶树的定型连在一起,具有完全相同的“狭义内容”,它们之间意义的不同不在于狭义内容而在于广义内容。“榆树”、“山毛榉”的狭义内容并不能使我们能够认出哪些是榆树哪些是山毛榉,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是专家(体现了社会劳动分工),然而,狭义内容也的确包含了关于榆树和山毛榉的可观察性质的一些具有实质内容的经验信息。按照福德尔的观点,社会劳动分工表明,语词的狭义内容可以包含一些关于所指对象的可观察性质的信息,但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使我们实际确定所指的对象。福德尔实际上是软化了原先的功能主义立场,不再坚持将信念、命题态度完全还原为大脑的功能状态,而只是主张信念、命题态度中的一部分即狭义内容部分是可以用中性的心灵语言来谈论的,是可以还原为大脑功能状态的。和普特南原先的功能主义相比较,我们不妨将福德尔的主张称为“温和的功能主义”。
但普特南并不接受这种温和的功能主义,在他看来,温和的功能主义同样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福德尔的主张如果要想成立,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项都有狭义的内容,而不只是那些对应于知觉定型的词项才有狭义内容。确实,福德尔自己曾经说过,除非每一个信念都有狭义内容,否则就不可能对它作出说明。(18)普特南抓住这一点,指出并非每个词项都有狭义内容,比如像“Zeitgeist”(德语“时代精神”)这样的词项,它并不和什么知觉定型连在一起,然而我们对它还是可以有一种信念(如“我们眼下所见的极端个人主义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如果还要说它有狭义的内容,那么这种狭义内容也只能是所指对象的可观察性质的函项,而不是什么超时空的可以用类似计算机语言的心灵语言加以描述的定型。(19)其次,知觉定型和对于一个词的理解并没有必然关系。比如,“知觉定型在翻译中并没有被保存,而且在某些场合下,对于翻译来说它也不是重要的”(20)。普特南指出,一个泰国农民所说的“meew”是暹罗猫,他的meew的知觉定型是“暹罗猫”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猫,但在翻译时,我们不会把meew翻译为暹罗猫,而是就直接将它翻译为“猫”。也就是说,我们把meew理解为所有的猫,而不仅仅是指像暹罗猫的那些猫。原先的知觉定型并没有保存在翻译中。他再举“女巫”(witch)这个词作例子。传统的“女巫”概念的知觉定型是“长着大鼻子和肉赘的又老又丑的女人”,然而,“女巫”这个概念的含义却不能等同于这一知觉定型,因为有一些概念内容比知觉定型更为重要,如“具有神秘的力量”等。所以,“知觉定型也许在心理学层面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就是意义——甚至不是‘狭义的’意义”(21)。
至此,普特南既指出了并非所有的信念都有知觉定型即狭义的内容,又论证了知觉定型和词项的意义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翻译中定型既不必要也不重要。这样,狭义内容不仅对信念来讲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它自己到底是什么都是无法确定的。就像普特南说的那样,福德尔等人“并没有提供固定一个词的‘狭义内容’的可选择的方式”(22)。于是,要把信念还原为狭义内容再把狭义内容还原为大脑的演算状态不啻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
四、令人困惑的罗蒂
普特南和罗蒂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明显,但在否定还原论这一点上他们是彼此呼应的。罗蒂曾经对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代表作《表象与实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我们至今所见的心灵哲学中对于还原主义的最彻底、最细致的批判之一”(23)。
罗蒂将分析哲学传统下的心灵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奉罗素、卡尔纳普为圭臬的“原子论派”,另一类是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的“整体论派”(24)。前者主张将心灵、语言看作可孤立研究的对象,把心灵还原为大脑,还原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对象,想一劳永逸地揭示心灵、语言的秘密。后者则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将心灵、语言作为固定的实体,认为科学的研究方式在此于事无补,心灵、语言只能放在历史、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理解心灵和语言,就是理解我们现在介入其中的社会实践的演变”(25)。
罗蒂所欣赏的整体论立场,显然和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事实上,普特南早在罗蒂之前就专门阐明过自己的整体论主张。(26)考虑到罗蒂对普特南否定功能主义代表作的高度赞誉,我们有理由认为,普特南是属于罗蒂心目中的“整体论派”阵营的,同时,也有理由认为,罗蒂也同样是否定功能主义的。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罗蒂最近发表的论心灵哲学的著述中,我们既没有在他的“整体论派”的“英雄榜”上见到他曾如此欣赏的普特南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对功能主义的任何批判的声音。在批判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原子论派”时,他的矛头所指显然是以斯马特为代表的“同一论”,而他所使用的论证居然来自普特南所放弃的功能主义!罗蒂的话是这样说的:
整体论者同意,关于大脑如何运作,会有很多发现,但是他们怀疑,关于心灵和语言,一个完美的神经生理学能告诉我们任何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心灵不是大脑就像计算机不是硬件一样。
整体论者指出,关于计算机电路的完美理解,对于理解你的计算机如何设法做到所有它所做的那些美妙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要理解这些,你就必须对软件知道很多。因为,计算机能运作很多很多不同的程序,而对于它当下运作哪些程序却漠不关心;同样的程序可以运作在许多不同种类的硬件上。根据整体论者的观点,心灵和大脑,文化和生物学,就像软件和硬件一样,彼此自由摇摆。它们可以也应该被独立地加以研究。(27)
在另一篇题名为《作为硬件的大脑,作为软件的文化》的文章中,罗蒂也明确指出:“文化是软件就像大脑是硬件一样”,“尽管软件每年越来越好,然而硬件却完全保持不变”(28)。
原先初看之下显得一致的普特南和罗蒂,其实有着重大的分歧。而分歧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文化当作软件看待?能否经过修改,继续保留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
罗蒂的基本观点是,心灵不能还原为大脑,因为大脑的物质结构可以保持不变,而心灵显然是变化着的;这种变化只能由文化、历史的演变史来解释。他继承了杜威“心灵是一意义系统”的主张,把这种意义系统看作是决定人们大脑运作的程序系统,即所谓的软件系统。我们的文化意义系统其实是决定我们大脑活动的关键,是决定信念、语言、意向性的关键。研究心灵,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这个软件系统。因为“软件正是运作硬件的一种方式,文化正是运作我们生理构造的一种方式”(29)。
普特南和罗蒂一样,反对把心灵还原为大脑,主张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理解心灵的内涵。他同样欣赏杜威的心灵概念,提出“心灵是一能力系统”。但是,普特南坚决反对把心灵还原为软件,反对将心灵理解为计算机程序。他曾多次批评罗蒂将文化语言共同体的标准程序化,以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就像计算机硬件和程序的关系,每个人不过是一个执行程序的工具。普特南指出:
罗蒂的想法是,许多谈话是受标准支配的,操一种语言的人依照该标准达成协议。……那些标准被比喻为算法,也就是说,被比喻为计算机执行的那种决策步骤。在这里,罗蒂所使用的方法与分析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我们将会看到,这不是罗蒂使用这种方法的唯一之处——不管他大肆宣扬与分析哲学的决裂。在解释某些事物在一个共同体的语言中如何为真和某些事物在该语言中如何为假时,求助于算法观念是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即使它仅仅是一个隐喻。(30)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分析哲学”指的是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幻想着寻找一种纯粹的科学方法,以此决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普特南称其为“唯标准观点”。初看之下,罗蒂似乎和这种观点势不两立,因为他反对科学主义的还原论主张。但当他把文化当作一种支配大脑运作的程序时,他就和卡尔纳普的立场殊途同归了,因为他同样要把意义、合理性等还原到一种程序上去,只不过这个程序和形式化的科学表面上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普特南说:
认为界定合理性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计算机程序的观点,是一种被精密科学激发起来的科学主义理论;认为界定合理性的仅仅是本地的文化规范的观点,则是一种被人类学激发起来的科学主义理论。(31)
两者没有实质的区别。
在这场罗蒂和普特南的争论中,笔者是站在普特南一边的。理由是,罗蒂的“文化软件论”会导致一种僵化的文化绝对主义。文化程序决定一切,犹如内涵决定外延一般,程序成了一种建构式的理论,当下的所有理解活动都只能还原到它那儿去。这样,程序成了一种新的“实体”,文化软件论成了一种新的原子论,它整个违背了罗蒂所倡导的整体论,又回到了一种准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普特南放弃功能主义的重要原因就是,所有的还原都是行不通的,所有的“内涵式”的思维方式都是应该放弃的。真正的整体论者或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应该始终坚持“实践优先”的立场,在文化意义系统和当下的实践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一种辩证的张力。诚然,我们所有的理解活动都离不开我们所继承的文化意义系统,它构成了我们当下理解活动的前提,是我们的“先验”理解结构。但是,任何先验的理解结构或罗蒂所谓的文化软件,都不可能固定我们当下实际的理解活动。实践的主体不是被动的计算机硬件,他/她永远有着在具体实践场景下对文化意义系统的解释问题,也永远参与着对于文化意义系统的修改、构造活动。罗蒂正确地指出,维特根斯坦是整体论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看作是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但罗蒂并没有真正领会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他片面地强调了维特根斯坦的“规则”决定论,而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遵守规则和具体实践场景、遵守规则和修改规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至此,原先关于罗蒂的困惑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了。他之所以对曾经如此欣赏的普特南只字不提,对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讳莫如深,原因就是,他还在追求一种把文化和大脑分别等同于软件和硬件的理论构造,还在做着准科学主义的梦。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追求,然而很遗憾,这个梦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也损害了罗蒂哲学的融贯性,为他的整体论罩上了阴影,使他在反对还原论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注释:
①这一判断的根据是:第一,普特南反功能主义代表作《表象与实在》(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的前三章来自于198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按推测,这两篇文章当成文于1986年之前;第二,普特南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曾说,该书的最早观点来自于1985年在普林斯顿的讨论。而在此之前,未见普特南有反功能主义的观点问世。
②普特南很早便意识到了还原论的问题。早在1973年,他就在《认知》(Cognition)杂志上以“还原论和心理学的性质”为题发表了反还原论的论文。当时他的主要批判目标是他自己早先的主张,即认为人可以被看作图林机,人的心理状态就是图林机状态或图林机状态的析取。他还没有意识到,要克服还原论,就必须彻底放弃功能主义立场。在他彻底放弃功能主义之后,他又重新将这篇文章收入他于1994年发表的《语词与生活》(Words and Life)一书中。
③④⑤⑦⑧H.Putnam:Wa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28,p.429,p.430,p.429,p.429.
⑥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什么是精确的解释时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目标’。”(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第5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⑨⑩(14)H.Putnam:Wo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38,p.439,p.443.
(11)见这一年所发表的“Reductionalism and Nature of Psychology","Philosophy and Our Mental Life”.前者载于Words and Life(1994),后者载于Mind,Language and Reality(1975).
(12)(13)Philosophical Topics,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Vol.20,No.1,Spring 1992,ed by C.S.Hill,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3,p.73,p.356.
(15)H.Putnam:Wo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44.
(16)(17)H.Putnam: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The MIT Press,1988,p.81、xiii.
(18)J.Fodor:"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Twin-Earth Problem",转引自H.Putnam: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The MIT Press,1988,p.131.,no.8.
(19)(20)(21)(23)H.Putnams: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The MIT Press,1988,p.45,p.46,p.46、back cover.
(22)H.Putnam:Wo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45.
(24)罗蒂心目中的“原子论派”的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是Noam Chomsky,Jerry Fodor,Steven Pinker,“整体论”的代表人物有Donald Davidson,Robert Brandom,Vincent Descomes,Jennifer Hornsby,Helen Steward,Arthur Collins,Lynn Baker.[cf.R.Rorty:"Holism and Historism",in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R.Rorty:"The Brain as Hardware,Culture as Software",in Inquiry,47 (2004),pp.219-235.]
(25)R.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77.
(26)关于普特南对整体论的论述,参见H.Putnam:Pragmatism:An Open Question,Oxford:Blackwell,1995.
(27)(29)R.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7,179.
(28)R.Rorty:"The Brain as Hardware,Culture as Software",in Inquiry,47(2004),pp.219-235.
(30)Hilary Putnam:Renewing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67.
(31)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136页,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