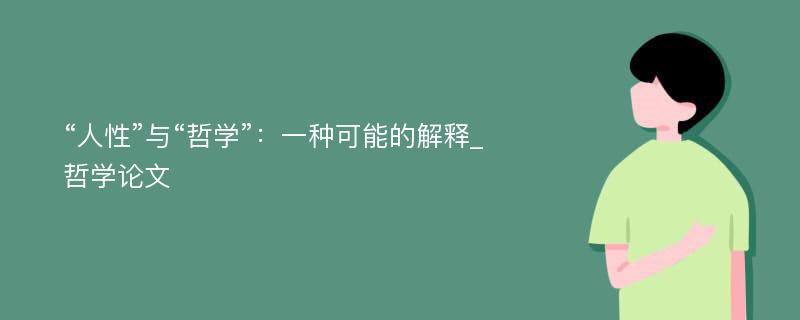
“人性”与“哲学”:一种可能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的自我追问,人性问题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对于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来说,它具有前提的意义。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1](P1)黑格尔也指出:“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2](P92)对“自我”的自觉确认,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把握,亦即对人之本性的揭示。因此,对于人及其存在来说,人性问题乃是一个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它同哲学的合法性(即哲学之所以“必要”和“可能”)问题内在相关。因为哲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最终有赖于人对自我本性的体认。
人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作为肉体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律的决定和支配;另一方面,人又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存在物,他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因而受道德律的决定和支配,正因为如此,人才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的存在者,从而具有尊严。也正因为如此,人的存在带有悲剧意味。因为人及其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为了消解这种二重化带来的二律背反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经验的意义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完成。对于人来说,这一点具有宿命的性质。
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使哲学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存在理由。首先,肉体构成精神超越的对象,由于人的肉体的存在,精神超越才是必要的。而精神超越本身就是哲学。所以,哲学仅仅对那些尚未实现精神超越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对于那些已经实现超越的人来说则成为多余。其次,精神对肉体的超越,也使哲学成为可能的。因为人的肉体存在是经验的,对肉体存在的超越意味着超验视野的获得。由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对于人来说带有本根的意义,而它又使哲学成为必要和可能,所以哲学的理由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在此意义上,哲学不过是人的本然的存在方式,而人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动物。
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哲学对人的存在及其二重化,都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洞察。罗素说:“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3](P378)而按照怀特海的说法,“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4](P82)《圣经》记载,圣保罗悲叹道:“我真苦呀!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肉体呢?……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服从上帝的律法,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5]耶稣说:“当归恺撒的归恺撒,当归上帝的归上帝。”[6]这些都不过是用宗教语言表达的人的自我反思而已。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扪心自问:‘你是谁?’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有灵魂肉体,听我驱使,一显于外,一藏于内。”“从亲身的体验,我领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新约·加拉太书》)的意义。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7](P190)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则说:“人有一个双重的本性,一个心灵的本性和一个肉体的本性。就人们称作为灵魂的那个本性来说,他被叫做属于灵的、内心的、新的人;就人们被称作为肉体的那个形体的本性来说,他被叫做为属于肉体的、外体的、旧的人。”[8](P440)但丁的《神曲》也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天堂地狱说”,“地狱”代表人的肉体本性,而“天堂”则代表人的灵魂本性。帕斯卡尔在谈到人的二重化时指出:“使得我们无力认识事物的,就在于事物是单一的,而我们却是由两种相反的并且品类不同的本性,即灵魂和身体所构成的。”[9](P35)荷尔德林说:“如果你有‘脑筋’和‘心肠’,那么,只表现两者之一就好了;如果你同时表现出两者,则两者都会诅咒你。”[10](P55)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是互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世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11](P156)康德区分了“现象界”和“本体界”,并在人的存在中寻求二者的统一。费希特把“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划分开来。黑格尔说,人“首先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其次他还为自己而存在,观照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为的存在,人才是心灵。”[12](P38)叔本华说:“生命呈现着两种状态,那就是外在或客观,内在或主观,痛苦与厌倦在二状态里都是对立的,所以生命本身可说是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二端中摆动。”[13](P14)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驾空于深渊之上。”[14](P8)雅斯贝尔斯说:“由于人将自己分为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心与物、责任与喜好、存有与现象、行动与思想、实际所为与行事本意等,他的见解也跟着有不同的意义。关键在于人总是要和自己作对。人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这种人格上的分裂。但是他并不满意这种分裂状态。他克服这种分裂的方法、他超越这种分裂所有的方式,在于显示出他对于自身的了解。”[15](P147)
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也有其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深刻体认。青年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就曾提出“精神原则”与“肉体原则”的冲突问题:“我们的一生”不过是“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16](P5)。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还提出“现有的东西”同“应有的东西”、“肉体本性”同“精神本性”之间的对立问题[16](P11)。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还提出了“经验的本性”和“永恒的本性”及其矛盾问题[16](P81)。所有这些,都奠定了马克思未来思想的“问题域”。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把人看作超越于自然界的存在,并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统一作为自己的理论旨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写道:“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7](P491)
中国哲学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也有着深刻的把握。《易传》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所谓的“形”,不是指外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指我们的形躯。所谓形而上或形而下,是代表生命的动向。“往上升越的路就是‘道’的路,往下凝聚的路就是‘器’的路,故一成道,一成器”[18](P4-5)。无论如何诠释,“道”与“器”的划界,显示了超验同经验的分野,它归根到底乃是人的自我意识外向投射的结果,从而在根本上折射着人的二重化结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明确划分了“不可道”之“道”和“可道”之“道”。“非”作为否定词使两种视野或境界的互盲关系凸显无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9]《庄子》也说,“生人之累”,“死者无此”。[20]《老子》还区分了“有执”与“无执”、“有欲”与“无欲”、“有为”与“无为”。庄子则提出了“有待”与“无待”、“形”与“心”、“物”与“道”的问题。孟子区分了“大体”与“小体”。佛教哲学中有所谓“色”与“空”、“此岸”与“彼岸”的划界。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更进一步展开了先秦的哲学问题。宋明理学的“天理”与“人欲”之争,同样也表达了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带来的本体论悖论。自先秦以来,“形”“神”关系问题就一直是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自觉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二重化,并揭示出它的悖论性质,这只是问题的开始,而非问题的结束。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显示的双重规定之间的关系怎样?它们对人的意义是否相同?若不同,其差别又何在?怎样理解“人性”才是恰当的?
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之间不是一种“平分秋色”的折衷关系,而是一种有主有从的关系。问题在于在肉体和精神之间,何主何从?相对而言,精神层面对于肉体层面来说有优先性(逻辑在先意义上的)和至上性(终极决定意义上的)。因为只有精神层面才能标识出人的特质,给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黑格尔说:“……但是作为人,我像拥有其他东西一样拥有我的生命和身体,只要有我的意志在其中就行。……我是活着而且具有有机的肉体这一点是以生命的概念和作为灵魂的精神的概念为依据的,……只有在我愿意要的时候,我才具有这四肢和生命,动物不能使自己成为残废,也不能自杀,只有人才能这样做。”[21](P55-56)只有人才能作出超越生命本能和生命极限约束的选择和决定。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的精神存在对肉体存在及其生物学规律的优先地位和超越关系。布伯说:“人离‘它’无法存在,但谁若仅仅同‘它’生活,谁就不是人。”[22](P51)对人之本性而言,人的肉体依然属于“它”。布伯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人只有超越了“我—它”关系,才能使自己从肉体存在的羁绊中提升出来。马里坦也提出:“在人身上,只有在精神和自由的生活占了感官和情感的生活的优势的时候,才真正算是一个人。”[23](P41)这一点,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那里已经得到过典型的表达。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之后,他完全有被保释出狱或逃走的机会,但苏氏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义务,没有逃避死亡,而是慷慨赴死,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人格。如果按照肉体原则和生物学本能的要求,逃亡是合情合理的。但若那样,苏格拉底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是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这是为苏格拉底所不齿的。中国的先哲也有对于精神存在优先性的明确论述。例如,孔子就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4]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25]其实,在肉体尺度和精神尺度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无以显示人的境界的高下;只有在它们彼此冲突、非此即彼的情况下,才能凸显境界的分野。孟子不仅划分了人的存在的两个层面,而且对其作出比较和评价,赋予其“大”“小”、“贵”“贱”之分,指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25]孟子还分别考察了“义”与“利”、“王道”与“霸道”、“劳心者”与“劳力者”及其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孟子都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这一立场体现着精神对肉体的超越。
人为什么必须追问“人性”?这是人为自己“立法”的需要。苏格拉底之所以特别推崇“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其用意大概在此。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及其悖论,使人对自我本性的确认面临着抉择。着眼于人的肉体存在,把人的生物学规定作为人性尺度和人的内在本质的立场,在思想史上一般表现为“性恶论”学说。在先秦思想家中,“性恶论”的代表当推荀子。他明确肯定:“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6]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道德只是人为的产物,而不属于人的固然之性,因而是外在的规定。荀子所说的“恶”作为人性规定,其基础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即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生物学性质。所谓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6]。所以,“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6]。此之谓“天”,不是“天理”,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然之性,而只是自然界赋予人的生物本能而已。因此,荀子说:“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26]按照荀子的逻辑,正因为人性恶,所以善对人来说才有意义。但这只是解决了善的必要性问题,却没有解决善的可能性问题。这是荀子性恶论的缺陷之一。另外,荀子的观点还抹杀了人的特质这一人性论的基础。所谓人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规定。尽管荀子表面上也强调“人之所以为人者”[27],但同孟子大异其趣。因为荀子固然把“礼义”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但“礼义”在荀子那里并不是人的内在特征和自律规定。如此一来,它也就不足以体现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了。人的肉体存在无疑构成人的存在的前提,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差异。”[28](P110)离开了人的肉体层面,人的精神及其超越也会因丧失其对象和背景而失去价值和意义。就此而言,肉体无疑构成精神的前提。但问题在于,“前提”并不等于“理由”。人必须“借助”肉体而“存在”,但并非“由于”肉体而“存在”。借用《庄子》上的话说就是:“生者,假借也。”[30]“借助”肉体同“由于”肉体完全是两回事,不容混淆。苏格拉底也说过:“诚然,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可是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有骨肉等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29](P64)苏氏认为,“没有分清原因和条件”乃是“一种严重的混淆”。而基于把人的肉体存在当作人性的内在理由的“性恶论”,就是犯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错误。
着眼于人的精神存在,对人性的预设则在思想史上表现为“性善论”的立场。就先秦思想家而言,如果说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那么孟子则可以说是“性善论”的代表。孟子把道德作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和基本标志,因为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30],差别就在于人有德性,即“良知”、“良能”。在孟子那里,人之本性也是不学而能的规定,与荀子不同的只是在于这种本能不再是生物学的规定,而是惟独隶属于人的规定。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31]按照孟子的观点,道德这一绝对精神价值乃是人的内在本性的体现和要求。因此,对于人而言,道德是内在的而大外在的,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5]。同时,对孟子来说,道德属于人之本体,而不是“用”,不是工具和手段的规定。这同荀子不同。在荀子那里,道德只是因为人性恶才有意义和存在的理由,因而不过是处在“用”的层面上的手段的规定而已。孟子反对告子所谓“生之谓性”的观点,意味着孟子主张人性尺度必须超越人的肉体羁绊才能凸显出来。告子把“食”、“色”作为“性”,显然是把人性的标准降低到了人的肉体层面。孟子针对这一点诘问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25]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32](P164)在这里,康德实际上提出了“自然律”和“道德律”的问题。它们分别对应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显示的两个层面。人的肉体存在,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必须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系生命活动及其延续。人的物质劳动就是这种交换的前提和表征,它受自然律的支配。人的精神存在,作为超越肉体存在的层面,属于绝对的价值世界,它适用于道德律。与此相应地,“自然”(取“自然而然”之意)有两种状态,即“必然”和“当然”。自然律是“必然”的;道德律则是“当然”(或曰“应当”、“应该”、“应然”)的。
在自然界中是无所谓“应当”的,因为自然事物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自主选择,它只是通过消极地适应外部环境而得以存在,因而表现为“他律”状态,即受异己的、外在的尺度的根本约束,从而是必然的。如同康德所说:“当吾人仅就自然过程而言时,‘应当’绝无意义。”[33](P400)人的肉体存在作为自然事物的一种形式,也不能不受到自然律的制约,如它必须符合生物学规律的要求。然而,由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人又面临着两可性,即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作出抉择的可能性空间。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最原始的根据之所在,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最初表达。正是这种两可性的存在,使道德律的现实表征成为缺乏保障的。道德律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人工规则。而人工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可违反性。K·波普尔在谈到人工规则时说:“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那么它是可以被违反的;如果它不能被违反,那么它就是多余的,没有意义的。”[34](P61)萨特也说:“那些承认规则的人,全部或几乎全部还是毫不犹豫地破坏规则。”[35](P312)陈康先生说得好:“规范性的原则并非不可违背的,乃是不应违背的。逻辑原则也只是如此;人的思想决不无条件地符合它们。”[36](P533)正因此,“应当”总是表现出某种“软弱性”。黑格尔就曾指出:“在这种‘应该’里,总是包含有一种软弱性,即某种事情,虽然已被承认为正当的,但自己却又不能使它实现出来。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就其伦理思想而论,从没有超出这种‘应该’的观点。”[2](P208)其实,这种“软弱性”不是它的缺陷,恰恰是其优点。因为正是这种可违反性的存在,才映现出遵循者的可贵。正是他们的抉择,赋予道德选择以崇高和尊严。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思想的芦苇”。
恰恰由于有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人才能够成为责任主体,善恶从而才变得有意义。黑格尔说:“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但当他作出自然的行为,顺从其私欲的要求时,他便志愿作一个自然存在。所以,人的自然的恶与动物的自然存在并不相同。”[2](P92)对于人来说,恶之为恶固然是由于顺应自然律的结果,但同时又是因为人也能够为善;善之为善固然是由于服从道德律的结果,但同时又是因为人也能够为恶。由于动物只是受自然律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对动物而言不存在善恶的问题,它不可能充当道德责任的主体。但人却不然。
那么,作为“当然之则”,“道德律”在逻辑上只有超越人的肉体存在及其体现的“自然律”才能得以确立和表达,但就人的现实存在而言,“道德律”同“自然律”必须达成某种必要的“妥协”,人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也就是康德试图寻求的“德”与“福”的统一。问题在于,一个具体的人在其现实生存中,究竟应如何恰当把握“应当”呢?这也是困扰哲学家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倘若“应当”同自然存在(它体现人的肉体原则)相妥协,那么将如何判断肉体欲求的合理界限呢?宋代理学家朱熹说:“饥者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37]他认为,“私欲”乃是“不当如此者”;而“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又此欲岂能无?”因为这是“合当如此者”[38]。可是,应饥之食与“美味”的界限究竟何在?维系生命基本需要的“度”又如何把握?由于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而是因时因地而异,因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古代看来是奢侈的需要,也许到了今天已成为最基本的生存欲求了。这种相对性使合理欲望的确定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难怪庄子早就发出过慨叹:“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天下之正色?”[39]“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40]据记载,宋儒二程兄弟同赴宴,座中有妓,程颐拂衣而去,程颢视而不见,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日,二程言及此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笑道:“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心中却还有妓。”程颐愧服[41]。这个事例说明,如果像程颐那样毫无妥协,恐怕连正常的生活都要拒绝,而不仅仅是有妓无妓的问题;如果像程颢那样丝毫不改变生活的外观,而是仅仅改变看待生活的方式,那么他的精神超越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这个难题在古罗马思想家圣·奥古斯丁那里也有着深刻的反省。他遇到的困惑是:“为维持生命本已足够的,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难确定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而进食,还是受饕餮的引诱而大嚼。我们这个不幸的灵魂对于这种疑团却是正中下怀,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维持健康的节制,乘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美名来掩盖口腹之欲。”[7](P213)奥古斯丁的困惑同样源于人之“自然而然”亦即“应当”的界限的难以确定。
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相对应,对人的存在的定位也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经验的知识论的视野;另一种则是超验的形而上学的视野。前者由于是一种错置,它只能导致对人的本性的扭曲或遮蔽。人的肉体存在同经验论立场具有内在关联。首先,经验视野所能发现并捕捉到的只能是人的肉体层面和生物学性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性论也只能是“性恶论”。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完全按照道德尺度践履的人终究是少数,正因此道德楷模才显得尤为可贵。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绝大多数人需要满足的是肉体层次的欲求,而能够超越肉体需要去追求精神需要的自我实现者总是极少数,从而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如果从经验立场出发,按照归纳原则加以概括,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性就是人的肉体存在所决定的生物学性质。从历史上看,性恶论往往体现着经验论立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以先秦思想家荀子和孟子为例,荀子的哲学带有明显的经验论色彩,它特别强调“辨合”和“符验”。荀子说:“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42]荀子为了替性恶论作辩护而批评孟子,倒显示了他的经验论立场同其性恶论的内在一致。性恶论肯定的乃是人的肉体层面,这与人的经验存在相契合。由于对人的生物学性质的肯定,基于性恶论所作的制度安排,总是在经验意义上具有明显效果;而性善论的超验性特征,却使它自身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故荀子认为孟子的主张难以取得经验效果。但诚如陆九渊所言:“学问须论是非,不论效验。如告子先孟子不动心,其效先于孟子,然毕竟告子不是。”[43](P50)不仅如此,甚至如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4]对性恶论来说,道德价值完全是一种外在于人之本性的他律规定,这同以经验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论关于主体—客体的对象性框架的预设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主体—客体的对象性框架内,主体无法摆脱来自客体这一外在他律的根本限制。
其实,反思和揭示人的本性,不是一个经验描述和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逻辑设定和规范性的问题。因此,它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选择如何,也不取决于多数人在事实上的状态如何,而仅仅取决于人之所以为人者所要求于人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康德说:“划分那以经验原理为其整个基础的幸福论和不允许丝毫经验原理掺杂于其中的道德学,乃是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的首要任务。”[32](P94)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并不是一个知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人类学本体论的命题。显然,那种“把‘认识你自己’看成关于人的知识的出发点,而这些知识又通向那些属于新类型的科学,并准备把在自然科学中成功地使用过的方法运用到人的研究上”的企图[45](P65),完全背离了苏格拉底的本意。赫舍尔说得好:“在提出关于人的问题时,我们的难题并不是人具有不可否认的动物性这一事实,而是人的行为之谜,而不管其有无动物性或其动物性有多少。关于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同动物王国有什么共同点,也不是由于人具有从其动物性中派生的机能。”[46](P20)雅斯贝尔斯也指出:“一旦他(指‘人’——引者注)成为知识的对象,就绝对不再是统一体和整体了,也绝对不再是人的。”[47](P154)在对人和人性的把握上,性恶论及其经验论立场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它遗忘了“人是试图认识自己的独特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试图认识的不是他的动物性,而是其人性”[46](P21)。把握人的德性,就无法绕开超验性的“纠缠”,这在苏格拉底和康德那里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总之,人性论上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分野,昭示着经验立场与超验立场的对立。人性论预设同哲学视野的选择是互为因果的。它最终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一般地说,性恶论及其经验立场形成了实证论传统,性善论及其超验立场则塑造了形而上学传统。从思想史看,实证论传统陷入了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而是一种“伪哲学”。它不仅堵塞了人的自我意识之路,而且也遮蔽了哲学之本性,因为它执着于“在者”而遗忘了“在”本身。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尤其是观念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由这一传统负责,特别是它的道德观和自由观。只有当实证论传统得到彻底清算之时,形而上学这一真正的哲学视野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展现。它为人性的重新发现提供了可能。当然,这还需要历史本身为其做好足够的准备。
标签:哲学论文; 人性论文; 孟子论文; 荀子论文; 性恶论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二重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