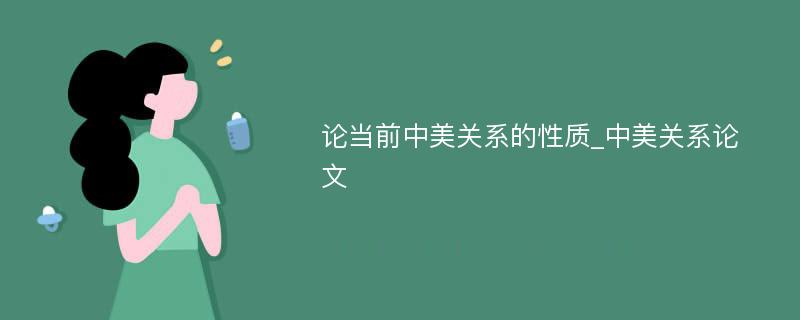
当前中美关系性质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到底为何?中美两国学者为此煞费苦心,围绕“战略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人”、“非敌非友”等等定位曾展开激烈辩论。但大体从1997年开始,随着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似乎成为中方对“定位”问题的主流看法;而随着不久前小布什所谓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的提法被正式纳入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时下“最流行的美中关系用语”,似乎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美国的主流共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呢?
一、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布热津斯基说过,美中关系“具有催化作用”,(注: Zbigniew Brzezinski,"Coping with China",National Interest,Spring2000.)如果这一关系发生变化,除美欧关系外,美俄、美日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变化,这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我国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注:阎学通:《冷战后的延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 )这是从双方的冲突和矛盾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克林顿多次强调,美中关系的发展“攸关21世纪美国人民的福祉”,这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两国关系的战略性。总之,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深具战略利害,这已成为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共识。
而这种战略利害性从表面上看,似乎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双方要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大目标,离不开对方的配合和协调;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又需时时防范对方的潜在破坏或挑战,或者更进一步说,一方国家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很可能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国家根本利益为代价。比如,美国要实现“世界领导”梦,必将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与其“平起平坐”,必将推行它那一套民主人权价值观,这就与中国追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根本目标相悖。反之亦然。
这一悖论实际上涉及到贯穿近现代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两个重大课题。一是守成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如何共同相处;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如何避免冲突。19世纪末美利坚帝国崛起过程中与大英帝国的矛盾冲突,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分别反映了这两种情形。在前一情形中,尽管美英同文同宗制度相同,英国当时陷入外交孤立而无力西顾,但双方“关税战”、间谍案、小规模冲突仍时有发生,而美国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则可说是美国代表的北方和英国支持的南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战(注:[美]J.布卢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版。)。“日不落帝国”的衰落和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是在摩擦、矛盾和冲突中完成的。显然,双方没有找到繁荣与共、和平相处的有效途径。美苏之间更是在势不两立中以一方的“惨败”而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略竞争状态。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用比较消极的眼光看,不仅集上述两种矛盾于一体,而且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这正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后近十年的“磨合期”仍具不确定性的原因所在。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一方面,美国有关中国的大辩论一直都在进行,但对中国却总难作出准确的战略定位,因而“非敌非友”、“潜在敌手”、“竞争对手”等等说法,不一而足。(注:有关这方面比较集中的讨论参见: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o the 21st Century —— An Asian Studies Center Symposium,November 21,1995",Heritage Lecture No.551.)另一方面,中国在判断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时,也多少存在同样的问题。用“西化、分化”一言以蔽之,似乎稍嫌陈旧、简单,但要相信美国政府宣称的“一个稳定、强大、繁荣、开放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注: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思今年5月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所作的演讲,题为“21 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又未免将信将疑甚或自欺欺人。不能不承认,中美正式交往时间虽然已经不短,但由于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不断变化,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始终在摇摆游移之中。
1997年中美两国首脑达成的“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从深层次讲,其实是两国领导人希望跳出历史的窠臼,为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规划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合作关系的努力,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第一,它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并表达了双方不希望走向对抗而希望实现双赢的良好愿望。诚如美国前总统布什评价的那样,美中两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保持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良好关系对世界和平最为有利,对美中两国人民的繁荣最为有利。(注: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书面采访,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8月21日电。)第二,它为处理两国关系首次确立了从首脑热线到人权对话机制、从军事交流到执法合作的全面、系统、有效的框架。正是由于这些框架的建立,才使得两国关系不因困难而倒退,历经风浪而前进。
但须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框架在表达良好愿望、展现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包含相当程度的“实利主义”成分。从美国方面看,和欧、日等“冷战朋友”巩固同盟关系,与同中、俄、印等“转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是其新世纪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注:"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Institutef 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0.),功能虽然不一,地位却同等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北约一俄罗斯“和平伙伴关系”、美印“新型伙伴关系”,都只是美全球战略布局题中应有之义,服务于其“参与、领导”的全球战略总目标。其在双边关系中的特殊意义,因而不宜被估计过高。从中国方面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同世界主要国家构筑的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也都共同服务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准则和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的总体外交目标,同样含有美国学者宣称的所谓“策略”的成分,因此,在看到其重大战略意义的同时,在现实关系的应对中不宜对此作不切实际的幻想。
简言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只是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期待,不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定位;是主观需要的结果,不是客观现实的描述。
然而,这一实质显然没有被所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国内许多报刊杂志上,“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具有多重限定的提法,往往被简化为“战略伙伴关系”六个字,并被用来描述或理解当前中美关系。这种简单化的做法看似言语上的简略,实则反映了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简单、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以“战略伙伴”标准来衡量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状况,自然就会对“考克斯报告”、“炸馆事件”以来一系列事态产生困惑,进而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在“炸馆事件”后,某国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慰问电里,就用了“美国对自己的‘战略伙伴’尚且如此”这样的语句,表明上述“简略”不仅对国内也对国际社会至少造成了认知上的偏差。
二、“战略竞争对手”说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是小布什等人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呢?
首先,对“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概念本身不宜作简单否定或排斥。不仅因为这一概念被许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认同,而且在逻辑上也站得住:(1)如前所述,中美关系构成了“战略关系”;(2)从本质上说,国与国关系就是“竞争关系”;(3 )“对手”不等于“敌手”。“竞争对手”本身是个中性词。正如一家美国媒体所称,大国竞争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和平调整分歧”(注: 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 23,1999.);小布什也一再强调,此一定位只是表明对中国“不怀恶意,但也不抱幻想”(注:参见美国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对外关系部分,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英文电。)。其次, 当我们仔细审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时,会发现,在涉及双边关系的几乎各个重要领域,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确乎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国际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则希望建立“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搞所谓“霸权稳定”。
安全领域,第一,中国倡导“相对安全”或曰“共同安全”,美国则显然在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双方在NMD和TMD问题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两国安全观的不同。第二,中国主张利用多边合作对话(比如“上海五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则仍不肯放手双边军事同盟。美国人爱把北约说成是多边或集体安全机制,但在北约这一多边组织的形式之下,体现的还是地地道道的美欧双边军事同盟的实质,根本不是中国倡导的“集体安全”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外交领域,中国积极发展“睦邻外交”和“伙伴外交”,通过前者,中国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换来了相互信任和共谋发展的局面;通过后者,则与世界主要大国构筑了形式不一的“伙伴关系”,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美国则惯搞“制衡外交”和“同盟外交”,“以邻制邻”、“海外制衡”地缘战略思想仍显见于美国冷战后的外交实践和新世纪的外交布局(注:袁鹏、傅梦孜:《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 一些美国保守派学者还把中国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理解为中国想重新构筑以“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从而最终埋葬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同盟(注:Larry M. Wortzel,"U. 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The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December 1998.)。
文化意识领域,中国坚持“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则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对所谓“人权”、“民主”的捍卫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而和平共处,美国则认定它那一套制度是全人类理应追求的目标。而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希望长期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战”局面,以利美国继续居中制衡、渔翁得利;中国则希望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伟业。
从上面这些比较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够得上“战略竞争对手”关系。较之“建设性战略伙伴”或“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局面”等提法,“战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因而不失为一种相对客观、准确和简练的表述。但问题出在,小布什在用“战略竞争对手”一词时,却不仅仅是对美中关系现状客观的定位,而更是出于对未来对华政策取向的定调,它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太过“虚幻”,应当舍弃;第二,克林顿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显得一手硬、一手软,且缺乏必要的政策连续性,必须修正;第三,对华政策应追求“均衡发展”(even—handed),“接触政策”还应继续,但在接触同时必须更强化遏制一手。用小布什自己的话说,在“没有恶意、但也没有幻想的情况下同中国交往”的同时,需要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注: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 ·布什1999年11月21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报界”节目记者采访时的讲话。)。可见,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对手”说所具的主观意识和政党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受此影响,其对华政策取向是消极、低调的,与目前两国领导人努力追求的方向显得背道而驰。
显然,如果用来描述当前中美关系的客观状况,作为理性处理中美关系的起点,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关系这一判断本身没有错。事实上,“战略竞争对手”作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本身存在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走向“合作式竞争”进而缔造“战略合作”关系;一种是变成“冲突式竞争”最终演成“战略对抗”状态。前者追求“双赢”,后者导致“双输”。21世纪中美关系的理想结局,应是追求前一种局面而避免后一种结果。这正是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初衷所在。但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对手”观,则从主观意识、政党利益出发,辅以浓厚的大选色彩,似乎更多强调美中双方的“战略对抗性”,并对两国战略合作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和悲观。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不能被中国学者所认同。
三、中美是“新型的战略竞争关系”
除了政治因素作祟外,美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或者排斥,是导致小布什“战略竞争对手”说泛滥的又一重要原因。比如美国许多人,包括布热津斯基等对中国素有研究的著名学者, 总爱把今天的中国与1890年前后的德国相提并论。(注:比如布热津斯基就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之间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Coping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对了解当年德国历史和当前中国现状的人来讲,这一比较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和不负责任。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状况与上一世纪之交(内战至“一战”期间)的美国更为相似。双方都在实现经济腾飞,都处于“大转折”的时期,都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美国则从“自由放任”朝“国家干预”倾斜,双方转轨方向相反,但追求的都是在市场和计划间达致均衡这一总目标),都在朝“国际化”迈进(美国是逐步调整“孤立主义”政策积极涉足海外事务,中国是高举“对外开放”旗帜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注: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用这样一种视角看待中国, 相信美国一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保守派人士对目前中国的崛起会有新的认识。
因此,当我们谈论中美是“新型战略竞争关系”时,参照系不是美国人爱提及的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而主要是前面提及的上一世纪之交的美英、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对战略竞争关系。我们通过比较会发现,与美英战略竞争关系不一样的是,当年美国迅速崛起时大英帝国正急剧衰落;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同样在迅猛崛起,美国则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因信息革命迸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仍然处在综合国力全面上升状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约1/4,假设美国综合国力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分别为7%、6%、5%,中国要达到美国同期综合国力水平所需的时间将分别为36年、47年、70年(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第7期。)。也就是说,在至少20年内, 中美的战略竞争将是极为“不对称”的。这便为两国共同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与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相比,则更有多种不同:(1 )美苏争霸是全球性的,中美竞争则充其量是区域性的。苏联当时是全球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中国今天还只是个具有一定国际政治影响和文化魅力的亚太区域性大国,中美矛盾、冲突的许多方面仅局限于亚太。(2)美苏争霸是集团对集团,中美竞争则更多属“单打独斗”。冷战时期的美苏主要通过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动用集体的力量展开争夺。苏联一直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中国的外交原则则是“不结盟”。除多极、单极这样涉及各自国际政治理念方面的分歧外,今天中美两国的主要摩擦和问题主要集中在双边领域。(3 )美苏争霸是“零和游戏”,中美竞争则具“双赢潜力”。军备竞赛、军事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等构成了美苏关系的主旋律;而政治交往、军事对话、经济合作则基本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流。
此外,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注: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 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的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9月14日电。 )布热津斯基在解释这种区别时说,苏联代表着对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民主国家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扩张主义的军事威胁;中国则并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从意识形态上向美国挑战的能力;中国没有参与任何重大的国际革命行动,而驱动其军火出口的,是商业利益或双边国家利益,而不是一种军事扩张。(注: Zbigniew Brzezinski,"Coping with China",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还有人注意到,苏联闭关自守, 因而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几乎与世隔绝;中国却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开放对外贸易并且吸引外来投资。(注:[美]吉姆·赫尔姆斯 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和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序,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
如果再做深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历史上的战略竞争关系相比,今天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还有两个最根本的不同:一是时代不同。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种时代里,“对手、规则、主战场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语)(注:Madeleine
K. Albright,"The Test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8.P.51.),国与国之间既是合作伙伴,同时又是竞争对手,而这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往往随着领域与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奥妙之复杂,谁也无法完全把握。在这种情势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非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比。就中美两国而言,任何一方都无法承担战略对抗带来的巨大代价,避免对抗寻求合作因而成为双方必须的选择。二是基础不同。中美关系20年的历史虽然曲折起伏,但两国关系螺旋式上升的总体发展态势却十分清晰可见。这正是中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础所在。
总括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其发展前景应是双方最终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大国合作“双赢”的新局面。至于如何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则显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中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