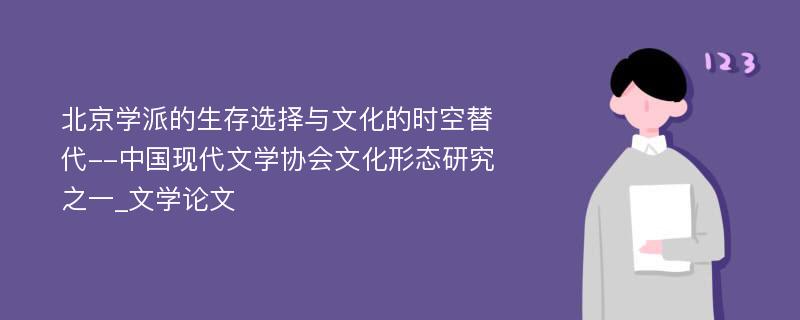
京派的生存选择与文化的时空置换——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形态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文化论文,流派论文,社团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 (1999)04—0072—07
“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从具体的时间和人员上都很难明确界定的一个松散的流派。正是它的整体呈现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使之成为这些年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热点。确切地说,从社会学、纯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个流派的成果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最早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专章论述;许道明的专著《京派文学的世界》(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京派文学批评观、散文、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论文。这些成果对京派在文学史中价值、地位的充分肯定,尤其在群体文学创作个性方面的分析,有学术研究的开拓性,特别对于整体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是,我认为对任何文学群体的内涵和外延的价值判断,或者本体的深入认识,并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和文学两极视点能够说透的,尤其对一个对象本身就较为复杂、研究又多有分歧的文学群体,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也可以在多维视角里切入对象本体,进一步考察其文学群体深层的文化意蕴。京派的研究无疑还有相当大的空白领域有待开垦。这里我们将“京派”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整合的语境中,侧重它的文化生存时空的群体本源形态的考察。京派群体文化内涵与文学个性的关系以及文化语境里的京派文化价值取向,对其文学的价值的影响和群体的个性形成的意义,是我们试图对这个文学群体作出新的探索的基本目标。
“京派”的由来,许多研究者已经明显看到“地域”因素实际在这个群体并不占为主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某种文学口号,甚至有意识的结社成派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文学史又确切可以清理出有这么一批作家群体的存在,一些当事人、文学史家也都有认定京派的文字。这就使我们要提出问题:群体名称的鲜明地域性与并未有多少实质性地域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无意识的聚合结社,却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流派,其真正个性价值是什么?只有回归它生存的文化故里,才能还原其生存的原貌。
文化语境里的“京派”,既是文学运作过程的文学群体,又是文学群体的文化整合。我们必须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探寻这个文学群体的文学特质、文化意蕴及其生存形态。我理解京派群体的文化现象,是以一系列的转换方式表现其文学社群的特征的:地域转换的虚实相间;观念转换的现代与传统的互补;生命形式转换的人生与艺术的同构。
京派:文化的原生态
“京派”地域转换中的生存时空:“虚”与“实”的原生态。京派缘起于晚清民初的梨园京剧、中国绘画流派,而在现代中国文坛叫响,是30年代初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公案。这里先不作“公案”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让我们从它生存形态的两个方面:自然生态和社会接受生态的具体表现内容入手。首先从本源的自然生态看,今天所谈论的京派文学社群,主要一脉相承于20年代中期滞留于北平的语丝社、新月社部分作家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同期在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部分师生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等;先后在《骆驼草》周刊(周作人主编,1934年创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沈从文主编,1933年在天津创刊)、《文学季刊》(郑振择、章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水星》文学月刊(巴金等编辑,1934年创刊)等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作为京派一分子的箫乾是这样概括的,他以1933年为界将其区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周作人为盟主,后期则以沈从文、林徽因的影响最大(注:《文汇报》1990 年5月1日。 )。朱光潜后来回忆沈从文的文学活动时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这两个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注:《花城》1980年第5期。)京派的形成,就其客观的本源, 并不是传统自然生态的血缘衍生的地缘群体的生存形态,这与前面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来自比较集中的江浙沿海地区不同,地域的概念对于京派群体主要是自然生态的“虚”化,异地文化圈的“实”体参照系,因为,上述格局的定位,从京派的原生态的自发群体而来。最初的群体形式没有丝毫过往地缘的乡情聚合,而是在相对隔绝的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圈内,具体说校园文化中较为普遍的文人雅聚、学术交流的沙龙和俱乐部等聚会。比如,京派成为流派之前,1924年前后,闻一多家中时常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徐志摩、胡适等经常在松树胡同七号定期举行聚餐会的俱乐部;周作人的八道湾的“苦雨斋”以《骆驼草》的刊物作者为主的常常聚会的新老“骆驼同人”。这种小型的文学圈子,甚至到30年代中期,北京东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沙龙”;北大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中按时聚合的“读书会”也未有间断过。京派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生态的文人聚会场所里孕育成流派的。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都市的精魂,他们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文化风貌及精神气质。这是超越群体人员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地域环境,在新的聚合地京城文化、校园文化、学者文化中所孕育的。因此,京派的生存形态在社会接受生态的内容,就推动了他的文化精神的传播和流派的约定俗成。尽管是以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坛论争引发的,但是,本质上表现了文化孕育过程中自然生态的必然走向,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化的文化状态充分展露的契机。这里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京派与海派”之争的问题上。我认为,这场文坛之争凸起的京派,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的,北方的京派生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于南方的海派,文化语境区别较大。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由北向南转移,政治斗争的中心地上海,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策源地,这里充满浓重的政治火药味。从文化氛围说,现代中国商业化的都市上海,文化状态自然迥异于北方。所以,最初的两派的争论多有传统文人相轻的情绪,彼此互不相让。沈从文说“海派”作家“名士才情+商业竞卖”,是“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而“海派”指责“京派”作家“独揽风雅”、优美,不能实实在在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我认为,这场“京派与海派”之争中,是上海左翼作家的参与论争和鲁迅的撰文,促使了京派的群体社会接受生态的成熟,即京派的群体形态完成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京派的虚化的地域因素转换成了实体的两地作家的尖锐对立。左翼作家在论争中,强调了京派以纯文学的超然政治、现实之外的态度不合时宜。鲁迅从两地文人不同生活环境和内在的文化机制中,以冷静透视两派的劣处为主。“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者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注: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显然,前者的政治标准,扩大了京派社会内涵的影响,而后者的文化地域的审视,凸现了京派文化的理性思考,这就使得本来自生滋长的群体,一下子具有了党派意识,有目标的要聚合起来排他,保持自己的群体,集团意识鲜明了。京派正是在一系列外来文化圈子对其劣处的披露中,增强了处在自身群体的个性特征的展示。诸如,批评京派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以及冒充风雅等等,多有嘲弄讽刺之状。自然京派论及海派也不乏过激之词。
京派的生存形态从一个借代的名称到形成实体的文学流派,它由虚变实的过程,正是群体生存形态的本源自然生态和社会接受生态的互动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原生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换过程。京派的文学史的定位,这些年更注意其文学群体的本质精神的社会化的分析研究,进行历史的本源的社群生态的考察,特别是文学群体生态的内在探讨,使得京派的本体逐渐得到还原。我们在进一步思索它的丰富本体时,愈来愈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地域文化视角独到而有睿智的评析,同时,也看到这一视角尚有深入探讨的可能。如果从鲁迅对京派的劣处分析,转为全面的文化透视,那么,京派的文学史面貌会更加鲜明。
京派:乡村与都市
“京派”地域转换中的生存时空:都市魂灵、乡村情结的文化意蕴。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存形态应该是动态的过程呈现其活力,而动态根本性特征是主体的参与,是彼此活动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形式。为此,京派群体文学观念、人生态度、创作内容等揭示出的地域文化的内在意蕴,就是其最有活力的生命形式。我认为京派的生命本体存在,就在于它的一切行为准则和方式,都表现为都市与乡村精神现象的整合。
首先,京派的观念形态的生存内核,表现为对人的自觉、文学的自觉的崇尚。这一基本的思想建构了京派群体的凝聚力。京派以传统士大夫就欧美贵族绅士的朋而不党、超脱潇洒的人格,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有了在沙龙和客厅里的文学,即强调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既不满自封在象牙之塔里的为文艺而文艺,又对文艺仅仅作为人生的宣传和工具持否定态度。京派对文艺的宽宏的思想源于他的文化思想指导,他们认为文艺产生在一种文化生发期,即在外来影响的刺激下的启发和扩大的视野,对旧文化的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是从传统习惯解放出来的思想无所拘泥地向各方面探险的活力,是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的生发过程。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时,就明确提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文艺的兴趣和热诚”(注: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1937年5月。 )。追求艺术的独立品格构成了京派的文学观念的精髓,群体的生存原则正是建立在彼此这种无意识趋同的一致性文学理想上。纵观京派群体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文学主张,可以发现他们是在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冲突面前,努力建构一个文化融合中的自足、自重、和谐的艺术天地。沈从文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小庙供奉的是‘人性’”(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还以自己“湘西世界”的独特创作,实践他的独立的艺术理想的追求,典型地描绘了京派群体的艺术理想的蓝图。他的原则宗旨,他的态度作风,他的情趣,都是京派文学审美的“自给自足”的精神代表,其他作家在此基础上遵循并丰富了京派的艺术理想。李健吾、朱光潜也在其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中,表现出完整、独立的审美世界,是他们信奉的标准和理想,“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须成一种自足的存在”(注:李健吾:《神·鬼·人》。)。“艺术所摆脱的是日常繁复错杂的实用世界,它所获得的单纯的意象世界”(注:朱光潜:《形象的自觉》。)。京派作家不仅仅全身心投入艺术“自足”的建构,而且还努力达到艺术的精美。京派作家沉浸于艺术的完美形式和构架的营造。朱光潜、冯文炳、箫乾等作家每每地表达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应该是均衡和谐的思想。艺术美的追求形成了京派群体生存发展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与群体生存的文化语境达到了契合。
其次,京派以独特的人生态度表现了与其文学思想的一致。京派群体地域文化尽管表层并不决定其形成流派的重要因素,但是它生存的这块土地是与这个精神现象的出现有联系的。京派的独立艺术的文学观念的群体核心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在于他们人生态度形成的文化语境。京派的自足、和谐的艺术世界的营造,基本源流来自他们对人生的看法。然而,京派的“人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主张,相反,“不为”的态度形成了它的独立和个性。“为人生”强调了文学对人生的制约作用,人生目的是创作的主要衡量标准。文学像人生一样实际,阐释文学变成了阐释人生。这是五四过后现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对文学的一种要求,不无正确。京派作家生活在京城,又大多数呆在相对隔世的校园里。因此,尽管政治时局依然动荡,但是却不乏文化的自由和宽松。京派作家并不是忘却了人生,而是有了另一种人生的解释。文学对于人生是自然的、自为的,不是强硬地结合和服务人生。朱光潜的艺术审美的“距离说”,实际就是最典型的超然人生的态度。需要说明的是,京派将文学与人生的“距离”拉开,是在人生自为状态里寻求“真切”和“真情”,是将具体实用的人生转变为审美的人生,是在艺术美的境界里探寻人生要义。确切地说,京派作家人生概念是一种大文化语境,是超越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当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等同于时代时,京派避开了政治生活的激流,采取了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与激烈的南方血与火的斗争现实面前,显得过分超然和不合时宜。可是,大文化语境里的多元人生观,又纯属自然的一种人生态度,更重要的是与京派作家的切实的生存环境和传统的精神承传相吻合。文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精神承传,使得京派群体的人生态度和审美选择以恪守人的自身为要。所以,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努力不断地改变人本身,远离时代政治,追求文学的纯正,在校园里、在客厅里、在书房里形成了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学观。这种自足、和谐的文学思想,政治社会的意义是单薄的,而在文学历史的层面不无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重要的是寻求京派的文学观的文化精神承传及其表现的内容,对文学提供了那些新东西。
再次,京派独立的文化性格和人生态度以及形成的相似相近的文学思想的聚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转换的视角考察,还会发现,作为文学流派创作世界的实践内容,是在古老中国的文化转型期,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传递转换的胶合。京派的生存状态直接体现了这种胶合的不断调整、更新、组合的运动过程,具体表现方式就是在其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城乡冲突”。都市的精魂乡村的情结统一于这群精神贵族身上,京派是将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的文化底蕴,全部蕴藉在这种生存冲突的内容里了。
京派是高等学府里高层次知识者聚合的文学群体,可是都市并没有成为他们创作实践的重要内容,相反“乡村中国”的图景出自京派作家的笔下。大家熟悉的沈从文的“乡下人”的眼光,不仅创造了独特的湘西世界,而且他也以此视角看到了冯文炳、箫乾的创作个性。他评论冯文炳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静中有动,具有平凡的人性美(注:《沫沫集·论冯文炳》。),读了箫乾的《篱下集》后说:“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而且“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注:《箫乾小说·题记》。)。另外,芦焚(师陀)主要写河南家乡的“果园城”,汪曾祺侧重写苏北乡镇世界等等。直接生存的环境是精神自由的校园,都市里的精英群体,却每每把目光投向另一种生存环境——乡村。京派在“城”与“乡”的对立中,立体的观照人生,寻找他们理解的人生立脚点。结果他们将城市的压抑、愤懑、孤独,转换成乡村的审美的生命形式。从而使得平和超然的人生态度和纯正文学观,找到了整合的文化语境。一个自在、自足的乡村社会,一个与城市现代文明迥异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呈现于京派作家的创作世界里。这与同样经历着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冲突的其他文学群体比较,不难看到京派生存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内涵区别。与20年代的“乡土文学派”比较,京派作家的创作总体同鲁迅谈乡土文学一样,是一种“侨寓文学”,不过“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京派作家和当年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乡土文学派作家同样属于被故乡所放逐流入都市谋生的一群。在现代都市里的生活价值观与传统乡村的生活价值观完全对立的冲突中,京派作家却取了不同于乡土作家的态度和表现内容。乡土文学派的创作是因都市里生活的坎坷,而滋生出作家“隐现的乡愁”,沉浸于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京派的乡村艺术世界里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亲和和热爱,源于“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沈从文《湘行散记》)这种尖锐对立的城乡冲突。他们以乡村的美的自然山水,长存乡里的文化道德、生活秩序、民风人情等农业文明,构成与现代都市文明的诸多污染和异化现象的批判和抗争。因此,乡土作家笔下浓重的乡土气息,地域差异的民风民俗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或地方色彩,到了京派作家的创作中已成为一个乡村性的叙述整体。乡土作家写农村的落后衰败、农民的苦难和不幸,表文学“为人生”的社会批判;京派作家的回归自然、返归农村文化是改造现代社会。他们努力寻觅民族文化中积极的精华,挖掘农村里一切美的东西,要在乡村人民身上构造起健全的民族性格,来寄托他们民族重造的希望。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芦焚的《果园城记》,废名的《枣》、《桥》等作品,都是以一种和谐、圆满的纯美境界,淳朴、敦厚的乡民,烘托着一种民族性格的内核,呼唤着传统的道德、农业文明的重构。与京派同期出现的30年代左翼社会剖析派的农村创作,表现城乡冲突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时期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等等作品,对于30年代前后农村生活的表现,展示了城乡冲突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命运。作家站在一个较高视野中审视农村,农村是社会化的、历史的命运观照。诚如茅盾所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关于乡土文学》)。这是左翼社会剖析派农村创作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发展。跳出了表层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纵深提高了农村题材创作的思想内涵。但是,这中间也淡化了广阔而丰富的农村生存状态。京派作家恰恰填补了这个淡化的生存状态,集中写乡村自在、自足的社会:人际关系、伦理标准、生活理想等一切都是美丽的;赞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小说里湘西人的野性、强悍,但又守信自约;杨振声、林徽因笔下的胸襟坦荡的渔民、挑夫、人力车夫,都是普通人平凡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写照。显然,京派作家的地域性转换,就其实际的创作内容,自觉地承担了现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过程中一种生存状态的表现,一种中介作用。正是以超越思想启蒙的乡村愚昧落后的揭露,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观察视角,进入伦理道德、纯朴民风的体验和表现,文化精神的寻踪,从而使得京派在城乡冲突、现代和传统的冲突中,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生存状态。
京派:话语与形式
“京派”地域转换中的生存方式:由人生化向艺术化、生命诗化的寻找。在现代和传统的冲突中,寻求自己独立的生存状态的京派群体,一开始就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内省自律和文学自身的形式建构,以一个完整的叙述体系反映了文学流派独特的个性取向和形式。
“京派”本源的原生态在地域的内容和形式里,就以虚实相间的地缘意象,表现了非同一般的群体生存基础。在其思想观念、人生态度、文学实践中,又进一步完整展示了“自我”和谐的群体生存内涵。文化体的京派对艺术纯正的追求,还表现于一种强烈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一种生命的热情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京派真正生存状态不是外在社会化历史的动力,而是内在生命主体的活性张力,充满着很强的主体自律和相互间的调节机制。文学流派的京派群体不同于其他流派群体,就是在从容的自律和紧迫的现实相悖论里,营造了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的经验方式,即表现为两层内容:一是生命的和谐就是艺术的和谐,也是其艺术表现方式的基本原则;二是文学与生命的一致,与生活的同步,也就有了其文学体验形式的艺术化、诗化的形成。
京派的文学群体的世界,以艺术和谐的基本表现方式和原则,形成了这个群体整体生命化的和谐圆润。从个体的作家中和到群体的严谨圆满,可以发现京派群体的文学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觉追求文学的整体性的形式圆满。在表层的创作样式选择里就能见一斑,京派的文学创作体裁包括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等门类,重要的是在这些文学样式里都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京派的许多作家身兼几个创作领域的代表就是最好的例子。沈从文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方面的建树;废名、冯至的诗歌、小说、散文均有成功的作品;李健吾创作和批评全面出击,成绩斐然,为京派的中坚分子理所当然。还有林徽因、萧乾、李广田、朱光潜、凌叔华等京派作家,也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多面手。在这种表层的文体形式的圆满里,京派作家不像以前的文学研究会的那种“健全”和圆满。前述文学研究会群体时,我们曾谈到这个群体以性格和文学组织机构的健全,体现着启蒙主义的姿态,以建立初创期的新文学的秩序,表现了理性化的全面的建设。所以,说文学研究会的群体“少年老成”有点过分,中年的稳健和理智可能更准确。京派群体的文学自觉的健全和圆满,与文学研究会的不同是情感化的、主体精神化的内在扩展的表现,而非理性化的有意为之。如果说文学研究会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及组织完善等方面是有意识地注意方方面面的统摄性,那么,京派对文学是生命的呼唤,文学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的生命和谐。生命的精神多元形式建构了京派的文学意识的健全。京派作家最钟爱、操持最为娴熟的创作样式,无疑是贴近生命自由的诗与散文,可是同时又能将诗与散文渗透到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中,从而达到全部的艺术内容和文学形式都是与生命本体的亲近和亲和。在这个意义上,以箫乾作家为例,可以看到文体差异对京派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体的内在张力表现的不同追求。箫乾既写散文又写小说,还有文学批评。这几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差别是明显的。但是,读一读萧乾散文《小树叶》创作集和《流民图》特写集,文体的分类是清楚的,但特写集作家以“游踪”为线索,记述的新闻特写与其忧郁自白的“小树叶”的精神实为一体,他的小说《篱下集》等,就是散文自白的形象化的传奇故事,或者是童年生活的特写体式,依恋过往而带着自传色彩。而箫乾的文学批评文字不多,但也是批评的理性与情感的配置“时刻着眼在作品全部的氛围、情调和观点上。……他整个的欣赏,也整个的评论”(注:箫乾:《书评研究》。)。作家不仅追求各种文体的写作的完整,而且主要是不同文体中寻求精神叙述的统一,艺术世界的和谐统一。箫乾如此,其他京派作家亦然。凌叔华、林徽因、芦焚、汪曾祺的创作世界追求一种艺术纯美和生命纯美的统一,从叙述形式到作品形象塑造,都以散文化、诗化的创作形式,写个人的生活感受,内容多为故乡与童年的回忆,或者着意刻划纯洁的少女形象,儿童视角里的成人世界等等,描绘出他们内心深藏的那块美好园地,保存的一些自然美、人性美的光影。所以,京派作家创作世界最看重的是叙述的整体性、和谐性。叙述的自觉、文体的自觉,超过了其他内容的一切方面。这正是京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地方。
京派如此看重文学与生命的整体性、和谐性,文学创作便自然趋向艺术化、诗化的追求。京派的群体生存方式是生命化的艺术展示,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艺术联系着生命,生命创造了生活,从而形成了京派文学整体的链条。这个链条环绕了一个纯美的艺术系统,即从人生出发,通过审美中介达到艺术的创造,最后完成对于人生的美化。京派的审美中介的艺术创造,是从现代和传统的转换中,寻求自我艺术创造的灵性和独立的表现方式。这就使他们在走向艺术化、诗化的过程中,通常呈现这样几种途径:
其一,用传统的艺术的传奇手法表现与现代的自传体形式的整合,创造了文学作品内在诗的神韵。京派的创作世界里,尤其是小说样式,许多作家自觉仿传奇的写作,如被鲁迅编入新文学大系的李健吾的《终条山传说》,讲述一个民间流传的水神河伯的故事。传说一个樵夫在终条山受到神秘的惊吓而死,另一个大胆的农民,却在某个月夜听见神的呼唤,走出石门,得到50两银子。小说象征性地指出了神对人的呼唤和期待。沈从文的小说传奇性带有湘西少数民族习俗,如《龙朱》、《一个农夫的故事》、《月下小景》、《医生》等等作品,以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非现实的叙事虚构方式,将故事中人物置于不同寻常的境遇、事件中,赋予生命的意义。《医生》中那位医生为救吞吃了珍珠的白鹅生命,忍受着被误解的痛苦。作家是借这个故事表达人类的牺牲精神,本是极平凡,也是极其高贵的。京派作家的创作世界的传奇色彩注重挖掘的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生命的庄严和自由。京派的现代自传体在叙事的时间和地点中加进新奇而有趣或者具有悲剧色彩的传奇因素。上述作品在传奇故事里都传达着作家个人经历的抽象化,表现作家以叙述者的身份对自我的理解与把握。他们在传奇故事趣味的叙述中渲染人的本源的生命创造力,表现出野生灵的生命神秘,意在揭开人性的一角,自我的更新发现,自我神性的舒展。京派作家的传奇故事是生命的传奇、人生的传奇、自我的传奇。
其二,将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创作与现代人的浓烈情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辟出新文学独特的一脉创作流,既是新文体又是新内容。京派文学创作世界叙述的整体性,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也是从五四的文学精神中不断开拓和创造,由此,构成了他们文学独特流派生存发展的重要契机。文体的自觉是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京派作家的创作特点,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群体与其生命的联系,是一种内化的实体,活的生命张力的形式化。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的写实性的创作,不乏主观抒情的因素,创造社的抒情性创作里,也并非没有写实的成分。但是,他们的创作从各自的取向上看,所具有的这些“因素”和“成分”充其量是一种基本文体格式的补充,是外化于创作主体的内容和形式的分裂。例如,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叶圣陶等作家的作品,在写人生诸问题,记述不幸人们的苦难时,进行人生“爱的哲学”的概括,或者“爱与美的和谐”的人生理想化使得写实性的创作笼盖了抒情的氛围。王统照的长篇小说《一叶》,主人公天根的个人经历的几个片断故事线索清楚,记实之中又常常夹入大段的独白、抒情。小说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距离,使你感觉到是自觉的自叙传。这是在五四写实文学里有代表性的。京派作家创作世界艺术化、诗化的自觉,对五四文学创作的超越是将上述孤立的“精神典型”现象,或曰精神与写实的分割现象,纳入了生命的有机整体。沈从文的《边城》,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作家以散文和诗的形式写他的小说。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故事,有深缩的人生悲凉命运的情丝,但它又是构筑在一个和谐的现实与梦幻的境界里的。小说的环境茶峒边城渡口,小说的人物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小说的恋爱故事,都是现象或者事件与意象的化合之境。京派的作家创作追求的就是这种带“原味”的生活和人生本真。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芦焚的《果园城记》等作品,脱去了编故事、造情节的小说作法,也削减了感情外化的宣泄或凌驾于物象之上的抒情,全部的内容都是环境、气氛、人物的有机沟联。表层似乎散落,内部却有“意”和“神”的贯通。现代小说文体由京派作家的努力获得了不只是一种文体的丰富发展,重要的是凸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生命艺术化的真实。
最后,我不想再画蛇添足地谈京派创作的民间语言和外来语言的结合,形成自己的艺术化的传递形式。从文体的角度已有了许多对京派语言的研究。如果从生存的转换视角来看,京派富有形式的语言意义,是与群体的悖论生存方式相关联的。京派作家都市里的精魂,乡下人的恋情,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的统一。当作家本着复杂矛盾的心态进行文学的建构时,特别是作家有意识要使生命与文学一致时,思想的载体,或者文学的体现者,对于其价值已经超出了载体形式本身。所以,我认为,京派的文学语言活力是他生存自然生态和社会接受生态的冲突、转换的结果。他们来自自己的乡村故里、市郊农村,同时,他们又都是都市里的高等学府的学者、教授、学生,集中于北方京津两地,他们有很深的传统文化文学的素养,也有的接受过欧风美雨的熏染,既保存民间道家的超然脱俗的名士风范,又吸收了西洋贵族的绅士情调。这些文化诸多因素的杂糅,首先反映在语言形式上,单纯田园牧歌的抒情语言,或现代艺术直觉印象的幽丽俊逸语言,都不能准确涵盖京派的复杂存在的表达形式。沈从文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的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注:《废邮存底·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以“水”的流动性来概括京派语言的文字特点,最贴切这个群体的生存形态的表现方式了。京派群体的都市与乡村的转换,现代与传统的转换,“流动”就是其本体形态特征,沈从文语言的柔韧、圆润,流淌着明慧清澈的湘西沅水;芦焚的语言清新冲淡、简约严峻,小城果园里洞察人生沧桑,流动着怀乡的情愫;林徽因、汪曾祺语言的纯正、纯真而有美感,自然而有节制,一切顺着人生“生存的河道”(注:林徽因:《人生》。)流淌;废名语言的带着村野的朴拙自然,周作人说,他的小说“像一道流水,大约总得灌注绕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注:《莫须有先生传·序》。)。京派的语言每个作家有个性上的差别,但是,整体上体现自然的“流动”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总之,这个群体身置动荡变革的社会,又不愿以激进的两极方式求得地位,保持距离的求真求美,生存转换建筑于生命与自然的契合,“流动”造就了纯真纯美的艺术田园。京派的这种生存方式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轻视了阶级和政治的作用,并不完全合适。而在文化的多元语境中,强调从人生出发,通过审美的中介,达到艺术的创造,从而追求美的人生目标,又不无体现文学历史的规律。“转换”提供了京派群体的生存,同样,正确地把握这个群体也需不断调整转换,认识的方式源于对象的本身。京派的生存价值永远属于它自身的执著追求。
标签:文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读书论文; 沈从文论文; 大学社团论文; 作家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