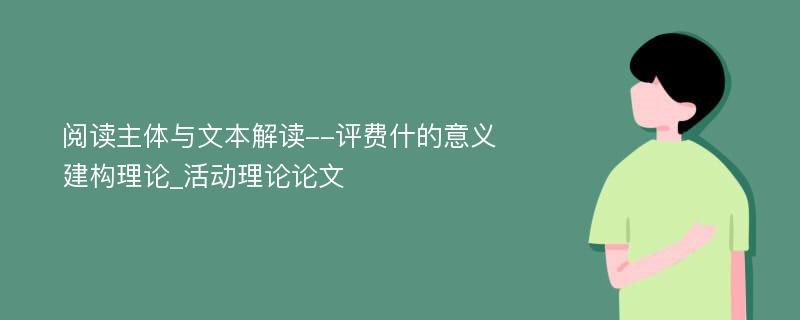
阅读主体与文本阐释——评费希的意义构造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文本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评费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W·伊瑟尔与H-R·姚斯为代表的一批联邦德国文艺理论家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文本意义阐释理论,震动了当时的西方文艺理论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一批学者也围绕着读者展开了争论,其中S·费希、N·荷兰德及D·布莱希各自提出了独特的阅读理论,即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三人之中,又数费希在理论界的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这些影响与争议主要来自他的阅读阐释理论。本文拟对这一理论进行扼要的归纳,着重指出其中引起争议的几个方面,并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本文中“阐释理论”的含义。“阐释”一词在批评理论中主要指对文本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有的理论家(如H-G伽达默尔、E·D·赫希)专门致力于探求文本意义的源泉,研究其存在的方式、实现过程以及验证方法,他们被统称为文学批评中的阐释学派。但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阐释活动则涉及到文学批评的一切方面,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历来就是文学理论关注的对象,当代西方文论的各家各派,几乎都是从文本意义入手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正如K·M·牛顿所说:“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强调对文本的阐释。”①本文中论及的便是这种意义上的阐释。如牛顿所言,始于六十年代,席卷欧美文论界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各种批评理论,也都从意义入手。这里所提及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有赖于读者的介入,是读者与文本相结合的产物。从一理论打破了形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费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阅读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因而其理论探索很快便超出了昔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所关注的重塑读者形象的问题,而把精力集中在对阅读现象的本体思考上。正是这种思考奠定了他在美国文论界的学术地位。
费希的意义理论在他早期的论文中就已初见端倪。七十年代初,他参与了关于读者作用的理论争辩,旨在打破雄霸美国文学批评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过分倚重文本有意排斥读者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的统治地位。几乎从一开始,他的阐释理论便以其新颖与独特而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他早期提出的读者模型,便是这个理论的一个极好的概括。说到读者批评,人们便会想起形形色色的读者模型。建立读者模型是读者批评理论的特点之一,其目的是使用这些模型作为表达各自阅读理论的工具,如姚斯的“历史的读者”,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荷兰德的“相互作用的读者”,里法代尔的“超级读者”等等。这些“读者”其实并非是指任何一类现实中的读者,因为实际的读者气质、素质千差万别,反应机制也各不相同,很难进行抽象概括。这些读者模型实质上是读者批评家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论,对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做出的抽象描述。也就是说,这些“读者”反映的是特定的阅读观,提供的是这些阅读观的高度浓缩的理论框架,借以说明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阅读理论中是如何进行文学阅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希的读者模型便是他的“情感文体学”的一面镜子了。
费希的这个读者出现于他在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在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了新批评理论家W·K·维姆萨特与M·彼尔兹利所谓的“情感谬误”,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学作品的表面词意与其深层蕴意相差很远,只有后者才是作品的真正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②因此,阅读主体便毋庸置疑地成了阅读活动的关键,而阐释理论所应关注的,也理所当然地是读者的阅读活动了。费希接下来的任务,是用一个读者模型来对读者的阅读活动(即他对文本不断做出的期等、假设、投射、修正等种种反应)做出理论阐述。他首先借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作为这个读者模型的理论基础,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语言使用者共同拥有一套生成该语言的句法规则,依靠这套规则,便可以生成转换出该语言所有的语法句。但是,语法的正确却不能保证交流的成功。例如“无色的绿梦喧闹地沉睡着”这句毫无意义的句子仅靠句法结构很难进行鉴别。因此,沃德豪斯将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扩展到了语义的范畴,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即建立一套相对于语义的规则,依据这套语义规则,加上乔姆斯基的句法规则,便可以产生出既合乎语法,意义也明白无误的句子来。尽管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本身还不完善,而语义规则的建立更是困难重重,但费希却从这两位语言学家那里得到启示,提出一个有关阅读的假设:读者之所以能正确地做出各种阅读反应,并与其他读者交流阅读体会,是因为他也拥有一套“内在化”了的有关阅读的句法、语义规则。阅读的句法规则限制读者对文本反应的范围,使得这些反应在句法上既“在预料之中”又“合乎情理”,而阅读中的语义规则限制反应中所表达的意义,使得反应在意义上具有“可能性”。拥有这两种规则的读者便能够对文本做出一切合乎逻辑的反应,且能与其他具备这些规则的读者相互交流。据此,费希推出了自己的读者模型,这个“读者”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能力:理解文本语言的能力,产生正确语义的能力及文学欣赏能力,故而被称为“有能力的读者”。
但是,这个“有能力的读者”及其所代表的阅读理论却最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生了矛盾。乔姆斯基与现代语义学家孜孜以求的是构成语法句或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的一套最基本的规则,即它们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符号只是这个深层结构的外在形式,任何对语言的构造或对语义的阐释都必须与语言、语义的深层结构相吻合,否则只能是误构。因此,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符号或语言的表层结构只是获取深层结构的手段,而非语言研究的目的。而费希的深层结构却与此不同。首先,他的深层结构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从语言的内在规律变为“有能力的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其次,深层结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语言研究的目的变成文学阅读的手段,不再占有中心地位;此外,这些“能力”也失去了深层结构原失具有的明确性与终结性。费希重构深层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很不情愿将文本的深层结构这个概念引入意义理论,因为这么做无异于承认:一、文本具有某种终结意义,对它的任何阐释都必须与这个终结意义相符,否则使是误读③;二、学批评关注的应当是文本的终结意义,而不是文本的语言符号。这显然违背了费希的初衷,因为他所追求的恰恰是读者对文本语言符号的主观反应,这种追求势必要破除文本意义存在“深层结构”这样的神话,甚至读者的“能力”这个新的“深层结构”相比之下也处于极次要的地位了。
费希对“有能力的读者”如何处理语言符号的描述很简单,主要表现为“提出假设及修正假设,做出判断与修正判断,得出结论及放弃结论,表示赞同或中止赞同,发掘原委,提出问题,做出回答,解决疑难。”④但对费希来说,这种处理却极为重要,因为文本意义最终产生于读者对文本符号的逐一解读之中。但是,费希把语言能力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尤其是他对读者处理文本表层结构的这种描述,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费希同样重视语言符号或文本在意义生成中的指导、控制作用,其实这正是他所竭力反对的。⑤在他看来,语言能力只能保证读者对文本即刻产生反应,而文本的存在只是为读者的反应提供反应对象。至于如何反应,怎样控制反应,反应的结果如何,则完全由读者本人决定。换言之,真正制约文本意义的,是读者本人在阅读时凭借语言、文学能力对语言符合所产生的他认为恰当的各种判断、推测,与文本及印刷符号毫无关系,这一点在下文的讨论中会看得更为清楚。伊瑟尔因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希的“有能力的读者”中缺少意义控制机制,“他在文本具体化的过程中自我调节反应,来达到控制反应的目的。”⑥伊瑟尔对费希的批评主要基于现象学阅读理论。他认为意义产生的过程是读者与文本双方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读者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文本的语言符号,即文本中的“确定点”。在二人对“观念性想象”(ideation)这个概念的定义中,双方的差异便一目了然了。伊瑟尔认为观念性想象是依据已经给定的事物来“产生尚未给出的事物”,⑦而费希则把这一过程定义为“从(先在的)一套对某个世界的假设中产生出这个世界来”。⑧由此可见,费希的意义制约机制或决定意义的“确定性”不是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是读者主观经验中的“先在假设”。
伊瑟尔的意义理论代表了六、七十年代很大一部分读者批评家的主张。他们突出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批评欧美文本中心论,同时也肯定文本在意义阐释中的指导作用。如T·托多洛夫探讨小说的意义时,便是从小说的文本结构入手的。W·布思在重建“隐含的作者”、“隐含的读者”时,也遵循文本的上下文。伊瑟尔的现象学读者(“隐含的读者”)本身便包含一个由文本结构所造成的“召唤结构”,吸引并指导读者进行文学阅读。与此相反的便是以解构思潮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在J·德里达、H·米勒以及R·巴特看来,文本符号乃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因而不可能向读者提供确切的意义。有趣的是,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几乎没有与伊瑟尔发生过争论,向他公开发难的,恰恰是他的同伴,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费希,争论的焦点便是意义阐释中的控制机制。伊瑟尔主张,文本中“不定点”的阐释有赖于与之相关的“确定点”的存在,后者是理解前者的唯一依据。他对此形象地做了说明:语言符号犹如夜空的星星,是“明确不变”的,而如何将群星连接成星空图案,则是不定的,因人而异的。⑨费希反唇相讥道,文本的意义控制作用是伊瑟尔制造的神话,因为所谓的“确定点”并非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中,而是读者主观活动的产物。因此他断言,“文学文本的群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和它们之间的连接线一样,变化无常。”⑩仅举一例来说明双方的分歧。弥尔顿在十四行诗《关于最近发生在沛蒙推的大屠杀》中,大量使用长元音,其中十一个诗行的韵脚均含有“O”音,评论家们认为弥尔顿借这种手法来表达自己惊愕、愤懑之情,并因此称这首诗为“最为雄壮的十四行诗。”(11)按伊瑟尔或传统阐释理论的说法,评论家的这种结论基于诗中的“给定点”,即长元音的频繁出现,任何与此相关的阐释都要受它的限制。但费希却会说,这些长元音完全是评论家们主观阐释的结果,并非是诗中的客观存在。
如此看来,费希似乎更接近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他确实常常不无赞赏地提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取消了语言符号的客观指涉性,为他的意义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后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解构毕竟不同于费希的主观批评,因为一旦文本意义完全消解,读者还怎么可能进行“线性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又如何进行有逻辑、有语境的联想、期待、证实,又何来意义供他创造呢?因此,费希需要明确的意义,以使他的情感性阅读得以顺利进行,并最终获得这个意义。既然意义可以获得,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确保所获意义的有效性,对费希来说,便是如何在意义产生的过程中设置一个意义控制机制。首先如上所述,这种机制不可能来自文本。其次,它也不应当来自读者本身。“有能力的读者”确实包含有三个“能力”,但这些能力只能保证他正确理解文本语言,却很难限制根据这种理解对文本进行阐释,因为阐释活动是读者对文本阐释的审美体验,主要依靠读者的个人经验,实际知识,综合能力,因此这种审美体验因人而异,不可能作为一种统一标准。最重要的是,审美体验虽然基于对文本语言的正确理解之上,却无法保证会被其他“有能力的读者”所认可。因此,费希最终就不得不把意义控制机制放在了“阐释集体”上。
“阐释集体”这个概念是费希意义理论的核心。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概念出现于费希的早期论述中,其基本含义也一直未变,这一点也证明上文中的一个看法,即费希对文本在意义生成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在写于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篇评弥尔顿作品集注本的文章中,他详细地阐述了阐释集体这个概念。该集注本收集了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等对弥尔顿作品的阐释,其中不乏论据充分但结论相佐之见。这种现象促使费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证实读者个人做出的阐释有效呢?如何解释多个相互排斥却同样有效的阐释并存这一事实呢?费希的回答是,一种阐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批对这种阐释表示理解的其他读者,他们之所以会理解,是因为他们在阅读中采用了同样的阐释策略。这群拥有相同阐释策略的读者构成了“阐释集体”,“阐释集体”的存在便可以证明任何一种文学阅读的有效性。下面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费希的这一观点:
(阐释集体)不是指一群拥有相同观点的单个读者,而是指拥有一群单个读者的一种观点或一种组织经验的方式,即它所假定的各种区别、理解范畴以及贴切与否的规定构成该集体成员的共同意识。因此,这些成员不再是单独的读者,而变成了集体财产,因为他们已经置身于这个集体的事业之中。正因为如此,这种由集体构成的阐释者会反过来构成基本相似的文本,当然这种相似性不应该归之于文本自身的特征,而应该归之于阐释活动的集体性。(12)
从费希的论述中,对“阐释集体”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该集体的组织原则是一套共同的阐释策略。因为所有的成员都承认并采纳这套策略,所以,集体成员的阐释活动便受到了制约,违反了这个组织原则,读者在该集体中的成员身份便中止了。费希相信,阐释集体可以防止阐释中的“完全随意性”,可以阻止“阐释的混乱”。(13)其次,这些阐释策略(即意义制约机制)并不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包括文本),而是读者的一种“意识”。这表明,费希把传统阐释中的主、客观二元对立关系消解了,主观阐释活动的制约机制本身便是主观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活动的特点,如可塑性、随意性、局限性。由于意义制约机制的主观性,意义本身便具有了很强的主观性,并势必导致客观文本的消失。因此,费希的结论便是,文本意义之所以不可穷尽,是因为存在无数的阐释集体,每一个阐释集体拥有各自的阐释规则,组成各自的意义制约因素,在各自的阅读活动中“创造”各自的文学文本。
费希的阐释理论在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他的论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原因之二,是他的理论与当今盛行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有相当的吻合,不仅对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传统批评理论有强大的摧毁力,甚至对当代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话语行为理论等)也公开提出挑战,气势咄咄逼人,相比之下,他的对手的反击则显得软弱无力。(14)但这并不能掩盖费希理论本身的缺陷。
首先,费希从未清楚地表明什么是阐释策略。最通俗的定义便是阐释方式。但严格地说,读者间的阐释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用不尽相同的阐释策略作为统一的组织原则,不免相互矛盾。在谈到阐释策略的具体内容时,费希也是含糊其辞,有时他似乎把它当成构成批评理论流派的那种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与理解,有时又作为读者鉴别文本形式特征的手段,近似于语言、文学能力,而有时又笼统地称之为读者个人的(也就是阐释集体的)“兴趣”与“目标”。(15)作为一种组织原则,阐释策略的含糊不清必将造成阐释集体的含糊不清。一个界定不清的阐释集体也许有利于其成员更自由地进行阐释活动,但却与费希对阐释集体的描述不尽相符,按费希的定义,它本应是一个组织严密、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的集体,只有如此,它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揭示阐释集体间的差异,才能说明阐释结果的多样化。
实际上,由于阐释策略完全是读者个人的一套先在观念,不需任何客观依据,所以费希也根本无法对阐释集体加以界定。读者既无法知道属于哪个集体,也无从了解自己集体中的其他成员。按费希的说法,确认阐释集体的唯一途径便是他人的首肯或会心的一笑。(16)由此可见,费希并不主张阐释集体可以或者应该界定,强行圈定,势必会束缚读者在阐释中的自由发挥。但是,不加圈定的集体无异于集体的解体。如果某位读者实在找不到集体成员,即他的阐释得不到其他读者的赞同,从理论上说,他的“假设”便不具有共同性,他的阐释策略也不具备集体基础,他所获得的意义也应当算是无效了。但费希对此并不以为然。他相信,阐释集体尽可以模糊,但在组织上一定存在,读者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阐释集体,纯属个人的假设是不存在的,他所做的任何阐释总可以找到知音,所以总是有效的。
如此看来,阐释集体作为主体主观活动的控制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便微乎其微了。实际上,这种控制机制形同虚设,因为阐释集体的存在(他人的首肯)本身便是读者主观阐释的结果。费希的这种说法为文本阐释的主观性开了绿灯,读者不必再为自己的主观解释寻找任何客观依据,因为阐释活动本身便包含了阐释结果的有效性。换言之,阐释的有效性与阐释的随意性这两个在传统意义理论中水火不相容的概念被费希合而为一了,正如费希所言:“不管看上去有多离谱,没有一种阅读是完全不可能的。”(17)如此说来,评论家不必对公众负责,困为他们或许本来就和自己不属同一个阐释集体。他也不必对自己负责,因为他的阐释总是有效的。如果把W.布莱克的名诗《虎》理解为比喻某种消化过程,或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做并不困难,只要能找到这么做的阐释策略就行,而这种阐释策略肯定能找到。(18)费希当然不乏支持者。R.克劳斯曼也坚持认为,E·庞德的短诗《在伦敦地铁车站》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人有必要经常饮用牛奶,因为“一首诗的意义便是任何读者真诚地相信它所具有的意义。”(19)当然,从理论上说,此类解释并非完全不可能出现,但它们毕竟离广大读者的期待相差太远,即使偶然发现个别知音,也很难证明它的有效性,非但如此,这种阐释的实际效果反而更令人怀疑了。
费希把意义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读者的主观意志上,最终也大大削弱了他的意义理论的说服力。一个完全依赖主观性的批评理论,到头来势必陷入不可知论,因为千变万化的读者及其阅读活动是不可能用读者的主观性加以归纳、界定的。所以费希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不得不吐出他的肺腑之言:阐释集体既存在又无法确认,“你会赞同(即理解)我,正因为你已经赞同了我。”(20)类似这种阐释中的循环论证在费希的意义理论中屡见不鲜:你同意我的观点,因为存在阐释集体,阐释集体之所以存在,正因为我俩的观点相似。再如:个人的阐释不会主观武断,因为个人受到阐释集体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却来自阐释者本人的主观判断。费希的这种论证始终围绕着读者的主观经验兜圈子,这就无法避免循环论证的弊病。尽管费希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阐释中的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他“终究却未能摆脱这种级端的主观主义。”(21)
注释:
①K·M·牛顿:《阐释文本》,哈维斯特·韦特希夫,纽约,1990,第6页。
②费希:《读者中的文学》,见《这堂课有文本吗?》,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下文中的引文也于该文。
③当代西方阐释学中确有人在追求文本的终结意义,如E·D·赫希。
④、(13)、(16)、(20)费希:《对〈集注本〉的阐释》,见《这堂课有文本吗?》,第158-159、172、173页。
⑤有些评论家据此认为费希早期重视文本在意义制约中的作用,后来发生了转变。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费希的观点前后基本一致,他从未明确表明文本有意义决定作用。
⑥、⑦、⑨伊瑟尔:《阅读行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1987,第22、137、282页。
⑧、⑩费希:《为什么没人害怕伊瑟尔》,见《举措自然》,杜克大学出版社,伦敦,1989,第80、77页。
(11)参阅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150页。
(12)费希:《变化》,见《举措自然》,第141页。
(14)例如,伊瑟尔在应战中(《无稽之谈》,见《批评家》,1981,9月号)明显处于守势,甚至有意回避了费希对他的主要批评。
(15)参阅《对中世纪知之甚少:波斯纳尔论法与文学》,见《举措自然》,第303页;《对〈集注本〉的阐释》,第165-167页;《变化》,第150页。
(17)参阅费希:《这堂课有文本吗?》,第320页。
(18)费希:《什么使得阐释可以接受?》,见《这堂课有文本吗?》,第347页。
(19)克劳斯曼:《读者创造意义吗?》,见S·R·苏莱曼、I·克劳斯曼合编:《文本中的读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1980,第153-154页。
(21)R·斯苔克:《费希鼓吹的阐释真理的相对性》,见《美学及艺术批评》,1990,第48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