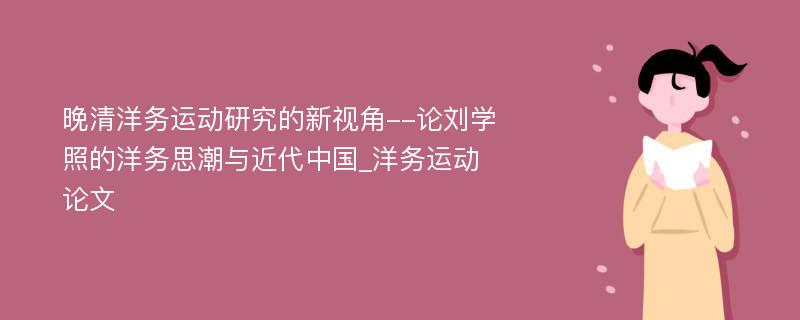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的新视野——评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洋务论文,晚清论文,思潮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所谓深入,除了理论规范的创新之外,其中较为重要的应是学术思路的转换和学术视野的拓展。新近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刘学照教授的专题学术论集《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一
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重建过程。因而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方面,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颇富神韵。“三长”之中,“史识”无疑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治史的眼睛”。一般来说,史识又首先体现于“选题”上,不同的“选题”,恰是不同的学术视野的展示。八十年代以来,洋务运动史研究呈现高潮,其中虽新见迭出,但在对洋务运动总评价这一关键问题上却见仁见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很多,产生分歧的领域也极为广泛。除了评价标准和评定的方法论比较悬殊外,在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的关系问题上也颇有争议。有鉴于此,《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一书的著者选择了“洋务思潮”这一研究领域,试图从思潮演变的角度对洋务运动进行重新认识,以便对其作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和说明。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以前,洋务思想文化的研究本属空白,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比较瞩目的学术成果主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这得益于史学界诸多学者的共同推动与努力,同时更与本书著者思路先开并首倡“洋务思潮”这一学术概念不无关系。
仔细推究,本书著者对“洋务思潮”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对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进行比较的结果。这最先反映于作者1983年发表的《论洋务政论家王韬》一文。该文中,作者第一次将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和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作了对比,指出两人的言论“在基本趋向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针对顽固势力而说的。所不同的是,这些话往往是王韬说得更早,见解更深,语调更激进。再有就是,李鸿章发之于庙堂和官场,纵论于上;王韬则每多公诸报章,横议于下,但都属于洋务思潮的源头。”(本书第109 页)作者同时指出:“王韬虽然不是洋务官员,但他始终钟情于洋务派,他虽然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进行过批评,但这些批评每多带有条陈和建言的性质,批评中寓以希望。……尽管到晚年,对‘洋务日明’也还没有完全失望。”(第113页)因此,王韬对洋务派的批评“其用意不在取消或代替洋务运动,而是为了充实和校正运动。”(第114 页)“这种理论虽然与洋务派思想有分歧, 但当时只是作为洋务思潮的一翼——激进的一翼出现的。 ”(第123 页)如果说作者在《论洋务政论家王韬》一文中侧重于对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之“同”的揭示,那么发表于1984年的《论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则侧重于对早期维新思想和洋务派思想之“异”的阐发。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究竟“异”在何处?作者同样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两者根本之异在于“重民”还是“重官”上。分歧的焦点是“利”和“权”的问题(第39页)。作者进而认为:“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的分歧,就其外观而言,是关于洋务的本末之争,而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则是重民还是重官,亦即重民还是抑民之争,这种分歧是客观存在的。维新和洋务逐渐由此分流也是必然的”(第40页)。
既有的学术观点或认为:洋务派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无实质区别,是同一的。或认为:后者是从前者中分化出来的,两者思想完全对立,不可相提并论。本书著者从寻找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异同着手,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洋务思潮”这一全新的学术命题。因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显然打破了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洋务时期的思想有了更新的认识。如若再深入推究,既有的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其立论的基础不外乎是从肯定或否定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出发的。本书著者对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新认识则着眼于“发展论”,即以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估价早期维新思想和洋务派思想。
应该指出,《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一书的著者不仅是“洋务思潮”这一学术命题的首倡者,而且是迄今为止对“洋务思潮”这一学术命题阐发最为完整和详尽的研究者。收入本论集的《论洋务思潮》一文集中反映了著者的这方面见解。这是一篇全面论述洋务思潮发生、发展及其分解,试图揭示洋务思潮两重性质及其演进规律的学术论文,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力和最为史学界所注意的一篇论文。该文的主要贡献,其一,在于从宏观上论述了洋务思潮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作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一次低阶段、多层次的学习西方,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潮”,洋务思潮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发生是“两个动因促成一变”,“两个源头汇为一流”。洋务培育了维新,洋务论者在“借法自强”大局上的共同认识推动了洋务思潮的发展。甲午战争的历史震动促使洋务思潮内部的诸种歧异加剧,从而导致维新从依附于洋务开始与之分流。其二,确立了“洋务思潮”在近代社会思潮史上的地位。作者指出:“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初,‘洋务’是中国社会新思潮的一面共同的旗帜,……‘洋务’论历经三十多年,在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上是历时最长的社会思潮。我们完全应该为它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史上立名”(第3页)。不仅如此, 作者在该文中还进一步阐发了洋务思潮在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上的一种中介作用,它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发展与变形”,也是戊戌维新思潮的“准备和借鉴”。洋务论者“发展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和‘筹制夷之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眼看世界’和‘师夷之长技’。”洋务同时又培育了维新,“继之而起的戊戌维新思潮……又是对洋务思潮的继承、发展和否定。所谓发展,是发展了洋务论者学习西方,借法自强的思想。所谓否定,主要是对洋务思潮主流派那种‘不变其本’、‘补苴弥缝’和‘不以民为重’、‘皆务压其民’这种反民主本质的否定。”(第23页)应该说,从晚清社会思潮演进的角度肯定洋务思潮的历史地位,本书著者同样是有首倡之功的。正是这一研究,才使洋务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史上的地位突兀而起。此后,不仅“洋务思潮”这一术语被史学界广泛沿用,而且在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等众多著作中都列有“洋务思潮”的专章。因此,可以说,“洋务思潮”研究是和本书著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从《论洋务政论家王韬》到《论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再到《论洋务思潮》,较好地体现了本书著者由微观到宏观的学术进路,同时也拓宽了晚清洋务运动史研究的视野。首先,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以夏东元先生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研究中的“发展评定论”的基本观点。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使不少学者将研究的视线转移到洋务思想方面来,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洋务运动研究只注意“正面切入”的研究倾向,从而推动了洋务运动和晚清社会思潮的研究。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研究的视角也应是多维的。如同现代摄影有正面照和侧面照一样,正面照固然标准、清晰,但侧面照也不失其应有的艺术魅力。可以认为,本书著者论洋务思潮的一组系列论文实际上正是作者给晚清洋务运动所拍摄的一组成功的侧面照,是作者学术视野拓展的展示。
二
从洋务运动史和晚清中日关系中的交叉点着眼,对洋务运动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这本论集学术视野拓展的又一表现。
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本书著者对近代中国人对日观的研究上。近代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也同是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东方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启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在一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日两国是相互影响和借鉴的。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和不思进取以及由此招致的民族灾难给岛国日本敲响了警钟,而日本明治维新的卓有成效给中国树立了榜样。显然,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都曾充当了中国“变法自强”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无疑,本书著者选择“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这一题目是耐人寻味的。
本书的著者首先从宏观上勾画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演进的基本轨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早期不甚了了到开眼相看,由知日到羡日,由羡日到师日,由师日到仇日的演变过程。“从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演变的轨迹来看,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多元的。其发展变化是曲折的。所谓多元,即亲切、轻蔑、钦羡、防范、仇怨诸心态斑杂毕呈。但这复杂心态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除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等恒在原因外,制导这个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落后。”(第303页)作者同时指出,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对日观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而被“日本帝国主义逼出来的,高呼反日口号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人对日观升华的一次大曝光”(第304页)。著者还强调指出, 轻日思想在清朝当政者中的根深蒂固是抑制和障碍洋务论者学习日本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甲午战后至二十世纪初,在挫折、失败中清算了虚妄自大观念,感到要学习日本锐意改革和发展教育的经验,固然仍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毕竟丧失了宝贵时间和有利时机。这应该是一条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第304 页)。无疑,这些来自于宏观的认识,不论就学术价值还是就现实意义来说都是值得重视的。
书中作者又着重研究了李鸿章的对日观。在作者看来,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巨擘和洋务运动时期“变法”论的最大鼓吹者,而且是晚清大员中的最大的“知日”派、最大的“防日”论者和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发表于1990年的《论李鸿章的对日观》一文,深入剖析了李鸿章对日观中轻日、畏日、羡日、防日诸心态的产生和发展,尤其重点分析了诸心态对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作者指出,李鸿章是“一眼看西方,一眼看东洋,领导着洋务潮流的。”“在他大量的涉日言论里,跃然躁动着一种优患意识和以力言‘借法自强’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但是,他究竟是腐朽清王朝中一位名列阁首、兼职封圻的要员。他热中于‘强兵治国’、局囿于‘中体西用’、受制于慈禧权势,从而使他的‘羡日’心态难以升华为高格调的学习日本的思想……始终盘桓在‘仿日自强’的水平上。”(第72页)“防日”论“推动了李鸿章对‘洋务自强’的努力,助产了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也加强了李鸿章长期坐镇北洋的政治地位。但是,李鸿章的‘防日’论”始终缠绕着‘羁縻为上’的羁绊。他对外十分仗恃成约和公法,非常迷恋‘以夷制夷’,绝对禁忌‘先发制人’,又保留几分封建官僚的虚骄之气。结果,总是‘有武器而不能战’,一再在‘圣朝包荒’的自慰下对日‘羁縻’,最后招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葬送了‘洋务自强’在人们心目中的希望”。因此,李鸿章“防日”论的是非正误的“洋务自强”的得失成败及李鸿章的历史功罪,“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第73页)。
如何评价李鸿章,尤其是如何估价他和晚清近代化的关系,史学界一直争论很大。为了进一步拓宽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研究的视野,本书著者1993年又推出了《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文。这是一篇运用比较方法对中日近代化历程进行深刻反思的论文,也是近年来著者学术思路不断深化的一种反映。强调近代化过程精英人物的主体意识的作用是该文的显著特征。著者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代化不仅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明显地凸现出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在近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观念,尤其是居于运动前沿的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运动进程的本质和面貌。因此,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行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等中日近代化运动本身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应该进行主导中日近代化运动的有关代表人物、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的比较研究。”(第74页)可以说,作者对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两位对中日近代化全局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展开的。
作者主要从知识结构、政治观念、世界意识、产业政策、西学取纳、政治民主、近代化实效、客观处境等方面详细比较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主要差别。在多方面比较的基础上,作者进而指出,“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具有一定封建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第96页)。作者由此归结到:近代化需要近代国家理性。正面提出近代化中的国家大员尤需凸现近代国家理性,即自觉塑造国民国家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变项的系统工程。如以此标准来衡量,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种单一的局部的经济、军事变革运动。显然,“不能凸现‘国民国家’这个近代化历史课题”是洋务运动难以收到实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历史主体的选择过程。历史进程中的失策往往与思想进程的滞后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强调洋务领导集团的群体素质和群体意识在洋务运动中作用,尤其突出强调站在洋务领导前沿的李鸿章缺乏近代国家理性,是导致洋务运动在实效方面难以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的见解是颇具洞察力的。
比较史学的勃兴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特征。在晚清近代化这一研究领域,虽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不可比,但仍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扎实而富于创见性的研究。本书著者的这一研究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显然,著者对“晚清中国人的对观日观这一课题的系列研究是成功的,也是颇有新意的,这同样是著者学术视野拓展的又一展现。
三
收入本学术论集的还有关于“近代中国”的其他论文,其中一部分是以晚清诗歌做史料论述有关晚清史的论文。虽然它超出了洋务运动史的范围,但它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有关,同样也展示了作者在近代史研究上的新视野。
诗中有史,用诗记史的现象在《诗经》时代就已存在。《诗经》向来就被视为中国的史诗。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同时也是一种有研究价值的史料。这方面,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可谓前驱先路。他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就是以诗证史和以诗论史的典范。近代以来,由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现实需要,文学领域也相应涌现了一大批的诗歌。应该说,这也是晚清史研究应充分利用和开发的一块领域。但由于诸多原因,这方面的研究至今尚属凤毛麟角,并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本书著者从七十年代以来,先后负责过《林则徐诗文选注》、《中国近代史诗选注》等课题,因研究需要,查阅了近三千种晚清诗集,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一首反对沙俄侵略的史诗》、《庚子诗史中的义和团与清政府》、《爱国诗人丘逢甲及其咏怀台湾的史诗》、《晚清诗史中的林则徐》等系列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是对作者所强调的“诗中有史”(第235页)这一学术论断的有力佐证, 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术功力的深厚。
诗中有史,诗中有画,诗中有情。史、画、情三者兼具,汇历史的再现和艺术的表现为一体,熔学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于一炉。就此而言,有关的“史诗”和“诗史”确是史学园地中的奇葩。作者这一研究也启示人们,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历史研究如能从相关学科的结合部扩展视野,将能更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能更大限度地实现其固有的价值。
专题学术论集是研究者一定阶段某一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总结。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科学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在某种意义上说,论文专集更能集中代表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更具有个人风格。《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一书就是具有这种特色的著作,这部论集的问世必将推动晚清洋务运动和晚清社会思潮的研究。但是,也应看到,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为后学,感到它似乎还有以下不足:第一,有关“洋务思潮”的论述是本书的重心所在,也是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应该说,作者无论从宏观和微观上都有比较精彩的论述。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不曾根据现有的思路写出一部有分量的洋务思潮专著,以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笔者期望这一问题能随着《洋务思潮研究》的面世而得到解决。第二,作者在李鸿章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都提出了不少很好的看法,只可惜不曾根据这些成果将其上升到史学理论的高度,形成一些规律性见解,这也是影响了作者有关论述的力度。第三,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近代诗歌的研究上。作者对晚清诗歌与近代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晚清史诗的史料价值问题都还缺乏总的论述。再者,作者在以诗论史的四篇论文中曾出现“史诗”和“诗史”的不同表述。如若细究,两者的含义还是不同的,究竟对这些涉及晚清历史的诗歌应怎样定性才合适,看来还需斟酌。
洋务运动的研究如何走向深入,这是史学界近年来普遍关心和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其实,收入在学术论集中的著者这些富有创见性的学术成果已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只有开阔视野、转换思路、拓宽领域,不断调整历史学的价值尺度,努力增进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洋务运动的研究才能走向深入,也只有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地对洋务运动进行“切入”,洋务史坛才能永远春意盎然并独具魅力。
标签:洋务运动论文; 李鸿章论文; 洋务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晚清论文; 新视野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