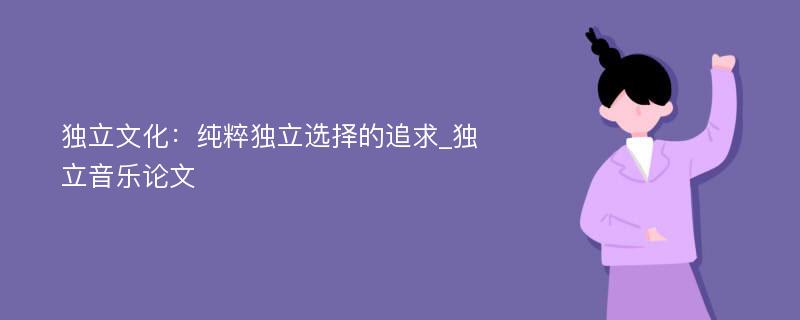
独立文化:追寻纯正的自主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正论文,自主论文,独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而来的美国独立电影,与其他形式的“独立”文化之间存在的共通之处,就是对主流媒体的自主选择。“独立”一词充满了矛盾,它曾经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抗,但同时又通过制造文化资本从而分化消费群。①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对独立文化的判断中,品位常成为讨论的核心,而所有的判断都呈现出负面的迹象。首先,一种观点认为,独立文化是以制造恐怖和非理性的禁忌为目的,让人产生不适甚至厌恶的情绪。
1993年,当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Miramax Films)被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收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将迪斯尼,这家全美领先的异类电影发行商冠以“独立”、“挑衅”、“非同寻常”、“自主”、“非传统的”、“附庸风雅”、“低预算”和“职业导向不明”等头衔②。而这些形容词有别于好莱坞通常意义上的价值观。独立电影的属性更倾向于独立文化,通过对主流的挑战从而确认自身身份。这种挑战和质疑首先来自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带来经济上的差别。“独立”意味着小规模、个人化、艺术性和创造性;而“主流”,对大部分的业内人士而言则意味着比艺术更值钱的大型商业化媒体工业。对于非主流媒体的拥护者而言,美国独立电影只是那些在好莱坞制片厂体系外被制作和观看的影片,不过是一些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影像记录罢了。
近些年来,“独立”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词,这个词背后囊括着譬如像“多元性”、“时髦”、“边缘化”、“不妥协”等一连串的标签,而这些标签远远超过作为一种经过严格制作的媒介产品的字面含义。“独立”不仅指电影、音乐、服装,还包括了文化其他表现形式,比如那些生产和推广此类媒介产品的企业和社会团体,更包括生产和推广中的实践形式。
迪斯尼对米拉麦克斯影业的收购,是更大范围的20世纪90年代主流媒体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好莱坞制片厂,开始着手于收购独立制片公司以及发行独立电影。与此同时,在音乐产业里,大型唱片公司开始与独立厂牌合作,比如开创垃圾摇滚的独立厂牌SubPop就隶属于华纳唱片公司(Warner Records)。随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一方面独立媒体的自主性似乎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独立”成了一个好使的词儿。一些影迷将“独立”看成是一种姿态,认为这些小型的电影制片公司需要重新命名③。而一些激进评论则认为,独立文化不过是主流媒体的一种增选方式,属于主流消费文化,依旧是以盈利为目的④。然而,相较于文化范畴内的“独立”,主流中的独立成分逐渐增强。事实上,如今主流中的“独立”文化产品是在跨国媒体集团的背景下被制作出来,继而进入消费的模式,并没有威胁到独立文化的中心。相反,多样性仍旧需要基于市场开发的成熟程度以及对主流消费类型(包括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有诉求的消费群体。满足这些定位的主流媒体,一方面可以对抗竞争,另一方面也为主流价值观增添更丰富的层次,进而如吞噬般,虏获文化生产领域的一切利润。
本文不讨论工业内的“独立”,而将“独立”集中于电影和文化的范畴。我认为“独立”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是对大众文化霸权含蓄的反击,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渴望替代它,成为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试图通过成为某种带有特权意味的文化品位,从而在精英受众中得以延续。独立电影和独立文化的核心是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博弈。“独立”可以被定位成是对同质化倾向严重的商业媒体的一种反抗,甚至是解决之道,但“独立”这种表现形式本身也是商业的,并且这种商业形式还有助于促进一类成熟消费者的兴趣。换句话说,独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反抗着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结构,但从源头上来讲,两者的差别只存在于这些结构内所服务的不同的特权集团⑤。而这种形态并非独立文化所特有的。不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运动,都为此提供了生动且可供参考的历史证据⑥。本文将讨论这种多元选择性的构成以及它陷入主导文化的历程。当今的媒体集团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但所有的选择均来自于自身,消费者只是空洞的存在。
针对独立文化的核心矛盾,我首先将讨论以下两个关键概念。“独立”作为对立文化以及“独立”作为品位文化。通过两个发生在相同时间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重要媒体事件以及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话题,作为讨论的主要案例,并通过两者的并置进而分析这些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两个案例分别是1998年饱受争议的电影《爱我就让我快乐》(Happiness),由托德·索伦茨(Todd Solondz)执导。另一个案例是大众汽车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制作的电视广告“Drivers Wanted”(通缉司机)。虽然后者看起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案例,但我认为这批大众汽车广告采用了风格化的处理方式,并达到了独立电影和独立音乐的理想标准。并且对独立文化的实践所做的贡献亦不亚于索伦茨的电影。
自上世纪80年代始,随着诸如圣丹斯电影节和米拉麦克斯等独立制片公司的崛起,如今已有大量关于独立电影的文献。文献中鲜少将“独立”定义为一种能跨媒介传播的类型,而是将重点放在单文本的生产和发行商身上,并不重视文化本身的循环性⑦。但是无论是制作或是受众接受层面,“独立”和“主流”之间均存在区别,在文本和受众分类两个方面最能体现区别。此时代的独立,也可能是彼时代的主流,所以无论是产品或受众,其意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⑧。面对如下将展开讨论的历史时刻,我坚持认为,“独立”是一个稳定的概念集合,并且这些概念里囊括了多种类型的艺术形式和受众群体。流行音乐的研究表明,以地方性的独立音乐为例,音乐本身表现出的真实性促使它在亚文化的粉丝群体中受到欢迎与认可,并在主流中获得自身的主体性⑨。我将本文建立在现有的对独立音乐和独立电影的研究基础之上,借鉴独立音乐的研究方法,在一个更广阔的“独立”观念里,重新审阅活动影像的传统⑩。
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关于音乐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例,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常规获得认可的观念:独立媒体反对的主导思想恰是主流媒体所支持的。桑顿的文章以俱乐部文化为例,表明独立媒体的生产和消费中蕴含着非常复杂的现实。独立媒体的主导结构里,挑战和延续社会的功能是并存的(11)。
当独立作为一种反对之声时,认为主流文化污染了观众,对受众产生盲目并且有害的影响。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斯蒂芬·邓库姆(Stephen Duncombe)的观点里,独立文化的制造者们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是既“纯粹”又“危险”的。
一部分从业者将自主性和真实性看成是自身纯粹性的来源,这种纯粹性鼓励他们通过文化生产来进行创造力的表达。而这所有的一切基于文化二元对立的形式之上:“地下文化的根源,源自于同社会主导隔离,它通过否定来确认自身的存在。”(12)在独立音乐和独立电影中,分裂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自主性和有能力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体现控制力的表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主性是真实性的产物。而纯粹的另一面即为危险,通过销售和增选组成地下传统。邓库姆以20世纪90年代广受欢迎的乐队绿日乐队(Green Day)为例:“当他们成为贪婪大企业的傀儡时,没有一支乐队能做出真正的选择。”(13)
独立电影在拒绝主流媒体后,体现了里根·布什时代中的新手艺术家普遍有限的技术和经济状况。(14)在许多情况下,低预算本身成了话语表述,意味着一种模糊的审美品质(忠诚、真实、洞察力)。在迈克尔·阿泽拉德(Michael Azerrad)书写的独立音乐史中这样写道:“地下独立呈现出生活的质朴,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是一个彻底的道德上的责任。”(15)其外观或声音正是在高速运转中保持可信度的产物。跟音乐类似,电影的制作成本可以放低,只有有限的资金和机构来支持,无论是独立摇滚还是独立电影都可以体现充满自主性的制作:黑旗乐队(Black Flag)、你记得吗乐队(Hüsker Dü,丹麦语,意为儿童游戏)、弗格奇乐队(Fugazi)的专辑,约翰·赛尔斯(John Sayles)在1980年的电影《锡考克斯7》(Secaucus7)中的回归,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于1984年拍摄的《天堂陌客》(Stranger Than Paradise),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1994年拍摄的《店员》(Clerks),罗伯特·罗德里格兹(Robert Rodriguez)1992年的《杀手悲歌》(El Mariachi)以及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1987年的作品《好莱坞清洗》(Hollywood Shuffle)。(16)只要流浪大型连锁书店里电影类图书的标题,就能清晰地接收到DIY的逻辑:“不需要忍受同伴的反叛”,“用一辆车的价格就能拍部电影”,“如何拍摄一部预算一万美元以下的电影”。(17)虽然这些书所面临的市场集中在好莱坞而非圣丹斯,但这些标题仍旧足以证明独立电影的核心气质,就像德里克·贾曼所说,“低廉产生美感”。这种气质中包含着适度的美德。(18)
独立电影与其他独立文化共享一条基本的准则,那就是用自身的不妥协性去吸引大量的观众。独立电影在让观众能够了解自己的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放弃本身的自主性,也不会以牺牲信誉,损失掉培养起的忠诚拥护者们为代价去获得普遍性的成功。当今,许多评论者认为独立电影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想在好莱坞开辟事业的非从业者拍摄的“敲门砖电影”,这类电影更加可信,因为真正的独立艺术并没有主流的抱负。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像理查德·林柯莱特(Richard Linklater)和斯蒂芬·索德伯格这样的导演,他们即使拍摄主流电影,也崇尚在电影中保留独立的质地。
一种看法认为独立电影中所表现出的对主流的敌意对“独立”的可信性起决定性作用,并且电影工作者和观众分享了这种敌意。这是为什么会出现独立电影的粉丝推进“低成本的小电影”流行的现象。比如2006年乔纳森·戴顿(Jonathan Dayton)和维莱莉·法瑞斯(Valerie Faris)共同执导的电影《阳光小美女》,这部影片同时在主流观众中获得很好的反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独立摇滚的粉丝坚持认为一个艺术家在尚未签约主流厂牌之前的录音作品总是更为出众一样。太过受欢迎使得一个艺术家透露出拉拢主流观众的趋势,这使得身处独立文化中的艺术家显得有点可疑。像一件讽刺独立艺术T恤衫上的标语所说的那样,“别人也喜欢的东西不是好东西”。(19)当吉姆·贾木许在1986年被问及“如何看待当今的电影状况”时,他回答说,“我认为公众不能过于愚蠢,至少还能保持怀疑,尤其是当他们面对权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独立艺术家往往得提防着避免被认为,或成为“收拾狗屎的人”。(20)真正的普及会威胁独立艺术家的信誉度,因为在大多数消费者的观念中,独立艺术作品是因为与主流文化相分离而获得意义的,独立艺术家是因为制作主流之外的艺术而获得身份的。桑顿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主流”是流动的,类别的确定基于通过评论来建构出一个他者,从而使对亚文化的投资正当化。(21)因为主流的存在,“独立”才能确认自身的独特性,同时主流使独立更具凝聚力。
但讽刺的是,即使是一个艺术家通过大众媒体的渠道获得成功,独立文化的可信性仍然在独立社区内部保持。涅槃乐队在1992年发布了唱片《滚石》,在这张唱片的封面上印刷着一件手工制T恤衫,上面写着“大企业杂志依旧糟透了”,这是保持受欢迎程度和维持独立信誉之间的微妙平衡。主唱歌手科特·柯本(Kurt Cobain)暗示过,在公共立场里反对企业文化是艺术家远离负面影响的一种手段。同样地,像索德伯格这样,这在独立电影界,长时间受到尊重和敬意的导演,但当他的作品推向主流市场时,譬如1999年的《菩提树下》(The Limey)和2005年的《气泡》(Bubble),可能被视为与他独立创作的根源以及以往“小”电影中形成的美学相冲突。当一些独立导演获得更广泛的成就后,只要他们能策略并合理改进那些尚未真正出售的新的流行艺术,就依旧能获得圈内的尊重和崇拜。当另类文化的元素被煽动,还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流行。无论是像柯本那样,对主流冷嘲热讽或是更微妙的批判,比如索德伯格在2000年拍摄的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中所展现的那样。这是一出传统戏剧,却以反企业化为主题。还有譬如1998年的《战略高手》(Out of Sight)和2004年的《十二罗汉》(Ocean's Twelve)这两部作品,导演在在类型化的材料里,都添加了极具挑战性的风格。
在柯本和索德伯格的例子里,相对于神话而言,独立文化的现实是,尽管反对虚夸的言辞,但是也并没有与主流和其他形式的媒体真正的分割开。在接受和制作层面均是如此。讽刺的是,那些以消费为主的东西,譬如电视节目的真人秀,在文化中占主导位置,这种形式使用了能耸动视听的手段,为观众提供了充分的视听感受,从而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观看位置。但对于独立文化和评论家而言,这种文化“好得如此糟糕”,并意味着丧失可信度的主流趣味。(22)不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立场,或者只是一个拒绝的借口,这意味着独立文化的消费者往往也是主流消费者。同时,企业化媒体也渐渐参与去开发一些适合主流消费的独立风格,从而吸引那些独立消费者。福克斯公司在它2003年-2007年推出的热门剧集《橘子镇》(The O.C.)中,将许多独立乐队的音乐作为电视剧原声。独立乐队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来宣传自己的歌曲,所以在非主流和“企业人渣”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有些分歧还可以通过博弈获得超越。当独立文化通过主流媒体来宣传或表达自己的时候,纯粹性和挑战性的力量都会削弱。在我们的观念中,面对主流和独立时,存在着二元对立的观念,即“独立意味好,主流意味糟”。但这种观念在这样的案例里被动摇了,高负荷的斗争消失了。当面对主流媒体时,我们巧妙地通过策略性的妥协获得表达的可能性。
在通常的流行意义上获得“热销”,同时在独立音乐界中转变为另一种可信性,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被广泛运用在电视广告中,包括莫比(Moby),流线胖男孩(Fatboy Slim)和尼克·德雷克(Nick Drake)的歌,不再仅仅限于在普遍的另类音乐家和粉丝中引起狂热追捧,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进步。这被认为是一种方式,在越发保守以及同质化严重的广播的电台和MTV播放列表中,贴上“热销”的标签,为本不太可能获得传播的“有趣的音乐”争取曝光机会。“热销”,如今被《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评价为“比低于五十美金的音乐会门票”更稀奇古怪的事。(23)大约在同一时间,2001年早期,《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则关于独立乐队苹果立体声的报道,当时这个乐队正挣扎着是否要将自己的音乐授权给索尼广告。标题上写着,“对摇滚乐队而言,‘热销’的含义今时不同往日,”这篇文章满怀同情的将这个案例比喻为“大企业的发薪日”:如果现在你想要听到有趣的、有野心的、具挑战性的流行音乐,你要去的地方不是主流电台而是电视,不是MTV台而是那些为银行、电话公司和止痛药制作的广告。由于流行电台已经限制了少量华而不实的青少年行为,伴随着地下跳舞音乐和另类摇滚的尖叫和重击,一面销售着产品,一面将触角延伸到音乐家所无法触及的领域。(24)
独立艺术家如何面对这种妥协?一个另类乐队的冠军提供了如下的案例:“我们从美国家庭的客厅开始颠覆。”(25)在柯本的T恤衫和独立导演的跨界案例中,合理化销售中,商业机构渐渐开始回归到独立艺术家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热销概念的回归,并不挑战独立结构中反主流的部分。相反,它并不将主流视为反独立的结构,并证明了另类媒体的从业者在保持足够的真实性和自主性的同时,更参与了对主流形象的重塑,并将此视为所能确信的独立文化的基础。
独立即卓越。独立文化是通向卓越位置的关键,从对立的立场来定义独立文化,这意味着观众通过这种手段能显示出不凡的品位。选择去观看独立电影,是观看好莱坞电影之外的一种选择,独立电影的观众允许真实性和自主性进入审美领域,成为相较于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言更为精致、独树一格的精英文化。无论是独立或是主流,无论是生产水平或是消费水平,技术支持均能起到作用。尽管媒体种类各异,但却是相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产物,这都影响着受众对这些产品的体验。此外,独立摇滚的听众和独立电影的影迷往往是同一群受众。这些文化形式的受众是重叠的,主要是年轻人(尽管我们经常将音乐粉丝刻板的定义为年轻人和成人影迷)、白人、受过教育的富裕的城市人。尽管独立电影号称是美国电影里最常为边缘化声音发声(女人、同性恋者、有色人种)的领域,但是美国独立电影运动中的主创在人口统计学上仍旧属于主流观众类型:城市人、受过教育、中产、异性恋者、白人(男性居多)。这并非指责独立音乐和独立电影以及他们的粉丝存在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只是从社会主流的角度出发,通过观众的自我分化,来确定音乐和电影领域里,独立与主流的差异性。(26)部分独立唱片店、艺术之家剧场是反对大型的全国零售商和连锁影城的主要场所。消费者更喜欢光顾小商店和剧场,因为这些地方含蓄的表达了“多即是少”的观念,这是对主流消费经验的一种拒绝。这有利于淡化文化消费领域的传统经验,譬如对电影和音乐形式口味的固化,这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消费者中起到巨大的动员作用。(27)
无论通过何种媒介,“独立”的功能是作为一种品位文化为其观众提供了一种有差别的感受。(28)独立赋予粉丝们一个逃离主流的空间,并能坚持认为自身比商业流行文化更具合法性。这是文化资本的一种来源,精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将自己和群众区分开来,从而延续自身的特权。(29)
参照传统意义上的高级艺术,独立电影所吸引的观众,常常声称自己是出于扩充见识和丰富兴趣去参与和欣赏独立电影的,他们通常有足够资金,还乐意与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团体。20世纪80年代,美国独立摇滚被认为是学院摇滚,因为播放的平台多为大学广播电台。所以“学院”所包括的内涵,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还意味着一个社会阶层。
如果“独立”一度曾是反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反对的企业化媒体以及所支持的意识形态,都属于品位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差别的定位,我们获得一个有力又满是冲突的价值观。大卫·海斯孟德弗(David Hesmondhalgh)在他关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独立摇滚的讨论中,同样认识到这点:“独立是矛盾的,现在看来,它反霸权的目标只不过是通过设置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边界,来维持自身的发展。”(30)但独立在某些方面依旧具有彻底性。“独立”质疑和挑战文化的现状,“独立”的精神是反对媒体既成的结构系统。“独立”颠覆主流中起支配地位的风格、类型和意义。“独立”是一种被剥夺的声音,但其感性在本质上而言是民主的,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创造。
在电影里,“独立”不间断地为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观点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而独立文化在内容上,往往去政治化的,而且并不反动(“保守的独立电影”像“犹太人教皇”那样,头戴假光环——如果它确实存在那也是一个奇怪的例外)。但从生产水平,特别是消费水平上来说,“独立”是一种建立在富裕之上的文化。人们会发现,艺术之家剧院里的装饰、氛围、提供的食品,跟普通影院相比,长久以来保持在不同也更为精细的水平上。(31)“正宗”的独立风格不会出现在打折的沃尔玛商场里,而是由城市的供应商来负责出售。圣丹斯协会的创始人,基邦·泰比安认为独立电影的市场并非像一个包装袋、一份套餐或者一件均码服装那样,将介于18岁~24岁的经常观看电影的观众做简单归类。相反,这些统计里更多的包括有稳定收入,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人,或是温文尔雅的研究生,或塞拉俱乐部的成员,和平主义者以及提倡种族自豪感的人,《纽约客》的读者,或开沃尔沃车的人。(32)
换句话说,独立文化的理想观众属于老生常谈中的自由派精英,从消费产品的角度看,独立电影可以类比为一部进口车或一份订阅杂志。(33)
“独立”曾经是具有对抗性,通过反对主流来强调自身,从而享有特权。“独立”反对当权派,就像同一时期的先锋派,它是属于资产阶级,并服务于基本保持状态的社会功能。在下面的两个案例研究中,我将通过考量它如何在两个来自相同文化和历史背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的实例中发挥的功能来探讨在独立运动影像文化中心的矛盾。托德·索兰兹的电影《爱我就让我快乐》表示出“独立性等同于真实性”的观点。而这种真实性成为好莱坞的另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中包含着这样的观念:电影制作者属于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能自由工作,不受大企业影响。这种理想的独立性是生意逻辑和艺术逻辑相互对抗的产物,是流水线和个体才华的结晶。在这个逻辑里,托德·索兰兹的《爱我就让我快乐》是一部释放着堕落的,郊区版的《汉娜姐妹》(伍迪·艾伦1986年指导)。
《爱我就让我快乐》这部电影由好机器独立制片公司的泰迪·霍普(Ted Hope)和杀手电影(Killer Films)的克里斯汀·瓦尚(Christine Vachon),在十月映画(October Films)的协作下完成(当时十月映画属于环球影业的分支)。《爱我就让我快乐》在1998年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并获得国际评论家奖,公映后引发大量讨论。之后,《爱我就让我快乐》又在包括多伦多电影节和纽约电影节等多个著名电影节上斩获荣誉,并在独立精神奖上获得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原计划在秋季档公映,但当环球影业的首席执行官罗恩·迈耶(Ron Meyer)在公映前观看了电影后,他被其中自慰的场景惹恼了。根据彼得·毕思金德(Peter Biskind)所言,迈耶马上命令十月映画放弃《爱我就让我快乐》的发行。(34)因此,十月映画的独立是一次性的独立,像米拉麦克斯1994年发行富有争议的《半熟少年》(Kids)时一样,出于对上级母公司负责的立场,将影片定位于“一部由艺术家带着强烈独立信誉度,制作而成的,主题灰暗的电影”。这些案例里,体现着独立性的修辞学意义,并透露独立价值的建构过程。
从许多方面看,《爱我就让我快乐》是那种典型的美国独立电影。电影处理话题性问题,包括处理了永远不允许出现在主流电影上的东西——鸡奸。更为臭名昭著的是,这部电影似乎引导成人去同情策划鸡奸的孩子。
在所有索兰兹执导的电影里,他通过对自满的郊区生活的暴露,展现出一种反文化的感性质地,通过叙事和主题构造来反对主流价值观。《爱我就让我快乐》的审美与其低预算(近300万美元)相符合,惊奇的布景设计,昂贵的明星,高饱和的色调,使用更为直接且现实主义的导演方式。(35)瓦尚这样评价《爱我就让我快乐》:“跟所有开创性的电影一样,前沿并具挑衅性。”(36)这种对当代生活毫不妥协的思考,激发着评论界去赞美它的诚实和勇敢。来自知名网络杂志《Slate》的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盛赞这部电影“打破所有禁忌”,将它比喻为“月之阴暗面”,并暗示着这部电影在好莱坞那些安全但雷同度颇高的选择中,提供了另一种独立的选择。埃德尔斯坦也调侃了环球影业对这部电影的轻薄。当时,环球影业的拥有者是邦夫曼家族(Bronfinan family),这个家族名下拥有加拿大知名的酿酒品牌施格兰(Seagram's)。埃德尔斯坦写道,“喝酒的邦夫曼能想着电影里干些什么呢?让一个醉酒的人去生产《爱我就让我快乐》,这是一种何样的讽刺”。(37)这段评价里透露出某种联系性:独立是好莱坞主流商业的解毒剂。《爱我就让我快乐》不仅跟大众市场的电影不同,还反对那些电影。所以好莱坞是危险的,而《爱我就让我快乐》是纯洁的。
这种逻辑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正来源于影响影片正常发行可能带来的极大争议。如果一部影片像烫手山芋那样叫制片厂无所适从,那就印证了它具有独立电影的文化真谛。就像一些流行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部影片在没有拿到美国电影协会(MPAA)审查指标的情况下发行,这就意味着它将失去许多影院和媒体的垂青。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影片将不太容易引起主流观众的注意。还有一些评论同时指出,由于一些制片方拒绝向审查妥协将影片剪到R级的标准内(38),导致影片在发行的环节就遭遇失利。同种情况也往往导致非主流文化的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值提升,他们不会因影片在主题上被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打上道德不适的标签而退避三舍。所以电影公司表面上似乎受到大投资方利益的威慑,而实际上却为上映一部有争议的艺术电影创造了良好市场氛围。正如《综艺》(Variety)的撰稿人托德·麦卡锡(Todd McCarthy)在他的“戛纳观点”中写道:“争议和批评会激发那些有洞察力和冒险精神的观众观看的欲望。”(39)因此在《爱我就让我快乐》此前境遇的前提下,好机器电影公司将影片推广到美国本土市场时,已经根本不需要利用影片有争议的内容和它在发行上遇到的麻烦来招徕观众。评论界大拿如《村声》的J·霍伯曼(J.Hoberman)将这所有的一切定义为“屈从着好莱坞的商业压力”,在评论中提及制片厂的反对意见是受欢迎的,可视为含蓄地佐证影片对自身主题的坚持(40)。鲍勃·伯尼(Bob Berney),好机器发行部的经理告诉《综艺》:“我们力推影片作为黑色喜剧的那方面,而评论界会自觉地引导观众去注意影片所包含的那些惹人不快的话题。”(41)
到了影片上映的时候,《爱我就让我快乐》被看做是一个警示信号。批评界将其视为好莱坞和独立电影在根本上水火不相容的证据。一个观察家写道:“坚持在制片厂制度之外工作已经不再是不受干涉和审查的保证了。自从大公司控制了发行系统,他们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独立电影业。”(42)这种警惕的呼声出于保卫非主流文化免受好莱坞全盘控制的意愿,但事实上《爱我就让我快乐》上映的实情却好像支持了一个全然相反的结论:在几大制片厂的控制范围之外存在着其他渠道可以传播这些独树一帜并无所畏惧的影片。十月映画的一个合伙人约翰·斯密特(John Schmidt)说:“尽管我们在法律层面有权利叫托德·索伦茨把片子给剪了,但是大家一起在好机器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共同商议决定才是最好的方式。”(43)
换言之,电影的创作者应该对影片的发放全程监管。影片中有争议的内容不应该为了配合主流社会的繁文缛节而简单地被删除。与此同时,独立电影的制片方本应只在非主流电影的圈子追求声名,然而现在他们却将电影票房不佳归结于“大多数人的没品位”(universal's fault)。他们指责好机器公司是发行菜鸟,无力为电影做应有的宣传(44)。这反映出独立电影人妄图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他们渴望艺术自主但又寻求利润,希望以质取胜但又仰仗市场行为。简言之就是艺术不应沾染商业的污点,但必要的商业方式使艺术“物有所值”。独立电影制作的核心矛盾在于:正如某一观察者所指出的,电影生产的天然属性中包含了促使具有功利心的电影投资人进行“商业冒险”的成分;而独立电影圈在文化层面上又始终存在着一股冲动,想要逆商业文化的价值理念而为(45)。
《爱我就让我快乐》带来的教训似乎意味着“会引发争议和观众抗议的电影应该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异教徒一样被回避掉”(46)。但是此片却很难被人回避。尽管它的票房进账并没有如制片方和发行方预料的那样多,但它的放映给纽约观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这部分地归功于它引发的争议(47)。它在家影院的首周票房达到平均每块银幕获利3.4万美元的出色业绩(48)。当然《爱我就让我快乐》最后在国内院线拿下了250万美元的票房,相比索伦茨1995年的电影《欢迎光临娃娃屋》(Welcome to the Dollhouse)的440万还是稍稍逊色了(49)。纽约首映后的一周它在洛杉矶又促发了争议,再接下来的一周里它又在超过15个城市里上映。这种市场推广建立在话题性、评论界褒奖和观众口碑三位一体的综合情势下,可视为是“闻风而动的传播术”(50)(aggressive specialized rollout)的典型代表。4周后,它共计在全美83个城市上映,并且票房收益逐周递增(51)。
事实上,就连环球公司都没有真的回避这部影片。尽管环球在表面上拒绝让十月映画上映这部影片,但暗地里贷款给一个新的放映商,以期如果此片好卖也能自己小赚一笔(52)。这种行为受到了先锋知识分子评论界的揭发,即制片厂既不想让自己的股东蒙受不良的社会舆论影响,但是又不肯错过赚钱的机会(53)。这段风波含蓄地揭示出自主权问题才是事件的关键。索伦茨之所以对影片能有自主权,恰恰是因为他代表了环球公司的利益。他的影片是在大制片厂见不得人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上映的,这一事实显然会令那些认为独立电影的存在价值来源于理想主义的独立艺术家和势力的好莱坞财阀之间相互排斥的人感到不悦。
独立电影先锋干将们的希望是:将非主流文化品牌化。独立文化的敏感特质在包装、品牌化和市场化等层面都对立于主流电影和音乐产业的商业主义。但如同约瑟夫·海斯(Joseph Heath)和安德鲁·波特(Andrew Potter)在著作《反叛者的国度》(Nation of Rebels)一书中极有说服力的论述:为什么反主流文化变成了消费者文化?在实际意义上,消费主义的产物和非主流文化的产物诸如独立摇滚和独立电影之间并无真正的区别(54)。归根结底,唱片、电影,还有游戏、服装、海报以及其他独立文化产品依旧处在一种消费主导的经济逻辑之下,他们的流通状况取决于能否给予购买者一种心理上的暗示,即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是社会真正的精英层,即使是这种精英在许多方面将自己定位为是反精英主义的,但他们也同样寻求那些能使自己与主流相区分的文化构成。事实上,反主流文化的产品、风格和理念已被主流的中间商当做一种消费文化的主打商品进行包装、贩卖了数十年。
卖主们需要先锋文化局外人的光环,像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说的,自从1960年代的文化非常期过后,美国的商业尤其是广告业,就开始分享反惯例的、个人主义的和异端色彩的反主流文化价值(55)。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广告不再像之前那样告诉消费者你和别人是一样的,而是诱导你相信自己的独一无二,并激发你对自我的热情。跟独立文化一样,许多主流文化也推销自主性并标榜真实。与《爱我就让我快乐》及围绕它周边的各种论调很相似,一些电视广告为消费者构建明晰且独立的主体形象,用令人愉悦的方式推销可选择性,并以此为特点连结消费者和产品。
在利用“与众不同”和差异这两个反主流文化观念上做营销策略,没有哪个大公司能超越大众汽车公司的显著成果。从1959年开始,甲壳虫汽车的广告就以规避了业内标榜汽车外形、款式抢眼的陈规而闻名。每当提及此款车,总要用一个“丑“字(“尽管我很丑,但是我能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并大力宣传“往小里想”(Think Small)。广告商试图让消费者对品牌营销的传统伎俩有所意识并产生厌烦。甲壳虫汽车产品本身确实小而无特点,但是大众公司和DDB广告公司反其意而为之将它们作为卖点。一本美国广告史的书将它作为案例摘录,“广告商出其不意地将该产品明显的弱点转变成了精心追求的优势”。(56)随着1960年代的消逝,大众公司极为高瞻远瞩地将甲壳虫汽车定位为“反叛常规者的选择”,欣欣向荣的青年反文化群体纷纷对此款车趋之若鹜,并将它易名为“爱虫”(Love Bug)。弗兰克认为“对大众社会批判理论的自觉和认同”(57)是大众汽车公司60年代的广告策略中“最厉害的武器”。换句话说,大众公司是在借用那些批判理论的流行辞令来销售汽车。反物质主义、反工业定制和反集体运动的独特理念竟然给一辆小汽车带来了无限机遇,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在196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中,这些理念往往要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消费品来表达,包括服装、音乐唱片和珠宝。像大众汽车一样,这些产品将自身打上对抗物质主义的标签。正如弗兰克所论述的:“通过与消费主义产品拉开距离的反广告形式,大众公司的广告让美国人认识到一种崭新的消费美学。”(58)
大众汽车品牌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在“Drivers Wanted”宣传战中又有过一次复兴,再一次声张了旗下汽车和青年反主流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将后者视为一种独立文化或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标签性质的广告语——“人在路上,不过是司机和乘客……我们需要一些司机”——听起来很像是之前旋律的变奏:大众公司将消费者区别对待,将他们视为自主的、有行动力的独立个体并将其从被动的接受中解放出来。这种理念已经听起来有些普通了,但“Drivers Wanted”宣传战将这套修辞通过声音、故事和图像,通过各个层面渗透在大众汽车的每一次出场里。因此,当我们想到独立文化一词的意涵以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它的情形时,甚至不得不要将它与电视广告这种几乎无法从主流文化中脱嵌出的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世界性的对反主流文化消费者的献媚,不仅仅是大宗商品借用独立的非主流文化特性而实施的一项营销策略,而与此同时,也反过来起到了推动并散播这种文化的作用。
大众汽车的第一波广告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包括将1997年“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的年度最佳收入囊中(59)。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驾驶着一辆大众高尔夫汽车漫无目的地在路上。他们路过一系列后工业社会的典型景致。影像的低饱和色调强调出他们内心世界的萧瑟和寂寥。与此相反的是这个广告文案呈现的却是轻松和游戏感。高尔夫沿途搭载了一个路人,他用口香糖吹出泡泡,模仿着战争片中的慢镜头,做着好像塑料人般的奇怪舞蹈动作;在经过一片住宅区时,他们在看见一把古老的椅子被丢弃在路边,便将它抬进车里,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椅子竟然在微笑(这是从他们相互间的眼神中反映出来的),于是便把它丢下车继续旅程。整个广告片没有一句对白,但是配乐却将一切都融合了起来:80年代早期的德国新浪潮音乐“Da,Da,Da”重复而无意义的合唱声和轻快的电子打击乐配合着银幕上低调怪异的冒险。在这一分钟广告片的最后10秒钟,一个年轻而时尚的女性嗓音响起:“德国设计制造,大众高尔夫。它满足您的生活,或者,您填补它的空虚。路上的人生,只有司机和乘客。”而“Drivers Wanted”的字幕最后划过屏幕,使整个表达十分完美。这个广告文案很机敏地表现了产品的一项优点——掀背式的后备厢设计使得空间足够承载一把老式座椅,而不是直接吹嘘自己的特点。而更重要的这个文案在文本层面上传递的信息:超现实风格的影像使得人物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观众则被暗示对他们产生认同。所有的细节都经过了精确的设计,以创造出一种打破常规、追求独立的新新人类的形象,而他们个性标签式的“无目的”正完美地体现在驾车四处游荡的行为上。“无目的地生活”的积极性在于它对抗主流价值观所宣扬的“进取精神”和“努力工作”。片中的主角们放弃成为听话的、去商场选购新家具的消费者,却更乐于当马路清道夫。因此,在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鼓励消费的文本中,我们却与表面上反对消费的新一代人产生了共鸣。这些逾越于主流评价体系的别样精英不仅通过这短短的叙事文本,也通过音轨中游戏式的重复“Da,Da,Da”,这种拒绝意义的声音,发现了他们自己。
大众广告战的胜利还得益于ABC电视台的热播喜剧《艾伦和她的朋友们》(Ellen),“星期天下午”的广告片伴随它一同播出(60)。这更增加了年轻、时髦且有良好品位的电视观众对它的好感。这不仅仅是因为广告片中两个男子结伴同行的形象被一些观众理解为同性恋,事实上是大众公司有意地要配合这部剧的播出,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像彭尼百货、温迪汉堡和克莱斯勒汽车选择了保守的态度,认为中庸的价值立场可以保证自己的品牌声誉,稳定住自己的目标市场(61)(别忘了那一时期ABC电视网的广告价格可是它平均价格的两倍,其时该电视网拥有全美超过四千五百万观众(62))。此外,大众公司“与众不同”的信条恰好完美呼应了对于多样性的历史性推崇。多样性已经成为了美国左翼文化,尤其是年轻、时尚的新左翼文化的要素之一。
驾着车四处兜风这在汽车广告片中是惯常套路,但是在大众的广告里,往往被赋予闲逛的色彩放在叙事的核心位置。“路上的人生”,一直在行驶、探索的生活方式,被视为非主流趣味的精髓体验。还有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大众敞篷车1999年被称作“银河”的广告片,也是类似“星期天下午”表现年轻人驾车四处游荡的一分钟广告片,同样零对白,适当配乐,简约的叙事既表现了品牌的理念,又突出它所针对的市场人群。
随着时间,有了越来越多吸纳独立文化的风格特征创造反主流美学的广告案例,比如苹果电脑大获成功的“Get a Mac”广告片(2006-2007),广告中两个男人分别拿着Mac和PC站在一个空白的背景前(63)。拿着PC的男人是严肃规矩的商务人士的行头,他的头发精心梳理过,他的措辞也显得有些不自然。而相对比的是拿着Mac的伙计,看起来很时髦。他的牛仔裤和带帽卫衣反衬着PC男的黑西装领带,他的衬衫敞开着,头发比PC男长,并且总是把手插在前面的口袋里。两个角色的对话分明显出用Mac的人比用PC的人更简约、轻松、理性也更少有麻烦缠身。而潜台词当然是说用PC的人不如用Mac的人酷。通过使用“酷”这个个性的能指,Mac成功地把自己从主流电脑市场中分化出来。跟大众汽车的广告一样,“Get a Mac”这个广告不仅建构了一种品牌更建构了一种风格,一种新的文化类别:我们和他们。它的意义远远超越营销一台电脑。
独立文化正在和消费主义文化融汇在一起。我举出以上这些广告片的例子,不是为了调侃那些认为独立的非主流媒体不应与像电视广告的主流媒体同流合污的人。我尊重他们想要与商业文化保持距离的意愿,尽管大部分的独立文化爱好者正在抹平自主的原创性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的立场差异。事实上我只是想反对那些指责真正的独立文化受到了商业文化的策反或者本身就是大企业文化策略一部分的观点(64)。这种观点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对另类文化的本真性有着不加批判的迷信态度,而迷失在主流标准对差异的划分中,被动地去定义自身的功能。更加错误的地方在于,它误解了独立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认为纯粹的独立性是一种确切存在的事物。与此同时,这种批评隐晦地用一种消极且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主流消费者,将他们视为放弃选择权、屈服于普遍商业势力的一群。这不仅给了非主流文化定义自身的权力,也同时定义了它的他者。我描述了广告如何借用了独立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并不意味着宣判独立文化死刑,只是为了说明主流文化极高的宽容度和适应力,而独立文化不应简单地被视作是一种结果而应是文化的主动参与者——评论家不应居高临下地看待问题,以他们自己的经验作为参照系来获得的判断并非可靠。
主流和另类文化的动力学机制事实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始终处在交互影响的流通状态,而非板上钉钉的水火不容。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真实”都不是绝对的概念,这些概念随时在发生着变动,因为它们取决于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想要如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实际需要。我们也应认识到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这些概念总是理想化、被拔高的。电影《爱我就让我快乐》和大众广告的例子都说明了,消费主导经济自发地寻求细分市场,吸引特定的消费群。而最终的结果是,在文化市场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独立文化产品。而将自主性、真实性、多样性这些修辞注入其中,使得这些独立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中显得更具合法性。这并不意味着说,独立电影或者其他媒体不具它们所自称的价值,而意在指出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固有的、隐藏着的道德公式。
注释:
①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Richard N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56.
②Bernard Weinraub,"Business Match Made in Hollywood," New York Times,May 1,1993.
③Michael Atkinson,"Autonomy Lessons:Paying the Price of Independence," Village Voice,April 14-20,1999.
④Naomi Klein,No Logo: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New York:Picador,1999); Alissa Quart,Branded: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Teenagers(New York:Perseus,2003).
⑤区别是布勒迪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提出的概念和标题,展示了法国社会里文化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这篇论文的想法受惠于他的论文。
⑥On bohemian Greenwich Village,see Malcolm Cowley,Exile's Return: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1920s(New York:w.W.Norton,1934); on the 1960s counterculture,see Thomas Frank,The Conquest of Cool:Business Culture,Counterculture,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⑦Jim Hillier,ed.,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A Sight and Sound Reader(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1); Chris Holmlund and Justin Wyatt,eds.,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ependent Film: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London:Routledge,2005); Geoff King,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Emmanuel Levy,Cinema of Outsiders:The Rise of American Independent Fil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E.Deirdre Pribram,Cinema and Culture:Independent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1980-2001(New York:Peter Lang,2002); Yannis Tzioumakis,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An Introductio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
⑧美国独立电影并没有超越它所在的电影史,在每一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兴起的独立话语,都与工业、技术或是文化结构相互回响着。在Tzioumakis口中的一个重心。我只是考虑美国独立电影和文化的更迭,并用涵盖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仍旧通行的“独立”概念与之呼应。虽然在这段时间里独立电影中出现许多变化,在此期间,好莱坞大制片厂的销售力越来越依赖于那些预算不断膨胀的,在奥斯卡赛季获得威信的大电影。而独立的核心概念在我的描述中却是保持稳定的。
⑨Matthew Bannister,"Loaded:Indle Guitar Rock,Canonism,White Masculinities," Popular Music 25/1(2006):77-95; David Hesmondhalgh,"Indie:The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a Popular Music Genre," Cultural Studies 13/1(1999):34-61; Ryan Hibbett,"What Is Indie Rock?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28/1(2005):55-77; Sarah Thornton,Club Cultures:Music,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6).
⑩这些媒体之间,比如独立音乐和独立电影,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依赖于自身的身份以及营销和推广。以索菲亚科波拉为例,她在自己的电影美学系统里将这些媒体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
(11)Thornton.
(12)Stephen Duncombe,Notes from Underground: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London:Verso,1997),141.
(13)Ibid.,154.
(14)Tzioumakis在他配音的《大集团时代里的独立电影》中,介绍了如何在这个时代中,低预算的电影制作如何在美国独立电影中获得话语特权。
(15)Michael Azerrad,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Scenes from the American Indie Underground,1981-1991(New York:Little,Brown,2001),6.
(16)Ibid.; Tiiu Lukk,Movie Marketing:Opening the Picture and Giving It Legs(Los Angeles:Silman-James Press,1997);Robert Rodriguez,Rebel Without a Crew or Howa 23-Year-Old Filmmaker with $7,000 Became a Hollywood Player(New York:Dutton,1995); David Rosen,Off Hollywood:The Making and Marketing of Independent Films(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90).While we should not take claims of heroic thrift such as Rodriguez's at face value,they are objects of significant mystique within communities of aspiring filmmakers and champions of altemative cinema.
(17)Rodriguez; Rick Schmidt,Feature Filmmaking at Used Car Prices,2nd ed.(New York:Penguin,1995); Bret Stern,How to Shoot a Feature Film for Under $10,000(and Not Go to Jail)(New York:Collins,2002).
(18)Quoted in Pribram,13.
(19)The vendor is Diesel Sweeties,http://store.dieselsweeties.com/products/nothing-is-any-good-if-other-people-like-it-shirt(accessed February 27,2009).
(20)Ludovic Herzberg,ed.,Jim Jarmusch Interview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sippi,2001),68.
(21)Thornton,87-115.
(22)Klein,77-79.
(23)David Browne,"License to Shill," Entertainment Weekly,January 12,2001,79-80.
(24)John Leland,"For Rock Bands,Selling Out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11,2001.
(25)出处同上。
(26)对于班尼斯特(Bannister)提出的一个论点,即独立电影特权和白人男性身份的关系。
(27)新的媒体承办商比如亚马逊、iTunes和Netflix的兴起,当然会提供出一个多种选择的平台,这个平台不断变化,从电脑到信用卡,令人叹为观止。见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将这种变化与流行文化的影响放在一起讨论,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生意的未来意味着少即是多?(New York:Hyperion,2006).
(28)Hibbett.
(29) "Cultural capital"is Bourdieu's term.
(30)Hesmondhalgh,38.
(31)Barbara Wilinsky,Sure Seaters:The Emergence of Art House Cinem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111-114.
(32)Jibab Tabibian,"Afterword," in Rosen,283.
(33)Hibbett makes many similar points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e rock in particular.Hibbett也对独立摇滚的讨论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
(34)Peter Biskind,Down and Dirty Pictures:Sundance,Miramax and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Film(New York:Simon &Schuster,2004),334.
(35)Howard Feinstein,"A tender comedy about child abuse? What is Todd Solondz up to? " Guardian(UK),March 26,1999.
(36)Dan Cox,"Happiness over at October Films," Variety,July 2,1998.
(37)David Edelstein,"Bleak Houses," Slate,October 18,1998(accessed October 2,2008).
(38)参照Janet Maslin 所著Happiness:Music Is Easy Listening and Dessert Is Hard to Take,New York Times,October 9.1998.
(39)Todd McCarthy,"Dark Side of 'Happiness' Explores Sexual Taboos,"Variety May 18,1998.
(40)J.Hoberman,"Kin Flicks," Village Voice,October 7-13,1998.
(41)Andrew Hindes,"Happiness at B.O.:Gotham Venues Embrace Controversial Pic," Variety,October 13,1998.
(42)Andrew Gumbel,"Letter from Hollywood:How 'Happiness' Won," The Independent(UK),October 25,1998,p.16.
(43)Dan Cox,"October axes 'Happiness'; Good Steps In,"Variety,July 13-19,1998.
(44)Biskind,336.
(45)Rosen,273,用语出自"undercapitalized business venture."
(46)Atkinson.
(47)有关影片票房上税的情况,参见Biskind,336;有关影片纽约首映的情况,参见Hindes,"Happiness at B.O."
(48)Christine Vachon with Austin Bunn,A Killer Life:How an Independent Producer Survives Deals and Disasters in Hollywood and Beyo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6),92.
(49) "Mixed Bag for the Rest of the Indies," The Hollywood Reporter,January 7,1999.
(50)Monica Roman and Andrew Hindes,"Happiness Forduo:Vets Berney,Kalish handle distrib' n for pic," Daily Variety July 23,1998.
(51)Andrew Hindes,"'Elizabeth' Rules:Art films bow big as Oscar season nears," Daily Variety November 9,1998.
(52)Biskind,336,一语出自"under the table",有关环球公司在这部影片上的收益情况参见Nigel Andrews,"Make way for the originals," The Independent(UK),April 15,2000,p.8.
(53)Gumbel.
(54)Andrew Potter and Joseph Heath,Nation of Rebels: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New York:Harper Business,2005);Potter和Heath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本来讨论当代文化,尤其突出讨论了1960年代的一些特点。
(55)Frank.
(56)Juliann Sivulka,Soap,Sex,and Cigarettes: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Belmont,CA:Wadsworth,1998),304.
(57)Frank,64.
(58)Ibid.,68.
(59)Bob Garfield,"The Best of TV:VW," Advertising Age,May18,1998,S1.
(60) "The Puppy Episode:Part I" originally aired April 30,1997.
(61)Joy Brema,"Volkswagen and Pop Culture Branding," The Brock Press,March 24,2004.
(62)Ron Becker,Gay TV and Straight America(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166.
(63)我所描述的是苹果电脑在美国的广告,他们在英国和日本投放的广告另有不同.Cyrus Farivar,"Apple's 'I'm a Mac,I'm a PC' Ads Cross the Pacific," Engadget,November 13,2006,http://www.engadget.com/2006/11/13/apples im a mac im a pc ads cross the pacific/(accessed October 2,2008).
(64)此类批评的范例还有Klein的表述,另有Quart and Kalle Lasn,Culture Jam:How to Reverse America's Suicidal Consumer Binge-And Why We Must(New York:HarperCollins,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