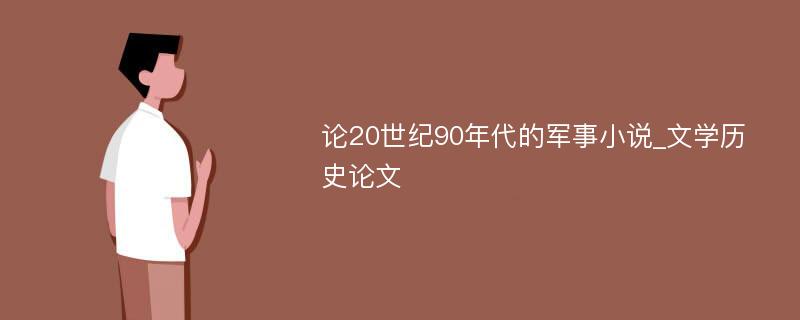
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及军旅小说,治军事文学的人们总是以无限怀念的口吻忆及八十年代,并把那个百废俱兴的时代称之为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第二个高峰。的确,作为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八十年代具有其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而且,军旅小说在八十年代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其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重大的飞跃,这是值得文学史家们永远记取的。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军旅小说已经在八十年代形成了高峰,而随之以后的九十年代便进入了所谓“低谷”状态。这样的描述未必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正是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延续与发展,虽然,在它前进的路途中不再有鲜花与掌声相伴,但这也使得作家们进一步沉入到现实的土壤中,在艺术的路途上艰难地探索着(这当然是就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仍然执着于艺术,并最终结出了虽然不算丰硕,但也还算得上晶莹剔透的果子的作家们而言)。我们看到,无论是就表现生活的深度还是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作家艺术个性的张扬方面,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一
战争,是军事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具有着常写常新的魅力。尽管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炮火与硝烟,甚至我们的军队连八十年代那样的短暂的战争也没有遭遇过,可战争仍然成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作家们所描写的大都是自己所经历的战争,那么,九十年代的作家们所写的更多地是他们心中的战争,不过我们这里所言“心中的战争”并非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战争的作家们对战争生活的壁虚构,而是凝聚了他们对战争的一种全新的思考与审视。对于战争,九十年代的作家们所保持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尤凤伟从有关战争的典籍中切入到我们民族半个多世纪前所发生的那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后相继推出了《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远去的二姑》、《姥爷是个好鞋匠》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战争小说,生于五十年代的邓一光早在他出生前战争的硝烟炮火便从他所生长的这片土地远去,但父辈们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却奇迹般地复活在了他的艺术生命中,终于使他在写了一系列的知青与都市题材的小说后以独具特色的战争小说而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同样是作为革命军人后代的姜安则以一个当代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与观照父辈们在战争年代的人生经历,从而赋予了她的也是写战争生活的新作《走出硝烟的女神》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年轻的赵琪和徐贵祥充其量也就是参加过那么一段短时间的南线战争,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审美视角却没有投向南线战争,而是指向人类的远古时代,即使离现在最近的时代也早已过去了七、八十年,如赵琪的《苍茫组歌》,与战争生活的疏离,使得他们得以跳开战争来审视与观照战争,并站在更高的角度描述与表现战争;而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战争经历又使得他们对战争的具体描述驾轻就熟,不至于把战争沦为个人意绪的产物。可以说,正是尤凤伟、邓一光等人的战争小说为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增添了新的特质。他们继承了徐怀中、叶楠、朱春雨等人在八十年代初所张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艺术的笔触伸向人的心灵深处,深刻地剖析并揭示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小人物以及身处战争之中的人们的本质真实,并对战争所蕴含的哲理与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
尤凤伟是以表现身处战争中的小人物的命运而蜚声九十年代文坛的。在其有关战争的系列作品中,作者直接将人物置于战争的残酷处境中,并在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中让其作出艰难的选择。《生命通道》中的苏原医生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人生的两难处境之中。如果不是为父亲奔丧而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也许正和妻子做着医学救国的美梦,可现实却残酷地撕碎了他的梦幻,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选择:一方面是求生的本能与欲望,另一方面是民族的良知与知识分子的正义感。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将人物置于矛盾的二元对立中让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将两者有机地杂揉到一起,让其在求生的苟且之中不断自我谴责着,并时刻伺机寻求着一条摆脱为虎作伥的路。当他终于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不满的日本军医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救助别人的生命同时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的生命通道时,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可恰在此时,他也开始遭到了来自各方面、首先是来自妻子的误解,不过灵魂得到升华之后的苏原医生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崇高的事业中而无法顾及个人得失了。他忍受着妻子误以为他已沦为汉奸而和真正的汉奸出走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实施着他的“生命通道”计划。可随着他的计划的一次又一次的实施,他所遭受的误解也愈益加深,以致在他战死多年后他的名字仍被当作汉奸而载入地方志中。一方面是战争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由此而迸发的民族的正义感与责任感所导致的英雄的行为的剖析,另一方面是被典籍所淹没了的战争与战争中的人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这不但是尤凤伟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在其他的战争系列小说中的美学追求。
与尤凤伟的擅长描写战争中的小人物的英雄壮举不同,邓一光是从另一个方面切近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本质的。曾经在都市与知青题材领域徘徊了近十年的光景的邓一光终于从父辈们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中找到了一座文学的富矿,或者可以说,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邓一光终于在战争的硝烟与炮火中找到了生命的契合点。在邓一光的身上,蕴蓄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渴望,而昨日的战争恰好成为他情感的喷火口,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昨日的战争,倒不如说他在借昨日的战争渲泄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其说他所写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人,倒不如说他在借这些军人形象的塑造张扬着自己关于“男人”(文化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上的)的全部理想。在《走出西草地》中,他把这种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内容借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出来;不过邓一光并非反现实主义地一味编制理想的花环,在他的作品中,理想与现实是有机地统一为一体的。他把人物置于生命的极境加以表现,一方面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肉体的伤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怀疑与冷遇,这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考验;不过邓一光笔下的朱成元和桂全夫们却经受了这种考验,而支撑他们的恰恰是作者所极力张扬的人格力量。不过,邓一光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对于前辈志士的赞誉并没有影响他以一个当代人的视角对历史、对战争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走出西草地》的故事框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对于理想人格的张扬和对于历史的反思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同样是表现父辈们的红色革命经历,姜安走的则是另外一条道路。作为女性作者,姜安更为关注的是战争中的女性们的命运,是那些曾经冲破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强加于广大妇女身上的桎梏而终于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的妻子和母亲们的命运。在新作《走出硝烟的女神》中,姜安以女作家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一群战争中的女性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其实,与其说姜安在这部作品中所关注的是女性们肉体上的艰难与困苦,倒不如说是她们的灵魂所经历的痛苦的裂变过程。作为中国妇女中最先觉醒的一群,她们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羁绊走向了革命。可是,残留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意识也在侵蚀甚至砥砺着她们的灵魂。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所接触的是代表着知识女性、工农妇女、红色后代以及老革命等各色女性形象,正是这群经历各异、性格千差万别的女性为我们演出了一场战争中的生命景观。其实,这部作品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新生命的孕育本身,而成为战争对女性灵魂的洗礼,并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战争中的历史真实以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新与旧的矛盾。就表现女性与战争的角度而言,姜安开拓了战争小说的一个新层面。
论及九十年代的战争小说,我们无法对赵琪的《穷阵》和徐贵祥的《决战》视而不见。如果说,尤凤伟、邓一光等作家试图以对昨日的战争的更为冷静客观的笔触深入挖掘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的历史的真实,以深刻地揭示战争的本质,那么,赵琪和徐贵祥在这两部作品中则将艺术的笔触伸向更为久远的古代,在远古的人们对于“阵法”的艺术化的穷究之中表现人类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终极理想。赵琪《穷阵》中的苏子,自幼生于军中从而厌倦了战争,可命运却又赋予他承担起爷台所未能完成的对阵法的穷究的重任。爷台钻研阵法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幕僚,而苏子却纯粹将之看作是一项用来自娱的艺术。他厌倦战争,不愿意参与到任何一方的战争中去,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迫不得已地卷入到一场战争中去。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矛盾着,最后终于在破阵的同时促使交战双方的和解,自己潇洒地离去,表现了作者对于和平生命的无限向往。徐贵祥的《决战》中的攻羽历史尽数十年的艰苦生活似乎也是为了在与司马卓的北蓼军对峙的过程中求得最终的和解,而一旦他手下的军卒射杀了司马卓后,他也以自己的生命张扬了其人格力量。如果说赵琪在《穷阵》中所极力表现的是苏子对于尘事功名的超脱与潇洒,那么徐贵祥在《决战》中所极力颂扬的则是攻羽人格的力量。不过殊途同归,两个作品所诉说的是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于和平理想的向往以及人类面对战争与和平所产生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通过对中国九十年代战争小说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从数量上远逊于南线战争所带来的八十年代战争小说的大量繁荣,也无法同五、六十年代尚武的社会风气所带来的战争小说的丰收相比,但在艺术成就上,九十年代战争小说是最高的。统而言之,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是以对于战争场面与战争进程的描写作为其主要特征的,而战争中的人则退居了次要的地位。尽管其中也不乏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但其艺术形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政治情绪的产物。而且战争视角的单一也影响了其艺术形象的塑造。可以说,从描写战争场面与战争进程的细致来看,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采取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从艺术审美原则的角度来看,它则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悖的倾向。尤其是对于一种空泛的崇高感的追求不同程度地妨碍了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也不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张扬。因此,如果一定要给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冠以现实主义称呼的话,那也只能说它是一种不够彻底的现实主义。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及人道主义旗帜的张扬,战争小说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叶楠的《画眉鸟婉丽的歌声》以及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等作品,以新的视角观照战争,写出了战争中的人的生动性与复杂性,不过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作品无论其数量还是反映现实以及人性的深度而言,都无法与九十年代的战争小说相比。因而可以断言,九十年代的战争小说是经过作家们近十年的探索,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它不但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趋向与美学观念,也将战争小说引向一片崭新的审美天地。
二
如果我们将理论探索的触角伸向九十年代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那么我们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以陈怀国为代表的农家子弟作家群所写的反映农家军人特有的军旅“情结”以及他们在部队挣扎奋斗经历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批评家们以陈怀国的一篇小说的名字《农家军歌》而笼统地命名为“农家军歌”,而且此类作品也曾一度为批评家所诟病,就连这批作家自己也在其后来的创作中有意识地纠正其偏颇倾向。陈怀国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完成了以对农家军人的反思为其重要特征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石钟山的《飞越盲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家军人在部队艰难的对自我的超越过程。的确,九十年代初期所出现的“农家军歌”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欠缺与拙稚,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农家军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承担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对崇高与神圣的淡化不同程度地消解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所一以惯之的“英雄”情结(笔者在另一篇谈及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论文中将其称之为“英雄神话”的解构)。作者一反五、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对英雄人物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的有意无意的拔高,而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卑琐的一面也大胆地揭示了出来,使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中出现了新的人物系列。应该承认,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部分真实。我们的军队是一支主要由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尽管在城市以及发达地区逐渐进入了现代化,可在边远地区的农村,农民仍然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又加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桎梏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更为先进的思想,因此,他们的视野便只能局限在以从军为手段的对土地的逃离以及逃离土地之后为寻求永远彻底的逃离而采取的种种无奈甚至有几分卑劣的手段上。这是生活的真实,但生活的真实并非艺术的真实,“农家军歌”的系列作品恰恰是在由生活真实的向艺术真实的转化上显示了其创作者功力上的不足,从而形成了其作品对小生产者意识仍然占着主导地位的农家军人们同情有余而批判不足的倾向,叙述表面的苦难与悲凉有余而向着农家军人的心灵深处拓展不足,影响了作品思想的深度与力度。可以说,“农家军歌”是以对现实的军营生活的揭示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一次突破,尽管这种尝试不甚成功,但其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发展史上毕竟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影响,那就是彻底打破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形或无形的禁锢;另一方面,其艺术上的欠缺之处又引发了更多的作家对于中国农藉军人心灵与命运的探讨,九十年代以农民军人的情感与命运作为主要审美视角的军旅小说的繁荣不能说与“农家军歌”的出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
如前所述,作为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农民的身上必然有着妨碍我们的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劣根性。实际上,“农家军歌”恰恰客观地昭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我们这支以农家子弟作为主体的部队是一支农民队伍的结论,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从1927年成立以来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以及思想文化上的不断提高,而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文明程度的现代化的军队,我们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因此,同样是以农家军人作为主人公的作品,阎连科的作品却与“农家军歌”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说《中士还乡》中的中士在退伍前后的种种表现是出于农民式的善良加之军队培养的结果的话,那么,在最近创作的中篇小说《大校》中,作者则以一家父子两代人的命运与追求展示了军营文化(或者称之为现代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悖离。
阎连科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一代来自于农民但却摈弃了小生产者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并掌握了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农家军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在塑造农家军人形象方面,阎连科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不但超越了别人,也超越了自我。
在表现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以及对农家军人身上小生产者意识的批判方面,黄国荣的《兵瑶》和陈怀国的《遍地葵花》可谓是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前者表现的是一个农家军人毁灭与新生的故事,后者则是通过一个具有浓厚小农意识的农家军人的堕落完成了其对于军人身上的农民性的批判。如何把长篇小说《兵瑶》中古义宝的人生转折看作是源于一次堕落,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了一些,其实,恰恰是那一次从传统道德观念上来说的所谓“堕落”的行为才是他内心真实感情的流露。如果说在这之前除了因为临入伍却被弟弟尿湿了军被而愁眉不展的农家子弟古义宝还有点真实性可言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在那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之前的古义宝则一步步地被别人也被自己装入到套子之中,扮演着别人需要他自己也需要扮演的角色,开始了他那以农民式的狡诈创业的全过程。可贵的是,作者的笔锋就在人物颇为得意的时候转了过去,让他跌入痛苦的深渊,并在对于痛苦的反思中开始了新生。全书上下两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完成着对农家军人小生产者意识的批判。在陈怀国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中,作者一反其早期创作中对农民军人生存处境的苦涩而悲凉的咏唱,将批判的视角直指其早期作品如《毛雪》、《农家军歌》、《黄军装黄土地》中曾经投注了极大同情的人物,而且把人物置于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比照,深刻地揭示了小生产者的习性在很大程度上妨害着军队现代化的要求,故而,凭着阿Q 式的狡诈即使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但终究要被时代所淘汰。应该说,作者对于农民军人的本质及其命运的揭示是深刻有力的,它不但标志着陈怀国创作上的飞跃,也体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种颇为流行的创作倾向,从对农民军人命运与生存处境的苦涩咏唱到对农民军人身上小生产者意识的深刻揭示与批判,标志着九十年代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内在矛盾的,仍应首推朱苏进在九十年代初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炮群》,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八十年代以来一以惯之的朱苏进式的风格表现了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奋斗的苏子昂与他深刻的精神悲剧,但是,作者仍然在他的人物身上投注了过多的理想色彩而使得其人物更多地表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冷硬,那种朱苏进式的强烈的论辩色彩也仍然存在于作品中。因此,单独看来,这部作品也许不失之为一部比较好的作品,而对于熟悉朱苏进作品的读者,尤其对于不断向前拓展的九十年代文坛来说,则不免因其审美意象的单调而略逊风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种遗憾。倒是与朱苏进的风格颇有几分相近的黄国荣的《陌生的战友》在揭露现实的矛盾方面表现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深刻洞察与透彻的分析。在这部篇幅不算太长的中篇小说中,作者以“我”对于一个已经去世的“陌生的战友”的追根究底的寻找表现了一个挚爱着国防事业但又孤高自傲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悲剧,并通过这种悲剧尤其是主人公死后其科研成果被剽窃的结局引发人们对于阻碍着我们的军队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因素进行了深思。可以说,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上来说,都在同类题材中属于上乘之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九十年代表现和平生活的军旅小说主要在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与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及冲突之间徘徊,毋庸讳言,这是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重大的题材领域。而且,作家们在这个领域也有了比之八十年代同类题材的军旅小说更为纵深的开拓;但是,也应看到,在表现人以及军人的人性与人情尤其是将军人置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加以探讨方面,这些作品仍然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不免让人多少感到有些遗憾。
三
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无论是战争题材的还是表现现实军营生活的,都显示出了创作者们鲜明的艺术个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抑或可以说是历史向作家们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八十年代那种狂热的浪漫主义激情已经渐趋消退,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像八十年代那种仅靠题材的翻新便可以名噪一时的现象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了。这也就要求作家们沉下心来,向艺术的精与美的方向努力。八十年代,虽然也有一些作家如徐怀中、叶楠和朱苏进等表现了自己比较鲜明的艺术个性,但这样的作家毕竟寥寥无几。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思想的多元化所带来的审美的多元化,作家们已经把艺术个性的张扬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从而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艺术个性的作家。提起尤凤伟、邓一光、赵琪、张惠生等作家,我们在阅读他们作品的同时感受的更多是他们的艺术个性。尤凤伟娓娓道来地叙述着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的一群无法左右自己的行为的小人物的悲苦,于平淡之中隐含着郁闷与激忿的情绪。邓一光则天马行空地把自己全部的理想主义激情挥洒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洋溢于作家的血液之中的狂傲不羁的个性。赵琪写小说如同作诗一般,对艺术氛围及意境的追求,可谓到了惨淡经营的地步;但他的作品又绝无刻意为之的生涩与刻板,而是洋溢着浓郁的诗情,令人惊心动魄的美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让你为之一震。阎连科的作品于质朴纯厚之中凝聚着人生的哲理,黄国荣的作品则时时流露着作者的聪颖与机智,张惠生的作品在对于“荷花淀”风格的追求中显示着其特有的深沉与力度。应该说,正是这些作家们不懈的艺术追求装点着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坛,使其放射出璀璨的光辉,并带动了一批年轻作家向着艺术的至真至美的方向拓展。这些作家及其他们的作品也向我们展示着,九十年代军旅文坛已经越过了八十年代的喧哗与躁动,向着更为稳健成熟的方向迈进。
如果我们把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虽然失去了其在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但其在沉默的艰难徘徊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仍然是可喜可贺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指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与历史提供给它的各种机遇或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来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横向的角度相比,它不但失去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在中国文坛所占据的主流地位,而且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技巧的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远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题材的作品相比,出现了相对的滞后状态。当然,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九十年代军旅小说主流地位的缺失主要来源于作家们思想观念与文学观念的陈旧。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主流地位是与一段特殊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联的,那就是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整个民族都处于一种高涨的政治情感之中,对于昨日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自我陶醉感使作家们,尤其是从战火与硝烟中走出来的作家们将审美的视角对准了往日的战争,而曾经经历或未曾经历过战争的读者们也希望从文学中感受到那想象中颇有浪漫色彩的战争或者他们向往的军旅生活。可以说,是作家们和读者的共同需求与相互作用促成了五、六十年代军事文学的繁荣以及其在当时文坛所处的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作品不但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他们那种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们的审美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多地以传统的思维定势看待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失之于浮光掠影的再现,而缺乏对于战争以及战争或者军事生活中的人的本质的认识与揭示。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高涨的年代,而九十年代就是作家们进一步向着人性的深处拓展的年代。而我们的军旅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同程度地与时代脱了节。无论是表现战争还是表现和平时期军事生活的作品,即使是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都有待于进一步向人的心灵深处拓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现出战争的全部的神奇瑰丽以及军队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军人深邃丰富的心灵世界。再不会有任何非文学性的因素为我们提供像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文学那样天赐的良机了,要想重新占据文坛的主流地位,只有靠我们自己,靠创作的实力以及以敏锐的目光对战争与军事生活的深刻感情。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个世纪。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邓一光论文; 尤凤伟论文; 决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