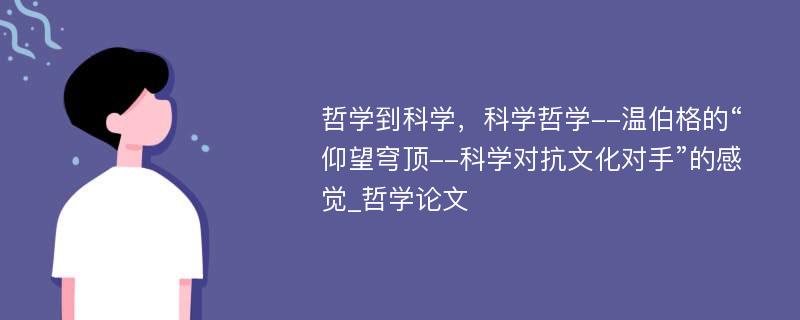
哲学对科学和科学哲学——温伯格《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读后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哲学论文,读后感论文,苍穹论文,对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温伯格(S.Weinberg,1933~)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由于创立把电磁作用和弱作用统一起来的“标准模型”理论的贡献,与萨拉姆(A.Salam,1926~1996)和格拉肖(S.Glashow,1932~)共享197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在许多研究论文之外,温伯格还出版过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的两部专著,以及关于宇宙学和基本粒子的两本科普小册子。此外,温伯格亦发表了不少关于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见解,积极参加到一些科学与文化的热门话题的讨论里来,成为在国际学术界的一位活跃的作者。本文主要介绍和评论温伯格近年出版的一本文集《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1,2](以下简称《仰望》),结合他十多年前出版的《终极理论之梦——探求自然界的基本定律》一书[3,4](注: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正文中所引用的均为《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和《终极理论之梦——探求自然界的基本定律》两书中译本的页数。部分引文由本文作者依据原文做了修订。) (以下简称《终极理论之梦》),谈谈有关科学和文化的一些问题。
2 科学以宗教为其对手
温伯格这本文集包括有他从1985年到2000年发表的二十余篇文章,原文书名叫“Facing Up”,即脸朝上的意思。在这本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埃(Tycho Brahe)的在其生前工作的天文台遗址上竖立的一尊塑像的照片。布拉埃的塑像做仰首观天状,温伯格说的“Facing Up”,指的就是这种仰望的姿势,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精神的象征。
温伯格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是这样写的:
“布拉埃、开普勒和牛顿,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的各项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关于世界的冷静观点。我们能够发现得到了的那些自然定律,都是同个人无关的,都是同一种神圣的规划或者任何人类特有的地位都没有牵连的。这本文集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仰望这些发现的必然性而奋斗。这些文章表达了一种理性论者、还原论者、实在论者和忠于非宗教解释的观点。总而言之,昂首仰望就是与低头祈祷相反的一种姿态。”
我觉得,温伯格这几句话表达了一种挚诚的科学精神。大家知道,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之日,正是她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之时。早期的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先行者,为了捍卫科学真理而饱受教庭的迫害,在不同的程度上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在其后的400年里,科学和宗教一直在争夺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支配权。由此看来,科学精神一开始就是以宗教信仰为其对手的,温伯格的观点正是这一种传统的延续。
3 科学以哲学为其对手
不仅如此,温伯格这本文集的副标题“科学反击文化对手”里所指的对手(adversary,或译“敌手”)或者对立面,除了宗教之外,还包括哲学。这也是温伯格一贯的观点。例如,在《终极理论之梦》里,除了有一章的标题是针对宗教的“上帝怎么了”之外,还有一章干脆就标明了“反对哲学”的主题。
在这一章里,温伯格说:“如果预先没有一种想法来指导,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不过哲学原理一般不能给我们提供正确的预想。”“物理学家当然也怀着某种工作哲学(working philosophy)。我们大多数人的哲学是一种简朴和便利的实在论,也就是科学理论的要素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信念。不过这也是从科学研究的经验学来的,而很少来自哲学家的教导。”“我们不应当指望靠它[哲学]来为今天的科学家提供任何有用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进行工作,或者告诉他们会发现什么。”([4],133页)
他还说:“从物理学家看来,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就是哲学了——仅有的例外是一些哲学家的工作能帮助我们避免另一些哲学家的错误。”([4],134页)不过,温伯格并没有完全否定哲学家对科学家的影响。他指的是“哲学家的见识偶尔也帮助过物理学家,不过一般是从反面来的——使他们能够避免其他哲学家先入为主的偏见。”([4],132~133页)“哲学的影响还是否定式的,它只是帮助科学摆脱哲学本身的束缚。”([4],136页)
在文集《仰望》里,温伯格也指出,“哲学偏见”是科学的“老对手”([2],44页)。而另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R.Feynman)则这样讲过:“科学真正存在所必需的,是在思想上不承认自然界必须满足像我们的哲学家所主张的那些先入为主的要求。”[5]由此可见,这两位物理学大师都认为,科学必须摆脱哲学偏见的束缚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温伯格还说:“我们不需要哲学家指令如何将哲学论证用于科学史或者科学研究本身,就像我们不再由科学家自己去确定科学发现如何运用在技术或者医学上那样。”([2],168页)这里的意思明显是,就像科学家发现了科学规律之后,在技术上的应用是工程师的事一样,科学研究应当由科学家自主进行,不需要哲学家的参与。
杨振宁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里谈到“哲学家的哲学”时说得更彻底:“我认为它和物理学的关系是单向的。物理学影响哲学,但哲学从来没有影响过物理学。”在回答关于如何评价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成就的问题时,他又说:“我认为坂田对物理学有相当的贡献,不过这不起源于他的哲学,而起源于他对物理实际的认识。我不同意他自称起源于哲学。他从哲学出发的那些作法都是得不出结果的。我认为他越少用哲学,他的成就越大。”[6]
不过,杨振宁这些话也许说得太绝对了。我们赞成费曼讲的另一句话:在寻找新的科学定律的时候,“可能哲学也会有助于你去猜想。”([5],178页)即是说,哲学对科学起到的一般不是指导的作用,而是在提出猜想或者假设时可能起到启发和借鉴的作用。例如,玻恩(M.Born)亦这样讲过:“我曾努力阅读所有时代的哲学家的著作,发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没有朝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前进。然而,科学使我感觉到稳步前进,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7]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玻恩既承认哲学对于科学思想确有启发作用,又认为科学是依靠本身的理论思维,而不是依靠哲学取得真正的进步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打过这样的比方[8]。 一位军事家能不能说《孙子兵法》或者别的什么兵法指导他打了胜仗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因为兵法书里讲了许多战略和战术,固然可以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但在每一次战役里采取怎么样的打法,毕竟是要由指挥官自行决定的。同样,你也不能够说“三十六计”指导你打了胜仗,因为根据具体情况要采用哪一条计谋,亦是要由指挥官自己决定的。如果应当“以攻为守”的时候,你用了“空城计”,那就一定会打败仗。所以,我理解费曼说的“可能哲学也会有助于你去猜想”,就是不同的哲学方法有可能供科学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运用的意思。
一方面,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往往受到某种哲学思想的支配,特别是会受到他所信奉的教条所支配。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同在某种哲学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一门描述性科学,例如生物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注重于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时候,受到讲究分析和归纳的哲学思想支配的科学家,就会由于适应科学现况的需要而取得成功。但在一门科学发展到了综合的阶段,例如建立能量守恒定律的那一段时期,就是讲究转化和统一的哲学思想支配的科学家取得成功的良机。又如,在放射性现象发现之后的20世纪初,本来处于领先的法国居里学派主要研究的是在放射性蜕变中释放的能量的来源,注重的是运动形式的转化,后来就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英国的卢瑟福学派主要研究的是原子和原子核的结构,注重的是物质的微观结构,接连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也是不同的哲学思想适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极好范例。
聪明的军事家能够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聪明的科学家亦能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采取不同的研究路线,各种兵法和哲学会有助于军事家和科学家决定他们的策略和计谋。所以,如果运用得当,兵法对于军事家、哲学对于科学家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那其实是参考和借鉴的作用,而不能够说是起到了指导或者引领的作用。从以上的一些引文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主张是同当代的一些物理学大师的观点一致的。
另一方面,的确有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在他们坚信的某种“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证伪的信仰问题。譬如,有人声称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取得了什么成果,或者靠求神拜佛治好了什么病痛,都是类似的一些问题。科学和对于科学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后者不存在与评价科学相同的经验标准。怪不得温伯格把哲学和宗教当作是科学的两种主要的文化对手了。
4 科学家不需要科学哲学
温伯格在《仰望》一书中,花了不少篇幅谈论关于科学的哲学,即科学哲学的问题。他观点鲜明地引用了他听说过的一句话:“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就像鸟类学对鸟类的用处一样。”([2],7页)
动物确实不需要,也不可能懂得动物学的知识,它们是依靠先天的本能以及个体的经验而在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而这种先天的本能亦不外是经过长期优胜劣汰沉积到个体基因里的历代祖先适应生存的遗传信息。例如,猫当然不懂得力学,但它天然具有掌握身体平衡的本领,无论怎么样跳跃或者坠落,都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体态,最后采取四脚落地的姿势。力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探索,方才研究出描写这种运动技巧的力学模型。
科学家亦不需要懂得科学哲学,他们的大多数是在研究工作中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念。这就像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专门学习逻辑学,而是在自己的思维、讲话和写作中形成合理的逻辑推理一样。温伯格在《仰望》里反复说,“我们通过从事科学而了解科学的哲学,而不是通过其他的途径。”([2],69页)“科学大部分是由内在因素指导的。”([2],84页)“许多科学家对什么是科学方法没有什么概念,这就像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为什么能够不倒下来没有什么概念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假如他们对这些问题想得太多,往往就会摔跤了。”([2],70页)
温伯格一方面指出:“我知道,在战后积极参与物理学进步的人当中,没有谁的研究得到过哲学家的工作的重大帮助。”([4],134页)另一方面又讲,“很少有科学哲学家把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作为他们自己的工作阐述的一部分。”([2],69页)在文献[3]里,他还引用了两位哲学家在这方面的言论作为佐证。一位是盖尔(G.Gale),他说科学哲学的“近乎经院哲学的论证只能引起极少数科学家的兴趣。”另一位是鼎鼎大名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他说“在我看来,要读我书的科学家或数学家认真照我说的去做,那是最不可能的事了。”([4],133页)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有盖尔和维特根斯坦那样的自知之明。例如,国内有些研究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作者认为: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不属于物理学家,而属于哲学家研究的范围;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停滞不前的地方,正是需要哲学研究全面介入的地方;他们的任务就是运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方法,系统地澄清与量子测量等问题有关的基本概念。
可是,上面所指的几个问题明明都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物理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们岂可越俎代庖?更不要说他们从来没有被证明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了。这正好应了温伯格批评一群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说的话:“他们不希望被看作是科学的依附者或者附属物,而希望被看成独立的审查者,而且也许是个高级审查者……”他们“希望……进行独立的判断,不仅仅是去判断进步是如何取得的(这是他们份内的事),还要去判断是否取得了进步。”([2],75页)而且,国内的那些哲学研究者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想要判断科学上的是非,还以为自己能够动手解决那些本该由科学家研究的问题。
按照温伯格,“即使哲学教条过去对科学家是有用的,但它变得……在今天的危害大于曾经起过的作用。”([4],135页)他指的“过去”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时代。实际上,就20世纪的量子理论而言,根本没有发生过哲学家成功地帮助过物理学家的例子。有的只是反例,例如玻普尔(K.Popper)早年在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判决性实验”,后来他反复为此做了检讨[9]。
再说,量子力学诞生80年来,其中基本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滞不前。就在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在贝尔不等式、交缠态、消干效应和测量理论等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突破。量子光学、量子信息、量子计算等方面正在蓬勃发展,并且近20年形成了量子力学的一种很有希望的新解释[10]。应当说量子力学一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国际哲学界正在忙于吸收这方面的新成果,而不是试图对物理学家们指手画脚。例如,2003年,《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已经收入了The role of decoherence in quantum theory(量子理论里消干效应的作用)这一条目,可见其受到哲学家重视的程度。
有人会说,马赫(E.Mach)和庞加莱(J.H.Poincaré)等著名哲学家对经典物理学概念基础的反思与批判,不是为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方法论的启迪吗?
我们说,这两位学者首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他们为相对论做的思想准备,主要是对科学概念的分析批判,而不是哲学上的论证。例如,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马赫的《力学发展史评析》和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他们的科学著作仍然是主要。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哲学观点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例如马赫的实证论哲学使他反对原子论(注:在参考文献[2]里多处谈到了这一点,见第25、94、107页。),庞加莱的约定论哲学使他断言“几何学的公理……是约定。”“一种几何学不会比另一种几何学更真;它只能是更方便而已。欧几里得空间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最方便的。”[11]这些观点都被不久之后微观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作为哲学家的马赫和庞加莱对20世纪初新物理学理论的诞生,主要起到的不是积极促进而是消极阻碍的作用。再说,这两人对量子力学的诞生,在思想上亦完全没有产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
5 坚持实在论,反击后现代
上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了以学术界左派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旗帜下集聚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一些学说。本来,如果它们仅仅属于在文学艺术里时常花样翻新的一些流派,也不会吸引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是,其中的极端言论在世纪末形成了一股反科学思潮,引起了科学界普遍的反感。
199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索卡尔事件”(Sokal's affair),引发了一场大争论[12]。在《仰望》一书里,收进了温伯格就此事件发表的两篇文章。他指出:“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存在着那些‘后现代’,他们喜欢涉足到量子力学或者混沌那样的前沿领域,装饰他们自己关于经验具有片断和随意的本性的论点。有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自然定律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按照温伯格的意见,那些言论都属于“学术上的胡言乱语”([2],114~115页)。
本来,运用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科学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可能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但把那种做法推到了唯我独尊的极端,完全否定科学规律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就走向反面了。温伯格认为,一般的社会建构论关于“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是有关某些客观事物的,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精神,它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观点“确实……过于夸张了”。而那种“激进社会建构论”或者属于“强纲领”的关于“科学理论除了社会建构之外什么也不是”的观点,“在我看来是荒唐可笑的。”温伯格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要害是“不仅怀疑科学的客观性,而且还厌恶客观性”([2],84~85页)。他在《终极理论之梦》的“反对哲学”那一章里也说过:“从科学是一种社会过程的看法得出结论,说我们最终的科学理论产物是因为社会和历史作用影响那个过程的结果,完全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4],150页)
温伯格坚持实在论的立场,他指出:“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物理学定律,仅仅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2],110页)“科学问题的选择和处理的方法可能依赖于科学之外的各种影响,可是一旦我们找到了正确答案就会发现它就是那样,因为那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2],121页)
温伯格在书中还着重谈到他的朋友、已故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甚至还有两篇以“库恩的不革命”为主标题的文章。温伯格认为,在库恩早期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里所得出“现在的标准和过去的标准之间完全无从比较”的结论是“太离谱了”。([2],70页)因为“只有在科学中的革命标志着从前期科学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自然的某些方面的转变程度,科学革命才似乎符合库恩的描述。牛顿力学的诞生是一个大的范式转变,从那以后我们对运动的认识就没有发生过符合库恩描述的范式转变。”([2],168页)温伯格指出,在库恩的后期著作里则“走向了谬误……他认为在科学上,我们实际上并不是朝着客观真理前进。”([2],70页)温伯格认为,库恩实际上“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本质。”([2],131页)
温伯格说:“库恩的所有这些观念使得像我自己这样以为科学的任务是引导我们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的科学家感到苦恼。然而,库恩的结论在那些对科学的主张持有更加怀疑的态度的人那里是合乎口味的。”不过,温伯格亦指出,“库恩对那些援引他的著作的人并不总是感到愉快。”并且引用了库恩1991年说过的一句话:“我是那些发现强纲领的声明荒唐可笑的人之一,那是解构主义走向疯狂的一个例子”,说明库恩并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对他的意见的曲解。([2],158~159页)
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极端形式传到国内之后,在科学普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等科学人文研究领域里占有不小的地盘。有些以“科学文化人”自居的“科学文人”(注:这是我在一篇文章里起的名称,见参考文献[13]。)舞文弄墨,拉帮结派,不遗余力地贩运西方的学术垃圾。有的人攻击科学家,说科学家没有资格谈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问题;有的人贬低科学,说科学不过是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的不是“真正的问题”,也同自然界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甚至把科学探索的本质说成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性的修炼”,等等。他们还把国内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具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大批判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等等,企图把他们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所遇到的批评说成是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
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物理学家温伯格和索卡尔等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批评,那不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驱动吧。其实,他们的观点不是信奉什么“主义”的结果,而是从自身的科学工作中形成的一种朴素的实在论,事实上代表了多数善于动脑筋的科学家的态度,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
6 为还原论辩护
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里写了一章“欢呼还原论”之后,又在《仰望》里继续发挥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在上面引述过,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就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一名不信神的“理性论者,还原论者和实在论者。”
什么是还原论?他在《终极理论之梦》里说,虽然各人讲的还原论意思不尽相同,但“每个人讲的还原论都有一点共同点,那就是等级体系的意思。即是说,一些真理比起它们可以还原到的那些真理(就像化学可以还原到物理学那样)说来,没有那么基本。”([4],43页)而在《仰望》里他又说:“更深的层次往往是更为微观的层次。”([2],33页)温伯格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还原论对于天气预报或许是或许不是一种好的指导,可是它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见解,这就是不存在逻辑上不依赖于物理学原理上独立的气象规律。”([2],91页)“没有只基于自身而不需要还原地从电子和原子核的性质来解释的化学原理……也没有可以不需要通过对人脑的研究而最终能被理解的独立的心理学原理。”([2],94页)
不过,温伯格不是一位排斥整体论或者突现论的还原论者。他说:“我不把我看作是一名不妥协的还原论者,我把我看做是一名折衷的还原论者。”([2],11页)他举例说,“统计力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那是因为当你处理非常大量的粒子时,就突现(emerge)出了新的现象。”但是“统计力学里没有不能从更深层次推演出来而单独成立的原理。”([2],33页)虽然“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不大可能对理解像超导那样的突现现象有很多直接的帮助……”然而,“尽管突现的现象确实突现了,但最终还是从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突现出来的。”([2],48页)
由此可见,温伯格既坚持还原论,又承认突现论。如果你高兴的话,也可以说他的观点是还原论和突现论的辩证统一。实际上,与其说温伯格积极鼓吹还原论,不如说他为还原论辩护,反击那些整体论者或者突现论者对还原论的攻击。从书中我们知道,温伯格提到的反还原论对手,首先是安德森(P.Anderson),其次是盖尔曼(M.Gell-Mann),这两位也都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不过,在《仰望》一书里,有多处摆明同安德森争论,而盖尔曼则没有直接点名,只是提到了盖尔曼主持的“圣菲研究所……是反还原论科学的避难所。”([2],90页)
温伯格同安德森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是否应当花费巨额资金建设SSC的问题而展开的。SSC是“超级超导对撞机”的简称,它是设计用于粒子物理研究的一台前所未有的超大型加速器。温伯格和安德森分别处于这场辩论的正方和反方。作为粒子物理学家的温伯格极力为SSC宣传和游说,那是很自然的,他在《终极理论之梦》和《仰望》里都用了不少篇幅谈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凝聚态物理学的安德森则认为对于粒子物理的支持太过分了,进而反对还原论的支配地位。顺便提一下,安德森在20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亦发表过认为我国过分重视纯粹的理论物理学研究的议论。安德森对于温伯格批评的反应,可以参看他为《仰望》写的书评(Phys.Today,July 2002)。
在《终极理论之梦》的最后一章和《新版后记》里,讲述了SSC 从预备到初期建设,直到于1993年被美国国会否决的历史。温伯格在《仰望》里嘲笑那些为了争夺研究经费而反对SSC的物理学家们说,“当由超级对撞机下马节省下来的基金被纳入到普通预算的时候,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2],99页)
7 科学发展的历史观
温伯格在《仰望》里以“物理学和历史”为题的一篇文章专门谈到科学史问题,在这方面他表示同意他的朋友、著名的科学史家霍尔顿(G.Holton)的意见,展开了对另一位科学史家也是一位社会建构论者的柯林斯(H.Collins)的批评。(注:这一节里的引文除另行指明外,皆出自文献[2]第100~111页。)
温伯格一方面承认,“人们应该用事情本身所处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待”历史,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学史和政治史是不同的。“当今的道德和政治标准不会与政治史或社会史相关,而现在的科学知识以某种方式与科学史有着潜在的关系。”温伯格指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中的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未知的”,“完全不存在再现过去的办法”。所以,必须要以现代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待过去的科学发现,才能够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所以,温伯格针对历史学家柯林斯的言论说,“一些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自然规律的实在性,可是在描述过去的科学工作时,却总是不愿意考虑现在的科学知识……问题在于这些历史学家忽视了现有的科学知识,就等于放弃了不能由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通向过去的线索。”([2],124页)
温伯格在这里指的主要是过去科学实验中的许多细节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现了。但我们有些科学史研究者的研究比这还要仔细,例如某位科学家蓄的是络腮胡子还是山羊胡子,他的故居门牌是12号还是14号等等,使我们想起了大量存在于我国“红学”研究里的繁琐考证。正如《红楼梦》里人物的许多生活细节同文学没有多大关系一样,科学家的许多生活细节同科学也没有多大关系。虽然那些考证的功夫值得我们佩服,但那毕竟与科学的发展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
温伯格还引用了霍尔顿批评一些科学史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一句话:“许多最近的哲学文献宣称,科学只不过是以一种永无止境的、没有意义的布朗运动的形式,从一种形式……不辨方向或者漫无目的地摇晃到下一种。”
温伯格针对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物理学定律就像棒球规则那样,完全是人为制定的产物的言论反驳道:“自然规律并不像棒球规则。它们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在它们的最终形式里,文化的影响已被消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些物理学规律仅仅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
8 科学反击文化对手
近年来,科学和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受到热烈讨论的话题。温伯格这本书的副标题标明了他的用意,我们就用这个副标题来作为本文最后一节的题目。
温伯格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科学和文化的关系的。他指出,“在现代科学诞生之时所需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在物理科学的世界与人类文化的世界之间隔开了一道鸿沟。贯穿整个历史没完没了的麻烦,都来自于从科学发现中吸取道德教训或者文化教训的这种企图。”([2],127页)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始的近代物理学,确实是从同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同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决裂中成长起来的。从那时候起,长期以来科学和文化好像是在两条轨道上运行。虽然科学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哲学和科学早就分了家,像宗教、哲学和道德那样的社会文化不必参加到科学本身的内容里去,所以后来就有了“两种文化”的讨论。
然而,人类社会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她在社会中起到了越来越强的作用。这不仅是指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且指自然科学成为了人类知识中最经受得起检验和最具有恒久价值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渐渗透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里去。所以,不少科学家认为,科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温伯格里就曾经说过:“像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我也认为科学发现属于20世纪文化中最宝贵的部分。”[14]费曼亦说过:“……对这个奇妙世界的欣赏以及物理学家看待它的方式,我相信,这些乃是现代的真正文化的主要部分。(可能有其他学科的教授们会反对,但我相信他们是完全错误的。)”[15]
根据这种看法,科学并不置身于文化之外,缺少科学的文化是不完全的文化。企图把文化独立于科学之外或者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做法,都是一些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做法。例如,独立于科学家的“科学文化人”这一提法就是一种不适当的称谓。他们自称为“科学文化人”,是否意味着只有他们才懂文化,科学家就不懂文化了?正如“生物科学家”是从事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一样,“科学文化人”就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来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而那些用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方法,把自然科学作为对象来研究的学者,即是说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等在内的“科学人文学”的研究者,或者还包括科幻作家、科学家传记作家等等,还是叫做“科学文人”比较合适,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称呼那些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人文学者为“文人”。一句话,“文化”不是“文人”的专利。这是我们在讨论科学和文化的关系时必须首先明确的前提。
译文订正
我没有看到过2003年台湾出版的Facing Up 的繁体字译本《科学迎战文化敌手》,不知道翻译得怎么样。2004年上海出版的简体字版《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的译文质量一般还可以,但亦存在着不少不应当出现的差错。以下是一些突出的例子:
第18页,“英国协会……的校长致辞”。原文是the presidential address...to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这里的 British Association 是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即1831年建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简写。协会的president称“会长”。 应译“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长致辞”。
第23页,“牛顿学派”的原文是Newton scholars,应指牛顿的研究者或者研究牛顿的学者。
第24页,“固体的”的原文是solid,此处指原子,应作“实心的”解。 牛顿认为一般的物体内部都像海绵那样有许多孔洞,好让以太一类的微细物质出入其间,而坚硬的原子则是实心而无孔洞的。“固体的”是形容宏观物体的,不可以用来形容原子,否则就会得出液体或者气体是由固体构成那样的荒唐结论了。(国内几乎所有科学史出版物都把牛顿这句话里的这个形容词译错了。)
第29页,“光子”的原文是phonons,应译“声子”。
第30页,“量子力学是一种基本原则,所有物理学的表述都要遵循它”的原文是 quantum mechanics is a grammar,in terms of which all physics must be expressed,意思是:全部物理学都必须用量子力学这种语言规则来表达。
第45页,“相位”的原文是phase,这里是“阶段”的意思。
第96页,“每件事情都处于量子力学的底部”的原文是 everything is at bottom quantum mechanics,意思是:“每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按照量子力学运作的。”
第104页,“比率”的原文是rates,应译“时率”,即“对时间的高阶微商”,“比率”是 ratio。
第108页,“理想主义(idealism)”和“反现实主义(antirealism)”应为“唯心论”和“反实在论”。
第113页末行,“人类”的原文是humanities,应译“人文科学”。
第119页,“量子实体”的原文是quantum reality,应译“量子实在”。“实体”是entity。
第119页,“合理处理”和“定量的推理”的原文分别是rational processes 和quantitative rationality。这里同一词根的两个词译法不同,令人费解。后一词组似应译成“定量的合理性”,好与前面呼应。“推理”一般用的是inference。
第161页,“张量”的原文是tension,应译“张力”。“张量”是tensor。
第173页,“英国史教授克尔(Kerr)兼……研究员刘易斯”。这一句子容易使人误认为有克尔和刘易斯两位教授或研究员,其实只有一位教授兼研究员刘易斯。原文里的the Kerr Professor of English History指一种为纪念Kerr 这个人物而设立的英国史教授职位,或者以Kerr冠名的“讲座教授”,应译“克尔英国史教授某某”。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还原论论文; 终极理论之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温伯格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仰望论文; 物理学家论文; 自然哲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