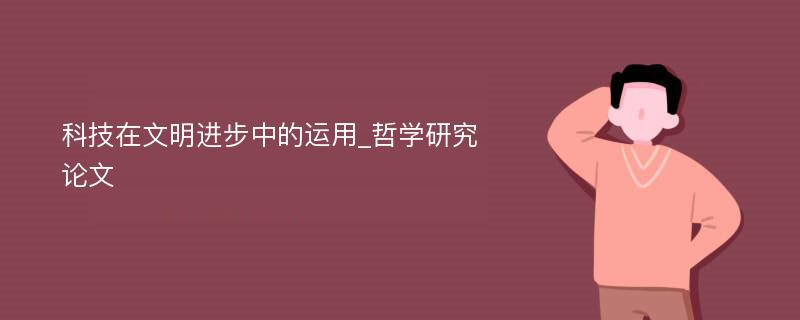
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技术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类无时不刻都在使用着技术,因为充斥在人类周围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工物,技术使用俨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技术使用不仅是技术在世的方式,也是人类生存的处境,人类因此具备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角色——技术使用者。国内学术界曾对实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对使用这一形式却重视不够。使用和使用者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在学术领域里缺失了,技术使用因此也就成为一种“熟知而非真知”的现象。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技术使用的分析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技术本质、技术生产、技术异化等大量技术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马克思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至理名言,揭示人类的目的和任务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人是如何在自然界中打下他们意志的印记?又是如何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而这种劳动正是在技术的使用中实现的。技术在本质上“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①可以想象,离开了技术的使用实践,人类不可能走出人猿相揖的界别。人类的历史,随着技术使用而逐渐演化:以手工工具为主的使用实践使人类彻底从动物界里脱胎出来;以机器为主的使用实践又使人类成为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主体;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又将人类带入了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的理论沉思。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表现为机器之类的劳动资料,他从劳动过程的视角指出,劳动资料延长了人的“自然的肢体”,在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到桥梁和传递作用,是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②马克思还形象地把劳动资料中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把那些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的总和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并进一步提出机器的发展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器官进化的工艺史。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蒸汽机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从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迅速引起了一系列产业的革命性变化,如纺织业、机器加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等。在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普及,商品经济迅速取代了自然经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同样,美国也借着工业革命的翅膀飞速赶超了英国,工业产值位居世界之首。对此,马克思总结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③
人类凭借着技术的使用来改造世界,而建立在技术使用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就成为了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特征的人类个体的存在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而要维持生命个体的存在就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要求即对食物的需求,“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人们要生产这些物质资料就得使用一定的物质手段,石器技术的使用使人类告别了猿类,取火技术的使用又使人类告别了生食时代,而自从掌握了栽培技术后,人类不再仅仅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这样,技术使用是与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生产过程中,因为使用的技术手段的不同,不同时代的人们造就了不同的生产关系,最初人们使用石器来加工和获取食物,后来使用铁器、铜器、蒸汽机、电力机,现在使用计算机等等。马克思考察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初期机器的发展过程后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⑤技术手段的革新,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因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⑥
技术使用在塑造了不同生产关系的同时,还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一旦满足了自己的基本物质需求,就会滋生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人类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将自己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之后也就将自己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了,人类有了自由思索的时间,并慢慢将其作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哲学家是最初的思想者,之后科学家从哲学家中分化出来,开始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把科学在中世纪黑夜之后重新兴起和迅速发展这个事实称之为“奇迹”,⑦并将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归功于生产,断言科学和技术虽然是相互影响的,但科学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也明确提出了生产是科学发展的动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⑧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大规模机器使用的看法。马克思指出,只有机器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自然力即风、蒸汽、电等才第一次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而自然力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改进的基础。在使用中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从而形成了发达的机器体系,即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这使得工人们聚集在同一个地点,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之下进行机器生产,从而大量降低了资本生产的各种成本,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17世纪的机器技术的应用,“为当时的大多数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支点和刺激”。⑨
在肯定技术及技术革命积极作用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忽视人的作用,强调技术只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自然界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都只是“人类工业的产物”。⑩人类虽然是各种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但是也离不开技术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人类发展早期阶段,因为人“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11)所以此时的人是比较全面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使用机器技术的结果使得劳动成为了同工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即“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己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12)此时的人成为了单一的、异化的个体……马克思时刻提醒着我们,人类创造和使用技术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身,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人类一切工作的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是得依赖于技术的使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3)
科学力量只有通过机械的运用才能被占有,才能加以利用,才能变成直接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再强调技术的强大力量,但他们也看到了滥用技术改造自然的后果,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14)因为每一次对自然界的征服活动都会给人类自身带来一些副产品。也就是说,机器技术的使用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繁荣,但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可逆的后果:“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5)所以,对技术的使用,人类始终要保持一种理性、一种睿智。
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提高生产效率与生产效益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技术使用的分析紧紧围绕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有浓厚的批判色彩。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应用机器才给无产者带来了很多否定性的后果,造就了人性的扭曲和变异,“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16)机器大工业使工人沦为了机器的零部件,剥夺了工人劳动的快乐,更糟糕的是“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7)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建立在此制度上的任何进步,比如,机器的改进、工具的改良、新技术的采用、新科学的应用、新市场的开辟、新产品的开发等等,都只会加剧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加速劳动群众的异化和贫困。因此,马克思号召无产者要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18)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人们才能自由地使用技术,并自由地享受对技术的使用。
二、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
技术哲学就是关于技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性思考,虽然人类很早就使用了技术,有了对技术的理性反思,但在哲学的发展史上,技术哲学却姗姗来迟。随着18世纪蒸汽革命的到来,人类揭开了大肆改造自然的新篇章,这才为技术哲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技术进行过系统深入的哲学反思,但只是到了1877年,“技术哲学”一词才正式出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字典中。这一年,德国工程师卡普(E.Kapp)《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面世被认为是技术哲学诞生的里程碑,他在书中提出了“器官投影说”,认为一切工具和机械都是人体器官的外化,是向大自然的“投影”,是人体结构对自然的“置换”,“这样,大量的精神创造物突然从手、臂和牙齿中涌现出来。弯曲的手指变成了一只钩子,手的凹陷成为一只碗;人们从刀、矛、桨、铲、耙、犁和锹等,看到了臂、手和手指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很显然,它们适合于打猎、捕鱼,从园艺,以及耕作。”(19)人也正是通过工具的使用而不断地创造自身。
世纪之交,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了“经验转向”的趋势。1998年,荷兰学者克罗斯(Peter Kroes)和梅莱斯(Anthonie Meijers)共同提出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研究纲领。经验转向的凸显实际上源自于传统技术哲学的困境。技术哲学如米切姆所说的是“作为一对孪生子孕育出来的”,(20)自诞生以来就分化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传统——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执着于是技术如何产生的,设计被当成是工程活动的精粹,也被珍视为解决现实世界控制和操纵技术问题的关键;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青睐于技术使用的社会后果,从而聚焦于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对技术的制约。这两种技术哲学传统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对技术使用本身的关注,从而导致了技术黑箱的形成,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就是要解蔽技术的“黑箱”。
继“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研究纲领之后,克罗斯又提出了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的技术解释学论纲,认为任何由人所设计制造的技术人工物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都具有物质属性,这表现为特定的物质结构,是自然规律的显现,人的意图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都具有功能属性,这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和计划性,意味着在人类活动的具体情境中它能够被用来实现某种目的,与人的意图密切相关,“人工物的功能是不能脱离于人类的使用情境的”。(21)克罗斯进而将人类与人工物有关的活动情境分为了两种基本类型:(22)一类是设计情境,这里人们关注的是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考虑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该如何建构一个物质系统;一类是使用情境,这里社会功能是人们首要考量的,关心的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该如何使用人工物。克罗斯的研究激起了人们对“如何才能够在设计实践中构桥搭架于一个客体的功能描述(设计过程的输入)和设计中所给定的结构描述(设计过程的输出)之间的鸿沟之上”(23)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从而推动了人们对技术设计的积极探讨,并已取得不少成果。
在国内,继陈凡教授率先把技术设计引入到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之后,乔瑞金教授等人也对技术设计进行了哲学反思,他们认为技术设计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所指涉的重要概念,是建构当代技术哲学的核心话语”。(24)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人工物功能实现过程的技术使用却依然处在技术哲学的边缘地带,鲜有人问津。即便如此,还是有技术哲学家对技术使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主要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唐·伊德(Don Ihde)、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和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等。
阿伦特认为,工具和器具的纯粹的“人的价值”仅限于劳动的动物对它们的使用,世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主要表现于劳动的动物所使用的工具和器具。她指出,以往关于工具与人的“手段—目的”之争只是一条无止尽的悖论,而要想摆脱所有纯粹功利主义哲学中的无意义困境,唯一的出路在于,“撇开由使用事物组成的客体世界,转而依靠使用自身的主体性”;(25)海德格尔也肯定了使用的重要价值,他把人工自然界看作是一种联系结构:“……锤子、钳子、针,它们在自己身上就指向了它们由之构成的东西:钢铁、矿石、石头、木头。在被使用的用具中,‘自然’通过使用被共同揭示着”;(26)米切姆对使用进行了经济学剖析,肯定了使用一词具有比制作更大的包容性,认为一项技术的使用至少有三个不同且重叠的含义:技术功能、技术功能的目的或结果、使用它的动作以完成它的技术功能;并从被使用对象的角度将使用过程划分为制作、维修或报废;从经济学的视角把技术使用的过程划分为: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密集)过程、节省资本的(劳动力密集)过程、中性的过程、潜在的技术和现实的技术、发明和创新、自然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等之间的比较;(27)伊德则认为,“技术是它们在使用中所是的东西,是它们在与使用者相联系的过程中所是的东西……没有离开关系和相关情境的所谓的‘单一’技术或工具之类的任何事物”,(28)所有的技术都是在生活世界里的使用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它们只有进入了使用者的手中,成为使用中的技术才成为了活生生的技术;芬伯格则强调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技术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某种类型的“使用”,他的次级工具化理论就对技术如何通过使用融入到情境之中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其中,在原创性这一环节中,使用者以数不清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技术装置和系统,使用者在初级工具化时期是消极的,但在此阶段能够改变技术甚至以与原初设想相反的方式使用它们,这个时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使用者个人原创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时期。(29)
在国内,舒红跃教授不惜重墨强调技术使用的重要性,认为技术使用是对已经存在的或已经在此的技术人造物的“现成”操作、控制或利用,而技术的发明、设计和生产最多只能提供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框架”而已,“技术完整的生命只有经过使用者的使用,经过使用者把自己生活世界的质料‘填入’制造者所提供的‘框架’之后才能实现”。(30)
通过近年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技术使用具有不同于技术设计的独特性。虽然就具体的人工物实践而言,技术设计是技术使用的前提,使用的总是某种业已存在的设计好的客体;但就总体的人工物实践而言,技术使用总是技术设计的前提,设计的过程不仅受使用的指引,还会涉及各种工具的使用。设计的价值也只能在使用中得到实现,设计只是为使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完成设计者设计人工物的意义。因此,技术使用比技术设计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历史也更为悠久,拥有着与技术设计不同的独特活动特征和价值底蕴,无疑也值得人们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本体论上,技术使用是技术的寓身之所;在认识论上,技术使用是技术活动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从价值论上看,技术使用则是技术价值的最终完成,由此对技术使用本身进行专门、系统的哲学解读颇有必要。其实,对技术使用活动本身的关注不仅吻合技术现象学“朝向事物本身”的精髓,也符合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趋势,直面人类实践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无疑更有利于理解技术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现时代,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的图景里使用者主体性的缺位,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没有使用者在场的关系、技术发展的历史是看不到使用者身影的历史,最终跌入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囚牢,而打破这一囚牢的关键就在于使用及使用者在技术中的归位。我们认为,技术哲学将人工物的聚焦点从设计范式转移到使用范畴上来的契机已然降临,对技术使用进行剖析必然会为技术哲学的理论宝库添加瑰丽色彩,也能使我们更加明晰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人类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些中肯的建议。当然,“多学科性质使得技术使用既兴趣盎然但也困难重重,这是一个缠结着模糊性和未解问题的领域”,(31)我们任重而道远。
三、技术使用的内涵解读
技术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它是如此引人瞩目却又如此令人困惑,它光芒四射却又暗含着层层危机。因此,当下人们开始将对技术的关注点聚焦到其物质载体——人工物上,人工物虽然是设计的结果,但它更是使用的结晶,因为其不仅着眼于使用,而且实现于使用之中。
技术的使用本质。使用活动是技术的寓身之所,技术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凸显自己的意义,释放自己的功能,技术结构也只有在使用中实现自己被建构的价值,技术的本质其实就是使用。“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因为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使用’”。(32)
海德格尔在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时,提出了“座架”这一独特的术语,用来思考现代技术的本质领域。在他所刻画的“座架”里,技术通过使用成为了一种解蔽方式,促逼着自然不断地转化为可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无疑,此种技术的促逼是向自然提出的蛮横要求。在制作阶段,作为劳动对象的工件承担着对整体性的指引任务;而在使用阶段,用具是通过制作阶段的工件所指引的整体性来与使用者照面的。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但正在制作中的工件是对某物可用性的创造,就连制作本身也是把某物用作某物的活动,因此,作为技术实践活动的制造本身就是对使用的揭示。处在使用中的某物都有着指向某种“质料”的指引性。桌子指向木材这种质料,木材指向树木,而树木则指向天然或人工这两种生成方式,这样,使用揭示了整个自然界。
技术的四种类型,即作为物体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33)也体现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技术使用计划的酝酿就是作为知识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而技术使用计划的展开就是以作为物体的技术为客体所展开的一系列行为,也就是作为活动的技术也同时现身。技术本身就是要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动态过程,是将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的过程,而这一切只能通过使用通达。可见,对技术的理解离不开对使用的剖析,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而不是设计或者别的什么。因此,离开了使用活动,技术以及人工物只能是空洞的、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丧失了其存在之所。
使用的技术内涵。使用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它甚至还在处于襁褓之中时,就在根基尚未牢固的罗马语系中发出了明确的技术讯息。从词源学上讲,英语中的“use”在拉丁语中的最初形式就是“usus”与“utilis”,原意是指“功利性”、“技巧性”等。可见“使用”一词本来就暗含着对“技巧性”的功利性使用,带有明显的技术意蕴。而在语用学中,“使用”原来指的就是对人工物的使用,不存在对非人工物的使用,使用情境已经预设了作为客体的人工物的使用对象的地位。我们可以说使用锤子、剪刀、桌子等,但很少会有使用矿石、太阳、河流等说法。因此,“使用”更多地是指向与事物特别是与人工物的啮合。换句话说,“使用”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技术性内容,特别是现代社会,使用越发离不开技术了,因为,“我们对人工物的使用是基本的”。(34)
而在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史中,使用活动的技术色彩也愈发浓厚。原始的人类从树上跳下来弯腰捡起了石头,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有意识的使用实践活动,之后根据自身使用经验的初步积累对石头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造,打制成了人类的第一件技术性人工物,理所当然地跨入了技术时代——石器时代,接踵而来的是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以人们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技术人工物为标志。可见,人类社会的使用活动与技术内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在技术的使用中建构着自己的王国,不断地向更高级、更优越的物质生活世界前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不但通过使用存在着、游戏着、消费着和战争着,还因为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而同步发展着和进化着,人类的身体器官、思维能力、物质机能也都是在技术使用活动中而不断地得到锻炼和强化并日趋成熟的。
技术使用:技术和使用在现实世界里的纠缠和显现。技术使用实际上就是使用者对技术的使用,是作为使用主体的人基于一定的目的而对“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35)所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活动。当然,对技术使用的界定离不开对技术发明、技术设计和技术制造的理解,因为一个完整的技术活动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发明、设计、制造和使用四个阶段。使用虽然是技术活动的核心和目的,但离开了其他三种技术实践,人们在技术使用上也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发明和设计将自然规律提炼为技术原理,并提供了技术原理现实化的可能性,而制造则将这种可能性物化为技术人工物,它们共同为技术使用预置了“已经在此”的技术。
可见,技术使用虽然是一个专属于技术使用者的实践活动,是使用者对技术的操作、利用和发挥,目的是通过某一技术功能的实现以满足自己某一方面的需求,但它却是以发明家、设计者以及制造者的发明、设计和制造活动为前提的,这样,技术使用凸显的虽然是使用者主体,但却隐含了发明家、设计者以及制造者等主体的身份角色。
毋庸置疑,技术使用内含着三大结构性要素——技术使用的主体(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人工物)及技术使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互动过程),其中,按照其表现形态可以简单地说,技术使用的主体属于人的要素,技术使用的客体属于物的要素,而技术使用行为本身则属于关系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技术使用的有机整体。
人的要素。“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6)因此对于技术使用这项实践活动来说,它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人。而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37)普罗泰戈拉那句骄傲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直以来是后人的误读。阿伦特指出,普罗泰戈拉的原话是“pantōn chrēmatōn metron estin anthrōpos”,其中,“chrēmata”一词并非“万物”的意思,而是特指被人使用着、需要着或者拥有着的东西,因此,正确翻译过来应该是“人是一切使用事物的尺度”,这无疑意味着一切自然事物都能够被视为人类潜在的使用对象。
物的要素。技术使用总是主体对客体——技术的使用,而技术又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因此,物的要素主要也就是指技术人工物,技术人工物是同时具有物理结构属性和社会功能属性的物质实体。其中,物理结构性揭示了自然的规律性,社会功能性则彰显了人类的意图性。技术使用的客体种类丰富多样,凡进入使用者的视野中的人工物都有可能成为技术使用的对象,直接表现为工具、机器、容器、技术产品等物质形态的技术。
关系要素。人和物是创新中的两个实体要素,除此之外,就是关系要素了,关系要素只能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技术使用中的关系要素表现于人与物之间相互联系、彼此限制的互动过程中,即技术使用过程。这些关系要素虽然没有一定的物质形态,只是一种关系质或关系态,但却是技术使用活动的灵魂所在,这些关系态的表现形式有知识和价值,正是在知识和价值的流动和反馈中,技术使用主体和技术使用客体才发生了生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作为外延的技术使用类型也是异常丰富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就有不同的技术使用类型:
根据设计者所预先设定的功能,技术使用有预设性技术使用和创造性技术使用之别。当使用者面对着技术人工物时,实际上面对着的是由设计者所提供的使用计划,使用者在使用技术人工物的过程中“可以追随设计者的计划,也可以展开他们自己的计划”。(38)当使用者按照设计者所提供的使用说明操作技术人工物时,就是预设性技术使用,使用者只是充当了原设计者的规划的执行者而已;而当使用者们抛开这个使用计划,根据自己对人工物功能的理解来操作技术人工物时,就是创造性技术使用。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者在使用实践中会发现人工物的新的使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修改人工物的原有设计。创造性的使用反对任何形式的以设计者意图为中心的有关人工物的使用说明,实际的使用实践甚至不与设计者的使用意识有关。
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层面,技术使用又分为个体性使用、群体性使用和社会性使用。个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细胞,是一切技术使用活动的最终承担者和落脚点。个体性技术使用是指以满足个人(包括家庭)的特殊要求为目的的技术使用行为;群体性技术使用则是指具有共同目的的个人所构成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技术使用活动。这里的群体绝不是个人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紧密有序的内在组合,群体内部虽然也有冲突有矛盾,但这只是他们个性的表现,他们的总体方向、目标和利益是一致而鲜明的;社会性技术使用则指的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处在同一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下的不同群体和个人构成的主体活动系统的技术使用。
根据技术使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手工工具性使用、机器性使用以及智能技术性使用。手工工具性使用是以手工工具为使用的对象,手工工具是与人类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工具,最初的手工工具极为简陋,如木棒、带有棱角的石块等,人类对技术的使用正是肇始于手工工具的出现;机器是一种用来转换和传递能量、物料和信息并能执行机械运动的装置,主要分为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如内燃机、蒸汽机、电动机、机床等,对机器的使用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预示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则指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表现为知识形态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对智能技术的使用开辟出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信息时代,正是以此为契机,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网络世界”和“虚拟社会”。
在目的层面,技术使用主要有生产型技术使用、消费型技术使用和军事型技术使用。生产型技术使用基于生产目的,着眼于通过技术手段的使用而生产出技术产品并投放消费市场从而实现技术的交换价值而获得经济效益;消费型技术使用立足于消费目的,通过对技术商品的使用从而实现技术的使用价值或者符号价值而得到精神满足;军事型技术使用则根源于军事目的,致力于军事武器的使用从而达到打败对手、征服敌人的目的。
在价值层面,根据人们使用技术时意愿的善恶,技术使用又可分为合理性技术使用和不合理性技术使用的基本类型。合理性问题一直都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它的边界比较模糊,衡量的尺度众说纷纭。目前人们探讨较多的是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对于技术使用来说,合理性不仅关乎使用的目的、价值、形式及效应,而且牵涉到利、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因此,合理性技术使用就是有助于利、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使用行为,反之,违背了利、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技术使用行为就是不合理的。
四、生活世界之于技术使用
生活世界生成于技术使用之中。生活世界(life-world)是现象学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人们可以感性体验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实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且还进一步拓展着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地将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技术的使用活动而达致的。生活世界生成于技术使用这一人类实践,而不是先验地就存在着的,是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化历程。当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成为既依赖于自然界又独立于自然界的力量时,人类就开始在使用实践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社会王国:石器技术的使用使人类开始打猎、捕鱼,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了第一前提;取火技术的使用使人类的取暖、照明、防寒、抵御野兽侵袭以及烹饪等等成为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人类从此告别了“生食”时代,理所当然地推进到了“熟食”年代;栽培技术的使用标志着人类迈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从此不再是坐等天赐,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天然植物的特性培育出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纺织技术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赤裸裸的生存状态,为进入到“知荣辱”的文明时代打下了基础。
生活世界是人类活生生的现实,是人类通过技术来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形成的,“从使用天然石块、树枝到利用石块、树枝、骨头来制造工具,从而猎获食物,从利用天然洞穴到建造巢穴、房屋,或者利用树皮遮体,以抵御大自然的袭击,是原始人的伟大技术创造”。(39)技术使用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人们生活着的世界。现时代,信息技术的使用甚至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于本体的看法,人们不再执拗于物质本体的信仰,而是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建构起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府、警局、社区、商场、娱乐设施等一应尽有,人们一样地进行着结婚、生子、工作等社会活动,除了建构出一个虚拟现实外,电子邮件、QQ等现代网络通讯工具也无时不在传递着信息,沟通着真实的心灵。信息技术通过使用者的使用已然融入到生活世界里,成为人们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在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技术使用实践活动中,人类社会不断地前行,因为主要使用的技术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内容。诚然,技术使用对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双面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建构作用,人类正是凭借着技术的使用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建构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便是消极的解构作用,新技术的使用会逐步腐蚀掉原有生活世界的形式和内容,动摇原有生活世界的根基,甚至会使原来的生活方式瓦解乃至消失。这就是说,技术使用不仅孕育了生活世界,也毁灭着生活世界;不仅建构着生活世界,也解构着生活世界;不仅是新的生活世界的起点,也可能是原有的生活世界的终点。这其实也是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在使用实践中的体现,对于生活世界来说,技术使用既送来了纯洁的天使,也带来了邪恶的魔鬼;既把希望和欢笑洒向人间,也把绝望和痛苦布满苍穹;既是人类身陷囹圄的根源,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途径。
技术使用现身于生活世界里。生活世界既依赖于技术使用活动,又限制着技术使用活动。前者是指生活世界生成于技术使用中;后者则凸显生活世界的“境域(Horizont)”作用。生活世界对于技术而言,就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境域,既是技术造就的关联,也是技术现身的场所,离开了生活世界,技术使用也就无处遁形,无所藏身。
胡塞尔特别推崇“境域”意识,强调对象从来不会孤零零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它们总是藏身在相互指引的意义网络中,也依赖于这种意义网络来现身,换言之,对象总是在某个意义指引的境域中与我们照面。海德格尔则认为,事物作为“用具”是在它们得到使用的某个境域中涌现出来的。也就是,事物作为某种“上手之物”是在世界的“因缘联系”之中与我们照面的。因此,上手之物所具有的使用性并不是由器物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境域”的世界所赋予的,这个境域为“上手之物”准备好了这样使用或那样使用的可靠性和合法性,使得我们能够在与事物的交互作用中自由活动。“没有这种相关情境的意义引导,没有这种我们一开始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领域,这种‘世界’、用具不可能产生”。(40)就这样,人们在生活世界里通过技术使用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着,由此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生活世界”既为技术提供了一个先在的情境,也伴随着人类不断更新的技术使用实践而孕育、生成并发展着新的情境。任何技术在投入使用时,都会面对着一个已有的情境,这用西蒙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的功能只能在人类使用的情境里面得以实现,(41)而这个情境又可分为“内部”情境和“外部”情境,“内部”情境涉及人工物自身的小环境,这是技术设计活动的产物,对其的描述可以仅仅使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它为“外部”情境提供了支撑;而“外部”情境则关乎人工物四周的各种要素和关系,是技术使用活动的展开,对其的描述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语言,更离不开社会科学的言语,“外部”情境实际上就是“内部”情境得以凸显的历史舞台。技术的功能只能在人类使用的情境里面得以实现,而技术一旦投入了使用,其功能的发挥又会形塑和改变着原有的情境,甚至能建构出一个全新的情境。
技术使用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里的情境化。毋庸置疑,生活世界里的人们使用任何技术人工物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意向性,也就是说这些技术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可以用“做什么的”来表述。“功能”一词通常是指某事或某物所具有的作用或者效能,技术功能则特指技术或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作用或效能。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某一具体的人工物所展现的功能表现为预设性功能、创造性功能和意外性功能。预设性功能指的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根据自己对潜在使用者需求的感知和理解,通过一定物理结构的设计而想要实现的功能。在产品进入到生活世界被使用之前,该功能只能处于预设的潜在状态;创造性功能则是指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在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经验而重新赋予人工物的功能,它不同于设计者所预期的功能,甚至设计者根本就没有料到这种功能,而是使用者自己所设定的功能,相对于预设来说它是创造性的;而意外性功能则是指使用者通过自己的使用行为所意外实现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者也许是想要实现人工物的预设功能,也许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创造性功能,但最终实现的功能却在意料之外,无法预测。不管上述哪种功能,总是“使用情境中的功能”,(42)它们是“外在的,是由使用者赋予的”。(43)
只有在活跃着各种使用者的具体生活情境里,技术人工物的意义才能得到昭显、功能才能获得释放。技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结构属性和功能属性——在生活世界里的寓意是不同的,前者暗含着自然规律的科学性,而后者凸显着社会生活的人为性。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已经“在此”的技术首先呈现的是自然属性,即物理结构和几何特征,诸如形状、质料、尺寸、重量、密度、颜色等等,技术在此时被概念化为中性的对象,并没有提示其跟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海德格尔称之为“应手之物”(readiness-to-hand),而技术的本质则应该被描述为“为了什么之用”,也就是说,技术只有被置身于生活世界里与功能联系在一起时其本质才能真实地显现。
不管使用者揣着什么样的目的去使用技术,技术使用的成功总是表现为人工物某一功能在生活世界里的实现,这样,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技术使用就成了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里的具体化、现实化过程,技术使用需要融入到使用者拥有着话语权的生活世界里去。“使用者根据实际目的的需要分派给人工物以功能”,(44)由于在具体的使用情境里,使用者有着各种各样的使用目的,因此,生活世界中技术使用者的面貌就是多种多样的,有生产型使用者、消费型使用者、军事型使用者等等。鉴于使用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情境化过程中的技术功能也就会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是同一件技术人工物,它在不同的使用者主导的使用情境里,也会发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功能,实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技术功能的情境化主要体现为技术知识的情境化、技术价值的情境化和技术伦理的情境化。
只有在使用中,技术的各项物理结构才能通过使用者对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意向的认知获得意义。当然,技术功能在使用实践中并不是都能顺利地情境化,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使用者的特定目的,这就是说,技术功能在情境化的过程中,还会遭遇“功能失灵(malfunction)”的问题。“如果你期待使用一个人工物来实现什么,那么你就可以在该物体不能达到你的目的时说该物功能失灵了。”(45)相对于技术使用活动而言,功能失灵就是人工物无法实现使用者预期发挥的功能。人工物是“一个混合的交往工具性物体(A Mixed Communicative-tool Object)”,(46)它们还在设计之初时就被设计者赋予了功能意向,在使用之时又被使用者指派了具体的、生动的功能任务。只有这些人工物才能在使用的情境里存在“功能失灵”的现象,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功能意向的产物,功能反过来又是构成它们本质的东西。
五、科学发展寓于技术与使用者的双向建构中
我国正处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走科学发展道路是我国的战略选择,这依赖于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依赖于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科技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竞争。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不断壮大人才队伍,是提高我国科技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47)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则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即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又再一次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从技术活动的类型来看,科学技术人才可分为四种类型:发明型、设计型、生产型和使用型,发明型科学技术人才的创新性是最强的,要构思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他们的创新深深扎根于原有技术的使用实践中;设计型科学技术人才致力于把前者的技术构思转化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又要兼顾现实技术使用者的需求;生产型科学技术人才则根据技术方案将技术构思转化为人工物,并投放市场;使用型科学技术人才着眼于技术人工物在生活世界里的具体应用。
在技术使用中,虽然是使用者主导着使用行为,但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并不是单向的,“技术一旦处于‘使用’中,必然会影响它们的使用者;反过来也是这样,使用者的行为——比如现存的习惯或者对人工物功能的理解——总是决定着技术最终如何发挥功能”。(48)可见,技术使用不仅是使用者的使用,是“已经在此”的技术人工物功能的实现过程,而且是使用者与技术的相互建构过程,“建构”就是指技术使用者“并不是消极地接受技术,而是会根据自己的特定目的将其定型,对其加以改变”,(49)正是技术人工物与使用者的相互建构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科学发展也就寓于技术与使用者的双向建构中。
“使用者(users)”在学术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它是经济学、心理学、信息学等学科研究的宠儿,但这都是从生产者、设计者和制造者的传统主体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因而在浩如烟海的“使用者”文献里,弥漫着柔弱、消极、被动的意蕴,人们关注技术活动的其他主体,而认为使用者是可有可无的,因此,长期以来使用者在技术发展史中实际上处于匿名状态。其实,使用者的主体性是无处不在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里,每个人都成了技术的使用者,更何况专门从事技术活动的主体——发明家、设计者和生产者,他们更是名副其实的技术使用者,即使是不发明、不设计、不生产的专职型使用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表达,也会左右技术的发展方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冯·希普尔教授(Eric von Hippel)为主要代表的创新专家们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提出了“使用者创新”的革命性观点(users innovation,柳卸林等将其译为“用户创新”),对使用者在创新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性进行了充分的挖掘,除了肯定传统理论中制造者的主体地位外,更加强调使用者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并以大量实例证明了使用者在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创新主体身份,“几乎总是使用者而非设备的制造者认识到了创新的需要,并通过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构建了一个原型并证明了这个原型在使用中的价值”。(50)
使用者的创新行为当然也是为了盈利,他们“期望通过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而受益”,(51)这个利不仅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盈利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个人的直接使用获利,这其实是最基本的方式,因为任何使用都是为了一定目的的满足;二是通过创新行为使自己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和舒适而获利;三是通过转让创新成果或者申请专利来获利;四是通过角色转化——自己成为制造者从而生产和销售创新产品以获利。可见,使用者和发明者、设计者及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可以重合并相互转化。
奥斯特(52)和奥德肖恩(53)以性别为维度,分别聚焦于飞利浦剃须刀和男用避孕药的发展,诠释了使用者是如何在一开始就影响着设计者,怎样一步步引导着设计者将有关使用者的假设转化为新物品的技术性内容。而在著名的自行车案例(54)中,高轮自行车这种新兴事物在现实使用中遇到了瓶颈,妇女们和年长的使用者们赋予了高轮自行车以一种全新的含义——不安全,这就为安全自行车的研制提供了动力,从而为安全自行车的发展铺平道路,使用者就这样不断发挥着自己对技术的建构作用。
使用者主体性重要性的凸显使得技术的设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生产者由原来的向使用者提供产品转为向使用者提供技能,出现了“使用者界面(user interface)”、“使用者卷入(user involvement)”、“使用者参与(user participation)”、“使用者创新工具箱(innovation to users via toolkits)”(55)等等设计理念,许多企业已经不再绞尽脑汁地试图理解使用者的需求,而是向他们提供工具由他们自己来设计和开发所需要技术产品,其中所需的试错过程也全部由使用者完成,这就使得专职的使用者也能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使用者设计”已经成为一种新理念。
对使用者主体性的张扬并没有否认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发明者、设计者和生产者的主体性,技术使用实际上就是使用者与代表发明者、设计者和生产者意图的技术之间的一种博弈,正是通过这种博弈,技术使用才成为了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技术与使用者的相互建构活动中,使用者展开着自己的使用计划,对“已经在此”的技术进行着消费、改进、驯化、设计、重构、组建以及对抗等等活动。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知识开始扩散和转移、技术内含的设计者价值诉求和生活世界中使用者对人工物的价值诉求之间开始博弈和协商、技术使用者责任意识和伦理体系也开始培养建立和强化。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也就内化于技术使用过程中的知识、价值和伦理的建构。
技术知识的建构。当使用者面对着一项全新的技术时,首先需要做的是理解这项技术“是什么”,即在知识论上对该项技术蕴含着的知识进行认知和重新建构。技术以人工物的形态面世之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以设计者语言表述的技术文本,技术想要成功地融入到生活世界之中,就必须转化为使用者的技术文本,这就涉及翻译和转译的问题。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翻译就是使用者试图理解设计者的意图和思想,而转译不囿于此,它不仅要理解设计者的意图和思想,还要理解其他使用者的意图和思想。
当技术从设计者世界转移到了使用者的世界时,实际上也就是进入了一种新的情境,它要实现自身的使命,必须要在新的情境中得到建构。相对于原情境而言,不妨称之为目标情境。也就是说,技术活动所涉及的情境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设计情境(原情境),另一是使用情境(目标情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境,各有自己不同的质料和形式,处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中的技术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和意向,折射出不同的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内涵。对于维持技术知识的有效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使用者自己的具体情境和生活世界。使用者对已经在此的技术进行知识的翻译和转译,这是情境化的起点,即首先用自己的语言将其加以认识和阐释,只有具备了手中的技术“是什么”的知识,才有可能形成它是用来“做什么”的知识,继而展开自己的使用活动。当然,“使用计划并非一成不变,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者发现了人工物的新的使用方式,就会在此基础上修改了人工设计物,从而改变了原初的使用计划”。(56)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知识能否顺利地扩散和重构,不仅受限于知识创造者即设计者表达知识的意愿及能力,更取决于知识转译者即使用者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
技术价值的建构。当使用者知道这项技术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使用它来满足自己哪种需要的问题了。这样,他就会对技术产生一种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和设计者预先赋予技术的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在设计实践里,设计者所使用的技术对设计者来说价值比较单一,体现出来的主要是工具价值,因为设计者的目的只是设计出能满足需求的工具。而在使用实践里,作为客体的技术就会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价值形态,如工具价值、审美价值、符号价值、人文价值等等。由此看来,当技术从设计情境进入到使用情境中时,在历经设计语言转化为使用语言的翻译与转译工作之后,就面临着两种价值的博弈与妥协问题了。
这场博弈与妥协表现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客体不仅会被主体同化,主体也会被客体同化,毫无疑问,主体反映的是具体使用者的特定价值诉求,而客体凝聚和反映的是设计者的价值背景、价值结构及价值取向。这样,客体被主体同化是指主体在使用技术客体时处于能动地位,能够动用自己的力量作用于客体并改变客体,使客体逐步内化成主体的本质力量,外在表现为使用者的价值诉求;主体被客体同化是指主体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客体虽然是被动的,但其自身所内敛的价值体系无形中会对主体施加影响,使之不知不觉中就受限于客体,在价值取向上逐步与客体保持一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技术使用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而无论是哪一方面,实际上都是在使用者所导演的价值博弈中进行的。对于一个成功的技术使用行为而言,博弈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使用者与设计者价值诉求的最终协同,常常表现为一方的退隐和妥协,当然任何一方的妥协都不是简单的妥协,而是博弈中的妥协。
技术伦理和责任的建构。使用者手中的技术就像是自己饲养的一个小动物,你在了解了它的习性并利用它以达到某种目的过程中,你也就在无形中产生了对它的怜爱,培养起了对它的责任。驯化本来是畜牧业领域的一个专用词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技术的社会学家把“驯化”一词引入学术领域,开始研究“技术的驯化”,根据驯化野生动物以使他们适应家庭生活的经验类推,认为新技术最初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种陌生的、刺激的、新奇的、具有威胁性的新事物,也不得不经历“驯化”以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居者,成为家庭的一分子,否则就得遭受从家庭中完全被排斥的命运。驯化的目的就是形塑,即将其塑造成使用者想要的形态。“驯化涉及使用者是如何制造了一个‘越来越由技术所调节的’的环境,同时又认识到那些技术也能够不被驯化以及被再次驯化、‘适应和改变’以满足变化的使用者需求”。(57)驯化要经历四个阶段:占有(成为一个技术产品或一项技术服务的主人)、客体化(展示的过程)、合并(使用,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以及转化(对技术物品的使用塑造着使用者与周围其他人们的关系)。(58)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所产生的”。(59)使用者作为确定而现实的人,不仅肩负着培养和维持正当而合理的使用方式的神圣使命,而且也背负着创新的艰巨任务,不管他能否意识到,这都毋庸置疑。科学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代表发明者、设计者和生产者意图的技术,更依赖于技术的使用者,只有在技术与使用者之间良好的可持续建构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
责任编审:孙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3—2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⑥参见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24页。
⑧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第20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
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220、109、45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
(1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3—46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13页。
(19)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0)Carl Mitcham,"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25,no.1,1985,p.73.
(21)Peter Kroes,"Technological Explanations: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vol.3,no.3,1998,p.18.
(22)Peter Kroes,"Design Methodology and the Nature of Technical Artefacts," Design Studies,vol.23,no.3,2002,pp.287-302.
(23)Peter Kroes,"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 Techné,vol.5,no.3,2001,p.6.
(24)乔瑞金、张秀武等:《技术设计: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论域》,《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
(25)汉娜·阿伦特:《制作的本质》,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118页。
(2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3页。
(27)Carl 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231-233.
(28)Don Ihde,Instrumental Realism: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73.
(29)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30)舒红跃:《技术与生活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31)Carl Zetie,Practical User Interface Design:Making GULs Work,Berkshire:McGraw-Hill Book Company Europe,2006,p.251.
(3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第53页。
(33)Carl 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p.159.
(34)Kurt Dauer Keller,"The Corporeal Order of Things:The Spiel of Usability," Human Studies,vol.28,no.2,2005,p.181.
(35)舒红跃:《技术与生活世界》,第3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页。
(37)汉娜·阿伦特:《制作的本质》,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117页。
(38)Marc J.de Vries,"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 Techné,vol.12,no.1,2008,p.23.
(39)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40)Michael E.Zimmerman,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Technology,Politics,and Art,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138.
(41)Peter Kroes,"Design Methodology and the Nature of Technical Artefacts," Design Studies,vol.23,2002,pp.292-294.
(42)(43)Peter Kroes,"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 Techné,vol.5,no.3,2001,pp.6,7.
(44)Peter Kroes,"Screwdriver Philosophy:Searle's Analysis of Technical Functions," Techné,vol.6,no.3,2003,p.25.
(45)Peter Kroes,"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 p.11.
(46)Randall Dipert,"Some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Artefacts:Defining 'Artifact' and Some Related Notions," The Monist,vol.78,no.2,1995,p.126.
(47)胡锦涛:《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7日,第1版。
(48)Peter-Paul Verbeek and Adriaan Slob,User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Shaping Sustainable Relations between Consumers and Technologies,Netherlands:Springer,2006,p.386.
(49)Ron Westrum,Technologies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Belmont,CA:Wadsworth,Inc.,1991,p.xvii.
(50)Nelly Oudshoorn and Trevor Pinch,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third edi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7,pp.541-557.
(51)Hippel E.Von,"Democratizing Innovation:The Evolving Phenomenon of User Innovation," Journal für Betriebswirtschaft,vol.55,2005,p.63.
(52)Ellen van Oost,"Materialized Gender," in How Users Matter: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ies,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3,pp.193-208.
(53)Nelly Oudshoorn,How Users Matter: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ies,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3,pp.209-227.
(54)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s: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7,p.17.
(55)William Riggs and Eric von Hippel,"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Commercial Values on the Sources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vol.23,1994,pp.459-469.
(56)Wybo Houkes,Philosophy and Design: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New York: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2008,pp.38-40.
(57)Graeme Gooday,"Tame Technology Studies," Metascience,vol.17,2008,p.96.
(58)Maren Hartmann,Thomas Berker,Yves Punie and Katie Ward,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32-139.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