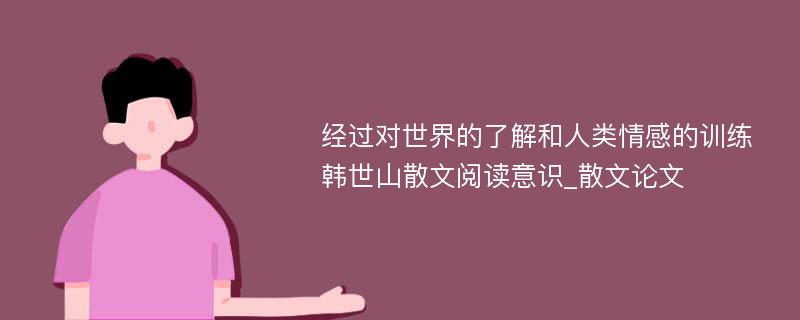
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后……——韩石山散文读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山论文,练达论文,人情论文,世事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初,我在选编《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时,曾为韩石山的散文创作写过不足两千字的批评文字。现在读来,不仅有点儿浮光掠影,而且显得局限及判断的狭隘。当时我只读过韩石山的两本散文集:《亏心事》、《我的小气》(均为百花文艺版),没有注意到他的另外两本书、即《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版)、《我手写我心》(山西高校联合版)——前者虽被称做“文学评论集”,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是“文艺随笔”,而随笔便是散文;那么后者呢,所谓“我手写我心”,写的全是闲话、随感、杂说、序文、信札一类的文字,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散文选集。与《亏心事》、《我的小气》相比,不同的则是这些散文都留有文艺或文化的印记。顺便说一句,即便是韩先生的“文学评论”,也具有比较充分的散文化的特点,完全可以区别于现今中国文坛上流行的“文学评论”,显得活泼、生动、随意、亲切,没有板着面孔的学究气,也没有故作深沉表情的装腔作势,可以说,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评论或某些文坛现象批评,也是可作散文来欣赏的,如《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明日来寻都是诗——评林斤澜的近作》、《巴里加斯的困惑——小说体的作家论》,等等。当然,这些文章的精彩还不仅仅在于散文化,更重要的是行文中的见解的独树一帜。
我只见过韩石山一面,且没有谈任何文学问题。关于他的一切,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者是观念,都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韩先生开始被文坛认可、被读者知晓,是因了他当时的小说;小说创作是他的看家本领。他著有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长江文艺版)、短篇小说集《猪的喜剧》(上海文艺版)、《轻盈的脚步》(北岳文艺版)、中篇小说集《魔子》(重庆版)、中短篇小说集《鬼符》(花城版)等,有如此厚实的“看家本领”垫底,写起散文来便自然而然地造成自己的特色,起码与那些专事散文写作的人所写的作品存有质地或文风或叙述形态上的差别——作为长处,小说家的散文要更多一些叙事性,写人也更生动活泛一些,因为写人记事及牵扯出一些“意味”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韩石山也不例外。譬如他的《三姨》、《光光的麦场》、《我们的年》、《拂不去的饿》、《杜士铎先生》、《终生的愧疚》等,且不说写人记事的精湛独到或出神入化,单说其中的某些篇章,实际上已离小说的叙述形态很近很近了。当然,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模糊——我觉得,领悟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散文创作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如何认知散文这一文体的观念问题。
韩石山的散文观念是清醒而开放的。他说:“散文是一种很宽泛的文体,表现在对其它一些小的文学样式的包容上。报告文学、书信、传记、序跋、游记、笔记,都属于散文。”就“宽泛的文体”一说,我觉得不仅富有现实性,而且深得中国散文传统的要义,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古代散文选本,都可以感觉到散文文体的宽泛性或包容性,即使是中国的古代文论,也拥有相应的散文色泽。中国的当代散文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狭窄,大约也与文体理解的局限性相关,而这种局限性的形成,又与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模式的广泛流行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谁的过错,而是一种形成了规模的误解。在我看来,韩石山的散文创作之所以造就了自己的蓬勃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散文文体观念获得了解放(或回归传统精神)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他把报告文学与传记依然认作是散文的看法,应该说是清醒而独到的。报告文学、传记的主要文体特点便是写人记事,是真实而富有意味地记录人生或人世;它需要见解、需要文采,需要阅世的洞察力与掌握对象个性的才能,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可以容纳一切值得运用的文学手段、甚至是真正的新闻修辞语言——意识到这一点,其意义绝不仅仅止于散文文体观念的解放,而且也是对当今报告文学或传记创作的模式化或平庸倾向的一种反驳与警告。
当然,韩石山的散文观念是多侧面的复合,文体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不谈其它方面,如修养、自信、幽默、调侃、自轻自贱、自伤自悼、以及“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之类,但有一点是不可不谈的,那就是在他的意识中,散文绝不是一种易写(“视之过低”)的文体。他说:“散文是文体的一种,也是其它文体的基础。写散文,可说是对作家才、学、识的全面衡量。当今文坛上新秀迭起,总的看来,多是识大于才,才大于学,或者才识相当,学力不逮。表现在作品中,往往辞在意先,文胜于言。古人的文章所以写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或饱经忧患,满腹经纶,或白首穷经,学通古今,在从政治学之暇,偶有所感,信手写出,便成传篇,岂是‘作’出来的?”这是韩先生十几年前说的话,但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针砭散文时势的犀利之力。
所谓“我手写我心”,仅仅是一种简捷的通俗说法,有点儿近似“有感而发”、“为事而作”;既是“我手”,又是“我心”,其中的“心质”却是举足轻重的关键。然而,正是这种简捷的说法,造就了一些肤浅者的误解,甚至产生出散文“易写”的错觉。实际上,因了“心质”或“感受”不易靠近某种理想境界的缘故,要写出好散文(即便是以“我手”),总是很难很难的——这种“难”的气息大约一直弥漫于韩石山的“潺湲室”。
在山西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家中,韩石山是“充分山西化”的典范之一,那种“护卫”一地而辐射整个文坛的才能,着实是一种文学智慧的卓越体现。在动荡而沮丧的中国“文场”,真正稳得住自己、信得过自己的作家,究竟还有多少?但一个作家要真正看清楚自己或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分量,大约是很不容易的——“潺湲室”中的韩石山自然有着深切的体验——他一直把他的写作间称做“潺湲室”。“潺湲”出自《九歌》,但到韩先生那里,便有了他自己的意思:一是迁居之前的小屋漏雨,大有“观流水兮潺湲”之感;二是乞望自己的文思如流水般潺湲而涌。就在这“潺湲室”,他感悟到了“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庸俗无聊。据他自己说,“先前多关注时势的变迁”,如今“多省视自己的情感”。当然,“先前多关注”不等于如今不关注,而“多省视自己”,说起来轻松容易,做起来却免不了胆怯犹豫,而且最终能“省视”到怎样的程度,甚至是可靠还是不得要领,这都是会留下问号的事儿,特别是,“省视自己”也离不开“时势的变迁”。但无论怎样说,韩石山毕竟是以散文的方式知难而上了(当然,我们不必追究这种“省视自己”是从何时开始的……)。
在韩石山的散文中,无论是《亏心事》还是《我的小气》或者是那些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感杂说,也无论他是以何种姿势省视,以何种表情传达,或以怎样的装束出现在读者面前,反正他的作品大都与“自身”相关——他的“多省视自己”,确不是雪白稿纸上的口号,或一幅悬挂在“潺湲室”的标语。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做得是否彻底则是另一个问题)。凡读过《亏心事》与《我的小气》这两本选集的读者,大约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省视自己的感情”,就得冷峻而又热忱地回眸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得瞧一瞧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就造就了韩石山散文创作的一种特点,那就是“忆旧”。其实,“忆旧”算不得一个散文家的很独特的“特点”,因为很多写散文的人大都具有这种“忆旧”的嗜好,而真正可以称为“特点”的“特点”,则在于“忆”了一些什么,以何种方式“忆”的,或最终“忆”出了怎样的“意思”。
在韩先生看来:“一个连自己的内心世界都不敢袒露,连自己形象都塑造不好的作家,尽可以让人崇敬,却难以让人多么的钦佩。”这里还用得上韩先生的一句曾当作文章标题的话:“要坦诚地面对自己”。
对于一个写过大量小说的作家来说,自然明白袒露“内心世界”及“面对自己”(且要“坦诚”)的含义,也清楚塑造自己形象的“流行方式”。在这里,韩先生选择了一种严峻而又不易把握的方式,即对于自己灵魂的回眸与拷问。当然,塑造自己形象显得不那么重要,何况,只有那种真实而令人信服的形象,才可能被读者认可或钦佩——惊人的完美恰恰让人产生厌恶感。就当今文场而言,也确实流行着某些丑陋的“塑造自己形象”的勾当,如披着谦虚外衣的自吹自擂,又如为了衬托今日的辉煌而絮叨昔日那些似苦非苦的所谓“苦难”,甚至还有沽名钓誉者,不惜乞求报刊或暗示朋友,以致发动自己老婆来为自己“包装”或“造名”……所以,当我读到韩石山那些面对过去而省视自身的散文时,便感受到一种由衷的亲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通;也因了他自己的形象塑造,是在拷问自己灵魂及透视自己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完成的,于是,所谓“亏心事”、“小气”、“狂态”、“孤傲”、甚至自轻自贱、自伤自悼之类的抒写,也成为一种形象的美,一种可以沟通、可以理解的审美内容——倘若运用一个陈旧而不朽的概念,那就是全因了自我省视或自我塑造的“真实”。
当然,韩石山写散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自己的形象——如果能从他的散文中感受到他的形象的存在,那只是一种“副产品”;作家形象之于作家文字中的存在,犹如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影子,你不以它为意,可它总是跟着你。撇开这个“形象”的问题不谈,那从他的那些富有“忆旧”色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一是从个人生活中折射出来的“历史”,一是从坎坷阅历中提供给我们体味的“人生”,再就是韩先生所崇尚的精神或情愫。如他在《孤傲人生》的结尾写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辛苦欢乐都是自己的。孤傲这一亦是亦非的品格,我若真有什么建树是因了你,若再受什么磨难,准还是因了你。”作为一种品格或人格,韩先生对于“孤傲”其实是极为欣赏的。又如那篇《终生的愧疚》,虽则充满了坦诚的自责,但最终要张扬的,仍是一种宝贵的“师恩”,一种永远不忘情谊的传统精神。
韩石山在写到“自身”时,那种正视自己灵魂(无论是崇高还是卑微)的态度是值得推崇的。他不掩饰、不做作、不自暴自弃、也不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生存经历的拷问是诚实而潇洒的,甚至还有点儿刻薄无情;不言而喻,其中还有着一个作家的机智成分的参与或调节。质朴愚拙也罢,从山沟里来的也罢,不会耸肩不会言OK也罢,他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灵魂,守护着那种充满浓郁乡情及传统文人品格的内心世界。诚然,这不是他的宣言,他也不会如此地宣言,但他的那些“忆旧”文字所包孕的,就是这样一种虽称不上完美,但又或多或少拥有脱俗意味的精神。从儿时生活开始,韩石山的经历是艰辛而幸运的。他总是轻松地诉说过去,无论是苦涩还是记忆中的温情或愉悦,但还是可以让人感悟到一种沧桑变迁的无情,一种时光似水的匆促,一种因记忆中的美好正在逐渐消失而滋生的隐痛。可以想见,韩石山的“忆旧”,绝不是为“忆旧”而“忆旧”,而是为了某种表达,或某种与现实相关的感叹——在那篇《光光的麦场》中,韩先生在“永别”了那“欢乐的少年时光”、那家乡的“光光的麦场”之后,他的感叹复杂到“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可以想见,此“喜”此“忧”,既为昨天亦为今天。在这“喜”或“忧”的传达中,在这“忆旧”的点点滴滴记录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收获到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或“历史”的东西,或一种拼凑中国当代形象的零星而珍贵的“资料”,这种特点是一般“青春期散文”所无法企及的——其中的原因,自然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描写的细腻生动,而且在于或主要在于作者的阅世本领及亲历底层生活的诚挚感情。
韩先生并没有以炫耀学问的方式直接抒写或感慨“历史”或所谓“文化”,但他以“渍痕”的形态,把“历史”或“文化”还原为活生生的、甚至“凡俗”的生活内容,并由此而显现出一个作家的本份。
我们常说,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怎样写”。这“怎样写”才可能真正体现一个作家的特点。就散文的“忆旧”而言,中国的散文作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而同代作家的经历更是“大同小异”,所以真正可能显示独特性的,传达方式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么,韩石山的散文传达有些怎样的与众不同呢?我想,最主要的便是幽默、自嘲(所谓“调侃自己”)甚至是“自轻自贱”,若要说得准确一点儿,那则是以上几种成分的综合,因为其幽默中往往掺杂着自嘲的因素,或他的“自轻自贱”往往就是一种幽默的方式,一种自我嘲讽的体现……收在《我手写我心》中的《闲话文人·要会调侃自己》,则是一篇透露了韩先生“秘密”的文章。他说:“调侃自己,或者说自轻自贱,是写文章的一个诀窍,也是一种胸怀,一种风度。”这话自然有点儿毛病,或者说是过于“拙”,因为既然是胸怀与风度,那便不是一个“诀窍”的问题了:说“诀窍”,或多或少折损了调侃自己(或自嘲或幽默)的本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调侃自己”是他的一种散文追求。不过,韩先生也可能会遇到麻烦,即无论是“调侃自己”(自嘲)还是“自轻自贱”(包括其中的幽默),究竟实施到何种程度?其中总有限度或分寸,一不小心过了头,那岂不真的糟贱了自己,而韩先生从心性上说,本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一个孤傲而藐视媚俗的人。但可以庆幸的是,韩先生把握得甚好,即便是《我的小气》、《拂不去的饿》、《狂态》之类的“调侃”或“自轻自贱”,也没有给自己脸上“抹黑”;相反,还多了几份有意味的情性袒露。在这儿,倒可以说既见了胸怀与风度,也贯彻了必不可少的“诀窍”。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韩石山散文中的“调侃”或“自轻自贱”,那仅仅是一种方式或途径,所企图通向的,则是自信或某种执拗的传达。他说过:“调侃自己,也可以说是幽默的一种。所不同者,幽默可对人也可对己,要的是聪明,而调侃自己,专对己,要的却是自信,那种源于学识和才华的双重自信。”这话自然是道出了作文或处世的真理(或“诀窍”),但以此来诠释自己的“调侃自己”(或“自轻自贱”),那便有了“露馅”的嫌疑。实际上,自信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心境平静,或说持有一颗平常心——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一不小心过了头;何况,“调侃自己”总是含有对抗世俗的意味,而任何方式的“过火”,都可能令读者生疑,弄不好会让人感到写作者的“故作轻贱”,或留下“炫耀羽毛”(学识和才华)的印象。可以想见,“调侃自己”的分寸,“自轻自贱”的程度,自然是对作家机智的一种考验,但更甚于分寸或程度的考验还在于:“调侃自己”——调侃什么?或此事此情是否值得“自轻自贱”?甚至可以说,你的“调侃自己”及“自轻自贱”的内容与走向,能不能沟通读者的期待,并最终引起共鸣?这便成为一个大问题。说到底,作家的素质、修养、见解与判断力,才是创作的关键;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尺度衡量的东西,却在冥冥之中成就你或毁灭你。
韩石山绝非“圣人”。他的作品(散文或其它)不可能篇篇都是佳作,或者说,多数作品精彩或比较精彩,自然也有不怎么精彩的,甚至是很平庸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品整体上一般化,但有些段落却十分耐读,以致让人拍案叫绝——什么原因?我觉得那是韩先生的见解或洞观的判断力在起作用。倘若能比较全面、也比较细致地阅读韩石山的散文,那读者便可察觉到,见解或判断力的概念在他的散文中是何等地重要。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在《亏心事》、《我的小气》这两本被标明为散文集的选集中,因了作品的叙事性倾向,见解或判断力大都隐含于字里行间,但在《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我手写我心》这两本选集中,文体及行文方式都因表达而发生了变化;凡精彩的篇章,基本上都以直接赋予或直接表达见解取胜,也就是说,这些篇章之所以精彩,那是因了见解精彩的缘故:随感也罢,杂说也罢,笔记也罢,大都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见解”是中国散文传统的支柱性因素,无论是含蓄委婉还是直言不讳:“见解”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力,而且也是作家的人格或精神品位。一篇散文,不管选择了怎样的文体方式或叙述形态——就古代散文而言,不管它是记、传、论、疏、谏、书、札、序、跋、铭,见解的贯穿及不可缺或,不可淡薄的特点,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诸如视点、态度、“叙述表情”(或情调)、倾诉内容、可能的结论或倾向,等等,都隐含着作家的见解因素,更不用说那些直接表达时世判断及见解的文章了。没有见解或缺乏判断力,等于抽去了传达的灵魂。
在这里,我要更多地涉及韩石山的那些以前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随感杂说(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笔)。
读韩先生的文章才知晓,他对“批评”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对“文学批评”是极为不满的,但这种“不满”又是清醒理智的,也是符合实情的。他的《批评的焦虑》写于1992年,而如今的批评风气不是更为恶浊么?平庸的说教,肉麻的吹捧,言不及义的表达,不读作品的“发言”,自以为是的“宏观把握”,东拼西凑的抄袭,等等,不是依然泛滥于文场么?我起码同意韩先生的两大观点,一是抛弃因循守旧的局面,所谓“没有论战,怎么能造就批评家”;二是重新认识批评的功能,对作家、对批评家都应有此要求。
就这些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笔而言,韩石山表达是犀利直捷的,一点儿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然,见解的可靠也就成为这些文章的脊梁。譬如他说:“一些游记文章,登在报刊上,给人的感觉,跟不道德的游客在古建筑的墙上刻上‘××到此一游’没有差别。”(《漫谈散文创作》)可谓快人快语,一箭中的。又如他说:“如今这世道,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这种“文化热”中的虚弱症或底气不足的病态,不是几笔就给勾勒出来了么(《不羞不臊侃文化》)?韩先生对作家的所谓“学者化”说法也不以为然,这其中自有他的理在:“倘若没有那份才情,那份胸怀,作家的学者化,除了增添几个平庸的学者外,绝不会成就什么学者型的作家。”(《文学三思》)在这些随笔中,自嘲间挟带着对于时世的讽刺,而一些幽默,也明显地包孕起针砭的意味。可以想象,若无见解及判断力的支撑,这些随笔也就失却了起码的意义,更说不上新人耳目了。
韩先生的独特见解,还表现在从文学现象的角度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名人名家的不妥。譬如说,他曾批评过王蒙为自己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所作的徒劳辩解。他说:“王蒙的过错在于,既有勇气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就应当有勇气捍卫它的纯洁,若不自信,获奖就该婉言谢绝。若自信,对那样粗暴的批评,则应当要么置之不理以示鄙弃,要么奋起抗争以示刚正。如今作出这样无力的辩白,形同乞讨……”(《是又怎么样》)虽则文章结尾写上了这么几句:“山野之人,粗鄙之人,不管当说不当说都一并说了,知我罪我,由他去吧”,但其中的“耿直”,还是一眼可以瞧见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所“批评”的不仅仅是王蒙。而且是或更重要的是批评了无聊的时势及那种无聊“墨客”的粗暴无理。又如,韩先生从《文学报》读到这样的报道:“老作家汪曾祺十分喜悦地说,近几年散文创作空前的好,不仅三十年代一些名家的作品不如现在一些青年散文家的散文好,五十年代那些带着面具的作品更是不能和现在的相提并论了。”当然,韩先生是敬重汪老的,但他还是觉得汪老说出了“昧心之论”。于是,他说了这样一番尖刻的话:“我不知道此老所说的‘三十年代一些名家’中包括不包括像郁达夫、朱自清、丰子恺、沈从文这几个人,其作品包括不包括《钓台的春昼》、《背影》、《缘缘堂随笔》、《湘行散记》这样的作品,若不包括我无话可说,若包括,那么‘且容小僧伸伸腿’。‘现在一些青年散文家的作品’中,可有一位有郁氏的酣畅淋漓,或朱氏的纤浓哀婉,或沈氏的沉郁自然,或丰氏的清纯风雅……”(《略工感慨即名家》)我不知道《文学报》的报道是否确实——若确实,那韩先生振振有词的“扶正”还是有见地的,且很能见出他的作文风格。
虽说韩石山曾劝诫别人“要打破一切规矩”,实际上,每个作家、特别是比较成熟的作家,总有一些“规矩”于冥冥之中规矩着他的写作。我想,韩先生的散文也不能例外——读者总能寻找或感觉到他的一些“规矩”。
在创作上,韩石山很欣赏《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无论是“皆学问”的“皆”,还是“即文章”的“即”,都是有点儿疑问或偏颇的。于是,我给我的这篇批评文章起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标题,叫做“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后……”
1996年9月初北京六里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