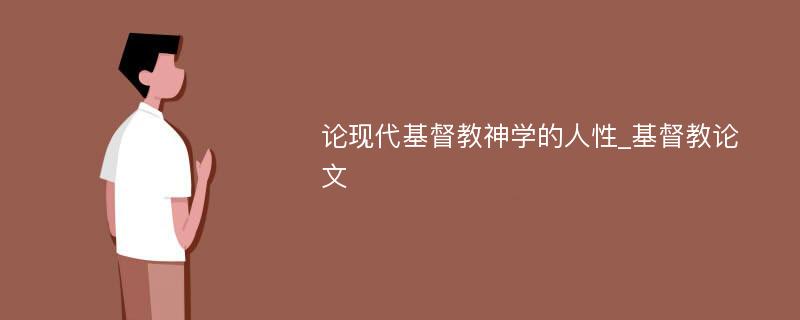
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神学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面对人性精神生活的真正思考是双重冒险,既是意义的冒险,又是意志的冒险。意义的冒险使思考从此世的现实生活中独立出来,而意志的冒险则使从现实生活中独立出来的思考重返人间,反观人性存在的精神命运。因此,真正的思考者在双重冒险中感悟到思考者所面对的精神命运同时就是人类存在的命运。现代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两位杰出的基督教思考者,法国的帕斯卡尔(1623—1662)和丹麦的克尔凯戈尔(1813—1855)。无论是前者的“追思神恩之夜”还是后者“非此即彼”的信仰抉择,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感契与告白,后来者均可以从中看到基督教神学对人性存在堪称深刻的体认和思考。
法国的帕斯卡尔在其为基督教辩护的著名告白中曾提出四组二律背反的神学命题:1.上帝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2.灵魂与肉体同在,以及我们没有灵魂;3.世界是被创造的,以及世界不是被创造的;4.有原罪,以及没有原罪。[①]这四组神学命题深刻地揭示了上帝问题、生存问题、存在问题及人性问题的内在关联。这一内在关联表现为逻辑理性不可思议的正命题与信仰生命不可思议的反题之间的基本张力。对于虔敬的基督徒帕斯卡尔来说,逻辑理性视为不可思议的正题恰是此在人类事实,而为逻辑理性所认可的反题则违背了人性的基本生存。帕斯卡尔的神学立场表明:人性精神生命的基本事实在于一种生存意志的本真寻求,在于人类本性之不可彻底逻辑化,以及对神圣真理的信仰确认。
帕斯卡尔四组二律背反的神学命题,揭示了西方历史上二种相对立的世界观与真理观,以及二种不同取向的人性思考。俄罗斯基督教思想家舍斯托夫(1866—1938)曾敏锐地察觉到帕斯卡尔神学正命题的人性力量和神学反命题的空泛无力。舍斯托夫认为,帕斯卡尔神学正命题指向圣经天启的信仰世界,是上帝启示予人的人性真理,源自上帝救赎的神圣恩典;而神学反命题则指向世俗的观念世界,属于形而上学逻辑推演的思辨真理,不过是人类狂妄理性的自我欺蒙。圣经启示的信仰真理必须从人性存在的基本事实中追寻,从逻辑不可能的可能性中祈盼救赎的神恩与罪感生命的根本解救;而思辨真理则只能求助于充满自明性的逻辑求证,借此寻找人性问题的解答并试图提供普遍的理性说教。因此,在舍斯托夫看来,帕斯卡尔神学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张力,正是源于耶路撒冷的启示真理与来自雅典的思辨真理之间的张力,同时亦是生活苦难的荒谬性与必然法则的自明性之间的对立,是敢想敢为与俯首听命之间的人性冲突。[②]对此舍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西方人俯首听命的人性谦恭史。[③]
然而,舍斯托夫的理解有着自相矛盾之处。其实,西方思辨理性固然表达了人性俯首听命的谦恭一面,同时却以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极大地宣扬了人性应有的权能。尼采曾说过,自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以后,人类开始离开中心向无限的X奔去。[④]人的主体性正是那个无限的X。康德倡导理性批判的哲学革命使人性世界及自然世界开始环绕主体性运行。主体性以康德标明的真实理性为根基与归宿,并因此而确立其本体论地位;同时,主体性也是现实人性的最终理念和最佳的行为准则,从而又使主体性化的本体论变成主体性化的伦理学。合乎理性的人性行为即是善,而违背理性的主体行为即为恶。人的主体性通过理性使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同时人的主体性通过为自然立法而走向人为自己立法,这就是人性道德的实践理性。故此,理性成为自然法则的同时亦成为人性自身的行为法则,理性在成为自然世界造物主的同时亦成为人性世界的救主。通过康德批判的真实理性,人终于成为人性存在的目的,人就是人性的所有意义与价值唯一而终极的存在尺度。古希腊智能普罗泰戈拉所鼓吹的“人是万物存在之尺度”的人文理念,在康德的真实理性中似乎已成现实。自康德以后,西方哲学史滔滔未绝的理性雄辩日益盖过思想本身的真正意义。正是康德里程碑式的哲学业绩,促使舍斯托夫深省:真实理性所标识的人类主体性是否等同于人性的所有价值?人的主体性是否就是人性唯一而终极的真实内容?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则是否能够宽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们的心灵苦难?同情和至善的美好愿望是否能够抚慰约伯的内在痛楚?是否能使列吉娜再回到克尔凯戈尔的身边?[⑤]这些出自人性最根本处的深刻思考使舍斯托夫认识到:人必须寻找高于同情、高于理性之善的终极事物,人性必须寻找上帝。因为,唯有圣约所启示的上帝能救助生存中的每一个人。
舍斯托夫关于真实人性的价值信念,隐含着现代基督教神学企图克服的艰难课题:必须诘问理性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合法性与价值根据。然而,当舍斯托夫回到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的具体化的个人性思想时,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史事实:漫漫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即是一种理性本体论的神学。众所周知,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曾受柏拉图理念论的深刻影响,而托马斯·阿奎那则把亚里斯多德主义引进基督教,并因此超越了奥古斯丁而奠立经院哲学化的神学体系。经院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存在论神学,其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理性证明,使上帝存在问题似乎可借助理性而加以确证。这实际上表明人类认知结构的理性世界与圣经天启的信仰世界具有同一性的精神信念。这也就是相信认知理性乃堪称可靠的人性根基。经过康德的理性批判,本体论变成了伦理学,使认知理性结构中的上帝论问题转化为道德化实践理性的基本设定。黑格尔在康德之后所完成的思辨哲学对希腊思想与基督宗教(特别是路德新教)的辩证综合,又使道德论的上帝成为思辨形而上学的上帝。至此,充分思辨化的理性上帝成为人性精神生活的最终基础。黑格尔相信,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性的亦就是神圣的和完善的。黑格尔的人性信念,实际上已经摒弃了圣经神学的信仰情怀。克尔凯戈尔严厉抨击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神学冲动正在于此。
二
尼采曾指出,人亲手用科学理性杀死了上帝。形而上学的上帝死了。其实,不仅科学理性可以拒斥基督教的信仰真理,如数理逻辑大师伯特兰·罗素试图以科学理性取代基督宗教,视基督宗教为一种无所用处的文明遗迹;而且,从人文理性同样可通往对宗教信仰的摒弃,如蒙田式的自我怀疑与尼采对大众理想的全面怀疑,启蒙运动对天主教会的历史性批判与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人本学批判。凡此种种针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论诘难,导致西方社会终于进入一个没有宗教的后宗教时代(朋霍费尔语,或称后基督教时代)。现代西方神学界所谈论的“宗教的终结”或“上帝隐匿的成人社会”,促使神学家们重新审视神圣事物与非神圣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与关联性。20世纪初,一些西方神学家所倡导的“神学革命”,其重要标识就是使上帝问题与人的问题同时进入基督教神学的思考视域。神学家布尔特曼曾经说过:“上帝问题与我本身的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⑥]
上帝论问题不仅是传统基督教神学人性论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现代神学人性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由于上帝问题的存在,人性问题的根本解答注定成为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上帝问题的深思与神思,当下关涉现实的人生问题。现代基督教神学对上帝观的重新关注,实即是对现世此在的人性问题的关注。当然,对上帝观问题的重新审视,其实也就是现代基督教神学危机处境的深刻表现。
现代西方“神学革命”的首倡者是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1886—1966)。巴特是本世纪最初回应神学危机的思想代表,他曾把现代西方神学的危机处境概括为三个命题:“我们作为神学应该谈论上帝;我们是人,不能以这样的身份谈论上帝;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这两个方面,同时敬重上帝。”[⑦]因此,巴特曾断称,世界就是世界,而上帝就是上帝。在世界与上帝之间有着严格而纯粹的界限。源于圣经启示的神学信仰既与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毫不相干,亦同推崇人的理性论证上帝问题的理性主义毫不相干。巴特认为,人的理性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谈论上帝,而只能接受上帝的神启。上帝的神启是一个生命事件,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事件。唯有通过十字架上的事件,人才可能看到、知道并理解上帝。巴特的神学立场表明,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法拥有关于无限存在的上帝的知识,只有通过无限超越的上帝存在才能领会人的存在本性。
上帝观是巴特神学的真正精魂。为此,巴特主张现代神学必须一切从源头开始,必须从唯一给上帝之道(Word)作根本见证的《圣经》开始。如果说,马丁·路德回到圣经是为了重新确立对上帝的真正信仰,那么,卡尔·巴特回到圣经却可说是为了重新发现上帝。巴特所重新发现的上帝是一全然异质的、绝对而纯粹的否定者形象:“上帝根本与此和彼的对立无关,他是纯粹的否定,因而是“此岸”和“彼岸”的彼岸,否定的否定,这一否定意味着为了此岸的彼岸和为了彼岸的此岸,意味着我们的死亡之死,我们非存在不存在。”[⑧]可见巴特神学的上帝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存在。作为纯粹否定的神性事物,上帝是评判神圣与非神圣的终极依据。如果肯定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具有价值与意义,那么对于这一切的否定也必须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否定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具有价值与意义,那么这一切否定的否定也必须具有价值和意义。世界与上帝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固然表明巴特神学中严格而纯粹的上帝观;在另一方面却深刻反映了现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时代处境:上帝并不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上帝之间的辩证处境意味着人与信仰真理之间的精神关联仍处于流离状态,仍处于走向十字架真理的途中。
从巴特神学的上帝观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基督教神学理论所隐含的三个终极预设:上帝是解决上帝问题的终极预设;上帝是理解世界观问题的终极预设;上帝是解答人的生命问题的终极预设。正是由于上帝问题的存在,人生问题的根本解答才成其为现实的可能和可能的现实。诚如布尔特曼所言,上帝问题与人本身的问题乃是同一问题。于此,人之解救问题即是上帝问题的根本所在。当然,神学的回应只能在于来自上帝神圣的救赎信仰。正是当上帝这一终极预设成为人性的信仰真理时,基督教神学才能在倾听上帝言述中展现其独特的人性思考。
巴特尝称,神学应该为了这个世界而存在,更应该为了人的上帝而存在。但是必须指出,如此敬重上帝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那曾撼动现实人心的“为了人的上帝”的宗教信念,只能是古典而纯粹的神学理想。而且,由于巴特神学并未指明从神到人的道路之真实性与唯一性的充分依据,反倒被其他神学家指责为“超然地不负责任”[⑨]。一句话,巴特试图从人与上帝之间的辩证处境中体认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并不能为西方人性危机提供现实的出路。
三
面对现代西方非神圣化的激变,同样来自基督教神学界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1906—1945)却作出了与卡尔·巴特不同的神学回应。如果可以把巴特式的神学回应概括为“为了人的上帝”的话,那么朋霍费尔式的神学回应则可称之为“为了上帝的人”。
不同于巴特严分上帝与世界的界限,并进而拒斥非神圣化倾向的神学立场,朋霍费尔更强调直面俗世非神圣化的现实态度。当然,朋氏的现实态度决非是主动迎合非神圣的俗世社会,而是基于他本人对基督教福音精神的根本理解。朋霍费尔把西方俗世化进程理解为人类已经成熟的社会性标志,表明西方世界业已摆脱对宗教的精神依赖,正走向一个根本没有宗教的时代,因此预示着现代西方一个“非宗教的基督教时代”的悄悄来临。这一非宗教的基督教时代,其根本特征在于:曾与人同在的上帝也就是被人离弃的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与上帝面对面相处,但不依靠上帝而生活。上帝被推出了世界,走上了十字架”[⑩]。因此,在非宗教时代里,与其说是人被上帝抛入此世,勿如说是上帝被人挤出此世。在朋氏看来,那个与人面对面相处的上帝,不再是巴特神学中解答上帝问题、世界观问题在神学上的终极预设,而仅仅是作为解决此世的人的生命问题的神圣存在与此世的所有人面对面相处。卡尔·巴特把上帝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终极预设,实际上却是把圣经中的上帝设定为纯粹的超越者形象,而朋霍费尔的上帝,则是通过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而与此世所有的人一道参与现实的苦难。因此,朋氏指出:人不应该把上帝当作软弱无力时的救助神思,不应在遭受失败或身处生存困境时才吁请上帝。他希望“不是在生活的边缘地带,而是在生活的中心;不是在软弱无力时,而是在力量中,因而就不是在人的苦难和死亡里,而是在人的生命和成功里来谈论上帝”[(11)]。于此可见,与巴特神学强调上帝纯粹而辩证的超越性相比较,朋霍费尔的上帝失去了更多的否定性特征,而增添了肯定现实人性精神的思想内容。
诉诸上帝论神学的真理观,巴特神学的真理是纯粹的、与此世的其他真理全然不同的、绝对的启示与权威,而朋霍费尔的信仰真理则更强调效法基督的献身救世的福音实践精神。巴特神学把个人性的信仰实践推向生存的边缘,而朋氏则把基督信仰拉向现实生活。巴特主张救赎的恩典只能来自神圣的真理本身,而朋氏则认为恩典的真理并不止于神恩自身,而更在于人性的奉献精神。为此他批评马丁·路德式的“因信称义”的恩典是廉价的恩典,是不付出做基督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并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朋氏认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思想观念上的认信,而更是行为实践上的追随与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性精神,参与并分担上帝在此世的受难。为了人的上帝最终将转化为对“为了上帝的人”的生命负责的现世情怀,并最终转化为“对世界负责”的现实关切。
在现实社会的时代处境之下,圣经启示的信仰真理应审时度势地转化为个体人性内在自觉并主动参与的价值信念。朋霍费尔囚中神思所表达的“对世界负责”并“参与上帝在此世的受难”的信仰实践,表明西方神学界开始放弃巴特对上帝超在之神圣性的神学理解,而转向追随基督的临世性与属世性,并进一步把上帝论与基督论统归于“对生命负责”的人性情怀中,使基督信仰更具备充实的人性根基。
必须指明,朋霍费尔“对世界负责”的现实情怀并非伦理主张,而仍然是一种基督教的信仰行为。“对世界负责”的信仰特质在于耶稣基督所践行的福音精神,其信仰根基在于人性生活与神圣性之间的生命关联,并非是人伦关联的世俗道义。他曾在《伦理学》中提出“末世与末世之前的事物”的神学观点,认为基督教神学确实扎根于并关注着终极的、超越的、末世的东西。但是,在终极的东西之前,有次终极的东西;在最终的事物之前,有次最终的东西。而这些就是人类在人伦社会中每天都在关注的那些事情。对终极事物的关注意味着,为着终极事物的缘故,也必须关注次终极的事物。[(12)]由此可见,朋霍费尔基于人神关系而非人伦关系展开其“对世界负责”的神学思考,其人性思考的最终指向仍是上帝在世界中的爱的福音信仰。
朋霍费尔的囚中神思所表达的人性情怀,表明在一个根本非宗教的俗世社会,确认个人对上帝神圣的真正信仰更需一种冒险精神。作为实践的真理与真理的实践,基督信仰只能来自人性生命的悔改,而决非来自道德教化意义上的人性完善。基督徒的人性使命即是此时此世的此在生活中主动分担上帝的苦难,而这就意味着悔改的完成。朋霍费尔认为,在这个俗世化时代,缺乏的不是信仰的理由,而只是缺乏走向信仰实践的勇气;人类并不缺乏生命的理想,而只是缺乏生命实践的激情与信念。一句话,并不缺乏为了人的上帝,而只是缺乏为了上帝的人。在信仰实践与宗教情怀日益流离的时代里,朋霍费尔毅然决然地否弃宗教化的基督教,使信仰实践落归现实人性的具体行动,试图借此能够明确基督信仰所本具的人性精神,当不失为明智的识见。
四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见,现代西方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现代神学日益意识到理性传统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并试图摆脱关于上帝存在问题的传统辩护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实际上只是在维护无神论,给无神论提供论据”。现代神学企图超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直面基督信仰的人性力量而撇开对上帝问题的理性论证。在强调上帝超在的神圣性的同时,也关注现实人性的实存处境,以使基督教神学取得信仰的人性根基。
其次,现代神学的人性思考,虽然离不开上帝论问题的重新审视,从而仍然有强调外在而超越的理论倾向,但试图从实存人性的基本事实中寻求信仰根基的努力,却表明其人性思考处于传统与现代纠缠难清的困境,并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因而也就不可能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
最后,现代神学的信仰真理不再是由奇迹加以证明、借教会权威加以确认的历史“事实”;亦不再是以“体系”加以确证的理性“真理”。而是向人类的自满自大与空虚绝望挑战的福音精神。因此现代神学所有深刻的人性思考,不可能完全摆脱由信仰所获致的人性完满,不可能没有人与上帝之间的终极关联。人性最终将在上帝的圣爱中完成与圆满。这就是现代神学人性论的基本识见。
从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基督教神学把信仰落实于实存的人性力量,严厉批评西方传统中由来已久的推崇认知理性的自满傲慢,似乎符合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文传统。但是,西方神学对“理性的傲慢”的批判,难道没有流露出那种“我比你神圣”(h-olier than thou)的“信仰的傲慢”神情吗?已有论者注意到以承绪中国文化道统自居的新儒学思想中“良知的傲慢”态度。[(13)]如果把新儒学“良知的傲慢”与现代神学“信仰的傲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可以借此反省不同语境下的人性思考呢?世界性的人文存在绝无例外终必关注人性中的创造力量。从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中,中国的人文传统或许能够领会到转化的对话可能。
注释:
[①][②]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07、182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参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253页,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④]尼采:《冲创意志》,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⑤]参见舍斯托夫《旷野呼告》第107页,方珊等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⑨]约翰·麦奎利尔:《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71、405页,高师宁、何光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⑦]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63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⑧]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64、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⑩][(11)]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第175、129页,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麦奎利尔:《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15页。
[(13)]参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中《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