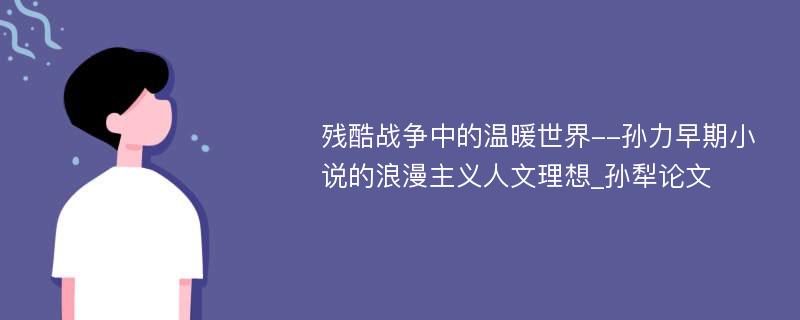
残酷战争中的温情世界——孙犁早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人文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温情论文,人文论文,残酷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07)10-0071-06
孙犁是著名的解放区文学作家,他之所以能在众多解放区作家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不仅是因为“白洋淀”系列作品的题材新颖,更是因为他对政治与战争的独特理解。他虽然也描写战争的残酷场面,但是战争本身却并不是他作品所要表现的正面主题;他虽然也讴歌崇高的政治信念,但是政治写意却又是以人性美与人情美的独特方式得以表露。所以,在孙犁早期的小说创作当中,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遮蔽了中华民族现实生活的深重苦难,血色浪漫的故事叙事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战斗士气,温情诗意的艺术画面洋溢着令人心醉的审美情致。这种渴望和平、向往宁静、追求完美的人文理想,既集中凸现了孙犁早期作品的浪漫风格,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美丽的心灵:人际关系的和谐颂歌
作为以写战争题材见长的解放区小说作家,孙犁早期的作品创作似乎很少去描写烽火岁月的残酷场面,也没有去刻意表现苦难人生的悲剧意识。恰好相反,他把社会生活的关注视角,投向了对普通农民美好人性的深刻发掘,并以一种令读者远离世俗尘嚣与现实纷扰的情感态度,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优美而宁静的温情世界。在这个充满着人性善良与和谐仁爱的完美世界当中,家人、战友以及军民间的亲密无间,使得孙犁早期小说呈现出犹如天籁地籁般的纯净画面。用他自己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来说,即:“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颗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1]242追求诗意、保持“纯”心的艺术追求,造就了孙犁早期小说的抒情风格,更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极高境界。
为人熟知的《荷花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古老而动人的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故事。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在没有征得家人同意的情况下“第一个举手报了名”参军。夜间回到家后,他“不像平常”的一笑泄露了心事,水生的妻子知道了真相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阻拦与哭泣,她虽然内心波澜起伏难以平静,但“女人的手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所有的抱怨都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含蓄表达。尽管对丈夫的离去心有不舍,可“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的坐在院子里等他”,识大体、顾大局的水生妻,终于以自己的理解和宽容,亲自帮丈夫打点好包袱送他出门。水生的父亲也深明大义,胸襟开阔。他对儿子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这样一个传统的送别场面,我们看不到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而是平淡质朴的骨肉亲情。水生走后,妻子终究有些“藕断丝连”,忍不住结伴去找丈夫,却阴错阳差地将日本鬼子引进了游击队的伏击圈,让水生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结束后,虽然水生有些生气地责怪道:“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但却将包装精致的饼干盒扔到女人们的船上。一句看似批评的话语背后,包含水生对于妻子的无限柔情。在这个极平凡的故事叙事里,作者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表现战争本身的残酷性,而是要表现妻子、丈夫、父亲三者之间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亲情关系;三者关系也完全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文化与夫权文化的落后因素,进而呈现给广大读者以一种解放区的全新家庭人际关系:这里的妻子美丽而贤淑,这里的丈夫英勇而柔情,这里的父亲善良而伟大。特别是在《嘱咐》里,父亲已永远离去,读者通过水生妻的一段话,对于这位极其普通的农村老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水生归队前,妻子一定要让丈夫去老人的坟上看看:“你去看看,爹一辈子为了我们。八年,你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人家照顾了咱们全家。……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跑,累得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也是一种人性的善良,作者并没有用什么豪言壮语去渲染普通百姓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然而这一席感人肺腑的亲情话语,令人为之感动唏嘘。《麦收》讲述了一个一家人齐心协力为抗战服务的动人故事。主人公秃大娘不仅将两个儿子都送上了惨烈搏杀的抗日战场,并且还支持年仅十五岁的孙女二梅参加村里的妇救组,秃大娘自己也忙前忙后为妇救组送茶送水。贯穿这个故事始终的情感导向,同样是家人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在这篇小说里,孙犁同样也为我们构建起了一幅共同抗敌、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
孙犁笔下这种和谐与温情的人际关系,不仅体现在家人之间,同时也体现在战友之间。《游击区生活一星期》里,“我”与19岁的游击组员三槐同住地洞,并“住在一条炕上……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在这种最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中,人际关系的温情与爱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三槐悉心照顾着自己的战友,“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他总是选择最甜的有锅巴的红山药叫我吃”。在《小胜儿》里,小金子与杨主任之间也是心脉相连。杨主任是那么的体恤战友,“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勇敢得没对儿,总叫别人小心。平时体贴别人,自己很艰苦”。战斗中,杨主任为了保护战友,“跳出了掩体和敌人拼了死命”。他牺牲后,小金子就病了,“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他的脑海里老是一幕又一幕地重复放映着主任和战友们的英姿,而“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小金子的所有思绪,都似乎随着已逝的英魂,飘飞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了。他有这么一段朴素而催人泪下的话语:“牺牲了。我老是想他。……老是觉得他还活着,一时想该给他打饭,一时想又该给他备马了。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罢了!”血肉相连的战友之情,在这无奈的思念之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孙犁笔下的第三大类人际和谐关系,体现为军民鱼水之情。《蒿儿梁》里,只是因为伤员们吃腻了小庄里的莜麦面和山药蛋,这里的女主任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川里为伤员们寻找大米和白面。在敌人袭击这个小村的时候,还是这位主任和那些淳朴可敬的村民们,及时抢救转移了八路军伤病员:“她(女主任)脸上流着汗,手拉着踉跄跑来的刘兰!在她旁边是由蒿儿梁老少妇女组成的担架队,抬来了五个伤员。……凡是有力量的,都在担架上搭一把手,把伤员送了出来!”深厚的鱼水之情,感人的军民关系,在孙犁的笔下简直是数不胜数。在《碑》里,赵老金一家人的心,始终与抗日勇士们紧密相连,李连长与战士们没有来访的时候,这一家子惦记着他们,渴望他们的出现;而当他们终于出现,并要求赵老金渡他们过河的时候,这一家人的心却又揪了起来。送走勇士们之后,大娘再也不能入睡,她坐在炕上侧耳倾听屋外可能发生的一切,尽管河滩里的风很大,她什么也听不见。但竟能从心里“听见了那一小队战士发急的脚步,听见了河水的波涛,听见了老李受了感动的心,那更坚强的意志,战斗的要求”。他们一家人都“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担心他们遇到什么危险。当李连长等战士英勇牺牲之后,赵老金一直延续着一个悲壮然而充满诗意的举动,他每天去李连长等战士牺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撒网,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英雄们的灵魂”。还有《刑兰》,尽管他自己家里穷得孩子在冬天裤子都没有得穿,他们却将很贵的木柴,一捆又一捆拿来给战士取暖;在《女人们》里,穿红棉袄的年轻姑娘,用“我”觉得只有“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动作,悉心照料着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总之,生活在孙犁笔下的人们,他们的一切行为深刻地喻示了仁爱与温情在民族集体意识中的厚实根基,他们的灵魂都是平等而纯净的。正如人类学家威廉森所说:“任何东西都有灵魂,没有一个灵魂优于另一个灵魂,不存在‘高’或‘下’、‘优’或‘劣’,也不存在‘支配’或‘从属’。这些高低优劣等区分只是从不清晰的思维中产生的幻觉”。[2]137孙犁正是用他自己单纯而具有诗意的童心去进行写作,他有意识地避开严酷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安与压力,而站立在人性的立场对人际关系的古朴、和谐与温情进行了充满诗意的讴歌与赞赏,进而还原出艰难岁月中人性的本真与美好。
二、恬静的世界:人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孙犁早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向读者展示一个令人陶醉的温情世界,其原因除了美好人性的诗意写真外,人性的淳朴与唯美的风光,也构成一道令读者难以忘怀的靓丽风景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作家都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导下,过分强化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实用功利意识,大大淡化了对美的事物的直觉感悟性。也正因如此,孙犁给当时的解放区文坛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他的笔下,人们重新感受到人与大自然之间单纯与和谐的原始美感。
在孙犁早期的小说创作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关系。《荷花淀》里,作者以“月光”、“苇子”与“女人”这三种意象,构成了一幅清丽雅致的艺术画卷。在月光如水的庭院中,“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象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罩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清新的荷叶荷花香”。在充满血腥杀戮的战争年代,水生妻这样的人物形象超越了现实苦难,在宁静而和谐的大自然中与天地灵气融为一体,俨然仙女下凡一般,给人以完美而圣洁的视觉意象。作者极力描写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并非是对残酷现实的有意逃避,而是对生活充满着坚定的乐观信念。孙犁将大自然赋予了浓厚的神奇灵性,它是游击队战士们的最好保护神,荷花淀“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危险来临之际,大自然成了庇护人们的理想去处,他们或躲到繁茂的荷叶下,或“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或藏到像迷宫一样的苇垛里。即使危险使他们无法再逃离了,大自然也便成为了他们生命归宿的最后场所:“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任何恐惧,大自然给了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无穷的力量和心灵安抚。
其次,是人对自然敏锐的感受力。孙犁的早期作品中,多处描写了人物对自然的态度与感受。他笔下的人物与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亲近之感。《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中,“我”对自然充满了兴趣与情感。当“我”在地洞里闷了几天出来后,“我看见旷野就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十分显然,这时的“我”已经将大自然当成了自己最亲密的生命伙伴。同样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感觉异常灵敏,“我”感觉到麦苗地“就要挺出穗头”,感觉到“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看到大自然被破坏,心痛不已,“心里想着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就难过的事”。将大自然比作自己心爱的孩子,可见他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已非同一般。
再次,是大自然也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蒿儿梁》中,尽管到处冰天雪地、一片苍凉,但在这苍凉之中,依然会绽放出热烈而令人振奋的美感:“全村只有一棵歪把的老树,但遍山坡长着那么一丛丛带刺的小树,在冰天雪地,满挂着累累的、鲜艳欲滴的红色颗粒。”在这儿,严冬酷寒中的大自然景象,似乎不忍心让抗日勇士们感受到苍凉与绝望,硬是执拗地展现出充满希望的鲜红亮色,暗示着作者内心世界中的必胜信念。《碑》中的八路军战士们牺牲在河里后,与赵老金日复一日执著的打捞相对应,那长年不息流动的浑黄的河水也“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浇园》里,自然与人的情感,再次合二为一。“一棵小葫芦攀援上去,开了一朵雪白的小花,在四外酷旱的田野里,只有它还带着清晨的露水”。小花与露水的意象,恰好暗示了两个年轻人之间刚刚萌生的纯洁爱情。大自然的人性化抒写,令人惊叹孙犁艺术想象力之丰富,同时这种诗意童心的创作构思,又极大地增强了他早期作品的审美内涵。
在外部狼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孙犁何以描绘出这样一幅又一幅人与自然平静和谐的画面呢?或许荣格的这段话能给人启示:“居住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等地的印第安人,相信他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的生活以超过他们有限生存条件的远景和目标。它给予他们以足够的空间来开拓其人格,并使其有充实和完整的人生。”[3]67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孙犁以及他笔下的荷花淀人是如此坚信自己是大自然的儿女,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客观存在,才使他们在自己的心中建构起一个宁静与悠然的和谐世界。当然,这个完美世界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着战胜强敌的巨大精神支撑。
三、崇高的信仰:血色浪漫中的人文理想
卡西尔在《人论》中曾指出,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他还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进一步说明,“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4]84孙犁便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总是尽量把璞雕琢成玉,尽可能地在乱石堆中发现美丽的东西。他早期小说创作,虽说产生于残酷的战争年代,但在他的笔下,战争的残酷性往往被大自然的诗意性所遮蔽,政治色彩也往往被柔和飘逸的抒情性所中和。正是因为孙犁早期作品充溢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我们认为他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家。孙犁毋庸置疑是一位红色典型作家,但是他在谈及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却一再告诫文坛后辈要“离政治远一点”,并说“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5]363的确,在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火红年代,孙犁以他的才华和睿智,灵活巧妙地写出了一部部艺术品位极佳的文学力作。他的小说创作尽管客观存在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又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从而最终实现了以艺术遮蔽政治,以浪漫冲淡血色,以乐观消解痛苦的人文理想。
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讲,孙犁可以说是一个执著于美的现代作家,他的一生都在热烈地追逐美,赞颂美,对此他本人从未表示过任何异议。晚年的孙犁在谈及那个特殊年代以及自己的创作时,仍然十分肯定地说:“善良的、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1]241确实,人类的情感都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愿意牢记生活中最美好的情绪意象,而刻意抹去那些不愉快或令人感伤的情绪记忆。这一点在孙犁早期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他的作品里,残酷的战争与人性的丑陋几乎都被作者主观消隐了,而美和善良的因素则明显得到了人为的升华。即使丑陋的东西被他撞见,他也会在作品中将它们改头换面,并为之着上美丽的衣裳。如他讲述《山地回忆》的写作时,就曾提到他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并不是小说中那位虽然泼辣、但是善良可爱的美丽女孩,而是一位刁蛮泼野且不讲道理的青年妇女。显然在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孙犁把他对山地女孩的美好印象糅合到这位人物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用的多是彩笔,热情的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6]53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融合。《荷花淀》里的女人结伴而行去看望自己的丈夫,却在淀里遭遇敌人,于是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战斗,然而这场战斗,也奏响着欢乐。躲在“铜墙铁壁”一样的大荷叶下的战士,只不过用了三五排枪的工夫,就用手榴弹将敌人的大船击沉了。战士们在欢歌笑语中打捞战利品,他们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还有一袋又一袋的面粉和大米,水生甚至还捞出了一包精致的饼干扔给女人们。这是一场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且收获颇丰的奇特战斗,由于作者的原始出发点是唯美而非血色,战争的残酷性显然是被作者的浪漫诗意给淡化了。《战士》里,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的革命战士,照样可以指挥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钟》里,尽管敌人武装到牙齿,然而只要大秋与他带领的青年游击组一掏出枪支,敌人便狼狈逃走。孙犁笔下的人物形象,活得也充满着诗情画意,比如:少女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女人们在敌人到来时虽惊惶逃跑,但敌人过去后她们便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的说笑着回来了”;尽管死神之手随时可能掠走这群鲜活的生命,然而只要还活在人世一天,她们便生活得“活泼愉快,充满希望”,坚信胜利就要来到。在孙犁早期的作品中,还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群人间精灵:《黄敏儿》中的孩子们可以在鬼子和汉奸的眼皮底下,来无影去无踪令敌人心惊肉跳;《芦苇荡》里的老人为了给受伤的女孩儿报一箭之仇,一人竟然能够神奇地消灭十几个日本鬼子。应该说《芦苇荡》最能够代表孙犁早期作品的血色浪漫艺术风格:他巧妙地布下钩子阵,神态自若地诱使鬼子进入圈套,然后用船篙一个个敲碎被鱼钩钩住身体的鬼子脑袋:“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的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上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而那位英勇神奇的老人则“举起篙来砸着鬼子的脑袋,象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而这位老人一边拍打着日本鬼子,一边竟还惬意地向苇塘望去一眼,因为在那里如同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的芦花下面,竟还藏着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盖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诗性与理想、浪漫与抒情,被作者发挥到了完美的极致。战争与政治、现实与理想、生活与艺术能够如此的完美统一,这在解放区作家当中恐怕是并不多见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崇尚自然、歌颂人性最典型的作家应该说是沈从文。他一生远离政治,远离都市,全力在作品中精心营造一个恬静、秀美、古朴的田园世界。他笔下的湘西民风淳朴,善良仁义,没有受到人类现代文明的任何污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边城生活洋溢着诗情画意。这种世外桃源的艺术想象,最终奠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无人取代的特殊地位。虽然孙犁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都与沈从文有所不同,但是他追求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创作基点,却与沈从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在孙犁早期的小说创作当中,明显打下了沈从文影响的深刻烙印。20世纪30年代,沈曾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孙犁对这份副刊别有钟情。他说:“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7]213由此可见,孙犁的小说风格与沈从文的审美习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非偶然。受《大公报》特别是其副刊里沈从文小说的潜在影响,孙犁要在他作品中构筑这么一个不落世俗、清新雅丽的艺术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沈从文是完全远离政治,因此他完全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悠然地做着理想主义的自然之梦。而孙犁不同,作为一个解放区作家,他的生活时刻都必须与政治紧密相连,战争、流血、死亡等等残酷现实,每天都在他身边发生,他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文学创作又不能不充分去展开生动活泼的艺术想象,理想与现实、政治与艺术、战争与生活的矛盾对立关系,是他面临的最大障碍。孙犁的聪明才智就体现在他并不回避现实矛盾,而且始终保持一颗难以泯灭的诗意童心,在不脱离现实政治与战争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赋予自己作品以最大限度的审美趣味性。这使得我们在他早期的作品里,既看不到中国农村的凄惨破败,中国农民的封建落后,也嗅不到战场厮杀的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飞溅血腥。孙犁用他想象丰富、文采生动的艺术之笔,消解了苦难,驱散了恐惧,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精神,为解放区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艺术追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里程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犁作品中唯美主义的艺术自觉并不亚于沈从文,他用田园牧歌似的笔调来描写战争,他在战争中言说人文理想的诗情与浪漫,他以自己对于战争与政治的理解与感悟,深刻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代性价值观的深度渴望,同时又以自身健康向上的乐观主义情绪,驱走了战争中人们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并鼓舞人们树立起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孙犁不仅是解放区文学的光荣与骄傲,同时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与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