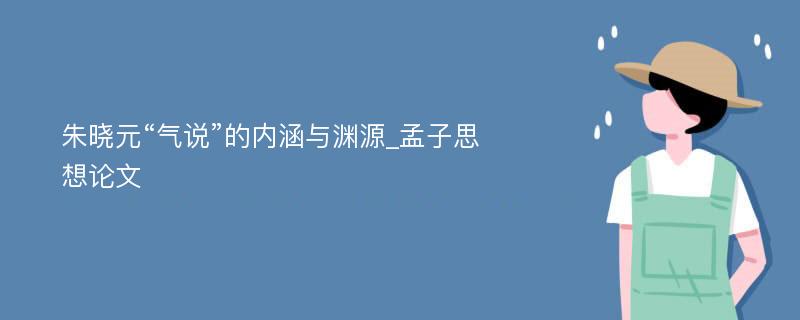
朱筱园的“气论”内涵与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朱筱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朱庭珍的“气论”,集中国古代“气说”之大成,建构起从养气、炼气的理论基础到具体内容、方法;从文学创作的“真气”说,到艺术鉴赏诚中形外之“文气”论等,是较为系统,较为完整的“气说”理论。
关键词 古代文论 养气 炼气 真气 客气 艺术创作 艺术鉴赏
清代云南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朱庭珍(1840~1903年),字筱园,号诗隐,举人,云南石屏人,在其文艺理论名著《筱园诗话》中,对中国古代文论核心概念之一的“气”,作了精确的辩析与精辟的论述,集中国古代“气说”之大成,建构了从养气、炼气的理论基础到具体内容与方法;从文学创作动力主体的“真气”说,到艺术鉴赏外著于诗文,诚中形外之“文气”论等,较为系统,较为完整的“气说”理论。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气”这个概念曾被广泛用来论述文学创作和鉴赏。然而,由于我们民族思维习惯的积淀,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常呈现出意会性、模糊性等特征,很多概念往往只能意会,很难对它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辩析。用“气”来论述文艺创作与鉴赏,有直觉感受的形象性、意会性,但同时也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加之“气”又衍生出许多复合词,如生气、神气、才气、气韵、气象、气格等等。这些复合词都带有直觉感受的形象性、意会性,由此而表现为在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中运用的广泛性。这样,更导致各家“气说”的复杂性。研究者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气”是“情”,有的认为“气”即韵,有的则认为“气”即“气势”,也有的认为“气”指“气质、才气”等等。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上面所谈到由于民族思维习惯,很少有气论者对“气”作出系统的有条理的科学分析,还在于“气”被引入古代文论后,直至朱庭珍之前还没有一个文论家建构起比较系统、完整的气说理论。清代是我国传统理论总结时代,朱庭珍的“气论”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本文拟对朱庭珍的“气说”理论进行分析、溯源,探究其内涵及其在古代文论中所处的地位。
一
对于诗文之“气”,朱庭珍认为:“诗人以培根柢为第一义。根柢之学,首重积理养气。”又说:“积理而外,养气为最重要,盖诗以气为主,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亦与人同。”(《筱园诗话》卷一。以下所引,只注卷号。)为了对朱庭珍的气论进行分析、溯源,我们还得追溯古代文论中“气”的来龙去脉。
“气”作为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是从自然概念和哲学概念引进的。然而,“气”最先是从与人生命的关系,推广到与万物的关系,再引进古代文论里的。正如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里所指出:“在一切语言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现方式都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人的感觉和情欲那方面借来的隐喻。……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人用自己来造世物”,“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无感觉的事物”,或是“把生命的事物移交给物体,使它们具有人的功能。”(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341页)中国古代文论中气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古人最初凭直觉感受,人有气则生,无气则死。认为充满人体内的是气,它是生命力量的来源。《管子·心术下》:“气者,身之充也。”房玄龄注:“气以实身,故曰身之充也。”《淮南子·原道训》:“气者,生之元也。”王念孙解释说:“元者本也,言气为生之本也。”王充《论衡·气寿篇》:“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进而,古人推而广之,“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用自己来造事物”,由气与生命的关系,推演为气与万物的关系。《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王充《论衡·自然》也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可见,气是物质生命的本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当气被视为万物之源之时,它不仅是自然概念,而且也是哲学概念。
“气”既然被视作物质生命的本原,其概念被引进古代文论,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果嫌前面引文“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物体,使它们具有人的功能”(维柯语)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方东树的话则泄露了古人把“气”引进古代文论的“天机”。他说:“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昭昧詹言》卷一)
在古代文论中,第一次把“气”和文学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论气,首先论证文章各有特色、风格各异,以及成就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家各有不同的气质个性,即“气之清浊有体”,先天禀赋各异。由于作家气质个性不同,决定了诗文风格成就的千差万别。在曹丕看来,作家的气质、个性是先天禀赋,不是后天“养”而致的,“不可力强而致”,即不是用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的。
关于“养气”说的鼻祖,当首推孟子。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也,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所养的“气”,并非“气者,身之充也”,“气者,生之元也”之“气”,而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个人修养、学识、品德行操等综合体现,即精神的东西。所养的浩然之气,乃是一种培养理想人格的方法。所谓“集义所生”,要“配义与道”等,是强调人的道德修养。
把曹丕的“文气”说与孟子“养气”说结合起来的首推刘勰。他说:“缀虚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心雕龙·风骨》)并引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肯定曹丕对孔融、徐干、刘桢的品评,认为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虽引用“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肯定作者先天禀赋对创作有决定作用的观点,但同时又认为后天学习对创作有很大作用,说“功以学成”,“习亦凝真”(《文心雕龙·体性》)。《文心雕龙》养气篇,则是刘勰专门论述养气的功夫对于创作重要性的篇章,论述了行文养气因时之古今、因人之少壮强弱各异,说明不养气的害处以及养气的方法。“学业在勤,功庸弗怠”,“玄神宜宝,素气资养”等都在说明养气的重要。“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等都是刘勰开出的养气良方。后来,象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辙、苏轼等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气说”。明代谢榛、清代沈德潜、章学诚等均对“气说”发表了不同见解,综观唐以来各家“气说”,主张“养气”可说是一致的。至于为什么要养气,有何理论根据,怎样养气等等,不是失之模糊,就是失之笼统。而朱庭珍的“气论”,不仅回答了为何要养气,并为之找到了理论根据,而且也回答了如何养气的问题。
二
朱庭珍说:“昌黎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浮者毕浮,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东坡曰:‘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是皆善于言气者。夫气以雄放为贵,若长江、大河,涛翻云涌,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动者也。然非有至静者宰乎其中,以为之根,则或放而易尽,或刚而不调,气虽盛,而是客气,非真气矣。故气须至动涵至静,非养不可。”(卷一)朱庭珍从哲学高度,为养气找到了理论根据,这就是“以静主动”。动与静是对立的,然而又是相反相成的。朱庭珍用长江、大河之水来喻“气”,也显然受韩愈、苏轼、苏辙等用水喻气的启发。用水喻气体现了我国古代文论直觉感受的形象性的传统。之所以说朱庭珍从哲学高度为养气说找到了理论根据,就在于他在韩愈“气,水也”的基础上,用水的特性“静”与水流之动——“涛翻云涌,滔滔莽莽”,形象地说明“气”为何需要养,积水越多,水流越大。静与动都是相对而言的,任何静止都是运动中的静止。在滔滔莽莽的江河中,就某一滴水来说是静止的,但它是运动中的静止。如果没有无数滴水,没有涓涓细流汇聚,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波浪涛天的气势。“非有至静者宰乎其中,以为之根”就是指此而言的。在朱庭珍看来,“气”要养,要不断补充,否则无源之水“放而易尽,或刚而不调,气虽盛,而是客气,非真气矣。”
自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到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再到韩愈《答李翊书》,先后赋予养气说以不同涵义。宋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则是被研究者所公认,是古代文论家论养气最著名的一篇。他说:“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这段话,上继韩愈,使孟子的养气说在思想内涵和理论方法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养气一方面是在内心修养,另一方面有待于外境的阅历。内心修养谈得比较粗放,仅举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因而“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对外境的阅历,则谈得比较具体,举司马迁周游天下,饱览四海名山大川,并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所以“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之后的古代文论家也大谈“养气”:如宋濂在其《文原》里说:“为文必在养气。……气得其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也;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谢榛在《四溟诗话》里也说:“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辩也。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火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琴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秋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白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诸家所养之不同也。”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也说过:“文以养气为归,诗亦如之”的话。与上述所论养气相比,朱庭珍的养气说要深刻得多,也具体得多。他说:“养之云者,斋吾心,息吾虑,游之以道德之途,润之以诗书之泽,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之府,优游而休息焉,蕴酿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涣然,常有郁勃欲吐畅不可遏之势,此之谓养气。”(卷一)从朱庭珍的养气方法看,主要是编重于内心修养,即思想修养,也包括艺术修养。而不像苏辙偏重于外境的阅历。二者都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谈养气的。“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使方寸中怡然涣然,常有郁勃欲吐畅不可遏之势”,说法各异,旨归同一,都是自己创作经验之谈,都是把“气”作为创作的动力,或曰内驱力。至于“外境阅历”方面,朱庭珍则把它归诸“积理”。他说:“积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语入诗也,谓读书涉世,每遇事物,无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长识力耳。……随时随地,无不留心,身所阅历之世故人情,物理事变,莫不洞鉴所当然之故……。”(卷一)朱庭珍外境阅历则偏重于对世故人情,物理事变的洞察,以增长“识力”;苏辙则偏重周览名川大山,而激发创作热情。
朱庭珍的养气说,扩大了苏辙养气说内心修养方面的内涵,并把它延伸到艺术创作的审美心理之域。“斋吾心,息吾虑”,显然受庄子“斋以静心”的影响。《庄子·达生》篇有一则寓言:“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心齐(通斋,斋戒)以静心。齐(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共巧专而外滑消,然而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鐻是古代一种悬挂钟声乐器的木架子,上面雕刻着鸟兽等装饰图象。梓庆削木为鐻是一个艺术创造过程,而“斋以静心”则是他彼时的心理状态。此寓言说明做事要排除杂念,顺其自然,就能事易工巧。“斋以静心”是艺术鉴赏创作活动的重要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曾说:“陶钧之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也说过:“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由此可见,朱庭珍的“斋吾心,息吾虑”,正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澄心静虑,排除世俗干扰,排除一切杂念,忘却自我存在,使心理机制处于极其敏锐的活跃状态,促成“郁勃欲吐畅不可遏之势”的心理态势。
朱庭珍的养气方法并不止于“斋吾心,息吾虑”,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修养(游之以道德之途)、艺术修养(润之以诗书之泽)、喜怒哀乐人之天性情感的培养(植之在性情之天)、以及理智与高尚志趣方面的培养(培之以理趣之府)等等。总之,朱庭珍的“养气”方法,是系统而较完备的,不仅斋以静心,还要进行道德、思想、艺术、人格、性情等方面的修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性情修养作为养气重要内容提出。强烈的抒情色彩,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之一。《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论及变风时又说:“发乎情,民之性也。”刘歆也说:“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太平御览》卷609 引)在此基础上,后来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刘勰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他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喜、怒、哀、乐等情感是人之天性,如果不注意这方面的情感培养,没有情感的人决不可能写出有感情的作品。因此,在养气内容上,朱庭珍特意提出“植之在性情之天”的观点。之所以然,朱庭珍是这样看的:“诗所以言志,又道性情之具也。性寂于中,有触则动,有感遂迁,而情生矣。性生则意立,意者志之所寄,而情流行其中,因托于声以见于词,声与诗意相经纬以成诗,故可以章志贞教、怡性达情也。”(卷四)当然,养气要培养性情并非朱庭珍首先提出。何绍基(1799——1873年),在《与汪菊士论诗》里,对养气要注意培养性情方面作了较深刻而具体的阐述。他说:“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刻流露出来。……若平日不知持养,临提笔时要它有真性情,何尝没得几句惊心动魄的,可知道这性情不是暂时撑支门面的,就是从人借来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也。”
朱庭珍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养气”内涵,而且还提出“炼气”新说。关于“炼气”的提出,是朱庭珍对古代文论中“气说”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其在思想内涵和理论方法上加以发展。他说:“气”,“及其用之之际,则又镇之以理,主之以意,行之以才,达之以笔,辅之以理趣,范之以法度,使畅,流于神骨之间,潜贯于筋节之内,随诗之抑扬断续,曲折纵横,奔放充满于中,而首尾蓬勃如一。敛之欲其深且醇,纵之欲其雄而肆,扬之则高浑,抑之则厚重,变化神明,存乎一心,此之谓炼气。”(卷一)文章之势,全凭气脉贯注。用“理”、“意”、“才”、“笔”、“理趣”、“法度”来炼气的目的,在于使文章气脉畅通,首尾蓬勃如一,最终达到“自然”。为此,朱庭珍特别强调,诗文“贵一气相生,词意浑成,精光熊熊,声调响亮。用笔则贵有抑扬顿挫,开阖纵摛之奇。造句炼句,则贵生辣警拔,力厚思成,又须无斧凿痕迹,虽炼而不伤气格,乃为上乘。”(卷一)对于“养气”与“炼气”二者的区别,朱庭珍说:“养于心者,功在平日;炼于诗者,功在临时。养气为诗之体,炼气为诗之用。”(卷一)可见,“养气”是蕴内、固本;炼气是形外、著文。时间区别在于平日与临时(用时)之分。从炼气的具体内容看,当代文艺理论中“提炼主题”、“谋篇布局”等已现端倪。
三
历代文论家所主张养之“气”,大多数都是从孟子那里继承下来的“浩然之气”。何为浩然之气?孟子也认为很难作确切解释。不过,他又指出浩然之气有两个特征:其一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并“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二是“配义与道”,“集义所生”。可见,所谓养“浩然之气”,是以“义”来养心志的问题。从刘勰到苏辙,都承袭孟子所持养“浩然之气”的观点,但对浩然之气的内涵,历代文论家均未作深入探究。朱庭珍在其“气论”中,标新立异,明确提出所要养的是“真气”,并非是“浩然之气”。“真气”与“浩然之气”有何异同,其内涵是什么?下文将对此作一些探讨。朱庭珍说:“似乎气之为气,诚中形外,不可方物矣。然外虽浩然茫然,如天风海涛,有摇五岳、腾万里之势,内实渊亭岳峙,骨重神寒,有沈静致远之志。帅气于中,为暗枢宰,若北辰之系众星,以静主动。此之谓醇而后肆,此之谓动而实静,功能层出不穷,不致一发莫收,一览易尽也。在识者谓之道气,诗家谓之真气。所云炼气者,即炼此真气也,养气者,即养此真气也。”以笔者之见,孟子所言,以及被历代文论家所接受的“浩然之气”,与朱庭珍所言的“真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承认“气”养而至这点是一致的;其次,承认养气对诗文有重要作用也有共识。区别在于历代文气论者,对“养气”只停留在表层认识上,也就是说,只看到所养之气形之于诗文的现象。二者关系如何没有作深入探究。如:苏辙在谈到孟子善养浩然之气时说:“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姚鼐《答翁学士书》说:“文字者,犹人语言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归庄也说:“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今读者君之诗,大抵皆气达而格正,声华亦琅琅烨烨。”(《玉山诗集序》)以上这些文论家论气,虽论及作家与作品两个方面,但对作家“养气”与作品之“气”二者关系如何,却没有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探究,至少也是只能意会,而没有能从理论上表达清楚。谢榛虽已认识到作家养气是“蕴乎内”,反映在作品里是“著于外”,但认识仅止于此,终究只得出“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辩也”的结论。(见《四溟诗话》)而朱庭珍的“气论”,则把养气作用于诗文的关系,即“静”与“动”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使“养气”说的理论更加系统,更加完善。他所主张养的“真气”,是处于主导地位(帅气于中)以静主宰着动,象北极星维系着众星一样。诗文表现出来的气,是生动的,多变的,“浩然茫然,如天风海涛,有摇五岳、腾万里之势”,但内心所养的气则是稳定的、沉静的,“渊亭岳峙,骨重神寒”。概而言之,“以静主动”。朱庭珍关于“养气”的阐释,已很接近辩证唯物论关于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阐释。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的本质决定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现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现象是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也是多变的、易逝的。就事物的总体说,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本质比现象深刻、稳定。可见,朱庭珍用“以静主动”的观点,来阐述“养气”与形于诗文之气的关系,既形象又深刻,是与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一般规律相贴近的。关于“静”与“动”的辩证关系,《老子》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十六章),把“静”看作是躁动的主帅。王夫之《问思录·内篇》也曾谈道:“静即含动,动不含静。”当然,王夫之并不是在谈作家养气以及诗文的气势。朱庭珍的“以静主动”的辩证思想,受到前人影响是无疑的。而把“静”与“动”的辩证关系运用到气论中,却是朱庭珍的独创。除此而外,朱庭珍还谈到“客气”,前面所引,在他谈到“养气”时说,诗以气为主,并以雄放为贵,就象长江大河波涛翻涌,一泻千里,但是“非有至静者宰乎其中,以为之根,”否则“放而易尽,或刚而不调,气虽盛,而是客气,非真气矣。”这里的“客气”是与“真气”对立而提出来的。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里曾说:“谢、鲍根据虽不深,然皆自见真,不作客气假象,此所能为大宗。后来如宋代山谷、放翁,时不免客气假像”,并非全是胸臆自流出。从方东树的话看,“客气”是指假借别人的思想感情、艺术风格等,不是出自本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朱庭珍这里所说的“客气”,其含义除假借和假象外,似乎还含有“匆匆过客”之意,假借毕竟是无源之水,假象也只能蒙骗一时,故曰“放而易尽,或刚而不调,气虽盛,而是客气。”
朱庭珍的气论还提到“真气不外驰”的问题,这也是历代文论家未曾涉及的。他说:“彼剽而不留,或未终篇而索然先竭者,正坐不知养气与炼气耳。……予幼作《论诗绝句》云:‘正声自古由中出,真气从来不外驰。’略见大意,可参看矣。”朱庭珍作有《论诗绝句》五十首,这是其三,全诗云:“炼笔刚柔贵得宜,诗家秘旨几人知?正声自古由中出,真气从来不外驰。”“正声”,是指以风骚为代表的诗歌优秀传统。李白《古风》其一,有“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句。“由中出”,用朱庭珍的话说,即“言为心声,诗则言之尤精者。”(卷一)也就是说,“正声”是发自内心,是诗人心中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决非违心之言、矫情之词。“真气不外驰”,是朱庭珍对气理论的又一发展。在《文心雕龙·养气》篇里,刘勰已注意到防止“气衰”的问题,他说:“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真气不外驰”是防止“气衰”的最好办法,对其内涵的理解,涉及到对朱庭珍气理论的理解。从以上分析可看到,朱庭珍“养气”不仅包括思想修养、培养理想人格,而且也包括艺术修养,是作家所具有的气质、人格个性和艺术个性的总和。因此,他的气说不仅具有伦理学、哲学的意义,而且也具有美学意义。他所说的“真气”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形之于诗文方面有相同之处,但“浩然之气”是指精神的东西,而“真气”不仅指精神的东西,也包涵其物质内容,即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元气”性质,否则“真气从来不外驰”就无法理解了。中国哲学中的“元气”,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原始之气,即天地未分以前的浑然之气;二是指天地之间总体之气。王充《论衡·谈天》:“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又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在朱庭珍看来,“真气”是“静者”,它“以静主动”,是动之“根”,根不可外露。因此,“真气”只可“养”,只能“炼”,不能“外驰”。而反映在作品上的气,是“真气”的升华,是个体精神的体现。真气犹如水,形之于诗文的气犹如浮力。水泄光了,浮力也就没有了。正如《庄子·逍遥游》所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综上可见,朱庭珍的气说有如下特征:
首先,气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作家个性、思想气质、艺术修养等禀赋,又是作品体现的气势。
其次,从创作论角度看,“气”创作的动力,它具有动力主体性的特征。蕴乎内,不可外驰,以静宰动。是动之“根”,因而朱庭珍谓之“真气”。
再次,从鉴赏论的角度看,“气”又是观赏诗文的一把尺度,“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形之诗文中的气是“真气”的升华与外著。诗文气势的盛衰取决于主宰它的“真气”之大小,犹如水深则浮力大,水浅则浮力小。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能看到,朱庭珍当之无愧是我国古代“文气”论的集大成者。他论气从养气、炼气,到炼就“真气”,形成一整套较完整,较系统的气说理论,有继承,有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养气”说找到了哲学理论根据,并把蕴于内的养气说与著于外形之于文的文气论,用“静”与“动”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精辟的阐释。他的“气说”理论处于集大成之地位,之所以不被人们认识,是“地势使之然”,他没有居高,其响也不远,加之是清代的云南,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地处偏辟,远离内地,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当代文学理论中,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已不再用“气”这一术语了。但研究古代文论,必然涉及很多关于“气”的理论问题,当代文艺理论中,仍有“气”衍生出来的很多复合词。因此,探究一下居集大成地位的朱庭珍的“气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对继承古代文论的精华,发展当今的文艺理论无疑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