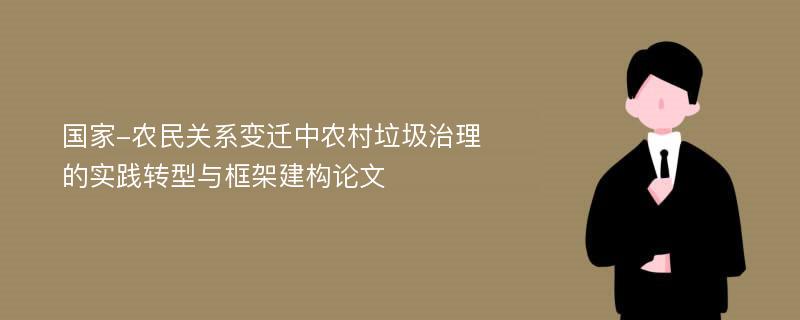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孙旭友 陈宝生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关键词] 垃圾围村;国家-农民关系;城乡一体化;合意治理
垃圾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伴生物,而垃圾问题却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事关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文件,对农村环境治理提出了系列要求。其中,对农村垃圾处理提出了政策配套、技术与资金支持、责任主体明确化、处理方式多元化等操作性方案。农村垃圾问题的生成,与垃圾成分、垃圾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垃圾问题的解决受到国家与农民实践关系的影响。农村垃圾治理在持续关注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等技术逻辑的同时,还需要把农民与国家关系纳入农村垃圾治理进程,把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嵌入农民与国家合意关系的实践构建中。
一、农民与国家关系:农村垃圾问题解决的重要维度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渗透,农村自然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尤为严重。垃圾污染作为我国当下农村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治理对象之一,制约农村社会发展,威胁农民生活环境,对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构成挑战。王金霞等学者[1]对全国26省141个村的调查表明:农村垃圾污染在农村总污染源中占到53%,成为目前的主要污染源。基于农村垃圾问题严重性与污染现实性共识,当前学界对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主要从“技术-管理”和“人文-传统”两个路径展开。
遵从“技术-管理”路径的学者,既承认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对农村垃圾问题的影响,也坚持农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技术之路。其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的基本理念是,面对农村垃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农民身体健康的威胁,可以借助垃圾分类、垃圾焚烧与卫生填埋等清洁技术[2]以及3R模式[3]、垃圾税[4]、城市环卫系统下移[5]、农村垃圾管理公私合作模式[6]等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模式得以缓解甚至解决。例如,聂二旗等人[7]提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气候和地形等因素影响,总体上宜采用分类收集、源头控制、就地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式。Bernardes等学者[8]针对巴西亚马逊农村垃圾的构成和处置状况,指出家庭垃圾源头治理是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
内容型激励理论聚焦于激励的内容,阐述如何利用具体的因素来激励人的积极性。将内容型激励应用于沙盘实训课程,重点在于激励因素的选择上。
坚持“人文-传统”视角的学者,在反思垃圾技术治理缺陷和农村垃圾清洁化倾向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垃圾问题既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后果[9],又是城市-现代与农村-传统二元对立的政治经济问题[10],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社会的地方智慧和传统知识来解决农村垃圾问题。[11]例如,蒋培[12]认为农村垃圾污染严重的背后是农民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的文化转型,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整体理性”观念,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的跨越。吴金芳[13]通过一个县域垃圾处理的历史分析,提出了垃圾处理需要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议。
已有的农村垃圾问题解决和治理应对研究,既有农村垃圾问题生成分析、倡导多元主体合作等方面的共识,也存在现代技术与传统知识的解决路径分歧,且在农村垃圾治理实践中都对国家与农民关系对农村垃圾问题的影响分析不够。这可能会带来两个衍生问题:一是掩盖农村垃圾问题生成的清晰度。农村垃圾问题的生成与垃圾成分变化、垃圾处理方式有关,只有把农民与国家关系纳入农村垃圾问题生成过程,才能清晰地认识到农村垃圾成分的变化与处理方式的转型。二是影响农村垃圾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农村垃圾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但需要动员国家与农民两者的“两个积极性”[14],也受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制约。而农民与国家作为农村垃圾问题解决的主要行动者,二者关系直接影响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理应纳入农村垃圾治理范畴。众多学者①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均表明:国家与农民关系不仅经历了多次转型和阶段变迁,也对乡村社会治理、村庄权力结构、国家政权建设、农村服务供给等乡村社会生活面貌带来不同的影响和实践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借助国家与农民关系变迁视角,通过对山东省W村②在生产生活废弃物循环利用、垃圾随意丢弃和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三个不同时期,垃圾(生产生活废弃物)成分的变化及其处理方式转型的考察,分析和展示村民与国家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角色,以及村民与国家关系对农村垃圾问题解决的影响,以此来推动“谁能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的治理实践。
二、乡村无垃圾:“政治-生活”约束下的农村废弃物循环利用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勤俭节约的国家道德倡导与农民内在生活规范,构成集体化时期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循环利用的推动力。如何把乡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并实现其最大的利用价值,关涉农民自身的生活安排与生计来源,而农民对生产生活垃圾的循环使用,使得生产生活废弃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农村垃圾充分融入村民生活和自然环境③。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不是问题,而是农民生活实践中必须面对的生产生活副产品,并且可以加以利用的另类生存资源。
一是得益于传统农业生产过程的有机性和农民“过日子”的传统习惯,垃圾与社会、自然三者可以相对均衡流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废弃物不但得以多次循环利用,使之内嵌于村民生产生活过程,也能借助自然的物理化学反应充分溶解,将生产生活废弃物融合进农村社会的生产和自然世界循环进程。这种“代谢循环”模式的生产生活,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有机性的表征,也一直被看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5]众多村民的回忆和生活经历显示,垃圾融入自然与社会的表现有:人畜粪便、秸秆等农作物废弃物可以转化为有机肥料用于农业生产,旧衣服可以反复利用,厨余垃圾可以用来喂猪等。
HPLC法同时测定余甘子中5种成分的含量及主成分、聚类分析 …………………………………………… 李 琦等(11):1491
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废弃物是否转化为垃圾,垃圾是否构成农村社会环境问题以及农村垃圾处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的选择,不仅受到垃圾种类与成分、产生机制、治理主体环境意识等影响,也深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等结构性力量制约。农村垃圾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的“有机景观”和日常生活元素,也成为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治理对象。
一是国家、市场等外部力量介入农村垃圾处理事务,改变了农民原先垃圾的制造者、受害者和处置者“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角色。国家等外部介入力量在推动农民自觉性后移之外,重塑了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垃圾治理,让原本带有“私”的性质的垃圾处置彻底转换为国家事务,农民从“国家与农民”合作中抽身。农民处置垃圾的活动逐渐脱离农民原有的日常生活逻辑,从生活化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农民丢弃垃圾和清洁工收拾垃圾的衔接性行为,以市场性合法机制与正当化交换逻辑作为基础,农民原有的自我处理意愿和自我约束行为消失殆尽。
伴随农村垃圾围村的现实与垃圾污染危害的逐步显现,农村垃圾家庭自行处理和传统循环利用的处置方式已被证明无法解决垃圾增量及其污染问题,迫使国家重新介入农村环境事务和担负起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在东部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实施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成为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必然选择。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是借助城乡公共服务统筹和均等化,通过基础设施和环境服务下移、农村垃圾上移的无缝隙链接,彻底解决农村环境卫生事务落后、农村脏乱差和“垃圾围村”等问题。国家在自上而下推动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和借助“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处理模式,把城市环卫系统延伸至农村生产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村庄事务的双重介入。
首先,美国政府各部门有权选择是否对相关主体予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例如,最新颁布的第13846号行政令,授权财政部长在征询国务卿的意见后,“可以”对从事相关受制裁行为的主体予以制裁②Section 1 of the Executive Order 13846 of August 6, 2018,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152.。可见,美国政府各部门需要在综合衡量后,再决定是否对相关主体予以制裁。同时,对于已经受到制裁的主体,美国政府也可以随时决定取消对其制裁。
三、垃圾围村:乡村社会个体化与市场化的环境风险
农村集体化时代结束后,城市化与工业化等社会结构性力量给农村、农业与农民带来了巨大变化。譬如国家及其乡村代理人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与关联度降低,国家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化学化工产品滥用,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能力提高以及个体化意识增强等。乡村社会“三农”结构的全面重构,对农村垃圾及其问题生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只有19.4%的垃圾得到有序处理,49.1%的垃圾被随意丢弃。垃圾还田和焚烧的比率分别为15.3%和12.2%。另外,其他少量垃圾被掩埋后丢于水体中。④这种农村垃圾无法在农村生活场域内和原生态系统中处理的乡村现实,是我国乡村社会“去社区化”等社会结构力量复合型塑的结果。
一方面,伴随社会经济改革开放、农村去集体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把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国家逐渐放松了对农村社会的监管,压缩了自身介入空间,乡村社会自主权增大。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行动单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个体力量在农村社会并行不悖[17],对乡村社会传统的地缘血缘亲和力和国家在乡村的组织力量造成冲击。国家力量在乡村众多公共服务事务中的逐渐后撤和农村社会自我组织力量的式微,都对农村环境治理和农村垃圾问题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是构建国家教育监督与村庄村规民约间的“双向”监管机制。农村垃圾治理与垃圾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内在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和生态人的塑造,也需要外在的监督约束。一方面,需要国家和社会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和监督等方式,达成乡村社会环境治理和农村垃圾处理的有效性,培育具有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环境行为的新时代农民;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和乡规民约的内在力量,发扬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知识的现代价值,抑制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行为。
农村垃圾成分复杂化、来源多样化以及直接丢弃的处理方式,跟传统社会那种“有废弃物无垃圾”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循环系统截然不同,导致农村垃圾无法在乡村原有垃圾处理体系和“垃圾-自然-社会”循环系统内消解。农业生产废弃物不能回归原有的农业生产系统和自然生态体系,以及农民生活废弃物也不再被有意识而有效加以再利用的“代谢循环断裂”[19],使得现代社会生态环境惨遭破坏,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垃圾化”。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又形成了“新的就是好的、互相攀比和高产出高消费”的生活样式和思想意识,使得垃圾持续不断被制造出来。农村垃圾丢弃于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理性化农民最为常用和方便的处理方式。农村垃圾被直接丢弃,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处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
一般认为,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由于不规则沉降、温度应力和浇筑工艺等原因会造成成品混凝土结构产生裂纹甚至裂缝,并对未来的使用构成隐患。在本项目标段内吉隆坡中心车站,设计采用1.4m厚度的底板、0.8m厚度的中层板和1.5m厚度的顶板,单次浇筑混凝土量大,板体按照车站长度分幅浇筑,单幅浇筑时间持续长达12h。因此如何控制和防止混凝土板结构产生裂缝,是本项目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四、农村垃圾问题: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实践后果
集体化时期,偏重生产而轻视消费,鼓励节衣缩食和勤俭节约,国家甚至把超出生存需要以外的消费政治化和道德化。“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和如何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有关消费制度安排的影响。”[16]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倡导,和农民自身的生活现实与生活风尚,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勤俭节约与物尽其用的生活实践在国家与农民两者之间达成了“合意”。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农业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循环使用并“物尽其用”,是一种生活能力和道德要求,更是体察政治立场坚定和道路正确性的表征。生活需求与国家政治倡导之间的合意,不仅有生产生活资料缺乏的现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等革命道德价值的思想链接,同时也受到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甚至村民群体内部的监督。
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所表征的不仅是垃圾治理模式转换和城乡关系转型,其背后还蕴含着国家与农民在垃圾处置等“公-私”混合地带的关系重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的逆转。在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之前,不仅农民跟垃圾的产生、处置和影响等问题完全捆绑在一起,带有垃圾的制造者、受害者和处理者的整体性角色特征,而且垃圾处置也深嵌农村熟人社会、地缘血缘关系之中和社区道德压力之下,导致农民行为在社区生活空间内具有他者与自我的双重约束性。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推进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处理事务,原本是想借助“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机制达成农村垃圾治理的目标,但是却带来了“农村原有垃圾处理系统废弃、乡村环境责任感消解等非预期后果”[20]以及农民置身事外与村庄约束无力的双重“脱嵌”。
二是受制于中国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与废物再利用的政治倡导等现实境遇与道德倡导。充分且循环利用生产生活资料成为当时乡村社会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考察个人政治态度和阶级取向的标准之一。
二是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之后,农民参与的主动性被排除,农民自觉监督意愿和农村社区的约束力量被消解。在政府主导垃圾治理模式下,现有制度设计忽视了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治理的重要作用,导致政府垃圾治理工作缺乏社会基础,社会主体参与垃圾治理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21](P116-121)W村内的垃圾清扫主要由购买政府服务的物业负责,基层政府主要加以工作监督和业务指导。而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之前的村两委组织能力和村落社区的约束能力,以及其所带来的道德压力、社区失范行为修正能力,在“政府监督物业清扫垃圾”的业务型市场关系之下,略显疲惫无力而无所作为。
五、合意治理:基于农民与国家双方意愿的垃圾治理框架
家庭是否会充分利用生产生活废弃物,不仅跟传统农业有机耕作方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关,也受到乡村道德、家庭评判、传统文化规训、社区关系等因素制约。乡村社会中能做到物尽其用和勤俭节约的家庭和个人,会被当成勤俭持家的榜样和会过日子的能手,往往能在乡村社会关系与人际关联中获得较高评价。农业生产过程与农民生活实践的有效链接,使得生产生活废弃物不仅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实现再利用和循环使用,而且带有社会道德和社会关系评价功能。
农民与国家合作治理农村垃圾和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既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体现,也是农村环境迈向总体性治理的切实需要。面对当前“官退民退、官进民也退”的农村垃圾治理困境,“农民与国家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关系”“谁能解决农村垃圾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等问题,不仅需要重新加以认知,而且需要借助历史视角重新反思国家与农民合作治理垃圾的经验,以便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环境有效治理,以及构建国家与农民新的合意性合作提供思路和框架。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切断农村垃圾问题生成的基础上,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这就需要把农民与国家的合意性贯穿进农村垃圾治理体系和治理进程,把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真正立足于农民生活意愿与国家政治意志的结合上,把社区作为农民与国家合意性治理的载体,构建基于“五个基点”的农村垃圾治理框架。
一是实现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且权责统一。农村垃圾治理属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项目,但也需要社会组织甚至农民个体的参与以及市场化机制的推动。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合作是治理农村垃圾的必然路径,而多元主体的权责和行动范畴明晰是实现农村垃圾合作治理的关键。例如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主要责任,尊重农民的生活意愿和培育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监管物业公司的“收费-服务”契约化行为等,而村委会等村集体组织也需要起到承接政府、监管物业和教育村民的责任。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同时也对税收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改进税收征管机制,将容易产生较大的税收风险。
二是达成农村垃圾源头分类与末端分类治理的有效衔接。农村垃圾治理以及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两头”治理力度及其有机连接。从农民生产生活实践入手,从源头上实现绿色消费、垃圾减量甚至零废弃、垃圾分类等。而国家需要在构建合理的垃圾处理方式、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建设科学的垃圾处理设施基础上,通过垃圾焚烧、卫生填埋等垃圾处理方式的有机结合,达成垃圾末端处理的科学化与有效性。
鲁西集团作为一个拥有40年化肥生产历史的国有企业,他们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投巨资先后上马了10万吨尿素硝酸铵溶液、10万吨液体肥、10万吨硝酸铵钙、六大类菌剂产品。
三是重塑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家园一体化。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原本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被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逻辑打破。要实现农村垃圾问题的有效解决,就需要重塑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家园一体化关系。这不但需要现代社会重塑“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植入“生态中心”的现代环境思维,也需要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和国家环境治理过程中,构建乡村社会与自然资源之间的流通均衡机制,实现农村垃圾在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循环转化。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大量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涌入乡村社会,使得农村垃圾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而且,伴随着城市文明、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农村社会的渗透,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很多物品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农村垃圾逐渐成为村民生活的困扰和自然世界的负担。化肥农药等生产生活资料,既得到国家社会的推广、科学的验证与农民的迎合,也带来了难以弥合的环境问题。王晓毅[18]在谈论农村环境持续恶化时曾提到,在农村几乎是没有垃圾问题的,但随着工业产品进入乡村,每个村庄开始面临垃圾的严重威胁。譬如塑料袋、玻璃瓶等工业产品在方便生活和逐渐代替传统生活用品的同时,却难以在自然中消解,而自从化肥代替粪便后,粪便便从珍贵的肥料转换为肮脏的废弃物。不但原有的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不能被合理利用而丢弃,而且塑料袋、玻璃瓶等工业产品也构成农村新型垃圾。
在烟囱施工中,砌筑是主要的工序。在砌筑中需要先搭设一个操作平台,供工人操作、堆料等。而且在烟囱升高后,需要操作平台不断地跟随上升。为此,在烟囱筒壁内侧每隔1.2 m留脚手眼,用4根Φ 48 mm钢管伸入脚手眼作为平台支撑横杆,在横杆上满铺5 cm脚手板作为操作平台。要求杆件、脚手板安装可靠牢固,不用时方便拆卸。
五是推动城乡环境统筹治理制度的实践落地。这既需要城乡统筹的环境治理理念和城乡垃圾一体化治理的制度设置,也需要在垃圾治理机制、垃圾处理方式以及垃圾处理资金投入等方面实现城乡互通有无。如城乡环卫一体化需要把农村垃圾纳入城市环卫系统,实现农村垃圾上移与就地化处理的有机衔接。
注释:
①参见黄振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等相关文献。
②笔者于2017年1月和2018年1月在W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对文中所涉及的地名与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③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和政治运动给中国农村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生态灾难,一直是环境社会学主流观点(参见易明所著《一江黑水》等相关文献)。但是,在宏大叙事和国家政治之下,集体化时期农民的日常生活却因物质缺乏而与国家倡导的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的道德要求达成合意,带来了农业生产生活废弃物循环化处理的环境友好行为。
④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调查数据。
(2)通过分析研究判断,鞍钢前峪尾矿库是存在液化可能的。液化最可能发生在地下水位埋深3 m以内区段,地震烈度大于7度时。主要区域集中在中心区偏南区段,面积约0.3 km2。
[参考文献]
[1]王金霞.中国农村生活污染与农业生产污染:现状与治理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Han Zhiyong,et al.Characteristicsand Management of Domestic Waste in the Rural Area of Southwest China.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2015,(1).
[3]赵晶薇.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5).
[4]Sobolewska,A.Factors Determi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Garbage Tax”in Rural Areas.Village and Agriculture,2008,(1).
[5]张强.我国中部某市农村垃圾现状调查及处理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
[6]Bel G,Mur M.Intermunicipal Cooperation,Privatiza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Costs:Evidence from Rural Munici-palities.Waste Management,2009,(10).
[7]聂二旗.中国西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对策分析[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7,(10).
[8]Bernardes C.,Risso Günther W M.Generation of Domestic Solid Saste in Rural Areas:Case Study of Remote Communi-tie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Human Ecology,2014,(4).
[9]李全鹏.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10]Lili Lai.Everyday Hygiene in Rural Henan.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2014,(3).
[11]陈阿江,林蓉.农业循环的断裂及重建策略[J].学习与探索,2018,(7).
[12]蒋培.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农民垃圾处置行为的演变及其环境后果[J].鄱阳湖学刊,2018,(5).
[13]吴金芳.从迎垃圾下乡到拒垃圾下乡:对垃圾问题的历史与社会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
[14]王晓毅.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要发挥两个积极性[N].北京青年报,2018-01-21.
[15]王婧.环境视角下的“传统小农”和“新中农”现象——基于南方稻作区黔、皖若干农户的微观行为考察[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16]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挪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在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8]王晓毅.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J].学海,2010,(2).
[19]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0]孙旭友.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21]杜春林,黄涛珍.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J].行政论坛,2019,(4).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Waste in the Changes of State-Peasant Relationship:Practice Transformation an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Sun Xuyou Chen Baosheng
Rural garbage problem gen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garbage components and garbage disposal methods,and the solution of rural garbage problem is restrict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peasants.The field survey based on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waste treatment methods in W Village of Shandong Province shows thatthe“consensus”of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farmers and the advocacy of national morality,making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wastes flow evenly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The moder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the peasants and the state’s moral constraints are withdrawn from the peasants’ personal lives,causing the villagers to discard garbag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Garbage village.The state’s involvement in rural waste control and urban-rural sanit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s has suspended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waste disposal,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ncomplete management of rural garbage and so on.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garbage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desirabl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asants on the basis of cutting off the problem of rural garbage,and construct a framework of garbage disposal based on“Five basic points”.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9-0219-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东部地区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机制创新研究”(17YJC840032)、山东女子学院高水平科研项目培育基金资助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垃圾围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2018GSPGJ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基于资源共享的图书馆大数据平台建设研究”(18CTQJ06)
孙旭友,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济南 250300)
陈宝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002)
【责任编辑:陈保林】
标签:垃圾围村论文; 国家-农民关系论文; 城乡一体化论文; 合意治理论文;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