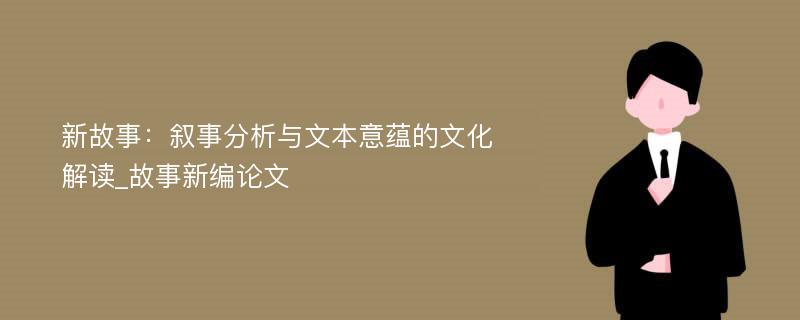
《故事新编》:文本的叙事分析与寓意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新编论文,文本论文,故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里,我试图通过对作品的细致解读,以期对《故事新编》的叙事艺术和文本结构的复杂性、独创性有个比较深入、具体的把握,这是一种微观研究的方式(注:我在《〈故事新编〉的空间形式》(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2)和《〈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鲁迅研究月刊》2000.1)两篇拙文中,对《故事新编》的文本叙事特征做过一些分析,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都未能全面展开。本文的写作就集中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方法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发。在小说的叙事传统上,中西方小说在深层的叙事模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有着各自的逻辑起点,操作程序和理论模式(注:参阅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时期以来,虽然西方叙事理论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当代小说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就如“不见”往往隐藏在“洞见”之旁一样,这种来自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视野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的发现。所以,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将尽可能对自己使用的一些来自西方叙事学的概念,诸如“反讽”、“结构”等作谨慎的分析。另一方面,我更倾向于运用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中的所常见的术语,如“纹理”、“曲笔”、“隐笔”等(注:参阅蒲安迪《中国的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我以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故事新编》的叙事艺术、文本结构有个更契合于它自身美学传统与文化语境的解读。
在叙事分析基础上,我将切入对《故事新编》寓意问题的解读。寓意是指文本中深于表面结构的“某种东西”,并且是与小说的叙述结构相契合的,即它通过种种特殊的艺术技巧深深地嵌入小说的叙述之中。我以为,在《故事新编》文本中,隐含着比我们一般性解读所把握到的讽刺寓意,更深广、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我们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一个重要文本。
1
应当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自觉地发展小说叙述艺术的第一人,他能极具才华地把他的独创性的想法表现出来,能极巧妙地把他的思想或经验转为创造性想象(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三联书店1991年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许多现代性技巧,在他的《呐喊》和《彷徨》文本中都获得了多样化、独创性的试验。我以为,《故事新编》的叙事艺术是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技巧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是他继《呐喊》、《彷徨》之后,独创才能的又一次体现。
在《故事新编》文本中,这种独创性才能首先是体现在小说中精妙的反讽艺术。“反讽”,简单的说,就是“表里不一”。它接近于中国小说评点传统中的“曲笔”、“隐笔”的内涵。反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前/后,表面/深层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这些差异,把作者暗含着的一种与文本表层含义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评价曲折地传达出来,这对读者的理解力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注:参阅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比如,我们来看《采薇》中那一段描写伯夷、叔齐逃出养老堂,路上遇到“小穷奇”抢劫的情景:
伯夷叔齐立即擎起了两只手;一个拿木棍的就来解开他的皮袍,棉袄,小衫,细细搜检了一遍。
“两个穷光蛋,真的什么也没有!”他满脸显出失望的颜色,转过头去,对小穷奇说。
小穷奇看出了伯夷在发抖,便上前去,恭敬的拍拍他肩膀,说道:
“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儿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
这段描写真是妙趣横生,它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反讽艺术的卓绝之处:“穷奇”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之一。“小穷奇”是鲁迅由此而戏拟得来,这里,作者只是作了一个微小的改动,即增加了一个形容词“小”。这一微小的改动却带出了一种全新的意味:“小穷奇”自称是“华山大王”,“小”与“大”构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这样,就微妙含蓄地使得“小穷奇”这一强盗形象小丑化。“小穷奇”在拦路抢劫伯夷、叔齐时,标榜自己是“文明人”,这样就把反讽的意味更推进了一层,使人们不禁想起在人类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的罪恶是借神圣的旗帜、口号而进行的,其残酷的程度不仅仅是剥夺一个人的财富,而常常是把成千上万的人们,送上了断头台、绞刑架和炮火口。在这里,我想起了加缪对法国大革命的一段精彩的评论:“法国大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会导致无限镇压的原则。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何尝不是这种“小穷奇”式的。也许,这种意味深长的反讽,正是一个天才艺术家的独创之处,他往往能在一个习见、简单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描写中,蕴涵着最丰富、最深刻的寓意。如果我们对这段描写进一步地加以细读与品味,那么,就会发现,这里的反讽意味不仅是指向“小穷奇”,同时,也指向伯夷与叔奇。伯夷,叔齐之所以要逃离养老堂,是因为他们恪守先王之规矩,反对周武王“不仁不孝,以暴易暴”的征伐行动。面对刀斧,他们敢于“扣马而谏”,然而,当被“小穷奇”拦住时,他们又是如此的懦弱、卑怯。作者有意让他们置身于嘲讽、屈辱的处境中,从而对他们矛盾的精神世界做了一次不动声色的反讽:他们在“小穷奇”的淫威之下,受尽屈辱、嘲讽而毫无一点反抗之心,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之神情。殊不知,古训早有“士可杀而不可辱”。伯夷、叔齐一方面迂腐地恪守已成陈迹的先王之规矩。另一方面,当自己的尊严被侵犯、侮辱时,却又毫无勇气加以捍卫,这就使读者不禁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投以质疑的眼光:事实上,此时的伯夷、叔齐只剩下逃命之绝路,遑论捍卫自己的尊严。然而,当一个人连捍卫自己的勇气和力量都没有时,就可想而知,他那坚守先王规矩的道路能走多远!鲁迅就是这样通过精妙的反讽艺术,把这一问题的思考,一层又一层地推进到读者的面前。初读起来,也许只是觉得充满谐趣。然而,当你细细品味时,你就会产生一种会心一笑的审美愉悦。我想,如此曲曲折折、层出不迭的反讽艺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只有在鲁迅的笔下能发挥得如此的淋漓尽致。在鲁迅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如张天翼、吴组缃、沙汀等人,都创作出不少优秀的讽刺小说,但是,读起来,总感到过于明晰、尖锐了一些,而缺少鲁迅所欣赏的那种“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风度。
像《采薇》这样的对反讽艺术的精妙运用,在《故事新编》中比比皆是。但是,它们在文本中,还仅仅是局部的。在《故事新编》中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通篇性的反讽运用,即作者不是偶尔运用讽语、反话,而是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篇章结构,从而使得反讽意味贯穿全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起死》,这篇小说的独创之处,不仅在于它采用了戏剧的结构方式,而且还隐含着多层次的反讽意味:首先是“汉子”与“庄子”之间构成一种反讽关系,“汉子”虽然愚钝无知,然而,却实实在在地使得“庄子”下不了台;其次是前后“庄子”之间又构成一种反讽关系,当“庄子”用马鞭敲着髑髅时,他的语气、神情是那么的得意,而到了后面,当“汉子”复活过来,问他要衣服穿时,“庄子”又是那么的狼狈、无能;最后,整个文本又构成对“庄子哲学”的“齐物论”、“超生死”思想的一个绝妙反讽。在文本中,这三个反讽层次是交融在一起,同时又是互为深化的。当然,这也是一般研究者都能明显读出的反讽意味。我以为,在《起死》这个文本中,还存在着一层更隐秘的反讽意味,它是指向鲁迅自身的。我们知道,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有一段大家都熟识的自述: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实际上,呐喊/彷徨,希望/绝望,确信/质疑的矛盾,一直贯穿着鲁迅一生的精神历程。即使在他成为左翼阵营的精神领袖之后,这些矛盾依然没有消失的。所以,我以为,写在其晚年的《起死》,是鲁迅对其一生所从事的思想启蒙的精神追求一种隐秘的自我反讽:对于复活的“汉子”来说,他的迫切需要只是衣服和食物,他根本无法也无心理解认同“庄子”所关注的那些思想。然而,那些“生人们”,即使唤醒他们,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鲁迅式的怀疑。我以为,《起死》就是对这一怀疑的某种曲折的回答:鲁迅正在困惑、怀疑自己或许会像文本中的“庄子”一样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但是,不同的是,清醒的鲁迅迫切需要能够通过这种自我反讽的艺术形式使自己超脱出来。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先生曾说过的那样:“对于鲁迅这样一位充满道德义愤和教诲激情的内心自觉的作家来说,反讽和超然是心理和艺术的必要。”(注:《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我以为,通过对《起死》的反讽艺术的分析,是我们进入鲁迅晚年心理和精神世界的一个隐秘的地道。也许,这一“地道”并非鲁迅有意指示的,但是,我们确实能够通过对他所创造的文本与《庄子》文本的细续,得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伟大的艺术创造中,总会交错、隐含众多的“线索”和“陷阱”,对于这样的作品,如果仅就其独立性来分析,可能只会呈现出单面的意义结构,如果把它放在这个作家所创造的其他文本系统中,让它们在一种互相映照,互相指涉的背景下来加以阐释,可能对其中的某些隐秘的意义结构,就会有更丰富的把握。而对鲁迅这样深刻、博大的艺术世界来说,更需要我们以一种复杂、丰富的方式去把握它。
在《故事新编》中,反讽的叙事艺术除了使文本的意义结构变得更精致、复杂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对叙事角度的操纵。比如,《出关》中描写“老子”在函谷关遭遇的那个情景,作者就是调动多重的视角来描写“老子”:先是从“关尹喜”的叙事角度来描写“老子”——此时的“老子”是位馆长,有学问的先生;接着从“帐房”和“书记”的叙事角度来描写“老子”——此时的“老子”又显得十分的迂腐可笑,正如“书记先生”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哼,还是这些老套。真教人听得头痛,讨厌……”;最后,作者的叙事角度又回到了“关尹喜”上来,经过一番“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玄乎含糊的折腾之后,“关尹喜”对“老子”已失去了热情,在此时的“关尹喜”看来,“老子”西出函谷关最终还会乖乖地回来的。作者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叙事角度的操纵,仿佛在“老子”的周围立起了多面的“哈哈镜”,“老子”的形象就在这不断变幻,而又相互映照的镜像世界中被变形、幻化,从而获得漫画化的艺术效果。又如《奔月》中的“逢蒙”这一形象,作者先是从“老太太”的叙事角度来描写的:“逢蒙”是一个英雄,而“羿”反而被误认为骗子。经过一系列的戏剧性情节的设置之后,作者把叙事角度调整到“羿”这方面来,此时的“逢蒙”才现出那种专会弄剪径的、无耻的小人的面目。正是借助于这多重叙事角度的操纵,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种“初是终非”或“终是初非”的印象,也使得整个文本的叙述角度富有变化。
反讽的叙事艺术还能有效地调整作者、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时,作者通过反讽叙事向读者暗示一种观点或立场,引导读者去把握字面之下的含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补天》中作者有意设置了一个站在“女娲”两腿之间的“小人物”。作者把“小人物”进行这样的空间设置,就是暗示了小人物淫荡、放纵的本性,从而使读者能够揭穿其道貌岸然的话语背后的虚伪性。有时,作者并不直接进行暗示,而是需要读者借助于叙事者,通过把握、体会文本的语言来捕捉其所隐含的意义。比如《理水》中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描写,作者就是通过“乡下人”这一叙事者,暗示给读者一种观点:“学者”们虽然满腹经纶,但他们所做的是一种繁琐、无聊的考证,对于像“禹”是不是一条虫的问题,他们却争得面红耳赤。而在乡下来看来,这种争论是可能理解的,他根据事实说道:“人里面,是有叫做阿禹的。”这句直截了当的话,即是对学者们所争论的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暗示读者:真理或真实的判断可能就是直接来源于“乡下人”这样的朴素经验,而那种纸上空谈的考据是无补于智慧的发现。
2
《故事新编》中的每一篇作品不仅仅是由一个以上的神话、传说文本叠合、缀联起来的,而且,还介入、融合了一些现实性文本。所以,整个文本的结构形态表面上看起来缺乏西方小说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但是,奇怪的是,只要我们立足于作品的细读,却又会感受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整体感”、“统一性”。阅读的困惑,促使我去探究这种“整体感”源自何处。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中的每一篇作品在结构上都存在着一种对称性。从构思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构的对称性,常常表现为历史与现实,想象与事实均衡地组合在一起。比如,在《理水》中,小说开篇对文化山上一群“学者”的描写,显然是源于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观察;《铸剑》中对“三头争斗”的描写,显然是一种想象性的创造。从人物创造的角度来看,这种对称性则表现为英雄/小人物之间的对比。比如,《补天》中“女娲”与站在两腿之间的“小人物”,《奔月》中的“羿”与“逢蒙”;有时,这种对称性甚至成为贯穿整个作品的基本理念。比如,《补天》中的创造/毁坏的主题,《铸剑》中屈辱/反抗的主题,《非攻》中的正义/非正义的主题,《理水》中的实干/虚夸的主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称性是我们为了分析的方便,而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的深层性的架构,事实上,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它们往往是错综在一起,表现为交融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联系鲁迅的其他小说创作,那么就会发现,在《呐喊》、《彷徨》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对称性结构,最典型的是“独异个人”和“庸众”这两种对称性的形象。可以说,这种对称性是鲁迅小说叙事的原型形态。如果更进一层来看,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性是源于中国传统的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型意义,才保证了《故事新编》中的小说的内在结构的整体感和统一性。也许,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从中可以发见中西方小说对叙事结构的不同理解。比如,西方小说的叙事理论认为,叙事是对人类经验的“模仿”,所以,一篇小说的叙事必须要遵循某种可辨识的时间性“外形”或“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小说文本产生首尾一贯的印象(即具有“起”、“中”、“结”三个段落结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史诗时,就认为在史诗的开头和结尾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上和形式上的规定性。而这种所谓的“规定性”,就是说,一段情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从开始提出问题到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给人以一种“有道理”的感觉,从而达到对应和平衡,所以说,它的结构意识是侧重于“外形”的整体感。(注:参阅蒲安迪《中国的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然而,中国小说的叙事理论强调的是叙事的心理学倾向和自然主义倾向。比如,古代文论中的所谓意在笔前、以心运文等说法,就是承认对心中意象的体验觉悟,是对一篇作品的阅读与理解先入的存在和内在的驱动力。中国叙事的这种心理学倾向,是与西方小说传统中的“模拟”倾向是互为逆反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叙事理论又宣称“文”作为具有审美意味的图形,它“普遍存在于自然之中,诗人们的创造只是参与已经存在的自然。”(注:欧文《传统的中国诗和诗学、世界的征兆》,载《学术集林》第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所以,中国叙事的结构意识是侧重于要求读者对小说文本内在意味的统一性的把握,并且,认为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是源于《易经》中所体现的阴阳二元对称的原型。因此,如果我们单纯地站在西方叙事的结构意识的角度来解读《故事新编》的结构,可能就会感到有某种的松散,那就更谈不上把握住其内在的整体感。
然而,我以为,更内在地体现《故事新编》文本结构的独特性,并非仅仅是文本中那种对称性的叙事架构所拥有的艺术统一性,而是那些存在于文本之中的更细致的“纹理”。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家所特别关注的小说结构的“针线”问题,它处理的是细部间的肌理,而无涉于事关全局的叙事构造(注:参阅蒲安迪《中国的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我以为,《故事新编》文本结构上的“细针密线”之处,大致有如下三方面:(一)意象结构法,(二)形象迭用法,(三)闲笔与空白法。所谓的“意象结构法”,就是在一个大的结构段落中,通过一个中心意象把该段落所要表现的种种涵义结合成一个富有诗意的整体。比如,《铸剑》中,前半部分的中心意象是“剑”,作者通过“剑”这一中心意象,引出眉间尺复仇的原因。同时,“剑”这一意象又把小说的主题象征化,“剑”在这里成为一种力量、信念的象征。小说的后半部分的中心意象是“头”,作者通过“头”把复仇的过程整合起来,与此同时,“头”的一系列上下浮游,与小说中人物的种种表情交融在一起,形成一幅瑰丽的画面。“剑”和“头”作为整个小说文本的两个中心的意象结构,使得小说充满着复仇/牺牲,信念/正义,悲剧/审美的内涵。《奔月》的中心意象是“后羿射箭”,作者通过这一中心意象写出英雄的困境:先写“后羿”的箭法太巧妙了,竟射得满地精光,现在只能射乌鸦了。接着,写“后羿”与“逢蒙”的对射,最后,描写“后羿”射月的情景。“射箭”这一意象既是对英雄末路的反讽,又是象征着一种英雄的精神力量。《故事新编》中有些文本,正是通过这种的意象结构方式,体现出鲁迅在小说结构上的精心构思。
通过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故事新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有许多形象、细节是反复出现的。我以为,在小说叙事的结构意义上,它们并非可有可无的,而是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它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形象密度,而且,还能让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叙事“回路”,获得巧妙的照应。比如,《补天》中反复出现的“小人物”形象,这绝不是由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而是一种另有深意的构思,他试图通过这一反复出现的“小人物”,构造一个卑微、委琐的形象世界来反衬“女娲”的创造性劳动的伟大和艰辛,从而,使小说的主题获得一种歌颂/批判的双重义蕴。又如,《采薇》中一直出现“薇”的形象。“薇”的形象在小说中总是与伯夷、叔齐的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一形象,其义蕴是点明,伯夷、叔齐的精神世界从根本上还是困扰于欲望之中。当“阿金姐”告诉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时,“薇”却又成为他们道德堕落的证据。然而,当道德的负担和自责,最后剥夺了满足饥饿的欲望时,他们生存的意志也就彻底地崩溃了。作者就是借助于“薇”这一形象的迭用,映照出其内在丰富的内涵,从而把小说的主题推进到反讽的层面,这就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又如,在《出关》中,“孔子见老子”的场面重复了两遍,除了一两处的对话有细微的差别外,看起来,这两个场面没有多大的差异。但是,细读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人物在说同一句话时,其背后的思想、感情、信念、所指,前后都是有所变化的。“老子”在第一次与“孔子”会面时,他在思想与精神上,显然都处于优势。而到第二次会面时就转为劣势,这时虽然说的话都近乎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两人所处的形势已经向相反方向转化,并在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作者的创造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这种迭用的结构中,写出同中有异的微妙区别。因此,这种形象迭用的结构特色,使得小说能够在一个文本之中成功地作到各种相同、相异因素的自由穿梭、操纵,从而使得作品的艺术结构在细针密线之中纳入了丰富的意味。这就如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但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注:《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如果说,文本的结构是一片清澈的河床,那么,这些迭用的形象就是水中铺陈的鹅卵石,是融在水中的云彩的映影,是河面上荡漾着的一道阳光,一切都自然浑成,而又相映成趣;如果说,这文本的结构是一片素净的背景,那么,这些迭用的形象则是变幻的、美丽的、花团锦簇般的点缀,如断素、零纨、珠花、剑气、花香与鸟语,一切都细密严谨,而又杂而不越。(注:参阅闻一多《庄子》。)
在《故事新编》文本的结构“纹理”中,我们经常能读到一些意味深长的“闲笔”。这些闲笔,有的是出现在“事”与“事”的交叠处。比如,《铸剑》中写眉间尺去刺杀国王时,忽然跌倒了,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接着,作者写“干瘪脸”少年扭住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他压坏了自己贵重的丹田。这看似闲来之笔,却是颇含意味的:在情节结构上,它引出了“形象谱系的延伸。“干瘪脸”少年显然是典型地代表着那一群麻木、自私、无聊的“庸人”,从而对比出“眉间尺”反抗的孤独。有的是出现在“事”与“事”的空隙之外,比如,《奔月》中“逢蒙”暗杀“羿”,就是出现在“羿”射死老太太的小鸡和正在策马回家途中这两件事之间,作者插入这一与情节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描写,一方面,具有中断和延缓叙述进展的结构功能;另一方面,又使得“羿”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闲笔有时又放在“无事之事”上,这里所谓的“无事之事”,就是指那些在文本中,并非直接推动情节发展的单纯的静态的描写。如《理水》中“水利局”的同事筵宴的描写,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闲笔,从与情节发展的关系来看,这里的“闲笔”具有很深刻的反讽意味。还有一种类型的“闲笔”,是放在小说的结尾,比如,《补天》的结尾关于秦始皇、汉武帝寻仙的故事,虽然,这段故事情节,与前面的描写有关连,但是,它的功能并不在于结构上的照应,而是,把小说的意义引向新的局面,即讽刺统治阶层追求“永恒”境界的可笑、荒谬。从这种在文本结构之中嵌入“闲笔”的现象,即:“事”常常被“非事”、“无事”所打断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某些特点来,我们知道,叙事文学构成的基本单位都是“事”或“事件”,如果没有一个个这样的基本“事件”单位,那么整个叙事就会变成一条既打不断,也无法进行分析的“经验流”。但是,中西小说叙事的区别就在于,在西方叙事理论中,“事件”是一种实体,人们通过观察它在时间之流中的运动,可以认识到人生的存在。而中国的叙事传统则相反,“事”或“事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而是可以划分成一对如静与动、体与用、事与无事这样彼此互涵的观念(注:欧文《传统的中国诗和诗学、世界的征兆》,载《学术集林》第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这就使得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处处能读到一些意味深长的“闲笔”,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却能潜在地推动了情节的互相转化和深化小说的结构意蕴。
3
《故事新编》中那诙谐风趣的艺术风度,以及集机智、幽默,滑稽于一身的喜剧形式,使得文本具有了浓郁的民间叙事的审美特征。这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一,《故事新编》中有着不少喜剧性、小丑化的人物形象。在过去的研究,很少有文章注意到在文本中这些同属于喜剧性人物系列的艺术形象之间,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异。我以为,正是这种差异性,相当曲折地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的智慧特征。《故事新编》中的喜剧性人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纯丑化的人物。如《补天》中的“小人物”、“小东西”;《奔月》中的逢蒙;《铸剑》中的“干瘪脸少年”、“大臣”、“国王”;《理水》中的文化山上的“学者”等。这些人物在文本中构成了讽刺、批判的对象。然而,更值得分析的是另一类喜剧人物,即那些代表着朴素真理的喜剧性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民间诙谐文化集机智、幽默、滑稽于一身的人物创造方式。比如《理水》中的“乡下人”形象,文本中是这样描写的: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从这段话来看,这个乡下愚人所使用的语言方式相当的生活化,比如杂入了民间谚语:“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并且这种杂入是随手拈来的,显得十分的生动自然。同时,在这段话中,还出现了中国民间猜谜方法中最常用的拆字法,“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尽管这个“乡下人”的推导是简单的,然而,他实实在在地使得自以为有学问的“鸟头先生”下不了台。在“乡下人”的身上充分体现了鲁迅对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智慧的一种深度把握,即在他们粗糙、简单化、甚至近乎滑稽的语言逻辑结构中,发现内在的朴素真理和那种愚钝之中暗藏狡黠,滑稽中寄寓机智的智慧。
民间叙事的特征在《故事新编》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在于大量介入粗鄙化、世俗化的叙事形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个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版。)所以,中国的民间叙事又常常是非常直率的,它坦然地面对自身的欲望,他们对世俗生活的场景具有感性化的把握。如果一旦把这些粗鄙、世俗的生活场景,大量地介入文本之中,它不仅承担着情节叙事的功能,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对人的欲望与粗俗生活的展现,具有象征叙事的功能。比如,《补天》中有这样的一段场景叙事:
伊将手一缩,拉近山来仔细的看,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他们也慢慢的陆续抬起头来了,女娲圆睁了眼睛,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杨叶。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是运用类似电影中俯拍的方式,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一幅粗俗、狼藉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之中,流淌的是一种纯粹的欲望之流。接着作者的视角渐渐地推进,开始了特写镜头式的描写,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形象怪诞的图景:用什么包了身子,雪白的毛毛。这些都十分独特地体现了民间叙事把握、描写人和其所存在世界的角度和方式。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奔月》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比如,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羿看了一眼,就低了头,叹一口气;只见女辛搬进夜饭来,放在中间的案上,左边是五大碗白面;右边两大碗,一碗汤;中央是一大碗乌鸦肉做的炸酱。
这里对食物的有滋有味的叙事,十分接近于民间艺人在讲述一个生活场景,那种细致中带有夸张的口吻,那种眼到心动的体味,那种对欲望的感性的、下意识的关注,都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叙述体文学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粗鄙化、世俗化的生活场景,在民间叙事中是一种欲望性的叙事,充满着感性的心理色彩。而当这一切因素被作者有意的、创造性地介入新的文本叙事时,它的审美价值就会产生一种增值化的过程:一方面,使得文本的叙事接近于生活的原生态,从而获得一种艺术真实感;另一方面,也使文本的叙事格调多样化。对于文本的叙事来说,叙事人和叙事对象的自身感知、把握事物的特点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就在文本中与作者的叙事立场,构成一个张力结构,共同深化和拓展了文本的审美内涵。
4
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我们对小说叙事表层之下“内在内容”,能有一个更透彻的理解,这就是关于如何在小说纷繁复杂的叙事形式背后,把握其内在“寓意”的问题。中国人对小说寓意的解读常常是,或者满足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嗜谈怪异的趣味;或者习惯于把小说当作一面反映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的镜子;或者执迷于索隐考据;或者直接把小说等同于非斥人即自况。这种种的阅读的心理惯性在《故事新编》研究史上依然存在。然而,我以为,在《故事新编》文本中还隐含着一种深层寓意,那就是,《故事新编》的创作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再阅读,再创作,再想象的过程,也是鲁迅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资源的一次努力。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较多地谈论鲁迅与魏晋文人,特别是嵇康的精神契合,而较少注意到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内在联系。我以为,先秦文化同样深深地锲进鲁迅的心灵,而且,给予他的不仅是一种激情,更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理性;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对话。著名诗人T·S艾略特在评论但丁时,曾说:“莎士比亚和但丁之间的区别在于,但丁有一套连贯的思想体系做为他的后盾,但这不过是他个人的幸运而已,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偶然的事件,碰巧在但丁的时代,思想是井井有条的,强有力的,而且是美丽的,而且还集中在一位最伟大的天才身上,但丁的诗歌从这一事实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即它的后盾是圣·托马斯的思想,而托马斯是和但丁同样是伟大和可爱的人。”(注: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对于生存在20世纪的鲁迅来说,远没有这种幸运:他背后的那一套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之后,早已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因此,鲁迅面临着更深远、更艰难的历史命运:一方面,他必须从自己独立的思考中,对传统文化做出理性的“扬弃”;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为自己、为生存在那一时代人们的思考,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立场,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资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先秦诸子中,对于墨家,历代以来的评论是相当矛盾的。比如,在《庄子·天下篇》中就说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但是“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由于门户之见则不免伐异而不存同,把墨子斥为“欺惑愚众”。《汉书·艺文志》则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开此后二千年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始,墨家在传统文化结构中一直被斥为异端,而被排斥在边缘性地位。但是,到了近代,墨学又成为一门显学。据说,梁启超所藏之书,在先秦诸子中,收得最多的是墨子,共九种。梁氏对墨子一向很推崇,在《子墨子学说》中,还明确说道:“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唯无学别墨而真墨”。墨子那种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当然是他在近代重新获得肯定的最根本原因。从鲁迅在1918年所写的《〈墨经正文〉重阅后记》中也可以见出他对墨学的重视。我以为,要更深入的解读《非攻》,必须把它与鲁迅写于同一日期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联系起来,实际上,在《非攻》与《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契合。鲁迅在杂文中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非攻》中所塑造的墨子形象,其意义就是象征着中国民族的脊梁。鲁迅得知过去的史籍“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因此主张“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以便“褫其华,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所以,我以为,在《非攻》中,正隐含着鲁迅一种重建和认同中国民族精神的明确的价值向往。
对《铸剑》的解读,人们常常是把它与《野草》中《复仇》的主题连结起来,这当然是一种读法。我以为,要更深入地理解《铸剑》的精神意义,还必须把它与《史记·游侠列传》相对照来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曾说:“救人于卮,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然而,更可注意的是《游侠列传》前面的那段小序,司马迁先是对游侠的精神内涵做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卮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接着,司马迁指出虽然游侠的地位、权力不如当世之权贵,然而,“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最后,司马迁说道,他之所以要写《游侠列传》,一方面,是“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另一方面,是为那些“俾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之士树立一种精神典范。我以为,司马迁所说的游侠精神,可以说,就是一种“诚”与“爱”:即对信义、承诺的诚实、真诚,对孤弱、贫困者的爱护。《铸剑》中的“黑色人”可以说就是这种游侠精神的化身。“黑色人”与《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朱家、郭解是同属于一个精神谱系。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他认为中国民族缺少的是“诚”和“爱”,造成这种弱点的原因,则是历史上的两次被异族入侵。我以为,鲁迅创作《铸剑》,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继《史记》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侠精神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再创造、再阐释,这背后隐含着一颗博大而痛苦的灵魂:他是如此清醒地看到我们民族在精神上缺少了什么,正是这种清醒的理性如大毒蛇,缠住了他一生的灵魂,使他痛苦、绝望;然而他又是如此执著于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作大事业,这种执著于,使他时时刻刻都在做着“绝望的抗战”。我以为,《铸剑》中就浸润着鲁迅这种冷峻而痛苦的激情。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解放,是贯穿鲁迅一生启蒙思想追求的基本主题之一。在古代中国,女性一直是被排斥于历史视野之外的,她们只有作为男性的附庸,才能被允许进入历史,并且也只能以一种屈辱、软弱的形象做为一种无表述的客体,出现在历史之中。我以为,在《补天》中,鲁迅试图发掘和重建的正是这种在传统文化结构中一直被压抑着的力量。在冰心、丁玲等女作家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自我位置和价值的追求,是何等的艰难!冰心讴歌伟大无私的母爱,把它视为女性价值的最高体现,殊不知,“母亲”恰恰是传统社会中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给女子的基本角色,它并不能构成女性本位价值的源泉。事实上,对母爱的讴歌只是在男权中心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女性的价值体认方式之一。在根本上,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妥协。丁玲笔下的莎菲则是另一种极端,她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带着一种施虐式的快感来折磨男性,玩弄他们的感情和肉体,以此获得一种虚假的主体意识。无论是冰心,还是丁玲的笔下女性,其最后的结局都是导向一种女性自身价值的消失(注:参阅倪伟先生的硕士论文(打印稿),华东师大中文系图书资料室。)。然而,在《补天》中不仅有对女性躯体的礼赞,而且,通过对女娲创造性劳动的描写,以确定女性的主体价值和力量。有意思的是,在《补天》中,鲁迅所讽刺的所有“小人物”都是男性,这也可以视为鲁迅对传统男权中心文化的一次绝妙嘲弄。我以为,对《补天》的解读,可以把鲁迅对母亲的敬爱和他散文中的另一组女性形象,如阿长,女吊等联系起来,鲁迅在他母亲的辛苦操劳和坚忍的意志中,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力量,他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就曾无限深情地说道:阿长“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他欣赏女吊的反抗性,我以为,在这些女性形象中,不仅寄寓着鲁迅对传统社会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化深刻批判,而且,体现了鲁迅对发掘、重建民族精神力量的一次严峻的思考。
标签:故事新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铸剑论文; 穷奇论文; 补天论文; 采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