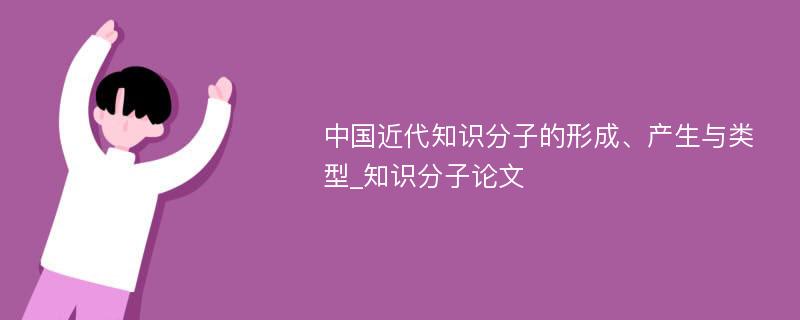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世代论文,中国论文,群体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3-0032-10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成长与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它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先驱者、引领者与催生者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这一群体的形成时间、世代交替与构成类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或称新型知识分子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流的意见是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段,尤其是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李泽厚、许纪霖两先生均称中国迄今已有六代知识分子,并将他们认为形成于这一时段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分别称为“辛亥一代”①与“晚清一代”②。姜义华先生也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③还有有多位学者认同或者说倾向于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观点④,他们认为“公车上书”标志着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形成,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到辛亥革命前夕发展成为一支可观的社会力量,对当时的社会转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有学者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转型的角度提出,“如果说晚清洋务派是最后一代中国‘士大夫’,那么戊戌的改良派人士算得上过渡期的知识分子了”⑤。“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⑥。
但也有学者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时间点前推到甲午战争以前乃至鸦片战争,或者后延至五四时期。主张前推的如:有的提出“19世纪40至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一代,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文化精英为代表”⑦,这一时段“为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期”⑧;有的提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是一部分开明士大夫被迫走出中世纪,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开始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的时期,也是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诞生的时期”⑨;有的提出“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⑩等。主张延后的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演化而来,他们受孕于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1840年前后)”,“诞生于天翻地覆的现代中国(1915年前后)”(11);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新式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大批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才形成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学者们围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时间的不同认知,既与他们对史实、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读有关,也反映出他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概念是有差异的。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知识分子”参与其间的历史过程也是杂然纷呈、丰富多彩的,史家们心目中与笔底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叙事”自然就有不同的面貌。
还是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说起。从广义上讲,古代所称的“士”或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且以知识谋生的读书人。1928年,夏丏尊发表《知识阶级的运命》一文,指出:“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人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13)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不能仅有书本知识,还倡导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最重要的是,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批评仅有书本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称“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4)。与我们强调“知识”有些差别,西方突出的是“智力”、“理解力”,英语中与“知识分子”相对应的其中一个词是intellectual,该词作为构成现今“知识分子”词义的源头之一早在16世纪末就被当作名词使用,意即“理解力”、“智力”;17世纪中叶,它被用来指人,意为“理解力强的人”、“智者”(15)。爱德华·希尔斯(E.Shils)就从广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现代知识分子也就是不仅了解文化传统,且掌握现代知识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思考探索、解决实际问题、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又有人强调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有“现代知识”就能叫“现代知识分子”,认为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仅是知识阶层中习惯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精英。即从狭义上讲,现代知识分子仅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当中比较关注专业与职业之外的公共问题,有着独立的精神品格,有着强烈的公共关怀,对社会持有批判精神、代表着社会良知的知识群体,他们被贴上“公共知识分子”、“公意知识分子”、“左拉型知识分子”等标签。这种狭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和俄国。左拉于1894年为抗议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诬下狱而发表的《我抗议》被认为是标志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历史文献,“未来的政府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后来,人们给“现代知识分子”下了这样的定义:“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16)“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源头是俄语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最初是指19世纪60年代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西方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这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青年贵族的主要特点为关心国家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英语中与“知识分子”对应的另一单词Intelligentsia即由俄语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转化而来。对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强调成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重要特点。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声称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公众为对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此后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已被学院体制驯服并屈从于金钱、地位和权力。他呼吁知识分子应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此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7)从强调公共关怀这一角度,许纪霖给出了狭义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8)苏力则将其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19)。
既然知识分子的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别,我们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时间就要对概念的差异有所考虑。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分别考察广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与狭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形成时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大致脉络就可以分疏为以下两条线索: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初步掌握现代知识并开始以现代知识谋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严格意义上的、不仅掌握现代知识且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诞生于清末(1895-1911)的戊戌到辛亥期间,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辛亥一代”。
广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从虚骄蒙昧中走出,睁眼看世界,提倡实学,接触西学,在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具有现代气息的变化,开始了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换。到1861年,他们编写、撰著了诸如《四洲志》(林则徐)、《海国图志》(魏源)、《康輶纪行》(姚莹)等22部世界史地著作。农民阶级中也涌现了以洪仁玕为代表的接触了新观念、新知识的农民领袖。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早期也出现了并非由科举出身而具有全新教育背景的新式读书人,如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的容闳,教会学校也开始招收和培养学生。这一阶段的教会学校有布朗于1839年在澳门创立的马礼逊学堂,马礼逊于1818年创立于马六甲、后于1843年迁到香港的英华书院,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于1844年的宁波女塾等50所学校,招收学生约1000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于1843年创立了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墨海书馆,王韬、李善兰等供职于此。到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20)。总之,在近代早期,西方现代知识在华传播的渠道已经打通,从事现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平台开始搭建,接触了现代知识并以着手运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雏形开始显露。
洋务运动时期,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正式启动,广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也正式诞生,供职于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文教事业与其他洋务事业的洋务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洋务知识分子群体的来源大致为:其一是从旧式官僚、传统士大夫转换而来。其二是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学堂。教会学校由1860年的200所,增加到1875年的800所,学生达到两万人。其三是洋务派创办的新式洋务学堂。1862年建立了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随后,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相继成立。除了语言类学堂,技术学堂与军事学堂也先后成立,如1867年设立的马尾船政学堂(1866年在福州设立,1867年迁至马尾)、1869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79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建成的天津水师学堂等。到1894年,清政府共设立了26所洋务学堂。其四是来自海外留学。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1872—1875年间,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0名,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第一届严复等30名留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此后又于1882、1886、1897年派出第二届9名、第三届34名、第四届6人留欧学生。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前后派出的留学生达到了199名。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文化事业,如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到1890年发展到了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21)。洋务运动时期,不仅在创办企业与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中培养出了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科技型知识分子,出现了王韬(曾在墨海书馆协助翻译《圣经》并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沈毓桂(担任《广学报》主笔达20余年)任职于现代报刊与出版机构的传媒知识分子,出现了其他一些在通商口岸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出现了已着眼于工具批判尤其是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构想、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人文型知识分子,还通过新型教育使一部分人接受新型知识、从而培养了将在下一世代登场的现代知识分子,包括像严复那样具有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
狭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队伍成长壮大。通过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接受现代观念、现代知识,成为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来源。到1898年各地办的新式学堂至少有100所,到1909年国内各类学堂约有5.7万所,学生160万余,其中中学以上程度者约万余人;民国元年,学堂总数增加到8.7万多所,其中中学823所,高等学堂122所,学生总数近300万人。另有教会学堂学生约14万人(22)。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千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两万多人(23)。留学欧美者不足千人。按清末的情况,知识分子大体应在中等以上程度。有学者估计,“到清朝末年,我国已出现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人数已有15万乃至20万左右”(24)。
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朱执信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正式诞生,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精英群体。他们把传统士大夫“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入世情怀,转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高度关注国家富强的目标,关注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关注相关公众、公益利益之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豪情,秋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义气侠风,林觉民“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宽阔情怀,都既是士大夫气概的延续,又是现代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的体现。清末知识分子又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从呼唤“君主立宪”的体制内修补,到“走向共和”的颠覆性改造,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集中写照。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各省1300余名举人进行“公车上书”,反对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联名上书,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关切,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标志。知识分子还从改良走向革命,据统计在1905-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379名会员中,有354人是留学生和学生,占93%以上(25)。清末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对专制政治的工具批判与体制批判上,还体现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文化批判上,体现在对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解构上。康有为宣布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圣经成宪”的古代儒家经典为“伪经”,严复批评汉学与宋学“无用”“无实”、中国政教“少是而多非”(26),谭嗣同号召冲决“俗学之网罗”、“伦常之网罗”,革命派提出“道德革命”、“三纲革命”与“家庭革命”,都是文化批判精神的体现。他们还批判了封建政教对国人性格、民族心理的摧残,包括封建政教对士人人格的荼毒,国民性批判成为清末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重要内容。严复等人还对八股取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切断了传统士大夫与传统体制的联系,打破了旧士人“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促成了带依附性的士大夫到有独立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二
中国现代化运动从19世纪中叶启动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50余年的历程,在现代化历程中孕育与诞生的新社会阶层——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也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命运多舛的成长过程,出现了前后相承的多个世代。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划分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三代说”、“四代说”、“五代说”、“六代说”、“七代说”等不同说法。鲁迅是比较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表过《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其小说《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都是表现知识分子主题的。他也在中国最早从代际角度触及知识分子问题(27)。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谈到新的小说写作计划,一部“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即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冯雪峰一代。“这将反映中国近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国知识阶层的真实的历史。”(28)在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代际划分的各种观点中,影响较大的还是李泽厚、许纪霖等人提出的“六代说”。李泽厚先生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提到了中国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国革命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七代将是全新的历史时期)”(29)。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的表述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许纪霖也指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30)另有其他学者提到过“六代说”,但具体内涵上有些差别,如有学者提出可从现代化的角度将知识分子划为“六代”:19世纪40-60年代、19世纪60-90年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20世纪20-50年代、20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31)。
“三代说”、“四代说”等说法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持论者不像主张“六代说”的学者那样把考察的视角放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成长的整个历程,没有把下限延伸至改革开放时期,而是把考察的时间区间放在以往意义上的“近代(1840-1919)”,或放在20世纪上半期即1949年以前。如有的学者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是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诞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直至清王朝灭亡,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他们走向政治舞台、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壮大且进行历史反思和重新选择的时期(32)。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早期出现了互相继承的三代知识分子,即以梁启超为典型代表的、改良型的“饮冰者”,以鲁迅为典型代表的、感情炽热的“疑古者”和以罗家伦为典型代表的行动者(33)。还有的将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分为4个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时代,辛亥时代,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34)。还有学者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过程分为7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35)。
李泽厚先生提出“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那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他所思考的应该是广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关注“辛亥一代”前的“洋务一代”,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从洋务运动开启的,知识分子是时代的风向标,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中国也就诞生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洋务知识分子。他提到“第六代”即“红卫兵一代”时,同时预言了“第七代”,称“第七代将是全新的历史时期”。离那时时间又过去了近30年,不仅“第七代”即60后已展示了新生代的风采,实际上“第八代”即70后、80后如余杰、韩寒等也已登场亮相,作为知识分子的“新新生代”、“跨世纪一代”崭露头角、屡显峥嵘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相伴而生,在中国现代化1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八代知识分子,即洋务一代、清末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解放一代)、“文革”一代(“红卫兵”一代)、后“文革”一代与跨世纪一代。
在建国前登场的四代知识分子中,晚清时期的“洋务一代”、“清末一代”分别标志着广义上与狭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我们再简略地看一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统治年代的“五四一代”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年代的“后五四一代”。
提及“五四一代”,人们会想起教师辈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和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名声显赫的代表人物。但在名人的身影之后,有着一支数量不断增加、政治关怀不断增强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据北洋政府第五次教育统计,1917年有全国高等学校84所,学生19823人。据《中国教育统计概览》(商务印书馆1924年),1922年5月到1923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为124所,学生34880人。1915年,全国有普通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1922年发展到547所,学生103385人。1917年,全国有实业学校475所,学生30513人(36)。留美学生到1919年超过了两千人。到1919年全国受过小学教育的已过千万。“五四”时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四一代”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一代。与以往的“洋务一代”与“清末一代”相比,“五四一代”有着更为强烈的公共关怀、政治抱负,有着更为清醒的民族反思、文化自觉,有着更为犀利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也有更富有远见的人生规划、社会理想,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公共性、反思性、批判性与引领性的特点。相比于“公车上书”诉之于庙堂之高的皇帝,五四青年学生转而寄望于自身的直接行动,寄望于社会大众、全国同胞,《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直接向公众发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身为学者、学生,他们并非不想潜心于学术、专注于文化,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促使他们挺身而出。1935年五四运动16周年时胡适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回忆:“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新青年》最初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政治的兴趣爆发了,“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并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提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37)。不过,在“五四遗产”中,胡适更看重的是文化运动,他甚至认为政治运动是对文化运动的干扰。他还认为,“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38)。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鲁迅对封建礼教与国民性的批判,胡适提倡的“打倒孔家店”与“健全的个人主义”,李大钊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第三文明”,傅斯年等建设“学术社会”的期许等,在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巨大与深远的影响,把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批判精神与引领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队伍继续扩大。有的学者估算,“五四”后30年中国各层次的知识分子不到500万,包括:高等学校或具有大专以上程度者25万人左右(含1912年前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3184人、1912-1947专科以上毕业累计210827人、留学生2万-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毕业约400万人(39)。“后五四一代”是分化、分流的一代,从社会角色上,有的从政,包括入阁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陈布雷等人,也包括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有的供职于传媒等“公共空间”如张季鸾、储安平、王芸生等;有的相对专心于学术或文艺,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钱钟书、沈从文等;有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摇摆,如叶公超等。李泽厚先生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在“后五四”时代救亡与革命成了主旋律,也成了当时最大的公共关怀,因此,过问政治以至投身革命也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只是深深涉足政治,又使其中一部分人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本色。“后五四一代”的政治社会关怀,相比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五四一代”,相比于晚清的“洋务一代”与“清末一代”,都要显得更为普遍,也更加突出。“‘救国’高于救个人。要‘救国’必须‘唤醒民众’。既然实行‘唤醒民众’,于是知识分子的精干运动逐渐扩大而为全民性的‘群众运动’”(40)。在“政治运动似蛟龙似的乘势而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部分人如李济、金岳霖、潘光旦、梁思成、梁思永等潜心于学术,在艰难的环境中致力于学术建设与文化建设。他们不再像“清末一代”与“五四一代”那样“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而成了分科细密的具体专业领域的专家,学术成就斐然可观,但社会影响力有所下沉。
在建国后出现的四个世代中,目前还掌握着“学术霸权”的是“文革一代”或者说“红卫兵一代”。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勾画了他所在的“文革一代”的性格特征:
“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上,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泽东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41)
在“文革一代”之前,包括“十七年一代”在内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周恩来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这里,“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就属于“十七年一代”,当然这一数字在1956年后在继续增加。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自然谈不上,也没有话语空间,要批判只有朝自己使劲或为自保落井下石,知识分子人格受到严重的毁损,学术也颇因政治运动而荒废,以至有人做出“知识分子消失了”的判断。直到蛰伏20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文革一代”一道反思“文革”,反思“思想改造”,发出“新启蒙”的呼唤。在“文革一代”之后,60年代出生的“第七代”与跨世纪的“第八代”没有经过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的洗礼,“文革”的疯狂对他们而言只是儿时的记忆或是阅读中的传说。政治运动造成的学术与知识的真空,原本是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还是让“文革一代”或者说由恢复高考后首先进入高校的77级、78级、79级组成的“新三届”抢先抓住了,“第七代”似乎还陷在“文革一代”的学术权势的夹缝之中。更何况这二代虽躲过了政治风浪的冲击,但迎来的却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市场化、功利性对学术与知识价值的冲击,对知识分子道义担当与学术精神的冲击,也是超乎常人想象的。人们呼唤大师,但学术似乎还在失守,“意义”还需继续寻求;在物质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的背景之下,即使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包装在媒体登场,总是让人想到背后的利益集团或功利考量,或者是被纳入市场化生产体制的“学术超男”与“学术超女”。倒是在网络的热点关注中,我们能看到包括70后、80后的“第八代”那种有着“公共知识分子”风范的关怀:对国家安全的忧危、对社会不公的质疑、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对事实真相的追问与对未来发展的关切。但在浮躁与快餐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新生代”,对于需要潜下心来、沉下心来的学术,我们惟有热切期待、耐心等待。
各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在属于自己的时代过去之后,往往对自身作为主角时所扮演的角色、所取得的建树、所提出的观点,尤其是自身的弱点,会有所检讨与反思。如梁启超在五四时代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批评清末“新学家”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胡适在“后五四”时代对“五四”的反思,还有晚年对自己早年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忏悔;“后五四一代”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中的检讨等。这些反思有的是由衷的,有的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是一种前行,有的是一种曲折;但都是时代转换的一种印记。
不同世代的知识人之间有相携与合作,也有冲突与紧张,尤其是后一世代对前一世代常会有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一个时代以一个世代为主角,但同时至少有三个世代在同台亮相、同显身手。清末的舞台上,主角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清末一代”,但“洋务一代”的张之洞还发表了《劝学篇》,而“五四一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已初试锋芒,如陈独秀于1903年发起成立爱国会、于1904年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鲁迅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早期文章,胡适也在《竞业旬报》等发表作品了。“五四”时期,主角是“五四一代”,包括老师辈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也包括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蔡元培是前一世代的,但功业主要在五四时期;但“清末一代”的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严复等还有着重要影响,“后五四一代”的郭沫若、俞平伯等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五四”年代,“后五四一代”成了历史的主角,尤其是接受并参与建构革命意识形态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逐渐确立起“独大”的话语霸权与知识权势,但“五四一代”的健将胡适等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解放的一代”或者说“十七年一代”也开始登场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解放的一代’与‘红卫兵的一代’几乎不分彼此,共同发动、主导或参与了新启蒙主义运动”(42),此外,还有“后五四一代”的王元化等人,同时在当时的论坛、研讨会、报刊上也出现了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人的身姿与声音。
在知识分子的代际嬗替中,有后一世代对前一世代的肯定与推崇,如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声称自己的名字是用了“适者生存”的“适”字,是严复译本《天演论》风行天下的纪念品;还称自己“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43)。
但更有前一世代视后一世代为过于激情、过于张狂,后一世代批评前一世代落伍甚至呼唤前一世代退场的声音。最早使用“后五四”这一概念、以“五四之子”自称的殷海光将这种现象称为“代间紧张与冲突”。他指出:“这里所说代间紧张与冲突,即是在同一个社会中,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有基本价值观念的背离,有种种紧张的对立情绪滋蔓,并且有着种种实际的利害冲突存在。”(44)不妨再以“五四”为坐标。有“清末一代”对“五四一代”的指责,如严复对“五四”学生罢课就十分不满,认为:“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45)“以数千学生乃任一二人毒打,信乎?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46)但“五四一代”又觉得“清末一代”落伍了。胡适质问并加分析:“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现在哪里去了?他们的消灭不外两个原因:(1)眼镜不适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为是一个出风头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汉子。现在人都笑他为守旧,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适用的眼镜换一换的缘故。(2)无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软了,人家给他些钱,或给他一个差事,教他不要干,他就不敢干了。”(47)鲁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批评章太炎、刘半农,“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但就在“五四一代”还在崭露锋芒之时,“后五四一代”的创造社成员对“五四一代”提出了质疑。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称“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像声嘶力竭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像寿终正寝”(48)。“我们分明又看到崛起的‘创造社’一群,又在他们与‘一代’之间竖起一道屏障。渐渐的,又同样将‘五四’一代归入落伍者的行列,要将其清除出学术思想的舞台”(49)。“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也曾激烈地批评“五四一代”的激情有余、深刻不足。
三
如何区分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有着许多视角。
原有的经典模式是党史研究路径之下的阶级属性分析。这种分析框架“一提起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关于其阶级性的界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然后,再据此来分析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50)。夏丏尊把知识阶层分为上层、中层与下层就近似于此,他指出:“知识阶级之中实有表层中层与底层之别:同一教育者,大学教授(野鸡大学当然不在其内)是上层,小学教师是下层;同一文人,月收版税数千元或数百元的是上层,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层。上层的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51)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是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特殊阶层。他用“毛”与“皮”的比喻来说明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附属于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把是否与工农结合作为区分知识分子政治属性的标准,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52)现代知识分子被“书写”在三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与工农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随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有的被看成反动派的帮凶、反动文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基本队伍的定性是小资产阶级,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被宣布为“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经过反复,“文革”结束后被重新确认。
再就是历史学研究路径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轨迹的阶段分析。人们使用了“传统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等概念,1840年与1919年是划时代的年份,鸦片战争被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开端(53),而五四运动则被看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礼”(54)。有学者从寻求自由的角度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儒家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入世为宦的道路,以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其价值;道家知识分子或隐逸知识分子,逃避政治,向往相对隔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环境,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与自由(55)。有学者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归纳为:生长在国门被强行打开,处处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社会之中,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民族情感;从知识结构看,既有传统知识,也有西学知识;有较强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却相对淡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的反动统治,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一般难逃悲剧命运(56)。而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有学者将其与“近代知识分子”作了对比:数量与规模较之近代扩大了;近代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但现代知识分子始终明确地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近代知识分子基本由封建士人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而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另有少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上层,多数长期留学海外,所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比近代知识分子深远得多;近代知识分子“科举之外无他业”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职业结构是一元化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发挥了比近代知识分子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作用(57)。这种分析框架显然没有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出发,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一角度上来。
其三是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下从社会分工、社会影响与社会功能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包括宏观层面的科技型知识分子、人文型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从事社会管理的制度型知识分子,也包括微观层面知识圈、学术圈的各个界别如经济学界、文学界、史学界等。当时,各界纷纷组织各学科的学会。从社会影响的角度,随着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引入,出现了专业知识分子(职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公意知识分子)的划分。“清末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与“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具有“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与“忧国忧民”的公共情怀,既是“知识人”又是“社会人”,其国学素养“绝后”,其西学背景“空前”,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巨大而深远,堪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高拥有大量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有学者列出了一串名单,“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都比较明显地是公共知识分子,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还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王小波,法学界的贺卫方,文史学界的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政治学领域的刘军宁等(58)。《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7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此后有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从专业知识分子的角度,目前看来值得称道的还是“后五四一代”,如李济、梁思永等开创的考古学,潘光旦、费孝通、孙本文等创立的社会学,梁思成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后又有学者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区分了一般性知识分子与战略性知识分子。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他于2010年8月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了《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一文,提出: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致力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但也要有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我们社会正需要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59)。此后,《人民论坛》组织了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
其四是文化学研究路径之下对知识分子群体类别的划分。如“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大思潮”框架下,对三大群体的分析。“五四一代”已出现三派的明显分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知识群体激烈批判传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社会问题采取激进革命、直接解决的方式;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个性解放,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杜亚泉、梁漱溟、吴宓等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或潜心于学术。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一脉有以鲁迅为代表的、集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还有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聚集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等;自由主义一脉主要是集结在《新月》、《独立评论》、《观察》周刊等报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传媒为“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影响政治,还有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致力于“中间路线”的民主人士;保守主义一脉有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十教授”等。9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分化出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等具有不同价值与思想倾向的群体。
还有其他研究路径之下的分析,如2011年岁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富教授豪车代步,穷教授发愁买车”的“富教授、穷教授”现象的观察,就是经济学研究路径之下的一种区分。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2页。
②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6页。
③姜义华:《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参见李晓:《20世纪初中国三代现代知识分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黄群:《戊戌维新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求索》,2007年第6期;张瑞静:《19世纪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初步形成》,《延边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纪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华东石油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藩云成:《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牛纪霞:《浅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山东电大学报》,2000年第1期等。
⑤郑也夫:《西学东渐与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
⑥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⑦沈艳:《“经世致用”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⑧黄耀柏:《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论纲》,《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专辑。
⑨黎仁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与特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⑩荆惠兰:《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1)陈占彪:《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12)王金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13)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一般》杂志,1928年5月号。
(1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5页。
(15)参看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第1页。
(17)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18)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9)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0)(2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第19页。
(22)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23)李喜所:《我国当代三次留学潮》,《天津日报》,2008年7月2日。
(24)姜义华:《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5)陈庆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日。
(26)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页。
(27)语冰:《90年代知识分子的代际研究》,学术批评网。
(28)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29)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92页。
(3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6页。
(31)沈燕:《经世致用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32)黎仁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与特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3)李晓:《20世纪初中国三代现代知识分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34)荆惠兰:《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5)程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探析》,《消费导报》,2009年第2期。
(36)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37)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1998年版,第575-577页。
(38)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胡适文集》(第11册),第575-577页。
(39)王金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40)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41)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2日。
(42)语冰:《90年代知识分子的代际研究》,学术批评网。
(43)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3页。
(4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01页。
(45)(46)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96页,第695页。
(47)胡适:《学生与社会》,《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48)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9-660页。
(49)章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近代中国与世界》(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50)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1)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一般》杂志,1928年5月号。
(52)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53)何一民:《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54)李新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礼》,《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5期。
(55)陆群:《自由之艰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磨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56)黎仁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与特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57)王金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58)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9)陶文昭:《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人民论坛》,2010年第15期。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晚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