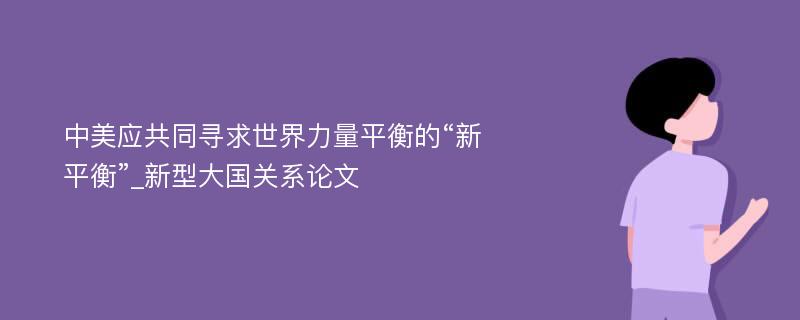
中美应共同谋求世界权力天平“新的均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天平论文,权力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新型大国关系”业已成为中美两国外交政策话语中共同的流行词。此种关系得以建立的关键前提在于,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超级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争。虽然中国仍然拒绝接受将中美两国视作全球最为重要的两极、共同管控世界事务的“G2”概念,但却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化解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和中国作为唯一有实力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鉴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符合美国一贯致力于将中国崛起纳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一呼吁,已经作出了积极回应。根据新华社报道,在2013年6月于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的“习奥庄园会”上,两国元首“同意建立中美新型关系,避免走向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老路”。①
中美两国领导人表态支持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对两国关系而言无疑是一个积极进展。不过,鉴于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新型关系的构建绝非仅有双方领导人的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双边关系趋紧的背景下)。正如中国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所指出的那样,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已经在中国引起很大疑虑。随着美国卷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这些疑虑逐渐加深。如果美国这种考虑不周的‘再平衡战略’继续下去,地区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那么一场军备竞赛将难以避免”。他进而从中国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政策是否正在损害两国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中美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从而有助于避免对抗和冲突?中美能否携手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共同应对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全球性挑战?②
本文认为,中国的崛起使得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得不对两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潜在的冲突进行战略应对。无论是不是一种考虑不周的战略,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应对中国影响力空前增长导致的亚太地区权势平衡的变化,此举自然会引起中方关于美国是否意在遏制中国崛起的疑虑。然而,遏制中国不仅会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还将破坏地区和平与繁荣,因而对美国而言并非可行之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在亚太地区独自维系霸权地位。两国必须探寻一种现实主义路径,携手构建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而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强权之间必然发生结构性冲突的历史宿命。
世界权力的天平是否在向中国倾斜?
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冷战结束后的许多年中,受制于自身有限的对外行为能力和地缘政治空间,中国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在国际上保持低调的同时集中精力壮大国家实力。在处理与美国关系问题上,中国试图“学会与霸权相处”,努力适应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现实,并作出相应政策调整。③因此,面对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和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EP-3型侦察机相撞事件,中国均力图避免对抗。为了探寻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主张各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实现和平共存。④虽然国家正在崛起,中国却仍较为谨慎地隐藏大国的雄心。有意思的是,“G2”概念出现后,很多中国人起初陶醉于中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得到了认可,而中国领导人却很快开始批评该提法“有可能成为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前沿的圈套”。⑤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认同“G2”的提法,认为这一概念“不恰当”,同时重申:“尽管已经取得显著成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几代人为之努力。”⑥
随着国家实力的巨幅提升,中国不仅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且在抵御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表现得比多数西方国家更好。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世界权力的天平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开始争论是否应该放弃消极的“韬光养晦”政策。尽管争辩仍无结论,但大家都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需要利用自身日益增多的筹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结果,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愿意积极主动地塑造外部环境,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作出反应,在捍卫本国核心利益上也变得更为强势和不妥协。陷入金融动荡的美国,看起来自顾不暇,迫切渴望资金充裕的中国施以援手,但仍然试图延缓中国的发展,这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再愿意对其迁就迎合。尽管中国当前在对美政策方面并未出现方向上的根本逆转,但其在相关问题上的言行已经在向减少容忍的方向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中美关系在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按照两国实力对比情况来处理双边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美国出于制衡苏联的目的开始与中国接触,但那时的中国远不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所以,美国并未将其看成是真正的竞争者。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开始将其看成一个真正的对手,两国关系也由此日趋复杂。除了在贸易、人权、台湾问题等很多双边领域问题上的分歧经常激化外,两国对彼此长远意图的疑虑也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中国人怀疑美国企图通过分裂中国、破坏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联合中国的敌对势力实施包围等手段,阻止中国强大;很多美国人则担心中国的大国雄心会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作为霸权国,美国的自身价值和利益与当前国际体系的规则、价值和制度息息相关,既得利益促使其极力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与此相比,崛起国则往往要求改变既有权力分配格局。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改变常常会带来冲突,甚至是大规模战争。⑦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争论,是应将中国视为威胁而施以遏制,还是看作机会而增加接触。作为该争论的一种反映,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常游移于两种观点之间,但最终总是回到折中立场,即在妥协与对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折中主义立场植根于现实主义,一方面与中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并务实地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同时又从权势政治的角度防范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准备应对中国像典型的崛起国家那样热衷炫耀武力的可能性。⑧为提升“两面下注”战略(hedge strategy)的有效性,2009年,也就是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便提出“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美国须明确表态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而中国则需要向世界保证其发展和日渐重要的全球角色不会威胁他国的安全与福祉。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于,如何从战略上的互不信任走向“战略再保障”。不过,“战略再保障”的概念很快被华盛顿所抛弃,因为它对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作出了立场明确的新回应,一度使一些人怀疑美国对华是否转向了单纯的接触政策。⑩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在继续探寻,“在相互依存和中国力量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如何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各自发挥全面作用,以推动双方合作”。(11)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心存疑虑,但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中国与美国力量差距仍然很大,无法承担同美国全面对抗的代价。中国将21世纪的前20年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战略机遇期”。(12)因此,习近平在2012年就开始呼吁通过对话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已经有过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事实(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于20世纪初的英美之间),而且也是由于该概念是“和平共处”这一广为使用的词汇的另一种表达。习近平用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战略互信、合作共赢等概念来描述“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共存关系被解读为中国政府承诺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作为回报,美国将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13)说“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新概念,还因为其中的大国定义仍然沿用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实力的定义。尽管中国已经根据现实主义传统与多极世界中的新兴“极”(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国)谈及新型大国关系,(14)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没有提升到中美关系的高度。只有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才堪称大国,因而必须携手“走出一条避免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构建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模式”。(15)
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给予了积极回应。虽然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崛起最终将如何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仍然不确定,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2012年3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纪念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4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讲话中,督促北京和华盛顿“寻求一个答案——一个关于‘既有强权遭遇新兴大国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16)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则清晰地指出,奥巴马政府将与中方一起超越“新兴大国和既有强权注定发生冲突”的命题,并将与中方一道“构建新兴国家和既存大国关系的新模式”。(17)在2013年6月习、奥加利福尼亚峰会召开之前举行的吹风会上,一名白宫高级官员也表示,由于认识到新兴大国与既有强权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为避免竞争带来的陷阱,双方领导人一致强调构建互动模式的重要性,以“堵住导致两国关系不稳定和争斗的最主要源头,避免将双边关系引向对抗之路”。(18)
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与中美竞争
尽管两国领导人均支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的确还是有可能将双边关系引向对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针对亚太的“战略再平衡”,已经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尽管美方辩称,“再平衡”政策只是为了在亚太这个世界关键区域追寻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未来,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且更新美国的联盟体系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每项政策都不过是其旨在阻碍中国崛起的整套遏制战略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再平衡”是以损害中国为代价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将会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对奥巴马政府而言,在让中方相信“再平衡”并非意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向盟友证明美国将恪守同盟义务,是一个巨大挑战。尽管奥巴马一再向中国政府保证“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有助于世界和地区的繁荣与稳定”,(19)但中国人对此并不信服。这是因为中方对“再平衡”政策的动机存有疑虑,认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与其平起平坐。无论“再平衡”是否旨在遏制中国崛起,中国都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随着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美国希望调整其在全球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方面的投入以实现“平衡”,而其推行“再平衡”背后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对一些亚太国家的呼吁做出回应——这些国家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区域权力平衡,因此美国应该在制衡中国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在周边外交中展开“魅力攻势”,推行“睦邻政策”,以提升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政策抛弃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做法(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论亲疏),改变了根据周边国家与美国、苏联的关系定位其与本国关系的传统(“以美画线”、“以苏画线”),不论周边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政治制度以及与其他大国关系如何,均与其发展友好关系。(20)自此以后,中国与很多先前关系紧张的周边国家改善了关系。中蒙关系正常化即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此前的蒙古曾长期被视作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卫星国;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e Gandhi)1988年12月访问北京的“破冰之旅”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两国间的首次高层访问;(21)第三个案例则是在与朝鲜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改善与韩国的关系。(22)在此期间,中国同印尼(1990年8月)、新加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和越南(1991年11月)等几个有影响力的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于1991年应邀参加了东盟部长级扩大会议,于1994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ARF)成员,于1996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明确表明了“站在亚洲一边”的政策立场,坚决拒绝人民币贬值。在当时的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必将导致地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损耗东南亚国家为复苏经济所作出的努力,进而给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积极反应,使得其赢得了在该地区影响力。199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应邀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中国与东盟每年一度的“10+1”峰会机制自此肇始。随后,日本、韩国领导人加入其中,“10+3”机制于一个月后创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首届“10+3”峰会上宣布将携手东盟共建“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3)
中国睦邻政策的成功,恰逢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亚太相对忽视之时。由于一门心思地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亚太事务从未成为小布什的首要议事日程。正如小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所言,“问题不在于我们有些忽视亚洲,而在于我们完全忽视了它……现在,我们实在太全神贯注在伊拉克事务上,全然忽视了亚洲”。美国国务卿赖斯错过2005年和2007年两次东盟地区性论坛的严重失策行为,即是上述论断的重要证据。(24)尽管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所有地区大国,都有各自与东盟国家的首脑峰会,美国却没兴趣召开“美国—东盟”峰会,这部分地是因为小布什不愿意到亚洲去参加这种“清谈”会议。实际上,参加这类首脑会议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出席会议本身就传递了对地区事务的兴趣和担当,而缺席反映出态度上的漠视,且容易招来非议。
鉴于中国的成功和美国的失策,伊丽莎白·伊卡诺米(Elizabeth Economy)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测了亚太权力重新配置的三种可能前景。其中的最佳前景是中国与美日分享地区领导权,促进地区内共识的形成,以应对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第二种前景展示的则是一种传统的平衡游戏,亚洲国家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借助中国绕开美国,并由此在对外战略上找到一条能更直接地实现其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国家利益的替代路径,但这对美国显然缺乏吸引力;对美国而言,最坏的前景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美国面对的将是一个对美国安全行动反应更消极、对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和金融体系依赖更少,以及可能会在美国所发起的关于人权或反恐等各项外交行动面前表现更冷淡的亚洲。(25)
然而,上述三种前景都未实现。这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实力潜能及其主导地区文化和政治的历史,决定了睦邻政策的成功只能是暂时性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虽然仍在重申其睦邻政策,但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上,则开始以更加强硬的方式表达主权诉求。“中国的核心利益”突然变成了一个流行语,其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核心利益”被定义为“国家生存的底线”且“在本质上是不可以谈判的”,(26)表明了中国维护其主权和领土主张的决心。以往中国官方关于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声明,一般是特指台湾、新疆和西藏问题,(27)而在2009年,中国领导人则将核心利益涉及的范围扩展到了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问题,并对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强力回应——包括多次尝试阻止越南和菲律宾舰船在争议水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在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导致两国陷入僵持、日本政府试图将钓鱼岛问题国际化之际,对其采取强硬的惩罚性措施,并动用军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以致引发外交危机。
面对亚洲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的“战略再平衡”自然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甚至是主动邀请,因为这些国家要么对中国“展示肌肉”深感忧虑,要么为了激起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而试图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很多亚洲人过去习惯问,如果让美国驻军和建设军事基地,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现在的新问题已经变为,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才能让他们留下来?这都是因为中国。(28)考虑到很多国家欢迎美国增加军事力量以应对权力平衡的快速变化,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从反恐转向了有力地行使其在亚太的领导权。因此“再平衡”很容易被理解为美国决心对中国挑战其亚洲领导地位进行反击,也容易被理解为对某些美国战略家的回应,这些人号召遏制中国,绝不能因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而使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招致削弱。
中国自然会怀疑美国是在自己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挑拨离间、制造摩擦,以便坐收渔利和保持自身影响力,进而长久地按照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因而保持高度警觉。(29)在中国官方看来,深藏在“再平衡”政策背后的,是华盛顿对中国在该地区上升势头的极度担忧和其削弱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决心。特别让北京方面紧张的是所谓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按照该计划,奥巴马政府围绕六条关键“行动线”(lines of action)展开外交:加强双边安全同盟;扩大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s);参与地区多边制度;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根基雄厚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30)中国将该计划视为美国全面运用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内的所有力量元素以阻挠中国崛起的一项综合政策。
北京发现,虽然“再平衡”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但是其重心却越来越集中于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重新部署。这一点在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E.Panetta)2012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体现得很明显:“美国的军事力量再平衡正在稳步、持续和周密地推进,将使这一关键地区的军事能力得以增强。”确切地说,美国海军将重新调整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军事力量布局,太平洋地区军力占其在两地部署的总军力的比重将由原来的50%提升至60%。(31)特别是,奥巴马2011年11月宣布将向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皇家军事基地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该部署会使得传统上聚焦于东北亚的美军将其影响力向西向南扩展,进而能够对南海安全施加影响。虽然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转向亚洲主要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其进行更广泛接触的一部分”,(32)但是中国仍然将美国针对亚洲实施再平衡的核心目的视为通过更多军力以及其他手段,在这个不安宁的地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
除了军事部署之外,美国重申其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地位、重塑其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双边关系的举动,也让中国忧心忡忡。就多边机制而言,奥巴马政府迅速调整了美国的东盟政策,向东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表明了美国与其提升关系的决心。2009年2月,希拉里将造访设在印尼的东盟秘书处作为自己首次官方海外之旅的一部分,以此表明美国的新政策。2009年11月,奥巴马在新加坡主持了首届“美国—东盟”年度峰会,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开启了美国对外关系的新征程。有观点认为,“此次峰会反映了长期被伊拉克和阿富汗乱局牵扯精力的美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之东南邻居的兴趣得以重燃”。(33)2010年7月,希拉里宣称,南海航行自由、亚洲公海领域的开放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并将促进在相关问题上的多边谈判作为美国外交优先日程,标志着美国开始介入南海领土争端。令中国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希拉里是在越南作出此番讲话的,而越南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均与中国存有争端,此时正试图利用其担任东盟轮值国主席的机会挑起争端、浑水摸鱼。一位记者甚至据此断言,“美国是在中国背后捅了一刀”。(34)暂且不论美国是否对中国有所预谋,但其的确是在大力发展与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同有着相同的忧虑——在它们看来,中国乐于在有争议的海域展示其增强了的军事实力。
为表达感激,东盟正式邀请美国参加定于2010年10月召开的第六届年度东亚峰会。美国不但接受了邀请,还本着成效至上的原则为东亚峰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准备将其发展成为“解决和避免争端的基础性地区政治安全机制”。(35)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奥巴马就将极富争议的朝鲜问题和南海问题带到了会场。在与会国多数亚洲国家站到了美国一边的情况下,温家宝表达了愤慨并作出回应,他指出,“外部势力”无权干涉复杂的南海争端,他还委婉地提醒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不要在多边场合讨论这一敏感问题,因为中国不希望一些东南亚国家将南海争端变成一个多边问题。(36)
随着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再度强化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双边关系,中国的疑虑进一步加深。应日本政府一再请求,希拉里重申,虽然美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但由于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因而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这就等于认可美国将在武装冲突事件中为“日本行政管辖之下的领土”提供保护。(37)中国将日本视作美国在亚太的代理人,自然对美国上述表态感到不安。在中方看来,日本之所以有恃无恐、一再挑衅,正是由于美日同盟给日本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抗衡中国崛起的信心和勇气。“结果,当中国试图在周边海域中控制争议岛屿时,就不仅是在和争议当事国对抗,而且是向美国发出的抗议信号”。(38)
遏制中国为何将弄巧成拙?
随着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实施,中美关系也日益变得争执不断。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外交努力,严重限制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崛起的能力。中国领导人尤为关注美国日益加强其对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介入的举动。从中国视角来看,美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针对亚洲的“再平衡”政策已经使该地区陷入混乱,并使得中美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强化其与该地区盟友军事外交关系的努力,则加剧了中国对于被美国包围和施压的焦虑。“包围”因而成为中国就美国东亚战略问题展开辩驳时的常用语。这种认识又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中国战略家关于美国试图集结其东亚盟国、进而遏制中国崛起的判断。
的确有一些美国战略家主张奉行遏制战略,认为应从多方面将“再平衡”的目标锁定为中国。尽管如此,美国的立场并非遏制中国崛起,遏制只是经过过度简化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框架争论中的一种极端观点。作为冷战结束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得不对中国的崛起作出战略应对。从历史经验看,霸权国面对崛起国的挑战,至少有三种会导致不同结果的应对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视而不见。近代史上,由于拒不面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崛起并进行相应调整,中国先是在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后又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华帝国最终崩溃并使中国蒙受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停滞。第二种方式是遏制。18世纪时,法兰西帝国试图遏制新兴的崛起国英国,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漫长的武装冲突和血腥战争,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被威灵顿将军打败才告终结。第三种方式是接受。面对19世纪后期美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大英帝国逐渐让美国承担起全球治理的更多责任。此举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而且使英国得以在“日不落帝国”衰落的世界保留其制度性遗产。
当今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将美国推到了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类似的境地。美国当然不会无视中国的崛起或将自己的霸主位置拱手相让,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全面遏制也终将弄巧成拙。第一,遏制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前苏联实施的政策时,主要措施包括“从经济上孤立苏联,摧毁其意识形态,以强大的美国核武库限制它的军事力量,联合北约和日本等同盟对其东西夹击,利用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对其施压。遏制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减少与苏联的社会和经济互动”。(39)尽管美国成功地实施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中国却绝非苏联。中美关系远比美苏关系要复杂得多。正如同基辛格所指出的,“苏联的经济力量薄弱(去除军工产业之后),对全球经济也并无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乃世界经济的有力影响者,是其所有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工业国的首要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长期对抗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并带来让各方都难以安宁的后果”。(40)的确,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360亿美元(美苏贸易最好的时候仅40来亿美元),且中国持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已然是美国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美国大学校园中有大约20万左右中国留学生),而奥巴马政府则启动了一项派遣10万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减少经济社会交往来遏制中国。
第二,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邻国愿意在其阴影下生存,他们之中却也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担与中国为敌或置身中美对抗夹缝之中所造成的后果。因此,美国也无法通过与亚洲国家合作构建反华联盟的方式遏制中国,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与一个市场广阔的新兴大国为敌的代价。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相信让美国与中国竞争最符合其利益,但多数国家认为与中美两大国同时搞好关系、不与其中任何一方为敌更能维护本国利益。中国的多数周边国家所热衷的是利用美国的存在压制中国,同时又强烈支持与中国接触,希望能将中国固定于地区合作框架之中。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想继续与一个繁荣的中国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能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中获益。环顾中美两国,很少有东亚国家愿意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或准备好了在中美两个可能的对手之间倒向某一方。以东盟为例,尽管其多数成员国“欢迎美国防范中国力量的增长,他们的经济却越来越依赖中国,且不想卷入中美两巨头之间任何可能的冲突之中”。(41)这些国家都希望看到,随着它们更明确地展示团结,中国的快速崛起能得到抑制,亚洲能够持续繁荣。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了防止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升级破坏地区繁荣稳定而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有鉴于此,多数东亚国家“拒绝试图在美国中国之间选边站的错误选择”。(42)
第三,由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奥巴马政府任职之时恰逢从短暂的美国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权力转移的关节点上。虽然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将会衰弱,影响力也会受到更大限制”。(43)面对一个日益复杂、脆弱、权力分散、竞争趋强的世界,美国能在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最终取决于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健康状况。从长远看,美国有待克服棘手的、阻碍其政府有效行动的政治僵局,并理顺国库,才能将精力投入东亚。尽管美国要在亚洲维系一个强大军事存在的承诺是真诚的,但如果不能解决所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不管美国意图如何,它仍将难以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能否兑现增加美国军事存在的承诺,长期负担在该地区的海空军部署,仍然很难预知。考虑到预算限制,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针对亚洲的“再平衡”持悲观态度。一方面,美国日益偏重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可能会导致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军力的缩减。不仅如此,调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和最大限度削减海军开支的计划可能撞车,导致前者在资金链上受到比预想更大的限制。(44)新加坡一位观察家因而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在较长时期内受制于其现实财政状况和未来政府管理方式的变迁……无论是否乐意,美国在亚太的角色(更不用说在全球的角色)从长远看是相对下降的”。(45)
第四,军事、外交等各种资源投入对于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不可或缺,奥巴马政府想在削减这些资源投入的同时在亚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然面临着巨大困难。虽然美国试图把亚太作为战略重心,但在中东、北非仍然是潜在动荡中心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的精力仍有可能重新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冲突之中,而这将使上述资源投入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因此,相对于“战略东移”(pivot),奥巴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更喜欢“再平衡”(rebalance)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因为最初使用“战略东移”提法时带来了一些意想之外的后果,这一提法使人联想到美国将从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完全撤离”曾引发广泛关切。(46)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想让中东问题继续像过去十年那样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但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潜在或显在的问题(如叙利亚发生严重内战、伊朗发展核武器、埃及新政府前途未卜、巴以关系陷入僵局,以及约旦、巴林两个亲西方君主国国内的不稳定)依然可能让美国麻烦缠身。有趣的是,当奥巴马在2013年年初开始其第二任期时,华盛顿的很多观察家都在猜想,美国政府是否会对“再平衡”政策本身加以“再平衡”,因为克里曾在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感到不安,在他看来,此举既不明智也无必要。当然,那时还是参议员的克里是否在阐释一种新立场尚不得而知,(47)不过其任职后的首访选择了欧洲和中东。他的外交优先日程是推动重启巴以和谈、伊朗核问题谈判以及叙利亚内战问题,而不是亚太事务。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奥巴马2011年11月作出高调访问澳大利亚、具有象征意义地宣布在该国增强军力部署的举措时,美国国内舆论领袖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尽管美国媒体对于政府针对中国的强硬姿态鲜有批评,但对国内乱局和中东旷日持久的战争感到愤怒的民众,却在指责政府包括在澳大利亚建设军事基地在内的新举措。
在这种情形下,尽管中国已经在亚太地缘政治新格局中崭露头角,美国还是不能按照零和博弈思维界定自身利益并施以遏制。在两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美国任何试图单方面遏制中国的尝试都难以得逞。
中美应共同谋求新的“权力均衡”体系
由于遏制中国崛起不现实,“战略再平衡”并非只是针对中国,而是美国界定其在亚太地区利益和优先事项的长期努力的延续。亚太正在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兴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鉴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对该地区的投入不足,“此次对外战略优先次序的调整,表明美国已意识到21世纪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48)中国在“再平衡”仍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同中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是其成功的关键。从现实角度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与中国接触,并接纳其成为国际体系中权责充分的全面参与者。与中国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关系不仅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事关美国亚洲宏大战略的成败。
基于上述认识,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既有强权通过对抗和遏制崛起大国来达到其所声称的防止冲突的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带来的恰恰是他们想竭力避免的结果”,因而,“我们尤为迫切地需要同中国合作”。(49)这可以看成是对美国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图的一份声明。体现在政策领域,奥巴马政府承认了中国的全球新兴大国地位,并建议将双边关系从小布什时期的“坦率、合作、建设性关系”升级为“全面、积极、建设性关系”。用“积极”代替“坦率”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不愿在敏感议题上挑战中国,也体现出其对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视。为了在他2009年11月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前定下合适的基调,奥巴马没有与10月份访问华盛顿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这背离了美国总统的一项重要传统。为表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奥巴马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首次明文规定:“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其重要。”在举行两国双边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的同时,奥巴马毫不犹豫地将双边高层对话提升到“战略”层级,并将中国定为“战略伙伴”——“一个中国渴望得到的标签”,而小布什政府任期内的中美安全对话所用的标签只是“高级”,因为要把“战略”的标签留给其同盟国。(50)该一变化表明,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美国逐渐开始愿意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平等交往。虽然战略与经济对话、经常性的首脑峰会以及政府间不同级别的制度化磋商,并不是可以使两国领导人轻易消除挑战、管控棘手的双边关系的外交“万灵药”,但这类对话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寻求共同利益、管理双边摩擦,以及协调应对全球和地区问题(这点日益显著)的有用平台。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还是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摩擦,而且不管外交政策如何高明,这种摩擦都难以轻易消除。为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同中国合作,奥巴马政府必须以现实主义的路径构建基于特定准则和规范的地区秩序,制定使中国能够壮大和保障自身安全但又不能使用武力强迫其邻国的行为准则。“以规则为准绳是美国政策得以有效推行的正确路径。而这一路径又必须以对忽视、违反或单方面改变既定秩序等行为的制衡能力为后盾”。(51)奥巴马政府必须证明,当中国损害美国利益和引起地区不稳定时,美国有能力按“规矩”办事。地区秩序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持一种能够抵制任何国家单独取得地区主导权的权力均势。回顾历史,冷战时期的亚太地区保持了相对相对较长时间的和平,其重要基础就在于中苏等为一方的大陆国家和美国及其沿海盟国为另一方的海洋国家,形成了一种权力均势并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海陆国家之间的平衡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开始向太平洋西岸倾斜,并引起了一些较小的海洋国家的担心。结果,为亚太地区带来稳定并推动亚洲经济奇迹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权力均衡逐渐被打破。(52)有鉴于此,美国重新采取接触政策就是要恢复该地区权力均衡,否则,就可能会引发有关各国对地区安全的担忧。
当然,权力均衡非常微妙。一方面,为了建立和平的地区秩序、制衡中国势力、影响中国融入新兴国际和地区体系的方式,美国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包括维护其与盟国、伙伴国的深厚关系;另一方面,权力均衡要求美国与崛起的中国分享责任与领导权。这对很多担心本国被敌对国家赶出亚洲的美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为阻止此种结果出现,美国曾经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作战,也曾在冷战中同苏联交手。因而,很多美国人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美国在世界上最富活力地区的根本利益的威胁。(53)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亚洲政策的基调一直是谨慎外交——修整太平洋地区的传统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美国的态度是,在中国表现出合作态度时,与之进行接触,同时要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其挑起战事。美国的目的是限制中国,而不是遏制中国”。(54)
美国已经无力像过去那样主导性一切、无所不包,因而必须把中国视为该地区的实力对等大国,并探求一条与其相处的可行路径。尽管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只能满足于做一个更谦卑的角色”,但它的确可能预示着“美国只有让给中国一些政治和战略空间,才能建立适应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和平新秩序”。(55)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投射力量的国家。中国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中美这两个最大的亚太国家需要加深理解、增强互信,至少应承认彼此在该地区的合法利益和地位,并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考虑对方关切。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一定要接受中国所有的核心利益诉求,但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符合既有国际准则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正当关切。中国政府已经阐明,在中国争取与大国建立新型关系过程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底线。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所说,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需要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底线,不挑战或突破对方的底线”。(56)
从这一立场出发,美国对地区冲突的涉入必须降低到合理范围,以缓解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问的紧张关系。美国应阻止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采取会导致敌意的挑衅行为。美国不可能仲裁每一争端背后涉及的纷乱的法律、历史和情感争执,因而必须谨慎地避免被其地区盟国拉下水,从而卷入到它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美国不应鼓励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亚太地区盟国为实现领土诉求而增加与中国冲突、甚至进而升级为更大的国际冲突的风险。中国实力迅速强大,使得美国很难再依靠自身曾经无可置疑的实力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实施有效的干预。美国必须考虑它是否能担负得起在盟国挑起的任何争斗中提供支持并同中国较量的代价,因为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发动战争对美国而言可能会极其昂贵和危险。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个能使双方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妥协之策并非易事,但它们可以先维持一种合作与摩擦并存的双边关系。换言之,尽管双边关系中的摩擦仍在继续,中美两国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继续加强交流磨合,同时“各自努力通过东亚峰会、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多边制度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基于共同利益的彼此接触也要继续推进”。(57)
意识到在一个中国崛起的环境中维护其地区利益并不必要发生冲突,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中采取了中立立场,并敦促所有国家遵循国际法。美国政府推动东盟国家进行联合,反对中国政府坚持只在双边场合讨论领土争端的立场,同时督促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并警告它们不要使用“制裁、恐吓和威胁”的方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支持南海争端当事国起草一个广泛适用和强有力的行为准则,以“建立平解决争议的明确程序与规则”。(58)美国一方面要给中国施压促使其采用外交手段解决海洋争端,另一方面又要在领土争端中保持中立,为了在两种立场之间寻求平衡,奥巴马政府在支持盟国和针对领土争端采取中立之间艰难地“走钢丝”。例如,尽管菲律宾领导人公开声称,根据1951年的《美菲互保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美国有义务在黄岩岛争端中为其提供保护,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心地避免作出任何官方声明对此予以承认或否认。美国政府对于黄岩岛是否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从未作出任何官方认定,虽然承诺履行《美菲互保条约》,但并没有不明确该岛礁是否在其涵盖范围之内。
在钓鱼岛争端中,自中国开始在其12海里领海的争议水域实施定期巡航以来,加上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两国问的冲突不断增加。日本有将美国拉入同中国冲突的强烈意愿——虽然这样做是一场豪赌,日本为此承担着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同中国开战的风险。此种形势给奥巴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其“最大程度挑衅亚洲邻国、同时让西方盟友为难”的外交政策不仅冒着和中国疏远关系的风险,也导致了美日关系疏远。一位观察家因而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在安保上全然依赖美国显得越来越不正常。当前这种安排给日本和美国都造成了压力,既让日本对自身极度依赖美国的现状产生焦虑和怨恨,也让美国担心东京方面可能会将其拖入对华战争。”(5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希望阻止中国对日本采取进攻性行动,也必须避免承受盲目支持日本政府一切行动的代价,如有必要,也将约束日本政府的挑衅行为。如果日本决心放弃和平宪法,自己掌握本国的安全命运,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全面提升核武研发能力直至宣布建立核武库,那么,美国“战略再平衡”政策将由于美国信誉和影响力受损而走进一个“恶性死循环”。奥巴马政府至今仍未能很成功地在中日两国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探索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的试验场。不幸的是,谈及双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每个国家总认为对方必须做出实质性改变,好像责任本来就应该由对方承担。很多美国人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在变得日益独断专行,强烈要求中国不要走上昔日帝国的扩张道路;而很多中国人则认为,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否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对等大国崛起的现实,并调整其与中国相处的方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方明确表示,构建两国关系的这种新模式只需要美国单方面的改变,这是因为,如同中国与美国打交道经验丰富经验的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及其外交部同事庞含兆所言,“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与此相比,“美国在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难令中方满意。中方并不是中美关系中难题的始作俑者,更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60)另一名中国外交官则进而明确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的局面,两国关系还会不时出现波折与紧张。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而这种后果对向来崇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的美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61)
作为21世纪相互竞争的两个世界大国,中美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和潜在危机点,它们之间的战略互不信任难以避免。(62)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日益汇聚,因为“两国间的权力分布更加均衡,为了解决在其所认为对本国前途至关重要的难题,每一方更需要与对方进行合作”。(63)G2概念所要达到的“战略两极”或“中美共治”虽然不切实际,但这一提法是对中美关系的核心地位以及两国通过合作管控彼此关系的必要性的一种确认。如果中美能真正携手,以它们的力量和财富建构一种持久的地区权力均势,而不是试图在外交或军事对抗中战胜对方,就一定能够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希拉里所言:“中美两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认为,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可能都得不到解决……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64)
无论中国政府是否相信奥巴马政府关于美国乐意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对等大国的说辞,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战略选择都是清晰的:既可以谋求地区主导地位并通过暴力对抗的方式将美国赶出亚太,也可以与美国开展合作并通过维持亚太地区权力均势避免恶性战略争斗,以确保双方之间的和平竞争。第一种选项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疑是不现实的。取得地区主导权从长期看或许会是中国的终极目标,但不会被视作中国在21世纪前期需要认真考虑的目标,这是由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决定的,也是因为该地区各国力量的消长变化仍在继续界定中国的权力范围。中国的日益强大已经促使周边国家采取了一些制衡行动,包括重新与美国结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实际行动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尤为重要。尽管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其真正的核心利益,但是在各种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包括与他国的领土争端上)继续保持战略克制,预防性地消除其他国家的制衡动机,绝对符合中国利益。在地区环境中被孤立于对中国没有好处。
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体系以及美国在亚太安全中的角色,为经济全球化和亚太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虽然中国政府对其中的一些规则可能并不满意,也想在制定和修订规则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但中国还是从中获益匪浅。尽管中国对美国在亚洲这块本国安身之地增强针对自己的军事和战略布局感到不安,中国也仍然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军事存在所塑造的地区稳定的受益者。作为现实主义者,中国领导人最终还是会认清权力对比的现实状况,那就是中美两国都不可能独自成为地区主导力量,权力均衡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美国维持其亚太霸权角色变得日益困难,但中国在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道路上也仍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巨大挑战,很难在亚洲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中国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本国内部。由于深刻而令人担忧的内部原因,中国也是一个脆弱的崛起国。为确保未来的崛起,实现中国梦,它必须首先处理好包括腐败、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等在内的各种国内问题。在中国解决这些国内难题之前,其未来崛起前景仍面临着不确定性。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一再强调“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65)正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努力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稳定同美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所以,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的努力进行了积极回应。
注释:
①"China,U.S.agree to build new type of relations",Xinhua,June 7,2013,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6/08/c_132442379.htm.
②He Yafei,"The Trust Deficit:How the U.S.'pivot' to Asia looks from Beijing",Foreign Policy,May 13,2013,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13/how_china_sees_the_us_pivot_to_asia.
③Jia Qingguo,"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y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4,August 2005,p.395.
④Liu Jiafei,"Sino-US Relations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No.60,June 2009,p.479.
⑤Jonas Parello-Plesner,"The G2:No good for China and for world governance",PacNet#31A,April 30,2009.
⑥"Wen rejects allegation of China,US monopolizing world affairs in future",Xinhua,May 21,2009.
⑦一项统计表明:“自1500年以来,崛起国与支配国的15次遭遇和竞争中,有11次的结果是战争。”Graham T.Allison Jr.,"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New York Times,June 6,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6/07/opini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html?emc=tnt&tntemail0=y&_r=0.
⑧Suisheng Zhao,"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1:75,2012,p.386.
⑨James B.Steinberg,"China's Arrival: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Keynote Speech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s%20September%2024,%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
⑩Josh Rogin,"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 Foreign Policy,November 6,2009,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11/06/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strategic_reassurance.
(11)David M.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Asia Policy,No.16,July 2013,p.52.
(12)Brad Glosserman,"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PacNet #40 Monday,June 10,2013.
(13)John Chan,"China Seek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Beijing will not Challenge US Global Dominance",Global Research,June 10,2013,http://www.globalresearch.ca/china-seeks-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china-will-not-challenge-us-global-dominance/5338462.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6月4日,第7版。
(15)Yang Jiechi,"Win-Win Cooperation",Washington Post,July 9,2013,p.13.
(16)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March 7,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17)White House News Release,"Remarks by Tom Donilon,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March 11,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18)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The White House,"Background Conference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June 4,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4/background-conference-call-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sidents-me.
(19)"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Vice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February 2012",http://www.cfr.org/china/remarks-president-obama-vice-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before-bilateral-meeting-february-2012/p27391.
(20)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21)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
(22)You Ji,"China and North Korea: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0,No.28,August 2001,p.396.
(23)Wang Yong,"China.ASEAN Stress Peace:Summit Agrees on Approach",China Daily,December 17,1997,p.1.
(24)Greg Sheridan,"China wins as 'US neglects region'",The Australian,September 3,2007.
(25)Elizabeth Economy,"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44,August 2005,p.424.
(26)陈岳:“中国当前外交环境及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4页。
(27)Wu Xinbo,"Forging Sino-U.S,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1,No.75,May 2012,p.393.
(28)David F.Gordon,"A trade opportunity Washington shouldn't pass up",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0,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trade-opportunity-washington-shouldnt-pass-up/2011/11/10/gIQA1K3t9M_story.html?sub=AR.
(29)Editorial,"Hillary reinforces US-China mistrust",Global Times,September 4,2012.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30902.shtml.
(30)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page=full%23.TpQwzShztTI.email.
(31)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Panetta,Shangri-La Hotel,Singapore,Saturday,June 02,2012,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
(32)Jane Perlez,"Diplomatic Memo,Political Worries in U.S.and China Color Obama Aide's Beijing Visit",New York Times,July 25,2012,July 25,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7/26/world/asia/china-an-eager-host-to-donilon-diplomatic-memo.html?_r=1&ref=asia.
(33)Philip Bowring,"A Comeback in the Pacific",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3,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09/24/opinion/24iht-edbowring.html?_r=1.
(34)Greg Torode,"How the US ambushed China in its backyard",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ly 25,2010.
(35)Amitav Acharya,"Asia in the New American Moment",PcNet,#49,October 14,2010.
(36)Christopher Freise,"By Invitation,Mostly: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US Security Presence,China,and the South China Sea",RSIS Working Papers,No.247,August 28,2012,http://www.rsis.edu.s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247.pdf.
(37)No author,"Clinton tells Maehara Senkaku subject to Japan-U.S.security pact",Associate Press,September 23,2010,http://www.breitbart.com/article.php?id=D9IDOG4O0.
(38)Zhongqi Pan,"Standing Up to the Challenge:China's Approach to its Maritime Disputes",ISPI Analysis,no.184,June 2013.
(39)Robert A.Manning,"US counterbalancing China,not containing",East Asia Forum,July 9,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7/09/us-counterbalancing-china-not-containing/.
(40)Henry A.Kissinger,"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Not a Necessit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2.
(41)Michael Yahuda,"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1,May 2013,p.446.
(42)S.R.Joey Long,Simon Tay,Kumar Ramakrishna,Carlyle A.Thayer,Zheng Wang,"Round Table:US Re-engagement in Asia",Asian Policy,No.12,July 2011,p.11.
(4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 DC,November 2008,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44)Mark E.Manyin,Stephen Daggett,Ben Dolven,Susan V.Lawrence,Michael F.Martin,Ronald O'Rourke,and BruceVaughn,"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March 28,2013,p.12.
(45)Tim Huxley,"Response to PacNet #35-US 1,China 0," PacNet.#35R,June 12,2012.
(46)Yoichi Kato,"Interview/Kurt Campbell:China should accept U.S.enduring leadership role in Asia",Asahi Shimbun,February 9,2013.术语运用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在探索如何重新聚焦亚洲时的混乱。最初建议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由于被指责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在敏感的中国看来)而被抛弃:随后提出的“转向亚洲”(the Asia pivot)则引起了美国的中东和欧洲盟友的抱怨,因为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本地区被抛弃了。现在白宫倾向于使用“再平衡”(the rebalancing),而一些政策制定者则直截了当地使用“回归亚洲”(return to Asia)的说法。Hannah Allam,"Obama is still searching for right tone in executing 'Asia pivot'",McClatchy Newspapers,January 22,2013,http://www.mcclatchydc.com/2013101122/180696/obama-is-still-searching-for-right.html.
(47)Dean Cheng,"Kerry's First Visit to Asia:Where Is the Pivot?",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sue Brief,no.3902,April 9,2013,http://thf_media.s3.amazonaws.com/2013/pdf/ib3902.pdf.
(48)Shawn Brimley and Ely Ratner,"Smart Shift,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Foreign Affairs,92:1.January/February 2013.
(49)James B.Steinberg,"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
(50)Timothy Garton Ash,"Two ways for West to meet China",The Straits Times,November 20,2009,http://www.straitstimes.com/Review/Others/STIStory_456690.html?sunwMethod=GET.
(51)Satu Limaye,"Beyond choos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East Asia Forum,July 23,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7/23/beyond-choosing-between-china-and-the-us/.
(52)Michael McDevitt,"The Evolving Maritim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East Asia:Implicatio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PacNet,#33,May 31,2012.
(53)Henry A.Kissinger,"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Not a Necessit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2.
(54)Philip Stephens,"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Financial Times,March 1,2012,http://www.ft.com/cms/s/0/50a2c246-6390-11e1-b85b-00144feabdc0.html.
(55)Hugh White,"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East Asia Forum,September 12th,2010,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0/09/12/the-end-of-american-supremacy/.
(56)Li Jingtian,"Building on the Bottom Line",People's Daily,July 1,2013,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3-07/01/content_16694116.htm.
(57)Carlyle A.Thayer,"Why China and the US won't go to war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East Asia Forum,May 13th,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5/13/why-china-and-the-us-wont-go-to-war-over-the-south-china-sea/.
(58)Ben Bland and Geoff Dyer,"US treads fine line over South China Sea",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3,2012,http://www.ft.com/intl/cms/s/0/e13ac9c4-f5e0-11e1-a6c2-00144feabdc0.html#axzz25Q1QJOne.
(59)Gideon Rachman,"A gaffe-prone Japan is a danger to peace in Asia",Financial Times,August 12,2013,http://www.ft.com/intl/cms/s/0/c4d9e34c-033a-11e3-9a46-00144feab7de.html.
(60)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http://news.china.com.cn/txt/2012-07/20/content_25969559_3.htm。
(61)Wang Yusheng,"Is it 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build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Foreign Affairs Journal,No.1,2013,p.102.
(62)Edward Friedman,"Building New Vital Mutual interests for a Better Future:A Rejoinder to Wang Jisi and Kenneth Lieberthal's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1,pp.368-378.
(63)David M.Lampt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Age of Obama:Looking Each Other Straight in the Ey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no.62,November 2009,p.727.
(64)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March 7,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65)Speech by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Welcoming Luncheon Hosted by Friendly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15,2012,http://www.chinausfocus.com/library/government-resources/chinese-resources/remarks/speech-by-vice-president-xi-jinping-at-welcoming-luncheon-hosted-by-friendly-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february-15-2012/.
标签: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奥巴马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天平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