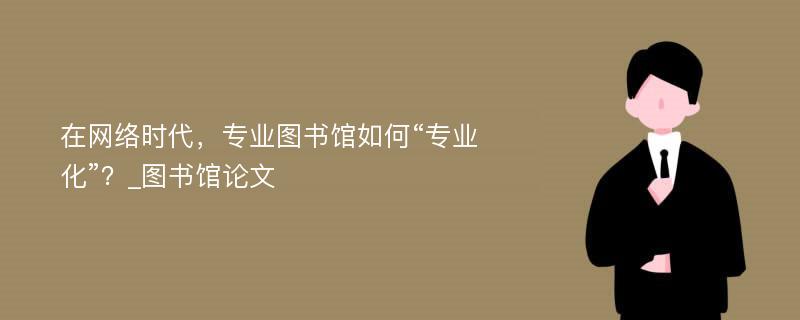
网络时代,专业图书馆如何“专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业论文,网络时代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y)的基本属性一般可概括为专业隶属、专业收藏与专业服务,即隶属于某种专业部门,收藏特定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特定的专业群体。专业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的本质不同就在于通过特定的知识组织来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知识学习、创新与运用的知识自组织过程,也就是“专业”特定范畴的知识保障。
1 “专业”的核心是组织知识
在纸质信息传播时代,专业图书馆的“专业”基本建立在文献单元基础之上。以文献单元典藏知识,以文献单元提供知识。其“专业”程度囿于文献的固态属性和馆藏的封闭状态而难以深化到知识单元,深化到具体的知识创新和运用的思维过程,因而重专业收藏的系统性而轻专业服务的针对性,不能充分体现出专业图书馆的“专业”特色。
无论文献单元还是知识单元,专业化的知识组织首先需要系统性,具备相对完整的专业知识建构,否则就无“专业”可言;专业化的知识组织也同样要强调针对性,即能够保障具体的知识信息需求,否则还是不足为“专业”。系统性是针对性的基础,针对性是系统性的指归:“系统”地满足特定知识需求。作为属性定语,“专业”的蕴涵不仅是馆藏的系统知识范畴,还指定了范畴内针对性的情报职能。
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了知识的数字形态,带来了无限的信息空间,不仅使专业化的知识组织能够突破馆藏的“封闭”而更具系统性,并使其能够突破文献的“固态”而更具针对性——以文献内涵的知识单元切入思维,形成针对思维不确定性的意义集合。因而能够更充分地“专业”。同时网络也带来了空前的信息冗余、信息“污染”和“爆炸”。铺天盖地的无序信息实为灾难,尤其对于知识创新和运用这种知识自组织过程。因而我们又必须充分地“专业”,“专业”地以知识单元的意义集合来保障知识自组织的情报需求。因为无论知识的学习、创新或运用,都包含在完整的信息过程当中,是一系列主客观知识信息交互的思维过程,是知识信息的发生原点,也是知识信息的接受终点,而思维则演绎了这一系列“交互”及选择、判断的知识流程,即所谓“知识自组织”。[1]信息冗余、无序给知识自组织带来的并非“无限空间”,而是信息匮乏和屏蔽,只能阻断知识自组织的进程——思维。因此,网络时代的专业图书馆应当以特定范畴的系统性知识建构为其“专业”基础,并依此而将针对性的知识整合切入到知识的学习、创新和运用的实际思维当中去。“专业”的核心就是为特定群体的知识保障而组织知识。
2 在网络平台上组织知识
专业图书馆在规模上通常为中小型,馆藏十几到数十万册,显然无法包容知识信息的“几何数增长”,即使在专业范畴内。在这样的馆藏基础上整合出来的“意义集合”难免“缺失”、“失时”,既乏“系统”,也难“针对”。其实我们也无须埋着头在自己的“三分地”上“包容”一切,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进入了共建共享知识资源的无限信息空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有限”融入到网络的“无限”,在对网络“无限”的开发与建设中达到“专业”的“系统”和“针对”。
其一,系统的专业知识建设。既然专业,就应当在专业领域具备优势。这种优势要从两个方面形成:从实体到虚拟。实体的文献收藏依然是我们“专业”的基础,即藏书建设。因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形式依然是文献,无论是进一步“虚拟”还是“二、三次”开发都取决于赖以生成的“一次”文献;并且,用户接受知识的主要形式依然是对于纸质文献的阅读、浏览,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中。[2]但是,毕竟已是网络时代,藏书建设无须也无力再片面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而应将策略转向一定知识深度的系统性,即侧重专业知识承传与积淀的经典收藏,代表专业知识的发展源流、体系结构及主要学派,形成专业知识建构的主干,构成专业领域内知识保障的基础。
现在有不少专业馆因为经费不足而舍书保刊,以重“时效”,也就是舍弃“系统”而侧重“针对”。殊不知人类成熟的思考、系统的知识主要承载于图书,而期刊则侧重新观点、新思路、新发现、新结论,是在知识主干上新春吐绿的枝和蔓。在专业的藏书建设及其后续开发中,经典缺藏无疑就割断了该领域人类思想的延续性和知识的完整性。主干支离缺漏,枝蔓还有根基吗?因此,无论是处在网络环境下思考,还是从经费制约计,我们都应当慎重处理书刊矛盾,辩证对待知识的“承传”与“时效”,从而找出两全之策。
书重“经典”,刊重“核心”,或许能够聊以两全。但是要根本上健全系统的专业知识结构并不失知识信息交互的时效要求,就必须积极地投入网络资源的共建共享,将有限的实体资源优势虚拟到网络的无限共享之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才能使我们在更加雄厚的资源基础上更加“系统”,更具“优势”。
其二,针对性的知识保障。完整的情报体系应当包含两个层次:多途径的知识检索和具体的知识提供,也就是针对不确定因素的“意义集合”。
在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中,多途径的知识检索并不只限于在网络搜索中涵盖题名、责任者、分类、主题等传统方式。网络资源丰富多彩,由于各种数据库系统编码结构、数据结构及表达方式不一,不同检索软件的界面风格各异,造成检索策略、方式的复杂多样,用户往往无所适从,因而需要“知识导航”。专业图书馆知识整合的一项新内容就是建立基本统一的公共检索界面,以及一体的一、二次文献数据库链接。使用户能够方便地由界面而深入相关网站数据库,由检索途径而达于原文,如此才能将自己的专业功能扩展到无限的资源领域。如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中心门户将国内外各种类型、制式的信息源、数据库及有关检索途径整合在“网络数据库”、“网络电子期刊”、“资源集成检索”、“科技资源报道”及“科技在线”五个界面之下,不同内容、层次的情报检索一目了然。以“资源集成检索”为例,读者只要键入检索词,就可以在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重要图书馆进行从“全文数据库资源”、“文摘、索引数据库资源”及“OPAC库资源”不同层次的跨库链接,能动地实现情报资料的查全与查准。[3]
所谓“意义集合”就是针对问题的知识组合,是更深层地切入思维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与传统的文献定题服务一脉相承。网络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知识信息数字化平台及虚拟咨询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快捷方式,使“意义集合”的组织和服务有了充分的知识贮备和物质条件。专业图书馆应当设立专门的参考咨询部门,其职能主要是承接专题数据库建立业务以及情报跟踪服务,并“链接”有关专家为咨询馆员开展情报分析。再以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为例,其主页界面下“我的数字图书馆”其实是个性化集成定制、用户驱动的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虚拟资源集合的个性化定制功能,其目标就是根据用户的学科、偏好等特征,通过用户定制、系统推荐和推送功能,为用户提供针对性的知识信息。门户中还附设“分布式参考咨询系统”:以前沿领域的科学家和资深咨询馆员为情报专家,通过开发和利用学科知识、馆藏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实现网上专题文献提供和知识咨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的知识需要为本的“专业”精神。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专业馆来说,网络平台似乎可望而不可及。数据资源虽多,奈何“囊中羞涩”,而内在问题还是小生产作派,对共建共享缺乏兴趣或积极性。正因为我们弱小,我们才更须联合!找准自己的优势所在,在共建中发展自己,在共享中强大自己,这是无可选择的“专业”之路。
3 走出隶属的藩篱
事实上,专业图书馆在“专业”过程中不仅受制于经费,还存在行政隶属的条块限制。这种条块限制不仅限制了部门内部知识组织与知识自组织之间的内隐链接,更限制了跨部门的知识共建与共享。
“内隐链接”是一种知识管理理念,即通过组织中的人际交流来实现每个成员内隐知识的共享,使每一个体的优势都朝着总体目标的方向发展,形成组织的整体知识结构。然而我们的隶属体制中正缺乏这种情报人员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机制,彼此“行政独立”,何谈内隐知识链接?更何谈“优势互补”、“切入思维”?一般而言,研究人员只具备“主观”上的专业知识优势,并不一定具备“客观”的专业知识组织,即文献情报人员所擅长的显知识组织优势,尤其网上情报检索与整合技能普遍缺乏。所以,研究人员与文献情报人员之间的优势互补实际上是借用后者的知识组织优势为其知识保障的“外脑”,推进其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交互,真正以知识组织来促进知识的自组织。因此,在行政隶属体制中,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一种促进组织内部“内隐链接”的交流机制:即情报人员必须了解专业的近期、中期和长远发展规划,从而合理地、及时地、乃至预先地配置文献情报资料;必须与专业人员加强接触,参与他们的课题论证、研究讨论、成果评估及理论实践等活动,以了解他们之所需、所急,在知识保障方面为其排忧解难。在一个专业的科学组织中,至少应具备这样一种最基本的“知识地图”[4]:Know-who谁需要知识?Know-what需要什么知识?以及Know-where那里有知识?
门庭冷落,这是时下专业图书馆的普遍境遇。究其根源,与“行政隶属”造成的自我封闭、自我孤立,以至自我限制也不无关系。知识是不应该附着于行政体制而“隶属”的。在网络环境面前,“进一步”才是海阔天空。以上所举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范例,其成功也并非全在于财大气粗,事实上它也是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上海、成都、武汉及资源环境科学四个分中心以及系统内120余个研究院、所和大学文献情报机构共建共享的一个数字化“联合服务系统”。系统下设“联合编目服务系统”、“馆际互借管理系统”、“读者网上服务系统”和“联合采购服务系统”四个子系统,是典型的共建共享模式。各成员馆在系统的共建过程中是自身优势的进一步强化;而用户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才真正感受到“畅游知识海洋”。
所幸的是这些成员馆都隶属于一个行政体系——中国科学院。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就有所不幸了,因为它们并非“隶属”于像中国科学院系统这样便于统辖的条状行政,而是各有所属、块状并列的“兄弟”关系。虽然大多数地方社科院图书馆的经费都捉襟见肘,极需联合,奈何身不由己。为何即使共同的利益驱动也总不如行政统辖奏效?值得我们反思。如果各主管部门都能将所隶属的专业图书馆作为自主的知识实体来建设,在管理上只着重于按照部门的总体目标来制定发展规划,提出服务要求并投入相应经费,规范其知识保障的范畴、层次及方式,而在权限上则根据知识组织的过程需要,尤其是超出隶属的“共建共享”,给予图书馆作为一个知识实体应有的运作空间,促使其在部门利益最大化原则之下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发展。这无疑也是将本部门的知识保障范围扩展到了社会化。网络的本质特征就是开放。要享受开放的环境,自己也须向环境开放。开放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
大势所趋,在共建共享的网络环境中整合知识、定制服务已成为专业图书馆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只有打破文献的“固态”与“封闭”,跨越隶属的“条条与块块”,专业图书馆才能在网络环境中名副其实地“专业”起来。
收稿日期:2004-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