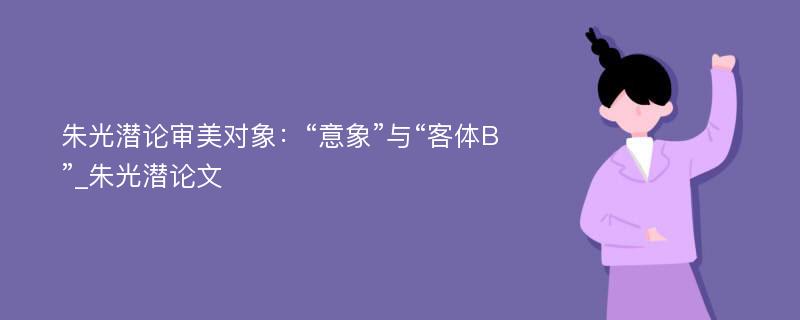
朱光潜论审美对象:“意象”与“物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对象论文,朱光潜论文,物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84-09)
作为审美对象的意象
通观朱光潜先生50年代前后的著述,其美学思想面貌变化之巨与其基本观点的持续之久,同样令人惊讶。他对自己作过痛切的批判,否弃过许多;但他却始终珍爱着并以非凡的勇气与毅力坚持着一个基本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
支撑这一主张的理论骨骼,是对审美对象的分析。审美对象,朱先生称“美感对象”,在前期,被名之为“意象”;在后期被名之为“物的形象”,或“物乙”。而不论“意象”或“物乙”,朱先生都确认它是客观事物的某些属性与主体审美能力“霎时契合”的成果,它完整自足,是审美者独到的发现和创造。这个审美对象,便是美感的源泉。
在前期著作中,朱先生“意象”一语,涵义极其丰赡。意象,又称形象、形相,既意指西语image、Idea的有关义项,又与中国传统美学“意象”一语的指谓相衔接。朱先生多向度、多层面地描述审美的意象,虽未就此作出严密的理论分析,却揭出了它最基本的美学意义:审美对象。
意象,首先被设定为美感的起点,所谓“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1]持有审美态度(朱先生称“美感态度”)的主体与客体事物猝然相遇,主体心中突然涌现浑整自足的意象,它脱净日常功利和名理思考,孤立绝缘,却给审美者以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意象,又被设定为美感全程的统摄因素:“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的世界”。[2]美感以意象为起点,也以意象为终端。在朱先生那里,美感是意象展开、延伸的过程。经由直觉(主要是想象),突然涌现的意象因不断融入主体情趣而倏忽变相,成为理想化的意象。所以,朱先生有时又说,美感经验即是“形象的直觉”。[3]
意象,更是艺术的心理本体,“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的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4]艺术,是对现实人生的返照,也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它超越着日常繁复错杂的实用世界,进入的是理想化的人生境界。
这样,意象便被视作审美态度的对象,全部美感的对象,和艺术家所创造的具有超越性质的又一审美对象。而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审美对象都是美的依托。朱先生从不曾明确表示过,审美对象即是广义的美,但他反复强调意象情趣化与情趣意象化两者恰到好处时呈现的价值,便是美。[5]由此他引出自己主客观统一的美论:“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6]心物婚媾,产生意象,意象即是审美对象,即是审美价值的承担者。所以,朱先生早期论述实际上包含一个等式:审美意象=审美对象=广义的美。
这个等式所从何来呢?应该说首先得自康德。朱先生晚年表白过:“大家都知道,我过去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信徒,可能还不知道对康德的信仰坚定了我对克罗齐的信仰。”[7]这番话说得很坦诚。因为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人们熟知朱先生早年曾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基础,融入“移情”说、“距离”说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所引进的“三说”后边,还有一位大后台——康德,即使他的批判者,也没有注意这个秘密。其实,朱先生用以统摄“三说”、融贯“三说”的法宝,恰是康德有关审美观照的理论:“无所为而为的观照”(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又译“超功利的观照”)。在康德那里,审美意象是审美观照的对应物,观照始终是对于意象的观照,意象也始终是观照中的意象。康德的审美意象有两义:一是“合目的性的审美表象”,当表象经由想象力(或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和谐活动)直接联系于主体的快感不快感,而不经由逻辑思考联系于对象本身时,这个审美表象体现的便是自由美;二是在艺术创作中凭着“天才”创造的、作为“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型”的意象(Idea),它既是形象的显现,又与某种不确定的理性观念相对应,体现的是依存美——“道德的象征”。而不论哪一类意象,它都以表象为起点,都有非功利、非概念的性质,既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照”的对象、凭借,又是它的成果。康德对两类意象的分析,实即对于审美对象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进而确定了作为静观的审美活动的特征。这一理论,深刻影响着西方美学,迄今仍在西方美学界激起回响。
朱先生引进的“三说”,原本都由康德“观照”说所衍申。“距离”说,以自觉的审美态度为观照提供心理前提,使审美者有可能将对象的表象从实体抽离,使之超拔于实用、认知关系,涌现审美意象;“直觉”说,论证了对象的形式(表象)与主体的情感两元“审美的先验综合”,恰如朱先生所言,“与其说近于黑格尔,毋宁说是更近于康德”;[8]“移情说”,与康德的“生气灌注”[9]论也有斩不断的瓜葛,它揭开了情趣意象化(客观化)和意象情趣化的若干秘密,将西方近代美学关于形式与情感关系的论述从经验心理学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显然,朱先生所引进的“三说”,本身便是对康德观照论的新拓展。
诚然,早期朱光潜的审美对象论是不成熟的。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并不严整,他时而承认意象与外物“美的可能性”有关,时而抹煞这一点,过分夸大主观心灵的创造作用,他在唯心的心物一元论与心物二元论之间,动摇着、游移着;这个理论的表述,也是描述胜于论证,缺少概念的严谨厘析和必要的逻辑推论。但是,他对审美意象的重视和对康德美学的深刻理解,却保证了他对西方近代美学新成果成功地作出批判性综合,截长补短,互为融通,表现出宽广的视野和卓越的识力。而这,也为他日后提出“物乙”论——确切意义的审美对象论,作了准备。
针对那种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原则机械引入审美的简单化美学观,朱先生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提出了“物甲”、“物乙”的假说。[10]“物甲”即物本身,它提供“美的条件”;“物乙”是“物的形象”(或艺术形象),它是美感的对象,是主客体的统一体,唯有它才能提供美。朱先生将“物甲”、“物乙”、美感归结为审美之链的三个主要环节:物甲是感觉的根据,艺术的素材,它是可知的,已不同于康德的“物自体”;物乙是客体事物的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意识形态,两者交融而创造的完整形象;美感则是主客交融创造“物乙”时所体验的快感,它既受动,又主动,是欣赏与创造逐渐深化与丰富化的过程。在两者之中,“物的形象”最为重要,它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应该被视为美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如果我们注意到“物的形象”实际只是“意象”的不同提法,那么,我们便可判断,照朱先生,物之所以美,美感之所以被引发,其秘密正深藏于作为审美对象的“物乙”里。这个对象“就是‘美’这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对象”,它就是广义的美;这个对象又即是美感的对象,全部美感的诞生地。审美对象处于居间地位,它一头肩起客体美的条件,另一头肩起主体的美感,充当着整个审美的重要中介。朱先生倾其毕生精力,捉住这个中介,坚持以主客体统一的哲学观点对它作哲学—心理学的解说,即便在他本人已成为“箭垛”的情形下,依然未改初衷。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到60年代,朱先生自觉转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上来之后,他理论兴趣所在,仍是这个“物甲”如何转化为“物乙”的问题。从审美对象这个中介出发,他的研究,呈双向展开:向着美的本体,他偏重以哲学方法去追究审美对象的根源,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根源之地求解本体;向着美感,他偏重以心理学方法讨论审美对象与主体审美能力的对应关系,中心论题是形式(意象)与情感在美感经验中如何结合。
在美论方面,他原先只求广义的美,强调审美对象的形式取决于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实为主体审美能力的作用),现在则力求从物质感性的历史性实践中去寻求“物甲”转化为“物乙”,即形成审美对象的条件与根源。他试图突破康德静观式的审美观照论,转向审美本体论,从审美对象的探讨追踪到产品之美的探讨。他提出“文艺是一种生产劳动”的观点,正是为了揭示艺术美的最终根源。然而,朱先生在美论方面的创获相当有限。他还不了解物质实践的客观社会性,常将实践中主体的作用和意识作用混为一谈,他也还不了解从产品之美到艺术美之间,还有一系列过渡性、转换性环节需要探明,需要诉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发生学。
审美观照论和审美本体论应该属于不同理论层次。前者回答什么是审美对象,什么是广义的美的问题,后者则需回答美的本体是什么,即“物甲”所提供的“美的条件”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美的本体,必须从人类物质实践的这个根源之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身,去探讨“物甲”所具备的审美属性。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朱先生的全部著作中尚未能正面触及。在当代西方美学中,这个问题尽管遭到美学取消论、怀疑论者的抹煞或掩盖,但只要承认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而且承认客观物是构成审美对象的前提,这个问题就实际上存在着。西方当代流行的现象学美学,尤其是杜夫莱纳的美学,同朱光潜美学,多有共同之处。杜夫莱纳以为,美即是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必须伴随审美态度而呈现,只在审美经验产生的同时才形成,这些看法,正是当年朱先生意象论与“物乙”论的题中已有之义。然而,杜夫莱纳也如朱先生曾留下物甲“美的条件”这个难题那样,留上了“可能的审美对象”是什么的难题:
是否说博物馆的最后一位参观者走出之后大门一关,画就不再存在了呢?不是。它的存在并没有被感知。这在任何对象都是如此。我们只能说:那时它再也不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只作为东西而存在。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作为作品,就是说仅仅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11]
博物馆闭馆期间,陈列着的画幅显然不同于其他日用的东西,它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必有潜在的审美属性,这些属性是什么,如何形成,显然不能漠视。
审美本体论在今日中国美学领域,有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学界对此实际上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审美对象即是美,或说美即是审美对象的情感价值,这实际上是回到朱光潜早年的看法,或者实际上持杜夫莱纳的观点。另一些同志主张,审美对象只是美的现象形态和经验形态,只能说明美的事物何以为美,并不能说明美的本质、美的本体是什么。美应该是客体的审美属性,但并非客体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成果。
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存在,既是50-60年代国内美学论辩的遗响,也是世界范围类似美学争论的回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美学在未来世纪的走向,关系甚大,而这一探讨,显然又牵涉到对朱先生审美对象论以至整个50-60年代的美学论辩的历史评价,无疑应在历史的反思中妥为解决。
朱先生60年代的美论用力甚多而创获不显,但在美感领域,却从他的审美对象论出发,深入探讨过美感中形式与情感的结合何以可能,美感论应如何综合西方近代美学的“意欲派”和“形式派”的既有成果,认知心理和动力心理在美感上如何沟通等重要问题。这方面朱先生虽只发表过一篇专论,却如灵光一闪,提出了深刻而又极富启发性的见解。
在《美感问题》(1962)这篇重要论文里,[12]朱先生以自觉理论形态提出了审美心理结构的课题,这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一课题的提出,对朱先生而言,恰是此前对审美对象长期考察的理论延伸。照朱先生,审美对象(意象)是物的某种属性与主体审美能力霎时契合所呈现,对审美能力的研究,必然要追究主体审美的心理结构,因为审美能力不是别的,正是这一心理结构动作的结果。朱先生曾就此提出过四大问题:
(一)有没有审美的能力或是一种决定人爱好什么和不爱好什么的总的心理结构或心理倾向?假如有,它是怎样形成的?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二)假如有一种总的心理结构或倾向,它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应不应考虑到生理方面的动物性的情欲和本能?应不应考虑到社会实践对本能或情欲所造成的改变?
(三)这种审美的能力或总的心理结构在具体场合是怎样起作用的?它完全是感性活动呢?还是也包含理性活动呢?……在审美活动中,意识占什么地位?是否有下意识的作用存在?如果有下意识的作用,它是怎样起的?
(四)究竟是对象的哪一种或哪些性质会引起审美的情感?是否对象原已有“美”的这种属性?如果有,它究竟如何界定?
这四大问题,分别涉及美感深层动力心理(审美需要、本能情欲、下意识)、表层感知和对象的美三个环节,涉及审美心理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这三个需要探讨的层面。朱先生强调,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运用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加以研究。这便为我国今日美学,提出了需要长期致力才能解决的重要课题。
正因为审美对象是审美的中介,所以朱先生提倡由此出发探讨对象的美,也由此出发探讨与之相应的主体心理结构,将两者视为彼此对应平行的课题。在方法上,也就沟通了哲学思辨和心理学描述,从而避开了西方近代美学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长期论争的困扰。朱先生的所有美学论著,谈美绝少有玄学气,谈美感又不乏理论深度,他的美学始终和人们活泼泼的审美实践声息相通,在研究方法上,也足以启人心智。
中国化的审美对象论
朱先生的美学,早就赢得“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美誉,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他的理论凭借尽出于西方,只不过多以中国艺术史料充实论证而已。这个印象其实是不确的。笔者数年前即曾提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就是朱先生择取西方美学从事理论创造的“内在参照系”。[13]现就审美对象问题,再予申说。
确定“意象”为审美对象这件事本身,就凸现着传统艺术精神。出自26岁的青年朱光潜之手的《无言之美》,预示了这一点。朱先生这篇讨论艺术含蓄之美的美学处女作,其理论涵量却远远超出于含蓄之美的自身范围。请看他对文学的描述性规定: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按指“美的艺术”——引者)。在文学作品中,言语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14]
这里为文学作品列出了“意象”、“语言”、“情意”三个要件,意象是语言传达的对象,意象和语言又蕴涵着情意,语言所传达的意象,正是引起美感的对象。在“言、象、意”相互关系的理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尚象”思维,居间地位的意象,及其作为审美对象的功能,不都呼之欲出了吗?
如同传统“尚象”思维理论那样,朱先生之推重意象,也建立在对语言功能的批判性考察基础之上。“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15]朱先生援引道家对言意关系的著名论断来立论,实际上也倾向于道家借重“象”以体道的直观感悟思维方式。更值得重视的,是朱先生断言艺术之所以美,就因为它能借助想象为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境界。这里埋伏着日后朱先生对艺术作为审美对象的理解,也完全符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很显然,在朱先生出国系统研习西方美学之前,他自己的美学观点已粗具雏形,而这,主要又是传统艺术精神浸染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在朱先生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些基本观点的持续一贯,同时也是传统艺术精神的持续一贯。
朱先生曾表示,他的美学思想“与其说近于移情说,无宁说更近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关于‘理象’(诸本原文均如此,疑为‘意象’之误)和‘意境’的说法。”[16]这也确是实情。
参照西方美学体系,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意象,可以视为审美对象。传统美学一向将“物象”与“意象”作出严格区别:物象是事物的外在状貌,意象则产生在审美者“观物取象”或“比物取象”的过程中。这个“观”与“比”,是在特定的审美态度即“虚静”态度之下进行的,它们不是单纯的观看或比附,而是在心物交互感应中主体创造性的心理成果。用郭熙的话来说,审美意象是以“林泉之心”饱游饫看之所得,它不同于地理版图的山水,也不同于作为物质实体的山水,而是意态纷呈,生机流荡又充满情意的“真山水”(《林泉高致》)。一句话,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与“心源”相统一的结果。
因此,对主体情意而言,审美意象就有了表现功能,所谓“立象而尽意”。中国传统美学关于意象,有诗骚两大类型之分,诗体传统着眼于感物动情,着眼于外物之象对人心的感发,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在物我双向交流中构成的意象,大抵属于知觉性意象;骚体传统着眼于“发愤抒情”、“舒愤懑”,它凸出主体在审美时的内驱力,一种压抑既久而又无计排遣的郁结,在当下的审美情境中找不到合宜的同构形式,于是转而从想象性意象求得释放和宣泄。审美者在情境触发下,心游神越,进入想象中的理想境界。这一由庄子首倡的“逍遥”之境,便是中国意境说的源头。意境说强调“境生于象外”,这个象外之境,说到底是想象性意象,不过更以其超越性、理想性见胜罢了。大约自魏晋以降,诗骚合流,体现在美学上也是“感物动情”与“发愤抒情”交相融合,意境之有无高下,于是成为中国评诗衡文的重要标尺。
朱先生早年的意象论,完全吸取了上述美学成果,并以此对西方美学作了必要的修正。如“移情”说,按立普斯的说法,本意是:主体以审美态度观看对象,由于设身处地的“同情作用”,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之由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进而将这一情感当作属于对象的东西加以欣赏。这样,主体所欣赏的,实为“人格化的自我”。所以沃尔林格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审美享受是客观化了的自我享受。”[17]然而,朱先生却毅然将移情说改创为“物我同一中的物我交感”,“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交流而已。”[18]
朱先生对“移情”说的修正有一个前提,即确认心与物在“生气”、“情趣”方面有“互相感通之点”,有“心灵交通的可能”。[19]正是这个理论前提,显示着中国以“气”论为基础的传统生机哲学的根本之点:承认宇宙万物都有生命元气在普运周流,心物之间可以相互感应。由此而演成东方式的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与造化为友”,追求两者的相契相安。这与立普斯“移情”说的哲学基础大异其趣。立普斯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康德、黑格尔美学关于心灵向对象“灌注生气”的原则。按照西方式的主客两分模式,客体始终是主体认知、改造的对象,它永远处在被动地位、从属地位,只是为心灵的生气提供一个投射的容器。应当说,这承续了西方强调人与自然分立与对峙的文化观念的余绪。由于对移情现象的心物关系持不同理解,中西两方对审美意象中形式与情感的关系看法也迥然有别。照立普斯,移情所呈现的“空间意象”是外物在联想作用下心灵化、人格化的结果,而照中国传统美学,意象则是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产物。
深刻的哲学分歧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还带来意象心理构成的不同解释。西方美学重视感知与情感的分剖,有关审美意象的构成,出现过“形式”派与“意欲”派两种对立观点。前者强调形式,强调感知与表象,凸出主体的知觉完形(Gestalt)作用;后者则强调意欲,强调情感,凸出深层心理驱力尤其是潜意识的动力作用,进而凸出内心体验以至神秘体验。中国传统美学不然。我国传统的意象理论,感知与情感,形而下的经验和形而上的体验虽有分剖又有联结与过渡,审美的认知心理的动力心理时时融贯。由于认知与情感都基于气的感应,由认知转换为内心体验,由认知判断转换为情感价值判断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的。外在感知和表象,诉之于“反观内视”,便进入内心体验,并且常常是超越性的人生体验。“体认”——基于经验直观上升为感悟,使主体从一般内心体验(情感)进入理想境界(意境)而体验人生的价值与真义。朱先生的早年著作,尤其《谈美》与《诗论》,反复发挥的“宇宙人情化”、“人生艺术化”的主张,实即建基于中国文化重经验、尚感悟、趋向反省内求的传统之上。
“宇宙人情化”和“人生艺术化”的主张,又引发出对审美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审美与艺术都超越于现实人生、现实人格,又毕竟是现实人生、现实人格的返照。它的功能主要不在实用,不在科学认知,不在道德教训,而在于人格的陶铸与修养。“颐情养性”,造就健全、高尚的人格,据朱先生看,便是审美与艺术的“无用之用”,功在千秋的“大用”。它包含着实用、认知和道德的功用,而又超越了这三方面的各自功用。朱先生重视人格的知性、伦理、情感诸素质的完整统一,痛心于俗人对“精神残废”的麻木不仁,为审美教育而大声疾呼。他的大量著述,实是旨趣高雅、文情并茂的审美教育优秀教材。朱先生之所以看重审美的“颐情养性”作用,可以说主要得益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参天地,赞化育,是全部文化的载荷者,是始终被关注的中心。和西方基督教社会将人格理想委之圣父、圣子、圣灵不同,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更多的是借助审美和艺术,予以高扬,予以实现的。朱先生的审美教育主张,深得此中精髓。
中国文化有一个开放的、极富涵摄力的总体模式。它通过“尚象”的直观感悟思维方式,将西方文化中历来被截然两分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而下与形而上、现象与本体在两分的前提下沟通起来,统一起来。这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个模式以最为灵活的辩证方式,综合着历史上的各家学说,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由这一文化模式衍申出来的传统美学,也秉有其固有的开放性和涵摄力。正因为如此,当朱先生以固有文化传统为参照,择别和引进西方美学时,他采取“批判性综合”的立场是一点不用奇怪的。朱先生在意象论方面中西参照,用中国传统的意象概念融会西方各执一端的二元论美学观,又用西方近代美学观来诠释中国传统的浑整描述的意象论,这一成功尝试,又一次证实了传统美学的这种开放性和涵摄力。
请莫以为中西参照是轻而易举的。若求参照成为名副其实的参照而不流于拼凑和比附,非但要有深厚的学养和高明的识力,而且要倾注大量心血。这一点,从朱先生的著述本身皎然可睹。中西美学的交融是一项巨大历史性工程,朱先生已经做的,只是这一工程最初的开掘工作。他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作过中西参证,有互补,有发挥,但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人们去继续探讨。处在世纪之交的我们,面对21世纪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交流,通过融会中西而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使命,更紧迫地压向我们双肩。此时此际,我们也当更为珍视朱先生和其他美学前辈为我们启导的良好开端。
朱先生垂范在前,后继者理当努力。
收稿日期:1996-11-20
本文曾提交1994年12月北京大学主办的“朱光潜美学研讨会”,1996年11月改定。
注释:
[1]《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卷1,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2]《谈美》,《朱光潜全集》卷2,第6页。
[3]《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卷1,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4]《谈文学》,《朱光潜全集》卷4,第161页。
[5]这一问题,朱先生早期提法两歧。他有时据克罗齐立说,将美说成是“表现”,说成是“心灵的创造”;有时又称美是心物交融为意象所显示的“特质”(如称“美是艺术的‘特质’”),实即审美价值。
[6]《谈美》,《朱光潜全集》卷2,第44页。
[7]《谈美书简》,《朱光潜全集》卷5,第246页。
[8]《美学批判论文集》,《朱光潜全集》卷5,第15页。
[9]康德将“灌注生气的原则”,视为“显现审美意象(aestheticideas)的能力”。见其《判断力批判》49节。引文为蒋孔阳译,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增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63页。
[10]《美学批判论文集》,《朱光潜全集》卷5,第51-96页。
[11]杜夫莱纳:《美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12]《朱光潜全集》卷10,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4-364页。
[13]拙作:《“补苴罅漏,张皇幽渺”——重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
[14]《朱光潜全集》卷1,第62页(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5]《朱光潜全集》卷1,第62页(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6]《美学批判论文集》,《朱光潜全集》卷5,第121页。
[17]沃尔林格:《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18]《谈美》,《朱光潜全集》卷2,第22页。
[19]《谈美》,《朱光潜全集》卷2,第21页。
标签:朱光潜论文; 美学论文; 康德论文; 谈美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朱光潜全集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家论文;
